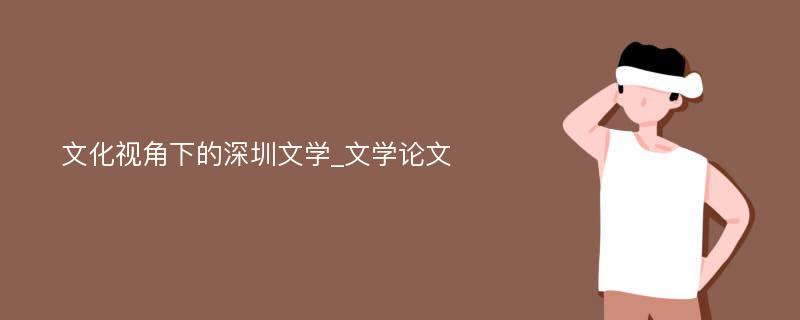
文化视角中的深圳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圳论文,视角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评估深圳十五年来的文学创作并预测其发展走向,是深圳文艺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拟从文化研究的视角作大略的探讨。
一、文化转型:深圳文学的人文背景
作为我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深圳,实质上就是最早进行社会与文化转型的地方。对深圳所处的人文背景和“文化转型”的基本因素,可表述为:窗口式的地理环境,移民式的人口结构,混合型的经济结构,过渡期的社会结构。因这些因素,深圳成为中国文化转型最活跃的一个地带,具有地缘和人缘两方面的优势。先从地缘优势来看,评论家余秋雨把深圳放在当代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中来考察,认为“当代世界为儒家文化、基督文化、伊斯兰文化三大文化板块相互冲撞所困扰,而深圳却是一个难得的文化缓冲、文化和解之地,是一块三大文化板块都为之留出了一定空间的‘三角地’,其文化环境疏松、可塑性很强。这种时空背景适合于以开放、探索、创新为特征的青春型文化生长。”(《深圳特区报》1994年11月25日)此说颇有见地。深圳作为连接内陆与香港的边缘地带,由于远离中原,既不象内陆地区那样有博大、深厚的儒家文化的积淀,亦不象香港那样长期承受西方文化的渗透。这种既不同于内陆又区别于香港的“松软地带”,便为新质文化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从全国文化格局来看,由于深圳最早踏入工业文明的门槛,最先进入文化转型的实践(试验),使特区文学创作具有特殊的意义。应该说明的是,这种意义不在于它的地域性,也不仅仅是一种题材优势,重要的是它的现代性。“深圳的今天,是内地的明天”,深圳的文化转型是伴随着社会转型而进行的,也就是从传统型文化向现代型文化的跨越。这种“现代型文化”包括它所反映出来的新文学观念、新的审美方式,也包括它所表现的现代生活方式、现代新型人格等。这些富有时代色彩的东西是植根于深圳这一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之中的。在这独特的人文背景中,将会创造出一套新的文化语境——这就是特区文学的价值所在。
再从人缘优势来看,深圳是个各地移民共处、多种语言混杂、新风旧俗渗透交叉的城市,当代改革飓风刮来的知识分子和民工南下潮,使深圳成为“藏龙卧虎之地”,一批崭新的、朝气蓬勃的作家正随着特区的繁荣而渐渐崛起,有自己独特的构成特色。这里有土生土长的本土作家,他们凭借对故土的挚爱和对文学追求的执着,勤奋耕耘,各有成就,当之无愧地跻身深圳文坛,引起了文学界的注目。
诚如深圳的人口结构是以移民为主,深圳移民作家也是这里文学队伍的主体。
大批外来作家带着中原塞外、西北江南的各种文化,投入深圳特区文化的熔炉当中,萌生着具有开放、探索、创新的文化品格,表现出深圳文学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文化转型给深圳作家们展现了一个社会变革异彩纷呈的崭新世界,呼唤深圳作家在这广阔天地里大显身手!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深圳特区,也向它的文学提出了一个历史的使命——为推动全国的文化转型作出自己的努力,这就是深圳文学所处的人文背景。
二、新的人文精神:深圳文学体现的文化观念
进入市场经济后,文学的审美取向和批评标准是否应该有所改变,是否要面对新的生活新的制度产生新的审美取向?笔者认为,探讨文学发展应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来观照。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每一代的美都是而且也应该是为那一代而存在……当美与那一代一同消逝的时候,再下一代就将会有它自己的美,新的美,谁也不会抱怨的。(《生活与美学》)所以,从深圳的创作实践来看,建立一种与新文明相适应的人文精神是需要的。
综观深圳文学十五年的创作实践,能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并引起“轰动效应”的,我认为大致有三次。而这三次“轰动效应”的冲击波,恰恰是来自深圳作家对新的人文精神的张扬!
第一次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刘学强有关特区青年更新观念的纪实体散文,着力弘扬“敢为天下先”、“应做就去做”、“无功就是过”等新观念,显示出开放之初特区生机勃勃的时代风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读此类作品,宛如读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是处在文化转型期的深圳作家心灵的呼唤,在内地引起不小的反响。《中国青年报》为此特辟专栏,组织全国青年开展对“深圳新观念”的讨论。内地许多热血青年,就是读了刘学强这类“新观念”的文章(后结集为《红尘新潮》,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而毅然南下投奔深圳的。尽管评论界对《红尘新潮》没有给予关注,尽管作家本人也在尔后从事小说、影视等多种题材创作并颇有收获,但我坚持认为,从文化视角看,或从深圳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刘学强迄今为止最大的贡献,仍是他那本薄薄的《红尘新潮》。
第二次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正当内地“寻根小说”蔚为大观之际,刘西鸿的短篇小说《你不可改变我》,以文化观念上的陌生感与超前性,引起了文坛的惊讶与亢奋。作家把希望的目光投注到经商品经济洗礼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身上。主人公在特区较为平等、自由选择的天地中,以“人不可改变我”的自信,去追求独立的个性意识。作品以新颖的叙述语言,“一种毫无牵挂的洒脱、一种积极进取的理想主义引起了关注,揭示了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在崛起,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在整合、构筑。这种新的人文精神与新的人际关系,使人再不把自己当作仅是政治、历史、文化的动物,而同时也关注自己的实践利益,讲求礼俗、宽容,而不太关心形而上的精神痛苦与折磨”,“崇尚一种创造性的美,而不仅仅以自然为美”(钟晓毅)。如果说,“寻根文学”体现了丰厚的民族文化传统,表达了人的某种深层的寻根愿望和怀旧情绪,那么,《你不可改变我》则是在雕刻着未来的民族灵魂。作品发现并写出一种“及时发光”的价值观、以及“不可改变”的变化着的个性,预示着整个中国的文化变革正是孕育在每一个个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嬗变与骚动之中,体现了刘西鸿对特区生活敏锐的感知力。作品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并拍成电影《太阳雨》,在省内外掀起一股“刘西鸿”热。
第三次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北方兴起“新写实”、“新历史”小说,王朔的“新市井”文学亦风靡一时,而在百万打工者汇集的深圳,却出现了“打工文学”这一奇特的文学现象。以张伟明的小说《下一站》、《我是打工仔》和安子的长篇纪实文学《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为代表,前者写出打工一族“东家不打打西家,勇敢走向下一站”的“潇洒”,张扬一种开拓、冒险、自强自尊的“打工精神”,后者则着力表现打工妹在充满机遇的深圳找到自我价值时的喜悦,呼唤“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两者都以主人翁亲身体验为背景,通过“文学”去展示“打工”的社会实践,唤起人们对打工生活的关注与再认识,不仅道出打工者的心声,张扬一种人文精神,同时还成为一个信息的窗口幅射到内地,从而在读者中形成热点。正如1992年7月29日《文汇报》发表《“打工文学”异军突起》一文中指出:“它以短、平、快的节奏冲入中国文坛掀起一股旋风。”
深圳十五年来掀起的三次文学冲击波,都是由三十岁以下年纪的青年作家发起的,亦均是以新的人文精神作为内驱力,在读者中形成一股旋风。不能否认,这些作品水平参差,有的还存在“思想大于形象”的不足。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些作品以新的审美取向,将艺术触角直逼文化转型期的社会心态,不单引起文坛关注,同时也拥有广泛读者,它昭示着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圳文学的文化走向,对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是一次挑战。如何看待这种文化现象,是摆在许多作家和研究者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
三、文学景观:从“打工文学”到“新都市文学”及其他
深圳作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专业作家,二是“打工文学”作者,三是报刊编辑。这些作家由于各自的人生经历和审美情趣的差异,使其创作异彩纷呈,构成了深圳文学队伍的主体,他们辛勤的劳作,描绘了特区绚丽多姿的文学景观。
景观之一:“打工者”构筑“新都市”
深圳,是当今中国外来劳务工聚集最多的一个地区,“打工”是当今深圳使用频率最高的词。
深圳打工文学的代表作家是张伟明、林坚和安子。林坚的《别人的城市》和张伟明的《下一站》,两篇小说及其题目被广东评论家称之为“有形而上的文化寓言的意味”,在广大打工一族中引起强烈共鸣,迄今已成为深圳的“经典说法”。张伟明、林坚的小说着意刻画打工者趋向现代文明的艰难过程,敢于直面人生,表现出一种“沉重的潇洒”。而安子的作品则以“微笑看世界”的视角,试图给打工生活涂上一层理想色彩,因而满足了众多打工者“寻梦”的审美需求。
1994年初,《特区文学》举起了“新都市文学”的旗帜。旨在从现代文化的角度,反映“新都市”及“新都市人”的心态、情感、生活方式及文化观念,揭示特区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文化冲突,塑造一批正在成长的“新都市人”的形象,从而促进中国“新质”文化的产生。可以说,在特区倡导“新都市文学”颇有意义,实则是社会、文化转型对深圳文学提出更新观念的要求。
“打工文学”与“新都市文学”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要展示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吸引,都要写出文化转型期的“都市人”(含“都市边缘人”)的生态与心态。可以说,是“打工者”在构筑“新都市”,亦是“新都市”在洗礼“打工者”。“打工文学”是“新都市文学”的初级阶段。大量的“打工文学”都写都市,但是否达到“新都市文学”的文化内涵,关键问题在于是否具有“都市意识”,是否具有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新的人文精神。比如,林坚与张伟明两人都在写都市。林坚的《别人的城市》,塑造了齐欢这个既能适应现代文明、发挥个人才智,又能取悦他人、保护自己的新人形象,表现出她与“都市”的亲和力,揭示了特区新城所具有的强大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向性,堪称具有“都市意识”的佳作。而张伟明的《我们INT》、《现在打盹》等作品,却表现出对现代文明的疏高、拒绝和对传统的田园风光及传统文化心理的眷恋。他的小说从审美角度看,起点颇高,但若以新的人文精神标准来衡量,他那“现代都市恶”的倾向即表明了一种文化观念上的滞后。近期对“新都市文学”进行创作尝试的有王小妮《热的时候》、张波《特区不浪漫》等,我们期待有更多能展现“新都市”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问世。
景观之二:从专业作家谈“阴盛阳衰”
专业作家是深圳文学的主干,在为数不多的深圳专业作家中,女性同胞又占绝大多数,真是“巾帼不让须眉”。若说文学界“阴盛阳衰”,深圳尤为突出。究其原因,据说是特区给男性同胞提供的机会更多,于是男女学古代分工,男的做生意女的“爬格子”,此说是否在理,留待以后论证。
黎珍宇与张黎明是深圳土生土长的专业作家,她们有许多移民作家没有的对深圳乡土独特的体验,都是擅长写女性题材,文笔泼辣,各有特色,并一直保持良好的创作状态。
张黎明从处女作《朗·策史葛舅舅》起步,到发表长篇小说《我的一只眼睛没有流泪》,至今已有12年的创作实践,展示出她在小说艺术把握方面不断走向成熟。
乔雪竹曾以长篇小说《无碑年代》在广东省获奖,另一部长篇《城与夜》也即将出版,近期正在进行《深圳的先民》等影视创作。李兰妮当初是以中、短篇小说引起文坛注目的,近年来却主要从事散文创作。
彭名燕象是闯进深圳文坛的一匹“黑马”。她调进特区不到两年,就写出并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38万字的长篇小说《世纪贵族》。
从事专业创作的文坛娘子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保持执着的文学追求,固守作家是人类良知的代表这一信念,在不断寻找精神家园中张扬人性精品与精神价值,尽管她们还要走一段寂寞的路程。
景观之三:严肃文学通俗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应运而生。迪斯科、摇滚乐、流行歌曲、卡拉OK的兴起,激发了个人参与娱乐的民主意识,使个人的情感、意愿、欲望得到充分、自由的渲泄和表达,因而得到大众的认同与热衷。与此同时,市场机制也介入了文学形态,促使相当部分文学作品进入流通领域,增长了许多作家的“大众文化心态”,于是,“严肃文学通俗化”便成了鹏城又一文学景观。
其主要表现,一是纪实体报告文学兴起。其中尤其引起轰动的是由市委宣传部写作组采写的长篇纪实体报告文学《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它熔思想与艺术、史实与理论为一炉,大跨度、全景式俯视、展现特区发展进程,形成一种“雄强博大”的艺术风格(同时也带着思辩报告有余、文学色彩不足的遗憾),在深圳报告文学领域开风气之先,这在报告文学越来越“广告化”的流风之中,起到了提升报告文学层次与品位的作用。尔后属这类风格的报告文学有《深圳的维纳斯之谜》、《深圳传奇》、《中国魂在深圳震荡》、《深圳纵横》等。二是期刊推出“消费文学”。为迎合市场的需要,近期各综合性期刊均推出诸如“社会热点”、“名人情史”、“明星轶事”、“黑幕佚闻”、“都市风流”一类的“消费文学”,颇具“快餐文化”的品味,八仙过海,各显“消费”,令人目不暇接,足见大众流行文化对深圳文坛的覆盖率。三是作家“造市”与“随俗”倾向。在市场机制面前,高雅(严肃)文学也是商品,与通俗文学一样需要市场研究。二者之间的区别仅在于通俗文学要迎合读者、迎合市场,而高雅(严肃)文学要去创造读者,创造市场。于是,在深圳的土地上,一批作家开始了文学“造市”的实践。他们大都有两副笔墨,既可写严肃的或探索性的小说,亦可写出“雅俗共赏”的作品。如倪振良的《深圳传奇》、王小妮(苏灵)的《深圳的一百个女人》,就在“造市”实践中将作品推向了文稿竞价市场。吴启泰是文学、影视的“双栖作家”,他的《无言的结局》、《美丽的谎言》等小说,展示都市风情与俗世百态,颇具娱乐性与可读性。女作家燕子也通过《新鸳鸯蝴蝶梦》来展示她“通俗化”专长;即便是以写严肃作品为己任的彭名燕,在她的长篇小说《世纪贵族》中,也注意借鉴通俗文学的某些手法,将社会小说与言情小说的手法揉为一体,增强作品的戏剧性与可读性。由此观之,“造市”与“随俗”虽然是初露端倪,但已显示出深圳作家“严肃文学通俗化”的倾向。
四、世纪之交:建设一个文学的“集散地”和“桥头堡”
当深圳文学转过了它的十五个年轮,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十五年,在人类文化史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就是将深圳文学放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来审视,也是一个并不算长的历程。但是,正是缘于改革开放“试验场”的历史使命,缘于社会变革、文化转型所提供的历史契机,使深圳文学成为构筑中国“新质”文化的“排头兵”,从而当之无愧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面对世纪之交,深圳已确立建设国际性城市的发展战略,深圳文学应如何定位?这是深圳文艺发展理论亟待探讨的一个问题。
余秋雨先生在谈深圳文化发展战略时指出,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深圳所要扮演的角色是‘文化集散地’,是传播各种文明的‘码头’。”此说颇有启迪。笔者认为,从深圳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来看,未来的文学定位有两点:其一是建设一个“文学集散地”,沟通海内外文学交流,形成百 花齐放的文学格局;其二是建设一个“桥头堡”,使深圳成为高扬新的人文精神、加快中国文化转型的南方文化(文学)的一个窗口。这就是时代赋予深圳文学不可推诿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