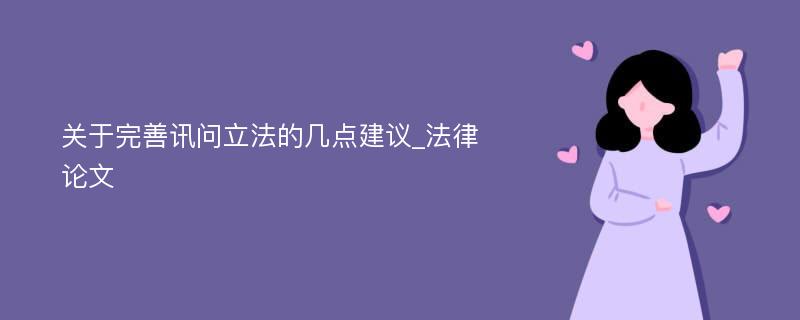
对完善质询立法的几点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建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质询是指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在人代会或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公务活动提出质问并要求予以答复的具有法律强制性的行为,是权力机关对“一府两院”实施监督的重要形式,也是各级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基本权力。从1954年宪法规定质询至今,我国的质询立法不断充实完善,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质询法律制度,有力地保证了人大监督权的正确行使。但也毋庸讳言,当前我国的质询立法尚不完善,并由此引发了一些理论和实践中的争论。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发挥人大质询制度的监督职能,应当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质询立法。
一、关于质询主体回避制度的立法建议
质询主体即有权依法联名提出质询案的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包括各级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按照我国宪法、组织法和代表法的规定,各级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都有权在自愿基础上参与有关质询案提出的联名。法律除了对联名人数的下限作出要求之外,对质询主体参与联名没有其他限制性的规定。
笔者认为,这样规定质询主体是不适当的。质询是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一种权力,而任何权力都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制约机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也不应例外。据统计,我国现有各级人大代表350多万名, 这些代表来自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在众多的代表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个别代表(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与所质询的问题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有时甚至可能出现本人就是所质询的问题涉及的当事人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质询主体不加任何限制,允许本来是政府行政事务的管理相对人或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所办案件的当事人,通过换位成为质询主体,就同一问题在人代会或人大常委会例会上对“一府两院”反过来进行质询,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果质询主体同时又是当事人,或虽不是直接当事人,但与所质询问题有某种利害关系,由于受其身份的限制或利益的影响,很难保证其质询的客观公正性,人大监督的效果也必将受到影响。
鉴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应通过立法建立我国人大质询主体的回避制度,明确规定各级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如果本人或其所在单位或其上下级单位是所质询问题的当事人,或虽不是当事人但与所质询问题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时,应当主动回避,不得参与该质询案的联合提名;如果已经署名的,人代会主席团或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应动员其撤回署名,或宣布其署名无效。
二、关于明确质询对象层级的立法建议
质询对象即受质询机关,是指依法应接受并答复质询案的国家机关,包括与提出质询案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同级的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把法院和检察院列入质询对象,是我国人大质询制度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质询与西方议会质询的一个重大区别。
根据我国人大制度和有关法律规定,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范围仅限于同级“一府两院”。因此,各级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所质询的对象,也应限于同级的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超越同级“一府两院”的质询是越权的,应视为无效。
虽然在法律上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明确的,但在实践中具体操作时却常常出现一些界限不清的问题。如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并且为了防止错误发生,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于是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案件只有一审,有的则要经过二审,有的甚至由更高一级的法院提审。此时质询对象应是哪一级法院?又如经过复议的行政案件,是以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政府机关为质询对象,还是以复议机关作为质询对象?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法律上找不到明确具体的答案。由此便出现了一些地方的省人大代表向省高级人民法院质询下级法院审理的一、二审案件,县人大代表向县政府所属部门质询经上级人民政府复议的行政案件等现象。
笔者认为,质询不能越级和质询对象只能对自己的执法行为负责应当是确定质询对象的两项重要原则。因此,应通过立法明确规定质询对象的层级,明确质询对象只能是作出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决定书等终局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按照这一要求,凡未经复议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或虽经复议但予以维持的具体行政行为,应以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原行政机关为质询对象;对经过复议改变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则应以复议机关作为质询对象。在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中,凡一审生效以及虽经二审但予以维持的,应以一审法院为质询对象;如果二审改判的,则以二审法院为质询对象;如果是经再审改判的,则以再审法院为质询对象。凡质询案中的质询对象不符合上述层级要求的,应视为质询无效,由人代会主席团或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不予提交质询机关答复,并负责向联名提出质询案的人大代表或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解释。
三、关于界定质询内容范围的立法建议
质询内容即质询案所涉及的具体问题,是质询案的主要部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中只规定质询案应具备质询内容,但对质询内容未作任何界定,因而造成实践中质询内容杂乱,且出现与询问、批评、建议、意见等监督形式内容上的混同。
应当明确,质询是一种较高形式的监督方法,其内容也理应具有较高的层次,并不是同级“一府两院”的所有工作内容都应当列入质询的范围。从理论上说,质询内容应当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任务相一致,只有涉及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和“一府两院”的重大违法违纪行为,才能成为质询的内容。对不构成质询内容的其他事项,可以通过询问以及提出批评、建议、意见等形式进行监督。
质询立法除了应将质询内容界定在重大事项和重大违法违纪问题上外,还必须明确规定,质询内容不得涉及党和国家机密事项。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例会公开进行,允许各种新闻媒体广泛报道。在这种公开场合,如果以质询形式提出并公开答复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内容,显然有违保密原则。从质询发源地的西方来看,在质询涉及机密事项时都有明确规定,质询对象此时可以以“事属国家机密”为由拒绝进行答复,议会也不得籍此责难质询对象。
除此之外,由于我国质询不象一些西方国家议会质询那样,把询问也列在其中(即西方的“小质询”、“普通质询”),因此,人大质询应是事后监督,质询内容一般应属于已决事项,拟议中的事项和未决事宜一般不应成为质询内容。如人民法院正在审理中的案件,由于审理结果尚未形成,不能就案件处理结果本身进行质询;但如果办案人员在审理中有明显的重大违法违纪行为,由于该违法违纪行为已经成为事实,可以进行质询,但这种质询仍是事后的。
为了保证质询内容的正确性,质询案的提议人和附议人应当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在充分论证分析的基础上,对照有关法律规定,有的放矢地提出质询案。
四、关于质询案答复与办理的立法建议
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质询案经人代会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后决定交质询机关答复。答复分为口头答复和书面答复两种。口头答复可以安排在不同的会议上,但质询案的联名提出人应当列席会议,并有权发表意见;书面答复除印发会议外,必须印发联名提出质询案的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质询作为一种监督形式,其特点只是提出问题而不直接解决问题,只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而不采取解决问题的直接措施;质询具有受质询机关必须予以解释和说明、给予答复的法律效力,但不能直接改变质询机关的决定、裁判和命令。这是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不同职能所决定的。
但是,仅仅将质询的监督效果限定在答复上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作为权力机关,不仅要发现问题,及时指出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存在的问题。当然,这种解决问题是指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督促下,“一府两院”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权去依法办理,而不是由权力机关越俎代庖。因此,在进一步完善质询答复立法的同时,应当明确规定对质询案中提出的问题需要纠正的,由受质询机关在会后依法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并将办理情况以书面形式报告同级人大常委会,同时抄送联名提出质询案的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关于质询案的答复,《代表法》第14条第5 款规定:“提出质询案的代表半数以上对答复不满意的,可以要求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这是对地方组织法有关质询规定的重要补充。但这里仍有两点需要明确:第一,“再作答复”必须在会议期间,而不能拖延至会后;第二,如果提出质询案的代表半数以上对再作的答复仍不满意时,大会主席团应当向人代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将会议监督延伸至会后,对质询问题在会后再进行调查。这是对质询监督效果的合理延伸,也是对西方议会质询后果的立法借鉴。与之相适应,地方组织法第47条中也应增加“提出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半数以上对答复不满意的,可以要求质询机关再作答复”的规定,并补充规定前述有关对再作答复的期间和仍不满意时的处理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