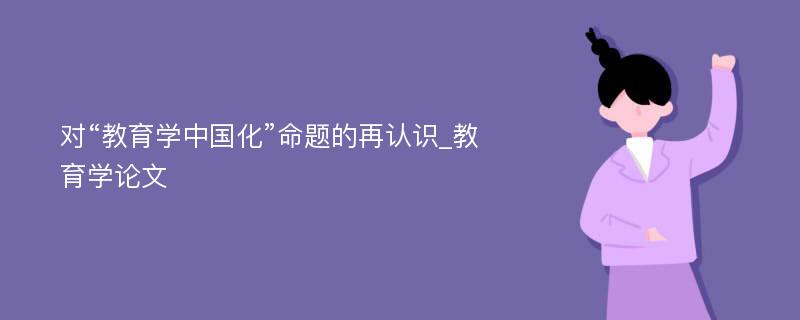
“教育学中国化”命题之再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教育学论文,命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教育学百年进程中,“教育学中国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教育学中国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当前重审“教育学中国化”命题,应该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一、“教育学中国化”之目标
“教育学中国化”有两个不同的涵义:一是建立中国的教育学,即要赋予教育学以特殊的性格;二指使教育学在中国充分地发展,使它与中国的社会发展联系,为中国所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学术界认同的是第二种涵义,如在20世纪20年代舒新城就竭力呼吁:“此时我们所当即于预备者,不在专读外国书籍,多取外国材料,而在用科学的方法,切实研究中国的情形,以求出适当之教育方法,使中国的教育中国化。”(注:舒新城.论道尔顿制精神学[J].中华教育界,1923.(13).)不难看出,当时我国研究西方教育学的主要动机便是要使西方的教育学与我国当时的教育实践紧密结合,盲目照办,无原则的移植已经为学术界所诟病。直到20世纪50年代,教育学中国化仍然简化为“原苏联教育学与中国教育实践的结合”。(注: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A].瞿葆奎.元教育学研究[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P417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教育学中国化”的争论逐渐多起来,有学者在总结该时期的争论时明确提出,“探讨中国化的主要目的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创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注: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A].瞿葆奎.元教育学研究[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P418至此,“教育学中国化”的第一种含义才真正得到认可。
“教育学”这一称谓最早源自西方,但在西方囊括一切的“教育学”早已退出历史舞台。那些具有原创性的教育研究成果都不是以学科的形式,而是以理论的形式出现的。如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伯恩斯坦的“编码理论”,彼得斯对“伦理学与教育”的研究,这些学者并没有自诩要建构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却都以敏锐的视角,抓住社会隐含的矛盾,穷多年之力,构筑了自成一家的理论体系。凡此种种,都表明教育学是不能够涵盖教育理论的,二者各有所指,不可等同。澄清这种语词混乱对于反思“教育学中国化”的命题大有裨益。
那么,“教育学中国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笔者以为,“教育学中国化”的最终目标是要赋予教育学以中国文化的特色,重建具有本土特色的教育理论,只有隐含本土教育理论的教育学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教育学。诚如有学者所言:“中国教育学要着重研究在中国这一特定空间和条件下的教育问题,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独特途径,探索中国教育运行的特殊规律,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注:鲁洁.试论中国教育学的本土化[A].许美德、潘乃容.东西文化交流与高等教育[C].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重建本土教育理论是“教育学中国化”的终极目标,中国教育学不仅要隐含深刻的教育理论,而且要有极强的中华民族认同。
因此,我国教育学重建需要澄清两个问题:一是要在科学规范的指引下,重建我国的教育理论;二是在重建教育学过程中,延续我国的教育学传统,以便保持我国的文化认同。前者要求我们重审教育理论的本质,进而探讨重建我国教育理论的可能性;后者要求我们关注我国传统教育学的转化问题。
二、教育理论的本质及重建本土教育理论的可能性
然而,何为教育理论?本土教育理论的重建何以可能?这些问题是实现“教育学中国化”目标的必要前提。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只有符合自然科学理论的标准,才可能是真正的理论,教育理论也不例外;还有学者竭力反对依照科学标准界定教育理论,主张教育理论要融合价值判断,体现特定的文化取向和文化关怀。前者强调事实,后者强调价值,构成了教育理论本质中的价值与事实之争。
价值与事实之争一直困扰着西方教育理论界,20世纪60年代,奥康纳(D.J.O'Connor)与赫斯特(Paul H.Hirst)就教育理论的本质和范围进行过持久的争论。奥康纳认为,“理论是:(1)通过观察可以证明的假设;(2)这些假设在逻辑上能够被证明是相互联系的,并自成一体。”(注:D.J.O'Connor,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57.)P75~76合理的假设不仅具有解释功能,而且是可以证伪的。只有符合上述标准,教育理论才是科学理论。广义的教育理论是“指以下述活动为目的的理性探索:一是解释教育过程和教育制度的运行方式;二是根据这些知识,在教育制度意欲实现目标的指引下提高教育水平。”(注:D.J.O'Connor,The nature of scope of education theory(1).Glenn Langford and D.J.O'Connor,(ed.)New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P48
赫斯特撰文与奥康纳展开辩论,二人的分歧在于:(1)以阐明实践活动为目的的理论与自然科学理论是不能等同的,二者具有不同特征,具有不同功能。在自然科学中,理论是科学活动的最终结果,而在实践活动中理论的功能在于其对实践活动的指导。(2)教育理论的功能在于准确地决定我们在教育研究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教育理论隐含着价值判断。(3)教育理论要糅合价值和事实。(注:Paul H.Hirst,The nature of scope of education theory(2).Glenn Langford and D.J.O'Connor,(ed.) New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P69~72
二人的争论实际上切中了教育研究中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教育理论既要客观地反映教育实践,又要指导教育实践,前者要求教育理论要有客观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类似波普尔所谓的“客观知识”。后者则要求教育理论要反映教育目的和教育手段中隐含着的价值判断。事实与价值在教育理论中能够融合吗?
教育理论是解释和指导教育实践的,这就决定教育理论不同于自然科学理论(如力学定律),甚至也不同于哲学、社会学理论。教育理论与政治理论颇有相通之处,虽然学习政治理论并不一定是为了参与政治,但政治理论承担着指导和解释政治活动的责任。曼海姆(Kar Mannheim)将政治知识分为两类:(1)类型学知识;(2)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知识。(注:[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黎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P167~174无疑,教育理论属于第二类知识。与政治理论一样,教育理论也不只是一些纯粹的“客观知识”,而是有实践指向的。赫斯特抓住了教育理论的这一特性,认为教育理论中应该隐含价值判断,这对澄清教育理论的本质至关重要。之后,卡尔、莫尔不再拘泥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对教育理论进行了归类,避免了奥康纳与赫斯特之争中的矛盾。(注:详见:[英]穆尔.教育理论的结构[A].孙绍荣等译.瞿葆奎,沈剑平.教育与教育学[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485~502.[英]卡尔.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原理[A].郭元祥,沈剑平译.瞿葆奎,沈剑平.教育与教育学[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557~579.)
实际上,这场争论之前半个世纪,社会学家韦伯就已经对社会科学研究中事实与价值问题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证。韦伯巧妙地回避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矛盾,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从文化意义上理解社会行为,依靠逻辑推理所获得的经验性规律只是我们理解社会活动的必要手段,但决不是最终目的。由此而言,奥康纳所推崇的经过严密科学推理所获得的经验性知识只是管窥教育活动的手段,真正的教育理论是我们据时代的价值观念,理解和应用这些知识时产生的“规则体系”。奥康纳和赫斯特的论争之所以陷入僵局,盖因二人都持有逻辑实证主义的立场,希望通过逻辑推理解决价值与事实的融合问题。事实上,经验问题可以通过逻辑推理解决,而价值问题则只能通过“理解”的方式解决。推而广之,教育理论的建构要从各自民族的不同文化取向出发,根据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每个民族都具有独特的价值传统,对教育活动有自身独特的理解和积淀。极而言之,我国本土教育理论的重建是可以实现的。“教育学中国化”就是要在我国传统价值的影响之下,吸收西方优秀的教育思想,建构指导我国教育活动的理论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自觉”绝不意味着封闭式的妄自尊大,因为真正的教育理论不仅要反映价值,而且要客观地解释教育事实。虽然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受制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但在建构教育理论过程中,要遵循科学规范。正如,韦伯在阐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时所言:
“换句话说,什么成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延伸到因果联系的无限性之中,这是由支配着研究者和他的时代的价值理念决定的;在如何进行研究,在研究的方法上,指导性的‘观点’虽然——如我们还会看到的那样——对于形成他所使用的概念性辅助手段是决定性的,但不言而喻,在使用它们的方式上,研究者在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受到我们思维规范的制约。因为科学真理仅仅是对于所有想获得真理的人都要有效的东西。”(注:[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李秋零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版社,1999.)P23
三、“教育学中国化”的核心问题
在我国教育传统的立场上,反思我国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思想的接续与转化是在更深层次上完成“教育学中国化”的核心问题。原因在于:
第一,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教育学是在脱离我国教育传统基础之上诞生的。漠视教育传统,使我国教育学在百年进程中始终处在引进与移植的困境中。
传统在文化重建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种独创性的文化都是在深厚的传统之上经由传统改造得来的。这主要是因为传统可以提供强大的“支援意识”。“支援意识”是哲学家博兰霓(Michael Polanyi)提出的概念,他认为重大而富有原创性的研究需要强烈的“支援意识”,支援意识是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中潜移默化的结晶,是研究者个人对社会和生活的独特体验。用博兰霓的哲学术语来说,影响一个人研究与创造的最重要因素,是他不能明说的、从他的文化和教育背景中经潜移默化而得来的“支援意识”。(注: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P29在学习外来文化时,如果研究者忽视本族文化传统,“集中意识”会越来越强,“支援意识”就会越来越弱,原创性就会渐趋丧失。库恩认为,科学革命是在传统中发生的,脱离传统是不可能产生范式转型的。因此,我国文化的重建必须基于我国的文化传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强烈的文化认同,而不被域外文化所淹没。“今天是中国人文研究摆脱西方中心取向、重新出发的时候了。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取得比较客观的认识,首先必须视之为主体,然后再通过它的种种内在线索,进行深入的研究。但这绝不是说,每种文明或文化都只能“自说白话”。不必与其他文明或文化相比较参证。……对西方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者也仍然应该各就所需,多方吸收。”(注:除英时.文化传统与文化重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P544
文化的重建如此,教育理论的重建也不例外。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初,为了适应师范教育的需要,在借鉴日本、德国和美国诸国的教育学理论基础上,我国创建了自己的教育学。我国教育学与教育传统之间的疏离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尽管有学者意识到我国教育传统对我国教育学重建的意义,但一百年来,我们一直没有谨慎地处理好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思想之间的接续问题,这使我国教育学一直没有摆脱“被殖民化”的危险,这绝非危言耸听。我国正统的教育史中,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被认为是将杜威进步主义教育思想与我国教育实践成功结合的典范,而实际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最接近王阳明哲学,是我国教育传统与陶行知个人经历的某种拼盘式反映。(注:[美]休伯特·布朗.中国教育中的美国进步主义:陶行知个案[A].王立诚译.[加]许美德,[法]巴斯蒂等.中外比较教育史[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P186~216由此可见,教育传统力量之强大,是任何一种域外理论所无法取代的。教育学界所沿用的西方教育学术语多大程度上是西方教育思想的本真意义?与其在西方教育学思想的笼罩下,亦步亦趋,不如真正从我国教育传统出发,探索一条重建本土教育理论的新途径。这种新的视角可以将“断线”的教育传统连接起来,真正实现我国教育学的民族认同。
第二,百年来我国教育学术界在对待我国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思想上仍没有摆脱二元思维的限制,对“教育学中国化”的学术生态持有极为浮泛的认知。
上个世纪20年代,知识界对赫尔巴特的教育学和杜威的教育理论趋之若鹜,一股学习西方的热浪在涌动。然而,西方近代的教育理论能否融入我国本土,如何融合?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学理上的清理。更致命的是,一百多年来,我们对教育传统的态度一直没有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阴影,我国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思想之间高度的对立状态一直没有从深层次上得到真正的缓解。
我国教育思想史是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分论各阶段教育思想的发展,通过大量的史料来印证教育思想的发展是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相适应的,教育思想的分类框架也是来自西方,因为我国的教育典籍中并没有教育目的、教育过程、教育方法这样的术语,这完全是西方教育学的术语。这种比附西学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我国教育传统的意义。
近二十年间,在教育学术中出现的各种概念术语来看,先是存在主义、现象学,后是批判理论、解释理论、解构理论,由此而生的“主体性”、“复杂性”成为教育学的热点问题。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域外理论的移植,甚至问题的发问方式也无一不是因袭国外,然而试问这些术语与我国的教育传统、当下的教育实践有何关联?对提升我国教育学的理论张力有何裨益?教育学界重视的是术语的移植和翻新,而不是思想之间深层次的融合与重构。殷海光先生早在60年代就已经对这种术语移植的所谓“中西”汇通论进行了批驳:
“中国近百年来之吸收西学,基本的推动力,……除了应急之外,就是新奇的心理。这样一来很容易走上‘浅尝辄止’的道路。结果,‘中学’荒废了,西学也只抓到一点皮毛。所以中国的学术园地里这样寥落。真正要吸收‘西学’,除了从语言文字的训练入手以外,必须在理论的构造上痛下工夫。‘理论构造’是‘西学’之‘体’的核心。掌握这个核心,‘西学’之‘用’就不难了。”(注:殷海光.殷海光文集(第三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P265
总之,教育学百年过程中我国一直没有处理好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思想之间的接轨问题,要么全盘反对,要么漠视,关注的是中外问题,“古今”问题一直被草率式处理。这样贫乏的学术生态当然不可能产生真正见解深刻、眼光深远、成一家之言的教育思想。因此,“教育学中国化”的一个拓荒性的任务便是以我国教育传统为中心,以开放的心态,反思我国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学说之间的接续与转化问题。我国真正原创性的教育理论只能来自本族的教育传统和教育实践。
四、“教育学中国化”的必要路径
我国教育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教育学中国化”的必要路径。我国的教育传统如何才能转化为本土的教育理论资源?历史上曾经有过各种不同的尝试,如“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但这些方案都没有有效地解决我国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思想之间的接续问题。教育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摆脱了继承传统过程中的“体”、“用”之争,旨在通过中西教育理论的融合,寻求一种延续教育传统的新典范,这种典范既不失西方的视野,又扎根于我国教育传统中,具有我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这一典范是海外学者林毓生提出的,他认为:“创造性转化是指:使用多元的思考模式,将一些中国传统中的符号、思想、价值、与行为模式选择出来,加以重组/或改造(有的重组以后需加改造、有的只需重组、有的不必重组而需彻底改造),使经过重组与/改造的符号、思想、价值、与行为模式,变成有利于革新的资源;同时,使得这些(经过重组与/或改造后的)质素(或成分),在革新的过程中,因为能够进一步落实而获得新的认同。”(注:琳毓生.创造性转化的再思与再认[A].王元化.学术集林[J].1995(6).)P196~197
教育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不仅要深刻了解我国的教育传统,而且要对西方的教育理论有透彻的理解,断章取义,片面移植都是违背这一原则的。对教育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不是通过西方的学术框架剪裁教育传统,而是对我国教育传统中隐含着的质素予以新的组合,根据韦伯的“理想典型”,对这些质素进行新的组合,使之适合当代的教育实践,解释和引导当前我国的教育实践,由此来重建我国的本土教育理论,最终实现“教育学中国化”的目标。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教育学中国化”命题仍具有其顽强的生命力,我国教育学之所以在百年进程中,取得的成绩颇为有限,除了政治原因之外,我们一直没有处理好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思想之间的接续问题,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思想之间高度的对峙状态并没有得到缓解。本文提出重建教育理论必须对我国教育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便是突破二元思维的一种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