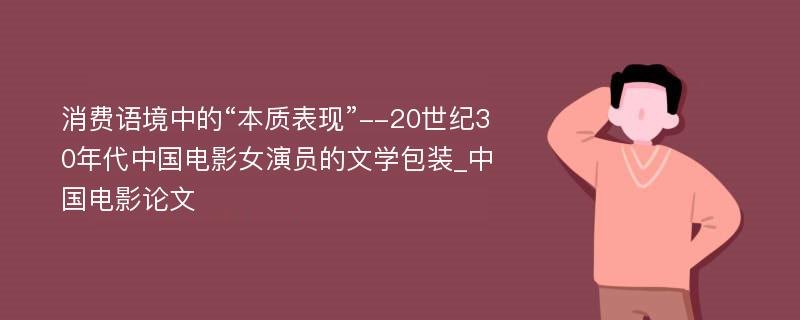
消费语境下的“本色表演”——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女星的文学包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中国电影论文,本色论文,女星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面对着内部的冲突和外敌的入侵,正处在一个变革时期。此时的中国电影,处在一个经历初期发展后的繁荣阶段。一方面,电影技术的发展给观众带来了有声影片,编、导、演等技术都有了新的提高;另一方面,制片厂制度初步建立,经过激烈的竞争后,“明星”、“联华”、“艺华”、“天一”等公司慢慢在上海立足。电影业的发展,使上海很快成为了“东方好莱坞”,电影在都市观众中非常流行,“在今日,一般民众——一般摩登化的男女青年,差不多都公认电影是他们生活上最大的慰藉,和最高的享乐”①。
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表演艺术已经十分成熟,并随着电影商业化进程的推进,出现了一批堪称明星的较大演员群体,他们在广大观众中享有很大声誉,也带动了电影市场的活跃”。②如胡蝶、阮玲玉、王人美、黎莉莉、陈燕燕、艾霞、陈波儿、王莹等女明星,金焰、高占非、赵丹等男明星。“‘明星’不再是一个单薄的外来名词,而实在地成为一种广泛流行、初具规模的社会现象和工业制度。”③伴随着电影明星的出现,“影迷”群体也登上了历史舞台。“‘影迷’(Fans)成为‘明星制度’(Star system)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不自觉地放弃了电影底文化内容的评价,而单纯地追求明星身价(Star value)”。④明星和影迷这两个相互依存的群体,迫切地需要电影以外沟通双方的媒介,流行报刊无疑是让影迷得以“亲近”明星的一种重要媒介。
翻阅这一时期的报纸和刊物,能看到很多明星的散文、随笔、诗作,主要见于《明星月报》、《电通》等电影公司主办的杂志,《现代电影》、《艺声》、《影迷周报》等电影类流行杂志,也有《现代》这样的文学杂志。这些创作,大多出自女星之手(或用女星之名发表)。电影女明星的这一“文学创作”潮在近年来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其中文笔较好的艾霞、王莹的作品集成《现代一女性》、《衣羽》两本册子出版⑤,研究者多关注作品本身,讨论电影明星的“文学梦”⑥,或将这些作品作为女星的“自我表述”⑦,这对于电影、文学及明星文化的研究都很有意义。本文侧重将这一现象放在当时的城市消费语境之下,从电影工业的明星话语建构入手,考察当时初步发展起来的电影工业是如何通过“文学”为代表的手段对女明星进行文化包装的。
一
经过晚清、民国初期的发展,印刷媒介取得颠覆性的突破,造就了一种以流行报刊为载体的大众文化。中国电影明星自从诞生的那一日起,就有意无意地开始了银幕之外的另一种“表演”:他们和影迷见面,接受小报记者的访问,并在报刊上撰文、写诗。而作为银幕的补充,画报、小报一类的流行印刷媒介使人们对电影明星的消费延伸到了银幕之外,各色杂志、画报、小报上充斥着对明星、特别是女明星私生活的报道,关注她们的日常生活、个人爱好,为观众提供了银幕之外对电影女星的另一种“凝视”。
电影女明星对这种“凝视”反应各异,但不管她们各自的动机有什么不同,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事实是:早在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中国电影业的初步发展、明星群体的初现,电影明星(尤其是女明星)群体就开始在流行报刊上发表文章了。例如王汉伦就在《电影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明自己为何选择电影演员这一职业:“谋一份正当职业、做一件轰轰烈烈的事、为女界争一口气。”⑧个别女明星开始利用印刷媒介展示自己的性魅力,例如“骚姐姐”韩云珍就不断给小报提供“骚诗”。⑨
在这里有必要对20世纪20年代这一中国电影初兴阶段围绕电影女明星的公共话语做一粗略的回顾和考察,从中可以看到“电影女明星”是如何在“娼优并论”的传统价值判断和流行媒介带来的显赫声名的矛盾冲突中一路扶摇直上的。在中国,男女演员在很长的历史时段中地位都非常低下,这种价值判断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的后半期。在1927年出版的《妇女杂志》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评价:
几乎所有踏上舞台的女人都是男演员的妻子、地位低下的女人,以及逐渐厌倦了在街边拉客的妓女。我们可以猜得出她们的价值观、做人原则和希望是什么。⑩而此时的王汉伦、杨耐梅等人,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业最早涌现出来的女明星,她们声名大噪并对都市时尚生活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在都市消费语境下,电影女明星由于掌控着时尚风向标而获得了某种特定的“文化权力”,这直接挑战了传统的否定性话语。但真正促使围绕女明星的话语发生改变的,是电影工业背后的商业利益。
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电影业经历了一系列结构转型,形成了一种以制片厂为中心的组织结构。经过激烈的竞争和淘汰,“明星”、“联华”、“艺华”、“天一”等公司成为中国电影业的主力。明星个体的走红和制片厂的盈利状况息息相关,这些电影制片厂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手段,开始了造星运动,流行印刷媒介自然成了制片厂的“利器”之一。电影制片厂开始创办电影类杂志,如明星公司的《明星月报》、电通公司的《电通》画报等,对电影女明星的溢美之词从电影界内部开始向外扩散。一段被广泛援引的刊登于1933年《电影月刊》上的话,显示了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评论界对电影女明星态度的转变:
自电影诞生之日起,女人便不能出现在银幕上……女人的缺席导致了电影人才的匮乏,为数不多的几个女演员,不论其艺术才能如何,都成为了明星。
那些记者和编辑都傻呆呆地盯着女人的身体……社会也受到吸引,将注意力投向她,到了将她称为明星的程度。而她呢?她也以“明星”自居,浓妆艳抹、衣着时尚,踌躇满志,装腔作势地用她所谓的明星风采吸引异性……
但是这些都过去了,因为电影已经在社会上存在颇久了。
实际上,这些女演员已经过时了。最好不要再提她们,说说现在这些幸运的女演员吧!(11)
这些“幸运的女演员”和她们的前辈们相比,“幸运”地出现在一个更加商业化的都市消费语境中。在这一语境中,明星身上的商业附加值被极大地利用,她们身处的电影工业系统不留余力地利用各种宣传话语挖掘她们的商业价值。
1933年,由《明星月报》发起了“电影皇后”的评选,胡蝶在这一次评选中以压倒性的优势胜出,共获得了两万多张选票,紧随其后的是陈玉梅和阮玲玉。若干年前,当胡蝶还是电影界新人的时候,《良友》画报在创刊号的封面上就采用了她的照片。胡蝶“封后”后,《良友》画报的编辑不无自豪地说:“通过《良友》,第一次,她的美丽的笑涡被广泛地介绍到群众中去。……随着《良友》画报的销量由3000增加到40000,胡蝶也从籍籍无名的新人而成为电影皇后”。(12)《良友》编辑的这席话自然有自我标榜的意思,但是流行印刷媒介对电影明星起到的宣传作用也确实不可小觑。
1935年,胡蝶应莫斯科电影节的邀请,赴俄、英、德、法等国进行访问,一时各大报刊争相报道她在外访问的情况。她从国外源源不断地发回稿件、信件,回国后又撰写或口述了大量的访欧心得,这些文章中的她,好学、幽默、有正义感、爱国心。“电影皇后”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她声名的巅峰。
胡蝶在《欧游印象记》中的开场,是当时“明星文学创作”最惯用的开场:
《艺声》编辑要我写“欧洲印象”,真使我感到困难,第一我这样浅薄的学问,怎样写得出这样大的题目,第二这几天承蒙期望者的不弃,是以来得忙些,可是编者盛意难却,我只得忙里抽闲,涂上一页,希望勿以澜言不教,那就我这浅薄的印象,也许会引出更有意义的文章。(13)
从这种常见的叙述中不难看出,杂志社希望发表明星的文章,让读者能够近距离地感受明星的生活和情感体验,明星们虽然总是“感到困难”,但也希望借流行刊物表达、塑造、宣传自己,于是两者一拍即合。总之,流行印刷媒介在二三十年代有关“电影女明星”的话语塑造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是银幕之外女明星重要的表演场域。女明星在流行报刊上发表文章,是她们银幕之外的另一种表演,也是电影工业宣传机器借以塑造女明星形象、维护女明星地位的手段之一。
二
早在20世纪20年代,明星公司就有策略地按照女明星自身的气质去安排她的银幕角色,雇佣和剧中女性角色气质相仿的女演员进行演出,以提高影片表演的说服力。到了30年代,“本色表演”取代“现身说法”,成了当时占主流的表演观念。孙瑜在《野玫瑰》中启用当时只有17岁的王人美,只不过希望她“在影片中扮演她自己”。(14)
这种策略的存在曾被解释为一种“现实主义”的选择,“因为有了摄影和电影化再现的现实感,伪装已无法继续”。(15)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批评者认为这种策略是一种社会约束,“它将女演员引向一种‘可信’的原则,这种‘可信’根植于对理想女人的社会性建构”(16),“天真”、“真”成了导演、剧作家、观众、女明星共同建构起的一种明星价值观。
在大量的对影星的宣传中,女明星的散文、诗作被用来表现、证明她们的性格、品德。再没有哪种话语形式比明星自己的文学创作,包括散文、诗歌、剧作、小说,更能展现她们的性格和才华,更能凸显明星的“本色”。
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女星,包括艾霞、王莹、王人美、黎莉莉等人,都是“本色派表演”的代表,周慧玲把艾霞视为“本色派表演”的先驱,“艾霞等人更主动介入电影工业,以她们的人格形象为包装的行销策略”,其中,“艾霞甚至曾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剧本内容,以自我指涉作为她创作和自我行销的手段,于1933年自编自导《现代一女性》”。(17)
这部电影的胶片已经失传,今天的人们只能通过艾霞留下的文字,包括她发表在《明星月报》中的《〈现代一女性〉电影本事》和发表在《申报》副刊上的以电影为蓝本的小说来了解这部电影。电影中的女主人公萄萄,是一个浪漫的、惯于享乐的、为了爱情不惜出卖肉体甚至犯罪的女性。电影上映后,艾霞在《明星月报》上发表了《现代一女性》编后感《我的恋爱观》,在文章中她这样分析萄萄这一角色:
她生长在那种环境中,她需要刺激,没有钱自然不能维系爱,没有爱当然没有刺激。……刺激对于她,就是人生的美酒,无上的安慰。(18)
1923年,年仅23岁的艾霞自杀,给后人留下了很多谜团。艾霞其人是否是她笔下呈现的性格,这一剧本的内容和她自己的生活经验究竟有多大关系,已无从得知。但从艾霞留下的诸多文字中可以肯定一点,她确实将自己描述成一个爱情至上又贪图享乐的“摩登女性”,和她所在的明星公司对她的“本色”包装一致。
她的文学才能也受到了公司和社会的重视,她被称为“四大明星作家”之一,但“性感野猫”无疑是公司更愿意强调的她的“本色”。1933年第1卷第3期《明星月报》上,《看!艾霞不打自招的口供》强调艾霞本人也是一个沉迷于恋爱游戏的摩登女性:
自然,这剧本里,她多少有一点“不打自招”的口供在里面,虽然我们不敢确鉴地证明。因为,她的本身就是一位不折不扣十足道地的Modern Girl啊!
一个Modern Girl的习性与爱好,我们大约不难想象而得。譬如带着男朋友踏着夕阳与初明的灯影散步,或者在花好月圆的时节同游公园,譬如喝咖啡,看电影,上跳舞场……
而艾霞的文学才能,不过是一点附庸风雅的陪衬:
不过您不要忘记,艾霞姑娘和上海一般皮相上十分摩登的小姐们可有着不同的地方,她不像那些小姐们一样,只会涂脂抹粉,沉湎于色情的物质文明的享受。她最爱好的还是静下来坐在家里,摇摇那一枝生龙活虎般的笔杆儿。
她的文字最重要的用途,是让观众得以认识她“摩登”、“现代”的本色:
她的文章,不仅具备一点流利与妩媚的女性作风,而且非常的爽辣、简洁。在她的文章里,我想读者也必然不难认识这一位“现代”的“女性”吧?(19)
归根结底,制片公司对艾霞文学才能的重视和强调,无非是明星制下制片公司的一种宣传话语。电影明星的类型化塑造,是明星制度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电影明星制初建期,当时的明星制度并不完善,加上对明星形象、性格的塑造通常涉及多种话语权力的斗争,很多明星形象呈现出了不连贯性。但针对女明星的宣传话语仍然显示出了“类型化”的努力,不仅是通过她们见诸报端的文字,也通过各种报道和图片来反映、强调女明星的不同“本色”。像王人美、黎莉莉就被塑造为性格活泼、身体健美的类型:“(黎莉莉)有着一个超时代典型的健美女性的体格,一对灵活的黑眼珠子,一双美的脚踝,以及一蓬南国女性特有的黑头发,有着天大本领,跨过了太平洋、地中海。”(20)
艾霞、王莹、胡萍等人则以“才女”、“左翼”面貌示人:“从左翼剧坛走到电影界来的小姐们,如王莹,艾霞,胡萍;她们除了把各个的天才,及熟练的话剧技巧,运用在“克美拉”之前,表演于银幕之上外,同时更能彰扬其舞弄笔墨的本事,以自编剧本自做主角,而见誉于时。”(21)
可见,即便是女明星中的“作家明星”,她们的文学创作更多地被利用为工业体制下的商业包装。因为从很多资料看,不管后人对艾霞、王莹的文学创作如何评价,不管以王莹为代表的明星作家在文学创作上做了多少努力,当时的舆论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对她们文学才能的评价上,而是放在这种才能对女明星的增光添彩上。
三
综合考虑以上两个方面,我们便不难理解这一时期女明星的创作关注的主要内容和呈现出的主要特点。女明星的创作多以“自己的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这是读者们最想看到的,也是她们自己最想要表现的内容。其中包括女明星们的职业生涯、旅行见闻、情感生活等。
对读者来说,女明星们“水银灯下”的生活无疑是充满神秘感的,很多女明星都写过以“水银灯下”为名的文章。例如“美丽的小鸟”陈燕燕发表在《艺声》杂志上的《水银灯下》:
虽做电影演员并不是和我在理想中那样的容易做,当我经验中第一次在水银灯的工作,却无理由害怕起来。惊慌了起来。许许多的人和许许多的眼睛包围着我,那时我对我自己是非常的失望了,因为我做不出一些儿的表情来。
我又用有志成的古训来鼓舞,以后慢慢地对水银灯下的生活感觉异样的兴趣了。(22)
陈燕燕强调的是演员职业的艰难,她是如何克服自己的恐惧并用古训来激励自己并取得成功的。她的表述显得楚楚可怜,并让人对演员这一职业的难度有了认识。同样的题目,胡萍的表达就要犀利得多,她更多地感叹电影女演员难以自我把握的命运:
年轻的电影从业员也正如春天的花木,鉴赏者是爱护备至的。等到叶黄花碎的时候。哼!谁管呢!于是我心惊胆颤,然而仔细一想,管它呢,人生本来就是做戏,戏演完了,就算终场啦。于是我将大笑,我将高歌!(23)
电影女星因为职业的关系,经常会到各地拍戏、宣传,赴国外考察、交流,这并非当时社会上的每个女子、甚至一般男性市民经常能有的生活体验。“旅行见闻”也因此成了电影女星热衷描写的题材之一。
胡蝶在成为“电影皇后”之后,在1934年和周剑云夫妇一同访问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在《胡蝶女士旅欧杂记》的描述中,她在所到之处都很受欢迎,被法国人看做中国电影的“嘉宝”式人物,并且以推广中国的电影、文化为己任:
我每到了一个地方,无论是商店,马路,或什么地方,人人都围着我看,彼此说着我的名字,有些较为大胆的便走上来和我说几句话,可是我们言语不通,他们只多半说一两句表示高兴话,像说我很漂亮等。
他们对我底衣服也常常赞美。我们去的时候,为了能够表现中国的美术,所以多带了几件刺绣的衣服去。
……
在座有许多人是第一次看中国电影的,他们很觉惊异,他们以前想不到中国也有这样相当成绩的电影的。……第二天报纸上的批评,也很为称赞。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旅行,把片子映给他们看,在片子的本身纵然不是很成功,可是在对外宣传中国的电影事业和文化上,却是成功的。(24)
胡蝶的这番描述,无疑是具有“电影女皇”所应具备的眼界的,她被包装为中国电影的使者、具有中国风格的“美”的化身。
同样是身处异国他乡,以呐喊“冲出黑暗的电影圈”闻名的王莹,在东渡日本留学时,写下了《东岛旅程之一——秋的祭礼》,在对日本“秋的祭礼”的叙述中,表达了对生活现实的绝望感和对祖国的思念:
两年来,当生活的鞭子,残酷地鞭挞着我跑到这社会上来的时候,一切的憧憬和光明的未来,都被这痛楚的现实击得粉碎了!——此刻,却立在秋风里,飘到这寂寥的异国,在别国人的闹热的祭礼中,怀念起满目怆凉的祖国来了。(25)
她的文章体现出了对异国文化、人性更深的思考。在当时日军侵华的背景下,她却在日本民间感受到秋田先生夫妇友情的温暖。她发表在现代著名文学刊物《现代》上的文章写道:
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和洪沟,不是国籍的、种族的,而是另外一些不合理的事物,相信着终有一天,文化的轮子会把这些给碾平了的!(26)
此外,女明星的感情生活,从来都是流行报刊对女明星最重要的关注点之一,能有女明星提笔写自己的情感生活、恋爱观念,自然再好不过。艾霞在《现代电影》上发表《恋爱的滋味》,写自己对爱情既投入又时常怀疑的态度:
恋爱是活动的刺激,起先我是由认真的恋爱而一变为不爱,由不爱而变为随便爱爱,而又真爱,而又在认真的爱中不敢认真,而又神秘,我也不能预知了。(27)
不可否认,她对“恋爱”的感觉和描述都是细致入微的,她的表述渗透着颓废的情绪又带着一丝天真。不管是否有意,这一形象与制片公司对她的包装、定位非常一致。
这些女明星的创作,多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体裁上以散文为主,也有少量的诗歌和小说创作,整体上看,质量参差不齐。以“作家”头衔闻名的王莹、艾霞等人的创作,从技巧和情感等方面看,确实体现了相当的文学修养,并且是一种感性化的时代情绪的表达。
结语
正如张勉治所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高度的视觉性和各种形式的宣传是漂浮在每位女演员演艺生涯上的云朵。”(28)20世纪30年代,女明星(或以女明星的名义)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是宣传女明星和电影的形式、手段之一,参与了20世纪30年代明星话语的建构,是当时尚未完善的明星制度中的一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文章,从特定角度考察当时的电影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当时女明星的生活和情感状况、价值判断。然而,正像理查德·德克多瓦(Richard deCordova)所说:“演员——如同作家——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一个真实的个人。这是一个由具体的制度制造并被该制度赋予了那个制度内具体功能的类别”。(29)
当时就有人敏感地意识到了“明星文学”服务制度的作用而对其进行质疑,例如《社会新闻》上一篇署名“陶陶”的文章中写道,王莹、艾霞、胡萍虽然“能彰扬其舞弄笔墨的本事,以自编剧本自做主角,而见誉于时”,但作者曾听闻“王莹胡萍的写作品,背后都有捉刀人,至少王莹每次发表的文章,都有人改过”,作者决定“姑且信之”。(30)判断20世纪30年代女明星发表在各期刊上的文章是否为她们亲自创作,并非本文的目的。事实上,王莹后来在文学创作上进行了长期锲而不舍的努力,在40年代末以小说《别后》入选赵清阁所编的《无题集》,后来又以自身经历为蓝本创作了小说《两种美国人》和《宝姑》,有学者评价她是“真真正正实现了她的文学梦”。(31)但历史地看,伴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和造星手段的成熟,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电影女明星文学创作热潮,可以被表述为她们的“文学梦”,更可以被概括为中国电影发展早期电影宣传话语对女明星进行的“文学包装”或“文化包装”。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有些女演员有着很不错的文笔和自觉的文学上的追求,她们作品中呈现出的审美、趣味、思想,是文学和电影研究都应该重视的。
注释:
①黄嘉谟:《〈现代电影〉与中国电影界》,《现代电影》1933年第1卷第1期。
②李少白主编:《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0~61页。
③杨远婴主编:《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文化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第38页。
④郑君里:《影迷与〈明星制度〉》,《影迷周刊》1938年第1卷第1期。
⑤艾霞著《现代一女性》(陈子善、张可可编)、王莹著《衣羽》(陈子善、张可可编)两本作品集于2012年1月由海豚出版社出版。
⑥参见张可可:《1930年代电影明星的文学梦》,《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1期。
⑦参见周慧玲:《表演中国:女明星,表演文化,视觉政治,1910—1945》,麦田出版社,2004年。
⑧王汉伦:《我入影戏界之始末》,《电影杂志》第13期,1925年3月。
⑨参见《罗宾汉》上刊登的《女明星的怀春赋》,1927年5月1日;《韩云珍口解春赋》,1927年5月4日;《韩云珍寒夜吟骚诗》,1928年1月11日;《韩云珍春宵赋新诗》,1929年2月26日等。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胶卷。
⑩凤歌:《妇女与电影职业》,《妇女杂志》第13卷第6期,1927年6月。
(11)阿灵:《女明星的幸运》,《电影月刊》1933年第26卷。
(12)《良友影人》,《良友画报》1934年2月第85期。
(13)胡蝶:《欧游印象记》,《艺声》1935年7月第1卷第2期。
(14)王人美:《我的成名与不幸》,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89页。
(15)张英进主编:《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和城市文化》,苏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
(16)同上。
(17)周慧玲:《表演中国:女明星,表演文化,视觉政治,1910—1945》,第69页。
(18)艾霞:《我的恋爱观——编〈现代一女性〉后感》,《明星月报》1933年第1卷第2期。
(19)黎痕:《看!艾霞不打自招的口供》,《明星月报》1933年第1卷第3期,转引自周慧玲《表演中国:女明星,表演文化,视觉政治,1910—1945》,第80页。
(20)佚名,《电影生活》1935年《游泳特辑》,转引自张英进、胡敏娜主编《华语电影明星:表演、类型、语境》,西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2页。
(21)陶陶:《野猫艾霞的特写面影》,《社会新闻》1933年第1~30期合订本。
(22)陈燕燕:《水银灯下》,《艺声》1935年第1卷第1期。
(23)胡萍:《水银灯下》,《时代电影》1934年第1卷第6期。
(24)《胡蝶女士旅欧杂记》,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8月,无页码。
(25)王莹:《东岛旅程之一——秋的祭礼》,《时代电影》1934年第1卷第6期。
(26)王莹:《秋田雨雀访见记》,《现代》1933年第1期。
(27)艾霞:《恋爱的滋味》,《现代电影》1933年第1期。
(28)张英进主编、苏涛译:《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和城市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
(29)Richard deCordova.Picture Personalities:The Emergence of the Star System in Americ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p15.
(30)陶陶:《野猫艾霞的特写面影》,《社会新闻》1933年第1~30期合订本。
(31)张可可:《1930年代电影明星的文学梦》,《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