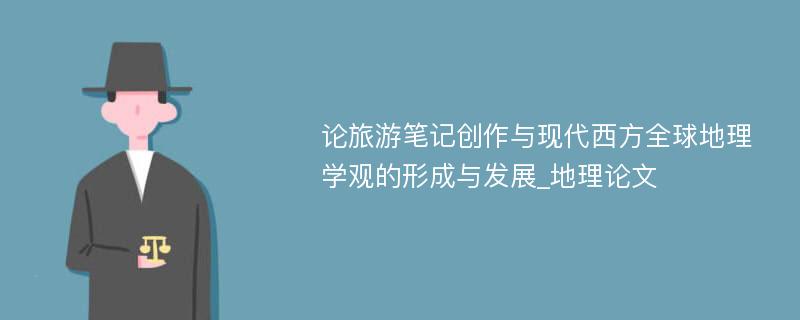
试论游记创作与近代西方全球地理观形成和发展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试论论文,游记论文,地理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人与自然的分离及人地关系的恶化构成现代生活的一个根本冲突,人们一边在创造景观,一边却在景观面前感到异化。但是,现代地理学却很少注意地理理论主观能动性和人地关系本质的研究。
七、八十年代以来,许多西方学者对现代主义时空观提出批评。首先,是一些文学批评家开始注意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地理性。如美国文化批评家、 比较文学学者萨依德在《东方学》(注: Said, Edward,"Orientalism" 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一书中分析了西方文化中伊斯兰东方作为一个地理概念的人为性。他在《文化与帝国主义》(注:Said,Edward."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3年,见该书第71页、69页。)一书中也指出了西方文学作品与全球殖民主义的联系。英国学者博埃默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一书中也分析了英国文学与其全球殖民经历的关系,指出西方文学与其空间扩张分不开:“旅行者和殖民者所凭借的就是他们手头所掌握的程式化的描述和具有权威性的象征,然后又把这些描述和象征在他们之间散布。”(注: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 韩敏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页。)同样,一些西方地理学家也开始提醒同行们不要陷入纯理论的、抽象的空间观里,而应塑造一个积极的、历史的空间观。他们强调文学创作与地理景观的关系,把后者视为一种文本,认为人与景观的关系仿佛作家与世界的关系。如美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Tuan)近年来提出要注意语言意识活动与地理景观发展关系的研究:
地理学在研究各种规模的地方如何得以产生时,几乎把注意力只放在物质过程和社会经济动力上,而没有公开提到语言的作用,似乎所有经济(和政治)力量不需要语言就能起作用,使物质世界发生变化。这种观点显然是荒谬的。如果过去的地理学家默然接受了这种观点,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长久以来一直认为地理学就是对地球的描述,语言只不过被用来描述,并没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仅就表面来看(也就是说姑且不谈语言与现实的关系这一复杂问题),这种看法在心理上也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如果一点用处也没有,那人们为什么还要讨论地理学,著书立说呢?(注:Tuan,Yi-Fu."Language and the making
of place:Anarrative-descriptive approach"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American Geographers,81(4),1991,第692页。)
段义孚还指出,地理学家注意语言与景观的关系有几个优点:使人们对“地方”产生的过程及“地方”的质量有更好的理解;使人们认识到“地方”的本质除情感与美学特征之外,还有道德的一面。因为语言在道德上永远也不会是中立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责任是创造好的建筑,我们就有责任说好话。因为这二者都是人类独有的创造世界过程的组成部分。”(注:Tuan,Yi-Fu."Language and the making of place:A narrative-descriptive
approach"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81(4),1991,第694页。)
在这些新思潮的影响下,不少地理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近年来都开始注意近代西方游记中景观描写的研究。如澳大利亚地理学家卡特(Carter)指出,现代旅行家作家既是历史学家又是地理学家,既是浪漫的骑士又是经验主义的科学家。(注:Carter,Paul."The
road toBotany Bay:An exploration of landscape and history" New York.Knopf.1988,第74页。 )卡特在《通向植物学湾》一书中详细分析了游记在澳大利亚殖民和建国过程中的作用,并批评了现代主义的“帝国主义历史”观, 提出要塑造“空间的历史”。 澳大利亚学者比肖普(Bishop)在《香格里拉的神话》一书中详细讨论了英国游记作品如何塑造了神秘西藏的形象,以及这个形象在西方的兴衰过程。(注:Bishop,Peter."The myth of Shangri-La:Tibet,travel writing and thewestern creation of sacred landscape. "London:The
AnthlonePress,1989.见该书第163页、3页、4页、4页、3页。)比较文学学者普拉特(Pratt )在《帝国的眼睛》中对西方有关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游记做了精辟的分析。尤其对“接触地带”(contact zone)西方与非西方交往的多层含义作了深刻的探讨。(注:Pratt,Mary L. "Imperialeyes: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New York and London:Routeledge,1992,第204页。)这些学者对游记在西方历史文化中的作用、游记中文字景观与殖民主义的关系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对游记中有关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思想内容也进行了揭示。本文试图借鉴西方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游记在西方现代地理意识发展中的重要性及游记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关系进行讨论,以说明人与景观的辩证关系。
二
文化是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文化离不开语言活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地理景观的话,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首先,任何景观都与语言意识活动有关,都与动机分不开。“纯粹”的自然对使用语言、有欲望的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不存在的,而且也是没有必要存在的。同样,纯粹的旅行也难以想象,因为既没有脱离了文化的旅者,也没有抽象的没有文化的边疆。不但人为景观如亭台楼阁是文化价值的反映和语言活动的产物,是一种“文本”(text),我们看到的所谓“纯粹”的自然景观(如自然保护区)也与我们的语言概念分不开,因此也带着我们的主观意识。游记读者往往会注意到,游记作品不但展示了外在的景观和旅程,更有趣的是在描写和塑造旅程的同时,作者的个性和思想也跃然纸上。所以当代美国游记作家保罗·索罗说,游记是一种自传,游记对作家自己内心世界的揭示,胜于对所描写的地区的揭示。(注:Thereaux,Paul."Riding the iron rooster:Bytrain through China" Ballantine Books,1998.)所以卡特说:“在观察者与被观察物之间需要创造出一定的距离”,观察者“需要能够远离自然,从安全的制高点指出自然”,“住宅并不把森林关在外面,而是把森林转化为一件文化对象,把荒野转化成一种美。”(注:Carter,Paul."The road to Botany Bay:An exploration of landscape andhistory" New York.Knopf.1988,第154—155页。 )段义孚也说:“语言具有影响力。我们所说的任何话都使一样东西显现,而使其他东西隐藏在阴影里。”(注: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93—694页。)也就是说人与周围空间世界的关系是通过文字来沟通的,离开了文化意识,自然的概念和与自然相对的人的概念便都不存在了。
其次,空间历史强调对语言的作用的认识,如对地名命名的意义的认识。卡特指出,空间历史的出发点“即不是哪一年,也不是某一个地方,而是命名的举动。因为通过命名,空间被象征性地转化成了地方,即具有历史的空间”。(注:Carter,Paul."The road to Botany Bay:An exploration of landscape and history" New York.Knopf.1988,序言。)事实上, “殖民的过程可以用语法的概念来表示:给一个地方命名,把它转变成可交谈的地方,就象造句一样。”( 注:Carter,Paul."The road to Botany Bay:An exploration of landscape and history" New York.Knopf.1988,第137页。)因为“在这种意义上,旅行已基本上不再是一项外在活动,它已成为一种认识论上的策略,一种认识方式。”(注:Carter,Paul."The road to Botany Bay:An exploration of landscape and history" New York.Knopf.1988,第69页。)从山脉河流到花草树木,人类生活在名字的世界里。当我们说“山”或专有名称如“天山”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这些语言概念如何影响我们对实际山脉的感受呢?西方扩张正是给世界重新命名的过程。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新世界的征服以文化符号如十字架和西方名称的建立开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创造了“新世界”。段义孚指出:“在澳大利亚,探险家与测量家比农民先到。在开荒和建造家园之前,这个大陆岛被先通过命名、测量、绘图、写旅行日志和日记转化为点缀着地方的条带和通道……。一探险家可能对地形进行了命名,并设计了路线和前景,却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做任何记录。他的将空间( space)转化为地方( place)的活动限于转瞬即逝的个人经历。有了日记和野外记录,尤其是经过修改和出版,他的个人经历——他的暂时的栖居地——与公共意识相接,并在其中扎根,因此获得更高程度的稳定性和永恒性,尽管没有对自然产生任何直接作用。”他又指出:“命名就是使某种东西成为存在,使看不见的东西成为可见,并赋予事物以一定特征的创造力。”在地名中,“专有名称与地理特征在熟悉二者的人们的意识中紧密结合,改变名称就是在改变地理特征本身,不论这种改变多么细微和隐蔽”。(注: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87—688页。)
可见大到社会道德、政治意识,小到个人情绪,主观意识与外部景观总是处在相互定义之中。每一个旅行家作家都会在风景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同样,语言文字景观也在影响物质景观,因为人们总是按一定的理想来改变自然的。在谈到作家与景观的关系时,美国当代游记作家富莱泽尔说:“作者在游记作品中揭示自己,揭示自己的心态、自己的生平事迹,有一个原因,即地方的外观有朝着与你观察它时的感情相同的方向发展的趋势。进一步说,若某地有足够的人在足够的时间内有相同的感受,这个地方就会开始产生共鸣;这些感受就会开始反映在这个地方的外观上”。(注:Friezer,Ian:"Carving your name onthe rock" Zinsser, Willaim:"They went:The art and craft oftravel writing"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1.第47页。)不难想象,这些人是通过语言活动来改变自己的环境的。正由于文字发表的关系,“当一个作家观察一个地方时,他就在改变这个地方的景观。”(注:Friezer,Ian:"Carving your name on the
rock"Zinsser,Willaim:"They went:The art and craft of travel writing"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1.第48页。)如许多政治家的思想对景观都有很大的影响,只是因为文字景观的极大的变化性使人们忽略了语言对景观的影响,反而认为有一个脱离了语言的景观体。
最后,文体和世界有着内在的联系。博埃默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指出:“对于帝国的控制不仅是对真正有形世界的控制,而且还需要在象征的层面上实行……。”(注: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 韩敏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8页。)从更深的层次上看,语言文字既是主观意识现象,也是一种空间生活方式,与现世生活分不开。西方语言文学的发达和地理扩张有着内在的联系。西方小说是一种很新近、最能代表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文体,从一开始就与地理探险有关,其标志就是《鲁宾逊漂流记》。殖民地意识是西方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帝国主义与小说互相支持,关系密切。不可能只阅读其中之一而忽略另一个”。(注:Said,Edward."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3年,见该书第71页、69页。)没有欧洲的全球扩张,也就没有我们所知道的欧洲小说。 ( 注: Said,Edward."Culture andImperialism"New York:Alfred A.Knopf.1993年,见该书第71页、69页。)文字与景观相互依赖,正是地理扩张和异地旅行拓宽了西方对外部世界的感觉,激发了西方文学艺术创作的灵感,引发了浪漫主义。(注:Pratt, Mary L.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Routeledge,1992,第204页。)如英国旅行家米灵顿谈到西藏景观时说,西藏清新的空气,密集的山峦和湖泊,对比强烈的色彩使有关景观艺术的想法发生了革命性转变。(注:Bishop,Peter."The myth of Shangri- La: Tibet, travelwriting and the western creation of sacred landscape."London:The Anthlone Press,1989.见该书第163页、3页、4页、4页、3页。)当劳伦斯问查尔斯·道迪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精力专门旅行,创作《阿拉伯沙漠》一书时,后者回答道:“为了把英国语言从斯宾塞以来的腐朽中解救出来。”(注:Fussel,Paul."The Norton Book to Travel."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87,第16页。)可见语言创作风格与地理活动分不开。沉闷的景观来自沉闷的语言。“文字景观”(letterpress landscape ),“文字画面”(word paintings)正是主观意识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西方地理扩张的过程、西方地理思想从神秘到浪漫到科学的发展过程,与文学风格的发展分不开。
三
文字创作与地理扩张的关系集中地体现在西方近现代史上。西方全球空间观的创建时期正是其地理意识与文学创作达到完美结合的时期,也即游记文学最兴盛的时期。从文化角度来看,西方近现代探险也是一项文字工程,是用文字创造一种世界观。博埃默指出:“但帝国本身——至少在部分意义上——也是一种文本的运作”(注: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 韩敏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页。),“对域外的一块土地进行命名,把这块土地的方方面面都转化为文本存在物,这就是一种行使主宰和控制。”(注: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 韩敏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页。)比肖普也说:“游记写作所关心的不仅是发现地方而且是创造地方”。(注:
Bishop,Peter."The myth of Shangri-La:Tibet,travel writing and the western creation of sacred landscape."London:The Anthlone Press,1989.见该书第163页、3页、4页、4页、3页。)在以科学艺术为指导思想的大众型的现代社会,游记是空间观的重要来源,建立大众文化的地理观是西方近现代游记的主要作用。这一点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近现代游记与出版的关系上来看,没有出版的近现代地理发现是难以想象的。“只有在旅行家(或别的幸存者)回到家,以文本方式,如地图上的名字,给皇家地理学会、外交部或伦敦传教会的报告,以日记、讲演和游记使发现成为存在时,他才算“完成”了旅行”。(注:Pratt,Mary L.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transcultur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Routeledge,1992,第204页。)许多探险家正由于没有把所发现的成果纪录出版而被遗忘。所以社会影响最大的探险家不一定是航行最多的探险家。西方探险史上不乏抢先报道地理发现的例子:而且假造探险结果的人物也屡见不鲜。从塞巴斯提安·卡伯特(Sebastian Cabot)到美国海军少将伯德(Byrd ),我们对一些基本的探险事实仍不能完全肯定。(注: Robert,David,"Great exploration hoaxes."San Francisco:Sierra Club Books.1982.)事实上我们的全球地理观主要来自英国人而不是葡萄牙或西班牙人,正是因为前者对出版地理发现结果的重视和他们的语言上的成就。这说明我们的地理观是基于对文本的社会承认,地理发现的真假实际上在认识上无法确证,只能被搁置起来。社会公认的探险家是能通过写作和出版使别人承认他们的“发现”的人。如澳大利亚不乏探险家,但最有影响的不是发现最多的或旅程最长的,如斯图亚特(Stuart),而是最善于描写其有限的探险经历的,如斯德尔特(Sturt)和爱尔(Eyre)。澳大利亚著名测绘家、旅行家和作家米切尔(Mitchell)对写作和修辞的重视也不亚于探险本身。旅行的长短与出版的多少也没有必然联系。如洪堡的南美旅行只延续了不到五年,而且主要限于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但他有关南美考察的著作长达三十卷之多。
第二,地理与文字创作的关系也反映在游记与小说在体裁上的相似上。小说的叙事体在18世纪末叶引入游记,成为以后游记创作的规范。游记中的旅程或路线相当于小说中的情节;有了路线,琐碎的小事被赋予了含义,“无论离题多远,无论话题多么不相关,旅程都能作为媒介,使我们能够、也必须回到主题。一旦旅程终止了,我们就认为游记也终止了。与纯地理描述或导游册不同,游记是以故事体来构架的。”(注:Bishop,Peter."The myth of Shangri-La:Tibet,travel writingand the western creation of sacred landscape."London:TheAnthlone Press,1989.见该书第163页、3页、4页、4页、3页。)游记中的景观则相当于小说中的不同人物,旅行家无形中象征着小说中的主人公。游记采用小说体裁的意义在于强调主观自我的创造力,这是其现代性的反映。无论是景观还是旅程,地理空间成了自我意识表现的手段。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小说主人公和旅行家在认识论上代表了西方的优越地位,给西方以创造的自由。而旅程或路线则是保持游记内容一致性和可信性的关键。因为一旦选定了路线,游记的叙事内容便基本上确定了。空间路线本身包含着叙述的逻辑,与主观意识分不开;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立场必然选择一定的路线,“路线给旅行家以叙述的权威”。(注:Bishop,Peter."The myth of Shangri-La:Tibet,travel writingand the western creation of sacred landscape."London:TheAnthlone Press,1989.见该书第163页、3页、4页、4页、3页。)
第三,游记作为一种文本是现代性的,这也反映在其内部矛盾上,既有艺术与科学的矛盾,又有科学艺术与宗教、政治经济利益的矛盾。这些必然导致道德上的困惑。加上西方空间观不断在外围遇到障碍和挑战,面临暴力,使游记叙述不时含有认识上的困惑。这种冲突是西方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在路线与景观的描写上均有反映。
四
空间路线与创作风格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线状的道路与线条组成的文字具有共同之处,二者均是创造活动的开端。一定的地理知识是一定路线和视点的产物也就不奇怪了。路线的选择受各种社会和心理认识因素影响,因此很少有纯粹的探险。因为虽然探险的方向乃至内容的可能性是无止境的,探险的路线往往是当地已经存在的道路,体现一定的认识姿态和策略。“这条路线欧洲人从未走过”往往被作为探险的标准,实际上这样的路线太多了,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是这一条而不是那一条。在近代西方,地理探险被作为一种英雄主义的举动说明它是一种社会现象,探险的路线和目标并非任意确定,而具有内在的逻辑。
18世纪中叶以前西方对世界的认识限于海岸线,对世界其它地区陆地的认识仍属想象。如在17世纪中叶以后许多人仍认为加那利(Canary)的特内里费岛上的山脉为世界上最高的山脉,海拔被估计为七、八英里(注:Whitman,Walt."Leaves of Grass." New York:Bantam Book.1983.第120页。)。科学地质学在17世纪末才出现。 从游记与地理知识发展的关系上来看,全球海洋探险时期西方在科学和艺术上均未形成独立的系统。对地理知识的追求只限于描绘海岸线及地名命名。海岸线作为地理观察的重心由于没有景观内容,只适于用地图表达,所以说这是地图的时代、线的时代,寻找黄金国加冒险的时代。海洋本身是单调的,对文字描写来说犹如沙漠;陆地遥不可及,地图上内陆常被想象的事物填充。这一时期的游记以死里逃生和满足好奇的内容为主,文字表述带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探险也直接服务于政治宗教等目的,旅行本身没有成为追求的对象。
以国家意识和自然科学为指导的内陆探险始于18世纪中后期,于19世纪达到高峰。这是参与大自然的变化过程、寻找原材料、创造工业财富、开发市场的科学时代。19世纪在西方是登山和寻找世界主要河流源头的世纪,河流成为西方陆地殖民时期探险的基础。如果说海洋探险是寻找幻想式的黄金国和乐园,内陆探险则沿河流通向山脉和丛林,并依靠科学从对自然的改造中创造出财富。这有一定的必然性。河流是海洋的延伸,是运动的象征、权力与自由的象征。西方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深入是以海洋为出发点的:“那些由海路前来的人能够带去进行防卫的人员和武器;况且,他们远非处在广袤的大陆中央被切断了本国的联系,而是能够借助送他们前来的船只由水路非常方便地逃身。
”( 注:Nicolson,M."Mountain gloom and mountain glory.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9,第151页。雷蒙·道森:《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常绍民、明毅译。北京:时事出版社、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41页。)内陆科学与艺术考察的“和平性”是以海岸或河岸停泊的军舰为保障的,其“非征服”性与海岸或河岸的暴力分不开。就商业来看,河流是运输的命脉;就科学和艺术的角度来看,河流提供了良好的观察点,使科学家能够更方便、更详细地勘查陆地景观,包括地形、地质、植物、动物和当地社会的情况,也使艺术家能够欣赏和描绘山地景色。确定河流线路、流向、主流支流的关系经常是探险家的首要任务,因为河流是陆地探险时期整个空间认识活动的基础。在方向上河岸象征文明,上游地区象征荒野。海洋与河流既是出发点,又是目的地。
五
对景观本身的重视是19世纪游记的一个重要特点。海洋探险结束后的几百年,全球陆地探险使欧洲接触到了新的自然景观。热带丛林、高山和沙漠景观与西欧的温带湿润气候形成鲜明对比,这些景观刺激了西方的空间感受,唤起了西方对自然的浓厚兴趣,产生了新的自然观。对内陆探险时代的旅行家来说,陆地表面给旅行家提供了丰富的观察对象,使欧洲地理视野由线转为面。具有连续性的陆地世界为文字描写和艺术创作提供了无比广阔的空间,为自然科学和浪漫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材料,除地形图、风景画外,游记的兴盛也很必然。景观意识的发展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强烈的景观或环境意识反衬出西方文化中强烈的主体意识。 不论是“如画的”(picturesque )景致、 “崇高的”(sublime)自然风光,还是科学观察对象,景观都在被西方人描写、 再创造。换句话说,作为显意识的景观概念反映了潜意识的西方主体的存在。二者相互定义、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科学自然观最初以机械自然观为代表,如18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林奈植物分类系统根据植物生殖器官的特征,以雄蕊的数目和次序把植物分为二十四纲,再按雌蕊的数目把纲分为目,使人们能够对任何植物进行分类。林奈的贡献主要在语言文字上。他的命名法在欧洲扩张早期,为西方从混乱的世界中创造出一个有序的世界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工具。因此有人把林奈比喻为伊甸园中的亚当。 (注: Pratt, Mary L."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NewYork and London:Routeledge,1992,第32页。)他曾在一年里为近六千种植物命名,除植物外他也曾为大量动物命名,真是“上帝造物,林奈分类”。(注:丹尼尔J布尔斯廷:《发现者》,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第627页、623页。)正由于它是一个语言命名系统,林奈的植物分类体系对当时游记的影响很大。不但许多植物学家奔赴世界各地,扩充西方的植物体系,写成科学著作;记录和采集植物标本也成了一种时尚的旅行活动,被一般的旅行家采用。而且这种科学观察风格也被用来描述地形、河流、甚至人。旅行家在作品中很少使用第一人称,也很少使用对话,所以所描绘的景观有一种永恒的超时间感。这种自然观在探险上最早的例子是库克船长的南太平洋探险考察。第一次考察的成员中包括有著名植物学家班克斯(Banks), 他们搜集了数千种植物标本及多种鱼类、鸟类、及矿物标本,也对当地人进行了观察描写。
18世纪末,机械自然观逐渐被自然史取代。科学旅行家在观察自然的同时试图透过景观表面寻找自然内部的规律。自然不再是单调的机械运动,而是神秘微妙、富有诗意的本体。这种变化的自然观试图对自然现象作深刻的科学解释,在自然内部找到事物发展的原因。如洪堡在奥里诺科河流和厄瓜多尔、秘鲁等地的考察就是一个例子。洪堡不仅搜集了大量植物标本,获得了大量气候资料,也进行了地质、天文、人口、社会等各种观察。他尤其注意自然现象的空间联系,他的贡献包括首次用等温线描绘世界气温分布,认识到了植物带随海拔变化的规律,提出了大陆度的概念,并且首次描写了洋流的运动。洪堡的景观描写雄浑壮丽、变化多端,大有崇拜自然的味道。与机械自然观相比,这种自然观给人赋予了更大的创造性,使人更有驾驭自然的感觉。可以说是科学与景观观察结合的顶峰。
洪堡之后,自然科学与景观欣赏似乎开始分道扬镳,西方对自然的科学把握趋于专门化,转向自然内部过程的研究。靠肉眼观察的、总体性的、或者说地理上的把握不再是自然科学的中心。同时对景观的欣赏也转以浪漫主义为代表。尤其在英国,对山地的审美态度在18世纪已从“阴郁”的恐惧转为“辉煌”的赞美(注:Nicolson,M."Mountain gloom and mountain glor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9,第151页。)。欧洲“大旅行”(Grand Tour)之后,西方对全球陆地景观进一步从感情上认同,使浪漫主义与世界地理的关系更加密切。浪漫主义景观审美强调外部景观本身的美,强调基于个人视觉感受之上的景观价值,注重景色的神秘性、不规则性,甚至把对神的感受寄托在自然之上(注:Nicolson,M."Mountain gloom and mountain glor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9,第151页。)。 与古典的“优美”相对应,浪漫主义的景观包括“崇高”与“如画”两种风格。前者指惊心动魄、雄伟壮丽的自然风光,尤其是山地与荒野。这种景观理想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达到鼎盛,其代表即所谓“目光所及,莫非吾土”(I am the monarch of all I survey)的视野之王的风格,在游记中均有反映。自然的不规则性、无穷性、神秘性使她不再只是人的思想的附属物,而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和灵感源泉,被赋予了“创造者”的特征。“如画”则介于“优美”与“崇高”之间,“没有优美和崇高那么强烈,但却值得重视”,其“前景应该变化多端——可由石头、农舍,或朴实的田园风光和家畜组成——并与平静的距离相对应。”(注:Gowing,L."A History of Art".Barnes and Noble Books.1995年版, 第750页。)“如画”所强调的“不规则性”和“随意性”也是现代性的。浪漫主义景观的代表是英国,这与其探险精神分不开。不仅英国风景画在西方首屈一指,而且英国小说中的景观意识也极为强烈,游记的创作与出版极发达,这种“文字景观”无疑也是西方最发达的。
六
西方游记中有关非西方文化和人际交往的描写也主要受科学和浪漫主义的影响。其中对人文现象的科学描写始终笼罩在环境决定论的阴影里。人文景观和当地人往往被作为自然环境或画面的一部分。如洪堡把拉丁美洲文化古迹描绘为美洲自然环境的产物。另外旅行家常常从西方人类学等角度把当地人作为一种自然物,提供所谓“人体景观”(bodyscape)的描述。非西方人往往不是被作为个体, 而是被作为一个类别的代表来对待。不少游记甚至把有关当地人生理特征的描写与对植物和动物的描写并列,或者当作统计资料列在书后附录中。作家往往把大量当地随行人员通称为“轿夫”或“肩夫”、“向导”等等,把他们一笔带过。对旅行家与当地导游的关系,旅行中的语言交流,当地人如何为西方旅行家组织旅程,如何以各种方式影响旅程都很少提及,似乎只有欧洲旅行家在观察浏览(注:Pratt,Mary L. "Imperial
eyes: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Routeledge,1992,第204页。)。即使在早期浪漫主义笔下,当地人也被描写成“高尚的野蛮人”(noble savage)。
描写人际交往较多的游记是所谓伤感游记( sentimental travelvriting)。 伤感游记在航海时期死里逃生风格的游记里已有雏形。在现代游记里则以更完善的浪漫主义的形式出现。伤感游记多使用第一人称和对话,多用主动语气,游记内容都与人物有关,景观描写不多。在描写人际关系时,西方旅行家和作家往往用浪漫主义平等互利的理想取代早期奴隶贸易时期的种族关系。历史地看,伤感游记与科学游记同步,二者不可分割,其共同基础是西欧启蒙主义,即科学、自由和平等互利的理想。因此旅行家把自己描绘得纯洁无辜,把自己女性化,使自己在性格上没有攻击性。伤感游记的一个主要题目是通过美化跨种族的爱情来使种族关系平等化,却很少问为什么这些浪漫的结合往往没有好的结果。(注:Pratt,Mary L."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transcultur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Routeledge,1992, 第204页。)同时这些游记也不能解释一个根本矛盾,即西方探险活动的根本上的侵犯性,也就是说西方旅行家为什么要背井离乡、游离他方。在一定意义上,传教可被视为伤感旅程的极端。传教文学中博爱精神与宗教偏见、对胜利的期待与失败的困惑的矛盾与伤感游记是相似的。这种结局包含在西方认识的出发点上,它与西方探险的流动性、暂时性分不开。
七
西方近现代游记在理想上主要受西方科学和浪漫主义的影响,但宗教意识也很强。即使科学性很强的游记在生死关头也常常提到神力的帮助。科学自然观和浪漫主义与“意匠论”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关系,往往互相促进,保持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同时西方殖民扩张也是游记内容的主要坐标之一。旅行家经常负有资本主义扩张的探路者( thecapitalist vanguard)的责任。 实际上“西方旅行家作家”的身份说明了西方游记的本质。由于西方作家仍是在用自己的语言、在自己的国家出版作品,为自己国家的人阅读,他(她)的旅程当然是环行的。也就是说他(她)并没有离开家园。实际上西方旅行家正是通过回乡、通过一种对所描写地方的逃避来维持他(她)的文字创作风格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的。这些旅行家常惧怕归程受到影响。这种逃避意识也构成近现代游记最致命的空间困境。
尽管游记是西方殖民主义文本的一部分,但与小说相比,游记叙述中非殖民性因素更多;这主要是因为它对空间性的依赖太大。游记多以自传的口气用第一人称写成,因此具有很强的时代性。这使游记的内容虽然很容易过时,被人们遗忘,但却能较真实地反映人与景观的关系。游记作家对其它地方的描写比对自己家乡的描写更坦率,所以会比文学自传更诚恳,更具洞察力。游记有自传的成分,目击者报道的成分,也有旅行见闻、回忆录、浪漫故事、散文及滑稽小说的成分,是一种用手头材料拼凑成的作品(bricolage)(注:Bishop,Peter."The myth of Shangri-La:Tibet,travel writing and the western creation ofsacred landscape."London:The Anthlone Press,1989.见该书第163页、3页、4页、4页、3页。)。所以游记在内容上要比小说丰富,可以说是一种多棱镜。与小说和其他作品不同的是游记是路上的产物,在游记中西方科学和浪漫主义的理想很难不遇到挑战。大部分游记中总有一些神秘的、为西方规范所不能解释或不愿看见的现象,使矛盾性成为西方游记的一个主要特征。难怪法素说“真正的旅行是充满讽刺的经历;最出色的旅行家和游记作家似乎是一些能够同时容忍两三个不一致的思想的人,或者说是既能当正人君子又能当丑角的人。”(
注:Fussel,Paul."The Norton Book to Travel." 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87,第14页。)索罗也认为: 证明自己原有认识是错误的, 这是旅行家的故事的本质。(注:Thereaux,Paul."Riding the iron rooster:By train through China"Ballantine Books,1998.)正是这些“不可解释的异常现象”使西方游记虽然受殖民主义的影响,却具有丰富的思想潜力。
游记所描写的地方有千差万别,写作的时代各不相同,同时不同旅行家背景、个性、经历也大相径庭。如旅行家中有的是传教士,有的是科学家,有的是探险家,有的是妇女,他们虽同属西方文化,对世界的看法却往往大不相同,反映了西方文化本身的多样性。但追求成功的探险家似乎总是被笼罩在失败的阴影里。那些没有留下游记的失败了的探险家如死于南极探险的司格特自不用说,即使成功者的游记中也常常流露出对失败的恐惧和为自己辩解的倾向,如发现了尼罗河源头的斯派克( Speke )与伯顿的矛盾和斯派克的自杀(注: Pratt, Mary
L."Imperial eyes: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New York and London:Routeledge,1992,第206页。),便仿佛揭示:空间的追求似乎与精神空虚分不开。换句话说,现代人的异化是一种空间的失落,是追求外部空间的代价,也是西方文明发展的必然性所在。
来稿日期:1999年10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