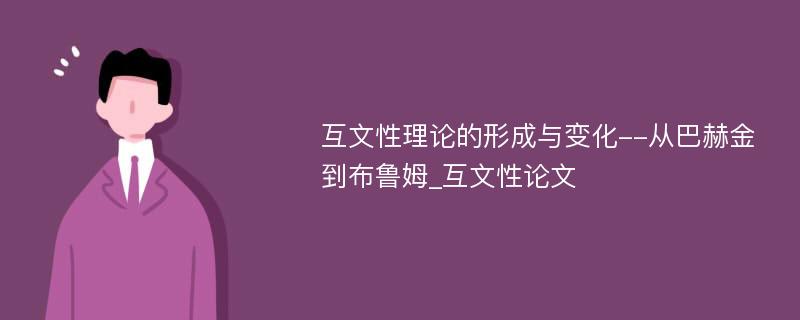
互文性理论的形成与变异——从巴赫金到布鲁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理论论文,布鲁姆论文,互文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9)04-0037-04
在西方已历经四十多年发展历程的文化研究,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学术界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它激发了当代学者的敏感点和兴奋点,在多本著作多篇论文中不断出现,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作为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正以其极大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人。但仔细阅读一些论文,发现许多人对“互文性”深有爱意,却并不明白其出身与来历,更不了解其发展与变化,本文即欲做一点基础工作,以备同行实用。互文性这一术语看似简单,实则极为繁杂。恰如蒂费纳·萨莫瓦约所言:“人们之所以常常不太喜欢互文性,那是因为透过互文性人们看到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庞然大物。”[1](P134)但无论人们喜欢与否,互文性在西方文论历史上确实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且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它在肯定和印证着传统的“引用”“模仿”等文本间关系的理论的同时,更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审视着文学艺术中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如文学的意义生成问题,文本的阅读与阐释问题,文本的边界问题,传统与创新的问题,文艺生产流程中的重心问题。可以说,它涉及当代西方几乎所有的文化理论和文艺批评实践。
互文性这一理论同其他所有的理论一样并非一蹴而就,在其形成的来路上有许多先行者,如英国作家亚历山大·蒲柏、T.S.艾略特等,其中产生了直接影响的是巴赫金。艾伦甚至这样评价:“在我看来,与其说互文性概念源自巴赫金的作品,毋宁说巴赫金本人即是一位重要的互文性理论家。”[2](P6)巴赫金认为,索绪尔关于语言/言语的分析显然忽略了语言的社会性,他对于“表述”有独到的理解:“表述已不是自然体和自然过程,而是历史事件,尽管是无限小的。”[3](P271)即“表述”总是包含人的具体“社会评价”,它具有两种属性:对话性和针对性。他认为任何一个“表述”都是对以往“表述”的应答——或反驳,或肯定,或补充,或依靠,即任何一个“表述”都具有对话性。可见,表述的开始,是对他人表述的应答;表述的结束,是对他人应答的期望,对话的张力就存在于整个表述之中,支配着整个对话,即使是独白语,甚至如科学著作,只要它期待被理解,它就是期望着应答,因而就具有对话性。既然表述总是两个主体的表述,即总是一个主体针对另一个主体的表述,表述的针对性便显而易见。也即只有当词语和句子处于上下文之中而具有了针对性时,才能成其为表述。巴赫金对表述/文本之间对话关系的思考,正是他的互文性思想的具体体现,这种展现了语言互动、制衡关系的理论的实质是“差异”(difference)和“他性”(alterity),而不是同一性和相似性。
巴赫金对于互文性的思考首先源于他的哲学思想。他认为“我”的存在是一个“我之自我”,“我”之外即是“他人”,作为主体,自我在存在中占据着不可替代、不可重复的地位,然而自我又是不完整而片面的,因为自我不可避免地有着盲区,而这个盲区却可为他人看见,如此看来,自我的存在决然离不开他者,自我的发展更需要借助他人的外位超视,“一个意识无法自给自足,无法生存,仅仅为了他人,通过他人,在他人的帮助下我才展示自我,认识自我,保持自我。最重要的构成自我意识的行为,是确定对他人意识的关系”[4](P88)。“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5](P344)。
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内涵就是关于互文性的问题,而这一理论更集中地体现在他关于小说“复调”理论的阐发中。巴赫金认为,传统的写作中,作者拥有着绝对的权威,而这一书写的霸权将人类生活本身的对话性遮蔽了,在作者独白式思维的控制下,一群沉默的奴隶毫无生气地被创造了出来,“他不是自由的人,他的思想被作者替代了,作者可以直截了当地代他思索;他的话语被作者打断了,作者代他说了,作者可以随意结束他的命运”[6](P43)。他因之极为看重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因其与一般的小说不同——即以其特有的“复调”性,与传统的“独白”小说区别了开来,他认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事件之中,相互不发生融合”[7](P1115)。
在巴赫金的作品中,“主角”这个词也很是独特,在理解巴赫金所创造和使用“主角”这一独特的词汇时,一定要明白它的真正内涵并非传统的典型形象和典型性格,而是一个有着独立和自由意识的个人,其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具有自我意识,他应当“不是无声的奴隶,而是自由的人;这自由的人能够同自己的创造者并肩而立,能够不同意创造者的意见,甚至能反抗他的意见”[8](P4)。唯其如此,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复调”,才能使作者与主人公之间、主人公与主人公之间的多种意识、多种声音的平等共存。可见,复调理论便是作者与人物之间和文本中人物之间互文性的具体体现。
“文学狂欢化”是巴赫金提出的又一具有互文理论意义的概念。根据巴赫金的考察,欧洲小说的始祖当为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认为真理产生于对话的交际过程中,并用“对照法”(将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观点加以对比)和“引发法”(以话激话,诱使对方阐发观点,以便发现漏洞,揭露其悖谬)的对话方式启发了后人,陀斯妥耶夫斯基正是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才合理安排情节,迫使自己的主人公讲话,构成令人信服的复调结构,而这种摒弃独白而欢迎对话的方式正是巴赫金竭力推崇的一种方式。对此,王逢振曾指出,“狂欢”是巴赫金独创的一个词语,“它丰富地涵盖了不确定性、支离破碎性、非原则性、无我性、反讽和种类混杂等等。……狂欢在更深一层意味着‘一符多音’——语言的离心力,事物欢悦的相互依存性、透视和行为,参与生活的狂乱,笑的内在性……”[9](P129)由此可见,“文学狂欢化”这一概念已具备“互文性”的基本内涵。
巴赫金已意识并谈到了“互文性”的内涵及作用,已具备了这一非常重要的思想,但他还未提出“互文性”这一概念,是克里斯蒂娃首创了“互文性”一词。克里斯蒂娃无疑是巴赫金的发现者,她综合索绪尔与巴赫金的语言观念,在丰富且发展了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同时,也为巴赫金的对话性、复调、狂欢等概念增加了新的维度,克里斯蒂娃在这一理论建构过程中的里程碑意义真是无人能比。与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米歇尔·福轲等人一道,在法国五月风暴的激励下,克里斯蒂娃,这位有着良好的天主教和马克思主义教育背景,兼容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保加利亚姑娘,迅速地成长并突显出了自己非凡的才华,《受限的文本》、《符号学:批判的科学和/或科学的批判》及《文本的结构化问题》等论文便是明证。
克里斯蒂娃在《受限的文本》中给“文本”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文本是一种超语言学机器,在此,瞄准的是交际对话与此前及同时的各种话语所发生的关系,并以此而重新分配语言秩序。因此可以说,文本是一种生产力。这一定义意味着:首先,文本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破坏——建立型的)再分配关系,人们可以更好地通过逻辑类型而非语言手段来解读文本;其次,文本是众多文本的排列和置换,具有一种互文性。”[2](P35)这就是克里斯蒂娃的文本观。她的文本观明显地与传统的文本观不同,她将文本看成是意义不断流动与变换的语言学机器,认为文本是一种生产力,且不知疲倦地操纵着主体,而文本的意义,只有当其与种种“超语言”实践相遇时——即与其它文本关联时才能充实起来。因此,按照克里斯蒂娃的理解,“互文性”就是指“文本的‘互文’特性”,“是说文本是由它以前的文本的遗迹或记忆形成”[2](P41),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拼凑,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参照物——镜子,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互相牵连,互相作用,形成一个无限开放的文本网络,构成一个由文本过去、现在和未来组成的巨大的文本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的演变过程。
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是对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的一种超越,它否定将文本当作一个独立自足体而仅对其进行共时性的研究的观点,认为文本不可能脱离其他文本而存在,任何一个文本实际上都先在地被叙述,它不仅仅是空间里的一个客体,更是时间里的一个客体,所以应当将文本放在历史与社会之中进行研究,而不要试图从单一的文本结构的关注中找寻到全人类作品的规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使束缚的链条被打开了,文本的意义则被无限地激活了。
克里斯蒂娃还对互文性的生成等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指出互文性实际上是增强语言和主体地位的一个扬弃的复杂过程,是为了创造新文本而无情地摧毁旧文本的否定的过程。克里斯蒂娃认为,语言学模式从索绪尔开始,经过结构主义的强化,已部分老化而失去效力,那种将能指与所指看作单一的线性关系并一味追求系统性的做法已无法回答语言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恰恰相反,主体是被投入一个巨大的互文性空间,被变成碎片或粉末,然后进入他或她自己的文本与别人的文本进行交流的过程中。这样,克里斯蒂娃便极大地消解了传统作品生成过程中作者的作用,而将“创造性”和“生产力”从作者转至文本的相互游戏。
总之,克里斯蒂娃以其无畏的胆识和气魄为“互文性”理论鸣锣开道,以其全新的观念让人耳目一新。
互文性理论的真正成形还要追溯到罗兰·巴特,他为互文性理论的宣传和阐释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1970年出版的S/Z一书中,他首先开始使用“互文本”一词,并借《通用大百科全书》的编写为互文本作了大力的宣传,用了近三万字左右的篇幅来介绍这个新词条,这是多么大的魄力和胆识啊。他无疑拥有一双慧眼。更为独特的是,罗兰·巴特与克里斯蒂娃关注文本的动态生成不同,他将互文性理论的研究重心明显地偏移到读者一边,以“作家”、“可写文本”、“愉悦”为互文研究的三部曲,正是在此意义上,他提出了“作者之死”,指出文学叙述不再是直接对现实发生作用,而读者才是真正参与文本的“表意实践”,其精髓在于崇尚阅读的乐趣和自由,并以一种独特的文本分析方法代替了他自己早期的“结构分析”。罗兰·巴特是一个具有着开放性思维和宽广胸怀的学者,正是有了他的支持与身体力行,互文性理论才真正走向它的辉煌。
在互文性理论的道路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还有布鲁姆,这位其“诗学误读理论”被伊格尔顿誉为“过去二十年来最大胆、最有创见性的一套文学理论”的耶鲁大学教授,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通过对互文性理论的心理阐释而提出一种新的诗歌理论。博采众家之长的布鲁姆以互文性确立自己的文本观,切入对文学史观的思考,并与大洋彼岸的法国文论家们一起创造并发展了20世纪的互文性理论话语。相对于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等法国理论家来说,哈罗德·布鲁姆对互文性的揭示有着更为大胆的推进,他赋予互文性以独特的动态意义。“在他之前,克里斯蒂娃、巴特等人都视互文关系为匿名的引用、静态的吸收。布鲁姆则正好相反,他的互文意味着卓越的诗人在与其前驱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2](P72)布鲁姆认为,前驱诗歌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其拥有“文本霸权”,这种霸权的性质相当于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社会霸权”或弗洛伊德所说的“心理霸权”;一切文本权力都伴随着一个强迫行为,一个所有权宣言。面对业已高高在上并一时难以撼动的前驱诗歌,后起者自我意识中强烈的姗姗来迟感导致不可驱逐的焦虑和恐惧,于是,后辈就在作品中以六种“修正比”对前驱作品进行误读,从而象征性地、仪式性地杀死前驱,为自己开辟生存空间。可见,与克里斯蒂娃不同,与巴特也不同,在布鲁姆这里,互文性表现为紧张的对峙、敌视和斗争关系,文本也不再是静态的语言符号的聚合体,而成了充满愤怒和喧嚣的战场,这就是变异与超越的具体体现。
互文性这个概念在克里斯蒂娃之后的使用可谓异彩纷呈,接过这个概念的理论家们均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对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修正和再阐释,甚至有些还可能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对立。学界的这种区分意味着互文性理论的开放性,并较为明显地呈现出了两个不同的走向:一个是解构批评,一个是诗学方向。前者以克里斯蒂娃本人理论的逻辑延伸和扩展,趋向于对互文性概念做宽泛而模糊的解释,关注如何通过“互文性”等手段去破坏文本的既定结构和认识范式,使所有的文本解读无限地指向边缘,代表人物有德里达、保罗·德曼和希利斯·米勒等;后者则脱离了克利斯蒂娃最初的意识形态批判意图,趋向于对互文性概念做精确的界定,使它成为一个可操作的描述工具,代表人物有热奈特、孔帕尼翁、里法泰尔等。
互文性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一个文学理论术语,究其实,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它高举着消解权威的大旗,强调发掘文本的诸多意义;“互文性的特点在于,它引导我们了解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使得我们不再线性地阅读文本”[1](P84)。从巴赫金强调文本中人物之间、人物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与狂欢的互文观,到克里斯蒂娃强调“文本是一种生产力”以及文本的历史性的互文理论,从巴特从接受主体角度着眼而认为读者才是文本意义生发的重要一环的互文观,到布鲁姆从创作主体出发而认为文学活动中充满着对峙与斗争的互文观,尽管其理论着眼点不同,理解的结果不同,但其解构传统的特点却极为一致。由此可见,在“互文性”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诸多学者做出了自己积极的理解、“误读”和建构,理解的角度与内涵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而这正是“互文性”这一理论的魅力所在。“互文性”的魅力还体现在这一理论的运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新近的一些论文中,学者们更将互文性这一理论扩展至绘画、音乐、舞蹈、广播、电影、电视、广告、互联网等研究领域,而互文性的具体表现也正为学者们不断发现,相信随着人们对互文性理论的不断关注,其意义和作用将更加突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