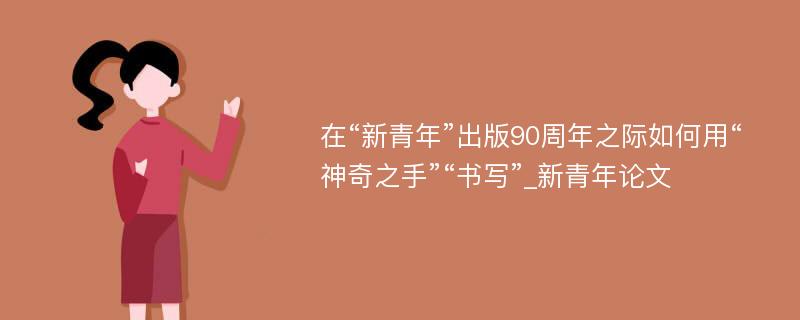
“妙手”如何“著文章”——为《新青年》创刊九十周年而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妙手论文,十周年论文,而作论文,新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谈及五四新文化人的气度,最容易想起的,自然是李大钊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此联语虽从明代忠臣杨继盛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演化而来,却因有李大钊等新文化人的生命做底色,显得十分妥帖。谈论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新青年》,应该着眼于“铁肩”,可也不妨关注“妙手”。
——作者
报刊业的迅速崛起,乃近代中国文学革命的关键因素。报刊面对大众,讲求浅近通俗,因而文章没必要、也不可能过于渊雅。另一方面,杂志无所不包,“总宇宙之文”,不同文体互相渗透的结果,导致文体变异乃至新文体的诞生。无论是梁启超之发起“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还是陈独秀的提倡白话文与新文化,都大大得益于迅速崛起的近代报业。
从文学史而不是新闻史、思想史的角度审视创刊于1915年的《新青年》,需要关注的,主要不是其政治主张或传播范围,而是其表达方式。将一份存在时间长达七年、总共刊行9卷54号的“杂志”,作为一个完整且独立的“文本”来阅读、分析,首先吸引我们的,是各种文体的自我定位及相互间的对话,还有这种对话所可能产生的效果。比起各专业刊物(如文艺杂志)的出现、各报纸副刊(如文艺副刊)的设置这样言之凿凿的考辨,《新青年》中不同文体间的对话、碰撞与融合,显得比较曲折与隐晦,需要更多的史实与洞见。
有“大体”而无“定体”
大凡精明且成功的报人,其心目中的理想文章,应该是有“大体”而无“定体”。那是因为,读者在变化,作者在变化,时局与市场也在变化,报章文体不可能一成不变。但万变不离其宗,主心骨不能动,否则东摇西摆,杂志很容易随风飘去。在这方面,陈独秀是老手,火候掌握得很好。胡适对陈独秀将编辑部转移到上海,以及搁下风头正健的新文学,转而介绍苏俄的政治革命很不以为然,那是因为胡适误解了陈独秀的趣味——自始至终,文学都不是仲甫先生的“最爱”。
蔡元培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撰写总序提及:“为怎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新青年》同人,大都认同这一思路。此外,坚硬的政论与柔和的诗文之间的互补,可以调剂谈话的氛围,丰富杂志的形象。《新青年》的一头一尾,政论占绝对优势,姿态未免过于僵硬;只有与北大教授结盟那几卷,张弛得当,政治与文学相得益彰。但即便是最为精彩的三至七卷,文学依旧只是配角。总共54期杂志,只有6卷2号将周作人的《小河》列为头条。负责6卷2号编辑工作的,正是一贯语出惊人的钱玄同。我怀疑钱玄同的编排策略,乃是希望“出奇制胜”,而不是颠覆《新青年》以政论为中心的传统。
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人,借助于版面语言,凸显议政、述学与论文,而相对压低文学创作,此举可以有以下三种解读:第一,“文以载道”的传统思路仍在延续;第二,《新青年》以思想革新为主攻方向;第三,即便“高谈阔论”,也可能成为好文章。表面上只是编辑技巧,实则牵涉到《新青年》的文化及文学理想。即便将眼光局限在“文章流变”,《新青年》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五四新文化人的“议政”、“述学”与“论文”,本身就具有“文章学”的意义。
五四新文化人何以选择白话文作为文学革命的切入口,组织易卜生专号意图何在,鼓动女同胞出面讨论“女子问题”为何没有获得成功,诸如此类大大小小的问题,只有放在政治史及思想史脉络上,才能得到较为完满的解释。可以这么说,《新青年》“提倡”新文学,确实功勋卓著;但“新文学”的建设,却并非《新青年》的主要任务。
“但开风气不为师”
“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一思路决定了《新青年》的注意力集中在“提倡”而不是“实践”。与陈独秀们唱对台戏的《学衡》诸君,正是抓住《新青年》的这一弱点,称“至吾国文学革命运动,虽为时甚暂,然从未产生一种出类拔萃之作品”(胡先骕:《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学衡》派的文学成绩乏善可陈,但胡先骕的责难其实必须认真面对。那是因为:“文学革命产生出来的新文学不能满足我们赞成革命者的期望,就如同政治革命不能产生更满意的社会秩序一样,虽有最圆满的革命理论,都只好算作不兑现的纸币了。”(胡适)鲁迅之所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专门提及《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一方面是承认“从《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回应社会上不绝如缕的批评。
正如鲁迅所说,“《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新青年》上,“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将诗歌、戏曲、小说列入“纯文学”或“文学之文”的范围,而将其他文字称为“杂文学”或“应用之文”,陈独秀、刘半农的这一“文学观”,日后影响极大。而我恰好认为,《新青年》的文学成就,不仅体现在白话诗歌的成功尝试,以及鲁迅小说的炉火纯青;更值得关注的,还在于《新青年》同人基于思想革命的需要,在社会与个人、责任与趣味、政治与文学之间,保持良好的对话状态,并因此催生出新的文章体式:“通信”和“随感”。
胡适说得没错,《新青年》上关于文学革命的提倡,“引起讨论最多的当然第一是诗,第二是戏剧”。但有趣的是,日后文学史家盘点《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实绩”,最为首肯的,却是小说和散文,而不是当年风光八面的诗歌和戏剧。
同气相求 众声喧哗
集合在“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大旗下的《新青年》同人,讲究同气相求,通力合作。这种同道之间为了某种共同理想而互相支持的精神氛围,既煮了不少夹生饭,也催生出一些伟大的作品。比如小说家鲁迅的“出山”,很大程度上便是这种“召唤”的成果。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提到《新青年》编辑“金心异”(指钱玄同)的再三约稿:“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为了慰藉先驱者,免得其过于寂寥,鲁迅终于不负众望,开始了“铁屋中的呐喊”。对于这段广为人知的“鲁迅诞生记”,另一个当事人钱玄同,在他的《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中,有十分精彩的描述。正是这种基于道义的共同参与意识,使得作为同人刊物的《新青年》,显示出很强的整体感。专号的经营,同题白话诗的出现,某些社会话题的不断重复,同一意象或题材在不同文体中的变奏等等,抚摩这半个多世纪前的旧杂志,你依旧能十分清晰地感觉到流淌在其中的激情与活力。
不是注重人际关系的酬唱,而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认准那是一件值得投身的事业,因此愿意共同参与。正是这种“共同参与”的欲望,支撑起《新青年》的“通信”,使之成为很可能空前绝后的“神品”。杂志设置“通信”专栏,并非陈独秀的独创;但此前此后的无数实践,之所以不若《新青年》成功,很大原因在于《新青年》同人全力投入,将其作为“品牌”来经营。
第三至六卷的《新青年》,其“通信”一栏五彩缤纷,煞是好看。这其中,陈独秀的个人魅力固然重要,钱玄同、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的加盟同样必不可少。比起简单地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同人之间的相互辩驳,更能促使讨论深入。即便推进“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大方向一致,在具体策略及实施方案方面,《新青年》同人间还是有不少分歧。于是,在“通信”栏中,展开了高潮迭起的论争——大到文学如何改良、孔教是否该批,小到《金瓶梅》如何评价,横行与标点是否当行,还有世界语的提倡、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等,几乎五四新文化的各个子命题,都曾在“通信”栏中“表演”过。
使用“表演”一词,并非贬低“通信”栏中诸君的高谈阔论,而是指向其刻意营造的“众声喧哗”局面,还有行文中不时流露的游戏色彩。确实是对话,也略有交锋,但那基本上是同道之间的互相补台。好不容易刊出火药味十足的王敬轩来信,可那又是虚拟的,目的是提供批判的靶子。也就是说,别看《新青年》上争得很厉害,那是有控制的“自由表达”。
“通信”:思想的草稿
《新青年》最具创意的栏目设计,非“通信”莫属。从文体学的角度考察《新青年》的“通信”,很容易想当然地上溯古已有之的书札。这种溯源不能说没有道理,“通信”所虚拟的私人性及对话状态,以及若干书札惯用的套语,在在提醒这一点。但这种“拟书札”的姿态,除了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更多的是为了获得独立思考以及自由表达的权力。换句话说,在《新青年》同人心目中,“通信”是一种“即席发言”,一种“思想草稿”。
作为留学生的胡适,“常用札记做自己思想的草稿”(《〈胡适留学日记〉自序》);而作为启蒙者的陈独秀、钱玄同等,则借用通信“做自己思想的草稿”。既然是“草稿”而非“定本”,不妨放言无忌,横冲直撞。《新青年》上最为激烈的议论,多以“通信”形式发表,如钱玄同之骂倒“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提倡《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以及主张“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等(参见钱玄同发表在《新青年》二至四卷上众多致陈独秀、胡适的信)。每期《新青年》上的“通信”,都并非无关痛痒的补白,而是最具锋芒的言论,或最具前瞻性的思考。一旦思考成熟,不衫不履的“通信”,便会成为正襟危坐的“专论”。对于不只希望阅读“思想”,更愿意同时品味“性情”与“文采”者来说,作为“专论”雏形的“通信”,似乎更具魅力。鲁迅建议“酌减”杂志上所刊“通信”的数量,可同时承认:“《新青年》里的通信,现在颇觉发达。读者也都喜看。”胡适晚年特别渲染陈独秀、钱玄同“二人的作品和通信”如何“哄传一时”。将“通信”从“作品”中析出,目的是突出陈、钱所撰“通信”影响之巨。
“通信”作为一种“思想草稿”,既允许提出不太成熟的见解,也可提前引爆潜在的炸弹。除此之外,“通信”还具有穿针引线的作用,将不同栏目、不同文体、不同话题纠合在一起,很好地组织或调配。在某种意义上,《新青年》不是由开篇的“专论”定调子,反而是由末尾的“通信”掌舵。
随感:褒贬抑扬,纵横天下
作为“后起之秀”,“随感录”专栏1918年4月方在4卷4号的《新青年》上登场。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随感”共27则,虽然比起独占鳌头的陈独秀(58则)还有一段距离,但还是遥遥领先于“季军”钱玄同(15则)。总共133则“随感”,陈、鲁、钱三君就占据了整整百则,单从数量上,都能清晰地显示《新青年》“随感录”之“三足鼎立”。更重要的是,比起前期偶尔露面的刘半农、周作人,或者后期勉力支撑的陈望道、周佛海,上述“三驾马车”,确实更能体现《新青年》“随感录”的特色。
在《〈热风〉题记》中,鲁迅曾这样描述其刊载于《新青年》上的“随感”:“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这段话初看十分低调,颇能显示当事人谦虚的美德。可细读之下,方知其大有深意——所谓回避“泛论”与“大事”,而从“具体而微”的“小事”入手,用嬉笑怒骂的笔法,褒贬抑扬,纵横天下,其实正是“随感”的文体特征。此类体裁短小、现实感强、文白夹杂的“短评”,虽有“究竟爽快”的陈独秀与“颇汪洋而少含蓄”的钱玄同等参与创建,日后却是经由周氏兄弟的苦心经营,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杂感”与“小品”,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上大放异彩。
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清报刊中,其实早已出现类似的篇幅短小、语带调侃的“时评”——比如梁启超的《饮冰室自由书》,但没有凝集为一种相对稳定且被广泛接受的文体。一直到《新青年》的“随感录”,方才将这种兼及政治与文学、痛快淋漓、寸铁杀人的文体,充分提升。政论与随感,一为开篇之“庄言”,一为结尾之“谐语”,二者遥相呼应,使得《新青年》庄谐并举。一开始只是为了调节文气,甚至很可能是作为补白,但“随感”短小精悍、灵活多变,特别适合于谈论瞬息万变的时事的特点很快凸显;再加上作家的巧用预/喻/寓言,“三言”联手,不难令读者“拍案惊奇”。
“随感录”的横空出世,不仅仅为作家赢得了一个自由挥洒的专栏/文体,更凸显了五四新文化人的一贯追求——政治表述的文学化。这一将文学工具化的思路,日后备受非议;可有一点不能忽略,搅动一池浑水,迫使众多文体升降与移位,这本身就可能催生出新的审美趣味与形式感。
谈论晚清以降的文学变革,思想史背景是个不能忽视的重要面向。只是落实到具体杂志,要不政治独尊,要不文学偏胜,难得有像《新青年》这样,“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齐头并进,而且互相提携者。而这一“思想”与“文学”之间的纠葛与互动,不只催生了若干优秀的小说与诗文,还丰富了政治表述的形式——《新青年》上的“通信”与“随感”,九十年后的今天,余香未尽,依旧值得再三回味。
标签:新青年论文; 文学论文; 钱玄同论文; 陈独秀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胡适论文; 文学革命论文; 鲁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