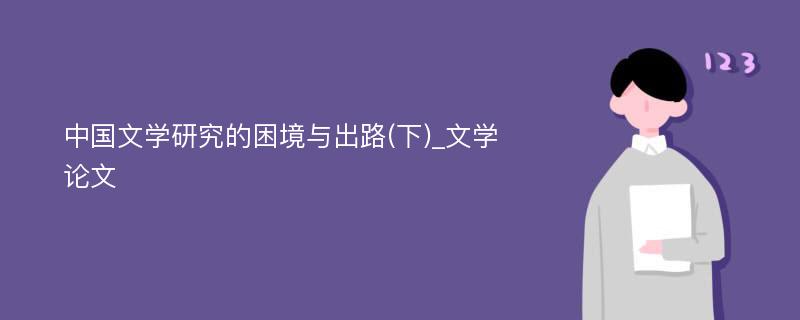
中国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出路论文,困境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例如《诗经·齐风》中有一首《鸡鸣》,描写一对男女的对话。女的说:晨鸡叫了,天亮了,朝会开始啦,快起来吧!男的却还赖床,说那不是鸡叫,天还没亮呢。诗分三章,层层递进,写得非常生动。(注:参阅拙著《白话诗经》第二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九三年),页263—267。)据《毛诗序》以及“三家诗”的说法,这首诗的主旨是陈述古代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宋代朱熹以前,大致相同,尚无异辞。可是越到后来,诗中男女的身分就越趋平民化。清代的姚际恒已经说作贤妃之辞固然可以,作大夫妻子之词亦无不可。民国之后,诗中的主角,阶级越来越低了。(注:如《诗经全译》,一九八二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初版。高亨《诗经今注》一书尤其如此。)似乎把书中主角的身分阶级降得越低,就越能提高这篇作品的价值。可是,这样的解释比起旧说来,究竟好不好呢?我们试看第三章有“会且归矣”一句,“会”字配合上文来看,和“朝”相承接,应指朝会而言,而且古人一般说来,是以“日中为市”,因此不采旧说,而认定诗中所写是一对劳动男女,事实上是值得商榷的说法。虽然说,这样诠释的背后,自有一套理论系统。但这套理论系统说不定可以适用于政治社会改革,却不适用于文学研究。读文学作品,太过强调意识形态,是不是合乎马克思的文艺审美观念,是值得商榷的。(注:参阅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第七章至第十四章。同兹依出版年月先后,列举数种如下:
郭英德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
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赵敏俐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王彬:《中国文学观念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
张全之:《突围与变革:二十世纪初期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学变迁》(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这些著作中,像《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示的思考》都很有参考价值,但偶尔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前者误用资料,将李渔《窥词管见》误为袁枚所著(见该书页581)等; 后者采用沈从文之说,误解温庭筠“小山重叠金明灭”词意(见该书页162)等等。)
据博厄斯《哲学与诗歌》一书说:“诗歌中的思想往往是陈腐的、虚假的,没有一个十六岁以上的人会仅仅为了诗歌所讲的意思去读诗”,这也是卢格讨论莎士比亚是不是戏剧诗人,竟以哲学体系的有无来作为评量的标准时,马克思要斥责他的原因。(注:G. 博厄斯《哲学和诗歌》,转引自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北京: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页113。)
因此,历来研究者在感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没有明确严谨的系统时,假使看到有自成系统的外国理论,不管它是否形式至上,或主张偏颇,或不适用于中国,或不适用于古代文学,就拿来强加套用,恐怕真的会“丧失了自我”而遭人非议了。(注:参阅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第七章至第十四章。同兹依出版年月先后,列举数种如下:
郭英德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
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赵敏俐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王彬:《中国文学观念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
张全之:《突围与变革:二十世纪初期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学变迁》(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这些著作中,像《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示的思考》都很有参考价值,但偶尔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前者误用资料,将李渔《窥词管见》误为袁枚所著(见该书页581)等; 后者采用沈从文之说,误解温庭筠“小山重叠金明灭”词意(见该书页162 )等等。冯至《要慎重使用西方的文学术语》一文也主张“不要过多地搬用西方的一些文学术语来评论或区分我们的文学,这样容易产生误解,而且会使很多问题搞不清楚。”见《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页231。)
四
接着,我们再谈研究方法。
谈研究方法,当然跟上述的文学观念、理论系统不能没有关系。他们是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的。而且,谈方法更不能离开研究的对象。假使对研究的对象没有充分的理解,那么所谓研究方法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文学虽然朝着新时代的文学方向发展,但就文学研究而言,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却是一个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关键时期。在此之前,西学虽已东渐,但旧学余波尚在。例如林传甲在一九○四年所写的《中国文学史》,(注:参阅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页 197;郑方泽:《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陈鸣树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仍然采用传统的“大文学”、“泛文学”的观点,所论不但包括经史子集,而且还有音韵训诂、金石书法和文法修辞等等。从现代人的文学眼光来看,这实际上是一本国文讲义,而非探讨中国文学真相的文学史。过去,大家都说林传甲这本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现在我们根据资料,知道在林传甲之前,有窦警凡在一八九七年所写的《历朝文学史》,(注: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黄山书社,一九八六年)云: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此书体制上似不属文学史著作)脱稿于一八九七年,早于林传甲所著《中国文学史》(一九0四年)。陈氏所言,系据刘厚滋《中国文学史钞(上)》一书所述。)跟林传甲同时或稍晚的,还有黄人、曾毅、谢无量等人的相关著作。(注:同参阅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页197; 郑方泽:《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陈鸣树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黄山书社,一九八六年)云: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此书体制上似不属文学史著作)脱稿于一八九七年,早于林传甲所著《中国文学史》(一九0四年)。陈氏所言,系据刘厚滋《中国文学史钞(上)》一书所述。黄人《中国文学史》约一九0九年由国学扶轮社印行;曾毅《中国文学史》一九一五年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印行;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一九一八年由中华书局印行。清末民初的文学史著作尚有多种,不赘举。)这些著作有的受了日本学者的影响,有的偶而采取欧西学界的一些论点,但基本上还是以传统的观念为主,方法上几无突破之处。(注:像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前记中自称“将仿日本久保天随、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例,家自为书”,而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一第一编第一章第二节亦偶引“欧洲白鲁克”等人之学说。同参阅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页197; 郑方泽:《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陈鸣树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黄山书社,一九八六年)云: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此书体制上似不属文学史著作)脱稿于一八九七年,早于林传甲所著《中国文学史》(一九0四年)。陈氏所言,系据刘厚滋《中国文学史钞(上)》一书所述。黄人《中国文学史》约一九0九年由国学扶轮社印行;曾毅《中国文学史》一九一五年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印行;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一九一八年由中华书局印行。清末民初的文学史著作尚有多种,不赘举。)
可是从二三十年代开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文学的研究,在很多方面有了新转变和新突破。譬如一九二八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一九三二年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及稍后的一九四一年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等,(注:同参阅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页197;郑方泽:《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吉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陈鸣树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郑振择《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对此颇有论述,见其《中国文学论集》(上海开明书店,一九三四年),页1—41。 )都已经撷取了新文学新观念新形式新方法,赋予了中国文学史新的面貌。
不但中国文学史如此,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论著,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端的。试看下列诸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刊行年代: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九二七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九三四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注:同参阅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页197;郑方泽:《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吉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陈鸣树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郑振择《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对此颇有论述,见其《中国文学论集》(上海开明书店,一九三四年),页1—41。 )虽然这些著作,在研究方法与治学态度上,尚有可以商榷之处,但它们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纪元,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我以为除了中国文学发展本身已经到了不能不变的因素之外,还跟清末民初以来新文化新思潮的不断冲击,大有关系。特别是当时一些著名学者,像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人,提倡新观念新方法,使研究者竞相效法,更有关系。所谓历史的归纳法,所谓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所谓中西会通,所谓二重证据,都使真正的中国文学研究从此拉开了序幕。(注:陶曾佑一九○七年作《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梁启超一九○二年作《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仅是笔者信手拈举的例子而已。当时标举小说的人,不胜枚举。参阅赵敏俐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二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郑大华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十大学问家》第一章(青岛:青岛出版社,一九九二年)、蒋英豪《近代文学的世界化》(台北:台湾书店,一九九八年),页151—170。《庄子·外物》所说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小说”与“大达”对举,此与《论语·子张》所说的“小道”,自是同义之辞。而东汉桓谭《新论》所说的“合残丛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据李善注《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杂体诗《李都尉从军》注引),则是以“短书”与高文典册相对。皆可徵见古人对小说并不重视。参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其它如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等等,并可参看。所引诸书,并请参阅。)
梁启超自己写的文章,“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文法”,不受传统古文约束,而在研究方法上,则以历史的归纳法、进化论的观点整理国故。他特别强调小说的社会功能和美文的文学价值,对于新文学的开创,自有推毂之功。王国维深受尼采、叔本华悲观哲学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以丰富的学养,“取地下之宝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注: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将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概括为三种,“一曰取地下之宝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古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第一种方法,王国维自称为“二重证据法”;第三种方法,下述《红楼梦评论》等文艺批评之作,皆属之。参阅《王观堂先生全集》(台北:文华出版公司,一九六八年)。)不但在经学史学上,有突破性的创获,就是在文学评论方面,如《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等,也都令人有登高望远、耳目一新之感。鲁迅是民初一大作家,但做起文学研究来也一丝不苟。他曾经接触培根、笛卡儿等人的逻辑思想,所写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曾参考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却能自成体系。(注:鲁迅一九0八年所作《科学史教篇》中,曾对培根(培庚)、笛卡儿(特嘉尔)的逻辑思想加以比较,而且在《华盖集续编·不是信》中,也说他写《中国小说史略》,参考了日本学者盐谷温的著作。上引资料,分别见于《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一册页25及第三册页221—241。)胡适则是提倡白话文的大将,主张“八不主义”,主张“采用西洋最近百年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来改良戏剧,主张用冷静客观的态度来整理国故,并且用历史演进法来考证旧小说。他对“五四”之后的新文学运动,贡献之大,是不容抹煞的。这些著名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影响是深远的。(注:同陶曾佑一九○七年作《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梁启超一九○二年作《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仅是笔者信手拈举的例子而已。当时标举小说的人,不胜枚举。参阅赵敏俐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二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郑大华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十大学问家》第一章(青岛:青岛出版社,一九九二年)、蒋英豪《近代文学的世界化》(台北:台湾书店,一九九八年),页 151—170。 《庄子·外物》所说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小说”与“大达”对举,此与《论语·子张》所说的“小道”,自是同义之辞。而东汉桓谭《新论》所说的“合残丛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据李善注《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杂体诗《李都尉从军》注引),则是以“短书”与高文典册相对。皆可徵见古人对小说并不重视。参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其它如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等等,并可参看。所引诸书,并请参阅。胡适引文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页662。 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一书亦可参考。)
可惜的是从四五十年代以后,本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却因为时代的遽变、政治的限制等等因素,分别在不同的华人地区分道扬镳,而各自发展。大陆地区,大多数的学者运用苏联理论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利用其中唯物辩证法和阶级矛盾的观点,来诠释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很多论著,今日看来,不难看到“不同程度地存在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注:见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页22。)文革以后文学大门又开放了,八十年代前后各式各样的新观念新理论及所谓“方法热”纷沓而来。(注:参阅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第七章至第十四章。同兹依出版年月先后,列举数种如下:
郭英德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
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赵敏俐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王彬:《中国文学观念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
张全之:《突围与变革:二十世纪初期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学变迁》(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这些著作中,像《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示的思考》都很有参考价值,但偶尔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前者误用资料,将李渔《窥词管见》误为袁枚所著(见该书页581)等; 后者采用沈从文之说,误解温庭筠“小山重叠金明灭”词意(见该书页162)等等。)
相对于大陆,台湾香港与海外的中文学界,除了延续传统文学研究之外,在不同时代流行了不同的外国文学理论及方法。好处是使旧文学可以推陈出新,有了新生命;坏处是有时削足适履,过于穿凿附会。空谈理论,侈论方法,与传统之过于徵实尚质,其失维均。
总的来说,有两个趋势值得注意;一是研究者的旧学根柢越来越低落了,一是恰好相反,研究者越来越接受西方文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这两个趋势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困境。
我以为:没有一种理论或方法是万能的,每一种方法都有其限制。因此,讲方法不能离开他的本体,否则就不一定适用了。(注:陈寅恪曾说:“不把基本材料弄清楚了,就急著要论微言大意,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此据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四年),页22。《文学遗产》一九八五年第三期“研究方法与研究态度”专号上,章培恒也说:“如果是从事先设定的框框出发,无论在研究方法上怎么改变,都没有多大意义。”)譬如说,王国维善于运用“二重证据法”,“取地下之宝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那是因为他本来就对“纸上之遗文”有广泛而深刻的认识,所以一旦有珍贵罕见的“地下之宝物”出土问世,他才能立刻取来“互相释证”。否则对出土的文物只能做猜谜游戏而已。清末民初以来,殷周卜辞、钟鼎彝器、简牍帛书以及敦煌抄卷等等古代文物相继出土问世,不少研究者只看到王国维等人的新发现新创获,却不问学问根柢,只谈理论方法,致使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多流于主观的臆测。就中国文学研究而言,即有人运用这种方法到旧诗词的诠释上,由于对原典的了解未必正确或解释不够周全,因而发生了不少值得商榷的问题。
例如唐代宫廷画家张萱有《捣练图》,宋徽宗曾加临摹,画的是用杵正捣练丝的华服丽人,有人却用来解释李白《子夜吴歌》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事实上捣练和捣衣是不同的。捣制练丝和捣洗衣裳怎么会一样呢?这和六朝唐宋诗词中常用“玉”来形容阶梯一样,怎么能说“玉阶”、“玉梯”都是真玉所砌呢?(注:见黄永武《珍珠船》中《与君同赏捣衣声》及《读书与赏诗》(台北:洪范书店),页 110。)例如一九六八年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的古墓中,发掘出保存完整的“金缕玉衣”之后,有人即用来解释唐代杜秋娘的《金缕衣》一诗,事实上,“劝君莫惜金缕衣”的金缕衣,泛指金色丝线所制成的华贵衣服,不一定指真的黄金丝缕。(注:参阅《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0年);杨牧《惊识杜秋娘》,见《中外文学》第一卷第十期,一九七三年三月。)又例如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利用宋人所摹唐代妇女画像及出土的唐代文物,将温庭筠《菩萨蛮》第一首的“小山重叠金明灭”解释为妇女头饰的妆成之美,有些研究者还加以引用,说是“别出新解,言之成理”。事实上这种说法不始于沈从文,而且大有商榷的馀地。(注:参阅拙作《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相关问题辨析》(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中文学刊》第一期,一九九七年),页121—149。“别出新解,言之成理”,语见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一书,页162。)
二重证据法之外,还有学者提出三重证据之说。就是在纸上遗文、地下宝物之外,还加上田野调查或文化人类学等等方法。闻一多的《伏羲考》、《说鱼》等文,就是其中著名的例子。(注:参阅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第八章“二重证据法与三重证据法”。同参阅拙作《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相关问题辨析》(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中文学刊》第一期,一九九七年),页121—149。“别出新解,言之成理”, 语见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一书, 页162。)对学术研究的努力与用心,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但研究的结论是否都适切,则尚有讨论余地。像闻一多所说《诗经》中的“鱼”字,大多与“性”、“配偶”有关。(注:参阅《闻一多全集》第三册(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说鱼》(页231—252),《伏羲考》(页58—131),《诗经的性欲观》(页169)。)我就觉得这种说法不妨暂时存疑,再看看有没有其他更坚实充分的证据。
更糟糕的是,因为新出土文物普遍受到肯定,竟然有人伪造假古董。《坎曼尔诗笺》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注:“坎曼尔诗笺”事件始末,参阅杨镰《〈坎曼尔诗笺〉辨伪》一文,见《文学评论》双月刊,一九九一年第三期,页4—16。诗笺作“诗签”。 )《坎曼尔诗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新疆博物馆某工作人员的伪作,把三首语意浅白意境不高的假“唐诗”抄在残纸上,署“坎曼尔”在元和十年所作。奇怪的是这假文物一九七一年在北京故宫展览不久后,郭沫若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即写了《坎曼尔诗笺试探》,发表在《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二期,肯定它的价值;刘大杰一九七六年在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也把它引述进去了,并且说第三首“揭露了大官僚残暴压榨的罪行”,说这是“维吾尔族”人的作品,是“难得的兄弟民族的史料”。(注:见刘大杰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页21。)除此之外,孙望《全唐诗补逸》、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以及中华书局《全唐诗外编》都先后收入。最后经杨镰多次深入调查和考证,才确定这些作品竟然是伪作。(注:“坎曼尔诗笺”事件始末,参阅杨镰《〈坎曼尔诗笺〉辨伪》一文,见《文学评论》双月刊,一九九一年第三期,页4—16。诗笺作“诗签”。 )他所用的辨伪方法,正是三重证据法。
至于应用外国新理论新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固然有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等成功的例子,但令人难以信服的事例也不少见。如在台湾流行以英美新批评、弗洛伊德学说研究中国诗学时,颜元叔解释王融的“思君如明烛”和李商隐的“蜡炬成灰泪始干”,说烛炬是男“性”的象徵,就引起不少讥弹。(注:见叶嘉莹《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中外文学》第二卷第四、五期,1973年;颜元叔《何谓文学》(台北:学生书局,一九七六年)书中《现代主义与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前瞻》等文。)大陆也一样,有人在研究《楚辞》或神话传说时,只要看到有男女的字眼或所谓性隐语时,就拿弗洛伊德的学说方法去套。(注:见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页364。 )关于这些问题,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有一段话说的好:
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文学史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或中国文学史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注: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0年),页223、224。)陈寅恪的这段话,虽然原是针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但也可以衍用到其他外来理论方法上。对文学理论方法来说,我们应该有个信念:输入不可耻,输出也不必骄傲。我们只问适不适用。这跟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享用外地物品及舶来品的道理是一样的。因此,适不适用才是重要的。像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法国侯思孟教授就以为不适用于中国古典诗词。(注:见刻《文学遗产》一九八九年第四期,《中国文学深刻地嵌入中国历史——法国侯思孟教授答本刊问》一文。他认为中国文学植根于中国历史之中,而中国诗人又非常“自传式”,欲知其诗歌内容,不能不紧扣此一特点进行研究,此非西方批评方式如新批评、结构主义者所能适用。)
清末民初以来,很多学者受进化论的影响,误以为一切文学的发展,也应该不断的“进化”。假使研究者抱持著这样错误的想法,其研究结果也就令人不能无疑了。像上述刘大杰一九七六年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为了迎合时尚,把伪造的《坎曼尔诗笺》收了进去,加以申论,同时把当时儒法斗争的思潮在书中也多所引申,结果,修订本的可信度反而不如旧版。研究者假使无视于此,误以为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一定后出的比以前的好,那就贻笑大方了。或许刘大杰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态度上没有错,但理论无穷,方法有限,用错了理论和方法,结果还是错的。
至于只讲求方法、空谈理论,只在表面下工夫的人,钱仲联有一段话批评道:
只有博览和精熟,才能纵览全局,有所比较,发现矛盾,有所判断,对某些问题,有所突破。作为一个真才实学的人,这要的是刘知几所说的“才学识”。那些为了一个问题,写考定文字,临时翻检一些工具书或相关的材料,拼凑成篇,看似“渊博”,实在不过“外袭”,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我对我自己和指导学生,常引此为诚。(注:见钱钟联《治学篇》一文,《梦苕菴论集》(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页539—543。)钱仲联的这一段话,对于那些以为做学问只是制卡片、查工具书、附脚注的所谓研究者,应该有一定程度的针砭作用。
五
最后,谈谈在困境中如何寻找出路。
研究学问,重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光是讲求观念、理论和方法是不够的。如果学问的根柢不深厚,治学态度不严谨,即使观念厘得清楚,理论能有系统,方法符合科学,一样会犯蹈空之失。
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来说,原典的解读是一项不容易的工作。没有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基础训练,想要准确地了解作品的本意,几乎不可能,除非依赖别人的翻译和解释;不能运用目录、版本、校勘等文献学方法,想要全面掌握材料的原始面貌,也几乎不可能,除非依赖别人提供资料或已经有了完善的本子。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的学者,大致说来,学问根柢都很札实,对国学古籍都不陌生,所以一旦接触到外国传进来的新学问,往往能即时取人之长,融会贯通。五十年代以后,一般研究者旧学根柢逐渐浮薄了,趋新而忘本的人越来越多,空谈理论,侈言方法,对研究的对象,可能原典读不懂,背景不了解,却不以为意,他们只是一味求新。一味求新的结果,是对中国古典文学越来越陌生了。
我们回顾清末民初以来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潮流走向,可以发现有不少人以为清末民初以前,传统研究的方法是欠缺的,观念是落伍的。甚至认为传统的传笺注疏以及目录版本校勘等文献学方法,不是科学方法。虽然这些传统文献学方法,有时真的过于拘守考据,“误把作诗当抄书”,就像朱自清所说的,“把诗只看成考据校勘或笺证的对象,而忘了它还是一首整体的诗”,“目无全牛,像一个解剖的医生,结果把美人变成了骷髅”。(注:王瑶转述朱自清论诗之语。见王瑶《邂逅斋说诗缀忆》,《文学杂志》第三卷第五期,一九四八年。)不过,这是就其弊端来说的,如果我们愿意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的话,传统的理论方法未必一无是处。
我们应该注意到旧学根柢深厚的人,谈西方新科学,他们或许不懂,但谈中国旧学问,他们自然在行,有不容怀疑的理解力。他们虽然不擅长于长篇大论,作结构严谨、系统分明之归纳分析,但他们是“高人交手,一点就透”的,不必费什么唇舌。古人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注:参阅拙著《清代文学批评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九八年),《清初诗学中的形式批评》,页30—67。)所谓“金针暗度”,道理就在于此。他们未必没有推理的过程,未必没有诠释的方法,只是没有和盘托出而已。金圣叹批《杜诗》、批《水浒》、《西厢》,现代人比较推崇,是因为他肯“授人金针”,“授人指头”。就像肯把吕祖点石成金的指头授给穷者一样,金圣叹肯把推论的过程,分析的方法,传授给腹笥俭啬、没有分析能力的读者。同样的道理,现代人比较推崇叶燮的《原诗》,也是因为它系统比较分明,结构比较完整,说理比较详尽。(注:参阅拙著《清代文学批评论集》中《叶燮〈原诗〉研究》一文,同参阅拙著《清代文学批评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九八年),《清初诗学中的形式批评》,页73—112。)事实上这跟清末民初以来, 文学读者由贵游士人转为庶民群众有关,没有文学的专业知识和创作经验,自然需要剀切的指导、详尽的说明,而不是三言两语式的指点。我们看陈世骧析论杜甫《八阵图》五绝二十个字的一首诗,要用一万多字来分析说明;我们看叶嘉莹老师赏析旧诗词,也动辄数万言,其道理皆在乎是。(注:见陈世骧《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一文,收入《陈世骧文存》(台北:志文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页127—149。此系一九五八年六月在台大文学院之演讲稿。至于叶嘉莹老师的著作,读者所习知,此不赘举。)
不过,要做到上述所言,也必须深造有得之人,才能办得到。不是浅学之士或托言感悟触发,或乱套一些批评术语,来自欺欺人,就可以示人津筏。深造有得,说起来容易,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却极困难。真正的深造有得,不但需要学养深厚,处处留心,而且更需要头脑清楚,态度客观。具备了这些条件,即使没有受过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不懂得什么时髦的文学理论,也一样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譬如说通行本的《战国策·赵策》有“左师触詟愿见太后”的一段文字,历来选本多题为“触詟说赵太后”。(注:如姚鼐《古文辞类纂》即是。)清代学者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据《荀子》、《史记》、《汉书》、《太平御览》等书,互相参证,认为“触詟”仅“触龙言”之误,当从《史记·赵世家》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王念孙从上下文理这样下判断说:“太后闻触龙愿见之言,故盛气以待之,若无言字,则文意不明”。(注:见王念孙《读书杂志》(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三年)第一册卷一,页99。)王念孙的推论,现在得到证实了。一九七三年冬,马王堆三号汉墓发掘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帛书中,正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这帛书的成书年代在刘向编订《战国策》之前,(注:参阅《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主编。页 427。此帛书抄写时间,据考证在汉文帝初年以前。)因此可以推测是《战国策》传本误将龙言合为“詟”字。我们由此可以看出王念孙读书的用心和推论的正确。
又譬如说,《诗经》中有“以介眉寿”(《幽风·七月》)、“以介景福”(《小雅·楚茨》)、“以介我稷黍”(《小雅·甫田》)的句子,起先大家都不知道“介”字应作何解。林义光根据铜器铭文屡见的“用匄眉寿”、“用祈匄眉寿”,“匄”即丐,当祈求讲,来解释《诗经》中的“介”字,破解了大家的疑惑。(注:见林义光:《诗经通解》(台北:中华书局,一九七一年),页101。 据该书自序,此书著成于一九三○年。)同样,《楚辞·天问》中有“该秉季德”、“恒秉季德”等语,历来大家都不知“该”“季”“恒”等字何解。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根据甲骨卜辞发现殷商先公有“季”、“王亥”、“王恒”等名,因而把这些句子都讲通了。(注: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此文著成于一九一七年。《王观堂先生全集》(台北:文华出版公司,一九六八年)。)试想林义光、王国维等人,要不是学问根柢深厚,处处留心,对《诗经》、《楚辞》读得精熟,如何能够在看到铜器铭文、甲骨卜辞等相关字眼,就能够即时挑出来加以应用呢?本世纪以来,很多学者用心于讲求理论方法,研究上却很少突破性的创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这样深厚的学问根柢。
除了学问根柢之外,治学的态度也非常重要。假使态度不严谨,不客观,再新的理论方法都没有用,不可能有好的研究成果。譬如说,汪辉祖是清代乾隆年间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可是在编《史姓韵编》的时候,一时不小心误把旧刻本《世说新语》的题款“临川王义庆”,读为“临川、王义庆”,因此把“刘义庆”立目为“王义庆”,传为笑柄。(注:见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页143。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例子。
又譬如说,明代前后七子都是主张拟古的,他们认为学问今不如古,所以主张创作要规弇古人的作品,尺尺寸寸,学习他们的长处。现在通行的中国文学史或中国文学批评史,常用两句话来概括他们的理论主张,就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注:自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以下,几乎所有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都采取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通行已久,很多研究者已经习焉而不察了。事实上这种说法也有根据,系出于《明史·文苑传》。但只要我们稍微严谨小心一些,就可以发现《明史·文苑传》的《李攀龙传》说的是:“其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注:参阅《明史·文苑传》(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五年),《李攀龙传》、《王世贞传》等。)连王世贞自己写的《哭李于鳞》一诗也说:“文许先秦上,诗卑正始还”。(注:见王世贞《弇州山人诗集》卷三十,《哭李于麟一百廿韵》,此据香港中文大学藏光绪三十三年刊本。)可见他们共同主张是:古文要学秦汉以前,诗则分体,近体要学盛唐以上,古体要学汉魏以上。这样才符合他们崇古卑今的文学观。(注:拙著《清代诗学初探》第一章、《清代文学批评论集》页76,皆早已论及。请读者参阅。)
治学态度除了力求严谨之外,还要力求客观。有的批评家或研究者,一旦选定了研究对象,就夸大这个研究对象的价值,甚至对古人作过度的同情。“了解之同情”是应该的,但不可滥用。譬如,李清照有没有改嫁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要提证据,不应该先存有成见。因为李清照改嫁之事,宋人的记载,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以及南宋大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八等等,都言之凿凿,应该事出有因。(注:参阅何广棪《硕堂文存三编》(台北:里仁书局,一九九五年),《再论李清照之改嫁》,页45—48;叶庆炳:《晚鸣轩论文集》(台北:大安出版社,一九九六年),《文学史上的辨诬与同情》,页61—81。)可是却有人(像朱泙漫的《李清照丛考》)(注:朱泙漫《李清照丛考》对主张李清照改嫁的学者批评得体无完肤。资料收集尚称完备,讨论态度则殊不客观。)不作理性客观的讨论,一味斥骂“李心传妄注”、“王灼狂吠”、“胡仔卑劣”等等,用了很多情绪化的语言,却提不出什么反对的证据。这样的讨论不客观,这样的“研究”成果让人不敢领教。
以上,都在说明学问根柢和治学态度的重要。从事中国文学的研究工作,想要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想要在遇见困境时找到出路,舍此而莫由。虽然说它们只是解决问题、寻找出路的先决条件,没有它们问题就无从解决,困境也会更多。“山重水复疑无路”,未必“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文学创作,表现的是作者的才情;文学研究,要求的是研究者的思辨能力。前者重在性灵流露,后者重在书卷酝酿,不过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光有思辩能力,光有书卷的酝酿,似乎还不够。譬如说,你想要研究旧诗词,不是光是搜集参考材料,光是应用一些理论和方法,就可以获得好成果的。最好是你自己还要有创作旧诗词的经验,这样你才更容易体会作者创作的甘苦,也才容易判断批评者的批评是否得当。上文所说的,观念要厘清,理论要分明,方法要落实,根柢要深厚,态度要客观,都是研究者不可缺少的条件,但如果缺少了对古典文学的“了解之同情”,而想要有更大的突破,更新的发现,则似乎终隔一层。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固然如此,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及其他研究论著,也应该如此。朱熹《鹅湖寺和陆子寿》诗有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这可以说是我们从事中国文学研究者应该追求的目标。旧学钻研,求其邃密,已极困难;汲取新知,求其深入,更是谈何容易!可是,路是人走出来的,即使这条路困难重重,寂寞难行,凡我同志,为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岂可不勉力以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