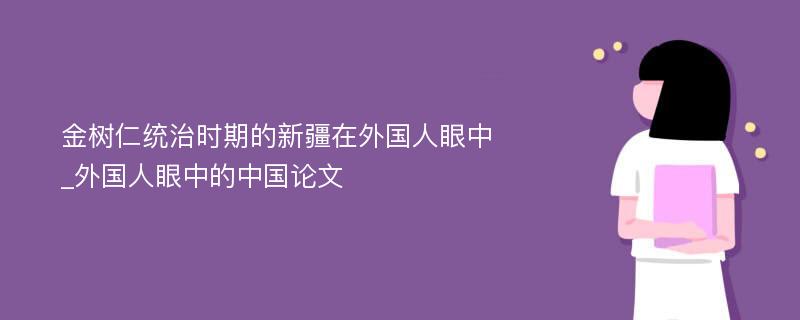
外国人眼中金树仁统治时期的新疆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疆论文,外国人论文,眼中论文,时期论文,金树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9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30(2008)06—0123—08
19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在殖民扩张等因素的影响下,西方对新疆的关注程度日益加深,有关新疆研究的著作不断涌现,从而掀起了西方人到新疆考察的高潮。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疆研究已经成为西方中国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有学者指出,步入20世纪后,随着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的不断高涨,西方国家的新疆研究濒于末路。甚至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除了欧文·拉铁摩尔(Oven Lattimore)和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外,很少有西方人将研究目光对准新疆②。
然而笔者认为,进入民国以后,外国学者并没有放弃对新疆的关注,没有停止对新疆的考察,西方国家也没有减缓对新疆的侵略步伐。相反,当时英国侵略西藏,俄(苏)长期以来侵占并分割中国北部边疆,特别是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使中国又陷入新的边疆危机之中。而这时的新疆正处于英、俄(苏)、日等列强的争夺当中,他们的势力此消彼长,使新疆始终处于动荡和危机之中。因此,随着英、俄(苏)、日在新疆争夺的日益激烈,阿富汗、土耳其、法、德、美等国对新疆事务的觊觎和染指,西方国家更加重视对新疆的考察和研究;欧美各著名的研究机构、博物馆和收藏家的需求促使西方文物市场再次繁荣,“丝绸之路热”、中亚考古探险和攫获文物持续升温,这也刺激了许多考古学者、探险家来新疆进行探险、考察;西方中国学尤其是新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一些外国公司在新疆拓展市场的需求③,亦使得不少学者在政府、学术机构或企业的资助下,来新疆进行考察和研究。就笔者所知,对金树仁时期到新疆探险、旅游、传教、工作的外国人,或者从他人著述中了解到新疆的外国人是如何描述新疆的这一问题,目前尚无系统的研究及论述。下面就这一时期外国人对新疆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作一简单的概述和分析,遗漏和不当之处敬请不吝赐教。
金树仁主新时期,聚集在新疆的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包括外交官、商人、职业情报贩子、传教士、探险家、旅行家、学者和从不同角度对中国这个边远省份感到兴趣的人物。其中探险家、旅行家、学者扮演了这一阶段新疆考察行动的主要角色,他们向其服务的机构提供有关新疆的发展史、政治、军事、地理、民族、宗教、交通、贸易、文化、气候等各个方面的参考资料。当时,来新疆考察的中外学术团体及个人就有五起之多④,如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法学术考察团、斯坦因考古队、美国苔利摩等五人以私人身份到新疆探险以及英国陆军中校司蒂华特到新疆探险。这些学术团体及个人的考察活动,有的是外国单方资助的,有的则为中外联合主办。因为金树仁认为其动机和行为十分可疑,所以总是设法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因而,这些考察团及个人原拟在新疆的活动计划,都由于金树仁的限制而没有全部实现。然而,正是这些考察活动,不少参与其中的外国人的沿途记录(日记、游记、实地采访)和他们回国后撰写的回忆录,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外国人眼中的新疆⑤。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外国学者非常关注对新疆的专门研究,他们或到新疆亲自进行调查研究,或参考国内外学者的著作、论文,甚至查阅相关的档案、文件,写下了不少关于新疆的论文。在他们的文章中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他们对当时新疆政治、社会的一些听闻和看法。当时国内学者将他们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发表于报刊上,这成为我们了解外国人心目中新疆的另一个重要窗口⑥。
首先映入这些探险家、旅行家和学者眼帘的是新疆美丽的自然风光——山脉、河流、湖泊、植被、动物等,透过这些他们看到了新疆气候地理地质特征及自然环境的变迁
贝格曼在书中是这样描绘新疆的野生动物的:“(距玉素甫艾力克河)仅500米远我看见一群神态怡然的野驴,它们悠闲地吃着青草。甚至发现我之后仍然显得十分安静,竖着耳朵,一动不动。只是在我设法走近时,这些骄傲的‘绅士’们才以极其优雅的姿势跑开了。你能十分清晰地听到蹄子踩在沙滩砾石上的‘嘚嘚’声和溅起水花的声音……后来只留下四只羚羊伴着野驴,却缺乏戒心,它们认为没必要逃走。”“几个小深蓝色湖泊坐落在库姆塔格脚下,与寒冷、黄色的周围环境以及沙丘形成鲜明对照,红褐色岩石从中浮现出来。终于我们又重见太阳。披着浅粉红色外衣的玛扎塔格山,从玛拉巴什(今巴楚县——笔者注)开始延伸,深紫色的阴影紧紧相随。”这就是特林克勒眼中色彩绚丽的新疆。
关于塔里木河下游河流改道的事实,斯文·赫定曾在书中再三提到——“我的前文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我们的考察团最先发现了塔里木河下游河流的这次大的变化,并绘制出新河道地图。这条漂忽不定的河流,如今又回到了2000年前的故道之中,回到了那条连接中国与罗马帝国东部前哨的著名商道——丝绸之路的身旁。”⑦对于新疆地理地质的变化,特林克勒做了较为细致的描述,他还对南疆地区春夏之际循环发生沙暴天气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哈士纶和贝格曼均发现新疆部分地区沙漠化现象非常严重,这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所记录,贝格曼甚至准备向新疆当局进谏,反映这种现象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
当时新疆的政治形势,是他们观察的重点方面
无论是探险家还是学者,他们都异常关注在新疆发生的“七七政变”,有人甚至对政变的主谋进行猜测——斯文·赫定认为:“虽然不能否认,杀害杨增新符合樊耀南的个人利益,但是据我对樊、金各自性情的了解,我更倾向于金树仁是这次事件的真正凶手。”
新疆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离心倾向,这在当时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此时来疆的外国人亦有所察觉,巴敦指出:“新疆在表面上,仍然属于中国,而实际上则与中国其余各部分显然分离,成了独立的状态。”密勒氏、拉铁摩尔等亦持相同的观点。斯文·赫定也观察到了这一点——“中央政府在新疆当局的眼里显然形同虚设。”佛奈明甚至认为:“迪化(今乌鲁木齐——笔者注)省当局,差不多是他们(苏联——笔者注)的傀儡,由他们代理人之活动,已经掌握了新疆五分之四的土地的完全政治统治权。”
金树仁时期,新疆军队军容不整、军纪废弛、恶习深锢、缺额严重、武器装备落后等现象,在外国人的笔下暴露无遗。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员之一米纶认为哈密边境守卡部队的“士兵并没有穿着合适的军装,看上去更像是一群暴徒。”至于军纪,雅林认为:“要是我们讲这里(即乌鲁克恰提,今乌恰县——笔者注)的军队的纪律给我们留下了好印象,即是夸大其词。”在斯文·赫定看来:“新疆原本是中国少数几个没有盗匪的省份之一,生活在这些善良的人们中间,我们从来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可是现在,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大街上,士兵竟敢伤害无辜平民。”在新疆不仅高级军官吸食鸦片成风,如驻哈密师长刘希曾“面色苍白,身体消瘦,周身带着长期吸食鸦片烟的特征”。即使是基层官兵亦多为“瘾君子”(即吸食鸦片者——笔者注)。新疆军队的缺额现象严重,“仅由一个独居的士兵驻守在中华帝国的这个孤立的边境哨所”,而且“他来回闲逛,消磨时间,白天的大部分时间用来抽鸦片。此外就是不时地从客栈的房顶向外张望,看看是否有新到达的人”,防务空虚由此可见一斑。同时,新疆的防御工事破旧,“修建这个哨所是作为抵抗一种假定的敌对情况的保护性措施……但是中国哨所却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墙壁是用泥土打成的,或许能用来挡住步枪子弹,但几乎挡不住其他东西”。
在外国人眼中,金树仁政府与苏联的关系比较密切。密勒氏指出,金树仁政府“为着该省商业利益的需要,自然与苏俄维持一种友善的关系”,且这种关系“绝不受中国本部的政治与政策的变更而有所影响”,《新苏临时通商协定》就是这种友善关系的产物之一。斯文·赫定更是相信,《新苏临时通商协定》“赋予了俄国控制整个新疆经济命脉的权利”。在巴敦看来金树仁政府就是亲苏的中国地方政府。他们对俄(苏)、英、日等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为争夺新疆而展开的激烈角逐极为关注。《中国在帕米尔及坎巨提主权缩小之一段史料》一文的作者论述了英国侵略中国帕米尔及侵占坎巨提的情况,外国人都看出了俄(苏)、英、日在新疆的重重矛盾,雅林觉得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喀什噶尔英苏关系由于双方都对对方在中亚的计划满腹疑虑而打上强烈的猜忌印记”。而佛奈明则发现:“日本特别底对于苏联在新疆之机谋非常畏惧。而对于她在新巩固自己地位趋向,使日人更不能有所忍耐。”巴敦也注意到了俄(苏)、英、日在新疆展开的激烈争夺——“俄人对于首府迪化,专施用政治的力量来监视一切,英国在近印度边境,喀什噶尔取有立足之地”,但是“自(一九三一年)以后,日本向亚洲迈进,中亚细亚局势为之一变。而日本侵略新疆的途径,系从内蒙古而来,日本另与阿富汗发生了外交的关系,以抵制英、俄的势力”。巴敦甚至认为,由于苏联在新势力强大,英、日有联合起来共同抵制苏联的可能,他指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独立为英人策动,“马仲英叛乱的背景,虽然尚不明了”,但“英日双方,对于苏联势力之攻击,焉有其可能性”。拉铁摩尔的观察更深入一些,他看出了各国在新疆的明争暗斗给新疆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现在正是新局多事的时候……英俄两国各欲夺取地方权力,致使局面日益混乱”,如果英俄直接发生冲突,“这是一个非常可怖的展望”。
这些善于观察的外国探险家、学者们也注意到了新疆上层势力之间的矛盾,他们发现不仅当局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之间存在矛盾——“反叛的火炬点燃了整个新疆,反对汉人统治的起事以燎原之势席卷了全省。‘虎王’尧乐博斯汗目睹哈密四周的世袭领地遭到火与剑的蹂躏,正躲在天山深处密谋着如何复仇。焉耆土尔扈特部的王爷和大喇嘛多布顿活佛拒不执行和尧乐博斯打仗的命令,于是被叫到乌鲁木齐去见省长金树仁将军,结果,他和随从都被暗杀了。”即使汉族官僚之间亦是勾心斗角,“汉人的高级官员们也和俄罗斯人串通起来,决定推翻金树仁”。
对金树仁统治后期新疆局势的混乱,这些探险家、学者们都进行了描述。尤其是斯文·赫定,在他的三部书中,对哈密事变的原因、变乱的扩大、马仲英入新、乌鲁木齐被围、“四一二”政变、金树仁倒台、金树仁获刑均有详细的记述。当然,在他的叙述中存在一些错误,如他说金树仁“任命两个儿子到最高军事岗位”,实际上金树仁是任命其四弟金树智为驻喀什师长、五弟金树信为军务厅长;又如他说一名汉族税收官强娶维吾尔姑娘为妻是哈密事变的导火索,其实这是一名汉族驻军军官,而拉铁摩尔错误地以为新疆变乱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改土归流、措置失当,深层的原因是“人口增多,大部分移民侵入游牧地带,农民与游牧人民潜存心中之传统的仇视增加许多”,显然他还缺乏对新疆的深入了解。
对于金树仁时期新疆传统的农业、牧业、手工业以及财政金融情况,也为探险家、旅行家和学者们所关注
雅林在前往奥达姆王陵朝圣的路上发现:“田野里玉米和高粱长得有人那么高。道路两边护堤上长着柳树,每一块灌溉田地都有堤围护着。”贝格曼注意到不少维吾尔族农民在自己的果园里种植了大量的葡萄和甜瓜。当时新疆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亦为这些亲履者所记述,“(车尔臣,今且末县)地里开始收割燕麦……有一个打谷场,有九头牛就像脱粒机一样干活,就我所见,牛的身后没有拖任何石磙”。由于水源由官方控制,“(卡尔克里克,今若羌县)富裕的人都住在条件好的地方,由官方灌溉,他们的玉米地一年约浇三次水。而穷人只能用剩余水来浇灌——如果有剩余水的话”。所以,“虽然这里给人繁荣昌盛的印象,但这种专断的配水现象只能造成更大的贫困。”
哈士纶记载了土尔扈特部落逐水草而居的无忧无虑的游牧生活——“从6月到8月,‘上百个山顶上的河谷’是蒙古人想象中的安乐之乡。数以百万计的肥尾绵羊、成千上万的马儿和数不清的牲畜群,在无边无际的新鲜多汁的草海中翻滚。在山坡上的放牧人,坐在灿烂夺目的百花丛中,在大自然的美不胜收的景致之中纵情欢乐。”
至于新疆(主要是南疆)的工业,雅林这样写道:“50年前,喀什噶尔没有工业。这也是当时整个新疆南部的状况。工业产品,绝大多数是消费品,都从苏联或印度进口,或某种程度上经过乌鲁木齐从中国中部地区运来。所有的东西都是驮队承载的。喀什噶尔是一个手工业城市。”
金树仁时期在新疆境内流通的货币种类很多,斯文·赫定记述了其中的几种:“我们到这里后,亲眼见到了新疆奇怪的货币。现在这里所用的货币几乎都是一种叫‘新疆两’的钱,它是在乌鲁木齐印制,形式只有一两一种。还有一种中间带有方孔的中国钱也能用。有时人们也使用‘元宝’,即一种船形的银币,它值50两。商人们则愿意换中国的银元,因为纸币一出省就作废了。我们卖出银元时,一块银元值2.5两,若要想买进一块银元,则要付3.5两了。”
新疆的对内、对外贸易,在外国人眼中具化为一支支或大或小的商队以及出现在市场上琳琅满目的货物
金树仁时期由内地通往新疆的商道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由陕西、甘肃通往新疆的车道,一条是由外蒙或绥远、宁夏通往新疆的驼道。货物由内地运往新疆或由新疆运到内地,主要依靠驼运,很少一部分用汽车运输,所以,探险家、学者们路遇的许多大大小小的驼队就成为他们记录新疆与内地贸易的主要对象——“第二天一早起来我们发现,这支驼队大约有1 200峰骆驼和90多个人。他们从归化来,去巴里坤和古城,去这两个地方,在较长一段都要行进在通往哈密的路上。这支大商队约代表不同的50家公司……这些公司联合起来,用租来的骆驼运送货物……他们运的主要是布匹、茶叶、香烟和日用杂品。”⑧
这时,与新疆进行贸易的国家主要是苏联以及英国、英属印度,新疆将畜产品和农产品外售,换成巴扎上、店铺里摆放的品种繁多的工业必需品和生活必需品,这些琳琅满目的货物又成了外国人眼中新疆对外贸易的具体体现。“印度、英国和俄罗斯生产的货物引起我们的注意……事实上,在固玛(今和田皮山县固玛镇——笔者注)每样东西都特别便宜。”⑨“喀什噶尔老城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所谓的安集延区,是用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城名命名的。在那个时代,安集延是苏联向新疆出口物品的始发地……在这里你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欧洲货,大部分都是在俄国制造的。但经常也有印度出产的东西。”⑩苏联与新疆的贸易往来(在大多数外国学者的眼中是苏联对新疆的经济侵略),引起不少学者的重视。拉铁摩尔发现:“近年以来,中国与新疆的贸易,困难日甚,事实上,已全被战争、土匪和控制通路的地方官吏之重税所割断;与印度的贸易,因为交通险阻的关系,亦难得有长足的进展;故新省国际贸易几全为苏俄所独占。”巴敦同样注意到新疆“全省大部分的对外贸易,以俄人为最多”。受雇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丹伯也看到苏联土西铁路建成对新疆造成的影响——“新省交通完全与内地隔绝,而西与北两方面,均与俄境相毗连也。尤可虑者,近顷苏俄土西铁路完成,与新疆边界成一平行线……此路通后,凡入新疆者,均取道于该路,即货物之转运出入亦然。”由中国本部入新之路,又“均控制于苏联之手”,由此新疆完全受控于苏联。《〈新疆与苏俄贸易关系的现状〉——中俄经济关系之史的解剖的一部》一文的作者制作了民国以来尤其是金树仁时期新疆与苏联贸易往来的多幅表格,详列双方的贸易额、贸易品的数量、价值比照等,提供了大量详细的数据。他清楚地认识到“当土西铁道完成以后,苏俄利用其与新疆交通之便差不多完全支配新疆”。他还称《新苏密约》为“屈辱的条约”。《最近新疆之经济情势》亦重点记载了新疆与苏俄的贸易关系。
亲历新疆的外国人对新疆的巴扎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斯文·赫定对鄯善、吐鲁番和车排子村的巴扎、特林克勒对玛拉巴什的巴扎、雅林对喀什噶尔的巴扎都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在巴扎上,每一个行业和手工艺行当都有它们固定的场所。在编织品和地毯巴扎,宁静而且没有嘈杂声,这与铜匠巴扎上的噪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食品巴扎地处特殊地段。这里集合了各式各样设备简陋的饭馆和露天小吃摊子。在食品巴扎上你可以买到现成的吃食。大师傅们会给你端来可口诱人的各种炒菜,烤在炉子上的肉,切成小方块的肉,米饭和香喷喷的抓饭,以及非常好吃的馅饼,应有尽有。凡是维吾尔人厨房里能做出来的或是汉族人烹调手艺所能做出的食物,在巴扎上都有。”这是雅林眼里人头攒动、琳琅满目的喀什噶尔巴扎。
金树仁时期新疆交通落后,路况极差,邮递函件十分缓慢,而且有着严格的邮件检查制度,外国人对此深有感触
对于在新疆的公路上乘坐汽车行进,斯文·赫定认为,“特别是在春天和秋天,乘汽车对人真是一种折磨”,甚至发出“新疆的汽车真应该升格为刑具”的感叹。在斯文·赫定看来“组织一支养路队是极简单的事情,但是中国政府太腐败,根本没有人过问这种事”,以致“像这样一条极好的汽车路,在积雪融化、秋雨连绵的季节也无法通行,就是在其他季节,也还有许多地段需要改进”。因此,如果“粘土路被水一泡,常常使汽车寸步难行。在这种情况下绕道行驶大概是最明智的选择,否则汽车就只好开一段推一段了”。
当时新疆的邮递方式落后,“邮差……骑在马上,两个邮袋挂在马鞍两侧。这样行走一天一夜,到下一站,交给另一个人继续传递。从塔城到乌鲁木齐有620公里路程,邮件要走7天”。而且,“这里的电报有‘骆驼电报’之称,过去曾发生过在塔城与乌鲁木齐之间用电报联络竟不如用骆驼联络快的事”。这一时期,金树仁承袭杨增新的闭关政策,公开限制人民的通信自由,派人检查所有来往信件,没收、扣留、延迟信件的事情时有发生,故而在考察队员狄德满回国时,斯文·赫定托其为他们带了一大包邮件,因为“在乌鲁木齐寄信毫无把握,信件在邮检员那里压几个星期是常有的事”。
新疆种类众多的民族、各具特色的民俗,是吸引外国探险家、学者们赴新疆进行探险、考察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
各民族的外貌、服饰、语言、居室、日常饮食等,探险家、学者们都做了详尽的记录。“在他们极好的胡子上面是具有雅利安人气魄的翘起的鼻子,他们大而发亮的棕色眼睛给我种族相近的亲密感觉。”这是维吾尔族男子给哈士纶留下的印象。而土尔扈特蒙古高级官员,“穿着汉人式的丝绸长袍,但色彩和发亮的料子上的单调图案却是草原蒙古式的,他们的头饰是帝王时代的装饰性帽子,帽子上插着象征头人地位的时而上下摆动的花翎”。在特林克勒眼中,柯尔克孜“妇女很庄重,戴着高的白色头饰,穿着漂亮的服装”。
少数民族欢乐祥和的节日场面以及婚丧嫁娶的风俗,是他们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封斋结束,人人都穿着节日盛装。一堆一堆的美味点心和糖果送往‘餐厅’,整整一天维吾尔人川流不息。”这是贝格曼眼中的维吾尔人传统的节日景象,他生动、详细地叙述了维吾尔人的婚礼场面,他甚至注意到了当时维吾尔人中的早婚以及近亲结婚等现象——“阿不都热合曼的两个女儿一个只有9岁,一个11岁,和从辛格尔来的两个堂哥结婚了。”而新郎的两个妹妹同时又嫁给了新娘的两个哥哥。“婚礼就在堂兄妹之间举行!”哈士纶则在书中描写了土尔扈特人快乐祥和的新年——“帐篷前面的地方挤满了穿着色彩鲜艳的节日盛装的蒙古人。空中充满了嗡嗡的嘈杂声,土尔扈特人像大孩子似地蹦蹦跳跳,一下子扑到彼此胸前,恭敬地屈膝以示对长者和上司的虔诚,可一下子又热烈地拍其后背。‘赛音西尼鲁!’(新年好)他们彼此问候,大家都为新年祝福。”
新疆各民族的热情好客,给这些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士纶的考察队快到卡尔克里克时,受到当地维吾尔人的热情款待:“在地毯上放有盛满酸奶的陶碗,各式各样的羊肉、新烤的面包、甜瓜、杏仁和葡萄干……我们都已达到饱食状态了,地毯上还是摆满了那样多的食物以致我们不能勾画出地毯上刺绣的花纹图案。我们喘着气,伸直腰,饱食之后愉快地注视着我们的主人。”拉铁摩尔注意到了新疆的跨界民族——哈萨克、黑黑子(即柯尔克孜),指出“游牧的哈萨克和黑黑子,他们都有同类的人种住居在苏俄统治的边区上,中俄两方的设施,都难免于被他们拿来比较。”拉铁摩尔对跨界民族这一现象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是很有先见和见地的。
新疆的宗教情况亦为金树仁时期来疆的外国人所关注
新疆每年有不少穆斯林花费巨额资财,不顾长途劳累,去遥远的麦加朝觐。探险家和学者们就路遇了不少前往麦加朝觐或从麦加朝觐归来的穆斯林群众:“我们经常遇见阿吉——去麦加的朝圣者,尽管携着家眷旅行,他们并不惧怕长途跋涉和穿越中亚群山地区的艰辛,只为了达到他们的目标。”特林克勒的书中还透露了这样一条信息——“1928年,中国政府实施了一项法律,每个朝圣的穆斯林教徒,在他出境之前,都要在该地区的衙门存入30英镑。这项法律得到批准,以便使朝圣者不可能移居他乡,或者回来后,仍拥有他们的财产。”显然这是新疆当局对前往麦加朝觐的一项限制措施。
雅林记录了南疆穆斯林朝拜麻扎的盛大场面。他还以为在当时“正统伊斯兰教的教规极其严格”,禁止不戴盖头的妇女出门,而且禁止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放高利贷。
特林克勒和哈士纶分别对伊斯兰宗教法与蒙古人的宗教法进行了记述。他们及雅林还发现,在新疆,原始宗教和萨满教的观念及遗俗一定程度上在许多民族的生产、生活中仍然保留着。
至于外国传教士在新疆的活动,斯文·赫定和雅林的书中对此都曾提及。斯文·赫定他们来到玛纳斯的天主教传教站时,“荷兰神父威尔特曼张开双臂欢迎我们……他带我们参观了他的小诊所、药品、学校、孤儿院和花园”。雅林则着重记述了瑞典传教团在喀什噶尔的活动及其对当地群众产生的影响。在雅林看来,瑞典传教团在喀什噶尔的传教活动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达到了最高峰。传教士们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医疗保健和教育上,“他们在这两个领域的贡献值得称赞和敬佩”。但是“在劝说人们改信基督教方面,效果很差”,因为“在伊斯兰教的追随者中进行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一直是非常艰难的……伊斯兰教本身就是一个劝人信仰伊斯兰教的宗教”。
这一时期来疆的外国探险家、学者也记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社会底层的贫苦百姓生活艰辛,如一些居民为了生计,不得不前往苏联中亚地区务工,“季节一过,这些劳工口袋装着挣来的一点钱,又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步行翻山越岭回到喀什噶尔”。而在群克村“这30所茅舍的居民靠叉鱼为生,据说穷人除了鱼,没有别的食物”(11)。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僚贵族奢侈豪华的生活,“款待我们的是无数道真正的中国大菜,有鱼翅、竹笋、海参、燕窝汤、烤鸭以及所有中国的高档餐桌上应有的美味佳肴”(12)。“有钱人和贵族们骑着气度不凡的马,马鞍子上蒙着绣有精美图案的毯子,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穿梭而过。那些不太富裕的人骑在毛驴上,而穷人们——他们是这座城市人口中的大多数——则步行。”(13)贝格曼还对当时新疆民间药品的匮乏和医疗条件的落后表示惊叹——新疆各地的“患病者很多,但无处就医”。
探险家、学者们笔下还刻画了一个个立体而鲜活的人物
“金树仁瘦高的身材、长脸、长鼻、尖脑壳……屋子里(会客室,笔者注)有6名身穿草绿军装的卫兵站岗。”“从进驻(督署衙门)之日起,(金树仁)便再也没敢跨出大门一步,作了一名自缚的囚徒。”(14)“王爷名叫沙木胡苏特,汉人称他为沙亲王。他是个70来岁的小胖老头,红润的肤色,和善的眼睛,鹰钩鼻,留着一把雪白的胡子……据说他征税比汉人收的要重。因此,就是在那些伊斯兰教的信奉者中他也已不太受欢迎了。”“他(沙木胡苏特——笔者注)听说有一种望远镜能看到最大的山峰,还能找出里面藏着的宝物。当然他确信我们有这种探宝器,因此他也很想要一个。你根本无法动摇他确信真有这种宝贝的念头。”(15)“尧乐博斯即‘老虎王爷’,他是沙亲王的得力助手,与汉人当局的关系也很好。”(16)塔城道尹李钟麟,“身材矮胖,脖子上顶着一颗大脑袋,圆鼓鼓的红脸上眯缝着一对小眼,别看其貌不扬,却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物。他诙谐幽默,是一个天生的滑稽角色。他乐观、热忱、善良,甚至不愿意去伤害一只苍蝇。他会说俄语,但又说不好,可说出的每句话都滑稽可笑,简单明了。”(17)“但当他(僧钦格根——笔者注)把欧式服装脱下,换上黄色喇嘛长袍后,在我面前的这个人简直就像变了性格一样。那敏锐而聪明的目光逐渐变得内向反省,似乎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他那生动活泼的面容渐渐镇静下来,进入了一种静谧的善于接受新思想的状态。”(18)金树仁的多疑、沙木胡特的贪婪、尧乐博斯的圆滑、李钟麟的世故、僧钦格根的超然都被这些外国人通过外貌、语言、动作刻画了出来,他们个个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金树仁统治时期,来新疆探险、考察者关于新疆的发展史(尤其是当代史)、政治、军事、地理、民族、宗教、交通、贸易、文化、气候等各个方面的记述及他们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对新疆的所思所想,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了解新疆的非常宝贵的第一手材料,通过这些使我们对金树仁统治时期的新疆就有了一个更为直观、全面、真实的了解和认识,这些材料与国内的有关资料互相补充,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新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更丰富的史料。
注释:
①由于历史的连续性与复杂性,笔者参阅的外国学者的著述及论文,在时间上并不是严格地限定在金树仁执政的1928-1933年这5年间,而是分别向前向后稍作延伸。
②James A.Millward,Beyond the Pass:Economy,Ethnicity,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1759-1864,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4,.n.5.引自贾建飞:《19世纪西方之新疆研究的兴起及其与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关联》,《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
③如法国雪铁龙汽车公司、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等。
④此外,还有一些不为官方所知的秘密考察活动,如《未完成的探险》一书中记载到:“第二天早晨,当两个顺路去中国新疆的英国人拜访我们时,我们仍在睡觉。他们是大尉曼、传教士和他的伙伴。”([德]艾米尔·特林克勒:《未完成的探险》,赵凤朝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7~208页);在《重返喀什噶尔》一书中,雅林是这样记录的:“一些到喀什旅游的英国人,其中有一个自然科学家弗兰克·卢德洛,在喀什噶尔度过了1929-1930年的冬天,他对植物学有着特殊兴趣。”([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崔延虎、郭颖杰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0页)
⑤如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结束后,瑞典方面以《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报告集》为总标题,在1937-1992年间,共出版11类56卷专册(中国方面,在建国前以《西北科学考察团丛书》的形式出版了8种专著;新中国成立后,黄文弼的吐鲁番、塔里木盆地考察报告也以特刊和专刊形式相继出版),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是中国现代科学史上一宗重要的遗产。其中为世人熟知的有斯文·赫定的“战争、湖泊与道路三部曲”:《大马的逃亡》(中译为《马仲英逃亡记》)、《游移的湖》(中译为《漂泊的湖》)、《丝绸之路》。《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是卷帙浩繁的《中瑞科学考察报告》(全名为《斯文·赫定博士所率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报告集——中瑞联合考察团》)中的3卷,也是整个报告集的总序或导言。斯文·赫定是个颇具文学才能的人,其写作态度亦十分严谨、认真,在坎坷旅途中不论条件多么恶劣,他总是坚持记下当天的经历及思考,即使是在骑骆驼的行程当中,他也能一边作地图测绘,一边写笔记。所以,读他的游记多有身临其境的感受。由于其经历的独特与富有传奇色彩,使《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成为西方人描写1927-1935年中国(主要是西部地区)无可替代的作品,书中许多形象具体的画面都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杨镰:《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代序)。还有[瑞典]沃尔克·贝格曼:《考古探险手记》,张鸣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丹麦]亨宁·哈士纶:《蒙古的人和神》,徐孝祥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德]艾米尔·特林克勒:《未完成的探险》,赵凤朝译;[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崔延虎、郭颖杰译。它们都是我们了解金树仁时期外国人眼中的新疆极其重要的著述。
⑥杨奋武译:《中国在帕米尔及坎巨提主权缩小之一段史料》,《时事月刊》3卷2期,1930年8月;[美]A.R.Tamberg.丹伯:《新疆与蒙古》,《东方杂志》第28卷第5号,1931年3月10日,第33~35页;[美]欧文·拉铁摩尔:《新疆问题的观察》,郭家英译,《天山》1934年1卷2期;密勒氏:《新疆最近的实况》,《开发西北》第1卷第3期,1934年,译自密勒氏评论第67卷11号的文章;[英]佛奈明:《英人眼中之新疆》,萧瑟译,《边疆》半月刊第1卷第3期,1936年;[美]巴敦:《美人眼中之新疆》,吴伟英译,《边疆》半月刊第1卷第4期;《〈新疆与苏俄贸易关系的现状〉——中俄经济关系之史的解剖的一部》,金童译自日本边疆支那十一月号;李作藩译:《最近新疆之经济情势》等。由于正文中的引述均出自以上所列举的著述或论文,故之后出现的引文,笔者就不一一注明了。
⑦[瑞典]沃尔克·贝格曼:《考古探险手记》,第41~42页,第89页也多次记载了这一现象。
⑧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第163页。
⑨[德]艾米尔·特林克勒:《未完成的探险》,赵凤朝译,第78~79页。
⑩[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崔延虎、郭颖杰译,第67~68页。
(11)[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崔延虎、郭颖杰译,第57页;[德]沃尔克·贝格曼:《考古探险手记》,第95页。
(12)(14)(15)(16)(17)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第233,270、269,197、205,199,255页。
(13)[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崔延虎、郭颖杰译,第62页。
(18)[丹麦]亨宁·哈士纶:《蒙古的人和神》,徐孝祥译,第256页。
标签: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论文; 新疆生活论文; 喀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