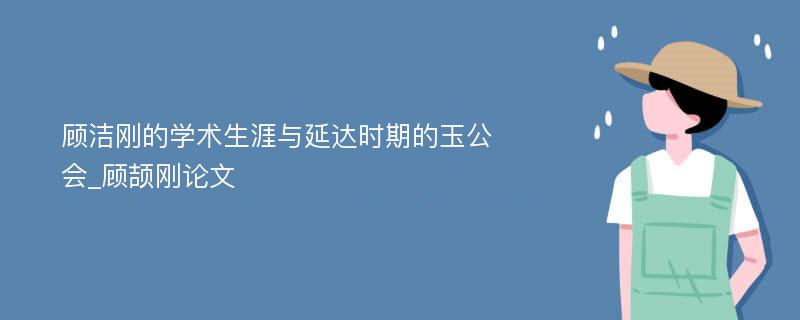
燕大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事业与禹贡学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期论文,学术论文,事业论文,燕大论文,顾颉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0)06-0035-07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学界一般认为,在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青的学科,说它古老,因为它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说它年青,因为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它建立的时间还不长”[1]。历史地理学的前身是沿革地理,以东汉班固于公元1世纪撰写的《汉书·地理志》为开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名称与概念,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此后中国学术界长期将“历史地理(学)”与本土固有的“沿革地理”相混淆,直到1950年侯仁之《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发表[2],这一局面才得以改观。西方历史地理学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已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侯仁之在以英国历史地理学家达比(H.C.Darby)为代表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影响下,不仅指出了“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的本质区别,还说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变迁为主”,“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都在讨论之列。1961年11月28日,中国地理学会在上海举行了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宣布成立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谭其骧任首任主任。至此,作为地理学一部分的历史地理学,在学术界开始正式被“体制化”。
可以说,20世纪上半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学术史上由传统沿革地理转为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过渡期。毫无疑问,此间最具影响的事件莫过于顾颉刚发起创办的“禹贡学会”及由顾颉刚和谭其骧主编的《禹贡》半月刊。《禹贡》半月刊自第3卷第1期开始,其英译名称由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改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一般认为这是“历史地理”出版物在中国出现的标志。正因为如此,顾颉刚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获得了学界的普遍公认。姜亮夫将顾颉刚一生学问影响最大者归结为如下三端,其一就是“历史地理之学,使中土有新建之学科而日益深厚,大为渡越前修”[3](P18),朱士嘉则认为顾颉刚“是中国上古史专家,又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中国民俗学的创始人”,1934年3月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创办之事“标志着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4](P136)。而历史地理学界更是将顾颉刚视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祖”[5](P101)。显然,顾颉刚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所起的促动作用居功至伟,而亲沐顾颉刚教泽的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诸位前贤更是为历史地理学的发扬光大进行了富于开创性的理论探索和研究实践。
仔细审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现代化历程,不难发现燕京大学(以下简称“燕大”)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地理舞台”作用。顾颉刚创办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之时,正是燕大的专任教授。禹贡学会会址及《禹贡》编辑部在燕大,禹贡学会的会员及骨干也以燕大的学生为主。后来成长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主将的谭其骧、侯仁之诸先生都是在燕大结缘顾颉刚,从而走上历史地理研究之路的。所以,初创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在人才培养、学术机构、专业刊物等方面都深深地打着燕大的“烙印”,可以说,燕大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萌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如果对顾颉刚当时在燕大的种种因缘际会的不予以钩稽复原,我们就无法了解中国历史地理学在草创时期萌生发展的具体历程。本文在此所欲彰显的正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燕大渊源,而历史地理学与燕大结缘的肯綮所在,就是顾颉刚在燕大的长期任职及燕大当时特定的时空背景。
与“宏大化叙事”相比,本文更乐于采取复原历史细节、再现历史场景的研究理路。文学史家陈平原曾在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运用过这一理路,他说:“作为研究者,你可以往高处看,往大处看,也可以往细处看,往深处看。我采取的是后一种策略——于文本中见历史,于细节处显精神。”具体方法是:“选择新文化运动中几个重要的关节点。仔细推敲,步步为营。”[7]具体到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现代化进程而言,足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历史细节有如下几处:其一,顾颉刚学术事业在燕大的继续。此关系到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其二,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的创立。中国历史地理学人才的培养与聚合因此得到最佳场所。其三,学术师承关系。此为当今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多元化特质的基础。囿于篇幅,本文无法全面铺开论述上述问题。作为开篇,首先述及的是顾颉刚学术事业在燕大的延续及其对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的影响。至于其它,则另辟专文。
二、燕京有何可恋?——顾颉刚与燕大的结缘
顾颉刚结缘燕大之原委,在新近出版的12册《顾颉刚日记》中有详细记载,加上此前出版的《顾颉刚年谱》和《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①,其中所载有关材料,足以让我们了解顾颉刚于1929年选择加盟燕大并执教达8年之久的缘由。
顾颉刚称“民国十年至廿五年一段时间,即我之开花期”,并且“此时精神充沛,发表力特强,一过此期则思想及发表力渐即于干涸”[8](第五卷,P140),而在燕大的岁月恰属于顾颉刚“开花期”的后半段,足见燕大时期在顾颉刚学术生涯中的重要性。
到燕大之前,顾颉刚在三年中辗转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之间,在每所大学执教的时间都不长,而燕大之所以吸引顾颉刚在此久留,待遇优越自然是原因之一。据《燕京大学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1929年8月1日、2日),执委会表决接受哈佛-燕京学社关于顾颉刚教授任教的报告,报告内容为“哈佛-燕京学社以月薪275美元邀请顾颉刚教授充任该学社研究教授,并以同意他在历史学系任教不多于3小时为条件”②。这样,顾颉刚的年薪就有3300美元。在同一宗档案中还讲到了历史学系讲师张星烺的薪水问题,此时张星烺的年薪为1000美元,另据《燕京大学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1929年8月8日),历史学系研究生助教(graduate assistant)朱士嘉的月薪仅有30美元。通过比较不难看出,燕大给予顾颉刚的待遇相当丰厚。但是,待遇和地位并不是顾颉刚决定执教燕大的首要原因。1929年7月28日,顾颉刚曾在致戴季陶、朱家骅信中提到:“在薪金上,在地位上,我在燕大所居都比中大为低,但是我本不计较这些,我所计较者只在生活上安定与学问进步。燕大既在北平乡问,甚为僻静,又一星期只有三小时功课,不担任事务,我可以依我六年前所定的计划,将应读的书读着,应研究的问题研究着。我无所爱于燕京大学,我所爱的是自己的学业。”[9](P134)可见,顾颉刚之所以离开中山大学而选择燕大,主要因为燕大能提供自己所渴望获得的研究环境和条件,经济收入是次要的。
燕大是以新闻学、社会学等“西学”著称的教会大学,何以乐于聘请专长于上古史研究的顾颉刚呢?这与燕大的中国化有关。钱穆称“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10](P154)。既然要中国化,就不能忽视作为中国传统学术重要内容的历史学,延揽顾颉刚这样的古史研究翘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据长期主持燕大的司徒雷登(Stuart,John Leighton)回忆:“哈佛-燕京学社为燕京作了许多好事,其中一件就是使我们——并且通过我们使中国的其他几所教会学校——能够把汉学研究提高到任何一所中国学府的同一水准上。”[11](P59)顾颉刚在1929年5月2日日记中也提到“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合办之国学研究所,去年已见聘,予以不能脱广州,未应。此次来,又承见招,拟应之”[8](第二卷,P279);6月12日日记又记“绍虞来,告燕京职事已通过”[8](,第二卷,P291)。其实,早在顾颉刚离开北大南下之时,燕大已有意延揽,据顾颉刚1926年7月11日日记:“刘廷芳先生谓早知我肯离北大,燕京方面已早请矣。”[8](第一卷,P767)显然,离开燕大中国化这一大背景,顾颉刚就不可能结缘燕大,历史地理学也几乎不可能在当时的燕大扎根。
就环境而言,人际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促使顾颉刚离开中大的主导因素之一就是他与傅斯年的人事纠葛,而最终选择燕大,则与洪业有很大关系。据周一良晚年回忆,当时“北大清华之间虽不无门户之见,但大体上这两所国立大学和史语所关系较近。而燕京是教会大学,自成格局与体系,与这三个机构关系都比较疏远。近年我才听说,洪先生与傅先生这两位都具有‘霸气’的‘学阀’,彼此间的关系也不融洽”[12](P29)。正因为燕大与北大、清华、史语所的关系较为疏远,而实际主持燕大历史学系的洪业与傅斯年关系也不融洽,这就为顾颉刚回避其与傅斯年的矛盾提供了可能。顾颉刚在致洪业信中如此写道:“史学系中,以您的关系为最深,照了一班人的通例,您大有对我侧目而视的资格,但是您毫无这种意思,依然容许他们的接近我。这足以证明您只有事业心而无嫉妒心,您是要自己做事而又要他人做事的,不是自己不肯做事而又不要他人做事的。这就和我的宿志起了共鸣了!我不能得之于十余年的老友而竟能得之于初识的您,岂不是一件最快乐的事呵!”[9](P141)显然,寻求和谐的人际关系,便于自身学业的开展,是顾颉刚进入燕大的主要考虑之一,也是此后他拒绝北大之邀的主要考虑。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顾颉刚于1929年5月应燕大之聘,一直任职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对于顾颉刚执教燕大的选择,傅斯年当年曾以“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加以质问,而顾颉刚在日记中则称“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辨也”[8](P536)。其实不必百年,顾颉刚在燕大的学术贡献已获得举世公认。如果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掀起的古史辨运动以及在中山大学引领的民俗学研究是其学术生涯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亮点,那么,他在燕京大学主导的历史地理研究则是足以与前二者并称的学术事业。
当然,燕大绝非世外桃源,人际纠葛、经费不足、事务繁剧等问题仍纠缠于顾颉刚的学术生活中。从这一时期的《顾颉刚日记》来看,他在燕大期间也数次动过辞职念头,打算转入中央研究院、北大等地。然而,两害相权取其轻,身处学术“江湖”核心地带的顾颉刚只得选择留在燕大。而燕大校方在发生利益冲突时每每能做出让步,也使得顾颉刚不忍离开燕大。
三、燕大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事业
顾颉刚在学界因古史辨伪而名声鹊起,他也自称“我的研究的目的总在古史一方面,一切的研究都是要归结于古史的”[6](P19)。从早年编辑《古史辨》至晚年注释《尚书》的学术历程来看,“古史”研究确实是贯穿于顾颉刚学术生涯的主线。当然,不同时期古史研究的着眼点或用心之处并不一致。在此,我们梳理燕大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事业,探求其中的旨趣变迁,借此理清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成立的内在理路。
(一)《禹贡》地理研究——古史辨之余绪
顾颉刚担任燕京大学教职后,仍旧从事古史辨伪研究,继续编校《古史辨》,讲授《尚书研究》课程,编辑《上古史研究讲义》。在1932年9月9日编订的本年计划中,顾颉刚首次明确列出了“编《禹贡》讲义”的目标,并安排助手助其编集、抄写《尚书》文字,绘制《禹贡》地图[8](第二卷,P648-645)。此后,顾颉刚进入对《尚书·禹贡》的专门研究中,其在燕大、北大(兼课)的课堂讲授也以《禹贡》为核心。
随着研究的深入,顾颉刚深感《禹贡》问题是复杂。1933年初,他在《尚书研究第三学期讲义序目》中写道:“《禹贡》之问题皆非可单独解决者,直当以全部古籍及全部地理书为之博稽而广核之也”,“且岂但书籍为需用哉,举凡历史、地理、地质、生物诸学之知识亦莫不当有”[13](P205),因此,顾颉刚的研究视野也顺势扩展到《汉书·地理志》、《周礼·职方》、《山海经》等书中的古代地理问题。于是,历史地理学(当时更多称为“地理沿革史”)变成了顾颉刚考辨古史的重要手段。顾颉刚自称:“民国二十年,我在燕京大学讲授‘尚书研究’一门功课,第一期所讲的便是《尚书》各篇的著作时代,其中如《尧典》《禹贡》等篇,因为出世的时代太晚了,所以用了历史地理方面的材料去考定它,已经很够。”[14](《序》,P1)可见,顾颉刚并非为了发展沿革地理这一学科,而是为了深入古史考辨而去利用这一学科的,故其对沿革地理的态度仅限于“够用”而非推广。如果说顾颉刚《古史辨》对古代史料的“辨伪的范围涉及到古书、古人、古地和古史传说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其中考辨古史传说和古书的分量较多”[15](P80),那么,对古地的考辨无疑是为考辨古史传说和古书服务的。
研究古代地理以为考辨古书成书年代服务,是顾颉刚古史考辨的重要研究思路。早在中山大学执教时期,顾颉刚已开设“古代地理研究”课程。从其《古代地理研究课旨趣书》看,该课程一方面探讨《禹贡》、《职方》、《王会》、《山海经》、《淮南地形讯》(以上为“甲种”)中“分野”、“分州”、“四至”、“五岳”、“四裔”、“五服”等地理观念,另一方面从甲骨文、金文、史籍等“当时”的地理材料去分析当时的疆域状况,而该课的最终目的则是“把这些材料和甲种相比较而推求甲种诸篇的著作时代”[13](P160-161)。对这一点,学界或存在误解,如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称:“1926年后,顾氏的学术活动,看来是忽东忽西,或民俗,或民族,或边疆史地,其实皆以前述之十七条或六大项为张本。”[16](P184)这里的“十七条”即《〈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提到的十七项“辨证伪古史”研究计划,其一就是“战国、秦、汉时开拓的疆土和想像的地域[如昆仑、弱水及《山海经》所记”[6](P75)。许冠三认为“1934年后积极推动的沿革地理研究,其初衷本为界定‘战国秦汉时开拓的疆土和想像的地域’”[16](P183-184),此说未必全是。禹贡学会及其刊物的取名,均源于《尚书·禹贡》,故顾颉刚的沿革地理研究更应该直接发端于十七项研究计划中的“《尚书》各篇的著作时代和著作背景”。据曾师从顾颉刚的王钟翰回忆:“他(顾颉刚)研究《尚书·禹贡》,发现其中问题太多,这些问题几乎涉及到中国古代全部地理,由此开始了历史地理研究。”[17](P53)
到燕大任职之后,顾颉刚仍旧坚持以沿革地理服务于古书成书年代考辨的研究理路,但此时沿革地理在顾颉刚的学术研究计划中并未处于前列。从1933年3月19日日记所列十二项“我应做的工作”来看,其工作中心仍在古史辨伪和民俗学,其中与古史辨伪有关的工作有五项,与民俗学有关的工作虽只有两项,但却排在第二、三位。相比较而言,位于第十六位的地理沿革史显然并非顾颉刚的工作重点。1933年5月31日,顾颉刚总结了到燕大四年来的工作,从中可以看到,只是到了第四年才“编《禹贡讲义三册》”,其研究的主要精力无疑仍在古史辨伪上。同时,顾颉刚将三年内应出版的书分为“古史及故事”、“尚书学”、“汉代史”三大类[8](第三卷,P52-53),显然,在顾颉刚的学术规划中并没有沿革地理的明确位置,只是在“汉代史”大类下有“汉郡县图说”,其性质或接近沿革地理。
需要说明的是,有论者认为顾颉刚“从1931年起涉足古代地理的研究领域,到1934年即达到古代地理研究的高峰”[18](P73)。如果我们注意到“顾氏之注意历史地理问题,本因禹的考辨而起,由大禹的传说而《禹贡》,而及于战国秦汉间的地理沿革”[16](P195),则顾颉刚涉足古代地理研究的时限则相应提前赴中山大学任教之前。可以说,经由沿革地理而考辨古史,是贯穿于顾颉刚学术生涯的一条研究思路。如此,则与其说“以一部分时间推广学用结合的历史地理学,以致延误了他的古史研究专业”[16](P173),倒不如说历史地理“延续”了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专业,所以称“禹贡学派”“是《古史辨》派的姊妹学派”[19](P342)是有道理的。
有论者指出:“从表面上看,古史辨运动似乎是一个破坏性的运动,研究历史地理则具有较多的建设意义,但实质上,辨伪的另一面其实就是考信,甚至可以说辨伪只是手段,考信才是目的,研究古代地理乃其考信之一环。”[20](P148)实际上,“辨伪”与“考信”好似一个硬币的无法分割的两面,“辨伪”即“革故”、“去伪”,“考信”即“鼎新”、“存真”。就性质而言,研究古代地理实为古史研究之一环,在这一环中同样存在“辨伪”与“考信”的问题。正如顾颉刚所言“我很愿意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同时也可以用了建设的材料做破坏的工具。”[6](P66)沿革地理就是这样一种工具。
(二)“以文字参加抗日”——学术价值的新取向
顾颉刚秉承乾嘉朴学传统,以沿革地理为手段研究古代地理研究,其突出表征有二:其一,在燕大、北大专门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其二,创建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尤其是后者,多为历史地理学家所称道,并视之为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
如上文所述,顾颉刚以《禹贡》为主体研究对象的古代地理研究,上承古史辨运动之余绪。也正是“因为他最早就是从讨论古史起家的,所以顾颉刚在有意无意间其实是将初期的《禹贡》当成古史辨运动之延续”[20](P165-166),翻检创刊初期的《禹贡》半月刊,确实发现关于古代地理考辨的文章占主流。但从总体看来,禹贡学会的学术活动及《禹贡》半月刊所载文章,并非局限于古史地理,而是存在一个由古史地理向当代边疆地理及民族的明显转向,《禹贡》半月刊的“东北研究专号”、“后套水利调查专号”、“康藏专号”、“察绥专号”、“南洋研究专号”等均为这一转向的产物。对当代边疆地理及民族问题的研究,显然溢出了古史辨运动的范畴。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向,与顾颉刚在新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学术价值新取向有着直接关联。
起初,顾颉刚抱有“学术至上”的观念。他主张:“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6](P42)显然,顾颉刚业已意识到“人生的约束”对求真知的影响。这种“约束”既包括个人的身体、人脉、金钱、权势,也包括国家民族的命运,乃至国际局势。余英时通过对《顾颉刚日记》的解读,发现顾颉刚并非固守“象牙塔”里的学者,正如余英时所说:“他的‘事业心’竟在‘求知欲’之上,而且从1930年代开始,他的生命形态也愈来愈接近一位事业取向的社会活动家,流转于学、政、商三界。”[21](P1-2)这也就是说,顾颉刚正是在燕大任职时期开始由单纯学者向三重角色转换的。1931年12月27日,顾颉刚曾在一封信中如此表白自己的心迹道:“在今日之时势中出《古史辨》,恐将为人所笑。但我以为如不能改变旧思想,即不能改变旧生活,亦即无以建设新国家。我编此书之宗旨,欲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知识,欲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政治与伦理,欲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8](第二卷,P593-594)这封信虽然体现出顾颉刚固守“象牙塔”的执着与自信,以及继续以纯学术的工作推进新国学建设的冀望,但也透露出他已意识到《古史辨》:“求实”以“改变旧思想”这一长远目标与当下整个民族抗日救亡这一迫在眉睫的目标之间的错位。
最终,富于爱国热忱的顾颉刚还是从“象牙塔”里走了出来,逐渐踏入学、政、商三界。顾颉刚自称:“爱祖国者人之情也,九一八事变起,北京已当前线,予亦不能自止其敌忾之心,以文字参加抗日工作。”[22](《小引》,P2)顾颉刚“以文字参加抗日”的主要工作有如下诸端:其一,参加燕大中国教职员抗日会活动,任宣传干事,主张通过征求大鼓词和剧本在民间宣传抗日;其二,参与创办三户书社、金利书庄,出版和销售抗日鼓词,后又独力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其三,创办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发起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出版边疆丛书。为了上述事业的开展,顾颉刚既积极与出版商、书店接洽,又多方游说教育部长王世杰、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交通部长朱家骅,争取政府津贴,并争取中英庚款董事会、中山文化教育馆等民间机构的经费支持。上述行为无疑给顾颉刚的身份增加了“政”、“商”的色彩。
顾颉刚“以文字参加抗日”的学术价值取向,在其1936年1月起草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得到了完整体现。该计划书称:“当承平之世,学术不急于求用,无妨采取‘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其效果如何可以弗问;此犹富者家居,狗马玩好唯所嗜,固不必为衣食计也。及至国势凌夷,局天蹐地之日,所学必求致用,非但以供当前之因应而已,又当责以弘大之后效;譬如蓬门荜户之家,凡劳力所入先图温饱,其衣食之余则积储为他日创业之资,不敢有一文之浪费也。以我国今日所处地位之危险,学术上实不容更有浪费,故定其价值之高下必以需用与否为衡量之标准。”[23]顾颉刚由“为学问而学问”到“所学必求致用”的转变由此清晰可见。
有研究认为禹贡学人当时抨击“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针对的是傅斯年等人[24],这其实是一种因误读史料产生时代背景而造成的曲解。批评“为学问而学问”在更大意义上是顾颉刚的“自我反动”。就与政治的亲密程度而言,傅斯年远比顾颉刚紧密。“九·一八”事变不久,傅斯年就编写了《东北史纲》,主张东北历来是中国领土。早在1935年,傅斯年就写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等大量旗帜鲜明的政论文章,“我们甚至可以说,傅斯年的学者生涯随着1937年7月7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开始而宣告结束”[25](P46)。可以说,傅斯年比任何人都有资格批评“为学问而学问”。顾颉刚于1936年9月曾为筹集禹贡学会经费之事致函傅斯年,信中说:“弟所以创办禹贡学会,发行《禹贡》半月刊,即是你们编‘东北史纲’的扩大,希望兴起读者们收复故土的观念,为民族主义的鼓吹打一坚实的基础。”[9](P168)顾颉刚不仅毫不避讳其民族主义情怀和目标,而且明显表露了在追求学术的致用价值方面视傅斯年为先行者并引以为同道的意思。因此,说禹贡学人批评当时“为学问而学问”的风气是针对傅斯年等人来的,无疑是对顾颉刚和傅斯年的双重误解。
四、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国故整理、民众教育与边疆开发的融汇
1948年1月22日,顾颉刚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做题为《我的事业苦闷》的演讲,讲述其在国故整理、民众教育、边疆开发三方面的工作经历[13](P333)。可以说,上述三方面是实际上就是顾颉刚对自己倡导及从事的学术事业的总结。三者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交叉、彼此影响,甚至呈现逐渐融汇的趋势,而顾颉刚倡导创立的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则标志着这种融汇的开始。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上述概念均有其特定的内涵。“整理国故”指作为古史辨余绪的古代地理研究;“民众教育”则指在日寇步步进逼的时局下激发普通民众的民族抗日热情,维护民族尊严,树立民族自信;“边疆开发”则以北部边疆(尤其是正在遭受日寇侵凌的东北边疆)的经济开发为重心,探讨与边疆有关的一系列问题。
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成立的之初,并未将“民众教育”、“边疆开发”置于与“整理国故”并重的地位。该学会及刊物的创办,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为了“要使一般学历史的人,转换一部分注意力到地理沿革方面去,使我们的史学逐渐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26](P3)。史念海也曾回忆说:“禹贡学会的组成实为颉刚先生从事古史辨的余波。辩论古史必然会涉及许多与地理有关的问题,而且亟需解决,这是组成禹贡学会的由起。”[27](P368)史念海是禹贡学会的早期会员,其观察自然可信。
但《禹贡》半月刊创刊半年后,其初衷就发生变化。1934年8月,顾颉刚在考察绥远时感到“察、绥两省旦夕有继东北四省沦亡的危险,心中着急,想唤起国人共同密切注视边疆问题”,于是将《禹贡》半月刊内容“转到了以研究边疆历史和记录边疆现状为主”[13](P223)。这一转变在童书业1937年6月撰写的《〈禹贡半月刊〉序言》中得到印证。该序言称:“自从东北四省失陷以来,我们的国家受外侮的凌逼可算到了极点,所以有血气的人们大家都暂时放弃了纯学术的研究而去从事于实际工作。至于留在学术界的人物,也渐渐转换了研究的方向,即如本刊的由研究地理沿革而转趋到边疆调查,就是这种潮流的明显的表现。”[28](P1)边疆调查,既包括对古代边疆历史、民族、地理的文献考察,又包括对当时边疆地区民族、地理现状的实地考察。尤其是后者,更能体现出经世致用的色彩。禹贡学会在1936年7月组织河套水利调查团,出版边疆丛书,编辑《禹贡》半月刊“后套水利调查专号”,均体现出对“边疆开发”的重视。顾颉刚在1935年9月4日给胡适写的信中说:“禹贡学会,要集合许多同志研究中国民族研究史和地理沿革史,为民族主义打好一个基础,为中国通史立起一个骨干。……禹贡学会的工作依然是‘为学问而学问’,但致用之期并不很远。我们只尊重事实,但其结果自会发生民族的自信心。而且郡国利病,边疆要害,能因刊物的鼓吹而成为一般人的常识,也当然影响到政治设施。”[13](P167)其中,研究民族史、地理沿革史(乃至撰写中国通史)属于“整理国故”的范畴;向民众鼓吹民族、地理知识则属“民众教育”,而传播的内容所涉及的“郡国利病,边疆要害”则将“边疆开发”涵盖其中。
“整理国故”、“民众教育”、“边疆开发”三者的融汇,使得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呈现出一番新气象。时在辅仁大学任经济地理一课的王光玮1935年8月19日在给顾颉刚的信中提到:“会刊能顺应潮流,改变态度,倾向现代人文地理方面,诚为得计。弟近治地理经济之学,对会刊的新姿态甚表欣悦。”[29](P547)同时,敌伪也嗅出了其中的新“味道”,否则也不会将之列入黑名单,致使顾颉刚不得不离开北平避难,将禹贡学会交给钱穆和张维华负责。
当然,“整理国故”、“民众教育”、“边疆开发”三者在禹贡学会的“融汇”不是“合并”。顾颉刚及其影响下的禹贡学会会员并未刻意将三者“捆绑”在一起。禹贡学会那些令普通民众疏远的考据性文章仍旧继续着“整理国故”的使命,1936年出版的《禹贡》半月刊“古代地理专号”显然起不到太大的“民众教育”作用。而“民众教育”的使命,更多由通俗读物编刊社专门承担。至于“边疆开发”,除了禹贡学会以外,还有1936年在燕京大学成立的边疆问题研究会和1937年4月成立的西北移垦促进会(顾颉刚任主席理事)。但是,上述机构、学会或事件在当时的号召力及对后世的影响力,均不足与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相提并论。
今日的学术史研究,固然可以表彰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但相应的定位和评价应恰如其分。可以说,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既不是历史地理学的“独奏”,也不是“无主题变奏”。理清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的主题及其变迁,无疑有助于认清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源流。由于“民众教育”与“边疆开发”主题的介入,淡化了“整理国故”的单纯性和严肃性。沿革地理作为“整理国故”的手段之一,由于受到“民众教育”与“边疆开发”主题的挤压,也就无法实现其向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迈进。
注释:
①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顾潮:《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 Minutes of the General Faculty Executive Committee,August 1st and 2nd,1929,北京大学档案馆藏,燕京大学档案YJ1929011。
标签:顾颉刚论文; 历史地理学论文; 禹贡论文; 地理学论文; 古史辨论文; 傅斯年论文; 山海经论文; 边疆论文; 历史学论文; 地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