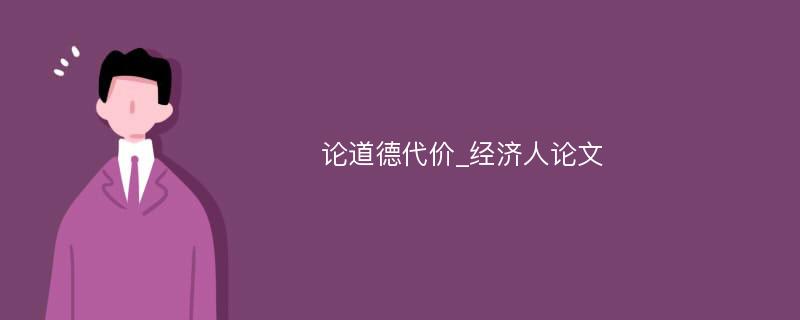
论德行成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行论文,成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德行为是否有成本问题?任何道德主体在履行道德义务、遵循道德规范、塑造健康德性的行为过程中是否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牺牲一定的自身利益和现实幸福?作为一个良序社会是否应该对那些为公众利益、为他人幸福牺牲自我利益的道德行为予以有价(物质)或无价(精神)的补偿?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将我们的视野引入对道德行为成本问题的理论审视。
一、德行成本的植根基础——利益权衡
从学理上讲,道德行为是指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由行为主体自觉选择而发生的有利于或有害于他人或社会的行为。它具有以下特征:一是道德行为必须是行为主体基于对他人或社会利益的某种自觉认识而作出的行为;二是道德行为必须是行为主体根据自己的意志所作出的选择,是行为主体对如何处理利益关系的自愿选择的结果;三是道德行为必须是涉及利益关系,有利或有害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从广义上讲,道德行为包括道德的和不道德行为(有利于或有害于他人或社会的行为)。为行文方便,本文把道德行为简称为德行。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总是处在与他人和社会的一定利益关系中,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他人或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这就决定了个人在进行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时,必然要将行为的目的与行为的后果、将个人利益的损益与他人或社会利益的盈亏、将自身物力财力智力的投入与最终效益的产出结合起来,全面权衡利弊得失。这种利弊比较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就是成本核算,对这一道德行为的分析就是成本——收益分析。
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 )那么什么是利益?在古代汉语中,“利”与“益”最初是分开使用的:利的本意是指工具之合用,后引申为害的反意词,表示对人有益的事;益乃溢之本字,初指盈、满,后表示所需物之充裕。尔后两字联用,表示“好处”。从伦理学上讲,所谓“利益”是指与一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人们通过劳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与享受这些产品的主体人的关系,反映了人们对周围客观世界一定对象的需要的满足。利益不仅体现着人类主体同物质对象客体的一种关系,而且也包括分配与享有客体对象时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利害、损益关系。由于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因而人的利益表现也是多样的:从范围上看,有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之分;从性质上看,有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之分;从层次上看,有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伦理利益、宗教利益等之分;从效用性看,有生物性利益(即满足人的生理需要的衣食住行等)和社会性利益(即满足人的社会需要诸如社会、文化、精神需求等)之别;从利益实现的程度上讲,有现实利益和可能利益之别等。
既然人们的需要是多层次的,利益表现是多样的,那么,作为行为主体在行为过程中,就要对各种利益的获得以及可能付出的代价进行成本核算和利益权衡,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核算和权衡可能有四种后果:一是成本小于收益,即净收益;二是成本等于收益,即收支平衡;三是成本大于收益,即负收益;四是零成本净收益,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搭便车”,即指没有参加该产品的生产,或虽参加但不承担相应成本,却能从中收益的情况。第四种后果是第一种后果的特殊表现。在常态下,作为行为主体在进行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时,出于自身利益的权衡,往往会选择第一种和第四种,而将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形予以排除,总希望用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取最大的收益产出。
然而,人是社会的人,个体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在一个缺乏道德规范的社会,在一个充满商业欺诈的社会,个体实现自身利益的成本会大为增加,因为他需要花许多人力、财力、物力,去了解交易对象的信誉,鉴别交易产品的真伪与质量,采取各种反欺诈措施,明确保证对方忠实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等。相反,在一个道德状况良好的社会,在一个“重合同守信誉”已成为人们普遍认同和遵循的道德信念的社会,个体实现自身利益的成本会大为降低,而造成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共同接受并一体遵循了普遍的道德规范。由此可见,道德规范在人们求利的过程中是有作用的,因而也是有成本的,也是可以进行核算的。
在这里,有两种特殊情况需加以说明。一是“搭便车”行为。由于道德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而公共物品是非排他的,因此,作为非道德产品的提供者同样可以免费享用,以降低自己的成本。从表面上看,“搭便车”者在求利过程中其德行成本的支出是零,收益是百分之百,而实际上他的这种净收益是建立在道德产品提供者提高自身成本的基础上的。如果听任这种现象长期存在和大量泛滥,将会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刺激人们在道德领域的投机行为,使所有人道德成本支出增加。二是“败德”行为。由于行为者经不起暴利的诱惑,为求个人利益满足,置他人和社会利益于不顾,肆意践踏道德规范,甚至铤而走险,走上违法乱纪道路。这种败德行为者的净收益实际上是其他受害者的净收益的净损失。从表面上看,败德行为者似乎也未支出任何道德成本,但从长期看,在一个良序社会中,败德行为者终将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加倍支付道德成本,使其“得”不偿“失”。
二、德行成本的人性设定——理性经济人
道德行为是有成本的,如果说从植根基础上来看,它根源于行为主体在求利过程中的利益权衡和成本收益分析,那么,从人性层面上来看,它来自于对行为主体的理性经济人假定。
理性经济人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这种理性经济人具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自利性,即这种人在经济活动中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遵循“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原则,不断根据市场各种信号的变化,及时作出恰当的行为决策,以期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这种经济人考虑的出发点首先是自我利益边界的不被侵害,或成本小于收益的利益增进。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4页。)二是理智性,这种人具有关于所处环境的相当完备的知识,并具有很强的计算技能和较为稳定的偏好,能知晓行为选择的“希求性”与“非希求性”(韦伯语)的结果,运用成本收益方法计算出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损益和盈亏关系,在“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7页。)这种明智性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经济成本上的精打细算,二是道德成本的统筹规划,即遵循交易规范,树立道德信誉, 以求获得长期的经济收益。
在现实生活中,理性经济人的自利性决定了其道德行为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在通常情况下,理性经济人在作出行为选择之前,总要对各种可选的行为方式的成本和收益的大小进行全面权衡,只有在他从中选择了一种最佳方式并确认这一方式可能给他带来最大利益的时候,他才可能选择这一形式,而对其他不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不能带来最大利益的方式,则统统排斥于自己的道德视野之外,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对于与自身利益相关、可能带来最大利益的方式,理性经济人不仅要采取,而且要想方设法去实现。尽管在常态下,理性经济人可能对出自败德行为而产生的较大收益采取谨慎与克制的态度,但在暴利的诱惑下,理性经济人中的意志不坚定者往往会放弃对社会道德规范的遵守,以求获取不道德的甚至违法的收益,因而理性经济人的自利性有可能导致不道德行为的发生。
另一方面,理性经济人的明智性决定其自利行为派生出道德行为的可能性。在经济活动中,每个理性经济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势必产生相互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于是“他们便成了敌人。他们在求达他们目的时,便彼此互相摧毁,或互相压倒。”(注:《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59页。 )这种状况的存在将严重阻碍每个人利益的实现,因此,每个理性经济人必然要作出一定的让步,付出一定的道德成本,并制定出能为绝大多数人认可的道德行为规范,以确保每个人利益的最优化,而不是最大化。这正如交通规则的产生;如果每个行路人都在马路上各行其是,那么难免会产生交通拥挤与混乱,使谁都无法达到预期目的。因此,为避免这种不利情况的发生,人们便理智地制定出交通规则以约束人们的无序行为。
正因为理性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和明智性两大特征,因而决定了其在经济活动中既要“求利”,又要“求德”。它不仅要在经济成本上斤斤计较,而且要在道德成本上仔细权衡,因为“求德”、付出一定的道德成本是长期获取最大收益的保障。如果只想“搭便车”,甚至为求利不惜采取败德行为,不愿付出任何道德成本和支付任何代价,那么这种求利只能是一时的,最终还是要付出代价的。
三、德行成本的社会补偿——制度安排
从前文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逻辑结论:德行成本根源于理性经济人在追求自身福利和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利益权衡和成本收益分析。理性经济人的自利和明智的本性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会遵循社会通常的交易原则,理性地将自己的成本支出控制在边际成本支出与边际收益相等的临界点上,对出自恶的收益持一种相对谨慎和克制的态度;然而在暴利的诱惑下,在经过了一番利弊权衡后,仍有可能选择败德行为,进行作恶。这说明理性经济人从本性上讲,既可能导致道德的行为,也可能导致不道德的行为,因而仅仅靠理性经济人的善良意志,期盼他的行为永远合乎康德所说的道德律令,恐怕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从一个良序社会的建构来说,它的立足点只能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合乎道德律令的行为选择上,对其为恶的倾向进行社会监控并诉诸制度安排和制度建设,提供“活的善”(黑格尔语),引导其自觉地“扬善去恶”。
那么,什么是制度?早期制度学学派创始人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注:[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9页。 )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诺斯认为:“制度就是人为设计的各种约束,它建构了人类的交往行为。制度是由正式约束(如规则、法律、宪法)、非正式约束(如行为规范、习俗、自愿遵守的行为准则)以及它们的实施特点构成的。它们共同确定了社会的尤其是经济的激励结构。”(注:D.
North,
EconomicPerformance Though Tim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Tnne 1994.No.3)由此可见, 制度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并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共同认可并一体遵循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行为规范体系的总和,二是指处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群体根据历史需要和自身利益需求制定、完善并要求人们执行规范体系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即制度安排和制度建设。
邓小平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333页。)也就是说,良好的制度规范有助于弘扬道德正气, 惩治败德行为,有助于克制理性经济人的私欲膨胀,抵御出于恶的收益的诱惑,使其自觉“抑恶从善”;相反,不良的制度规范不仅会给理性经济人中的意志不坚定者提供“从恶”的借口与方便,而且会使其中的“老实人”变得“不老实”,甚至“弃善从恶”,竞相效仿败德行为。由此可见,一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为此作出的制度安排。造成社会道德失范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个人品德修养,而在于制度本身的不健全或者其正当性引起社会成员的怀疑与否定。因此,加强制度建设、进行合理制度安排,对于规范理性经济人利益权衡和成本收益分析的行为、对于构建一个德福一致、公正良序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在当前,加强道德规范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安排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通过各种制度安排,营造德福一致的社会氛围。一个良序社会不仅应当向它的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的生存环境,建构公正的社会秩序,而且应对其社会成员进行善的价值引导和精神塑造,从道德制度安排上确保人们通过正当手段获取自身福利和效用的可能性,使社会的善指向德福一致。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盛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劣是卑劣者的通行证,那么,在这样的社会中,由于德福的不一致,德行只能成为少数人的奢侈品,而不会成为公众普遍接受的行为方式,这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混乱和无序。因此,加强制度建设和制度安排必须首先保证制度本身是合乎正义的或接近正义的,离开制度的正义性来谈个人的道德性,无疑是一种空想。二是通过各种制度安排,确立德行有用的价值理念。一个德福一致的社会应当努力构建起依靠赏罚严明的机制来调节分配的公正的社会结构,不仅要给“遵纪守德”的“老实人”以制度和道义上的支撑,而且给“违纪败德”的“精明人”以物质和精神上的惩处,使败德行为者成为事实上的“吃亏者”,这样,才能在整个社会中树立“德行既是美好的,又是有用的”价值理念。三是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建构德行成本的补偿机制。既然任何道德主体在履行道德义务、遵循道德规范、塑造健康德性的过程中,往往都要支出一定的道德成本、付出一定的代价、牺牲一定的自身利益,那么,作为一个德福一致、德行有用的良序社会,就应对那些道德产品的提供者在制度上作出明文规定,给予他们有价(物质)和无价(精神)补偿(许多地方已建立起“见义勇为基金会”),否则,社会正义就无法得到真正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