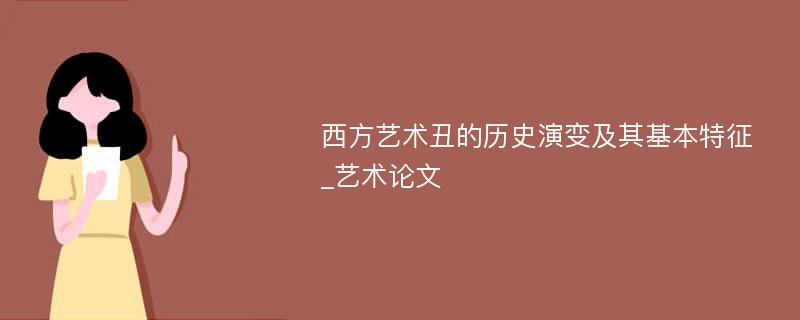
西方艺术丑的历史流变及其基本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特征论文,艺术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美”、“丑”就作为一对孪生的概念出现了。可以说,人类社会有多长,“美”、“丑”的概念就有多长。然而自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时期开始,“美”就在艺术中占据了优势地位,“丑”遭到极度排斥,忒拜城的法律甚至明文规定:“不准表现丑!”时至今日,艺术丑在艺术王国里的地位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就导致我们对艺术丑的历史流变、艺术特点、发展方向等问题还讨论甚少。本文即试图在这几方面做些探索。
一
自人类文明肇始以来,生产的发展、各种社会规范的确立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这些都为人们对理性的追求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到了古希腊时期,借着人类童年时期那种高扬理性的乐观精神,古希腊哲学呈现出由多向一的总体趋势。从米利都学派的“始基”,到毕达哥拉斯的“数”,到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都力图将世界从纷乱复杂向简单纯粹上升,从杂多向纯一上升。柏拉图就曾为人类设计过一级一级的理念世界,从最具体的理念一直到最高的理念“善”。希腊文明衰落以后,理性精神虽一度在西方泯灭过,但发展到经院哲学那里,理性又重新获得了至上的地位。胡尔夫在《中古哲学与文明》中写道,早在15世纪,人们就“毫不怀疑理性的力量可以把捉外界的实在,可以在相当程度内认识一切的事物”。[1] (P.74)这之后,由大陆理性主义一直发展到德国古典主义哲学时期的黑格尔,绝对理性登上了西方哲学殿堂至高无上的宝座。
这一时期的理性崇拜所倚仗的根基实际上是理念背后的“神”。理性至上和“神”至上是绝然分不开的。早在原始时期,人们认为一切皆有灵,崇尚“泛神”;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则把诗人创作时的灵感和“神”联系在一起,认为诗人是神的代言人;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中,“形式因”(包括目的因和动力因)也为“神”作为第一动力留下了不可或缺的位置;到了中世纪,理性更变成了神的理性,托马斯甚至试图为上帝的存在作一番理性证明;这之后的康德虽然认为上帝的存在无法用纯粹理性加以证明,但在实践理性中又把它请了回来;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则几乎成了“神”的代名词。
在这样的神学和哲学背景下,古典时期的伦理学也朝着“至善”方向发展,人成了“大我”,个人也是作为类的附属物而存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一直是西方传统德性的主要教本,而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核心德性就是理智德性。[2] (P.16)远在荷马时代,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决定于他的社会角色,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个人必须作为一个种类的目的而存在,到了中世纪,人的存在则决定于神学目的。[2] (pp.232~235)总之,在古典时期,人必须为某个超越自我的目的而存在,其行为准则也应该首先为了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而非实践的“外在利益”[2] (P.18) (如下棋,提高棋艺属于实践的“内在利益”,获取奖金属于实践的“外在利益”)。古典主义伦理学有一条黄金法则,那就是:“怎样被对待,就怎样待人。”[3] 康德则把这条黄金法则解释为道德律令:“这样行动: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4]
在这样的神学、哲学和伦理学背景下所产生的西方古典艺术,如果不用单纯的、绝对的、永恒的“美”来表达,我们简直难以找到别的任何一种替代方式。古希腊人就曾明白无误地宣称:“我们是爱美的人!”[1] (P.39)为了美貌的海伦,他们发动了十年战争,并且认为这是“值得的”。甚至如果一个人长得奇丑不堪,连画家都不愿意为他作画(一位古代诗人曾这样说:“既然没有人愿意看你,谁愿意来画你呢?”[5] (P.297);而纵然这位画家大发善心为他作了画,也不是因为他的丑陋,而是“因为这画是我的艺术才能的一种凭证,居然能把你这样的怪物模仿得那么惟妙惟肖”。[5] (P.298)关于艺术,希腊人有三大原则:道德主义原则、形而上学原则和审美原则。[6] (P.26)总之,卑劣、低俗、丑陋的对象是不应该进入他们所供奉的艺术品的。柏拉图这样总结希腊人关于美的理想:“这种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它只是永恒地自存自在。”[7] 遵循着这样的信条,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们的伟大抱负之一仍然是尽最大可能描绘出人的美。当一个15世纪的画家在处理画面上的人物时,他总是想方设法让人物面容姣好,体态优雅,“以至在耶稣诞生图中,他们从未如实地画出初生的基督(那不够美)而是把基督画成一个至少年满周岁的婴儿”。[8] (P.32)
沿着这条纯粹的“美”的路线一直往前,到文艺复兴时期,“美”最终成为了“把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牢固地凝聚在一起……的统一的标准”。[9] (P.20)奥兰达在当时就最早提出了“美的艺术”(fine arts)的概念[9] (P.27),一直到1750年鲍姆嘉登创立Aesthetics时,美仍然独霸着艺术王国的领袖地位,“‘丑’本来就在鲍姆嘉登所创立的Aesthetics中无法有真正的立锥之地。”[1] (P.77)
当然,古典时期的艺术作品中也还是有“丑”形象的。亚里士多德对“丑”的论述在古典哲学家中就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艺术中纵然会模仿丑,也只是因为“每个人都能从模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如果我们在艺术作品中看到讨人嫌的形象而产生了快感,那么这种快感来自于两方面:第一,推论的快感,“比如认出作品中的某个人物是某某人”;第二,由作品的“技术处理、色彩或诸如此类的原因”所引发的快感。[10] (P.47)总之,艺术丑就它本身而言,是不存在实际艺术价值的,丑如果不把美当作遮羞布,就不可能单独存在于艺术作品中。
二
到了19世纪以后的现代时期,随着生理学、心理学、医学、天文学等现代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理性的根基“神”已经被彻底推翻,人们开始认识到理性并不是万能的。在哲学殿堂上,就有了一个“神”被赶走以后留下的空缺。非理性思潮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大张旗鼓地登上了哲学舞台,丑也在这一时期随着非理性一起进入了艺术天地。
西方的各种非理性哲学思潮对丑艺术发展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萨特以及海德格尔等人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流派。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认为,意志是世界的内在本质,但人生痛苦的根源恰恰在于人具有生命意志,因此对这种生命意志的否定是人的根本出路;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哲学认为,生命本身就是直觉,理性应该服从于直觉;存在主义哲学更把人的存在描述为“烦”、“畏”、“死”、“沉沦”、“恶心”、“绝望”等状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则把人的生存动力归结为“里比多”,从而引起了学术界对人的潜意识以及非理性层面研究的广泛兴趣。
这一时期的伦理学则处于由传统的理智德性发展到现代情感主义德性的过渡时期。狄德罗、休谟、康德、克尔凯廓尔等哲学家都试图为传统道德理论作一番合理性证明,但都相继失败了。[2] (pp.6~8)实践的内在利益与个人生活整体正在逐渐消失,功利主义道德伦理大行于天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为人们行动的信条,“个性至上”变成了最响亮的口号。艺术丑就是在这样的哲学、伦理学和社会背景下堂而皇之地登上了艺术舞台。另外,艺术丑在现代时期的兴起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艺术家自身社会地位的变化。早在奴隶社会以及封建时代,艺术家首先不是作为艺术家,而是作为其他社会角色而存在的。这其中有“从政型”(如但丁做过佛罗伦萨的行政官,孟德斯鸠做过法院院长)、“从军型”(如法国的司汤达)、“从商型”(如巴尔扎克),等等。[11] 但到了现代时期,艺术家大多成了自谋职业者,他们一旦从艺术的象牙塔中走出来,面对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现实世界,必然会抛弃那种古典式的关于美的盲目理想,而如实地把丑恶的社会现实融进艺术之中。艺术丑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雨果1827年发表的《〈克伦威尔〉序言》为标志,艺术丑开始在美的庇护下进入艺术殿堂。雨果在评论近代的诗时写道:“它会感到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美,感觉到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正是在这个时候,诗……把阴影掺入光明,把粗俗结合崇高而又不使它们相混,换句话说,就是把肉体赋与灵魂;把兽性赋与灵智。”[12] (P.183)但这时雨果眼中的丑仍然没有独立的艺术价值,他认为丑只能因美而存在,也就是说,它的意义只在于以丑衬美:“滑稽丑怪却似乎是一段稍息的时间,一种比较的对象,一个出发点,从这里我们带着一种更新鲜更敏锐的感觉朝着美而上升。鲵鱼衬托出水仙;地底的小神使天仙更美。”[12] (P.185)与雨果同时期的韦塞则将这一“以丑衬美”说推展到了极致:“真正的丑不能进入艺术领域,除非在它完全处于从属地位的时候。”[6] (P.509)艺术丑发展的第二阶段以歌德的《浮士德》为标志。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中,美丑正如靡非斯陀所言,开始“挽着手儿在芳草地上逍遥”[13],丑终于开始与美并肩共存于艺术作品中。至1853年,罗森克兰兹出版了西方艺术史上第一本关于丑的专著《丑的美学》。在书中他写道:“丑是一种轮廓鲜明的对象材料,不在美的范围以内,因而需要另外加以论述”,但他接着话锋一转,认为丑“又始终决定于对美的相关性,因而也属于美学理论范围”。[6] (P.512)所以,尽管罗森克兰兹第一个在西方理论界以专著形式论及了丑,但他眼中的丑充其量也不过是美学大框架中的另一半,丑依然离不开美。其后的1857年,是艺术丑引起文坛轰动的重要的一年。这年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出版,并招致了一场有碍风化的诉讼案[14];波德莱尔出版了著名的诗集《恶之花》,这本诗集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该书使波德莱尔提出的“以丑为美”、“从恶中发掘美”的丑美说在艺术界轰动一时。艺术丑发展的第三阶段以艺术领域兴起的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流派为标志。在绘画领域,莫奈于1874年创作的《日出印象》标志着真正的现代派绘画的诞生。在音乐领域,斯特拉文斯基于20世纪初创作并演出的《春之祭》被看成是现代音乐的标志。[15] (P.237)演出中大胆地使用了不谐和音、复节奏和多调性,那阴暗神秘的音乐,剧烈而不规则的节拍和跳音的爆发,整个乐队的咆哮,都使观众感到震惊。“观众们很快就分成赞成与反对的两派。贵夫人用她们的‘香包’打来打去,道貌岸然的先生们相互殴打。”[15] (P.238)在文学领域,表现主义则开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先河,表现主义大师卡夫卡更被尊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16] 艺术丑在这一阶段的发展特点表现为:它已经开始在艺术领域拥有自己的地盘,不再依伴于美而是以独立的形象登上了艺术舞台。
三
随着现代工业文明不断发展,工具理性给人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问题: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核威胁、暴力犯罪、同性恋、吸毒、自杀……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非理性特别是集体非理性行为也日益增多: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意志主义(如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带来的经济危机、社会主义不尊重经济规律带来的大停顿)、法西斯主义(如德国奥兹维辛集中营就曾“理性”地思考过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消灭几百万波兰犹太人[17])、国家交往中的非理性行为(表现为“言行不一致”,“不冷静的作风”等几个方面[18] (P.349))。这一系列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不得不让人们开始反思:理性(集体非理性也表现为一定范围内的理性)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解构主义哲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理性的,也没有一个先在的“逻各斯”中心,因此,我们应该“向同一性开战”。“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作为理性的堡垒已经彻底崩溃,这个世界根本就无法理解,如果有也只是意义的“撒播”和“分延"(differance)。新解释学认为,理解是人的存在的本体,人是理解的产物,而理解者总是带着成见去理解对象的,因此,成见是理解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新实用主义认为,一个命题的真伪并不完全取决于经验,而同时取决于命题内部的逻辑一致性(即自圆其说)。因此,真理的标准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标准问题。“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19]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这样解释其知识实用主义:“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值而被消费”[20] (P.3),“知识不再以理念的实现或人类的解放为自身目的”。[20] (P.106)理性精神在这一时期遭到普遍质疑还表现在其他几个领域:第一,在自然科学领域,波恩受爱因斯坦学说的影响,认为科学不能证实只能证伪;费耶阿本德提出多元主义方法论,强调科学研究中应该重视那些非理性和主观因素;另外,像克劳修斯热力学第二定律及熵的概念,普里高津耗散结构理论以及在数学、量子力学、生物学、化学等领域的非线性科学的发展,也都向传统的科学理性观念发起了挑战。[18] (pp.426~429)第二,在一般的社会科学领域。麦金太尔通过对社会科学中一些普遍概括的特征进行分析,发现“社会科学在预言上的无能和它们没有发现类似法则的普遍概括,显然是同一条件下的两个症状”。[2] (P.113)“不论人们如何完美地一再公式化地表述它们(指普遍概括),也不可能把运气这一因素从人类生活中抹去。”[2] (P.117)因此,“不可预言性不仅不是无法阐明的,而且完全可以与决定论的真理和谐共存”。[2] (P.126)这一观点表明,在一般的社会科学领域,理性的无上地位也在遭到质疑。第三,在伦理学领域。传统的理智德性已经丧失了践行空间,取而代之的是情感主义德性。情感主义德性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个人摆脱了社会身份的束缚,而成为任由情感支配的自我;第二,个人的行为缺乏任何终极标准。“不论情感主义自我声言忠于什么标准、原则或价值,这些东西都须解释为态度、偏好和选择的表达,这些态度、偏好与选择本身并不受标准、原则或价值的支配。”[2] (P.43)第三,以他人为手段。“把他人当作手段,也就是通过在不同场合中施加有效影响或进行谋算,力图把他人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他人永远是手段,而不是目的。”[2] (P.32)
在这种反理性、无中心、无意义、无标准、无原则的哲学和伦理学背景下产生的艺术,几乎将美赶进了死胡同,后现代时期的艺术面临着“理念消失”、“形式解散”、“表现眩惑与畸趣(Kitsch)”的命运。[21] 意大利人皮耶罗·曼佐尼于1961年制作了每听30克、共90听自己的大便,并冠名为“艺术家之屎”,结果像巴黎的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以及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这些著名的博物馆,都收藏了曼佐尼的“艺术家之屎”。后来,伦敦的泰特美术馆以22300英镑的代价购买了一听,其价格竟高出黄金达40倍。对此,泰特美术馆的一位女发言人说:“曼佐尼是地位十分重要的艺术家。他的这件作品(指‘艺术家之屎’)对20世纪艺术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是一件开创性的作品。”[22]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一书中说过的那句话:“说话就是斗争……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为了赢才玩游戏,人们可以为了发明的快乐而玩一下。”[20] (P.18)后现代时期的艺术家们正是怀着这种“为了发明的快乐而玩一下”的心态,去创作各种奇形怪状的作品的。我们不妨看看这些“反美学”的后现代丑艺术:波洛克将画布铺在地上,提着颜料桶把色彩甩上去,就成了一幅画[23] (P.456);“偶然音乐”作曲家凯奇创作的《4分33秒》,表演过程竟然是让钢琴演奏家在钢琴前静坐4分33秒:季娜·帕奈则在舞台上以切自己的手心来完成作品。她还不断创新,除切手心外,还切自己的眼皮、血管,并据说最终导致了她的死亡。[24] 其实这不仅是她个人的死亡,也预示着艺术的死亡。
四
纵观艺术丑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发展演变,我们发现,艺术中的丑是在与美的不断较量、磨合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由最早的丑必须戴上美的面具,到丑依伴于美,再到丑独立出来,这一发展演变过程表现出如下五个特点:
第一,艺术作品中对丑的描写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对丑的肯定,另一类是对丑的否定。其中,对丑的肯定经历了由肯定其威力巨大到肯定其个性伟大的转变,如早期的作品多肯定丑形象在数量或力量方面的巨大(如丑神),近代的作品则更多地肯定丑形象在品性、人格方面的伟大(如《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对丑的否定则经历了由否定其外在形象的丑,到否定其内在的恶,再到否定其本质的假的转变。如在古典时期,几乎每一个丑恶的艺术形象都有一副丑陋的外形,因此,外形丑是这一时期丑形象的共同特征,到了近代,人们开始认识到“恶”乃是丑的根源(但恶的对象却不一定外形丑陋,因此近代的丑形象不再以外形丑陋而是以内在的恶为标志),大量的恶形象涌现出来(如莫里哀笔下的答丢夫、唐·璜,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哈代笔下的德伯维尔等);到了后现代时期,荒诞(假)又一跃成为艺术丑的主题,卡夫卡的《变形记》、海勒的《第22条军规》、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作品成为荒诞艺术的典范之作。总之,无论是肯定性的丑还是否定性的丑,其发展都经历了由外在到内在、由形式到内容、由现象到本质的演变过程。
第二,艺术丑的发展还经历了由重客观传达到重主观创意、重再现到重表现的转变。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艺术丑就重视对形象的客观模仿,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列举的对“最讨人嫌的动物形体和尸体”[10] (P.47)以及“其貌不扬”而又“低劣的人”[10] (P.58)的模仿,指的就是一种客观再现。当时的苏格拉底甚至对艺术家们的主观表现能力心存疑虑,问道:“看不见的东西能够模仿吗?”[6] (P.60)但到了近、现代,艺术家们开始在丑艺术中贯注自己的思想,并打破传统的艺术戒律,力图创新。如迪尚的作品《下楼梯的裸体者》,就试图把运动感纳入绘画,从而向认为绘画是静态艺术的传统观念发起了挑战;而那些把“现成物”当作展览品的艺术家甚至也受到人们的肯定,如批评家里德就认为,因为这些艺术家在把现成物(如河里的浮木或者干脆是布头、铁钉、破鞋垫之类的东西)拿到展览厅以前经过了选择,而“选择亦是创造”[25],因此,“现成艺术”是值得肯定的;甚至当高更的一个学生问他:“树留给人们的印象是绿色的吗?”高更回答说:“那么,就把你调色板上最漂亮的颜色画上去。”[8] (pp.214~215)
第三,艺术丑在发展过程中,其社会职能还经历了由发挥艺术的救赎功能到发挥艺术的批判功能的转变。早期的丑艺术形象如欧那尼、卡门、靡非斯特、弗罗洛,等等,或者本身是漂亮善良的,或者尽管自身丑恶却是为了衬托美而存在的,总之,丑的存在只是为了肯定世界的美好,艺术丑最终发挥的是艺术的救赎功能;然而到了现代,艺术丑的最终目的则不再是肯定世界的美好,而是批判世界的丑恶。这种批判性不但在表现主义、存在主义小说中得到充分体现,而且在最具前沿性的流行音乐中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披散着头发、身着奇装异服的年轻人嘶吼道:“你们建造只是为了毁灭/此外,什么也没干!”[26] (P.74)(鲍勃·迪伦《战争魁首》)“必须有什么办法从这里出去/这里到处都太混乱。”[26] (P.79)(鲍勃·迪伦《沿着了望塔走呀走》)“当我把针头戳进我的血管/我成了耶稣之子,海洛因呀/你是我的妻,你是我的生命/海洛因,你就做我的死亡吧!”[26] (P.81)(地下丝绒《海洛因》)对于大众文化的这种批判现实倾向,法兰克福学派在理论上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艺术的功能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因为“肯定性的文化用清白的灵魂抗议物化,但最终只能屈服于物化”。[27] (P.22)因此,艺术的政治性就在于它能够批判、颠覆既存现实。“在这个意义上,今日的精英主义很可以有一种激进的内涵……革命的艺术完全可能成为‘人民之敌’。”[27] (P.27)
第四,艺术中的丑逐渐独立于美的过程,也就是艺术形象由共性美逐渐发展到个性丑的过程。古典艺术是美的世界,后现代艺术中的丑则几乎泛滥成灾。从某种角度说,美依赖于共性,丑则依赖于个性。康德在分析美的特征时就指出:“美是那不凭借概念而普遍令人愉快的。”[28] 这表明,美的对象必须建立在普遍、共性的基础上。但丑却与美绝然不同,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认为:“美只有一种典型;丑却千变万化。”[12] (P.187)应该承认,一部分崇尚个性的丑艺术有其可取之处,如在画中切开一座房子或一个人的躯体,当运用出色的技巧进行表现时,还是比较能够吸引人的;但也有一部分丑艺术作品却极端表现个性,以至于像某些立体派画家所宣扬的那样:“它远非要人们感到欢乐,而是要使他们感到迷惑。”[23] (P.451)印象派画家莫奈就常常作些让人看不明白的画,以至于“有时自己写生回来,也不明白自己画的画,于是,就把人叫来,让他看看画的是什么”。[29] 如果艺术真的发展到了这种极端个性化、甚至连艺术家自己都看不懂的地步,那么这个世界看来确实是彻底无法理解了。这就应了福柯那句话:人也死了。
第五,与前者相关联,艺术形象由共性美发展到个性丑的过程,也就是艺术风格由“唯美”倾向发展到“唯丑”倾向的过程。从广义的角度说,古希腊艺术是“唯美”的,在那时,艺术王国里“唯美独尊”,艺术丑还处在酝酿阶段;到了现代时期,丑大量登上艺术舞台,与美携手并进,这无疑给艺术天地带来了全新的气息,因此,这时的丑艺术仍然处在上升阶段;但到了后现代时期,丑艺术开始泥沙俱下,艺术中的“唯丑”倾向日增。艺术家们甚至提出了一系列的“反传统”要求:(1)艺术不必反映现实;(2)艺术与美无关;(3)艺术不必要求别人懂,尤其是不必要多数人懂。[23] (P.458)他们还宣称:“在当代,如果一幅画看起来像一幅画……那么它决非一幅好画。”[9] (P.69)迪尚曾经把一个题为《喷泉》的小便池送去艺术博物馆展览,对于这件事,沃尔特斯托里夫给以合理的解释说:“有趣的不是对象本身,而是迪尚这一提交活动本身……在这种姿态中存在着一种对审美的否定。”[9] (P.56)据栾栋在《感性学发微》一书中的记载,当他和不少西方艺术家谈及当今丑艺术盛行的问题时,他们对这种现象毫不奇怪:艺术在今天不就应该是这样吗?若要走俏,丑到绝妙。这是巴黎美术学院高材生们谋求成功的一个高招。[30]
丑在艺术作品中从附属于美到并列于美再到独立于美,这一系列的发展演变促使我们必须从一个更全面的角度去看待艺术问题。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从正面对艺术丑的创作实践给以积极评价,认识到在艺术中丑是美的有益而必要的补充,从而在艺术创作、艺术鉴赏以及艺术批评中努力克服对丑的偏见;另一方面,我们又应该看到艺术丑自身发展的一些不良趋势,如极端追求个性以及唯丑的倾向,而对其进行正确的批评和引导。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艺术作品中美与丑携手并肩,共同往健康、良性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