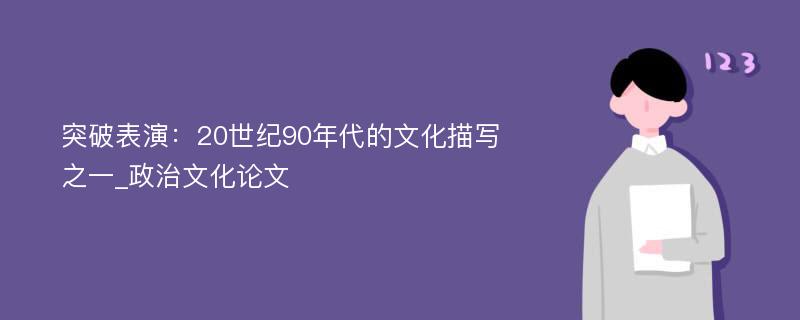
突围表演——九十年代文化描述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意识形态、禁忌与记忆的消费
在精英知识分子的心理体验中,八十年代的终结,颇类似于一场被陡然击溃的“伟大的进军”;而九十年代的到来,更象是在拔地而生、斩而不尽的文化市场面前所再次遭遇的全面溃败。于是,一种新的“断裂”说、一种新的关于终结/开端、关于中国大陆的现代/后现代的描述,清晰地划定了彼此分立的八十和九十年代。仿佛确乎是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以枪击事件完成的行为艺术作品《对话》,将“整个八十年代艺术送上断头台”,或者说是昭示现代主义的终结与“现代性伟大寻求的终结”①。那么,作为另一个八十年代先锋艺术的代表、《析世鉴》(《天书》,1987年)、《鬼打墙》(1991年)的作者徐冰,1994年归国的作品《是强奸罪还是通奸罪?》,则以装置-行为艺术呈现了另一个文化现场与文化现实:展厅中遍地抛置着众多的中、英文的书刊报纸,似乎是一个高密度的文化、文字空间,而两只剔去了毛的猪,则在这场地旁若无人地践踏、追逐、交配。在发情的公猪身上书写着毫无意义的英文字母,被逐的、“屈居下方”的母猪身上则密布“天书”。这是否是《天书》或《鬼打墙》的伸延?是否是《对话》与枪击事件的复沓?其中“文化不可交流”、表达与失语的“极度焦虑”、文化的荒诞与反文化、意义的颠覆,究竟意味着八十年代现代主义“亡灵”的东归,抑或是后现代文化的书写?精英文化溃败者的“狂吼”,抑或是非官方的中国大陆公共空间的出现?对民族文化的亵渎,抑或是对后殖民文化的反抗?这一颠覆、亵渎意义的空间,同时成了为多重阐释、意义所穿透的空间。
勿庸置疑,历史的断裂并非线性过程的终断,并非空间的清晰划定,而是在历史的断裂处裸露出的一个共时的剖面。然而,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的多重变迁,尚不足以将八十年代的文化空间挤压为一个扁平的沉积带,并将其全部覆盖。事实上,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更叠,呈现为远为繁复的错综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说,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社会同心圆结构的多重裂变,已然孕含着九十年代的政治文化、消费文化,浮现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的权力裂隙;孕含着金钱作为更有力的权杖、动力和润滑剂的“即位新神”;孕含着文化边缘的人的空间“位移”与流浪的开始,以及都市边缘准“社区”的形成。只是由于浸透了狂喜的忧患、关于“世纪之战”的主流话语及指认的错误与命名的误区,这一切始终处于文化匿名之中。作为这一特定的误区,八十年代,徐冰的作品被指认为某种非意识形态、或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化空间的出现,但人们所忽略(有意忽略?)的,是它始终与鲜明的意识形态行为相联系。其中最为重要的忽略,正如刘裘蒂君所指出的,“《天书》和《鬼打墙》作为文化批评的颠覆性,实际上延续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与崇高的美学,延续了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的反动与利用……。而徐冰的艺术是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批判,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徐冰对文化/反文化的观点与现代中国史上的‘文化观’有何牵连?”②事实上,《天书》正是作为一种恰当的“包装”,成为八十年代末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作品:戴晴的《梁漱溟 王实味 储安平》的封面。而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当徐冰作品遭到主流批评家的讨伐之时,在北京重要的旅游景点,出现大量印有天书片断T恤衫,并饰有淡黄色的中国传统信笺衬底,不同于1991年夏季,一度牵动北京的“文化衫事件”③,印有“天书”的T恤,除了为少数青年学生辩识并穿着外,主要成了外国游客们的选购对象。对于后者说来,这只是一种小小不言的趣味消费,“天书”之原旨尽失。在“目不识丁”的外国游客眼中,中国的象形文字无一不是“天书”,古怪有趣、莫名其妙。确乎,徐冰1994年作品并非《天书》、《鬼打墙》的复沓;其中展现的不仅仅是文化的颠覆或象形文字的虚妄。如果说,《天书》的原名《析世鉴》显露出某种八十年代“伟大叙事”的痕迹,更象是一种关于人类文明寓言的建构,一种现实命题的转喻方式;那么,《是强奸罪还是通奸罪?》则在一种未必自觉的意义上,成为一种第三世界的文化寓言④。作品无疑以极为直观的方式,呈现了西方与东方、权力与欲望、种族与性别。不期然之间,徐冰“现象”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节点:政治与文化,边缘的抗衡与对主流的回归,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情结”,文化包装与消费,权力、文化诉求与东方奇观。
在整个八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始终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潜本文,始终是一个所指不断增殖的能指,同时是一个政治及表达的禁忌,一个意识形态的雷区,一个历史的写作、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不断地曝光、遮蔽并阻断的区间。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八十年代的政治、文化现实中,“文化大革命”更象是一个多重意义上的隐喻与转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封建法西斯专政”、“十年浩劫”作为文革的唯一代称、或曰隐喻,确乎是新时期的真切起点,而“伤痕文学”则成为新时期文化的开端。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于文革的话语,构成了八十年代最为深刻的政治文化悖论之一。对文革的权威结论,同时成为一种关于终结与开端的权威话语,一种不容置疑“历史断代法”;同时,它却成了一个编年史、历史叙事的权力话语的连续性与整体性的困境;因为它划定了一个异质的、禁忌性的时段,一个总体性的图景因之而不复完满。相关的事实是,尽管“伤痕文学”迅速由一种异己的声音成为文化的主流,但其必然的延伸——政治反思文学却即刻触礁。对文革的反思势必成为一种历史的追问和现实的质询。因此,文化大革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禁忌,更象是一个转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成了中国革命史、中国当代史、历史巨人毛泽东、新时期现实困境作为话语禁忌的指称。而从另一个角度上看,整个八十年代文化正是某种转喻型的文化;一如历史文化反思继政治反思、并代政治反思而起;对现代化的讨论迅速成了对传统文化的清算与批判。徐冰之应运而生,正是由于对一种转喻形态的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一种“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文化“修辞”方式。但八十年代后期,西化的宏观政治学——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精英知识分子所完成的对这一理论与实践合法性的阐释与论证,事实上以历史的诡计、或历史必然的方式,将文化市场、文化消费、文化工业的机制引入了中国的政治文化现实之中。
于是,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在主流意识形态制空权的消弱与强化之间,在文化的“语词奔溢”与失语之间,在权力中心的无限扩张中的“内爆”,在边缘朝向“中心”的顽强进军与不断放逐之间,类似禁忌必然作为一个实际上空前脆弱而诱人的环节,被率先突破。因此,中国革命史、中国当代史与文化大革命的叙事作为一种权力话语的生产与复制,作为历史写作、作为禁忌与记忆;“文化毛泽东”作为一种新的、来自于“中心”与“边缘”地带的意识形态实践;由潜在到公开地,与文化市场、消费社会的浮现,形成了错综的抗衡、对位与合谋关系:一种鲜明的主流的、或抗衡的意识形态实践,同时是对意识形态的有效的颠覆与消弥,一种主流与边缘的共振中的裂解。八、九十年代之交,文化大革命和“文化毛泽东”,作为不同的表象系统,成了一种最为广泛而深刻的流行,成为一种具有特殊快感的消费对象。事实上,其作为一种多元决定、别具意味的对意识形态、禁忌与记忆的消费,正是中国大陆文化市场和“准文化工业”第一次成功地、大规模的、对文化时尚与流行的制造;同时,它又反身有力地推进了借助(挂靠)国家文化机器、体制而初露端倪的庞杂的“独立”文化“系统”和蓬勃兴起的文化市场,其中包括大量名目繁多的“文化公司”、音像公司、广告公司、形形色色的书商、星罗密布的个体书摊、大量的报纸“周末版”和众多的新创刊的学术杂志或“休闲型”杂志、国家电视台的栏目承包(“栏目制片人制”)、“独立影人”、以作家、艺术家名义命名的、批量生产文化消费品的“创作室”、“工作室”,“自由撰稿人”因此萌生并壮大。而这一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彼此重叠而又相对独立的“系统”和市场,则在不断拓宽着权力结构的裂隙,提供着某种亵促尴尬而充满生机的“共用空间”,或曰“类公共空间”。其间跨国资本对中国大陆文化市场的介入,则因其强有力的操作原则和金钱背景强化了这一对意识形态、记忆与禁忌——中国特殊文化资源的消费;同时更为深刻地裸露出九十年代中国在前工业现实与后现代文化、国家民族主义之轭与后殖民文化挤压、意识形态控制与消费文化的张扬间的困窘。
一如徐冰以似乎颇为相象的作品,跨越了八、九十年代;特定的意识形态禁忌与对这一禁忌的消费则似乎在连结起并断裂开八、九十年代大陆文化的同时,印证了马克思的一段谶语:历史总会二度出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
梦魇与禁忌
事实上,在八十年代文化中,文革始终是“一位”最为重要的在场的缺席者与缺席的在场者。一方面,它是必需小心绕过的礁群,一个近在咫尺、却难于进入的历史时段的雾障;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一个不断被借重的“历史时段”与“事件”,因为它潜在包容着某种特定的“历史”断代法在其中,它始终可以成为某种权力话语摆布现实的“说法”,某种社会“共识”得以生产、再生产的原材料。只是它必需以“过去完成时态”割断,成为一个拒绝被质询、追问的对象。于是,在八十年代主流叙事作品中,文革始终作为一个朦胧的血色背景、作为序幕、作为被叙事件及人物的史前史、为一个特许发生“例外”、“悲剧”、制造“病态”、“怪诞”的往昔空间。在其中,文革更象是一个关于创伤的记忆痕,或一夜梦魇所留下的苍白的面色;或者说,它更象是一种集体性的“前意识”。叙事的过程则是一个对创伤记忆疗救、或者不如说是遗忘的过程。但它又必须是“不能忘记的”;不是为了“活着,并且要记住”,而是为了保留为某种“空洞的能指”,用以不断地将难以解脱的现实困境还原为灾难性的历史成因,为种种现实的政治、文化策略提供其合理性的阐释。或许可以说,文革作为一个转喻的禁忌和对禁忌的转喻,始终不断地在以转喻的方式繁衍、膨胀。
然而,禁忌又毕竟在不断被重申。在中国电影最后的黄金时代——八十年代,直面文革时代的影片屈指可数,并大多命运多舛。《枫》、《芙蓉镇》均一度遭禁映,前者则在言辞激烈的抨击中被迫修改;而《苦恋》则成八十年代初思想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而且成为至今未得解禁的少数影片之一,此后再没有一部电影能得此“殊荣”。类似影片的命运印证了禁忌的不可触犯。而事实上,对这一禁忌的维护,成了新时期文化审查制度中最为重要的、不见诸条文的“条款”之一。但作为权力运作的秘密之一,这一禁忌的划定,极为有力地加强了大陆社会的精英知识分子某种堂·吉诃德式的“突破禁区”的热情,及市民心态中特定的“禁书”、“禁片”情结,引发了一种对文革“真相”、“珍闻”、当代悲剧、政治内幕、秘闻的空前的、不间断的关注与热度;在不断地强化、制造着一种特定的政治文化“窥视癖”的类型。当八、九十年代之交“文化工业”、市场及消费机制开始介入大陆的文化体制时,类似的政治文化现实指示出一个已经创造完成的、极为广大的读者/观众“群落”,标志并暗示出一个潜在的、特定的“买点”,一个可资发掘、利用的消费心理,一种政治窥秘与亵渎所提供的消费快感与消费方式。
事实上,不是精英知识分子的写作或主流文化范本,而是一个在八十年代具边缘性的通俗类作品:恐怖片《黑楼孤魂》(导演梁明、穆德远,1989年)有趣地标明了一个多元决定的文化临界面。这是一个孤魂复仇的“鬼故事”。而事实上,影片取材于一部美国的恐怖片《幽灵》。但这在划定的搬迁区、即将被拆除的旧楼的地下室(一个关于记忆的象喻)间出没的、冷血复仇的孤鬼,却是一个在文革时代遭虐杀的小姑娘的冤魂。于是,影片的恐怖感、或曰消费快感,便不仅来自于“鬼故事”的惊吓效果,而且来自于文革亲历者“政治迫害情结”(在某些时候,甚至成为某种被虐与迫害妄想)的共鸣、放大与叠加。影片巧妙地触动了一个作为禁忌的“事实”,即在文革岁月中,普通人对过剩权力的分享,如何制造着暴力、虐杀。但这与其说是一种质询,不如说是一次移置:因为在这一幽灵复仇的故事中,文革场景已由一种政治场景转移为欲望场景;遭复仇的对象之一,曾因淫欲而强暴了小姑娘的母亲,将她逼上死路;而另外两个人则因为觊觎姑娘的遗产:一尊金佛像,而偷窃、虐杀了她。幽灵的复仇手段之一,是从洞开的地下室之门中,让呼啸的旋风,裹携着成团的美钞,于是贪欲者便无法自禁地追随着步入杀戮之地。作为一种文化潜意识的呈现,影片在另一个层面上呈现了一个性别场景。因为叙境的孤楼,是一个看得见过去、听得到未来的象征场所:一个偶然在此地录制影片音响的女演员,恐怖地看到了历史中的暴力,而她的恋人——录音师,则惊讶地在录音带中听到未来的声音,那是复仇者的暴力场景。有趣之处在于,女人在这里“看”到了男人对女人的施暴:强暴、劫掠、虐杀,而男人在这里听到了女人对男人的侵害:小姑娘的冤魂如何残忍地逐一向男人复仇。但在这里,文革梦魇/旧日的暴力场景/男人对女人的施暴是不可见的:除了女演员恐怖变形的面孔,观众一无所见;而复仇场景/女人对男人的戕害却清晰地展露为一个完整的过程。而女人每一次对历史中暴力场景的目击,总是发生在她即将与恋人步入亲昵的时刻,恐怖每每使她奔逃而去,使男人美梦难成。一个有趣的临界面:对文革禁忌的触动、退缩(因为它仍然是不可见的)与消解,被官方说法所阻断的记忆成为恐怖出没的幽灵,对拜金、欲望的暧昧态度,现代化进程中的男性心态和与既由权力、又由女性诱发的阉割恐惧的潜在流露。这一切有效而有趣地组合在一个消费形态之中。这一临界面的呈现再次印证着当代中国政治禁忌在文化市场机制中特定的消费性,印证着文革记忆的特定消费性,预示着九十年代对意识形态的消费将与对另一禁忌:性爱(以男权话语为基准的)的消费,与暴力/色情——“永恒”的商业文化的操作原则相联手。
窥秘与奇观
九十年代初年,当精英知识分子在深刻的挫败感中陷于现实表达的禁忌和历史命名的失语之时,悄然形成于八十年代的文化市场机制,却陡然呈现出它的勃勃生机。1990年,大陆第一部地道的肥皂剧(时称“大型室内剧”)、五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渴望》问世,造成了一阵沸沸扬扬、“不可抗拒”的“《渴望》冲击波”;其创作者公开表达了他们对意识形态内涵、意义营造的轻蔑和对消费操作原则的崇尚⑤。继而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出映。自此,大型肥皂剧的创作开始风靡。极为迅速地,各半官方的、民间的音像出版公司、广告公司、银行系统和种种经济实体纷纷染指肥皂剧的投拍。1992年底,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各电视台的栏目“承包”和“栏目制片人制”的试行,则在更大程度上,为社会资本、八十年代边缘文化介入经典意识形态机器打开了缺口。而在政治禁忌、市场需求、现存体制与市场机制脱轨中举步维艰的各国家、地方大型出版社、电影制片厂,则在更大规模上开始以出卖“书号”、“厂标”的方式,以换取其企业及从业人员的生存。于是,一方面,是主流意识形态制空权的空前加强,而另一边却是文化市场与文化工业机制愈加深广地分享着经典意识形态机器的权柄,并开始了一个不间断的、将其转换为资本的过程。
而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出现于1990年的“毛泽东热”(笔者将在下篇中详论及此)。暂且不论这一文化现实的多元决定因素,它事实上以中国出版业(官方或民间的、国家的或个体书商)一个奇观式的狂潮覆盖了大陆书籍市场。与此共生与伴生的,是难于计数的、名目繁多的涉及中国革命史、中国当代史、文革史的秘闻、野史、报告文学、人物传记、中国共产党领袖、将帅传奇、文革惨案、内幕,以洪水破堤之势涌现。数千种出版物,每种数万、数十万印数⑥。一瞬间,类似出版物取代了琼瑶、三毛、亦舒、金庸、梁羽生覆盖了个体书摊的台面,并进一步雨后春笋般地催生着个体书籍市场。尽管此间王朔的流行、“梁凤仪现象”,先锋、新写实文学的畅销、《废都》“事件”、“陕军北上”、“顾城之死”、“布老虎”的包装与推销形成了一个个小插曲,但中国当代史政治揭秘(或杜撰)则成为一个轰动效应稍减、但势头不衰的持续的流行趋势。似乎未经任何过渡,一个绝对的禁忌,成了一种绝对的流行。事实上,此间特殊的文化禁令一再被重申:明确文革“题材”的禁忌、规定某类出版物为某官方出版社的特权;但不仅屡禁不止,而且一定程度的禁令实际上将成为此类书刊的至佳广告。而继《废都》、《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的流行、及围绕着这一流行的众声喧哗之后,一个新的流行文学配方被“确认”:或真或伪的民俗、风情、赤裸的性爱描写、以及重要的、贯穿性的当代史事件背景。此外还有以先锋文学、“纯文学”、现实主义为旗号的纯色情、暴力写作及男性角色的变态心理描述。于是,出现了一批此前无人知晓的、为流行而制造出来的作家及作品的批量生产(诸如老村的《骚土》、京夫的《八里情仇》、哲夫的《天猎》、《地猎》、《黑雪》、亦夫的《土街》、禹明的《妻命》,还有署名罗珠的《黑箱》、《巫城》、《巫河》)。如果说,这一“长篇小说”创作的热浪,在成为《废都》、《白鹿原》等而下之的拟本的同时,实践着政治场景的色情化,完成着由历史场景向潜意识场景的移置;那么,似乎其动机远为严肃、纯正的、延续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报告文学传统的写作,则在实践着同一文化功能。同样未经任何过渡,也毋需合法性的论述,在这一“中国当代史政治揭秘”的流行趋势中,任何既定的文化等级:严肃与娱乐、高雅与通俗、主流与边缘、历史与文学、纪实与虚构,尽失其间的沟壑与界线。从费正清的精装版《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到《她还不叫江青的时候》;从米兰·昆德拉的译本系列到《骚土》、《天猎》;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党史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作为党史读物《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到团结出版社的《文革创将封神榜》、从我国著名史学家、各国汉学家的史料翔实的中国当代史专著、传记,到《中南海珍闻录》;从《汪东兴日记》到叶永烈、权延赤的报告文学集⑦,它们共同分享一种揭秘/窥秘的快感,共同分享着一种触犯禁忌、亵渎神圣的快感,尽情地满足着远离权力中心的普通人对当代政治内幕、历史事件谜底、秘闻的饥渴,对曾作为膜拜、敬畏对象的“伟人”的个人隐私的想象性的窥视;不再是性/政治在所谓深层结构中的置换游戏,而是在制造流行与消费意义上的和谐而默契的小狐步舞。这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消费,一种对意识形态的消费;禁忌感的存在则成为消费快感的隐秘的不尽之源。
而与此同时,八、九十年代之交,在权力话语的生产运作过程中,作为一个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化手段,同样出现了关于中国革命史和当代史叙事的、经典历史表象的大规模涌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极为典型的政治策略:创造一套定期重演,以重现国家初创时期的“创伤情境”的民族叙事,以便使国家回到一个特殊的时刻——即一个刚刚建立自己国家的时刻,一个决定民族命运的关头。它不仅是一种“再确认”,而且在不断的重述中重返那一艰难时刻,“藉此来定期地重新召唤国家创始初期的那股力量。”⑧于是,八十年代末,作为“娱乐片”(商业电影)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政府对“主旋律”电影的倡导、扶植,在九十年代迅速被“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创作所取代;而且有关机构以指定厂标的计划性指令生产、政府基金的大力资助和以“红头文件”保护的拷贝定数、“票房”收入来确保其在机制混乱的市场“竞争”中获胜。于是,九十年代初革命历史巨片的不断涌现,一度遮蔽了中国电影业风雨飘摇的现实困境。《开国大典》(导演李前宽、萧桂云,1989年)、《大决战》(总导演李俊,1991-1992年)、《周恩来》(导演丁荫楠,1991年)、《开天辟地》(导演李歇浦,1991年)不断以庆典的方式,在全国各个城市各大影院同时献映。然而,在九十年代初年的特定现实中,主流话语间纵横的结构性裂隙,已然破坏了这一特定的民族叙事“完美复制”的可能;而作为八十年代新时期的权威叙事策略之一,是文革时代成了另一个初始情境与危急关头;于是,作为“主旋律”的革命历史巨片,同样面临着绕开并借重禁忌的困境。一个有趣的情形是,在实际上各方面都获得了巨大成功的巨片《周恩来》当中,文革岁月呈现为破碎而充满裂隙的时段与叙事组合段;许多与周恩来总理的政治生涯密切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显现为叙事链条中的时段缺失,或残破不全的片段展露。事实上,此片的观众在其充满感情热度的观片过程中,必需不断地以自己的记忆来补足叙事体自身的裂隙与失语。而“革命历史巨片”,作为一个重新呼唤凝聚力的、经典民族叙事的复制,作为一种非消费或反消费的方式,却在不期然间被接受为另一种消费对象。在九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巨片”、“主旋律”电影中,尽管其中相当一部分因“红头文件”而保证了百分之百的票房收入(集体票);但1990-1991年,在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座率超过了百分之八十的影片,刚好是《周恩来》、《大决战·辽沈战役》(因其中的林彪形象)和《焦裕禄》。姑且不论影片自身的艺术成就,正是这三部影片中更多呈现了权力话语复制中的困境,包含中国当代史揭秘式的(非)“买点”。至此,在“中心”与“边缘”,不同的权力结构再次形成了不无荒诞的对位与合谋。一种不谐共振在不断拓宽着现实与话语空间中的裂隙。
而在另一个侧面,作为东西方冷战时代的遗产,同时由于六、七十年代西方左翼学者对文化大革命的热情讴歌,和八十年代欧洲知识分子对这一历史性误读的清算;“铁幕后的红色中国”——当代中国的政治史、内幕秘闻、文化大革命的个人“纪实”(郑念的《上海生死劫》、张戎的《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在美欧的畅销),在西方世界成功地制造了对当代中国政治的消费趣味,制造了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说“专制国家”的“禁书”、“禁片”欲。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是否在其本土遭禁,成了西方国家重要的文学奖,尤其是各国际电影节选片、评奖、授奖的指认及评判文学艺术电影的“标准”之一。而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在西方世界的获奖,则是其得以进入西方文化市场的唯一窄门。1986年,当意大利导演贝尔特鲁奇在中国拍摄影片《末代皇帝》时,由衷赞叹“中国是一个尚未被可口可乐、麦当劳占领的国家”⑨;但极具反讽意味的是,他本人及其影片已然成了跨国资本染指中国文化资源,占领、返销中国文化市场的“先头部队”。而且也正是他本人,率先发掘了相对于西方文化市场,当代中国政治史这处矿脉。在西方银幕上,第一次出现了当代中国政治场景及如此“真切、迷人”的文革表象。同样是在《末代皇帝》中,贝尔特鲁奇将东方、中国定位在一个种族/性别的文化置换游戏当中。追随贝尔特鲁奇而到来的,不仅是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和诸多欧美导演;而且正是可口可乐、麦当劳、必胜客与和路雪。然而,八十年代,尽管西方世界为跨国资本所支持文化工业系统不断觊觎已然打开国门的中国,觊觎广大而潜在的中国文化市场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但彼时的意识形态及文化市场壁垒,尚非“宙斯化身为一场金雨”所能进入的。而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危机、精英文化、严肃艺术的困境,终于为跨国资本对中国文化市场、文化资源的介入,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这一次,他们得以文化的拯救者、艺术的保护人、发现并拯救天才的伯乐,而实际是淘金者的身份染指中国。张艺谋成了他们的第一个发现,而极为迅速地取代了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艺术电影的成功模式:展现“铁屋子”/四合院/囚牢中的自虐、互虐的悠长岁月;自《蓝风筝》(导演田壮壮,1991年)始,一个新的模式呈现为一个完整的、贯穿性的当代中国史背景中的情节剧。继而,陈凯歌在远为雄厚的海外资金背景的支持下,推出了恢宏的巨片《霸王别姬》(1993年),并一举逾越了张艺谋,跨出了西方艺术院线,进入了欧美商业电影的轨道。张艺谋接着推出当代情节剧《活着》。影坛“第五代”的“三剑客”在世界范围内,“再现”八十年代的辉煌。在这一新的成功模式中,中国的当代政治场景取代奇异空间、佳人画卷、东方风情,成了东方奇观的主部;而对红色中国的揭秘、曝光,使类似影片具有远过于“异国情调”的消费价值,似乎是八十年代中国第五代的艺术与文化探索的获救与延续,但事实上,在这一模式中,任何本土文化意义上的政治、文化反思、批判的使命与力度已悉数殆尽。其中,当代中国的政治场景与其说是一种真实的剥露,不如说更象是色彩绚丽而扁平虚假的景片;更象是一部情节剧所必需的一个“人物”,一个扰乱了普通人正常生活的、拨乱其间的小人;与其说,它展现了一个民族真实的、不无切肤之痛的历史经历,不如说它更象是提供了一处富于戏剧性、以出演生离死别、恩怨情仇的舞台空间。而影片对现实与政治文化禁忌的触犯,又成为使之成功返销国内市场的重要“买点”,似乎是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对意识形态、禁忌与记忆消费的一个更为深广的背景,又似乎是不谐和共振的一个外部漩涡。
一个特殊的历史空间。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意识形态控制,还是公共空间?后现代,还是后殖民?或许只是一种描述,或许只是一种突围表演: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空权下突围,从权力运作的困境中突围,从记忆与现实的困扰中突围。突围,同时姿态不甚优美地陷落于消费社会的网络之中。
注释:
①参见张颐武《新世纪的声音》,《今日先锋》,P105,三联书店,1994年5月。
②《颠覆字/书》,台湾《诚品阅读人文特刊·文字》16期,P31,1994年6月。
③1991年夏,根据一位画家的设计,北京市场上推出一批印有彩色文字的“文化衫”,上面或印有建国以来使用的各种票证:诸如粮、油、菜、蛋票,工业券等等,横批“拖家带口”,或小书“发财,没本儿;当官,没门儿;上学,没劲儿”,大书“一无所有”,或仿古稿纸,上面印满北京流行俚语。或简单写着“别理我,烦着呢!”、“架不住三句好话”等等,以工商名义查禁。
④在海外期间,徐冰创作了《文化谈判》,已涉及东西方文化命题。
⑤电视剧的编剧、策划之一郑万隆称,《渴望》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丢孩子、拣孩子、养孩子、还孩子”,“豆腐白菜,白菜豆腐,好看好玩儿而已。”香港1993年国际评论年会上的发言。
⑥参见1990-1993年的社科新书目。
⑦其中一个颇为典型的例证,是规模最为宏大的丛书《共和国风云实录》(程敏编,团结出版社)。其中包括《浩劫初起》、《红卫兵秘闻》、《中南海珍闻录》、《风雨天安门》、《文革创将封神榜》、《文革洗冤录》、《大冤案与大平反》等等“揭秘”卷,但丛书实际上是报刊杂志上有关文章的辑录,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八十年代后期命运不佳的通俗刊物。而其中一卷《蓝色梦幻:大串连》,事实上,是一部分关于八十年代“出国潮”的报告文学;另一卷《漩涡中的共和国风云人物》,则赫然辑录有《从中国影后到文化界第一实业家——刘晓庆访谈录》、《从“奶奶”到秋菊——巩俐》、《张艺谋绝情前后》等等影星、歌星轶闻。
⑧[新加坡]Garaldine Heng Janadas Derene《父权国家:新加坡的民族主义、性与种族》。台湾陈光兴、杨明敏编《Cultural Studies内爆麦当奴》,P106,《岛屿边缘》杂志社,1992年6月。
⑨《贝托路齐如是说》,顾明修译,P202,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2年3月。
标签:政治文化论文; 消费文化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文革论文; 艺术论文; 九十年代论文; 周恩来论文; 废都论文; 鬼打墙论文; 历史论文; 徐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