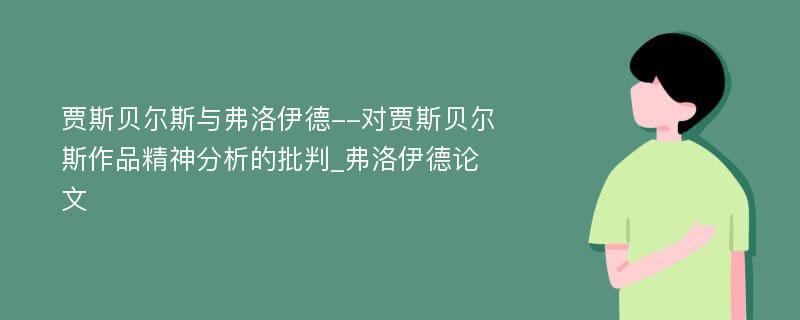
雅斯贝尔斯与弗洛伊德——雅斯贝尔斯著作中的精神分析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贝尔论文,弗洛伊德论文,著作论文,精神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末对德国的精神病学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从这时开始精神病学研究中的自然科学模式渐趋动摇,心理学理论从实践的生理心理学理论进入到现象学理解的整体心理学理论。在这世纪之交,雅斯贝尔斯与弗洛伊德作为同时代人出现于精神病学界,被认为是“一个历史事件。”(注:H.阿科克涅希特:《精神病学简史》,斯图加特,1957年,第89页。)雅斯贝尔斯是德国最早的临床精神病学家之一,他既不是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反弗洛伊德主义者”。但他出于兴趣,在许多论著中都曾致力于批判弗洛伊德的研究,他与弗洛伊德展开的论战被称作德国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之间的一场历史性论战。
雅斯贝尔斯注意到了精神分析具有深刻的观察力,深入到了生活史的深处,但他同时严厉批判精神分析趋向于把理解认识加以绝对化,把人变为它所设计的样子。雅斯贝尔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下述两方面:第一,弗洛伊德的著作五花八门、莫衷一事,无法把握其核心。“人们看不出,一种理论是如何被把握的,在所有问题上是如何被检验、修正的。如果照此方式想成为真正的自然科学的操作方法,那它在任何时候都应是作为全体的理论,同时在每个问题上都应是清楚明白。但是,精神分析决不是这么一回事。”(注:K ·雅斯贝尔斯:《普遍精神病病理学》(1946),柏林/海德堡,1973年,第451 页。)第二,弗洛伊德混淆因果关系与可理解关系,这种混淆使其理解心理学的能力归于无效。 因此,“可理解关系”(Verstandliche Zusammenhange)被重新解释为外在于意识的“规则”, 被重新解释为“因果关系”(Kausalzusammenhangen),从而使其成为理论。
一、基本分歧
1.无意识
雅斯贝尔斯对弗氏的批判特别集中在《释梦》(1900)上。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欲望的满足,进而又根据梦的内容把梦分为显梦与隐梦,从隐梦到显梦的过程叫梦的工作,反之,从显梦到隐梦的过程就是梦的解释。精神分析学家可通过分析对象提供的梦的描述,分析解释对象的真实心理动机,或无意识深处的症结或病根。然而,在雅斯贝尔斯看来,此书的致命错误在于用一种特殊的、 意义深远的“越界”(Grenzuherschreitung)代替了理解心理学。这界限就是“无意识 ”,在雅斯贝尔斯的术语中,就是“外在于意识的关系”(Ausserbewusste)。在弗洛伊德看来,梦的解释乃是通达无意识心灵生活的捷径。梦的工作迫使我们接受一种包罗万象、意味深长的无意识的心灵活动。弗洛伊德不仅许诺了通达无意识心灵生活的广阔道路,而且发展了一种全体人类心灵生活的理论概念。早在1897年,他就宣称:“一句话,梦包含了神经元的一般心理学。”(注:S·弗洛伊德:《心理学草案》, 载于《精神分析的起源(1887-1902):致威尔海姆·弗利斯》,法兰克福,1962年,第184页。)多年后, 他又写道:“梦的图式的最一般应用标志着,梦中实际上存在着解开癔症的钥匙。”归根到底,梦成为“一切精神病理学图景的标准蓝本。谁理解梦,谁也就能够识破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心理机制。”(注:S·弗洛伊德:《无意识》(1913), 《弗洛伊德全集》,第10卷,法兰克福,1960年,第398页。)
无意识是精神分析学说的基石。 在弗洛伊德看来, “无意识”(Unbewusste)即是本真的现实心灵生活。正如外部世界的实在一样,无意识按其内在本性也是不为我们熟悉的。换言之,正如为我们的感官所觉察的东西是有限的一样,意识活动赋予我们的认识也残缺不全。梦的要素的显现、失误、神经症症状,其根据均在于意识所不能通达或意识不到的隐匿心理现象即“无意识”。此外,弗洛伊德不仅要描述或归类无意识现象,还要把无意识理解为心灵中某种相互作用的力量,表达为有目的的相互影响的趋势。最终,在弗洛伊德的压抑学说中,无意识获得了动力学意义。无意识构成心灵的深层基础,它是人的生物的本能、欲望的贮藏库。无意识过程不受客观现实调节,而是服从于享乐和不满的原则。
在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方法论秩序中,无意识问题同样起着重要作用。雅斯贝尔斯区别了作为大洋之“泡沫”的直接地可通达的心灵生活与作为大洋之“深流”的无意识。但对于他来说,这一无意识“深流”并非模棱两可、无差别的。恰恰相反,他严格区别了作为“未被觉察的”无意识与作为“原则上外在于意识的”无意识:前者是理解心理学的合法对象,因为它事实上是被体验过的、被觉察过的、后来可回忆的心灵事件;反之,作为外在于意识的无意识是某种原则上不同的心灵事件,它事实上是“未被经历的,原则上外在于意识的东西。”(注:K·雅斯贝尔斯:《普遍精神病病理学》(1946), 柏林/海德堡,1973年,第9页。)理论上,外在于意识的无意识是为说明(Erklaren )的目的所设想的,因而永远是不可觉察的、不可体验的心灵事件。因此,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说,外在于意识的事件属于说明的心理学领域,尽管理解的心理学亦可部分地接近这种事件。精神分析的原则性错误在于要求一种“漫无边际的可理解性”,误将说明心理学工作当作理解心理学的工作去做。换言之,弗洛伊德的研究大都停留在外在于意识的事件结构上。在无意识问题上,雅斯贝尔斯一再提出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被体验过还是未被体验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可理解的还是不可理解的?”外在于意识的心灵事件原则上是未被体验过的,因此也是不可能理解的。如果这类事件一旦成为理解心理学的对象(如精神分析),那么这个事件便关涉某一“特殊种类的理解”。雅斯贝尔斯称为“似乎理解”(Als—ob—Verstehen),因为在此并未重新体验到未被意识过或未被觉察过的心灵事件,而是设计了外在于意识的事件。在弗洛伊德那里,雅斯贝尔斯发现了大量这类“似乎理解”现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多半不是关涉一种理解和意识内未被觉察的关系,而是关涉一种外在于意识关系的“似乎理解”(注:K ·雅斯贝尔斯:《普遍精神病病理学》(1946),柏林/海德堡,1973年,第452页。)。可以说, 雅斯贝尔斯关于“未被觉察的关系”与“外在于意识的关系”的区分类似于弗洛伊德关于“前意识”与“无意识的”的区分。但是,必须指出,二人之间概念区分的标准是判然有别的。在雅斯贝尔斯那里,概念区别的主要标准是可体验性、可理解性等现象,而弗洛伊德对这类传统生命哲学范畴则完全陌生。在他那里,概念区分的本质标准是所谓动力学观点。例如,他的“抗拒”(Widerstand)概念就带有明显的动力学特征。
2.内驱力
除了无意识概念,雅斯贝尔斯与弗洛伊德的思想分歧还突出表现在对“内驱力”(Trieb)概念的解释上。 内驱力概念是精神分析学说的又一基石。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内驱力学说是最有价值的学说,但也是精神分析理论中“最不成熟的部分”。弗洛伊德之所以重视内驱力,是因为这是心灵现象与躯体现象的边缘现象:“尽管精神分析工作中,生物学术语和观点无论如何都不能占统治地位,但我们不可避免地在我们所研究的现象描述中业已广泛使用了生物学术语和观点。我们只能把‘内驱力’选作心理学解释与生物学解释之间的一个边缘概念。”(注:S·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旨趣》(1913),《弗洛伊德全集》,第8卷,法兰克福,1960年,第410页。 )他后来的许多“内驱力”概念都贯穿着这一解释。在《精神分析导论新编》(1933)中,他也指出:“因此,内驱力跟某种刺激不同。一如某种恒定的力量作用,内驱力源于躯体内的刺激源泉。一如外部刺激时变得可能那样,内驱力是不可逃避的力量。在内驱力上,我们可以区别源泉、客体和目标。源泉乃是躯体中的兴奋状态,目标则是这一兴奋的扬弃。在由源泉到目标的途程中,内驱力在心理上变得有效了。我们把内驱力想象为某种驱向特定方向的一定的能量总和,由于这一驱向,它便具有驱力之名。”(注:S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新编》(1933),《弗洛伊德全集》,第15卷,法兰克福,1960年,第102页。)
弗洛伊德甚至把“愿望”(Wunsch)也解释为“心理装置中的事件”:“我们把某种出于不快而指向心理装置中的快乐之流称之为一种愿望。”(注:S·弗洛伊德:《释梦》(1900), 《弗洛伊德全集》,第2——3卷,法兰克福,1960年,第604页。)在此, 也关涉心灵领域与躯体领域之间的边缘领域。因此,在精神分析中,所谓内驱力与驱力满足、愿望与愿望的实现等,总是从两方面得到观察。一方面,内驱力、愿望等被想象为原则上可定量的自然科学概念,至少被想象为“一定的能量总额”;另一方面,这些自然科学概念又是心理学上可把握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在心理学上总是代表着那个源于躯体内的、伸进心灵的刺激。
在此,我们姑且不涉及与驱力相关的弗洛伊德的“性驱力”(sexuelle Triebkrafte)。重要的是,在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概念中,内驱力概念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他是在完全不同的方法论关系中使用此概念,并充实了新的内容。
从“冲动”(Drang)和“意志”(Wille)现象出发,雅斯贝尔斯从现象学角度限制了被体验过的人的驱力活动。内驱力被称之为“被体验过的本能,即机能。这一机能发生于每次冲动,其事件并不具有自觉的内容和目标。但是这类冲动过后,一种复杂的合目的的事件便实现其目标。”(注:K·雅斯贝尔斯:《普遍精神病病理学》(1946), 柏林/海德堡,1973年,第263页。)因此,对雅斯贝尔斯来说, 内驱力是肉体需要(如饥饿、睡眠等需要),是一种创造性形态(例如,表现冲动和描写冲动中的躯体活动),或是行为原动力(Antrieb), 即有意识地实现其目标的原动力。这一界定表明,在他那里,所谓内驱力是理解方法的实践对象。此外,雅斯贝尔斯还试图正确地评价被体验过的人类原动力的全部复杂性。例如,他认为:“快乐是有秩序的、合谐的生活机能的表现。快乐在于心灵的平衡和身体的健康。”(注:K ·雅斯贝尔斯:《普遍精神病病理学》(1946),柏林/海德堡,1973年,第264页。)
但是,在内驱力问题上,两人更重要的分歧在于,雅斯贝尔斯坚持“纯粹精神的内驱力”即“生存”(Existenz)。生存是他的内驱力秩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坚决拒绝把内驱力归结为“性驱力”(注:K· 雅斯贝尔斯:《普遍精神病病理学》(1946),柏林/海德堡,1973年,第300页。)。 尽管他承认心灵生活中存在着弗洛伊德所表述的升华的内驱力命运, 但他同时强调“精神的原动力”(geistige Antrieb )对低层次驱力的支配作用,出于生存的冲动,精神的原动力把内驱力用作工具、化作力量源泉。这就是说,升华中存在感官驱力,但感官驱力转变为全体心灵生活的要素。
由上所见,在内驱力问题上,雅斯贝尔斯与弗洛伊德的思维模式和观察方式相去甚远。弗洛伊德把内驱力理解为生物学观察方式与心理学观察方式之间的边缘概念或数量因素,雅斯贝尔斯则拒斥对内驱力的数量解释,而对此仅仅借助理解心理学加以方法论上的整理。弗洛伊德力图把被体验过的丰富多彩的内驱力尽可能还原为基本要素、基本驱力,雅斯贝尔斯则仅仅致力于从现象学上看见和描述被体验过的心灵领域及其驱力。因此,弗洛伊德是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家,他相信古老的科学思想,相信心灵现象后面隐藏着不变的本质,因而致力于一种本质终极解释,并试图把自己的理论“借助于大胆的加速度应用于全人类。”反之,雅斯贝尔斯则是倡导方法论意识和多元精神病理学理念,拒斥任何一种包罗万象的人的认识。他是康德的追随者。对于他来说,人的全体始终是理念,心理学理论仅仅是有限事实领域的想象和图景。科学只能探索真理,但不能穷尽真理。
3.抗拒和移情
关于精神分析理论,还必须提及两个基本概念:“抗拒”(Widerstand)和“移情”( Ubertragung)。弗洛伊德如此重视这两个概念,以致称之为精神分析区别于其他研究方向的主要标志。在他说来,任何研究方向,只要肯定这两个事实(抗拒和移情)并把它们作为工作的出发点来接受,那么这个方向就可称作精神分析,即使它在其他方面收效甚微也罢。事实上,抗拒理论的展开构成弗洛伊德全部精神分析发展的主线。所谓“抗拒”,就是指病人反抗医生的治疗。“抗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包含有病人已往生活中许多重要的材料。因此,克服这些反抗乃是精神分析的重要工作,是使治疗稍见成效的明证。
同样,“移情”概念对于精神分析的治疗和理论也具有深远意义。治疗学家与其病人的关系不仅受制于现实状况,也受制于移情作用,即病人移情于医生。移情可表示为热情的求爱;也可采取较为缓和的方式;假使一个是少妇,一个是老翁,则她虽不想成为他的妻子或情妇,却也想作他的爱女,里比多的愿望稍加改变而成为一种理想的柏拉图式的友谊愿望。弗洛伊德认为病人移情于医生,不是起于医生,不是起于受治疗时的情境,而是早已形成于病人内心,然后乘治疗的机会移施于医生。因此,精神分析的本质要素是:“探讨某种与疾病自身本质息息相关的内在现象。”(注:S·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1917), 《弗洛伊德全集》,第11卷,法兰克福,第10页。)进而言之,抗拒和压抑是同一历程的两面,精神分析的目的就在于克服这个抵抗,把潜意识欲望化为意识,治疗就可以奏效了。然而,这个抵抗是不易克服的,需要精神分析学家的高度技巧。
雅斯贝尔斯并未直接论及“抗拒”概念,但他从弗洛伊德的《癔症研究》中得知了与此相关的“压抑”(Verdrangung)概念。所以, 他谈到了“起于压抑的可理解的有意义的记快缺失”(注:K ·雅斯贝尔斯:《普遍精神病病理学》(1946),柏林/海德堡,1973年,第 257页。),谈到了“吞咽”(Herunterschlucken)、 防御和反感体验的压抑”等等。但他对这些概念的应用与弗洛伊德的解释截然不同。弗洛伊德把神经症分为现实神经症和精神神经症两类,认为现实神经症是性功能紊乱在躯体方面的直接反映,而精神神经症的症状则是性功能紊乱的心理反应。两者均植根于遗传的性格构造和后天的压抑体验。与此相对照,雅斯贝尔斯则认为,“压抑并未总是基于人格方面的活动,而是时常基于从未被觉察过的内驱力与愿望的对立斗争,因而基于某种‘滞留’(Zuruckstauung)。压抑本身决不导致癔病。在正常人那里, 压抑司空见惯,但并不导致心理障碍。但在某些人那里,压抑却遇上移置为被压抑物的癔症机制。在癔症症状中,‘转换’(Konversion)是病理性的,但其发生不具有分裂性质。转换伴随躯体症状发生,并且在心理上,转换表现为情感及其丧失,表现为机能障碍等。”(注:K ·雅斯贝尔斯:《普遍精神病病理学》(1946),柏林/海德堡,1973年,第377页。)实践表明,不同类型的神经症,不仅临床表现不同, 其致病因素和发病机理以及病程、预后和治疗方式也不一致。各种神经症之间的差异远远超过它们的共同之点,其异质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与弗洛伊德的生理病因说不同,雅斯贝尔斯力求从症状学上阐明癔症(被分裂的心灵生活或被压抑的情感)等神经症,具体步骤是:(1 )确定透发性心灵体验;(2)弄清内容上的症状与体验的可理解关系;(3)鉴别发泄及其症状消失下,催眠状态中的记忆丧失;(4 )分析各种无法理解的具有异质性内容的表达方式(例如,性感表情等)(注:K ·雅斯贝尔斯:《普遍精神病病理学》(1946),柏林/海德堡,1973年,第339页。)。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移情就是病人对医生的爱恋或敌意。从这一移情观中,雅斯贝尔斯意识到,精神病治疗学中最重要的是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生存与生存的关系(注:K ·雅斯贝尔斯:《普遍精神病病理学》(1946 ),柏林/海德堡,1973年,第673页。)。在心理治疗中,如果“移情”不被认识和克服,那它将变成一座极其危险的“暗瞧”。因为移情现象是起于病人典型需要的情感要求,但这种一厢情愿的情感要求会“破坏”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交往,会妨碍同一水平上的理解交往关系(注: K · 雅斯贝尔斯:《普遍精神病病理学》(1946),柏林/海德堡,1973年,第673页。)。因此, 雅斯贝尔斯的根本信念是,医生与病人之间应建立两个个体之间的理解交往关系,其前提是,“保持客观性”和“遵循看不见的距离。”医生与病人之间“常存在斗争,有时是为了威力,有时是为了澄明,”(注:K ·雅斯贝尔斯:《普遍精神病病理学》(1946),柏林/海德堡,1973 年, 第674页。)但这是一种“爱的斗争”, 即两个生存以各自不可混淆的自我存在相互介入的过程。与此相对照,弗洛伊德的治疗概念是建立在一种操纵的情感交往基础上的,它并不导致两个伙伴之间的生存交往,故永远不能成为科学努力的对象和内容。内容分析疗法有成功也有失败。病人从对他们自身和对他们的全部生活经历的详细分析中得到的满足并不能成为治愈。同任何心理疗法一样,精神分析的疗效尤其是治疗两年后的效果是无从证实的,更难以证实的是最著名的心理学家与无名之辈的治疗效果到底有没有区别。
二、人的形象和本质
19世纪末对德国的精神病学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因此,我们应从19世纪末德国精神病学的历史状况中理解雅斯贝尔斯和弗洛伊德的独特个性。
弗洛伊德是一个决定论者,他的心理学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假定心灵现象是一个连续的确定性现象。 众所周知, “决定论”(Determinismus)或因果性概念对古代至19 世纪欧洲哲学传统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例如,同时代的自然科学家v.赫尔姆霍茨、R·麦耶尔, 精神病学家T·麦尼特、C·韦尼克都属于决定论传统。弗洛伊德对传统决定论奉若神明,视其为科学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深信,不仅所有有生命的、无生命的和自然事件,而且所有心灵事件都是连续的、确定的。针对“自由意志的幻想”、“心灵自由的幻想”,他总是倡导“心灵事件的严格决定性”(注:S·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1917),《弗洛伊德全集》,第11卷,法兰克福,第42页。)。他注意到,那些有意识地被体验过的心灵生活关系总是重新呈现出“空隙”(Lucken)和“遗漏”(Auslassung),而某些心理现象(神经症、精神病症状)的出现又往往无缘无故。对这些现象,我们既不能从躯体角度也不能从有意识的心灵原因角度给出令人满意的因果说明。弗洛伊德越是关注心理事件中“空隙”和“遗漏”,他就越是假定心理深层的无意识的决定因素。由于反复扩大无意识的决定因素,在他那里,“过度决定”便成为精神分析的决定性原则:一方面,心理现象的原因获得“动机”特征;另一方面,相互抵触的动机构成“某种与原因重合的梦幻或神经症的意义”。
雅斯贝尔斯并未抹煞精神病理学研究中因果性原则的价值。“我们认识到因果性在任何地方都不会终止,并且,在某些自然事件场所里,与可理解关系相比,因果关系总是占上风。因此,在任何地方都不许禁止因果思维。”(注:K·雅斯贝尔斯:《普遍精神病病理学》(1946),柏林/海德堡,1973年,第375页。)但是, 雅斯贝尔斯坚持以自己的理解方式解释弗洛伊德关于连贯的心理决定论假定。在他看来,精神分析归根到底是理解心理学,因为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所有心灵现象都是“确定的”,即在我们的意识中是可理解的。这是一种可与自然科学的假定(一切受制于因果关系)相匹配的假定,即存在一种特殊的心理因果性,这种因果性恰恰是可理解的决定性。雅斯贝尔斯承认,反常心灵状态和症状植根于病人过去的心灵史,从中显露一张可理解关系的“完整之网”。“弗洛伊德的功绩在于,用他的‘过度决定’概念揭示了这一事实。”(注:K·雅斯贝尔斯:《普遍精神病病理学》(1946),柏林/海德堡,1973年,第330页。)
然而,在论及弗洛伊德的可理解概念时,雅斯贝尔斯明确地与弗洛伊德的“自我理解”(Selbstverstandnis)概念保持距离。 他指责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看作一门自然科学是“自我误解”。正是这一自我误解促成了弗洛伊德所谓连续的心理决定论假设。这一假设是错误的,因为弗洛伊德的自我理解是错误的。弗洛伊德要求的错误在于混淆了可理解关系与因果关系。即把一切心灵生活,一切心灵事件都视为可理解的、有意义的。可是,“只有无限的因果性要求才是合理的。而无限的可理解性要求则是荒谬的。”(注:K·雅斯贝尔斯:《普遍精神病病理学》(1946),柏林/海德堡,1973年,第452页。 )这一错误与其他错误相联系。弗洛伊德从可理解关系出发,构筑了关于总体心灵进程之原因的理论。(注:K·雅斯贝尔斯:《普遍精神病病理学》(1946), 柏林 /海德堡,1973年,第257页。)总之,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弗洛伊德在概念乃至工作方式上都存在着原则上的方法论混乱。究其根源,在于他的“自我误解”,它最终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向歧途:即试图认识“总体心灵进程的原因”。
对于同时代精神病学家的科学观来说,精神分析的诊断学以及弗洛伊德的理论图景是陌生而难以接受的。一方面,弗洛伊德总是强调他的见解的独一无二性;但另一方面,他在自身的工作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之间看不出任何原则上的方法论区别。这位精神分析创始人陷入了特殊的方法论困境:每一项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都需要科技称号,都必须动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思维图式。与传统精神病学对精神现象(梦、失误、神经症和精神病等)的解释截然不同,弗洛伊德科学努力的最终目标是把所有健康心灵生活和病态心灵生活统统归诸于质料上、数量上可描述的过程。
弗洛伊德的全部著作都贯穿着对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矛盾心理:既拥护又保持距离。这一矛盾恰恰是雅斯贝尔精神病理学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论战的决定性基础。雅斯贝尔斯深感奠定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精神病学业已停滞不前,这一感触恰恰是他的精神病学的出发点。因此,当弗洛伊德借助病人方面的具体经验构筑理论概念并证明其合法性时,雅斯贝尔斯却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方法论上,不是创造理论,而是批判地看待业已在精神病学中应用的一切方法,审查其方法论基础,进而指出其局限性。这一方法论反思,使他认识到建立在应用自然科学方法基础上的精神病学的“自我理解”是片面的。反之,其他特殊的精神科学分支虽零星地被应用于精神病学,但其本身根本没有受到正确的估价。与诸如弗洛伊德一类的同时代精神病学家不同,雅斯贝尔斯深信,科学并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方法并没有包容所有知识价值,它甚至从未包含过最重要的知识价值。因此,他强调精神科学的合法性和自主性,力倡精神病学中的现象学研究方向,要求在精神病理学中用理解心理学充实说明方法。
雅斯贝尔斯认为,弗洛伊德事实上从事一种理解心理学。但另一方面,由于弗洛伊德信奉自然科学的工作方式,其自我理解不过是自我误解。由于缺乏方法论反思,弗洛伊德学说中某些有价值的部分也变得黯然无色。因此,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弗洛伊德学说并不代表科学事实而是代表“信仰定理”(Glaubenssatze)。最终, 他像卡尔·波普一样把精神分析学说归结为“伪科学”,因为其命题是无法确证的。
雅斯贝尔斯对精神分析的批判还集中在精神分析运动的“世界观”倾向上。尽管这一缺陷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并不那么明显,但在他的学生G·荣格、F·费伦奇那里仍可以发现这一缺陷,即一种对偏执、强制、异端邪说、“心理神话学”的嗜好,偏爱将研究作为世界观、偏爱科学迷信。他感到这种嗜好和偏爱在精神分析的原则中根深蒂固了。由于弗洛伊德的发现,精神分析运动对有关人的知识作出了贡献。但是,精神分析学说声称它能提供有关人的绝对知识,给人带来完美的幸福,那是自我欺骗。精神分析学说自命为是科学的生活态度,但事实上它却抛弃了真正的科学,成为一种“新的巫术”形式。精神分析运动发展成为一个正统的信念始于弗洛伊德把不忠实的门徒逐出教门,这是具有方法论性质的内在趋势。但是,依靠社会途径获得排他性权利主张,会导致宗派的形成,导致敌视和背离科学的非理性主义后果。
弗洛伊德对所有思辩哲学思维表示极度怀疑,而把自己的“科学世界观”视为自我反思的高级阶段,而雅斯贝尔斯则强调为了防止以科学认识手段把一种恶劣的哲学加以绝对化,哲学反思是必不可少的。弗洛伊德在总结精神分析运动史时写道:“只要人代表一种强大的理念,人就是强大的。”(注:S·弗洛伊德:《无意识》(1913), 《弗洛伊德全集》,第10卷,法兰克福,1960年,第113页。)但是, 按照雅斯贝尔斯的方法论观点,科学并不能完全认识人。作为生存,人是开放的,人的本质处于一切科学可认识性的彼岸。由此可见,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之间的论战,不仅具有方法论和意识形态背景,而且直接关系到人的形象和本质这一人类永恒的课题。(注:H ·席彼尔格斯:《精神分析意识形态的历史与批判》,载于《医生与基督徒》(1969),第14页。)
三、结语
至此,我们根据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著作中所展开的同弗洛伊德的论战,指出了二人著作中的不同的方法论背景和理论背景。两位精神病学家分别代表20世纪初德国精神病学的两种典型立场。弗洛伊德始终坚持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思维模式,反之,雅斯贝尔斯则力图把现象学要素引入自己的精神病理学中。根据方法论反思和编排,他把弗洛伊德的著作看作是一种根本性方法论错误乃至精神分析创始人的“自我误解”。
在对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进行对比分析时,我们必然考虑到下述两方面的事实:一方面,迄今精神分析的科学方法论编排问题远未解决;另一方面,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概念的本质方面,尤其是可理解关系与因果关系的方法论区别虽为同时代德国精神病学家接受,但未曾经历严肃置疑或深入探讨。有鉴于此,摆在精神病学界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在澄清两人不同的观点、方法基础上,设法寻求开放性对话的基础。例如,能否用弗洛伊德的动力心理学观点,进一步深化现象学描述性精神病学的诊断学?又如,能否用雅斯贝尔斯的方法论范畴对精神分析进行科学理论上的整理和编排?这必是一项棘手的工作,但也谅必是一项富有成效的工作。
标签:弗洛伊德论文; 雅斯贝尔斯论文; 精神分析论文; 心理学论文; 无意识论文; 内驱力论文; 机能主义心理学论文; 心理学发展论文; 科学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