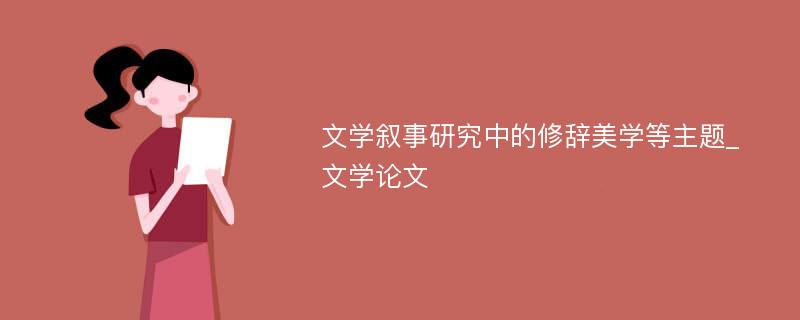
文学叙事研究的修辞美学及其它论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题论文,修辞论文,及其它论文,美学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7-0025-07
叙事学(narratology)与未来学(futurology)是截然对立的两门学科。叙事的默认时态是过去时,叙事学家如同侦探家一样,是在做一些回溯性的工作,也就是说,是在已经发生了什么的叙事之后,他们才进行读、听、看。(我不考虑以下这一复杂情况:有时候,在进行叙事分析之前,我们对叙事分析方法的运用,预示了我们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分析结果。)与此相反,未来学的默认时态是未来时,未来学家预测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他们通常是处于对多种条件、力量、人物等决定未来的因素了解甚少的压力下努力工作;因此,不能用未来学家的分析来解释叙事学家的分析。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一不可解释性很令人启发,而我却认为它非常令人沮丧。这一反应或许可以解释为:为什么我是叙事学家,而不是未来学家。的确,它解释了为什么我选择通过评介文学叙事研究的历史之于当下研究工作的意义,来预测叙事理论的未来。说得更具体点,我对当下的文学叙事研究做了一个大致的回顾,区分了目前文学叙事研究的五大显著论题,而我所讨论的重点则是第五个论题。这五个论题分别为:非模仿叙事(nonmimetic narrative),数字叙事(digital narrative),真实与虚构之分(the fact/fiction distinction),叙事空间(narrative space)以及修辞美学(rhetorical aesthetics)。
当下,文学叙事研究不仅充满活力,而且种类繁多。说它充满活力,是因为发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更为普遍的叙事转折(narrative turn)将文学叙事研究放置于一个更大的语境之中。文学叙事现在被更为明确地、毫无争议地认为是叙事的种类之一。它与法律、医学等其它叙事相关,但又与它们有着明显的不同,并由此产生了以下两种结果:(1)尽管研究方法不同,文学叙事研究依然有较大的潜在研究价值。即便对于使用叙事来解释经验、组织知识的对话,这项研究工作也是大有裨益;但是,这项研究工作也受到其研究结果是否仅仅适用于文学叙事这一特例的检验。(2)其它类别的叙事研究为文学叙事打开了新的视野,或是彰显了它们与文学叙事的共同之处,或是强调了它们与文学叙事的区别,或是修正了我们对文学叙事的理解。例如,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在《困惑的坦白:法律与文学的认罪》(Troubling Confessions:Speaking Guilt in Law and Literature,2000)一书中,创造性地并置了复杂的犯罪坦白的法律处理与虚构文学或非虚构文学中的坦白分析。
叙事理论与广阔的批评理论潮流之间所保持的对话,使得当下的文学叙事研究呈现出多样性色彩。文学叙事研究不再以单一的正统研究方法为主导,而是以一系列的研究方法为特征:形式主义、女性主义、认知科学、修辞理论、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等。在这些研究方法中,特别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方法之间几乎没有冲突。相反,不同研究模式的实践者一般都乐意相互学习,用其它方法的洞见来提升自己的研究质量,得出自己的结论。
本文因篇幅所限,不可能将每一种研究方法都详加讨论。读者若想更清楚地了解这些研究方法,可以翻阅近几年发表在《叙事》 (Narrative)、《叙事理论学刊》。(JNT: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当代诗学》(Poetics Today)以及《文体》(Style)等杂志上的论文,也可以阅读布莱克维尔出版社出版的《叙事理论指南》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一书所收录的 35篇论文、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的“叙事理论与阐释”(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of Narrative)系列丛书以及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的“叙事前沿系列”(Frontiers of Narrative Series)丛书。当然,还有很多的著述没有被一一列举出来,我在此所陈述的只是文学叙事研究领域的部分内容,并且以讨论如下五个显著的研究论题为主。
一、叙事理论与非模仿叙事传统
那些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文学叙事的著述,都力图将再现社会现实的小说视为研究对象。例如,韦恩·布斯(Wayne C.Booth)的《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1961)、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的《叙事话语》(Narrative Discourse,1980)以及米歇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小说话语》(Discourse in the Novel,1981)等。布莱恩·里查森(Brian Richardson)在《不自然的声音》(Unnatural Voices,2006)一书中,颇有说服力地指出,模仿趋向(mimetic orientation)导致了人们对叙事本质,尤其是对叙事话语的本质做出了误导性的概括。理查森以悠久的反模仿叙事文学传统为理据,建议对那些被普遍接受的关于叙事话语的认识做出多处修改。在这些修改建议中,他分析了第二人称(或直接称谓)叙述、第一人称复数叙述、多人称叙述。除了讨论这些具体论点之外,理查森的这本著作还直接指向非模仿叙事传统的研究以及其对叙事理论的影响。
二、叙事理论与数字叙事
处在2006年,我们意识到,对数字技术的来临以及对早期“超文本叙事”发展的兴奋,使我们过于夸大了数字叙事和文本叙事之间的区别。但是,随着数字叙事的持续发展,以及叙事艺术家继续以这种新媒介进行创作,数字文学叙事的重要性和广泛性只会增加。因此,叙事理论需要评价叙事媒介的长处和短处——用这些发现来理论化数字叙事与文本叙事之间的相似和差别,这样就可以增加我们对二者的理解。玛丽—劳勒·瑞安(Marie-Laure Ryan)在《作为虚拟现实的叙事》(Narrative as Virtual Reality,2001)一书中,将数字叙事以及由数字叙事激发的互动性,放置于由文本叙事产生的虚拟现实及由文本叙事激发的浸入语境之中,为数字叙事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叙事理论及虚构与非虚构之分
詹姆斯·弗雷(James Frey)《岁月如沙》(A Million Little Pieces,2003)一书的杜撰风波吸引了近期媒体的注意。一开始,著名的电视脱口秀主持人欧普拉·温弗莉(Oprah Winfrey)为其主持的《读书俱乐部》栏目选择了该书,在得到有关该书杜撰的消息之后,又从栏目的书单中删除了该书,再次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至由来已久的关于虚构与非虚构之分的论争。弗雷的书是否从回忆录的文类走向了虚构类文学?或者说,尽管该书的伦理缺陷已经为公众所熟知,但它是否还属于回忆录这一文类?读者和评论家对于叙事是否具有真实性的陈述,提出了叙事是否内在地具有虚构与非虚构标记的问题。尽管多里特·科恩(Dorrit Cohn,1999)为所谓的“虚构性标记”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然而,对这一问题,目前学界还没有一致的回答。在我看来,这场论争将还会继续进行下去,苏珊·兰瑟 (Susan Lanser,2005)的观点应该是最有新意的。兰瑟并没有对虚构与非虚构做出严格的二元对立式划分,而是区分了附加文本、隔离文本以及平行文本等三种类型。在诸如学术论文的附加文本中,话语中的第一人称“我”与作者是完全等同的,而在诸如不可靠叙述的虚构类型的隔离文本中,话语中的第一人称“我”与作者是有区别的。在平行文本中,第一人称“我”有时候是附加的,有时候又是隔离的。这些区别使得兰瑟颇有说服力地认为,小说是典型的隔离文本。例如,无论何时,只要作者利用叙述者之口对世界本质做出归纳,读者都可以凭借直觉辨认出其中的附加话语。兰瑟的方法不在于——也不试图在于——解决所有关于虚构与非虚构之分的论争,而是在于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一个新的途径。
四、叙事空间
诸如热奈特(Genette,1980)、保罗·利科 (Paul Ricoeur,1984-88)、彼德·布鲁克斯 (Peter Brooks,1984)以及戴卫·赫尔曼(David Herman,2002)等叙事理论家,皆对叙事时间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实际上,虽然叙事与时间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是可以客观公正地说,文学叙事理论在叙事话语和叙事时间等研究课题上了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叙事时间比较起来,叙事空间被相对地忽略了。然而,近年来,随着不同派别的批评家将注意力转移到叙事空间这一重要课题上,叙事空间被忽略的局面正在发生改变。在此,仅举两例,苏珊·弗里德曼(Susan Friedman,2005)近期倡导建立一种所谓的“空间诗学”(spatial poetics)。空间诗学不仅承认空间与时间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不再视空间为一个静态的背景,而是将它视为叙事结构的一个动态因素。玛丽—劳勒·瑞安(Marie-Laure Ryan,2004)从认知视角出发,倡议建立一种“文学地图”(literary cartography),即读者用来重建叙事空间心理地图的分析策略。
五、叙事美学
对这一论题的研究至少有两个新的趋势: (a)在经历了数年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之后,文学理论回归到探讨文学作品作为艺术客体的质量与美的问题;(b)很多从事叙事伦理研究的批评家,意识到文学叙事的伦理之维与美学之维之间的交融性。我近来在修辞理论领域所做的研究也是循着这样的认识(Phelan,2005,2007),也使用了叙事判断的概念来探讨伦理、美学以及用以区分它们二者的方法。
修辞性方法将叙事定义为某人在某种场合出于某种目的告诉某人发生了什么事,这一定义旨在说明叙事所具有的文本动力(textual dynamics)(叙述已经发生的事情)和读者动力 (readerly dynamics)(在听到关于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叙述之后,某人的反应)。实际上,修辞性方法将叙事进程定义为文本动力与读者动力的综合。而叙事判断是这一方法下一个有用的概念,因为它直接将文本动力与读者动力联系在一起:叙事判断虽然是通过讲述传达出来,但它同时也是读者的活动。
我还要区分以下三种不同类型的叙事判断:阐释判断(将某事视为X而不是Y的决定),伦理判断(关于构成人物活动价值、叙述者活动价值以及作者活动价值的决定),美学判断(关于叙事总体质量和具体质量的决定)。我进一步注意到,这三种叙事判断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我们如何阐释人物的行动,会影响我们对人物行动伦理之维的判断,而对伦理之维的判断又会影响我们对这一时刻的叙事,以及最终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叙事的判断。此外,同阐释判断与伦理判断并无二致,美学判断也是我们叙事修辞经历的一部分。美学判断不仅为阅读之后的活动服务,而且还为阅读过程服务。因此,我想把叙事判断的概念作为用来理论化形式、伦理、美学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方法。
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在美学判断必须具有公正性概念这一问题上,学界还存在一定的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至少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自“个人偏好”(de gustibus)传统,认为对叙事质量的判断是个人品味的东西,因此会不可避免地反映出我们的主观兴趣。很少有理论家会像热奈特一样,近期在一篇名为《什么是美学价值》(What Aesthetic Values?)的文章中,为这一反对意见提出新的见解。热奈特认为,做出美学判断无异于对价值做出判断,而对价值的判断总是对某人自己而言的价值的判断,因此又是主观的。对我有价值的东西,并不一定对你也有价值,反之亦然——因此,没有一个人能通过呼吁艺术客体的公正性,来说服对方接受不同的判断。
另一方面,以政治批评为中心的批评家反对美学批评,这些批评家认为美学判断是一个或另一个更大的权力体系的功能之一。这些关系有可能是社会阶级所造成的——美学判断有可能是维护阶级差别的一种方法。那些有钱的有闲阶级可以奢侈地为乔依斯或品钦作品中的难点而感到焦头烂额,而这一焦头烂额行为,又将会加剧他们同那些没有时间阅读文学作品的阶级之间的差别。或者,从政治信仰内在化为第二性质这一意义上来说,美学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功能。在这一点上,尽管从公正的美学判断来陈述,一个人依然可以认为20世纪80年代之前很多的男性文学经典都是如下意识形态的结果:处于权力地位的男性认为,男性作品的质量在总体上要高于女性作品。
这些反对意见使我对美学普遍性的主张产生了怀疑,但是它们不能使我放弃研究修辞美学,修辞美学类似于我在《为了生存的讲述》 (Living to Tell about It,2005)一书中提出及后来在《体验小说》(Experiencing Fiction,2007)一书中进一步发展的修辞伦理(rhetorical ethics)。修辞伦理不是寻求在一个具体的伦理体系上建立自己的基础,而是致力于揭示出构成具体叙事的伦理,是叙事潜在地要求读者在阅读叙事时所要接受的价值体系。修辞伦理下一步所要做的工作是参与叙事伦理与我们阅读叙事时所产生的伦理之间的对话,这一对话能扩展并包括其他读者的伦理反应。如果这一对话能够真正得以展开,那么它可以使读者更改——改变、加深、扩展了他们的伦理信仰。
无论是从叙事内部还是到更大的质量判断,修辞美学都起着作用。通过以下两个因素,修辞美学得以开始:(a)根据具体叙事因子在更大叙事(larger narrative)内部的目的,来决定其质量,(b)根据更大叙事所确定的条件,来决定其质量。接着,修辞美学走向评价与一个人在阅读中所产生的美学标准相关的条件;对参与叙事会引起新的美学标准的观点,它持开放态度。在我讨论下面这些具体例子的时候,这些论点应该会更加明晰。我将以雷蒙·钱德勒 (Raymond Chandler)的小说《沉睡》(The Big Sleep,1939)及由小说改编的电影为例,该电影由霍华德·霍克斯(Howard Hawks)指导,亨佛莱·鲍嘉(Humphrey Bogart)、劳伦·巴考尔 (Lauren Bacall)主演。
正如彼德J.拉宾诺维茨(Peter J.Rabinowitz,1987)与戴卫·里克特(David Richter,1994)所指出的那样,钱德勒的小说不同于一般的侦探小说,因为主要人物侦探菲利普·马洛最后没有与主要的反面人物艾迪·马斯面对面。此外,虽然马洛查出了杀死拉斯蒂·雷根的凶手,然而犯罪的消除并没有恢复他所在世界的秩序。相反,小说最后以马洛的这段叙述文字结尾:
在你死了之后,躺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呢?在一个肮脏的污水坑或是在小山峰上的一个大理石塔上?你死了,你在沉睡,你不会受到诸如那样事情的困扰。对你而言,水与油、风与空气都无甚重要了。你只是在沉睡,不在意你死的是多么恶心以及躺在哪里。过去的我是现在的恶心的一部分。比拉斯蒂·雷根还要恶心。但是这个老人没必要成为恶心的一部分。他可以平静地躺在华盖床上,他那没有血色的双手叠在已经等在那儿的垫子上。他的心脏有一阵不安的咕哝。他的思绪苍白得像尘土。很快,他就要像拉斯蒂·雷根一样,进入沉睡之中。
在去市中心的路上,我进了一家酒吧喝了两杯Scotches酒。但是两杯Scotches并没有使我感觉好点。它们所做的只是让我想起了Silver-Wig,而我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她。(pp.230-31)
霍克斯指导的影片有着不一样的结尾。马洛(由鲍嘉扮演)与马斯在阿瑟·盖格尔家中相遇了,马洛用计使马斯在走出门外时死在他同党的枪口之下,秩序得以重新确立。另外,马洛得到了维维安·斯泰伍德(由巴考尔扮演)的帮助,在马斯死后,他们在电影中的调情演绎成了情窦初开的浪漫,电影的最后一幕镜头以两人互视对方的眼睛而结尾。
从修辞美学视角看来,在更大叙事的条件下,每个结局在美学上都是令人满意的;而在各自的条件下,每个叙事在美学上也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小说的结局是比电影结局更大的美学成就的一部分。不止于此,此判断是每个叙事的形式、伦理、美学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果。
当钱德兰没有走入侦探与敌人最终碰面的叙事俗套,他就面对了一个如何为叙事提供完整性的问题。通过聚焦于侦探对叙事中先前事件的理解,而这些理解又暗示了这些事件如何永远地改变了侦探,钱德兰机智地解决了叙事完整性这一问题。小说不断重复的一个主题是,马洛是一个追求维护或重新恢复被这个世界所忽视的价值的现代骑士,这些价值包括:献身真理、实现顾客最大利益的承诺、对那些视正直高于金钱、高于舒适的人们所承担的责任。小说的结尾表明,马洛这一现代骑士在自己的追寻征途中妥协了,因为他所斗争的邪恶太过于普遍,以至于使他在相互竞争的价值观之间做出了一个令人不满意的选择。小说的结尾还表明,对于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马洛没有犹豫:他决定不让斯泰伍德将军得知他女儿谋杀拉斯蒂·雷根的原因是因为雷根拒绝了她的性要求。但是,这一决定等于说,马洛最终成为维维安和马斯二人掩盖谋杀罪行的同谋,也使他成为“恶心的一部分”;而且,马洛的困境没有出路,没有真正的安慰(饮Scotch酒,或是对Silver-Wig的回忆)。简言之,通过让马洛反思叙事事件,来传达他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困难却令人仰慕的伦理选择,尽管这个选择毫无用处。钱德兰最终毕竟解决了叙事完整性的问题。换句话说,钱德兰通过马洛在整个叙事中所做出的一系列的伦理选择,替换了侦探小说恢复秩序的俗套。认同钱德兰的叙事形式,也就等于认同其叙事的伦理细节与美学质量。
霍克斯所指导的电影的结尾,在其叙事条件下也相当不错,因为它为叙事的两个主要不稳定因素提供了令人非常满意的解决方案:马洛与马斯之间的冲突以及马洛与维维安之间的冲突。为了能使马洛与维维安之间的关系成为电影的主要不稳定因素,霍克斯还使用了干涉马洛查案的潜在不稳定因素,这一潜在不稳定因素的实现与否,依赖于每个人物的伦理选择。维维安不想让马洛发现马斯对她的控制,因此她努力将马洛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们俩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从而使马洛不会再继续追问是谁杀了拉斯蒂·雷根的问题。因为斯泰伍德将军没有明确地要求马洛来追查这个问题,因此维维安奢望自己能取得成功。但是,霍克斯电影中的马洛与钱德兰笔下的马洛一样,都忠贞于自己所追求的事业,以及他感觉斯泰伍德真地想知道拉斯蒂的死因。在马洛第一次与马斯的亲信拉什·卡尼诺以及后来与马斯本人面对面时,通过让维维安来帮助马洛,霍克斯暗示道:维维安接受了马洛的价值观,这种选择最终使得维维安从马斯身边解放出来,并使她为自己和马洛之间的相互吸引,做出了更为自由的行动。通过这种方式,霍克斯的结尾不仅揭示了马洛通过除掉马斯来恢复秩序,而且还为马洛与维维安的终极伦理选择提供了回报。鉴于更大叙事,电影的结尾是恰当的、有效的、令人满意的。
同时,由于以下两个原因,霍克斯的结尾不如钱德兰的结尾成功:形式上不够挑战性;读者对伦理信仰的参与性不够意义重大。相反,霍克斯的结尾以传统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熟悉的“善有善报”式的安慰。从使用叙事条件来判断叙事,再到直接判断这些叙事条件,为了说明这样的美学判断,我打算解释两个重要的总体标准(general criteria):(1)与成功地遵循传统的叙述结构相比较,使用有难度的叙事形式是更大美学成就。(2)同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相比较,使读者参与同解决叙事形式问题紧密相连的复杂的伦理判断,是更大的成功。但是,即便在阐述这些标准的时候,我想说明的是,这些标准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它们不能超出钱德兰与霍克斯的叙事所起作用的条件。其它类型的叙事有可能使其它的总体标准与我们的美学判断更为相关。
本文只能简单地讨论或揭示几个有吸引力的、有争议性的——关于形式、伦理、美学之间相互关系的论题,这些论题必定会伴随着在美学判断方面产生的新兴趣。在此,仅以几个其它论题为例。尽管修辞伦理与修辞美学之间的类比是有用的,那么在哪些方面这些类比有可能具有误导性?在叙事进程中所做的美学判断与叙事进程后所做的美学判断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一个人如何在主张总体标准多元化的同时,又不落入关于个人偏好问题的窠臼?判断一个给定叙事条件的选择标准,究竟能走多远?它们又在何种程度上是合适的?鉴于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将结束此文并满怀信心地预测未来:我将为这些问题寻求令人满意的答案,而不懈努力。
(本文原为James Phelan,“Rhetorical Aesthetics and Other Issues in the Study of Literary Narrative,”发表于美国Narrative Inquiry,16:1 (2006):85-93。本文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作者费伦教授的帮助,译者在此向他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