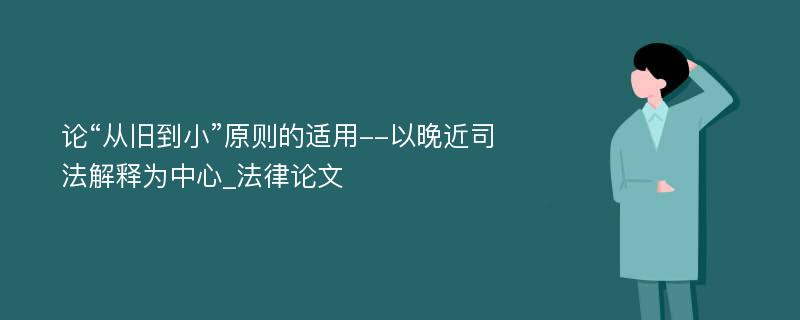
论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以晚近司法解释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司法解释论文,原则论文,晚近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现行《刑法》)第12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该规定即《刑法》时间效力上的从旧兼从轻原则,若干司法解释对其进行了详尽的解释。但上述简略规定仍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其作些细致分析。
一、1997年10月1日之后是否还能适用类推定罪
一般认为,类推制度与罪刑法定原则存在着直接的对立和冲突。由于现行《刑法》废除了类推制度,而在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从而导致在1997年10月1日即现行《刑法》生效以后审理此前发生的适用类推的案件时,如何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产生了一定困难。最大的问题在于:现行《刑法》第3条的规定是否能够在决定类推案件时予以适用,即在1997年10月1日之后,将现行《刑法》第3条适用于1979年《刑法》,凡是“原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能定罪处刑,因此对于按照当时应类推定罪的行为,现行《刑法》即使规定为犯罪的,也应当按照从旧兼从轻原则宣布不构成犯罪。这一问题实际就是学者所谓的从旧兼从轻原则是否绝对的问题。(注:参见陈忠林:《关于刑法时间效力的几个问题》,载杨敦先等主编:《新刑法施行疑难问题研究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版,第342页。作者认为,既不能将现行《刑法》第3条绝对地适用于从旧兼从轻原则,也不能把按照1979年《刑法》的规定需要类推定罪的行为,都按照现行《刑法》新增的相应条文定罪处罚。但对其法理依据未作详细论证。)
对此,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的过程中,曾经有人认为,1997年10月1日之后一律不应适用类推,因为此类行为《刑法》原来就未规定为犯罪,现行《刑法》又未规定可以类推,按照从旧兼从轻原则,不应再适用类推。但是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不再核准类推案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第2条指出:对于按照修订前的刑法需要类推定罪,修订后的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一律不得定罪判刑;对于按照修订前的刑法需要类推定罪的,修订后的刑法也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如需追究刑事责任的,应适用修订后刑法第12条的规定处罚。第3条规定,1997年10月1日以后,各级人民法院审理发生在1997年9月30日以前,按照修订前的刑法需要类推定罪的案件,应当按照本通知第2条的规定办理。这些规定实际说明,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于1979年《刑法》需要类推定罪同时现行《刑法》也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仍然按照从旧兼从轻原则处理,不应将现行《刑法》第3条的罪刑法定原则适用于此类情形,因而并非一律不适用类推。
刑法的适用过程具有其整体性,即在定罪量刑过程中,在已经决定适用哪一部刑法的前提下,应将该已被确定适合的刑法整体地运用于某一案件中,而不是将其中某一条文和另一刑法中某一条文相并合地适用于这一案件,即不能同时适用两个以上不同刑法的条文。从旧兼从轻原则也只能决定究竟应该适用哪一部刑法,诸如现行《刑法》第12条等类似的条文仅仅是确定适用哪一部刑法的规范。在决定哪一部法律对于被告人最为有利时,只能要么适用新法,要么适用旧法,在这两者之间选择其一,而不能将新法和旧法的规定加以分解,然后将其中有利于犯罪人的因素组合拼凑为一个既不同于新法、也不同于旧法的综合性规范,否则就成了由法官来制定适用的法律规范。(注:参见[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陈忠林:《意大利刑法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但是意大利刑法学家贝特洛切利对此持相反看法。)同样,现行《刑法》第3条所谓的“法律”也仅指现行《刑法》以及其后作为该法体系之内的规范,而并不是指现行《刑法》之前的规范。正是刑法适用的整体性原则决定,不能将现行《刑法》第3条适用于按照1979年《刑法》定罪量刑的案件中。因此,如果按照从旧兼从轻原则决定适用1979年《刑法》,而1979年《刑法》既然规定了类推,毫无疑问就应当适用类推定罪量刑。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上述司法解释的相应结论是合理的。
但是问题远非如此简单。《通知》第1条规定:1997年10月1日以后,各级人民法院一律不再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第79条的规定向我院报送类推案件。(注:相关司法解释的讨论案曾认为,1997年10月1日以后一律不再适用类推,个别案件或者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或者直接以盗窃、诈骗犯罪从轻处罚。在此,我们并不讨论在现行《刑法》适用前提下适用类推的必要性,因为所涉及的必然是极其个别的案件,我们仅仅是在严格遵循《刑法》规定的前提下讨论这类案件的法理运用。)这一规定与上述结论的矛盾之处在于,既然需要按照从旧兼从轻原则而依照1979年《刑法》类推定罪,而按照这一规定,基层法院可以直接适用类推程序而无须按照1979年《刑法》第79条规定必须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显然又没有整体地适用1979年《刑法》有关类推的实体和程序的所有规定。对于类推适用,我们一直采取了极为谨慎、控制的态度,而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程序限制是最为重要的控制手段。由于我国并未建立判例制度,所谓最相类似的条文并没有确定性,而如果类推罪名不准确,那么和现行《刑法》相比其量刑何者为轻就会更加错误,最终导致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错误,侵害当事人的利益。因此同样基于法的整体适用原则,所有类推案件仍应当按照1979年《刑法》第79条规定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也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被外界苛责在罪刑法定原则确立之后仍然核准类推,恰恰相反,在决定从旧适用的情况下,只有依法核准类推才是程序合法公正的体现。
应当注意的是,在适用类推的情况下,虽然按照1979年《刑法》第79条的规定,被类推的行为应当按照本法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从轻的比较应当在1979年《刑法》中被比照罪名的刑罚和被类推的行为在现行《刑法》中新确定罪名的刑罚之间进行,而不是在被比照罪名的刑罚与该罪名在现行《刑法》中的刑罚之间进行。
二、从旧兼从轻原则的整体适用抑或选择适用
与上述类推适用的问题直接相关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即从旧兼从轻原则中,究竟是应当整体适用(即所谓的“从”)某一相对较轻的法律,还是选择适用数法律中对于犯罪人有利的法条?
如上所述,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中,存在大量的选择适用的例子。例如《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犯罪分子1997年9月30日以前犯罪,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需要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第59条第2款的规定。”而同一解释的第5条却又规定:“1997年9月30日以前犯罪的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适用刑法第68条的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出现在同一判决中,基本的定罪量刑适用某一刑法的分则规定,但是在某些总则性问题上,有的却适用另一刑法的规定,或者在这些总则性规定适用过程中,有的诸如减轻处罚的适用援引旧法的规范,而另一些诸如立功的适用援引新法的规定,导致适用法律混乱。
上述解释虽然都是在遵循从轻原则下所作的选择,但是仍应受到质疑。笔者认为,所谓的从轻不应当是指每一具体法条的两两比较(从而寻找在不同性质的规范上对于犯罪人都为有利的规定,而无视其法源的不同),而是在两部法律之间寻找一个整体上处刑较轻的法律(在决定对某一行为适用哪一法律的基础上,不允许再采用其他法律中单独地看可能对犯罪人更为有利的法条)。显然,必须照顾到法适用上的整体性,避免法的支离破碎,而使不同效力阶段的法律(已经废止的和现行生效的法律)在同一判决中得到同样的重视和应用,导致不同效力阶段的法律在同一适用阶段产生冲突。在整个有效的法体系中,有效的法律或者应当被予以适用的法律(在刑法中,对于当时发生的行为,当时的刑法即使已经被废止,但在适用的意义上也可能被特殊地认为仍然有效),是整个法律中的所有规范而非个别法规范。个别法规范不能脱离整体法律的效力而单独存在,前者只有作为后者的一个细胞才具有适用上的法律意义。同时,法律整体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在逻辑性,条文之间必然相互协调,某一制度的废立也往往在整体上同另一制度的废立相配合,同整体刑法的价值理念相符。而混合适用不同法律的法条却反其道而行之,打乱了法律的内在逻辑,混合了不同的价值观。总之,在法的适用上,不应当同时出现多个对于刑事法律关系进行规制的有效法律。
因此,在轻法的寻找过程中,法官必须将他手头的案件对照多个法律规定中的第一个法律来斟酌,然后再考虑第二个、第三个或其他所有法律规定来认定犯罪人的犯罪事实,并科处刑罚,不同法律规定中的任何联系(实际指并合适用)是绝对禁止的。(注:参见[德]弗兰茨·冯·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也就是说,是从一轻的法律,而不是从若干轻的法条组合。只有将各种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并将犯罪人应承担的具体后果进行综合比较之后,才能得出相对较轻的结论。在我国台湾地区,这一见解也成为实务界和理论界的通说,该说认为法律之比较,应就罪刑有关之一切情形比较其全部之结果,而为整个之适用,不能割裂而分别适用有利之条文,如旧法为有利,则全部适用旧法,如新法有利,则全部适用新法,保持法律之整个体系,不可新旧法掺杂适用,紊乱系统。(注:参见高仰止:《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85页;刁荣华主编:《最高法院判例研究》(下册),台湾汉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谢兆吉、刁荣华:《刑法学说与案例研究》,台湾汉林出版社1976年版,第49页。中华民国最高法院刑事庭总会1935年7月曾决议:关于刑法第2条第1项但书适用之方法如下:(一)先审查应否谕知无罪,次审查应否谕知免诉或不受理,再次则审查有无法定必应免刑之情形。(二)如无前开情形,则比较新旧法之罪刑孰为最有利于被告者,其比较之标准如下:比较时应就罪刑有关之共犯、未遂犯、连续犯、牵连犯、结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减轻,暨其他法定加减原因与加减例等一切情形,综其全部罪刑之结果而为比较。酌量减轻则毋庸比较。参见高仰止:《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89~90页。)总之,所谓新旧法律何者为轻,只有在综合各种定罪量刑要素,对新旧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后犯罪人应当承担的具体后果进行综合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相关司法解释的参照也是必需的。显然,按照整体性原则,上述司法解释均存在一定矛盾,在能够认定整体上属于处刑较轻的刑法而加以适用的前提下,相应地关于量刑过程中需要考察的诸如立功、自首等因素都应当并且已经在前一阶段即整体考察何一刑法为轻的过程中得到考虑,因此在有关自首、立功等具体规范之间完全没有必要作出如何从轻的解释。
有的学者认为,新旧法律之间可以交替引用,比如定罪量刑时适用旧法,但是适用刑罚时依照新法,或者相反。(注:参见曲新久:《刑法的精神与范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7页。)在法国,对于这一问题一定程度上采用了与上述司法解释相类似的办法。对于新法中既有比旧法更为轻的规定,也有比旧法更为重的规定,比较新法相对于旧法而言究竟是轻还是重,很难作出评判,例如1891年3月16日的被称为“贝让热法”的法律即属于这种情形,该法在规定某些刑罚缓期执行的同时,又创立了“小累犯”矫正刑(少年犯的轻罪刑罚),这是加重刑罚的一种原因。对此,该法的这两部分规定均分别得到适用。比旧规定更为温和的有关缓期执行的规定适用于该法之前犯罪的初犯犯罪人,相反,对累犯加重刑罚的规定也就是更为严厉的规定,不适用于该法颁布之前实施的犯罪行为。1980年12月23日有关强奸罪及侵害他人贞操并对《刑法典》第331条及随后条款的规定进行修改的法律,也是这种情况。(注:参见[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法总论精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165页。)也就是说,在可以予以分割的情况下,新法中较轻的规范可以溯及适用于以前的行为,但是新法中较重的规范不能适用于以前的行为。
法国刑法的上述规定虽然并不一定针对同一当事人,但其精神同上述司法解释基本是一致的。关键在于,如此一来,刑法适用的整体性就遭到了破坏。就现行《刑法》第12条的字面含意而言,也只是就是否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角度而在“当时的法律”和“本法”之间进行整体比较,而不是在具体规范之间的两两比较,并进而决定在个别规范之间进行从轻选择。而是否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比较,是在定罪量刑过程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既然定罪量刑已经决定适用哪一刑法,即意味着上述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交替引用刑法就没有必要。如果所谓刑罚的适用是行刑过程中的规则适用,涉及的问题就是如下所述行刑规范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
三、行刑过程中相关刑法规范的溯及力
在此主要是指假释、减刑等规范的适用。对于这一问题,相关司法解释采取了相互矛盾的双重标准。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9条规定:1997年9月30日以前犯罪被宣告缓刑或者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1997年10月1日以后的缓刑考验期间或者假释考验期间,又犯新罪、被发现漏罪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应当适用现行刑法相应条文撤销缓刑或者假释。(注:对于撤销缓刑,在该司法解释制定过程中,曾经有人认为根据从轻兼从旧原则,既然适用旧刑法对犯罪人有利,应当适用旧刑法。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及大多数专家则认为适用新刑法撤销缓刑并不违背从旧兼从轻原则,但其理由是:犯罪人在缓刑考验期间的违法、违规行为是发生在新法施行期间,犯罪人明知或应知新法规定此种情况要撤销缓刑,却仍然实施了违法违规行为,这表明犯罪人的恶性较深。)同样,其第7条规定:“1997年9月30日以前犯罪,1997年10月1日以后仍在服刑的犯罪分子,因特殊情况,需要不受执行刑期限制假释的,适用刑法第81条第1款的规定,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是其第8条规定:“1997年9月30日以前犯罪,1997年10月1日以后仍在服刑的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第73条的规定,可以假释。”(注:对此,在该司法解释制定过程中,专家多数同意,可以适用旧法规定予以假释,理由为:犯罪是发生在旧法施行期间,只要符合旧法规定的假释条件,就应当予以假释,否则不符合从旧兼从轻原则。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认为应当适用新法,不得假释,理由为:如果假释,则可能新法实施几年或者十几年以后,还要用旧法来裁判假释案件,并且不得假释也并未继绝犯罪人的自新之路,对符合条件的可以适用减刑。)
上述规范在标准上存在着双重性。对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规定而撤销缓刑或假释采取了从新且从重的标准(1979年《刑法》并没有在此情况下撤销缓刑或者假释的规定),对于特殊情况下的假释的程序限制也是如此(1979年《刑法》并没有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限制);但是对于假释的前提条件却采用了从旧兼从轻的原则。这一规定的弊端在于;首先,对于同一假释犯,存在着在宣告假释阶段适用旧法,而在撤销假释阶段适用新法的可能,而且旧法和新法在对犯罪人的利益保护上并不一致。其次,存在着在只要尚未经过漫长的追诉期间,就可能在新法实施后许多年甚至十几年仍然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旧法宣告假释的可能。
上述矛盾实际来源于从旧兼从轻是否适用于程序性规范这一问题。对此,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仅仅将这一原则适用于实体法中,但不适用于程序法。《法国刑法典》第112~2、3、4条确立了刑事程序法律即时适用的原则,其理由是:程序性法律既不变更犯罪的特征,也不改变犯罪人的责任与刑罚的确定,仅仅与认定犯罪及追诉犯罪、案件管辖与追诉程序、执行刑法和执行拘禁有关,而且被推定高于旧法并且旨在保障最佳司法的新的程序法应当即时适用。(注:参见[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法总论精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在日本,也认为刑事诉讼法是适用诉讼行为时的新法。(注:参见[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但在英美法系,美国最高法院在1789年Calder诉Bull案中,将溯及既往的范围适用于任何为了证实犯罪而改变法定的证据规则,因而允许采纳比犯罪时法律所要求的不同的或较多的证据的法律。(注:参见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但是并非任何程序规则都能够溯及既往。由于证据规则的改变可能导致定罪量刑的完全不同,因而直接影响到行为认定及量刑的结果,所以可以从轻溯及既往。但是有关缓刑、假释的撤销,是在犯罪人刑事责任确定之后的事情,对于其定罪量刑并没有任何关系,根本不属于现行《刑法》第12条从轻原则范围内的事项。因此,对于不影响实体责任的程序规则不存在从轻的问题。固然,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或者影响实体的程序性规则的区分在一定情况下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上述司法解释关于缓刑、假释的撤销适用新法的程序规定,虽然对于犯罪人而言似乎是从严处理,仍然是符合上述要求的。因为,应当按照新法撤销缓刑或者假释的原因,并不在于犯罪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新法规定较为严格的考验条件因而具有较大恶性,而在于上述程序性规则所具有的即时适用性。
但是适用假释的前提条件从旧却并不符合上述逻辑。这一规定虽然是从轻因而对于犯罪人有利,但是问题关键在于适用假释时是否有必要考虑旧法或轻法?《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0条第1款规定,规定行为构成犯罪、加重刑罚或以其他方式恶化犯罪人状况的刑事法律,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理论上认为对正在服刑的被判刑人进行假释的条件更为严厉的法律属于恶化犯罪人状况的法律,因此没有溯及力。(注:参见[俄]斯库拉托夫、列别捷夫主编:《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3页。)而在法国,新的程序性法律的即时适用受到限制,即不得侵害当事人已经取得的权利。(注:参见[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法总论精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
如上所述,从旧兼从轻的适用范围是定罪量刑的内容。而假释所涉及的仅仅是在定罪量刑之后,在刑罚执行阶段考察犯罪人的改造状况而决定是否对其进行优遇的一种措施,同其本身的定罪量刑完全没有关系。犯罪人在改造阶段是否遵守有关规定,从而是否能够适用假释,是决定某人的刑事责任的判决不应予以考虑的内容,也不属于现行《刑法》第12条所谓的“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范围。“有利于被告人”和“处刑较轻”这样的法律措辞也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即使假释条件属于决定被告人是否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的规则,但也并不属于现行《刑法》规定的处刑较轻问题。而且在旧法失效如此长时间之后,仍然适用旧法宣布假释,有违新法的效力原则,使新法的尊严受损;同时将是否适用假释不仅取决于改造表现,而且取决于犯罪时间,也无法说服具有同样的改造表现但在新法生效后犯罪因而不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因而不利于起到假释的一般预防效果。显然,适用假释的前提条件从旧并不符合上述从旧兼从轻原则的范围。
四、审判监督程序中刑法的溯及力问题
对审判监督程序中刑法的溯及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案件,适用行为时的法律。”但在适用行为时法律的同时是否需要考虑从旧兼从轻原则?进一步而言,这一问题关涉到轻的法律能否溯及到已经生效的判决。显然,上述司法解释并未给这一原则的运用留有余地。
各国刑法的有关规定表明,人道原则在刑法中的进一步渗入,使轻法能够溯及既判案件的做法成为一种潮流。例如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第1款规定,如果在犯罪之后依法规定了应处较轻的刑罚,犯罪者应当减刑。这一规定的隐含内容就是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后法,不仅应当适用于判决尚未确定的案件,而且应当适用于判决已经确定的案件。同样,《意大利刑法》第2条第2款规定,任何人不得因行为后的法律规定不为犯罪的行为而受处罚;已被判刑的,停止执行并消除有关后果。学者认为,在其他人都可以不受处罚地实施某种行为时,一个人还在为该行为而受刑并承担法律后果,显然是不公平的。《法国刑法典》第112-4条第2款也有类似规定。在俄罗斯,这一做法曾经在理论界有争议,而且在实践中也不予适用。但是新的刑法典第10条比前述规定走得更远,前者只规定在新法除罪情况下可以溯及既判案件,而后者更扩大至刑罚减轻情况之下的既判案件溯及。它规定,规定行为不构成犯罪、减轻刑罚或以其他方式改善犯罪人状况的刑事法律,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即适用于在该法律生效之前实施犯罪的人,其中包括正在服刑的人或已经服刑完毕但有前科的人。如果犯罪人因为犯罪行为正在服刑,而新的刑事法律对该行为规定了较轻的刑罚,则应在新刑事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减轻刑罚。显然,从旧兼从轻原则在《俄罗斯刑法典》中的适用对象是新法生效之前的犯罪人,而不问是否具有生效判决,不像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适用对象是新法生效之前犯罪并且未获生效判决的人。
当然,现行《刑法》第12条第2款又规定:“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显然,为了尊重既判力的神圣权威,从而使规则运行乃至社会关系在一定期间内维持其稳定,不能因为法律的变更而对所有生效案件进行重新审判。即不能仅仅以法律变动可能使同一行为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为由,而对已经生效的判决产生疑问,并进而要求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对生效判决进行审查。但是我们可以采取一个更为折衷的立场。在已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第205条规定的合法理由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中,应当考虑到从旧兼从轻原则,以决定处刑较轻或不认为是犯罪的问题。其原因在于:首先,此时前一判决的效力已经处于不确定状态,不存在所谓的既判力神圣性问题。而在新法生效情况下,对于某一案件的审判不可能不顾及到新法的规定。既然所有新法生效前发生的案件在新法生效后的审判过程中,都要考虑到从旧兼从轻原则,而不能硬性地、孤立地适用行为时的旧法,那么就没有理由将因审判监督程序而重新审判的案件作为特例。其次,在重新审判过程中,最终经过审查,如果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或者适用原先旧的法律存在错误,那么应当作出新的判决,如果不顾新法对同一行为已经处以较轻刑罚或者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仍然机械地遵从旧法,显然是仅仅考虑了法律的稳定性而没有对公民的权利予以足够的重视,社会也不会从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再次,我国已经于1998年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应当在最能够反映社会人道程度的刑事法律中作出与其规定相符的关照。虽然上述相关规定的操作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确定已经判处的刑罚在较轻的法定刑幅度内是否合适,是一件微妙之事,从而不易确定减刑幅度,但是我们可以在重新审判过程中,对宣告刑进行重新衡量,适用较轻法定刑,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同上述规定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有限的折衷,对于在审判监督程序中最终审查认为原判没有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错误,仍然应当尊重既判效力,以避免犯罪人滥用审判监督程序以达到改变既判的目的,致使生效判决的权威无法得到完整体现,造成另一种司法不公。因此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仍然依赖于立法部门采纳上述类似规定,以体现刑法的人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