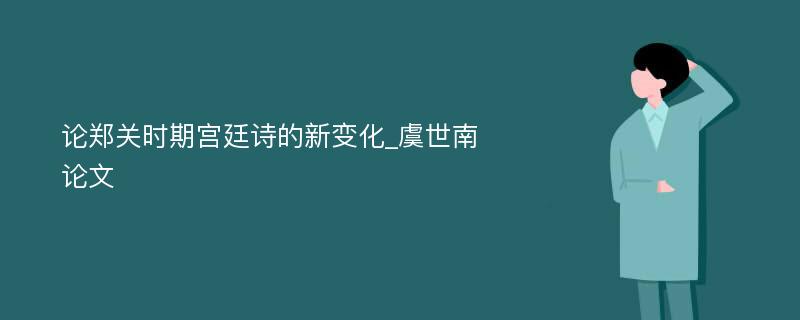
论宫体诗在贞观时期的新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贞观论文,时期论文,论宫体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闻一多先生在《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指出,宫体诗“当指以梁简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以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不仅说明了宫体诗抒写艳情的特质,而且对宫体诗形成和流变作了断代性勾勒,揭示了宫体诗起于萧梁、盛于陈隋、终于初唐的发展轨迹。宫体诗在梁、陈时期是宫廷文人赏玩风月艳情的文学载体,而在唐初贞观时期则发生了重要变化,逐渐从梁、陈诗风中摆脱出来,从狎客文人手中解放出来,在赏玩狎昵的情趣之外拓展出若干新的表现领域,形成不同于梁、陈宫体诗的特点。卢骆王杨把宫体诗从宫廷推向市井,正是以贞观时期的宫体诗作为桥梁的,探讨贞观时期的文化环境对宫体诗创作的影响,分析这时期宫体诗变化和发展的具体特点,对于深化宫体诗研究具有促进作用。
一
唐初文化领受着南朝文化和北朝文化双份遗产,自成体系的南、北文化以及绮艳轻靡和刚健质朴的两种不同风格为唐初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和多种选择的余地。在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唐太宗李世民的文化主张对于贞观文坛发展走向起到了关键作用。
唐太宗文化主张的核心是文化建设要为政权建设服务,他通常从政治角度认识文化问题,用政治与文化互为表里的观点把文化盛衰与政治兴亡紧密地联系起来。《帝京篇序》云:
予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1 〕他游息前代艺文,目的在于“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通过艺文考察历代政治得失,作为唐王朝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借鉴。他反对周穆、秦皇、汉武、魏明诸帝纵欲奢侈的生活,进而反对淫靡浮华的文风;提倡节俭中和的作风,进而提倡雅正端庄的文学,欲“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贞观时期的宫廷文学就是在这种以政为本、务求雅正的文化思想的导引下向前推进的。
然而,文学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特规律,思想观念的更新与具体实践的改变并不总是同步实现的,旧时代的文学风尚就是一种文学惯性,每个人的文学情趣和品位更是建立在长期文化积累基础上的相对稳定的审美形态。新的文学思想可以指导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却不能够在短时期内遏制旧的文学惯性,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们已经拥有并且乐于接受的文化积累。唐太宗作《帝京篇十首》,旨在“以明雅志”,其三云:“鸣笳临乐馆,眺听欢芳节。急管应朱弦,清歌凝白雪。彩凤肃来仪,玄鹤纷成列。去兹郑卫声,雅音方可悦。”〔2 〕这首诗前六句沿袭宫体诗的常用题材,描写艺妓歌舞的欢娱场面,最后两句则直刺郑、卫靡音,抒发去淫声、兴雅音的愿望。用宫体题材否定宫体文学,倡导雅正诗风,在前代帝王诗歌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它实开宫体诗新变之先声。但是其八云:“建章欢赏夕,二八尽妖妍。罗绮昭阳殿,芬芳玳瑁筵。珮移星正动,扇掩月初圆。无劳上悬圃,即此对神仙。”〔3〕这首诗借汉指唐,妙龄姣妍的宫妓,华贵艳丽的服饰, 配合着珮移扇摇的轻盈舞姿和未曾见诸文字却犹若萦绕耳际的哀丝豪竹和低吟慢唱,真实地展现了唐太宗充斥着脂粉艳情的宫闱生活。篇末抒慨,亦可见得唐太宗对艳妓美色的贪恋和对享乐生活的追求。作为唐太宗的手笔,如果把它放置在梁、陈文人的宫体诗中,人们很难在两者之间找出一道比较清晰的界线加以区别。《帝京篇十首》之其三、其八两首题材相近而主题相悖,表明唐太宗在倡导文学革新的过程中,其自身受到旧文学的严重制约,以致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脱出梁、陈宫体樊篱,而不能够完全开创一种与他的革新主张相适应的文学新格局。
在一些可信程度较高的典籍记载中,唐太宗对南朝艳靡文化的实际态度与他的革新主张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唐诗纪事》卷一载, 〔4〕太宗尝作宫体诗,并且要求虞世南赓和。虞世南认为此诗“体非雅正”,不敢奉诏。虞世南在陈、隋时代以善写宫体诗著称,他竟然认为唐太宗所作有失雅正,说明唐太宗宫体诗的艳靡气息决不亚于虞世南昔日所达到的程度。《唐会要》卷三十二载:“太宗谓侍臣曰:‘礼乐之作,盖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之隆替,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之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之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以是观之,盖乐之由也。’太宗曰:‘不然。夫音声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悦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5 〕在这段材料中,唐太宗用“自然”观点阐释文艺的本质属性,认为音乐歌舞既不能振兴政治,也不会败亡江山,国家兴亡“非由乐也”。自汉代以来,儒家把音乐歌舞与政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把文艺的雅媚作为政治隆替的重要标志。御史大夫杜淹持这种观点,唐太宗在《帝京篇序》里也抱有这种认识。然而,一旦离开抽象的理性层面,具体地评价南朝文化,唐太宗便背离了自己倡导的崇雅求正的主张,陷入一种悖论。客观地说,“音声感人,自然之道”的文艺观要比礼乐教化思想更接近文艺的本质,但是,唐太宗站在新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立场,用“自然”观点阐释南朝艳曲《玉树后庭花》和《伴侣曲》,则另有隐衷。在大唐基业百废待兴之际,唐太宗要使自己冠冕堂皇地处在新型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领袖地位,必须借用儒家传统的政治文化一体论作为思想武器,把文艺引导到雅正道路上,利用文艺教化功能为政治建设服务。与此同时,他与绝大多数北朝贵族一样倾羡南朝文化,嗜好艳情文学,而儒家礼乐思想不允许他同时握持着新旧文化两端,因此,要心安理得地重温昔日的文化旧梦,就要把南朝政治衰亡与文艺颓靡的关系割裂开来,这才是唐太宗提出文艺“自然”观点的本意。
唐太宗是贞观宫廷文人群体的领袖,他一方面倡导雅正诗风,另一方面对梁、陈宫体文学怀着深度的爱好;一方面出于政治功利的需要在理念上否定梁、陈文化,另一方面对这种文化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认同,贞观时期的宫体诗就在这种新的文学主张与旧的文学存在叠合交汇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二
唐太宗面临的时代环境是贞观宫廷文人所共同面临的环境。贞观年间,一批著名文人活跃在唐太宗周围,其中陈叔达是陈代宗室,虞世南、褚亮在陈、隋时期以善写宫体诗而曾经受到宫体大师徐陵的赞赏,还有李百药、蔡允恭、许敬宗等都在隋朝做官。这些文人经历过宫体诗风炽盛的时代,入唐以后聚集于宫廷,组成了以唐太宗为首的宫廷文人群体。这个群体的文化根基是梁、陈文化,他们的文学内质属梁、陈时代,虽然江山易主,而他们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文学趣味并没有从本质上有所改变。由于政治建设的需要,唐太宗倡导文学革新,标举雅正诗风,使艳情文学在宫廷中丧失了创作土壤,宫廷文人不能够象南朝狎客文人肆无忌惮地描写声色艳情,而必须在文学活动中体现以政为本、务求庄雅的新风尚。于是,从脂粉香泽旧题材中翻出新意,把风月声色与政治需要融汇一体,便成为宫体诗的发展方向,借宫体“旧瓶”装谀颂“新酒”,既适应时代环境又符合文学规律,顺理成章地被宫廷文人奉为通幽曲径。
虞世南是唐太宗最宠信的宫廷文人,被誉为“德行淳备,文为辞宗。”〔6〕在贞观宫体诗的新变中, 他是把宫体题材与歌功颂德主题出色地结合起来的诗人之一。《侍宴归雁堂》诗云:
歌堂面绿水,舞馆接金塘。
竹开霜后翠,梅动雪前香。
凫归初命侣,雁起欲分行。
刷羽同栖集,怀恩愧稻粱〔7〕。
虞世南首先从描写歌堂舞馆落笔,却没有沉湎在欣赏和陶醉之中,而是笔随心移,借用归鸟飞雁意象挖掘宴聚欢娱场景的新内涵——“刷羽同栖集,怀恩愧稻粱。”以飞雁同栖比喻君臣欢聚,以稻粱之食比喻沐浴君恩,表达自己举动受恩宠无以报答的愧疚,也婉转地颂扬了唐太宗的功德无量。虞世南在陈、隋时代是写艳情诗的胜手,“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8〕, 尝作《应诏嘲司花女》诗云:“学画鸦黄半未成,垂肩亸袖太憨生。缘憨却得君王惜,长把花枝傍辇行。”〔9〕对照《应诏嘲司花女》和《侍宴归雁堂》两诗, 《应诏》诗把宫妓作为取乐对象,以戏谑宫妓获取欢情快意,《侍宴》诗主旨则在于抒怀言志,起兴于声色歌舞,归结于托物明志。两诗同样运用传统的宫廷题材但趣味和内涵大相径庭,前者轻靡而后者庄雅。这些不同之处都体现了宫体题材在贞观时期的新变化。许敬宗是贞观宫廷中资历稍浅的著名文人,生活糜烂,闺门不检,他的诗歌在渲染艳情方面与梁、陈诗歌相比毫不逊色(详见后文),唯独描写宫廷生活属于例外。《奉和仪鸾殿早秋应制》诗云:
睿想追嘉豫,临轩御早秋。
斜晕丽粉壁,清歌肃朱楼。
高殿凝阴满,雕窗艳曲流。
小臣参广宴,大造谅难酬〔10〕。
这首应制诗写宴聚娱兴场面,使用了“朱楼”、“雕窗”等语,把笔触伸进静幽隐秘的宫闱深处,对“清歌”弥漫,“艳曲”云流的宫廷生活亦有所涉及。但是,作者没有大肆渲染歌情舞态,也没有流露丝毫的赏狎心理,而是借声色之乐表达对浩荡天恩的颂扬,抒发知恩图报的心愿。《奉和宴中山应制》诗云,“中山献仙姑,赵媛发清讴”,“一举氛霓静,行龄德化流”〔11〕。同样是把歌女舞姬融入皇恩德化的主题之中,其措辞庄雅,不似南朝宫体的冶词艳句。把南朝宫体的轻艳题材与歌功颂德的严肃主题结合起来,是贞观宫廷文人在文学活动中普遍使用的创作方法,除了已经列举的虞世南、许敬宗之外,李百药、上官仪等著名宫廷诗人也都有类似的诗歌作品,如李百药《奉和正月临朝应诏》,上官仪《咏雪应诏》等。
贞观宫体诗在艺术性方面也表现出若干共同特点。其一,对宫廷歌舞声色的描写都是片断性的,不是把宫体题材从宫廷生活的整体中提取出来,列为特定的对象给予完整的表现,而是把易于诱发艳情的内容安排在对宫廷生活的整体描写中,作为宫廷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对待,借以言志述怀,表达歌功颂德的主题,从而避免以声色写声色,陷入艳情诗的沼泽。其二,偏重直观描写,不讲究对宫妓形容和歌舞韵味的具体展示,塑造意象主要使用朱弦、舞袖、清歌等固定形象,有一定的泛化倾向。其三,在描写过程中通常不融入作者主观内心感受和感情体验,多用理性态度进行客观描写。贞观宫体诗的这些特点派生于一个基本原因,即宫廷文人在有意识地把宫体题材服务于歌功颂德的主题,竭力促使着香艳内容进入颂诗轨道。在这种创作意识的驱动下,宫廷文人预宴赋诗主要目的不是驰骋才情,也不是寻芳猎艳,而是从文学侍臣的地位迎奉皇帝的喜好,以换取龙颜一悦,著名诗人宋之问在《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诗中写道:“飞花随蝶舞,艳曲伴莺娇。今日陪欢豫,还疑陟紫宵。”〔12〕明明白白地说出了宫廷文人在欢娱场合的“陪欢”地位。艳靡题材一旦变成歌功颂德的材料,创作重心必须发生偏移,把抒情改变为制题,把对艳曲靡音和妍姿美色的描写转化为表层欣赏和深层谀颂的混合体,由此形成了贞观宫体诗的片断性、意象的直观性和情感的理性化等特点。
三
贞观宫廷文人在反映宫廷生活的诗篇中很少表现艳情,梁、陈以来的艳靡诗风在宫廷文学中明显地呈现消褪趋势。然而,宫体诗在贞观时期的影响依旧炽盛,宫廷文人虽然不能够在宫廷文学活动中接踵南朝狎客文人,却把南朝宫体诗的内核从反映宫廷生活外移到了反映贵族文人的家庭生活,为艳情诗的延续找到了新的表现空间,这是宫体诗在贞观时期的又一个显著变化。
贵族文人在家庭生活题材中表现艳情,其主要描写对象是家妓。唐初,朝廷对官员私蓄家妓没有明文规定,直到中宗神龙年间情况始有改变。《唐会要》卷三十四载:“(神龙二年)敕三品以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女乐不过三人,皆不得有钟磬。乐师凡教乐,淫声、过声、凶声、慢声皆禁之。淫声者,若郑、卫;过声者,失哀乐之节;凶声者,亡国之音,若桑间、濮上;慢声者,惰慢不恭之声也。”武德、贞观年间,贵族官僚广蓄家妓者主要有两种人:一是皇亲国戚,依靠血缘或裙带关系受封食禄;一是开国功臣,凭借杀伐或帷幄之功盘踞高位。这两种人各有仗恃,新王朝建立后沉湎于安乐享受的生活,如李博又“有妓妾数百人,皆衣罗绮,食必粱肉,朝夕弦歌自娱,骄侈无比。”〔13〕李孝恭“性豪奢,重游宴,歌姬舞女百有余人。”〔14〕上层贵族崇尚奢侈,竞逐豪华,追求声色感官刺激;另一方面,家妓地位卑贱,是以姿色美貌和歌舞艺能侍奉主人的婢女。唐律明确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15〕因此,主人可以任意驱使和狎昵家妓,犹如使用自己的财产。
在用家妓题材表现艳情的创作道路上,杨师道是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是隋司空杨雄少子,后投奔李氏,尚桂阳公主,封安德郡公,由旧士族转变为新权贵。史称他“雅善篇什”,“退朝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园池,而文会之盛,当时莫比。”〔16〕其《咏舞》诗云:“二八如回雪,三春类早花。分行向烛转,一种逐风斜。”〔17〕这首小诗字字落实在色艺二字之上,后两句具体描写艺妓的歌情舞态。艳妓歌舞的欢娱场景激起了他隐秘而微妙的心绪微澜,引发了他对春色的联想和赏春寻芳的冲动,婉曲地流露着一种狎昵心理。这首诗把脂粉题材与艳冶情调融为一体,深得梁、陈宫体诗的神韵。在《阙题》诗里,杨师道对艳情欢娱的展示更加显露直白,诗云:
兰丛有意飞双蝶,柳叶无趣隐啼莺。
扇里细妆将夜并,风前独舞共花荣。
两鬟百万谁论价,一笑千金判是轻。
不为披图来侍寝,非因主第奉身迎。
羊车讵畏青门闭,兔月今宵照后庭〔18〕。
诗里这位扇里细妆、风前独舞的女子是杨师道众多侍妓中的宠儿,从她“两鬟百万”和“一笑千金”的身价中,反映了豪门贵族千金买欢的风流生活,他们不仅享受着家妓的歌舞欢情,还拥有她们的青春和美貌。这首诗用七古体式直陈声色欢娱,以至于不避“侍寝”、“奉身”等俚词俗语,格调轻艳尘俗,体大而气盛,异于南朝宫体之风韵,开卢、骆市井艳情之先声。
许敬宗是另一位擅长表现家妓艳情的诗人,他生活糜烂、贪恋美色,曾经在府第建造飞楼七十余间,供家妓在其上跑马嬉戏,肆意取乐。〔19〕其妻裴氏婢女有姿色,裴氏亡故,他竟不顾当时良贱通婚的士族婚姻大忌,纳婢为室。〔20〕其《堂堂词二首》其一云:“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其二云:“懒整鸳鸯被,羞褰玳瑁床。春风别有意,密处也寻香。”〔21〕两诗皆写艺妓春情,前首尚属含蓄,后首直接描写深闺秘阁中的女子,用床榻之景展现她为情所困的慵态,更借“春风”有意、密处寻香的拟人手法,传达作者寻芳赏艳的心理。贞观宫廷文人是唐代最早的文人群体,其中大多数文人生活在两个、甚至三个朝代, 在南朝宫体诗风笼罩下完成了文学成长的过程。入唐以后,随着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改变,他们已经不能原样照搬梁、陈文人做法,直接用宫闱题材渲染艳情。于是,诸如陈师道《咏舞》、《阙题》和许敬宗《堂堂词二首》这类反映家庭生活的艳情诗应运而生。
贞观宫廷文人写家庭生活中的艳情有一定的范围,他们只限于反映自己的家庭生活。对于同僚文友的爱姬宠妾,在诗歌中也经常描写,但主题是表现主人富贵豪奢的生活和崇高的社会地位,艺妓歌舞只是被用来烘托场面,是显示贵族得意人生的道具。例如,杨师道的文友杨续《安德山池宴集》诗云:
狭斜通凤阙,上路抵青楼。
簪绂启宾馆,轩盖临御沟。
西城多妙舞,主第出名讴。
列峰疑宿雾,疏壑拟藏舟。
花蝶辞风影,苹藻含春流。
酒阑高宴毕,自反山之幽〔22〕。
这首诗写杨师道的府第和家庭生活,前四句写景,五、六句写人;接着四句再写景,最后两句又写人,结构非常工整。“狭斜”四句写杨府位于皇宫近侧,华楼轩盖高下毗连。对杨府位置的描写实际上是对宅第主人地位的暗示,显示杨师道侍奉君侧,深受宠信,是大权在握的重臣。“西城”两句写杨府艺妓众多,艺能精湛,艳名传扬;每当主人宴朋会友之际,皆有回雪之妙舞,绕梁之清歌,令高朋贵宾赏心悦目。“列峰”四句写峰、壑、花、蝶等细景,借助着风影、春流的衬托和宿雾、藏舟的想象,展现了杨宅山池雅致的风景和宜人的春色,隐含着主人高雅的情致和优裕华贵的生活。最后两句写酒阑人散。这首诗的素材由景物、艺妓歌舞、文人欢宴三种成份构成,主题是表现杨师道豪华富贵的的生活,而诗中对艺妓歌舞的描写则是对杨师道贵族生活的一种外在展示,而不涉及艳情。除杨续之外,当时著名宫廷文人岑文本、褚遂良、上官仪、刘洎、许敬宗等都有同题之作。这些同题诗篇章结构虽然有所不同,但对艺妓题材的使用和所表现的主师则与杨续诗完全一致。
闻一多先生认为,“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从宫廷走到市井。”〔23〕这是从起、结两个端点勾勒了宫体诗在初唐阶段演变的线索。如果把这个线索进一步具体化,可以看出,宫体诗进入市井固然是在卢、骆手中,而离开宫廷则始于贞观年间。贞观时期,唐太宗从政治需要出发,提倡兴雅音、去淫声,欲将宫体艳情从宫廷文学中驱尽,替之以端庄雅正的思想主题,其结果导致宫体诗殊途发展:其一,残留于宫廷文学中的香艳题材与歌功颂德的政治主题结合,逐渐从艳体转为颂诗。其二,传统的宫体诗从宫廷移到了上层贵族的家庭,由原先对宫闱艳情的描写转为对家庭艳情的描写。上述两种趋势是宫体诗在贞观时期的重要变化,也是宫体诗离开宫廷而走向市井的第一阶段。卢、骆诸人年少才高,名大而位卑,不具备贞观贵族文人丰裕的经济条件和艳妓成群的生活环境。艳情诗在家庭生活中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以后,中下层文人便把创作对象下移到青楼娼门,致使市井艳情进入诗歌领域,宫体余风扩散于闾门坊间。这是宫体诗在初唐时期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也是宫体诗的终结阶段。
注释:
〔1〕〔2〕〔3〕《全唐诗》卷一。 本文所引《全唐诗》均据中华书局1960年版。
〔4〕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
〔5〕本文所引《唐会要》均据中华书局1955年版。
〔6〕〔8〕《旧唐书·虞世南传》。本文所引《旧唐书》均据中华书局1975年版。
〔7〕〔9〕《全唐诗》卷三十六。
〔10〕〔11〕〔21〕《全唐诗》卷三十五。
〔12〕《全唐诗》五十二。
〔13〕《旧唐书·李博乂传》。
〔14〕《旧唐书·李孝恭传》。
〔15〕《唐律疏议·名例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
〔16〕《旧唐书·杨师道传》。
〔17〕〔18〕《全唐诗》卷三十四。
〔19〕《太平广记》卷二三六,中华书局1961年版。
〔20〕《旧唐书·许敬宗传》。
〔22〕《全唐诗》卷三十三。
〔23〕闻一多:《唐诗杂记·四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