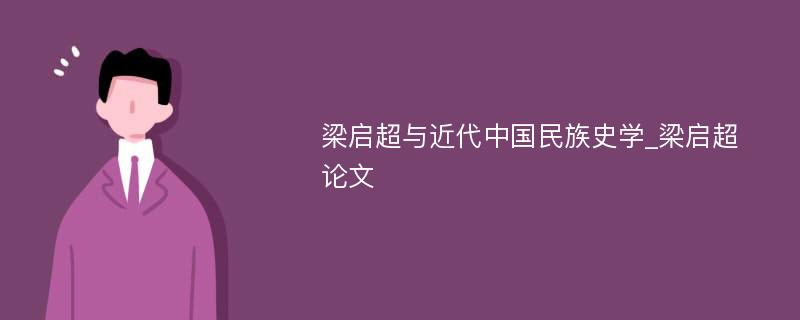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民族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民族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近代史学研究中,梁启超拥有的史学成就与扛旗之功,已为大家所熟知。有关他的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不计其数。但细考所有关于梁氏的论著,着重讨论和研究其民族史学成就和特点的却寥寥无几,实为遗憾。而梁氏对民族史学的重视程度是极其显著且影响亦是极为深远的。诚如其友林志均所说:“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存其坚密自守者在,即百变不离史是观已。”(注: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笔者认为任公于史学中最“坚密自守者”乃民族史学。早在20世纪初,梁氏就在多篇论著中谈论民族、人种等问题。如在其尽人皆知的两篇掀起“史界革命”的文章中,就直言道:“民族为历史之主脑,势不可以其难以分析而置之不论”;“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足见其对史学中民族史学之重视和认识。后来,梁氏又写就许多专门的民族史学论著,彰显出民族史学是萦绕于其头脑中的最切要问题,也表明他对该问题的兴趣之高和探究之深。
一、梁氏民族史学的基本内涵
20世纪初的中国,有关中国境内民族起源的论说喧闹一时,尤其主张中国民族外来之说煽惑极盛,1906年梁启超写就《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在其中就提出了自己的种种困惑和思考,如其所言:“我中国民族,即所谓炎黄遗胄者,其果为中国原始之住民,抑由他方移植而来,若由移植,其最初祖国在何地,此事至今未有定论。”接着,梁氏列举了其所研究关注的八个问题。即:
“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自初本为一民族乎,抑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一问题。
若果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则其单位之分子,今尚有遗迹可考见乎,其最重要之族为何为何,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二问题。
中华民族混成之后,尚有他族加入,为第二次,乃至第三四次之混合否乎,若有之,则最重要者何族何族,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三问题。
民族混合,必由迁徙交通,中国若是初有多数民族,则其迁徙交通之道,有可考见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四问题。
迁徙交通之外,更有他力以助长其混合者否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五问题。
迁徙之迹,限于域内乎,抑及于域外乎,若及于域外,其所及者何地,其结果之影响若何,此吾所欲研究之第六问题。此问题即“中国以外更有中华民族所立国与否”之问题也。
中华民族,号称同化力最大,顾何以外来之族多同化于我,而我各省各府各州县,反不能为完全之自力同化,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七问题。
自今以往,我族更无求以进于完全同化乎,抑犹有之乎,若有之,其道何由,此吾所欲研究之第八问题。”(注:梁启超著《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A]》《饮冰室合集·合集》30-45(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带着上述诸多问题,梁氏把中华民族分为八族详加讨论,详细考辨每一民族的起源、民系、分布地域、发展过程、迁徙路线、生活习性和心理特征等。如果说这只是梁氏对中国民族史的粗略构想和思考,那么,事隔十五年后,梁氏于1921年秋在天津南开大学作讲演,后该讲演稿于次年结集出版,命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该著开篇就对“史之意义”作了如下定义概括:“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5。)接着,他又坦言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中国史之内容和精要。以便供“现代中国人之资鉴”。
他说:举要言之,则中国史之主如下:
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敌,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
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族几何,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生结果何如?
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
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
由此,他认为“遵斯轨也,庶可语于史矣。”(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5。)毋庸置疑,梁氏眼中的中国史之架构与中心论述就是一部中国民族史。至此,梁氏的民族史学内涵已在其中表露无遗。
二、梁氏民族史学之特点
梁启超站在时代的高度,以深邃的世界全局的眼光,依据中国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与现实,阐释了他对民族问题的一系列卓越见解,成为我国近代以来运用科学观点和理论方法系统研究民族史学的领军人物,并对20世纪的民族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究其民族史学之特点,可得如下几点认识:
1、竞争进化、无限希冀的民族史学观。如前所言,梁氏在20世纪初就在多篇论著中论述中国民族史问题。其实早在1899年,梁氏就写了《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一文,在文中他充满信心和热情地呼唤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强大和复兴,并寄寓热切的厚望。“二十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有可豫断言者。”(注:梁启超《论中国人种之将来》[A]《饮冰室合集·文集》1-9(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他从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和地理环境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说明。“今于人事置不论,请专就其人种之特质而论之。”“一曰富于自治之力也。”“二曰有冒险独立之性质也。”“三曰长于学问,思想易发达也。”“四曰民人众多,物产沃衍,善经商而工价廉,将据全世界商工之大权也。”“有此四原因,规以地势,参以气运,则中国人于来世纪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此非吾夸诞之言也。”(注:梁启超《论中国人种之将来》[A]《饮冰室合集·文集》1-9(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此时的梁氏已积极运用从西方传入的进化史观,来研究和论述中国民族史学。他在《春秋载记》、《战国载记》等文中,从历史进化的视角,详尽地论证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兼并争霸对推进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巨大历史功绩,认为它是国家统一,民族意识形成的历史必经阶段和重要准备,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民族心理、民族观念的建构和秦汉之际统一国家的建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无庸讳言,他将人类社会发展史简单归为单纯的民族竞争史,是偏颇和不科学的。但更应看到,他的这种论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的针对性。在当时也具有开启人们多视角多层面透视历史现象的积极意义。
2、多元融合、汉族为主的民族史学观。1901年,梁氏就在《中国史叙论》中谈到中国境内民族来源的多元性,就是汉族也不是出于一祖。1906年,梁氏明确提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注:梁启超著《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A]》《饮冰室合集·合集》30-45(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1922年,他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再次指出“我中华民族本已由无数支族混成,其血统与外来诸族杂糅者亦不少。”(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30-45(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是由各小部落在黄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长期繁衍生息,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合化合吸收其他各周边民族,而形成今日之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他又通过大量考辩并利用近代科学发现成果,指出其所“臆推我国各地区原始时代所有民族之大概”:“大抵诸族之起,非沿大江,则缘大湖。黄河流域,则有我中华民族焉,洞庭湖、鄱阳湖及扬子江中游灌域,则有苗族焉,岷江灌域,则有蜀族焉,嘉陵江及扬子江上游灌域,则有巴氐族焉,淮水灌域,则有徐淮族焉,两江灌域,则有百越族焉,滇池及洱海灌域,则有百濮族焉。”(注:梁启超著《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A]》《饮冰室合集·合集》30-45(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这一观点被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所证实。这在现实上打破了大汉族主义的优越感,也在理论上否定了历史统治阶级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从而批驳了传统的顽固的民族一元论。他将中华民族同化诸异族所用的程序归纳为八点:1.诸异族以国际上平等交际的形成,与我族相接触而同化;2.我族征服他族,以政治力使其逐渐同化;3.用政治上势力,徙置我族于他族势力范围内;4.我族战胜他族,徙其民入居内地,使濡染我文明;5.以经济上之动机,我族自由播殖于他族之地;6.他族征服我族,经若干岁月之后,遂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7.他族之一个人或一部族,以归降或其他原因,取得中国国籍;8.缘通商流寓,久之遂同化于中国。(注:梁启超著《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A]》《饮冰室合集·合集》30-45(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这里梁氏用“我族”代指汉族;“他族”指代中国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重在探索和评析中华民族逐步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
3、各族平等、文化交融的民族史学观。梁氏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开篇即言:“本篇即五千年史势鸟瞰之一部分。”(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30-45(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将中华民族史视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上摒弃了封建正统史观和大汉族主义民族偏见,把民族完全置于平等的地位。“前所论列之八族,皆组成中国民族之最重要分子也,其须当邃古之时,或本为土著,或自他地迁徙而来,今不可考,要之自有史以来,即居于中国者也,而其中除眇濮二族外,率皆已同化于中华民族,无复有异点痕迹之可寻,谓舍诸族外更无复华族可也。”(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30-45(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他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证了中国民族史与中国文明史之间的关系,他说“中国者,华夏民族所创建也,中国史者,华夏民族发展之记录也,然此民族非一旦所成,历万数千年磨练乃渐凝为颠扑不破之一体。此民族又非孤根特达,实包罗无数种姓,次第同化混合,始庞然确立其中坚,……此数千年国史所由成立也。”(注:梁启超《太古三代载记》,《饮冰室合集·专集》30-45(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他还提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两次学术文化高峰,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春秋战国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大规模融合的时代,而此时的学术思想达于全盛。(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魏晋六朝、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融合的高峰,它亦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学术文化出现新的高潮。由此可见民族融合对中华文化的巨大影响。
此外,尤值得一提的是梁氏的不断探讨、自我批判的民族史学精神。这在其民族史学论著中十分凸显。如在当时对于中华民族的来源和流变,说法种种,势头较大是民族西来说,20世纪的梁氏作为一位勇于探索新知的爱国学者,也对此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曾一度相信民族西来说,如其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言,“我中国民族,即所谓炎黄遗胄者,其果为中国原始之住民,抑由他方移植而来,若由移植,其最初祖国在何地,此事至今未有定论,吾则颇祖西来之说,即以之为假定前提。”(注:梁启超著《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A]》《饮冰室合集·合集》30-45(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后来民族起源论一时难有定论,而梁氏并没固于已见,而是勇于怀疑和否定以前主张,其论道”中华民族为土著耶,为外来耶?……吾以为在现有的资料下,此问题只能作为悬案,中国古籍所记述,即毫不得外来之痕迹,若拾文化一二相同之点,攀引渊源,则人类本能不甚相远,部分的暗合,何足为奇,吾非欲以故见自封,吾于华族外来之说,亦曾以热烈好奇心迎之,惜诸家所举证,未足以起吾信耳。”(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30-45(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可见,梁氏对于学术探讨并不随波逐流,盲目接受,而是从自己的判断和思考出发,没有足够的证据和资料,就阙而不补,征而不信。梁氏敢于推翻旧说和自我批评的这种精神和态度实为今天的史学家们吸收和发扬。
三、梁氏民族史学形成之背景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矛盾空前激化,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纷纷走上政治舞台,为挽救民族危亡和生存而殚精竭虑,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对民族史的研究深受重视。从另一方面而言,当时的中国处于新陈代谢的社会变革中,西方新兴的各种学说和理论方法纷纷传入国内,因此梁氏还受到当时从西方传入的各种社会思潮和学术理论的影响。现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1.德国的民族主义史学。近代德国史学产生于德意志民族国家思想兴起和统一运动时期,由于受到时代历史使命感的激发,一开始就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从整个19世纪的德国史坛看,影响最大的有四派。(注: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特别是客观派史学,经过兰克的系统阐发和传播,一度风靡西方,成为近代西方史学的主流,并远传到东方,尤激起20世纪初正处于民族救亡高潮时期的中国学术界的共鸣。由于受此种历史观的影响,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叙述到:“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可见梁氏积极主张史界革命和提倡新史学,实受当时颇为流行的德国民族史学的影响。
2.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和巴克尔文明史观。他们认为地理环境与民族性的形成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主张依据自然环境解释人类社会文明的消长。这在梁氏许多论著中彰显无遗,如梁氏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所言:“欲知中国何时始有人类,当先问其地气何时始适于住居……吾确信高等文化之发育,必须在较温腴而交通便利之地。”(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30-45(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他充分利用西方实证论和汉学考据法,比较清晰地论述和概括了我国古代各民族发展演化及其融合的历史历程,并从大量历史材料中分析考辨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而其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更有精细论述,这已为大家所熟知,不再展开论述。
3.西方近代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立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传统金石学的发达,二是西方考古的理论和方法的传入与使用。梁氏在这两个方面都有介绍和研究,并不断利用于中国民族史学探讨和研究中。如他早在1901年的《中国史叙述》即介绍了当时在欧洲已趋于成熟的考古学理论,可见他已相当全面的了解西方考古学的新概念,并且注意到田野发掘的作用。另外,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之第四章《论史料》中用大量篇幅评论了当时地下出土的材料,谈论这些资料对历史研究的重大价值。他把史料分为两部分:“文字记录以外者”和“在文字记录者”,而在文字记录以外者又分为三类:“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而这些史料显然是可以属于民族民俗研究之范畴,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和早期民族史之裨益可谓无穷。梁氏对李济田野发掘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以及对其儿子梁思永从事考古发掘的积极鼓励和引导,都表明了梁氏对于近代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关注和对中国民族史学研究作用的提倡。
4.社会学中的人种学观点。梁氏在《中国史叙述》中专列“人种”一节来谈论西方流行的人种分类法和中国人种的划分。在《新史学》中他又提出:“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历史……若在今日,则虽谓人种问题为全世界独一无二问题,非过言也。”(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此外,梁氏还大量吸收借鉴欧美汉学家和日本研治中国史学专家的成果。以及其他新兴的学科理论和方法,如人类学、地质学、社会心理学等。
四、梁氏民族史学成就和不足之处
梁氏在中国民族史学的研究上始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探讨。在20世纪前期,中国民族史的问题纷繁芜杂,不易理清。诚如梁氏所言“每读国史,见其称外族,曰夷蛮戎狄,其事迹互相出入,眩瞽不可方物,吾深苦之,当亦凡治斯学者所同以为病也。”(注:梁启超著《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A]》《饮冰室合集·合集》30-45(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但他没有为此而退却,而是怀着宏大的气魄和非凡的学识,以客观理性的治学态度积极探求民族史学问题,“势不可以其难于分析而置之不论”,不断写就了民族史学性质的论著。如在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中专有“人种”一节来讨论中国民族的种类和来源,实乃中国近代第一篇较有科学性的民族史专论。其《新史学》一文中关于“历史与人种之关系”,是中国最早的简易世界人种学,也可称为最早的世界民族史篇章。《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梁氏写于1906年,它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中华民族发展简史。1922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是在上篇论文基础上,对其主要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和深化。这篇论著可作为梁氏民族史学观的理论代表作。
不可否认,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梁氏这些论著甚为简陋和偏颇,其中包含的民族史学观点和理论方法,存在着诸多错误之处。如其对中国民族的分类和渊源的判断,甚为粗略和不符合实际。但我们不应苟求彼时的学人,应该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从其立场和学术背景来辩证的分析考察。诚如白寿彝先生对其《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的评价所言:“有些话说的很有见识,概括能力也很强,但在对各个民族的分别论述和古今民族的演变上错误很多。从民族史研究的发展上看,这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注: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梁氏的这些论著,无论是当时还是今天来看,都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和历史地位。梁氏创造性地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较为系统地探讨研究中国民族问题,梳理各民族融合、演化的关系,彻底地打破了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的传统的史学观。他以史学家宏观的视野和理性思维,透过复杂纷纭的历史现象,站在世界全人类的角度,将中国民族史问题视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对近代民族史的研究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成为本世纪学术史上运用近代观点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继他之后的民族史论著,大都把梁氏有关民族问题的几篇论文和讲演稿列为主要的参考书。梁氏关于民族史研究的方向和民族史撰述的内涵及架构,也为后人作了重要的示范和引导。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史论著大量涌现,而其写作思路基本上是按照梁氏的民族史论著模式编写的。梁氏关于民族史学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研究范式被许多学者所认同和吸收,其在民族史学研究领域内的开创之功实不可没。
标签:梁启超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历史研究法论文; 饮冰室合集论文; 新史学论文; 中华书局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