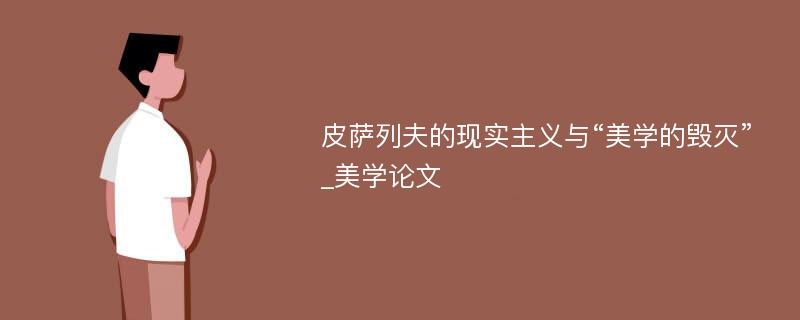
皮萨列夫的现实主义和“美学的毁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美学论文,列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的俄国美学一直处于动荡不安,风起云涌的社会转型之中,因此,在它的逐步酝酿和发展过程中,必然地带上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鲜明时代特色,呈现出强烈的社会革命性质,展现出尖锐的思想批判锋芒,并且以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的美学为当时俄国美学的主潮。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经历了从别林斯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再到杜勃罗留波夫和皮萨列夫的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和体系逐步完善起来,同时也逐步显露出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和体系内部的一些不可回避和难以克服的矛盾。
从总体上来看,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现实主义理论由于当时社会革命的形势需要,出现了单纯从艺术(美)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上建立美学原则和体系的激进倾向,这便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现实主义美学。这种倾向在皮萨列夫的继续推进过程中显露出了它的危机,因此,皮萨列夫发出了“美学的毁灭”的警世之呼。
一
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皮萨列夫(лмитриЙBaHoBиЧ ΠиcapeB,1840-1868)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后期的代表人物。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并流放和杜勃罗留波夫逝世以后的19世纪60年代,他写下了一系列美学和文学批评论著,如《巴札罗夫》(1862),《现实主义者》(1864),《有思想的无产者》(1865),《恼人的虚弱》(1865),《美学的毁灭》(1865),推动了俄罗斯现实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的进一步发展。
皮萨列夫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断然反对用“美学”这个术语来定义其艺术的观点。为了定义自己的艺术观点,他常常使用“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批评”、“善于独立思考的现实主义”等概念,“现实主义”成了皮萨列夫自己的哲学观和美学观的名称。他甚至偏激地认为:“美学和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势不两立的,现实主义应该彻底地根绝美学。”“美学、无意识、墨守成规、习惯是意义完全相同的概念。现实主义、自觉性、分析、批评和理性的进步也是意义相同的概念。但它们与第一类概念是正相反对的。”(注:参见M·Φ·奥夫相尼科夫《俄罗斯美学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9页。)由此可见他对“现实主义”一词的重视,也可以看出他所说的“美学”概念的特定含义和某些不确定性。
皮萨列夫在刚刚从事文学批评时,还认为艺术创作本质上是中性的,并且无权“干预生活”,在一篇关于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的文章中甚至声称:“具有预定的实用目的的创作是不合法的现象”。不过,他的美学观点毕竟是在别林斯基开创的现实主义美学的影响下形成的,因此在一篇分析屠格涅夫的小说《贵族之家》的评论中他也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基本倾向。他说:“……艺术作品越少偏向于训诫,艺术家在选取他打算用来装修自己思想的人物形象和场景时越是不偏不倚,他描绘的图画就越匀称,越接近生活,他就能越快地通过这幅图画达到所期望的效果。”(注:参见M·Φ·奥夫相尼科夫《俄罗斯美学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7-298页。)而且,在1859-1861年俄国的革命形势的促进下,皮萨列夫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政治观点由自由主义转化为革命民主主义,哲学观则转向唯物主义,美学观点也更加倾向于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现实主义,最终形成一种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体系。这时,他坚决反对“纯艺术”(为艺术而艺术),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实质在于,没有对迫切社会问题的解决,没有对人民痛苦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描写,没有同对社会下层的压迫所作的斗争,就不可能有艺术和美学(注:参见M·Φ·奥夫相尼科夫《俄罗斯美学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9页。)。这样,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现实主义理论,并在《现实主义者》这一纲领性的著作中阐述了这一理论体系。
皮萨列夫采用了席勒和赫尔岑等人关于现实主义概念的广义的用法,即经常用现实主义来代表唯物主义,并与理想主义相对。因此,他所谓的“现实主义者”,就是根据形势的特点行动,渐渐达到社会生活的改变,为根本改造社会而准备条件的人。而且,他的“现实主义纲领”包括一系列克服俄国文化经济落后、改善人民处境的改良措施,它的最后目的“在于一劳永逸地解决有关饥寒交迫的人们的无法避免的问题”,而实现这一目的并不在于广大人民群众,而是知识分子,即“有思想力的现实主义者”,他的美学和文学批评不过是这个现实主义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现实主义者》的后半部分,即从第22章起,皮萨列夫论述了他自己的现实主义的美学观和艺术观。首先,他坚决反对“一心一意崇拜单纯的美”和“纯艺术”,而是主张文学应当揭示“人类的痛苦”,揭露现实生活中的尖锐社会矛盾,履行崇高的社会使命。他十分赞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庇埃尔·勒鲁(1797-1871)的意见:“从最高的观点来看,可以称为诗人的是那样一些人,他们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向我们揭示人类的痛苦,而可以称为思想家的是那样一些人,他们探索着能够减轻并治好这些病痛的方法。”(注:参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5-130页。)并把这一思想作为他论述科学和艺术的现实主义论文的基础。他明白地宣布:“彻底的现实主义必须蔑视一切没有重大好处的东西;但是我们所理解的‘好处’这个词,完全不是我们的文学论敌要强使我们接受的那种狭窄的意义。我们绝不会对诗人说‘你去缝靴子’,或者对历史学家说‘你去烤馅饼’,但是我们坚决要求,作为诗人的诗人和作为历史家的历史家应该各在各的专业方面带来真正的好处。我们要诗人的作品能够在我们面前清晰地、鲜明地勾画出我们为了认真思考和行动而必须知道的那些方面的人类生活。”(注:参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4册, 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5-130页。)他所谓的诗人,泛指一切通过语言创造形象的艺术家。这些人要成为给社会带来好处的诗人,在他看来当然应该反对唯美主义。他说:“首先我要坦白地说:我绝对不承认有所谓无意识和无目的的创作。我怀疑,这不过是神话,是唯美派评论界为了造成更神秘的印象而创造出来的。”(注:参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4册,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5-130页。)这无疑深受别林斯基在《智慧的痛苦》等文章所阐明的观点的影响。他同时认为:“一个真正的、‘有用的’诗人应当知道了解目前使他的时代和他的人民的最优秀、最聪明、最有学问的代表们发生兴趣的一切。诗人,作为一个热情的、敏感的人,一方面要了解社会生活的每一次脉动的十分深刻的意义。同时也一定要用全力来爱他认为是真、善、美的东西,来恨那妨碍真、善、美的思想获得血肉并变成活生生的现实的大量卑鄙龌龊的勾当。这种爱是和这种恨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它构成并且一定要构成他灵魂的灵魂,构成他整个存在和他整个活动的唯一的、最神圣的目的。‘我不是象旁人那样用墨水写作’,别尔内说,‘我是用我的心血和我的脑汁写作。’每一个作家都应当这样写作,而且只能这样写作。谁要是不这样写作,谁就应该去缝靴子和烤馅饼。”“为了真正用心血和脑汁写作,就必须无限地、深刻而有意识地爱和恨。而为了爱和恨,为了使这种爱和恨摆脱个人自私自利和浅薄虚伪的任何杂质,就必须反复思考和认清许多事物的本质。当这一切都做到了,当诗人以他强大的智能认识到人类生活、人类斗争和人类痛苦的全部伟大意义,当他看到个别现象之间的牢固的联系,当他明白,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可以做的、应当在什么方向上和以什么动机去影响读者的智能,那时候对他说来,无意识的、无目的的创作就变成绝对不可能的。”(注:参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5-130页。)因此,照他的意见,“诗人——如果不是伟大的思想战士,大胆无畏的、无可指责的‘精神武士’,像亨利希·海涅所说的那样,便是渺小的寄生虫,用装腔作势的小戏法来取乐别人的渺小的寄生虫。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诗人——如果不是能够撼动世代恶势力的大山的巨人,便是在花粉里翻掘的小甲虫。”(注:参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5-130页。)这些都表明了皮萨列夫的现实主义美学的社会目的和思想性与情感性的统一。这也是他的现实主义美学对于革命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
其次,皮萨列夫的现实主义美学的真实性原则也更加着重于与艺术家本人的情感、思想相结合,因此,他直接提倡的是艺术家的真诚与生活的真实的结合。他宣称“真诚是必需的”,不过不应该“完全满足于细微的思想和感情”,他把“所有不了解人类生活中伟大的、真实的、严肃的方面的诗人”都称为“穿着晨衣在公众面前游逛”。他还举出歌德的例子来说明“任何一种智力活动,只有当它和真诚的、坚定的、深刻的信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是伟大的,有益的。”(注:参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5-130页。)他又分析了海涅的性格矛盾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并认为“海涅的抒情诗并不是别的,而是十九世纪优秀人士在其中消耗生命的那些思想与感情、惊慌与忧伤、交替发作的冷与热的巨细无遗的和真实到不能模仿的图画。”(注:参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5-130页。)由此他又论及抒情诗,认为“抒情诗,按照它的本质来说,是比叙事的和戏剧性很强的诗歌要真挚得多,直接得多。写戏剧或是小说必须经过长时期的思考;同时必须研究生活;这种研究的果实,甚至在作者不能使形象获得只有多才多艺者的力量才能创造的那种鲜明性的场合下,也可能是有趣的、有教训意义的。相反地,抒情诗人只抓住自己个人的瞬息间的情绪,并把这些情绪记录下来,而抒情作品的优点正是在于它要做到尽可能地自然,诗人的情感或思想要被抓住,并且要非常直接地和不加修饰地表现给读者看。但是要知道,只有本身是出色的并因此能在别人心中引起感情和思想活动的东西,才有权利这样赤裸裸地被表现出来。所以很显然,抒情诗是最高度的、最困难的艺术表现。只有第一流的天才才有权利成为抒情诗人,因为只有杰出的人才能在使社会注意他的私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好处。”(注:参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5-130页。)这些精辟的分析把现实主义美学的真实性、典型性的原则与文学艺术的思想感情的真挚流露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使这些原则的论述从与生活联系更紧的叙事的和戏剧的文学扩大到似乎与人的主观世界联系更紧的抒情文学,无疑是在别林斯基关于文学分类及其特征的基础上,对现实主义美学的真实性和典型性的拓展和深化,尤其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彼夫过分强调生活和生活美的一种补充,对整个俄国和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思潮和发展应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特别是对列夫·托尔斯泰的情感现实主义和陀思耶夫斯基的心理现实主义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此外,他在《现实主义者》中还规定了“现实主义批评”的任务。当然,他首先是不以唯美主义批评为然的,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种“宁取形式而舍内容的批评,已经多么彻底地歪曲了自然概念”(注:参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5-130页。)。他所倡导的“现实主义批评”,虽然对于世界和俄国的文学大师们,如普希金、果戈理、歌德等有些不尽公允的批评,但是,在美学理论上还是提出了正确的原则的。他说:“现实主义批评在对待前人留给我们的大量文学作品方面的任务就在于:从这一大批作品中选出能够促进我们智力发展的东西,并说明我们应当怎样运用这些精选的材料。”“但是现实主义批评还有另外的、也许是更严肃的任务。在严格地评价过去的文学著作的同时,它必须更仔细地、更严格地注视着当代文学的发展。”(注:参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5-130页。)因此,他的现实主义批评仍然是以现实为依据的,以“活生生的现实的利益”作为批评尺度,他极力主张“一个生于十九世纪,受到健康的、人的教育的真正的诗人,既不可能是一个落后分子,也不可能是一个观潮派。因此,如果在一个有才能的人的作品里显露出陈腐的倾向或是对当代实际需要抱着冷漠的态度,那么现实主义批评就必须细心地分析这种不正常的、有害的现象的原因。”(注:参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5-130页。)他号召诗人都成为现实主义者:“在我们的时代,可以不是一个诗人而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因而也是一个有用的工作者,但是做一个诗人,同时却不是一个深刻而自觉的现实主义者,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谁如果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就不是一个诗人,而只是一个有才干的不学无术者,或者是一个巧妙的招摇撞骗者,或者是一个浅薄的、但是自尊心很强的人。现实主义批评必须缜密地保护读者出众的头脑和口袋,使不受这一切缠扰不休的畜生的侵袭。”(注:参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5-130页。)这无疑是19世纪60年代中最强烈的现实主义宣言,尽管其中包含着一些激进的、宽泛化的东西,但是,它也强有力地推进了当时现实主义文学和美学的发展,或许对于以后苏联美学界和文学界把现实主义尊崇得过分绝对化也有一些影响。这也反映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美学观点与他的现实主义的内在联系。
从《现实主义者》的某些论述来看,好像皮萨列夫是太过于偏执于现实生活及其利益的,其实,在他的现实主义美学理论中也有重视幻想和想象的另外一面。这在他的《幼稚想法的落空》中表现得最为明确。他说:“上面我已经指出,伊尔杰尼耶夫很早就感觉到幻想和现实之间的差别。你们也许会说,我们大家迟早都会开始感到这种差别,最好的教育也不能完全防止一个人产生这种非常不愉快的感觉。我同意你们的话,但是并不完全同意。差别有各种各样。我的幻想可能赶过自然的事变进程;也可能完全跑到任何自然的事变进程始终达不到的地方。在前一种情形下,幻想是丝毫没有害处的;它甚至能支持和加强劳动者的毅力……这种幻想中并没有任何会败坏或者麻痹劳动力的东西。甚至完全相反。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这样来幻想的能力,如果他不能间或跑到前面去,用自己的想象力来给刚刚开始在他手里形成的作品勾画出完善的图景,——那我就真是不能设想,有什么刺激力量会驱使人们在艺术、科学和实际生活方面从事广泛而艰苦的工作,并把它坚持到底……只要幻想的人真正相信自己的幻想,仔细地观察生活,把自己观察的结果与自己的空中楼阁相比较,并且总是认真地努力实现自己的幻想,那么幻想和现实的差别就丝毫没有害处。只要幻想和生活有联系,那幻想决没有什么坏处……”(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97-98页。)这些话出自于一个极力推崇从生活出发的现实主义者之口,应该说他是对幻想在现实主义艺术之中的地位有比较清醒认识的,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美学并不是胶着于现实生活的“照相机式”的理论。
二
皮萨列夫专论美学的论著《美学的毁灭》是一篇很独特的文章。不过,在前苏联和我国一般流行的观点认为,《美学的毁灭》等著作中,“他发表了许多错误的论点,这些论点实际上否定了建立科学的美学理论的可能性”(注:参见M·Φ·奥夫相尼科夫《俄罗斯美学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2页。)(注:参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版,第105-130页。 ),“他的著作比起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最高成就来说是倒退了一步,而且在哲学和美学方面还犯了一些严重的形而上学的错误”(注:参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5-130页。)。但是,我们经过对原著的客观认真的分析却认为,《美学的毁灭》似乎并没有多少大的错误,也不见得就有什么严重的形而上学倾向,毋宁说,皮萨列夫敏锐地从营垒内部感到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内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而沿着这种内在的矛盾就会必然达到“美学的毁灭”。其实,宣布艺术或美学必定衰亡、毁灭的,从柏拉图开始就未中断过,像伊丽莎白时代的清教徒,路易十四治下尚今派的“几何型”党派人物,启蒙主义者卢梭,绝对辩证论者黑格尔,边沁主义信徒和普鲁东等,关键在于他们如何论证这种毁灭的必然性,从中我们可以见出一些有价值的观点或规律。
《美学的毁灭》一文完全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推衍和阐释,皮萨列夫关于“美学的毁灭”的结论,完全是由《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基本观点中推导和分析出来的。我们从这个极端化、激进的结论的推导和分析的过程,不仅可以见出皮萨列夫的一些偏激的美学观点,更可以发现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内在的难以克服的矛盾,实际上为美学在俄罗斯的进一步发展合乎逻辑地指出了一个现实主义美学的倾斜和消解的历史前景。而我们以前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过于僵化地视为现实主义美学的高峰,完全不顾它内在无法克服的矛盾及其必然自我消解的倾向。事实上,我们文革时期的“美学的毁灭”就是一个反例证。
皮萨列夫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写作《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之时就已经在头脑中把美学问题取消了。他说:“作者(车氏——引者按)看到,由我们社会的智力呆板而产生的美学,照样也支持着这种呆板。……为了在软弱无力的文学中唤起它高尚而严肃的公民义务的意识,就应该完全消灭美学,应该把它打发到炼金术和星相术被打发去的地方去。”(注:Д.И.Писapсв.Сочннснияв чстьlpсх томaх, Госудapствсннос Издaтс чьство художсствснной Читсpaтуpьl Мосκвa 1956,ТоМ 3。第419-425页。)他还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中开头的一句“如果还值得谈论美学的话”这个附带条件,从中分析出:“作者早就清楚,谈论美学的价值仅仅在于,为了彻底地消灭它,并且永远让那些受到哲学和寄生虫的庸俗市侩行为欺骗的人们清醒过来。因此,作者当然说的不是新的美学理论的建立,而仅仅是旧的美学理论的毁灭,而且根本上是一切美学理论的毁灭。”(注:Д.И.Писapсв.Сочннсния вчстьlpсх томaх, ГосудapствснносИздaтс чьство художсствснной Читсpaтуpьl Мосκвa1956,тоМ 3。第419-425页。)这当然反映了他的偏激,然而也说明“美是生活”就已经包含着美学的自我消解的必然性。这是读过《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人们可以分析出来的必然结果。
在他看来,“美学,或者关于美的科学,只有在美具有某种独立的意义,不依赖于无限多样的个人审美趣味的情况下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权利。如果只有那种令我们喜爱的东西才是美的,如果因此而所有最多种多样的美的观念结果竟然都是合理的,那么这里美学也就化为乌有了。如果每个个别的人都形成了自己个人所有的美学,那么,把个人的审美趣味导向必然的一致性的普通美学就始终是不可能的。《审美关系》的作者正是引导自己的读者走向这种结论,尽管没有完全公开地说出它。”(注:Д.И.Писapсв. Сочннснияв
чстьlpсх томaх, Госудapствсннос
Издaтс чьство художсствснной Читсpaтуpьl Мосκвa 1956,тоМ 3。第419-425页。)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皮萨列夫坚持了美的唯物主义的客观性,并揭开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中潜在的美的主观性和对客观性的颠覆,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述美的本质时确实是从人的美感和审美趣味出发的,而认为“美包含着一种可爱的,为我们的心所宝贵的东西”,美是“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注: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这里面当然就隐含着美离不开人的主观感情、理解等意识了。那么,当美必然随着人的满足与否为转移的时候,美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也就被取消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美学理论,而且根本不可能导向一致,因而美学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这种分析和推导应该说,并不是毫无道理的。
皮萨列夫对于“美的生活”的命题作了分析,认为这个定义也必然导致美学的毁灭。他认为“美的生活”的定义过于泛化,似是而非,而且主要涉及到对象与生活的关系,而与对象的外观形象构成关系不大,比如在观看一个人的面孔,他说:“我们观看一个人的面孔,就好象在买金银制品时我们察看一下纯度成色。纯度成色并不给予物品任何美;它仅仅保证它的价值。在有作者给我们所下的那个美的定义的情况下,美学,对我们最大的快感,就消逝在生理学和卫生学之中了。”(注:Д.И.Писapсв. Сочннсния в
чстьlpсх томaх, Госудapствсннос Издaтс чьство художсствснной Читсpaтуpьl Мосκвa 1956,ТоМ 3。第419-425页。)这些分析和推论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美是生活”定义的人本主义、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缺陷呢?
正是由于“美是生活”的定义必然导致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客观现实中的美是充分地美的并且完全满足着人”,所以“艺术完全不是产生于人想要弥补现实美的不足的要求”。对此,皮萨列夫推论:“换句话就是说,艺术的目的不在于为了创造那种在自然界中没有也不可能有的美的奇迹”(注:Д.И.Писapсв. Сочннсния в чстьlpсх томaх, Госудapствсннос Издaтс чьство художсствснной Читсpaтуpьl Мосκвa 1956,тоМ 3。第419-425页。)。针对着关于艺术的目的问题,他又一一考察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各种艺术的观点。
关于建筑包含某种实用目的和审美目的相结合的艺术,车尔尼雪夫斯基,要么把建筑等实用性艺术驱逐出艺术殿堂,要么规定“凡是以满足审美趣味和审美感受为目的的工业部门、工艺”都列入艺术。对此,皮萨列夫推论道:“如果艺术的本质、目的和解释就在于它对美的渴望”,那么“连在镜子前涂脂抹粉的老太婆也成为把自己本身变成艺术作品的艺术家”(注:Д.И.Писapсв. Сочннсния в чстьlpсх томaх, Госудapствсннос Издaтс чьство художсствснной Читсpaтуpьl Мосκвa 1956,тоМ 3。第419-425页。)。他还以大量事实反驳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真的艺术与奢侈无关”的观点,他说:“如果以轻视的态度来看待披肩,钟表,亭子,那么思想家完全是对的;但是,当一开始断言,真正的艺术与奢侈无关的时候,他就完全不对了。真正的艺术与经济的考虑根本没有丝毫关系。真正的艺术是永远靠人类奢侈的汁液为生的寄生植物。真正的艺术是奢侈的形影不分的伴侣,它无论如何不可能与奢侈无关。”(注:Д.И.Писapсв. Сочннсния в
чстьlpсх томaх, Госудapствсннос Издaтс чьство художсствснной Читсpaтуpьl Мосκвa 1956,тоМ 3。第419-425页。)应该承认,皮萨列夫抓住了艺术的超功利性的某些特征,至少在异化劳动的状态下,在私有制的情况下,艺术是与统治者和有闲暇者的奢侈相关的,有时艺术的确“非常乐意逼使自己的创造性思想沦为娼妓”(注:Д.И.Писapсв. Сочннсния в чстьlpсх
томaх, Госудapствсннос Издaтс
чьство художсствснной Читсpaтуpьl Мосκвa 1956,тоМ 3。第419-425页。)。由此,我们似乎也感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观和艺术观的良好愿望和空想主义的性质。
三
与此同时,皮萨列夫还对某些把建筑等当作“这个时代和民族的整个生活,整个世界观,整个精神要求”的体现的观点(注:Д.И.Писapсв. Сочннсния в чстьlpсх
томaх, Госудapствсннос Издaтс
чьство художсствснной Читсpaтуpьl Мосκвa 1956,тоМ 3。第419-425页。),作了分析。他认为,如果相信这种观点,那么“为了有充分根据地研究过去他们完全不需要书面文件了”,不过,他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在已经知道时代、民族的背景材料之下的一种推测,因此,这是一种“根据不足”的见解(注:Д.И.Писapсв. Сочннсния в
чстьlpсх томaх, Госудapствсннос Издaтс чьство художсствснной Читсpaтуpьl Мосκвa1956,тоМ 3。第419-425页。)。这是否也透露出了一点,那种认为“艺术再现生活”的观点的某种机械性理解的“根据不足”呢?
关于绘画与雕塑,皮萨列夫分析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谓“彼得堡没有一个塑像在面孔轮廓的美上不是远逊于许多活人的面孔的”的说法。他认为,这种说法是“美是生活”的结果,“还因为雕像的美并不在生活,即不在于脸部的表现,而在于轮廓的严格准确性和各部分的完全适合性,所以,活人的每张完整无缺和智慧灵巧的面孔当然就比形形色色的大理石或者铜制的面孔要美得多”(注:Д.И.Писapсв.Сочннсния в чстьlpсх томaх, Госудapствсннос Издaтс чьство художсствснной Читсpaтуpьl Мосκвa1956,тоМ 3。第419-425页。),而且绘画的技巧手段也不完善,从而也证明自然的美比艺术美要完善。
至于音乐和文学(诗),他认为,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都不过是“生活现象的可怜的再现”,“无非是对现实的一种苍白的、一般的、不明确的暗示罢了”。他认为,“以这样的方式一一考察了所有的艺术以后,作者提出了这样的一般结论,活的现实中的美永远高于艺术中的美。所以,如果艺术不可能创造出现实中不存在的美的奇迹,那么,试问,它究竟应该干什么呢?它应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再现现实。——它究竟应该再现什么呢?——生活中人所感兴趣的一切东西。”(注:Д.И.Писapсв. Сочннсния в
чстьlpсх томaх, Госудapствсннос
Издaтс чьство художсствснной Читсpaтуpьl Мосκвa 1956,тоМ 3。第419-425页。)这不是十分明显地指明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对于艺术的贬低了吗?试想,以这样的观点对待艺术,艺术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再说,艺术既不关涉美,又低于现实生活的美,那么,它又如何去“说明生活”呢?这里是否也包含着“再现现实”的艺术,在低于现实美的层次上,必然使现实主义走上自然主义归宿的内在可能性和必然性呢?这里面也揭示了“美是生活”定义的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论述诗的不确定性时,皮萨列夫有一些精辟的论述:“众所周知,各个不同的演员扮演同一个角色也完全是不同的,而且其实同样令人满意。一位演员这样理解剧中人物的性格,而另一位演员理解得是另一个样子,第三位则又按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如果大家都同样具有天才,那么最细心周到而求全责备的观众也必然会完全满意;可见,大家都理解得不错,而且,诗的形象类似于不确定的方程式,众所周知,这样的方程式允许有许多个解。”(注:Д.И.Писapсв. Сочннсния в чстьlpсх
томaх, Госудapствсннос Издaтс
чьство художсствснной Читсpaтуpьl Мосκвa 1956,тоМ 3。第419-425页。 )这里很充分地分析了文学(诗)和艺术的创作和欣赏的创造性,包含着20世纪中叶以后才流行起来的阐释学美学和接受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这似乎也表明现实主义美学在19世纪60年代前后在旧唯物主义哲学范围内已经快走到了它的尽头,正在寻求新的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来看,《美学的毁灭》似乎敏锐地感悟到了美学的真正革命即将来临,即“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论述了《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基本内容以后,皮萨列夫又考察了以这本书的那些理论原则为基础的文艺批评的倾向。他尖锐地指出:“《审美关系》说,艺术无论在怎样的条件下都不能创造出自己私有的世界,它永远被迫局限于再现那个现实中存在的世界。这条基本的规定责成批评家一定要在与艺术作品借以产生并为之而产生的那种生活的关系之中来考察每部作品。”(注:Д.И.Писapсв. Сочннсния в чстьlpсх томaх, Госудapствсннос Издaтс чьство художсствснной Читсpaтуpьl Мосκвa 1956,тоМ 3。第419-425页。)这无异于说,这种现实主义的批评家局限于现实生活的范围内,仅从艺术作品与生活的关系来评价每部作品,因此,根本与美学毫无关系。所以,他又说:“渗透着《审美关系》的思想的批评家的作用完全不在于,要把准备好了的美学规范的各种各样文章运用到艺术作品之上。不是为了改善死板规则的无个性和无热情的维护者的职务,而是批评家要转向活人,这个活人把自己的整个世界观,自己的全部个性特征,自己的整个思维方式,自己的人的和公民的信念,希望和情欲的总和带进而且必须带进自己的活动之中。”(注:Д.И.Писapсв. Сочннсния в чстьlpсх томaх, Госудapствсннос Издaтс
чьство художсствснной ЧитсpaтуpьlМосκвa 1956,ТоМ 3。第419-425页。)这种批评就是单纯的内容批评,由于种种原因极容易导致庸俗的社会学批评。这在以后的苏联和我国的特定时期内已经有了历史的证明。在皮萨列夫看来,由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什么是有思想的人”,“什么是引人兴趣的”这些关键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所以像“艺术再现人在生活中感兴趣的一切事物”,“只有值得有思想的人注意的内容才能使艺术不致被斥为无聊的娱乐”这样一些问题也未解决,但是,“在每一种个别情况下,批评家对艺术作品的批判都依赖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决定了内容是不引人兴趣的,换句话说,是不值得有思想的人注意的以后,批评家,根据《审美关系》的作者的原文的说法,才有充分的权利对该艺术作品以轻蔑或冷笑来对待。”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他说:“现在假定,一个批评家以轻蔑看待艺术作品,而另一个批评家——则以赞叹看待它。这样,在自己的判断中发生冲突之后,他们彼此之间争辩起来。一个说:内容不是引人兴趣的和不值得有思想的人注意的。而另一个则说:是引人兴趣的和值得注意的。毫无疑问,这两位批评家之间的争论从一开始就完全不是在美学的立足点上进行的。他们彼此之间将争论,什么是有思想的人,什么应该是这个人认为值得自己注意的事物,他应该怎样看待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他应该怎样思考和活动。在这场争论中他们将不得不展开自己的整个世界观;他们将不得不顺便也看一下自然科学,历史,社会科学,政治学、道德哲学,但是,在他们之间却连一个字也不说及艺术,因为全部争论的涵义都在于艺术作品的内容,而不在于艺术作品的形式。正因为两位批评家彼此之间不争论形式,而只争论内容,正是因为这样他们两人都认为,内容比形式更重要,——所以他们两人终究都认为自己是《审美关系》中所叙述的那种学说的信仰者。”(注:Д.И.Писapсв. Сочннсния в Чстьlpсх томaх, Госудapствсннос Издaтс
чьство художсствснной Читсpaтуpьl Мосκвa 1956,тоМ 3。第419-425页。)因此,他认为,这种批评主张的是:“对艺术作品作出最终评判的权利,不属于只能够判断形式的美学家,而属于判断内容,即生活现象的有思想的人。关于有思想的人应该是怎样的,《审美关系》当然未置一词而且也不可能说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完全超出了它所解决的任务的范围。那么可见,在关于有思想的人的问题上彼此产生分歧时,批评家们没有丝毫根据援引《审美关系》。这就好像某人在争论间接税时开始援引数量地理学教科书一样俏皮。数量地理学——是非常受人敬重的科学,但是,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它却完全是不够资格的。”(注:Д.И.Писapсв.Сочннсния в чстьlpсх томaх, Госудapствсннос Издaтс чьство художсствснной Читсpaтуpьl Мосκвa 1956,тоМ 3。第419-425页。)这样,他就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美学割裂内容和形式,而专注于内容来进行文学批评的内在矛盾性揭示了出来,并指明了这样“生活的美学”完全与形式的美学无关,因而它也只关注艺术以外的哲学、历史、政治学、道德哲学、自然科学,而全然不顾及艺术的艺术性和美学特征,而且关于一些评判的关键问题也没有回答,所以,批评家要依据它来进行批评就是一种滑稽的事情。这里似乎也显示出了“内容的美学”的局限性,而在呼唤着“形式的美学”的出场了。
不论皮萨列夫在何种程度上是忠实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也不排斥《美学的毁灭》写于沙皇政府的监牢中因必须适应官方审查的需要而采用的某些曲折隐晦笔法,然而,从总体上看来,皮萨列夫的这篇带有某些偏激思想的论文,不仅从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内部揭示了这种美学的种种内在无法克服的矛盾和缺陷,而且也客观地显示出现实主义美学在旧唯物主义范围内发展的困窘,因而万般无奈地宣称“美学的毁灭”,尽管皮萨列夫在运用“美学”这个概念时有其不确定性和特殊含义,他有时用来特指“唯美主义”,有时用来称谓注重形式的理论,有时又泛指统治阶级的腐朽文化。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他对现实主义美学的坚持和发展,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宣布现实主义美学“毁灭”的无奈和严肃。
收稿日期:1998-2-20
标签:美学论文;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 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论文; 文艺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