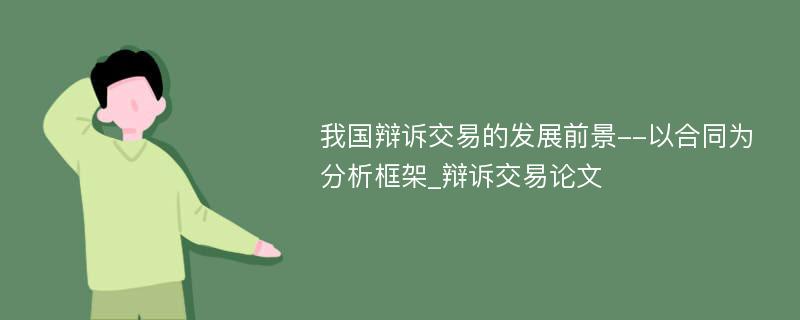
辩诉交易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以契约为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前景论文,契约论文,中国论文,框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辩诉交易在中国的现状
最近,我国司法实践中发生了一例有关辩诉交易的案件:
被告人孟广虎因车辆争道与被害人王玉杰等人发生争执并厮打,致被害人王玉杰重伤。公诉机关以被告人孟广虎犯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但孟广虎的辩护人认为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公诉机关则认为,本案其他犯罪嫌疑人在逃,而无法判定被害人重伤后果是何人所为是客观事实,如继续追逃则需要大量时间及人力和物力,而且由于本案多人混斗的特殊背景,证据收集也将困难重重。但此案导致被害人重伤的后果,孟广虎理应承担全部责任。双方意见发生严重分歧。公诉机关便与辩护人协商此案是否进行辩诉交易。辩护人在征得被告人的同意后,向公诉机关提出了辩诉交易申请。控辩双方随后进行了协商,双方同意,即被告人承认自己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表示愿意接受法庭的审判,自愿赔偿被害人因重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要求法院对其从轻处罚。辩护人放弃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观点,同意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证据及罪名,要求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公诉机关同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请求,建议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并可适用缓刑。
控辩双方达成协议后,由公诉机关在开庭前向法院提交了辩诉交易申请,请求法院对双方达成的辩诉交易予以确认。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接到申请后,由合议庭对双方达成的辩诉交易进行了程序性审查,并决定予以受理。为此,法院又组织被告方和被害方就附带民事赔偿进行庭前调解,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此案从开庭到宣判仅仅用了25分钟。(注: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2002年4月22日。)
该案的出现引发了理论界的热烈讨论,媒体也不知疲倦的进行积极宣传,并且,我们的立法机关与实务部门也都开始了积极大胆的探索,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全国各地也采取不同方式进行大胆的尝试。比如,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证据立法和刑诉法修正案的研讨中,都提到了辩诉交易问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正在制定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制度,在该制度设立中间,涉及了很多有关辩诉交易的问题。还有很多基层司法机关,虽然没有明文提到辩诉交易,但创设的许多适用规则体现了辩诉交易的精神,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出台的《轻伤害案件处理程序实施规则》(试行),根据该规则第1条和第3条的规定,对某些轻伤害案件,为了确保合理定纷止争,有效节约司法资源,如果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能达成和解,检察机关就可以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处理。
面对如此浪潮,学界必须思考,辩诉交易在我国究竟会有怎样的发展前景?而这离不开对辩诉交易起源与发展动因的理论阐释,同时,还需要对辩诉交易的司法功能与适用局限及其对传统司法制度的影响,进行客观与冷静的分析。
二、辩诉交易的起源与发展
(一)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而出现
辩诉交易出现原因的流行观念是,它是二战后法院的一种制度革新或腐败现象:新工业社会使大量案件涌入法庭,其必然要求“批量生产的司法制度”(assembly-line justice),辩诉交易制度就作为案件超负荷的一种回应而出现。该观点虽不无道理,但只是揭示了现象。有学者从法社会的角度,并以最早出现辩诉交易的战前波士顿为分析对象,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在杰斐逊时期(the Age of Jackson),工业化、移民以及城市化带来了严峻的社会冲突,并且,地方的政治机构贫乏且无组织性,法院就作为国家的代理人发挥了促进社会良性秩序,保障健康的市场发育、个人安全和经济增长的职能。在1830年到1840年间,辩诉交易作为政治稳定化过程的一部分以及获取合法制度的自治性(self-rule-accomplishments)的一种努力而出现。而法律制度的自治性对辉格党整合波士顿的社会与经济精英而言至关重要。为达到此目的,发源于英国普通法中的分散性宽容(episodic leniency)的传统被改造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辩诉交易,它在有效的把社会冲突吸纳到法庭的同时,还维护了精英在判决政策中的裁量权。(注:Mary E Vogel,The social origins of plea bargaining:Conflict and the law in the process of state formation,1830-1860,LAW & Society Review,Amherst 1999.)
也就是说,辩诉交易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而出现。它深受“市民共和主义理论”的影响。随着政治学说的普及,已不再可能仅依靠法律强制来维持社会秩序。一个政权要想维护其正统性,获取民众的广泛认同(popular consent)至关重要。如果获得了这样的认同,这将极大增强其拥有稳定政治生活的可能。从历史的角度看,政权曾经凭借向民众培植其合法化的意识形态来获取支持,在这一塑造政治合法化的过程中,法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把冲突吸纳到法庭,法律救济先发制人的取代了超法律的、政治的纠纷解决途径。法律的普适性与形式平等性确保了政权能够代表大众的所有利益。但为避免制度的过度刚性而带来的僵化后果,以获取当事者同意为基础的辩诉交易制度,就充当了制度与社会生活之间润滑剂的角色。
(二)可以有效的缓解程序正当化危机是其发展的动力
辩诉交易制度之所以经久不衰,并在当代社会有所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它可以有效的回应多元化社会对程序的挑战,缓解制度危机。
整个人类社会在总体趋势上正步入多元化的时代。其中,不同的利益诉求都得以彰显,不同的价值取向都得以尊重,人们对自由拥有前所未有的渴望,对不同价值的选择倍加珍视,但由此却带来了权威的脆弱、认同的困难、确定性与安全感的丧失。这在刑事司法领域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致于出现了“程序正当化的危机”:传统的以“单线性与强制性”为主要特征的诉讼程序,无法满足诉讼参与者多元的利益要求。一个刑事案件的处理,总是陷于多元价值间的两难选择而不得兼顾,最后往往出现国家控制犯罪的目标不能达到的同时,却还让参与者丧失了应有的主体性。总之,传统的执法模式缺乏当今社会所要求的价值负载能力,它也不能承受多元化所带来的张力。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如果司法模式不增强多元利益的包容力,不为参与者的自由选择提供制度保障,其结果必然是司法体系不堪重负而濒临崩溃,社会不满流向制度之外、严重冲击社会秩序。
面对司法程序的信任与正当性危机,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但其中都体现了一种契约精神,即通过诉讼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协商,达成共识性合意,使诉讼程序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价值包容力,以期在多元社会继续运作。(注:该思想与当代公共哲学的主题不谋而合。其主题内容是,“在多元差异主体间进行不断地对话与交往,力求取得共识、整合出合法性规范,从而成为全球化的游戏交往规则。”任平等:“公共哲学”(四篇),载《新华文摘》1999年第8期,第32页。)而辩诉交易恰恰就是契约观念注入刑事司法程序的产物,它可以有效的回应多元化社会与“后现代思潮”的冲击。(注:其中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法律学界兴起的“新公法运动”(New Public Law Movement)。倡导该运动的学者广泛吸收了法学之外的市民共和主义、神学、女权主义。释义学、实用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成果,以重构、发展其既有理论。新公法运动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多样性的社会背景下,为了再塑法律权威、避免信任危机所作出的必然反应,是一种后现代法学思想的体现。在程序理论领域,它对纯粹的程序形式主义提出置疑,认为其缺乏价值负载能力,从而更加关注实质的正义。由此产生的新程序主义强调目的法的力度(dynamics of purposive law)、公共协商,结构性失衡和通过对话达致真理。(William N.Eskridge and Gray Peller,The New Public Law Movement:Moderation As A Postmodern Cultural Form,Michigan Law Review,Feb1991.P728)其中内含的主线就是一种“契约式治理”,在法律程序中注入利益选择、平等协商与对话的契约精神,而且在实践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辩诉交易中的契约观念分析
辩诉交易制度(注:其通常是控辩双方进行权益交换,但也有其他变形,如德国是被告人和法院就诉讼的处理方式进行协商。参见魏根德:“德国刑事案件快速处理程序”,载《法学丛刊》第178期。)虽然在道德与司法公正方面屡遭责难,(注:可参见Michael Gorr,The morality of plea bargaining,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Tallahassee;Spring 2000.)但它在美国仍十分盛行——不仅在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中有明文规定,而且,美国所有的司法机构都允许甚至鼓励辩诉交易。它在司法实践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85%-90%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结案的。司法人士普遍认为,如果没有辩诉交易制度,美国整个刑事司法体系将面临崩溃的危险。
那么,辩诉交易为何在司法制度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以及为何被告人与检察官特别青睐该制度?节省司法成本几乎是通说。如有学者认为,近一个世纪以来,辩诉交易制度已经成为美国刑事司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人与非法律人都普遍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大量的案件使既有的司法体系难承负荷。(注:可参见Michael Gorr,The morality of plea bargaining,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Tallahassee;Spring 2000.)当然,除了它使大部分刑事案件迅速且最终的得以解决之外,还有其他更多方面的原因: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审前羁押阶段被告人的“被迫懒散”对社会造成的腐蚀性影响;它有效防止了那些有继续犯罪倾向的被告人在审前释放阶段侵犯社会的可能;它大大缩短了从指控到最终处置之间的时间,这非常有利于恢复那些最终判处监禁的犯罪人的名誉。(注:Santobello v.New York,404U.S.257,261(1971).)
但笔者认为,从辩诉交易制度的起源以及发展动因来看,它体现了一种契约精神、一种与当下多元社会相契合的观念,是其在现今美国茁壮成长、并波及很多国家的根本原因。(注:正如有人认为,辩诉交易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但如果认为辩诉交易不过是用最低的司法成本来处理案件的手段,这将是很严重的错误。它有更多的契约性价值:它消除了由审判给控辩双方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它为刚性却无常的制度带来了一定的确定性与灵活性;它被用来缓和强制量刑规则的严酷无性,使刑罚更加准确的回应案件的特定性、尽量作到个性化的对待;实践中,很多重要的执法活动是通过与被告人的合作来完成的,如以宽大处理换取情报、协助以及为严重犯罪提供证据,而这主要依靠辩诉交易来完成。参见: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Law Enforc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The Challenge of Crime in a Free Society 135(1976).转引自Lloyd L.Weinreb,Criminal Process:Cases,Comment,Questions(fifth edition),Westbury,New York,The Foundation Press,Inc.1993.P890.)在阐述具体理由之前,必须交代清楚的是,辩诉交易中体现了什么契约观念?
契约的发展史表明,不同历史时期,基于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文化观念的变化演进,与社会相契合的契约观念也一直在变化,比如与自由市场相吻合的古典契约观念与伴随福利国家思想发展而来的现代契约观念就有明显的不同,前者崇尚无拘无束的自由交易,后者强调国家干预与契约主体间的协作。由是,就有必要明确,对现代刑事司法发挥作用的契约观念之主旨。通过理论分析与制度比较,笔者认为,在当代刑事司法领域,除了有“犯罪控制与保障人权”的显性观念作为制度的价值支撑外,通过“对话与协商、获取合意下的社会治理”的契约观念,它如同成文规则之外的“潜规则”、长江波涛汹涌之下的“暗流”,也现实地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真实、自愿的合意是核心理念,它体现的精神是: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运用自身主动性增进自我利益提供回旋余地。而合意的获得离不开如下前提条件:契约主体之间地位的平等、自由的选择、交涉能力的均衡、诚实守信的品格、契约的法律审查以及必要的救济。辩诉交易中的契约观念。
在辩诉交易中发现契约观念或以契约原理作为分析框架的,在美国判例中已不足为奇。U.S.v.Williams(1999)案,运用契约法中的“双方性事实错误”原理回应了对辩诉交易的挑战;U.S.v.Standiford(1998)案,运用了契约法的“解除条件”原理对辩诉交易作了解释;Kraus v.U.S.(1995)案,运用契约法中的“欺诈性诱因”(inducement by fraud)理论回应了对辩诉交易的责难;U.S.v.Clarke(1995)案,以契约法为分析框架,解释了辩诉交易的协定;Msrgralli-Olvera v.INS(1994)案中认为,答辩协议在本质上具有契约性质,可以根据契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它;Brook v.U.S.(1983)案中则直接认为辩诉交易在法律上就是一种契约。(注:转引自KIRKED.WEAVER,A change of heart or a change of law?Withdrawing a guiltyplea under federal rule of criminal procedure32(e),Journal of Criminal Law & Criminolgy:Chicago;Fall 2001。)但也有判例明确提出辩诉交易不是契约,不可适用契约原理,(注:如U.S.v.Olesen,920 F.2d 538,541(8[th]Cir.1990)Gov's of Virgin Islands v.Springette,614F.2d360,364(3d Cir.1980)U.S.v.Barron,172F.3d 1153,1158(9[th]Cir.1999))但笔者认为,即使是刑事法问题的辩诉交易,它仍然可以受契约法原理的调整,只要它的运用是为了确保被告人获得应得权利。而且,司法实践中的辩诉交易,的确体现了一种现代契约观念:即平等主体之间,通过理性对话与信息交流,基于自由的选择,最终达成真实、自愿的合意,以实现各自的利益所需。具体分析如下:
1.交易主体之间地位的平等
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检察机关与被告人平等的受宪法保护;二是被告人不受强迫,意志自由。被告人有自由选择的机会,如在美国,被告人可以作无罪答辩,有罪答辩或不愿辩护也不承认有罪的答辩。同时,在作有罪答辩时,控诉方应赋予被告人在刑罚方式上充分的选择权,单一的刑罚方式是变相的限制自由。只要不违背第五修正案,应给予被告人有罪供述尽可能的自由。(注:有两个判例确立了该主张,它们是:Bram v.U.S.,168 U.S.532(1897);Malloy v.Hogan,378 U.S.1(1964))有罪承认必须是自愿的,否则不受宪法保护。它常被法庭比作“非自愿的自白”之禁止。根据Boykin v.A1a(1969)案,被告人放弃接受审判的权利必须是“明知且理智的”。
2.交涉能力的均衡
辩诉交易的核心是一种权益交换,保证该交换真实性的重要条件是交易双方具有均衡的交涉能力,而其中的前提是双方要拥有对等的信息量,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必然导致交涉能力的不平等。具体而言,有罪答辩是对正式指控罪行的所有犯罪要素的承认,除非被告人了解控诉方掌握的事实证据并理解与事实有关的法律,否则,根本谈不上真正的自愿。美国对此有两个明显的制度予以支持:专业律师的协助与控诉方必要的证据展示,而前者离不开适用广泛的法律援助制度。(注:在McMann v.Richdson案中,法庭认为,一个有罪答辩不能因为它是由强迫性供述所激发而进行攻击,除非被告人没有得到称职律师的帮助。参见McMann v.Richardson,397 U.S.759,90 S.Ct.1441(1970)从该案可以发现,被告人在辩诉交易中获得律师帮助的重要性。)
3.诚实守信的品格
契约之所以能够签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事者都确信对方信守诺言,诚实的履行协议义务。并且,有相应的保障措施,如对契约采用书面形式,规定违约方的法律责任等。辩诉交易中重点要防止检察机关的反悔,(注:作为辩诉协议一方的控诉机关,如果不能兑现他的允诺,这个协议将面临着无效的危险。因为有罪答辩是基于被告人与控诉方的协议而作出,所以,作为对等的一方,控诉方必须履行他所出的承诺。Santobellov.New York,404U.S.257,262(1971);当被告人与政府有了答辩交易,法庭应该确保被告人获得协议中的“应得物”,同时,在确定政府是否履约时,可以适用契约的基本原理,即如果被告人履行了协议中的义务,那么,政府必须受协议的约束。U.S.v.Giorgi,840F.2d 1022,25 Fed.R.Evid.Serv.75.)因为被告人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赋予其反悔的机会。(注:根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32条(d)项规定,只有被告人说明正当理由,法庭才可以允许其撤回有罪答辩。其他情形,被告人的“违约特权”也将止步,如U.S.v.Gregory U.S.v.Gregory,No97-1687,2001U.S.App,LEXIS 5424,at 11-17(2d.Cir.April 2,2001)KIRKE D.WEAVER,A change of heart of a change of law?Withdrawing a guilty plea under federal rule of criminal procedure 32(e),Journal of Criminal Law & Criminology;Chicago;Fall 2001)这也是追求实质意义上的平等而作出的努力。
4.契约的法律审查及必要的救济
为确保答辩协议的真实性,法院必须进行法律审查。(注:Santobello v.New York案中意识到为保证答辩协议的真诚性,法院的审查是必需的。Santobello v.New York 404 U.S.257,264,92,S.Ct.495,500,30L.Ed.2d 427(1971).)在接受有罪答辩之前,法官必须在公开的法庭上亲自询问被告人,主要确保两方面事情:一是确认被告人清楚、明知必要的案件事实与诉讼权利,如答辩所针对的指控性质以及作有罪答辩的后果。如果作有罪答辩,那将意味着让渡很多诉讼权利,如放弃要求审判的权利、将不能正式面对指控方以及将不能在法庭上进行质证。而这种弃权必须符合正当程序条款方可有效,它必须是故意让渡或对明知特权的放弃。(注:Johnson v.Zerbert,304 US.458,464(1938).)二是确保答辩自愿。答辩必须是自愿的,而不是强迫、威胁的结果,也不是脱离答辩协议中许诺的结果。而且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强调答辩协议要制作文书,以便审查。(注:纽约州的政策是:只认可那些严格按照辩诉交易程序而达成的协议,且以“记录”为准,控诉方脱离记录的承诺无效。法院认为,该政策提高了有罪答辩的准确性,维护了辩诉程序的诚信品格,并确保了定罪的最终性。Siegel v.New York,691 F.2d 620(2d Cir.1982).)
一旦发现协议有违法之处,或者任何一方有违约的行为,法院就会给受损害方必要的救济。如在Santobello v.New York案中,多数派观点认为,如果指控方不履行承诺,被告人有两种救济途径可供选择: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强制履行协议,或者给予被告人撤回有罪答辩的权利。有的法官不同意该意见,如法官Marshall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必须撤回有罪答辩。(注:参见James B.Haddd etc.,Criminal Procedure:Cases and Comments,(fourth edition),The Foundation Press,Inc.1992,P1059-1060.)
四、以契约观念为核心的辩诉交易之独特司法功能
以契约观念为核心的辩诉交易制度,可以有效的缓解多元社会对程序正当化带来的冲击,使刑事司法制度获得了包括参与者在内的广泛社会支持。具体而言,辩诉交易有以下司法功能:
(一)它为刑事司法制度注入了民主自治精神
辩诉交易中“自由选择与合意”的契约观念,在司法程序中的相应制度设计为:负载不同价值与利益的诉讼程序、保障合意真实与自愿的规则。这样,无论什么差异的利益诉求都能比较恰当的整合到司法程序之中,诉讼主体可以积极的进行利益选择而不是完全的被动承受,这就从另一视角保障了程序的民主自治精神。而且,这种选择与自治不仅适用于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对侦控机关也同等有效。由此可见,契约观念和管制思想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可以为参与者能动性的发挥提供空间,从而体现其主体性。
(二)它增强了司法的确定性
现代司法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不确定性”,从超然的角度看,也许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但这对那些与司法结果休戚相关者而言,却无异于一种痛苦——诉求被搁置、肉身被束缚。所以,控诉机关与刑事被告人热切希望获取比较确定的结果、最大程度的降低诉讼风险就成为必然的反应,而辩诉交易就能比较有效的满足该要求:通过协商,议定出双方都可接受的利益处理意见,再加上,系列保证协议内容实现的制度措施,就把诉讼参与者对司法不确定的恐慌降到了最低限度。
具体而言,辩诉交易对控诉方来说,增加了对犯罪者定罪的机率,部分满足了国家刑罚权的实现,尤其是污点证人(tainted witness)的证言,它是实现对其他被告人成功指控的重要保证;而对被告人来说,其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命运更多的充满着不确定性,有时诉讼的进行就是一场赌博,而辩诉交易则消除了这种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赋予了被告人对自己命运在相对确定的条件下进行利害权衡和选择的机会;法官在很大程度上也乐于接受这样的处理方法,因为“没有审判,法官根本就不会犯审判上的错误”,也就避免了裁决结果被上级法院推翻的风险,从而维了护法官的职业信誉。
(三)它使司法制度能够回应来自犯罪学与刑法学的理论挑战
犯罪学中的“同意理论”(注:作为社会控制体系一部分的刑事司法,在犯罪学领域有两种具有统治地位的评价观点:“同意理论”与“冲突理论”(consensus and conflict theory)两者各自发展出了同意模式与冲突模式。前者认为,法律的发展是基于全社会的广泛同意,并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后者认为,法律是群体利益与权力动作相冲突的产物。同意模式在20世纪初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即使其影响力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下滑,在60年代丧失了其在法社全学与社会控制理论领域的奠基角色,并且现今主要理论已不再认为同意模式是最好的法律模式。但同意理论的假定在一定程序上已被现今流行的法律理论证实了其可靠性。如今,同意理论往往寄寓于“关系模式”(mutualiat models),或者某种冲突模式之中。冲突模式也被称为“功能主义理论”(functionalist theory),它可以说是同意理论的一种变形。它认为法律旨在谋求更多的社会福利。凭借有序的处理争端在规训越轨行为以及控制犯罪学领域仍有着重要的影响。Ronald L.Akers,Criminological Theories:Introduction and Evaluation,Roxbury Publishing Company,1994.P15-23.)与刑法学中的“人格责任论”(注:刑法中的人格责任论是为解决刑事责任的评价基础而出现的,即依靠什么样的评判标准来断定行为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它是行为责任论与性格责任论的折衷,即不仅要考虑行为人的外在个别行为,还要结合其人格态度,共同来决定他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其中的人格态度隐匿于行为背后,秉承了行为人先天的素质,受制于生活环境,并有其主观努力追求的综合结果。人格责任论要求刑事司法必须结合犯罪嫌疑人具体情形区别对待,而不能笼统处理。)在各自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基于刑事一体化的内在冲动,它们对刑事司法制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对既有体制也形成了较大的冲击。它们出于保卫社会、尊重犯罪嫌疑人的治理精神,强调刑事司法在犯罪治理方面不应致力于一时的“打压”,而应寻求以降低犯罪率为要旨的犯罪控制渠道。申言之,刑事司法要结合犯罪主体的特点与生活背景,作出个性化的反应。而辩诉交易能够对此作出比较满意的回应:控诉机关结合犯罪嫌疑人的人格特征,谋求以“同意”为基础的司法结果。由于该机制也对被害人利益一并参考,并为社会节省了资源,所以,它真正体现了“照顾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并增加社会福祉。的“同意理论”之精神。
(四)它能帮助刑事司法实现“双赢”
一边倒的“单赢单输”或“胜者通吃”的司法制度是有悖于社会治理精神的,司法程序的设计应该以获取“双赢”目标。合意下的契约是达此目的便捷利器,而辩诉交易的实施就是一明证。美国的Brady v.U.S.案特别强调了辩诉交易中的“利益相互性”(mutuality of advantage)。从政府的角度讲,准予被告人作有罪供述,可以尽快的实现惩罚目标,节省本已稀缺的司法资源,而且这也与刑事司法制度的恢复性目标相一致;对被告人而言,他看到了被宣判无罪或可以获得较轻刑罚的可能,同时可以减少“暴光”程度,尽快的进入矫正程序,并消除审判的实践压力等等。可以说,正是这种互惠机制使美国超过75%的案件通过辩诉交易结案。(注:Lloyd L.Weinreb,Criminal Procen:Cases,Comment,Questions(fifth edition),Westbury,New York,The Foundation Press,Inc.1993.P864.)
综上,可以说,以契约观念为核心的辩诉交易凭其独有的方式,维护了刑事程序的信誉与正当性。(注:正如有人对辩诉交易的评价:辩诉交易不仅使法官与检察官从近乎窒息的工作量中有所解脱,它还减少了检察官败诉与法官裁决被推翻的风险因而维护了他们的职业声誉。事实上,凭借缩减诉讼中事实或法律错误,辩诉交易保障了整个司法制度的信誉及其正当性。(George Fisher,Plea Bargaining's Triumph,The Yale Law Journal,Volume 109,March 2000,P867).)虽然,它并不是那么的名正言顺,似乎还有点不光明正大、缺乏磊落,但它毕竟胜利了。
辩诉交易在美国刑事程序中取得统治地位,其最有力的证据,也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在过去的150年里,很难找出其他的创新程序能与辩诉交易的发展与盛行相媲美。”虽然辩诉交易历来并没有好的“名分”——它取代了追求真理的高贵之战,它给我们的是一纸躲躲闪闪、偷懒式的停战协定,即使它的历史不值得我们为之吹起嘹亮的号角,但它还是胜利了——它的兵不血刃与暗渡陈仓使其横扫刑事司法领域,并击败了负隅顽抗的陪审团。(注:George Fisher,Plea Bargainlng's Triumph,The Yale Law Journal,Volume109,March2000,P858.)
五、辩诉交易在司法适用中的困难以及对传统司法的挑战
(一)司法适用中的困难
既然契约观念成为辩诉交易的内在主线,那么,让契约精神得以充分体现是实现辩诉交易目标的前提。从满足契约的角度讲,辩诉交易在司法实践中将面临如下困难:
1.难以明确适用范围
辩诉交易意味着国家放弃部分追诉权,即基于刑事政策、诉讼主体自主性协议的独特功能以及诉讼民主等因素的考虑,国家权益可以部分变通实现。那么,范围或限度如何确定?
国家在保卫社会过程中,可以选择不同的治理策略,但必须有合法性的底限。国家权力不可能无限制的与私权“兑换”,否则,将与“黑帮政治”无异,其将给社会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在刑事司法领域,主要涉及到:哪些案件、哪些程序制度可以适用协商性司法?依据的标准是什么?采用重罪与轻罪的分类标准,还是其他刑事政策的考虑?再加上工业社会的发展,侵权与犯罪的界限日益模糊,这就为适用标准的选择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2.难以真正保障主体间交涉能力的平衡
控辩双方要想获取交涉能力的平衡,主要是提高被告人的对抗能力,毕竟他们缺乏专业知识。这需要两方面的支持:他能聘用到水平不错的律师;该律师也能真正的从被告人利益出发与控诉方进行协商。而实践中,这两方面都难尽人意。
首先,当事人的贫富差距直接影响所聘律师水平的高低。贫穷的被告人只能聘用专业水准一般的律师,而且,特贫困者只能依靠政府所提供的援助律师,实践表明,从事法律援助的律师的水平往往低于其他专业律师。这就使那些贫困的当事人无法真正与控诉方对抗。
其次,当事人聘请的律师往往出于自我利益考虑,想尽早结束案件,而不顾当事人的真实意愿。最终使当事人的利益受损。
另外,即使律师真正关切当事人,水平也可以,仍存在“代理”中的转述问题——当事人的意思被曲解或被忽略等等。
3.审查与救济的困难
为保障协议是真实与自愿的产物,就必须有法院的审查和必要的救济相辅助。但具体到实践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真实与自愿的标准如何确定?二是控诉机关的裁量权如何控制?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在Brady v.U.S(1970)案中,最高法院指出,关于有罪答辩的自愿性的标准必须被实质性的界定。最终采纳了第五巡回区上诉法官Tuttle的观点:一个有罪答辩中,被告人充分意识到了它的直接后果,包括法庭、控诉方或其律师向他作出的承诺的实际意义,那么,该答辩才会有效,但如果出现威胁、误解或承诺本身不恰当——承诺是被告人与控诉方之间非法交易的结果,如涉嫌贿赂的情况,这会导致答辩无效。但我们仍会发现,该案所指出的标准仍非常富有弹性,无形中增加了法院审查的难度。
控辩双方达成协议的重要前提是,控诉方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否则无“资本”与被告人进行交换。但过度的裁量权往往易被滥用,比如,检察官如果考虑更多的是超法律变量,如种族、阶层、年龄以及性别,而不是相关行为与法律内的变量,如被告人被指控的罪行、以前的犯罪记录、有罪还是无辜,结果必然是不公正的,但对检察官的裁量权又很难进行法律控制。(注:美国检察官有着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只要不是故意违反公正的基本标准,诸如因为种族 宗教信仰而有所偏私,执法中有意识的选择是合宪的。但司法界也认识到,这样的裁量权容易被滥用,因此,在Bordenkircher v.Hayes案中,Stewart法官认为,检察官的行为要符合宪法第14修正字模当程序条款的要求。James B.Haddd etc.,Criminal Procedure:Cases and Comments,(fourth edtion),The Foundation Press,Inc.1992.P1063.)同时,被告人还面临着被报复的危险。(注:在Blackledge v.Perry案中,法官指出,辩诉交易中不可能杜绝检察官报复性的指控。(引自Jerold H.Isreal & Wayne R.Lafave,Criminal Procedure,法律出版社(影印本),432页。))
另外,辩诉交易还有其他的司法弊端,比如,它消解了控诉方的举证责任而可能导致控诉的惰性;控诉权力滥用的潜在性将逃避审查等等。
(二)对传统司法制度的挑战
主要是攻击了传统的司法公正原则。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刑事司法制度已经发展出了许多基本公正标准,作为一种底限,它们在保证被告人正当诉讼权利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辩诉交易却无情的冲击了那些被认为“不可替代”的价值原则。(注: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它遭到了诸多非议。在Unitde States v.Griffin案(Unitde States v.Griffin,462 F.Supp.928(E.D.Ark.1978)中,法官Eisele对辩诉交易提出了反对意见:辩诉交易程序有一种贬低所有参与者——控诉方、被告人、甚至法官——的倾向;它为险恶的暗示留有“后门”(bacd-room)而难保程序公正。由此所带来的结果是:公众的冷嘲热讽以及对司法程序正直品性丧失信心。)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适用中的“罪刑不均衡”必然破坏法律适用中的平等原则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一定的罪行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刑罚,同罪同罚。但辩诉交易的结果是,根据控辩双方的协议,重罪未必有重罚,最终必然出现罪刑不均衡、法律适用的不平等。特别是在共同犯罪中更为明显,两个面临相同指控的共同被告人,如果一个人作有罪答辩而另外一人坚持自己无罪,他们最后的刑罚将可能大相径庭。
2.从“无罪推定”到“有罪妥协”
无罪推定原则已成为当今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它保证了被告人在没有被法院定罪之前的基本人权待遇,使其享有包括辩护权在内的充分诉讼权利。可以说,它是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对抗侦控方的核心武器,是传统刑事司法公正的底限。但辩诉交易却根本上抛弃了无罪推定原则,采用的是有罪妥协原则,也是一种有罪推定原则,即控诉方要求被告人承认有罪、被告人自己承认有罪为相互妥协的前提,最终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协议。由是,协商性司法冲击了正统司法的基本准则。
3.冲击了司法的预期性
合理的一致性应该是刑事司法制度的一个目标,它的重要价值在于能给参与者一定预期。而辩诉交易却无法创造先例,因为它的每一次协议都充满了个性与变数,让那些后继者无法作出合理预期。
六、辩诉交易在我国的前景展望
有两方面问题必须讨论:一是我国司法现状,主要考察我国是否已经具备导入辩诉交易的本土资源;二是辩诉交易在中国发挥功能需要哪些前提?我们已经具备抑或尚有欠缺?
可以说,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十分抵触契约观念,认为它与司法追求的目标格格不入。这主要来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传统观念的力量。交易、契约自古以来名声较差,即使司法中有“服判”之说,也很难说具有契约精神。(注: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法文化是以争取同意为特征的,并以如下资料作为支持:《唐律疏议》中的“狱竟取服辩”条的规定;在清代,上级对重罪案件自动进行复审的目的是取得被告人的自我认罪书,而州县自理的轻微案件的审理则是一种使当事人心服或口服的解决问题的程序。详细论述参见季卫东著:《宪政新论——全球化时代的法与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104页。笔者不同意如此看法。中国历史中的刑事审判追求被告人的心服与认罪,仅仅是为司法的专横提供“体察民情”的外衣,实质上并没有赋予被告人自主选择权,也没有真正的主体地位,由此获取的同意只是一种“压制”下的合意,一种抽取契约精神的协定。)二是官方流行话语与态度。流行的观念把刑事司法目的界定为“打击犯罪、保卫社会”,工具性的意味十分浓厚,这就使得控诉方与刑事被告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对话。
抛开辩诉交易的弊端不谈,如果它的制度优势能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得以体现,我们还有哪些差距?
(一)现实的差距
可以说,让辩诉交易发挥良性功能,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主要集中在观念与具体制度两个层面:
1.观念有待革新与转变
首先,基于纳税理论与社会契约论,国家不可遥遥在上,它应该和包括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在内的公众进行平等对话。
国家虽然有管理权、一定的强制执行权,但也应该提供平等协商的空间,营造出真正的对话平台,因为只有在“理想的对话情景下,所有论辩参与者才会机会均等、言论自由、没有特权、真诚、不受强迫。”(注:[德]考夫曼著:《后现代法哲学》,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在这一平台上,公众首先应有广泛的自由选择权利,正如杰斐逊在1801年的首次就职演说中所说的,“一个开明而节俭的政府,它将制止人们相互伤害,但仅此而已,在其他一切方面将放手让人们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和从事自己的事业。。(注:米尔顿·弗里德曼,米斯·弗里德曼著:《自由选择:个人声明》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页。)其次,国家应该放弃纯粹依靠暴力来治理的方式,需要注重协商与论谈的功能,这是步入民主国家的重要条件。英国学者芬纳在其著作《政府发展通史》中指出:20世纪后期主要的政体形式就是论坛国家,“论坛政体的主要原则是可解释性,即进行劝说,而不是强制实施它的主要措施。”(注:“世界是如何被统治的——评芬纳〈政府发展通史〉”,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4期。)
其次,司法应关注参与主体的现实利益。弗里德曼曾经把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都看作市场。在其中,结果取决于人们追求自身利益(广义的)时的相互作用,而不取决于参与者认为可以大肆宣扬的社会目的。(注:米尔顿·弗里德曼、米斯·弗里德曼著:《自由选择:个人声明》,商务印馆1982年版,第4页。)其实,司法制度也受该规律的支配,真正决定司法过程与结果的,往往不是法律规定的检察官职能的运作、追求一般舆论认为的司法目标的结果,恰恰相反,检察官、法官以及被告人“自身的小算盘”却经常起着关键作用,比如,检察官不愿意败诉、法官不愿意冒自己的裁决被推翻的风险、被告人也往往有着更多的利益考虑而不是仅仅追求程序保障、较轻的刑罚。这些因素非常“隐蔽”的对司法程序的实际进展发挥着作用,但制度设计者们忽略或者不愿意考虑这些因素,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既有法律制度与实践运作的脱节,而辩诉交易恰恰弥补了其间的沟壑,揭示了司法真实的侧面,通过它,我们能洞察司法过程中利益是如何进行较量的。同时,立法者与学界必须有揭去司法高尚面纱的能力,否则,辩诉交易无法获取生存的土壤。
另外,我们应认识到,“解决纠纷”也应是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之一。而我国刑事诉讼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展示国家公权力的一个道具,不要说关注解决刑事纠纷了,就连基本的对抗都很难保证。以英美为代表的对抗式诉讼,从某种角度讲是一种解决纠纷的模式,它非常注重如何让争端双方都获取比较满意的结果,而不是侧重谋求国家公权力如何获胜。也正因为如此,辩诉交易在对抗式模式中更容易形成。如果我们的司法目标体系中不注入解决纠纷的诉求,辩诉交易存在的动因将大大减损。
2.制度方面的不足
辩诉交易得以运作的制度前提是,必须有保障契约双方地位平等、意志自由、有对抗与利益交换可能的制度。虽然我们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口头掸“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家喻户晓,但它没有任何制度保障;刑法典虽然明确规定了自首与立功的情形下,被告人可减免刑罚,但它和诉讼制度没有建立对接,所以,即使被告人自首或立功了,如果侦控机关不信守诺言,他就未必减免刑罚;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对控辩双方的不平等对待俯首即拾,由此可见,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十分缺乏“契约精神”,特别是制度保证下的契约精神。主要的制度性缺失表现为如下两大方面:
第一,司法体系缺乏必要的诚实信用品格,对契约观念缺乏有力的制度保障。基于侦查与控诉的需要,侦控机关可以在刑事司法中适用“欺诈”的方法,很多国家对此都能达成共识。但我们的制度缺憾在于,侦控机关可以适用什么样的欺诈手段,底限何在,以及他们违反承诺的法律后果等等,都没有任何制度规定,以至于侦控方可以信口开河的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承诺,即使不能兑现也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但常此下去,丢失的将是整个刑事司法的信誉。
司法应该具有诚实品格,这样才能激发公民对法律的忠诚乃至一体遵守;如果公民觉得司法运作充满了欺诈与骗局,就可能对本国司法丧失信心,漠视法律的心态与相应行为就当然出现并可能蔓延。由此造成的损失在短期内将难以弥补。所以,一国司法体系应该是令人尊重并讲究信用的(respected and believed)。如果司法能发挥什么作用的话,它必须的前提是令人尊重并值得信赖。(注:Ronald J.Allen,Richard B.Kuhns Constitutional Criminal Procedure,(Second editi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1)P945.)并且,公众对这样司法信念的必需保留就一国法治而言至关重要。正如有学者所说,公众对公平与正直司法运作的信心是法治赖以存在的基础,而且往往在胜败悠关(at stake)之际具有超越性价值(transcending value)。(注:Welsh S.White and James J.Tomkovicz,Criminal Procedure:Co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Upon Investigation and Proof,by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orporated.(1990)P426.)
第二,控辩双方“交涉能力”严重失衡,使契约观念寸步难行。可能是基于职权主义模式的原因,我们刑事制度的一大症结是:控辩双方缺乏对抗条件,双方的交涉能力严重失衡。面对控诉方的力量本已远远超过辩护方的事实,我们的立法对这一差距并没有进行有效的协调,使得司法中的这一“跛脚现象”愈演愈烈。比较明显的例子如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难;刑事辩护律师随时冒着涉嫌伪造、毁灭证据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危险;现行刑诉法改革了起诉方式之后,辩护方获取案件事实信息的渠道更加狭小。这种公权力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极度不信任与敌对的司法制度,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辩护律师不能获取必要的案件事实信息,同时也不敢轻易自行调查,他们将没有任何资本与控诉机关进行对抗与交涉,即使控诉方提出可以协商解决,辩护方面临的也只是“要钱还是要命”的选择,自愿必定是虚假的、被胁迫的,所以,在这样的制度前提下,即使有契约的外壳,也不会形成真实、自愿的合意。
(二)致力于构建成熟的刑事司法制度
在目前的中国,司法改革已成为法律界的热点话题,虽然其间论域广泛,但有一个重要的、具有导向性的主题被不合理的忽略了,即一国司法制度成熟的标志是什么?笔者认为,司法是为社会而存在的,一个成熟的司法制度,它必须能够真正的适应社会现实、有效的回应并解决社会中的司法争端。所以,对社会现实的充分把握是构建成熟司法制度的知识前提。
当下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化、民主与自治精神不断提升、越来越注重人文关怀的共同体。司法制度必须相应作出调整才能保证程序的有效性,通过增强制度的包容度、寻求制度的多元化,(注:正如Milton Keynes Audit(multi-institutional bureaucratic)(Andrew Sanders & Richard Young,Criminal Justicd,second edition,Butterworths,2000,P61))使诉讼制度有生产“让所有利益主体都满意的结果”的能力。这就致力于构建成熟的刑事司法制度而言,不失为理性的选择。
具体到我国,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工具式”刑事司法制度早已不能适应市场十分活跃的社会现实。历经学界对正当程序理论的引介、实务部门相应的改革努力,追求程序公正的观念,正逐步深入民众与司法制度的骨髓,这与市场追求形式与规则平等的思维不谋而合,因此,严格遵循规则之治的正当程序模式对我国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该模式的缺陷在我国同样未能避免,如它的高成本使贫穷者望而却步;它的精细与复杂使审判日益笨重;它的刚性使其丧失了必要的人文关怀以至近乎残酷;它的单调性使其无法回应多样性的争端,在解纷止争面前日显捉襟见肘。也许如上弊端所致,虽然人人都向往“阳光司法”、“看得见的正义”,但现实中“单方面接触”、追求“黑色正义”的现象屡禁不止。基于辩诉交易的独特运作方式与功能,它可以对正当程序模式所产生的盲点进行有效的弥补。所以,结合司法实践,辩诉交易在中国的命运将是作为正当程序模式的补充而确立。
但辩诉交易毕竟对传统司法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前者以纠纷的真正解决为出发点,充分考虑了诉讼主体的现实利益,注重当事者之间通过“合意”完结诉讼,体现了一种契约观念;而后者固守刑事司法是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而设,注重严格的规则之治、追求绝对的程序公正。这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司法模式,在价值诉求与司法实践中必然相互“拆台”。这在当下中国真正的程序正义理念尚未真正确立之际,却出现了具有后现代意味的契约式司法,就司法改革而言真有些反讽意味。而学界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刑事司法领域究竟能为辩诉交易开辟出多大的空间,即其范围如何确定,制度间的冲突如何解决?还有其间的其他具体问题,笔者会继续进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