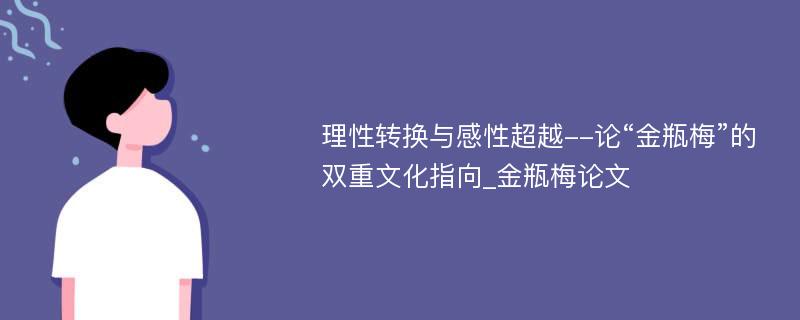
理性的皈依与感性的超越——论《金瓶梅》的二元文化指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瓶梅论文,感性论文,理性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瓶梅》的价值指向表现为鲜明的二元对立。在小说中,作者始终为警饬世俗、惩戒四贪的创作主旨所驱使,在理性支配下,喋喋不休地进行宗法道德观念的高谈阔论。但另一方面,当将笔触伸向了世俗社会的各个角落,在对世俗生活的红男绿女们进行真实再现的时候,又冲破了自己道德劝惩的藩篱,去呈现芸芸众生没有理性节制的追求,不为群体意识羁绊的个体意识的张扬,商品经济冲决小农经济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人欲的膨胀与竞逐,以及由新经济因素滋生而带来的与传统的价值观念、理想人格、评判标准大异其趣的社会潮流。这种二元的文化指向,使作品一方面明显具有迂腐的道德说教的意蕴,另一方面却在感性上回归人性的真实,悖反于某些陈腐的宗法传统观念。
一
兰陵笑笑生的女性道德观是落后的、保守的。女人是祸水的观念在其头脑中根深蒂固。“水性下流,最是女妇人。”(第69回)“大抵妾妇之道,蛊惑其夫,无所不至。虽屈身忍辱,殆不为耻。”(第72回)小说开篇伊始,作者就借刘邦、项羽故事,大发其道德议论,认为项、刘二人“固当世之英雄,不免为二妇人,以屈其志气”,“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要求女子必须以“贞”、“节”自砺,恪守宗法观念所规定的妇道,“持盈慎满”,做个封建“淑女”。入话故事结束后,作者便声明道:“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了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永不得着绮穿罗,再不能施朱傅粉。静而思之,着甚来由?况这妇人,他死有甚事!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第1回)第4回回首诗曰:“酒色多能误国邦,由来美色丧忠良。纣因妲己宗祀失,吴为西施社稷亡。自爱青春行处乐,岂知红粉笑中殃?”这些说教的意思非常明白:妇女为一切罪恶之源;女性应该贞洁、守分,遵从尊卑的安排;西门庆、陈经济之死,完全是因为贪恋《金瓶梅》中恶源的代表之一——潘金莲的缘故。
《金瓶梅》的具体描写果真阐述证明了以上的观念与意旨吗?回答是否定的。小说中一系列的罪恶事件诸如武大郎遭毒害,花子虚被气死,宋惠莲上吊,宋仁命丧,来旺儿被无辜递解,蒋竹山惨遭毒打、药铺被砸,苗青杀人越货而逍遥法外,都能归罪于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弱小、可怜的女性吗?武大郎的悲剧,由西门庆与王婆联手导演,潘金莲只不过是在畸形反抗不道德婚姻过程中迷失了自我的情况下,去按“导演”的要求“敷演”而已。花子虚之亡,除了他自己霸占家产、狂嫖滥淫、恶了兄弟妻子的内因之外,还有其结拜兄弟西门庆垂涎其财产、妻子的直接外因。宋惠莲是在虚荣、受骗、蒙昧中清醒过来以后,在跪求无望、家破夫散的情况下,斥责了西门庆这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惯了。害死人,还看出殡的!”对一切都绝望后才“自缢身亡”,撒手人间。宋仁是在为女儿的喊冤声中被西门庆打点贪赃枉法的正堂知县李大人,遭受毒打后气病而死。来旺儿被递解徐州,是西门庆为了淫欲的满足,要霸占其妻而施的毒计。至于说到蒋竹山的不幸,归根到底在于他开生药铺撑了西门庆的买卖。总之,是污秽、龌龊的社会与罪恶的男性世界导演了这一幕幕罪恶的悲剧;而女性的命运却完全被操纵在男子手中,她们是罪恶社会迫害的对象。透过《金瓶梅》的感性描写,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在男权社会中的种种不幸。
《金瓶梅》里描写了众多的女性。吴月娘可谓作者表彰的最“本分”、最守妇道、可作闺阃楷范的人物。最不本分的、受作者指责最多的莫过于潘金莲、李瓶儿了。吴月娘一生唯西门庆一人是从,她反抗过殷天锡的强暴,在梦中抗拒过云离守的调戏。在对西门庆的狂嫖滥淫、胡作非为劝阻无效后,她便缄口不言,每天只是礼佛诵经,虔诚地接受女尼的宣卷劝化。夫主的爱敬,她得不到;生活的乐趣,与她无缘;就连床上的夫妻恩爱,她也极少体验。伴随着这位恪守妇道的正室妇人的,永远是落寞孤寂,她只有在虚无缥缈的佛祖处寻找到一丝慰藉。在守活寡的漫漫时日中,她丧失了自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女子,她身上没有青春的活力,即使偶尔有欲的冲动,也往往要遮盖上一层道德的面纱——出于为夫主生子传嗣的考虑。总之,作者是按照宗法道德的标准去塑造、赞扬吴月娘的。但读者透过文本所呈现的吴月娘的遭际,来对其生存价值进行评判时,只会得出与作者完全悖反的结论。李瓶儿,是介乎吴月娘和潘金莲之间的女性。她一生凡四适。无论是在“夫人性甚嫉妒,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后花园中”的梁中书府中作妾的日子里,还是嫁与唯知吃喝嫖赌的花子虚的岁月中,抑或招赘“中看不中吃,蜡枪头、死王八”蒋竹山作倒插门的短暂时光内,她都处于青春的压抑、性的饥渴之中。后来遇到了西门庆,她才真正得到了本能的满足,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至于一夜也离不开男人、受作者谴责最多的潘金莲,本性聪明伶俐,多才多艺,不屈从于命运的捉弄,不相信冥府、天道的安排,而不惜一切、不择手段地去追求她所认为的本应属于自己的幸福的权利。她与西门庆通奸,她偷陈经济,她将小厮拉进被窝,既是出于性的饥渴,又隐含着先是对不道德的婚姻,后是对西门庆将其偏置的一种变态反抗情绪。这些描写固然引起人们对潘金莲畸形性格、变态抗拒行为的非议,但更能引发人们对其堕落原因作深层思考,从而对女人是祸水的陈腐观念提出异议。
在《金瓶梅》的女性世界中,孟玉楼与吴月娘一样也是作者肯定的人物。但具体理论起来,孟玉楼是算不得贞节的。她先嫁杨宗锡,次醮西门庆,西门庆尸骨未寒,她竟又迫不及待地再适李衙内。小说第18回,孟玉楼在吴月娘面前议论说,李瓶儿在花子虚未死几时,孝服未满就嫁人,使不得时,吴月娘骂道:“如今年程,论的什么使的使不的?汉子孝服未满,浪着嫁人的,才一个儿?”而当时孟玉楼正是再醮西门庆不久。可见,在吴月娘这个真正“贞节”的女性心目中,孟玉楼当然也在“浪”列。在小说中作者没有把孟玉楼写成如金、瓶、梅、王六儿等那样床上功夫扎实的人物,而是将她与吴月娘归为一类。严格说起来,她与吴月娘有着很大的不同。她们对封建礼教谨从慎依的程度绝非“量”的差异,而是“质”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吴月娘才是整部《金瓶梅》中能够称得上“贞节”的女性。然而,作者感性描写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与其理性评判却完全相反。不贞的孟玉楼远比守身如玉的吴月娘幸福。西门庆在世时,吴月娘眼睁睁地看着他一房一房地往家里娶妾,明目张胆地嫖妓宿娼,暗中私通仆妇丫头,自己落得独守空房,百般无奈之余,不得不在僧尼的宣卷讲经中打发时日。西门庆死后,她由守活寡而守死寡;正妻名分的牢笼,限制着她必须像王招宣府的林太太那样为夫守节守孝来打发余生。不同的是林太太寂寞难耐时,是靠偷汉子来获取满足,而吴月娘万念俱灰,让自己麻木于宗教的天国中。她的悲哀不仅仅在于她个人的主观因素,更在于理学的异化,宗教的欺骗,使她丧失了自我,成为一具没有思想、没有活力的理学标本、宗教躯壳。而“等而下之”的孟玉楼身上却无时不表现出青春的活力,人性的闪光。她始终是自我的主宰者。丈夫杨宗锡死后,她谢绝了张四舅对尚举人的保举,而选择了西门庆这一富商。在妻妾成群的西门府邸,她既作了有效的抗争,而又不露声色,让潘金莲做自己的马前卒。在西门庆死后,她果断、明智地“爱嫁李衙内”,“青春年少,恩情美满”(第92回)。当陈经济拿着她往日丢失的金头银簪子来要挟时,她更是将计就计,为维护自己的幸福而惩治了这个流氓浪荡儿。尽管作者在价值评判时,理性的褒扬更倾斜于看重名分、恪守宗法传统妇德的吴月娘一方,但感性的描写却有着让读者认同孟玉楼享受生活、追求幸福的指向。作者理性肯定的吴月娘在丈夫生前死后的遭际让人觉得可悲,而感性描写中的孟玉楼的择夫、改嫁却让人觉得明智,她的结局堪称幸福美满。
二
《金瓶梅》中宗教观念的二元指向也是非常突出的。
有明一代,虽然各位当国者崇道敬佛各有所爱,但儒、释、道三家归一的趋势已日渐明显。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释道》中说:“我太祖崇奉释教,……至永乐,而帝师哈立麻,西天佛子之号而极矣。历朝因之不替。惟成化间宠方士李孜省、邓常恩等,颇于灵济显灵诸宫加奖饰。又妖僧继晓用事,而佛教亦盛,所加帝师名号,与永乐年等。其尊道教亦名耳。武宗极喜佛教,自列西番僧呗唱无异,至托名大庆法王,铸印赐诰命。世宗留心斋醮,置竺乾氏,不谈,初年用工部侍郎赵璜言,刮正德所铸佛镀金一千三百两,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议,至焚佛骨万二千斤。逮至今上,与两宫圣母,首建慈寿万寿诸寺,俱在京师,穹丽冠海内,至度僧为替身出家。大开经厂,颁赐天下名刹殆遍。”由于各教一瞬间的荣辱崇斥,便促使其加快了相互吸收、彼此靠拢的进程。《谷山笔尘·释道》中曾载万历时期的大儒于慎行的如此言论:“江左(按指东晋)以来,于吾儒之外,(佛道)自为异端;南宋以来,于吾儒之内分两歧(按指斥释道为异端与否);降是而后,则引释氏之精理阴入吾儒之内矣。”甚至会出现《明史·礼志四》中所说的“祀孔子于释、老宫”这种三教同祀的现象。明代中叶宗教的流布社会、深入人心,使得兰陵笑笑生在理性上对其具有相当虔诚的崇信与皈依思想;但不同教门的荣辱毁誉,神职者流的卑鄙污秽,又使得兰陵笑笑生在进行感性描写时,自觉不自觉地冲破了理性的羁绊,对肮脏的神职人员进行入木三分的嘲弄与揭露。这样,便使得《金瓶梅》在宗教观方面出现了二元对立的文化指向。
出于劝善惩恶、惩戒四贪的创作命意的需要,作者对佛道的描写占去了大量的篇幅。全书的结构框架,也有明显的佛道意识支配的痕迹。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无不是在宗教宿命的安排下,完成今世之一劫。正如作者在全书终结时所说:“闲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西门豪横难存嗣,经济颠狂定被歼。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可怜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西门庆集四贪于一身,作恶多端,恶贯满盈,死后妻妾四散,遗腹子出家,果报累累;潘金莲受到剜心碎尸的报应,李瓶儿子亡身殒,庞春梅淫纵命丧,陈经济惨遭杀戮。这些安排,正是作者理性上宗教观念的体现与反映。
然而,兰陵笑笑生在具体描写僧尼、道徒的宗教活动时,又极尽讽刺、鞭挞之能事。作者揭露了僧道神职人员的荒淫无耻、亵渎教规,借清净之地大干淫荡卑鄙的勾当。第8回中为冤死的武大郎烧灵、 做水陆道场的众和尚,“见了武大这个老婆,一个个都昏迷了佛性禅心,一个个多关不住心猿意马,都七颠八倒,酥成一块。……色中饿鬼兽中狨,坏教贪淫玷祖风。此物只宜林下看,不堪引入画堂中。”“淫妇烧灵志不平,和尚窃壁听淫声。果然佛道能消罪,亡者闻之亦惨魂。”和尚是“色中饿鬼”,尼姑更是不守本分。第40回针对吴月娘深信王姑子之举,作者道:“看官听说:但凡大人家,似这样僧尼牙婆,决不可抬举。在深宫大院,相伴着妇女,俱以讲天堂地狱、谈经说典为由,背地里说釜贪款,送暖偷寒,甚么事儿不干出来?十个九个,都被他送上灾厄。有诗为证:最有缁流不可言,深宫大院哄婵娟。此辈若皆成佛道,西方依旧黑漫漫。”僧尼是财色的化身,道士更加龌龊。碧霞宫的庙祝道士,“也不是个守本分的。……极是个贪财好色之辈,趋时揽事之徒。……原来他手下有两个徒弟,一个叫郭守清,一个名郭守礼,皆十六岁,生的标致。……到晚来,背地便拿他解馋填馅。明虽为师兄徒弟,实为师父大小老婆。……看官听说:但凡人家好儿好女,切记休要送与寺观中出家,为僧作道,女孩儿做女冠、姑子,都称瞎男盗女娼,十个九个都着了道儿。有诗为证:琳宫梵刹事因何?道即天尊释即佛。广栽花草虚清意,待客迎宾假做作;美衣丽服装徒弟,浪酒闲茶戏女娥:可惜人家娇养子,送与师父作老婆。”(第84回)总之,贪婪、荒淫、欺诈、行骗是僧尼道士的共同特点。作者如实地描写出现实中神职人员的无耻行径,无疑是对宗教的极大嘲弄。而这种厌佛恶道的描写、贬佛斥道的文字,与小说整体框架所呈现出来的宗教意识恰恰是一种鲜明的二元对立。
三
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往往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评判标准,即道德评判与历史评判。所谓道德评判,是指对人物、事件的善恶审视;所谓历史评判,是指对人物、事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审视。二者有时统一,有时却悖反。
兰陵笑笑生对商品经济冲击下出现的多元并存的社会意识的评价就陷入了尴尬的二难境地。他在理性上表现为一种道德眼光,运用宗法道德的标尺,去褒贬金钱肆虐下各个阶层人物的言行举止;但当他从艺术规律出发将笔触伸向现实生活时,却又表现为一种感性的、不由自主的历史评判态势。
从理性上来说,兰陵笑笑生对西门庆之流的所作所为是深恶痛绝的。说西门庆是新兴商人也好,还是官、商、霸三位一体也好,总之他身上的市井味、商贾味特别重。这个形象只能孕育于《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七中所说的“务要委曲周全,勉为商人计”、“凡能宽一分,使商人受一分之赐,莫不极力为之”的明代中叶变“抑商”、“贱商”为“重商”、“恤商”的社会条件之下。而商人意识形态的典型表征,就是对财对利的趋之若鹜。兰陵笑笑生把西门庆写成一个众恶所归的人物,一再地对他贪财嗜利的行径进行谴责。小说第48回,作者借山东监察御史曾孝序的参本,斥责西门庆:“本系市井棍徒,夤缘升职,滥冒武功,菽麦不知,一丁不识。纵妻妾嬉游街巷,而帷薄为之不清;携乐妇而酣饮市楼,官箴为之有玷。”并且,作者让吴月娘以道德的完善去拯救西门庆堕落的灵魂,挽回西门家族衰颓的命运。在作者的理性观念中,人欲横流,人心不古,风俗浇薄,道德沦丧,根源正在于商人的兴起,金钱的肆虐。而只有儒家纲常伦理这副“灵丹妙药”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才能消弥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切罪恶。
然而,作者的感性描写却又冲破了这种理性评判的局面,表现了商品经济的强大生命力、商贾阶层的横行社会以及由此带来的观念形态的变革。西门庆这个拥有巨额金钱的商贾,雄心勃勃,野性十足,大有睥睨一切、傲视万物的气概。他凭恃手中的雄厚资金,玩官府、法律于股掌,表现出对封建政权的亵渎不恭。他跻身官场以后,五品提刑官身上竟罩上二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穿着的青缎五彩飞鱼蟒衣,甚至他的妻妾们也都明目张胆地穿着《明律例》、《明会典》中严禁民妇穿着的大红衣服。他凭着毫不吝啬的金钱馈赠与上千两银子的酒席盛筵,使得那些上上下下的封建官吏以结交西门庆为荣耀,出入于他的门庭,拜倒在他的脚下,并且给他的商业经营、牟利需要大开方便之门。总之,金钱的威力,商贾对封建等级秩序的僭越,对宗法传统的悖逆,都在这些客观描写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正是这种客观的描写,使得《金瓶梅》成为一部研究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的巨大变革的不可忽视的力作。
四
德国心理学家施普兰格尔在《价值的等级》中曾说过:“在两种价值之间舍此取彼,这是一种极简单的心理行为。但是,一个人受到以往文化的影响,受到某一特定的集体道德观念及一种独特的、冲突性的情境的影响,那么他所处的这种复杂的伦理情境和那种简单的心理行为就相去甚远了。”他并认为,“集体的准则在意识中所起的作用就是指出最高、最关键的行为价值,其强度之大,是任何个人的准则和怪癖都不能抗衡的。”《金瓶梅》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互不包容的二元价值指向,原因是极为复杂的。
首先,就中国封建城市市民本身的素质来说,16世纪的中国市民,其构成成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失去土地而流入城市的农民。他们不可能割断与封建土地制度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没形成过属于自己阶级的独立意识,没有西欧中产阶级那样共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野心。浓重的时代和历史的心理积淀,使他们面对突如其来的社会变革无所措手足。一方面,时代的变革促使他们摒弃安常守故的生活准则,冲破宗法传统社会的宗教观念、道德观念而去追财逐利、放纵自我;另一方面传统的小农意识和封建的伦理纲常、宗法观念又是他们观察思考问题时不能超越的怪圈。新旧观念时常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发生冲突与融汇的双向运动,“利”的追逐与“义”的羁绊、“欲”的满足与“理”的枷锁在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时常发生着激烈的冲撞。他们既吮吸着新思想的滋养,又因袭着宗法传统的重负;既有着伸张自我的要求,又无时无刻不受着潜意识中宗法传统观念的制约。作为市民文学的典型载体,《金瓶梅》正反映了这种历史的真实。
其次,就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属性来说,他们任何时候也没有摆脱过对封建统治阶级和宗法政权的依赖,摆脱不了已化为骨髓血液的宗法文化积淀的制约。他们有的尽管暂时成了统治者的弃儿,落拓于市井闾里,但他们潜意识中的宗法观念、卫道基因却一直在相当程度上主宰着他们的言行。可以说,鲜活的“弃儿”社会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灵感,促使他们站在市井的角度去全方位描写“弃儿”社会的生活、理想,表现这个社会人们的痛苦与抗争,并在这种描写中宣泄胸中的不平与块垒;但正统儒家思想已化为一种情结存在于他们的思想深处,兴观群怨、文以载道的诗教与创作观的制约又要求他们必须对自己的故事和人物作出理性的判断。既然“六经、《语》、《孟》,谭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好,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作为辅助政教的文学创作在内容上就应该“不谬于圣贤,不害于风化,不戾于《诗》、《书》、经史”〔1〕,达到让“怯者勇, 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2〕的目的。于是,告诫连篇、 新旧观念混杂的小说大量出现。劝喻世人、警戒世人、唤醒世人的冯梦龙,“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的凌濛初,塑造小说人物“以为世型”的陆人龙等,就是这种创作倾向的代表人物。就《金瓶梅》这部小说来说,兰陵笑笑生一方面看到人欲张扬对冲破理学禁锢的积极意义,于是他便从市民意识出发,肯定人的自然本质,去表现女性对自身幸福的希冀与追求,商人对金钱财富的索取以及睥睨封建权威的勃勃雄心;另一方面又看到了人欲的放纵危害到了这个社会根基的稳固,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于是他就又操起了儒家伦理这把标尺,站在卫道的立场上,对他笔下的人物进行道德的衡定及伦理的褒贬。他一方面诅咒现实中神职人员的龌龊行径,另一方面又对宗教的劝善本意和抚慰苦难人生的精神抱有深深的敬意。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市民意识与宗法观念在他头脑中不断交战,彼此消长,这便使得他在观察问题时陷入了一种双重价值的二难境地。
再次,就时代的因素来说,明中叶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纷繁复杂的。用宗法伦理观念、等级观念、尊卑观念等去规范、整合人们的灵魂,是历代封建王朝一以承之的统治措施;用宗教的鸦片麻醉人们的意志,也为历代统治者所惯用。在明代,被朱氏王朝高度推崇的程朱理学,甚至排斥和扼杀人的一切欲望,宗法道德对人性异化的程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观念铸造了人的灵魂,规范着人的理性世界。兰陵笑笑生生活于是时,他因袭着宗法传统文化的重负,当然会由此出发来评价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然而,明中叶又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竞争的时代。在意识形态领域,随着新的经济因素的产生、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而萌发的迥别于宗法意识形态的反叛狂潮,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有着千姿百态的表现形式。以李卓吾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对程朱理学及宗教欺骗的揭露,对利与欲的大肆鼓吹,在当时影响颇大。这种以纵欲为基本特征的社会情绪,对每一个社会现实中的个体都有着莫大的震撼力。传统的价值体系的稳固的根基动摇了,而建立新的合理的道德规范的土壤尚未形成,于是世俗社会陷入了无所适从的极度迷惘与困惑之中。在这种困惑与迷惘中,人们以自我为中心,去挣脱理性人格的枷锁;立足于个体的自然本性,去轰毁理学这条异化人性的锁链。兰陵笑笑生体察到了这种世俗观念的变迁,当他以忠实生活的创作态度去描写他身边的纷纭世界时,就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突破自己观念中根深蒂固的信条,真实地反映出这种“冲突性”的“伦理情境”。总之,作者理性与感性的分裂,使《金瓶梅》在观念形态上呈现出驳杂的色彩。市俗文化与传统文化、市民道德与宗法道德的冲撞与交融,孕育出了这部杰出的具有二元文化载体的小说。
注释:
〔1〕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序》。
〔2〕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
标签:金瓶梅论文; 兰陵笑笑生论文; 西门庆论文; 文化论文; 二元对立论文; 读书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孟玉楼论文; 潘金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