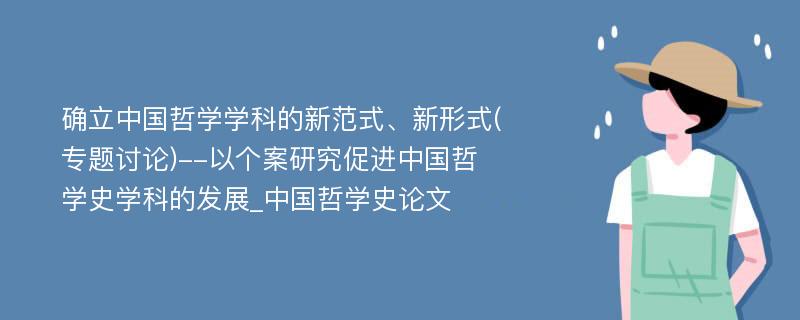
创建中国哲学学科新范式与新形态(专题讨论)——以个案研究推进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学科论文,专题讨论论文,哲学史论文,范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3-0046-15
近年来对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展开的讨论,引发了学术界检讨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我认为,这种检视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哲学如何才能健康发展。21世纪的中国哲学能否重振旗鼓,挺立于世界哲学之林,首先要看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传承如何。21世纪中国哲学是传统中国哲学的延续。我们只有准确解读传统中国哲学,并且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哲学作出准确评判,才谈得上传承与发展,才能有21世纪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新发展。
在20世纪,以西学为摹本的中国哲学研究自身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将古代中国哲学史上真正具有哲学价值的一些重要作品边缘化甚至排除在外,二是将一些体现中国哲学特性的文本内容牵强附会于西方哲学体系,造成误读失真。这两点造成了中哲史的个案研究的颇多问题。
例如,《周易》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保存完好的原创著作,分为卦象与经文两个部分,经文是对卦、爻象征意义的一种例说。魏晋学者王弼讲的“以言明象,以象尽意”,准确揭示了卦爻符号与经文之间的关系。以经文揭示卦象的含义,以卦象含义推论具体事理,成为《周易》的主要功能。《左传》、《国语》保存有二十二条历史记录,其中不乏直接援引《周易》分析具体事理。《周易》以其类比思维的方式,影响并规范着中国人的思维实践。从逻辑思维的角度看,《周易》不仅有阴爻、阳爻这两个初始符号,有八经卦、六十四复卦这两大类对象语言,有说明这些对象语言的卦爻辞即自然语言,还有一系列进行类比推理的语法语言。这是一个具有类比性质的符号推理系统,其推理的结论具有或然性。《周易》不仅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个符号推理系统,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唯一的一个类比推理之系统。从哲学思辨角度看,中国哲学史上凡有所成就的学者,都受到过《周易》的影响,他们精彩的思辨成果往往都与《周易》密切相关。其中大多数人都有一部甚至数部与《周易》相关的研究著作。令人遗憾的是,近现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者却大多忽视了对《周易》的研究,他们所编著的通史类著作往往将《周易》主要视为占筮书而已。这样,一部本来具有高起点的中国哲学史便成了一潭无源之水。虽然目前在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里已恢复了《周易》的应有地位,将《周易》的推理逻辑作为中国逻辑史的起点,但是这一专业研究成果尚未引起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者的普遍关注。
如果说,忽视《周易》是一种放弃,那么,对公孙龙思想的评判则明显是一种误读或曲解。公孙龙是一位从事纯学术研究的哲学家。先秦诸子甚至所有的古代学者,都将做学问与经世处事联系在一起,唯独公孙龙一心从事“离形而言名”的纯学术研究。他因“疾名实之散乱”而力图“正名实,化天下”,全然不同于孔子通过“正名”走向“复礼”的政治意图。他的“唯乎其彼此”的唯谓原则,将正名理论上升到逻辑的高度,其理论价值不在同时期的西方亚里士多德之下。他在《指物论》中既讲“指也者,天下之所无”,又讲“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将研究提高到了哲学的层面。他在《名实论》、《白马论》等文章中讲的是逻辑,而其《指物论》则无疑是一种哲学思辨,讲的是逻辑哲学。保存至今的公孙龙的五篇文章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具思辨色彩和理论价值的原始文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对公孙龙哲学思想有什么准确的理解。明代末期,程智对公孙龙思想作出了比较准确的阐释,尤其是对其“真白”、“真指”、“真物”的描述性定义,揭示了公孙龙思想的核心①,指出公孙龙所谓的“真白”,是指“不著形质,不杂青黄之白”,即脱离具体事物、脱离其他颜色而独立存在的一种颜色;所谓“真指”,即“不至之指”,是一种不指谓具体对象的独立存在;所谓“真物”,是一种“与天地皆极之物”。这种“天地莫测”、谁也不能确切捉摸到的物,不是凭空虚幻的,而是一种客观存在。在三“真”基础上,程智运用公孙龙在《指物论》中的论述,对指与物、指与物指的关系作出进一步的阐释,认为从“真指”到“物指”之间,有一个“是非相错,此彼和同”的指物过程;经历了这一过程之后所形成的“指”,就不再是抽象的真指而是具体的物指了。例如,“不著形质”的“真白”,是“不白石物而白”的抽象;“真白”一旦与石、马相兼,就成了具体的可以看得到的白马之白、白石之白,形成“白马”、“白石”之类的物指。公孙龙的思想细密精微,其所思所辩似乎不著人间烟火,属于纯学术研究;其所达到的哲学理论的高度也并非他的同时代人所能理解,甚至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能够真正懂得他的慧心所在。两千年之后的程智读懂了公孙龙,但是“不喜举子业”的程智对公孙龙思想的阐发并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也未能引起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者的注意。在汗牛充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著作中,从未出现过程智这个人的名字。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近人并未读懂公孙龙,自然也对程智不感兴趣了。冯友兰说:“《指物论》是不好懂的。其所以不好懂是因为它企图回避物质存在的问题。”②其实,关于“物质”问题,公孙龙在《名实论》中讲得很清楚:“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在《指物论》中也说:“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由于不理解公孙龙的真实思想,曲解也就在所难免。冯友兰在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中提出了名家内部存在看“离”、“合”两派,并认为惠施属于“合同异”派的代表,公孙龙属于“离坚白”派的代表。这一结论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而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误读。公孙龙的《坚白论》虽然主张“离坚白”,但是他在《通变论》中对“羊合牛非马,牛合羊非鸡”及其“与马以鸡,宁马”等分析之辞,其实涉及的是不同层面上的“合同异”问题。我认为,说公孙龙既讲“合同异”也讲“离坚白”并不矛盾;所谓矛盾,是因为硬性把这两个命题按上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帽子而造成的。冯友兰等大家不仅给公孙龙按上了绝对主义的帽子,还将“木贼金”这类本来无关乎政治的言辞硬性与政治挂钩,认为“这是他对新时代的诅咒”③。
对老子、庄子思想的曲解,也是中哲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近年来,随着地下考古的重要发现以及人们认识角度的逐渐转换,这方面情况有所好转。中国文化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黄河文化,一是长江文化。黄河文化以儒学为轴心,以孔、孟思想为代表;长江文化以道学为轴心,以老、庄思想为代表。儒学主张“相濡以沫”,道家主张“相忘于江湖”。取得了政权的封建统治者,选择“相濡以沫”的儒学为其主流意识是十分自然的。道家受到儒学的压抑长达两千年之久。五四运动以后,一部分倾心于儒学的当代学者仍在“疑古”的名义下否定老子的存在,否定《道德经》的真实性,以至在相当长时间里,关于老子思想的介绍被置于战国中、后期,以确保孔子思想的领先与独尊地位。近年来楚简的出土,表明了战国中期的墓主人就已经收藏有多种版本的《道德经》;《道德经》成书于《论语》之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老子关于世界本源的追究及其履道的体验,充满着哲学的智慧;其“相忘于江湖”的主张,明确表达了群体生存应以个体发展为基础的思想;其关于“小国寡民”的构想,也可以成为我们建构和谐社会的借鉴。而庄周绝云气负青天、鹏飞九万里的豪情逸态,则典型地展示了长江文化的开拓进取精神。在其汪洋恣肆的文字中,蕴涵着丰富的天人至理,决非神秘主义、相对主义等等帽子所能掩盖。“以道观之,物无彼此。”他是站在道的层面上看待世界,是从世间万物中看到了同一的“道”。而后来的佛学正是借助于这条跳板,轻松地登上了中国的文化舞台,丰富了中国哲学。
由于中国传统学术中最富有思辨色彩的这些原创作品及其学派或被淡化、或被曲解,中国哲学的个案研究或被不屑一顾、或被云缠雾绕,合法性危机的出现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
宋代学者朱熹经常告诫学生,做学问要有自己的“地头”,否则是一辈子替别人打工。他说的“地头”,指的就是个案研究。个案研究的首要工作就是细读原著,从细读原著中理解先人的思想。哲学是一种智慧。体悟先人的智慧,需要我们通过深究先人之言体会其意。朱熹讲的“涵咏”,就是对这一种过程的描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我们需要通过对先人原著的“涵咏”,开垦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地头”。农民对土地有深厚情感,是因为那块土地是自己的土地;一个在别人的地头上打工的人,不会对土地产生多少情感。如果对传统中国哲学缺乏情感,也就很难谈得上对传统文化的真正传承与开新,很难找到治21世纪中国哲学的真感觉。是否重视个案研究,不仅关系到能否准确解读和评判传统中国哲学,更在于能否科学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此而言,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情感。
注释:
①全祖望:《鲒琦亭集·外编》。
②③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2册,第168、1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标签:中国哲学史论文; 公孙龙论文; 易经论文; 哲学专业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史论文; 冯友兰论文; 程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