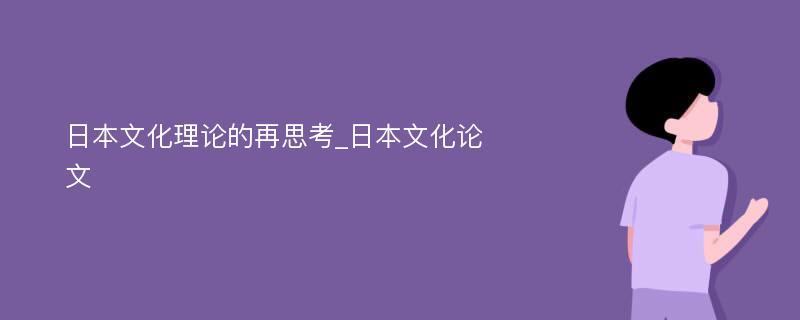
日本文化论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日本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506(2003)11-0001-05
日本文化论又称日本人论,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多次出现的学术争论,并对当时的社会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做为一个集合名词,它指针对来自西方的价值观、思想、实践等而言的、探讨成为日本人意味着什么之类问题的总称。严格地说,它不是某种学术体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某种民众心理,是传统意识对时代需要的折射。因历史条件的不同,每一时期的日本文化论的基调也很不一样。本文主要论述二战后的数次日本文化论及主要观点,以揭示战后日本文化论的特点和走向。
一、战后日本文化论的兴起
美国日本学家戴尔(Peter Dale,1986)曾做过统计:在1946年至1978年的近30年约有700部日本人论的书出版,其中25%是在最近的3年间,即1976年至1978年出版的。通过对有关日本人论出版物内容的分析,他还发现,这些书大多有3个核心命题或动机:第一,作者们明确主张日本人指文化上、社会上单一的种族存在,日本人的本质在史前时代就已形成,自此至今,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二,他们认为日本人的基本特性明显地区别于其他所有已知的民族;第三,这些著述常常充满了有意识的民族主义色彩,表露出对一切出自非日本的分析模式、概念和方法论的敌意。
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日本文化论会如此兴盛?这与同一时期的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抬头有关。三吉正男(1989年)指出:二战后不久,日本人的政治、经济都被西方人设计,他们把日本改造成反共桥头堡,让日本人在经济上追赶西方,却又教给日本人需要保持“战争赎罪意识”,禁止公开地表达民族主义情绪。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后,日本迎来了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繁荣时期。取得了经济上、政治上的成功,民族自信空前高涨。随着日本日益成为全球性竞争者,加之“日本冲击”在海外所向披靡,“日本优越论”的意识在国内赢得了相当广泛的喝彩。此外,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西方国家兴起了对西方在历史上处理国际事务时的道德正当性和政治公正性的质疑,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和反主流主义骚乱,西方文化的合法性受到重大挑战,这些都为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提供了国际支持力量。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在经济上的成功,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在日本国内也掀起了对日本文化和传统精神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关心。一些学者将日本战后的复兴理解成日本独特的生态环境、民族精神、社会结构等的产物,出现了新的“传统文化热”和“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这些人中以一批京都大学的资深教授为代表,如梅原猛、上山春平、今西锦司、梅棹忠夫等。在他们的提议下,由日本政府赞助,成立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所。相对于战前京都大学以著名哲学家西田几多郎为首的“京都学派”,他们被称为“新京都学派”。
梅原猛(1925-),早年受到西田哲学的影响,但后来产生怀疑,特别是西田哲学中对人生的绝望、不安情绪,尤其令他不能满意。他试图创立新的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不同于西田哲学、实存哲学,是鼓励生、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生哲学。在探讨人生哲学问题时,梅原猛全面考察了欧洲文明及其哲学,看到了欧洲文明的弊端是忽视对生死问题的关心,而以日本文化为主的东方文明则对这一问题有深刻的分析,提供了许多思想资源。以后,他开始转向研究日本文化,提出了独特的日本文化论。
他认为:日本文化的精髓是美感与宗教。前者表现在日本的文学、艺术和生活方式中;后者体现在日本人的情感、判断和行为态度中。据此,他批评了许多日本文化的研究者,如和辻哲郎、铃木大拙等。在《地狱的思想》一书中,他展开了关于日本文化的研究视野。他认为:日本思想有3个构成原理,即生命的思想、心的思想和地狱的思想。这3种思想源流都与日本传统宗教有关,是神道、佛教在不同历史时期给日本人带来的启示和教诲。到了镰仓时代,3个思想源流合一,日本文化定型下来。
以后,他又考察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他提出这两种文化是异质的:前者是“和”的文明,强调慈悲与平静;后者却是“力”的文明,主张攻击和报复。历史的发展表明,西方文明在今天出现了许多困境,造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东方文明则将有助于缓解这些矛盾。人类应向东方文明借鉴智慧。
上山春平(1921-)提出了“深层文化论”。他认为日本文化是由多层文化积淀而成的。最表层的,即现在的人们所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化了的、欧洲化了的“大众文化”、“现代文化”。这是近一百年来,特别是二战后的变革所带来的结果。潜存于这些表层文化之下的是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农业社会的文化,这在日本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最深层的则是日本土著的原初民所创造的绳文时代的狩猎采集文化。如此层层剖析、挖掘日本文化的深层结构又是为了说明什么呢?上山认为:这是为了让日本人确立起日本人的立场,更好地思考“人应当怎样生活?”这样的问题,并进一步地从日本人的视角出发做出“我们日本人今天应当怎样生活”的选择。
上山还考察了人类文明史的问题。他把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分成自然社会时代和文明社会时代。文明社会时代又包括第一次文明时代(农业社会时代)和第二次文明时代(工业社会时代)。日本文明在这样的历史中,先后吸收了中国和欧洲的文明形式,但从根本上说,中国文明才是日本文化的母体,因此,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日本人要学会从东方文化或日本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据。
政界人士,或者说不少政治家们也不甘寂寞,加入到“日本文化论”的大合唱中。日本前首相中曾根曾宣布日本已经在经济、智力上赢得了西方,他断言,除了日本,“没有一个民族向他的人民培养了一种信念,……也没有一个民族把丰富的信念精确地传达给他的人民”。另一位前首相大平正芳在1979年发起了“文化时代”的计划,力图对“日本文化特殊性”做出全新解释,并建立一个真正的“具有理解力的日本文化”。
随着日本向海外扩张,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与许多国家产生了贸易摩擦,另外对亚洲劳动者流入的拒绝和对国际事务的冷漠、消极态度,都引起了人们的反感;首先从海外出现了对日本文化、日本精神的批判倾向。澳大利亚的日本学学者彼特·德鲁于1986年出版了《日本独特性的神话》,对日本文化做了全面、甚至可以说偏激的批判。虽然有日本人对这样的批评持情绪化态度,但多数日本人冷静地接受了这些批评。之后,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和日本国内民主势力的要求下,日本的对外政策开始向明朗、积极的方向转化,力图使日本文化在国际化中占据一席之地。
二、日本文化论的课题
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日本文化论,主要是以西欧近代社会为基点而展开的,而这之后,探求日本独特性的倾向日益加强。为数不少的日本学者将“日本社会”、“日本人”理解成特殊性的概念,即日本人(或日本社会)的性格特征就是日本人固有的传统特征,难以成为与外国人进行比较的指标,也不可能为日本人之外的民族所真正理解。因为他们相信,基于A不同于B这一认识,A和B是异质的,肯定就是完全不同的,就好比烟与钢笔不同一样。
日本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南博监编了一套《日本人论》(大空社,1996年)丛书。这一系列丛书揽括了明治24年至昭和19年各种有关日本文化论问题的40册书,其中包括:《日本风俗改良论》(土肥正孝,明治24年)、《日本人》(芳贺矢一,明治45年)、《日本国民性的研究》(野田义夫,大正3年)、《日本民族性概论》(佐藤正,大正10年)、《日本的言行》(大川周明,昭和5年)、《论日本人的伟大》(中山忠直,昭和6年)。在全书的“序言”中,南博写道:“与所有的国家相比,象日本这样,热心于本国国民性问题,并用学术研究、评论、随笔等各种形式出版、发行大量此方面的读物,是没有的。通读全卷书后可知,在明治时代的日本人的心理中,维新后初期所抱有的对西方先进各国的劣等感、与此相反的优越感、赢得了日清、日俄战争胜利而产生的列强意识,三种情
绪是复杂地交错在一起的。”
日本文化论常常以多种形式出现,如日本国民性论、日本人论、日本社会论等,它们都属日本文化论的子课题,但侧重各不相同。
对有关日本人论的著述加以分类、抽象和整理可知,日本人论又包含了如下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第一,地域性的问题。在农村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中,众所周知的东北日本和西南日本等的分类就是一例。这类讨论是对日本人、日本文化的细致研究,属局部性研究,这类研究的成果大多对统一的“日本文化”持慎重态度。因为他们认为:即便说是日本或日本人,也很难简单地用一个方面来概括。不过,如今的人口流动、都市化、国际化、情报化等又使它们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地域性的确切区分变得越来越困难,这类研究也逐渐失去了重要性,变得稀少起来。第二,属性的问题。日本人中仍然存在男女、职业、学历、世代等方面的明显差别。这类研究主要采取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的视角,大多倾向于揭示社会问题,保持客观、中立的研究态度,对日本人、日本社会或日本文化持有距离的审视。第三,立场的问题。这类研究就是人们通常说到的“日本文化论”,它们大多立足于宏观判断,强调直观感受和个体的经验事实,主观随意性较强。日本文化论主要是有关国民性、社会性性格等的理论,但是,在具体论述时,就有传统式立场和现代式立场的差别;此外,日本人所提出的日本人论和外国人所阐述的日本人论之差别也经常被夸大。
在大量的日本文化论的争论中,描述日本人的社会性格以及构成其核心的社会态度的关键词有很多,不同的研究者会从各自的角度设置完全相异的关键词。我们将众多的关键词加以分类,划分为以下5种:第一类是指出日本文化具有容许矛盾两个方面并存的宽容。具体表现为:二重结构、两重性、多重的多样性、真心话与表面原则、执著与绝望、义理与人情等,对立的两极矛盾互不影响地杂糅在一起的宽容。第二类是强调日本文化特点在于:柔软的、调和的平衡感。如调和、相对主义、柔软性、境遇主义、和、方便主义、暧昧、随大流、通融、平衡感、没有逻辑的逻辑、以并非固定的判断标准判断事物的社会态度。第三类是肯定日本文化的真谛在于相对的、但又细致的界限,包括界限、区分、微妙、以心传心、留心、用心、没办法等强调与世间他人的关系的态度。第四类指出日本文化属情绪化的体系,包括从诚、真心中寻找正面的力量以及各种“气”所包含的上进心、求道心,具体地有溺爱、耻辱、感性、情绪、感受性、物哀、寂寥、风雅、幽玄、不做作、一期一会、诚等。还有人指出:“气”是日本文化最独到之处。“气”原指元气,本意是一种生命的能源。气的基础是诚、真心、正直、本性、好奇心等正面的力量,所以还有干劲、愿望、士气等意思。“注意”(气がつく)是点,“用心”(气がきく)是线,“留心”(气がまわる)是平面,“关心”(气がくばり)则是立体。第五类指包含新生意识的时间感,如禊、“对不起”、对大自然的敬畏、再生观、新
生观等。这些都体现了对时间的感觉,日本人的社会生活中就有很多象征,如:七五三
节表示从幼儿过渡到了儿童;成人式表明从儿童成为了青年,结婚式则是从青年到成年
三、几个有代表性的立场
穴田义孝在《日本人论的再思考》(载于《日本社会论的再思考》)一文中,对近30年来的日本人论的讨论做了回顾。他认为:日本人论是以日本人的国民性或者说日本人的社会性性格为主展开的讨论。社会性性格指构成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成员间共通的、一致的行动倾向。下面对日本文化论中若干有代表性、且赢得了较多赞同的观点进行评述。
1.日本社会的自我论和主体性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在传统社会中,日本是缺乏自我观和主体意识的。在有关日本文化论中,不少日本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有人提出,日本社会缺乏自我观源于日本社会中的每个个体自我意识不足,培养有自我意识的个体正是日本眼下应努力推进的事业。樋口清之在《柔软的日本人》中说:没有理念、缺乏意识形态、做为成人的主体性不足、没有市民革命的经验、农耕民的性格、国际化意识不足、自我矛盾等否定性的关键词,都表明了在日本人中确实有避免依据某一特定标准明确做出判断或结论的倾向,即主体意识和自我观念不甚明朗。
也有学者不赞同这样的观点,他们提出:社会的自我本身具有民族、文化的差异,没有与西方一样的“自我”并不等于说日本社会没有“自我”。如穴田义孝认为:依据W·詹姆士、G·H·密顿的观点,社会自我是与主体性概念紧密相连的。客我me是由自我I促成的,自我I带来了个人行动的独立性和社会变革,由此形成了社会适应、维持社会秩序之根源的客我。因此没有截然分开的主我与客我,“主体性”是一切独立存在的人及文化所共同的。穴田又进一步提出:真的主体性是Ego,在自己主张的I中有I的主体性(绝对的主体性),在调整社会关系的me中,也有me的主体性(相对的主体性)。主体性存在于社会性性格的底层,是做出判断的主体。如在社会中存在做为共通感觉的习俗规范,习俗规范通过教养或者模仿而被人们遵守,社会性性格的本质完全不发生变化是不可能的,但它又是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当需要调整时,做出调整和如何调整这类判断的是构成社会的成员们,他们就成为了判断主体。在日本社会中,Me的比重强于I,它表现出无论如何重视社会要求的行动倾向,都会使自己I的主张受到压抑。但在I的主体性中又包含了任性的个性和不顾及他人的可能。这是日本人最本质的行动倾向。这没有价值观上的好坏之分,而只是日本人的智慧,我们应善待之。
森冈清美提出了变质(transmutation)和变形(transformation)的概念。变质就是本质发生了改变的概念,变形则指形式、外观发生了变化,本质却未必改变的概念。他认为:在日本历史上思想或社会结构等所经历的主要是变形,因此构成日本社会内核的因素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并被保存下来。
2.日本人的“间人主义”
浜口惠俊于1977年发表了《‘日本人式的’再发现》一文。根据浜口的主张,日本人的人性观,与东亚人相通,却与西方人差别甚大。日本人表达“人”的词,是“人间”,这个词还可以指“人类”,即“间人主义”,强调的是“一个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它具有这样的特点:它提倡相互依存、相互信赖,主张与人关系才是人的本质特征。“间人主义”是日本人的行动样式之普遍准则。
间人主义又可以称作“集团主义”,它表现为连带的自肃、自省意识,而非个体内省的自律感。具有连带自省意识的日本人,强调对他人,特别是相关者,如家庭成员、公司中的同事、村庄中的邻人等的利益与感受的顾及,深刻意识到自己与他们的相关性。日本人之所以成功地运营了近代资本主义,就在于日本人能够依据自身所在的系统的关联性渐渐地提高到对社会序列的认可、接受范围更大的社会组织的人际关系和经营功能上更为可取的生活方式,从而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的现代转型。
但有批评者指出,浜口的观点包含了如下问题:第一,他假设日本人的行为态度是个别-情境主义的,即认为日本人大多采取依照特殊状况而行动的态度,但日本人又是如何结成稳定、长期的集团关系,如企业集团、村社集团的呢?日本人在集团内的固定性行为与他的情境主义态度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第二,浜口认为:“间人主义”是东方人的一般特征,在这一点上,日本人与他的近邻保持了高度一致性,那么,做为东方人的一般特征的“间人主义”与日本人的“间人主义”是同一的吗?如果是一致的,“日本人式的”原理就不存在;如果不一致,日本人的独特性又在什么地方?
笔者认为:尽管浜口未对此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但是,日本人与其他东方民族所理解的“间人”还是有明显差别的,日本人的间人主义是“关系优先型”的,在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如中国、朝鲜等则主张存在某些普遍性的规范,这些规范优于人际间关系,是人所必须遵守的。
3.认真的日本人
千石保于1991年写了《“认真”瓦解了》一书。他在书中提到,以1977年为界,日本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从工作优先转向闲暇优先,从勤奋努力转向喜爱游乐,从认真的态度转向马马乎乎的态度。人们不再为了实现某一目的或目标而加油拼命,仅仅行动或活着本身就有了意义,不同以往的新价值观形成了。
他在书中援引了许多社会调查、民意测验等数据。如在最近的有关新员工的工作目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年轻人在这方面的新表现。在新员工中,持有牺牲自己为企业而奋斗意识的人几乎没有,他们的工作目的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工作是实现快乐生活的手段。
千保石分析道:支配日本人行动的内在动力源于“理想”这样的目的意识和“欲求”这样的本能基础。“理想”激发了日本人执著、认真的工作态度;“欲求”使日本人不断产生了摆脱困境、不安的工作动力。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认真态度的瓦解,理想也丧失了,欲求不再与欠缺、不满足相联系,而变成日常生活观念,想体会一种不同于他人的、有生机的“快乐”、“忠实于自己而活着”的愿望变得强烈起来。
此外,千石保还指出:在一些年轻的日本人中,“不能不这样”、“必须如此做”的绝对价值观崩溃了,“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的相对主义思考方式非常盛行。各人追求新的观念,信奉以原则为对立面、任意地行动式的“不知约束者”的哲学。但这很危险,因为无论什么社会,如果没有“原则”之类的绝对理念,就不会有进步。
4.心情主义
日本著名思想家相良亨在《传统伦理观的基调》一文中提出:日本人的传统伦理观的基调是重视心情的纯粹性。如果追溯日本人对伦理的自觉方式,就可以看出,把伦理做为客观的法则而加以追求的态度在日本并没有获得成熟发展,也没有构成日本人伦理观的基本内容。日本人在伦理方面的努力表现为求得主观的心情之纯粹性,这一倾向非常明显。而且,日本人所孜孜以求的,不是针对表现为客观法则的伦理的心情纯粹性,而是撇开一切理论化、抽象化的心情纯粹性本身。
相良亨主张,日本人的祖先最初所理解的伦理,就文献可知的方面看,是记纪和宣命等中体现出来的清明心。清就是指能看透水底般清澈的感觉;明就是源于太阳、没有云彩、一望无际般明亮的感觉。古代日本人用这样的感官式的形容来理解人所应有的心情状态。因此,就像清流一样,向世人袒露出内心的底端;就像太阳的光芒没有云彩遮挡一样,看出他人的真心。换言之,透彻的清明心就是没有私,(注:日语中“私”既可以做“我”讲,也可以做“私心”来理解。)在与他人相关联的场合,清明心本身就成为古代日本人的伦理自觉的表现形式。
在近世,强调诚、诚实,尊重心情的纯粹性,强调丝毫也不能有混浊之意的态度,这样的思考方式又发展出知耻的思考方式,不纯的心、邪念会产生不正的行为,这是最为可耻的事。以武士道为代表,这种知耻的思考方式传布到其他各阶层的人中。伊藤仁斋、吉田松阴等人都强调“诚”,这对明治维新志士们来说,“诚”是最大的行动原理。
在吸收外来文化时,日本人也是以自己的方式加以取舍。日本人引进了儒学、佛教,但在基本伦理学观点上仍然主张主观的心情主义。外来思想所提倡的伦理学观点大多基于道或道理等观念。在中世,日本人也有行为应遵循客观道理之类的东西,但是,这些道理可以理解为实际上就是先使主观的心情变得无私之后,才能表现为此时此地应遵循的道理。所以,道理的问题就成为具体地对道理的感觉的问题,又还原成了心情的存在方式。总之,日本人强调的是与这些道理或道相吻合的、有生机的心情存在方式。这一点又被不少日本人理解为“正直”。正直指以应当的态度,对面临的事件、事情所具有的是非善恶进行直观的觉悟。正直不只是知性的直观或情的感受,它还包含了利用当下感受到的心境进行行动的能力。正直有时又可以叫“朴素”。重视心情的纯粹性这一倾向,导致了日本人重视人伦关系、力求在人伦关系中与他人达成心情融合的行为方式。
尾渡达雄在《伦理学与道德教育》(以文社,1989年)一书中也指出: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表现为心情主义。心情主义就是去掉私心,在自己与他人之间自然而然地达到沟通,人与人之间实现整体的融合。心情主义在古代,表现为“清明心”,主张与美丽的自然融为一体,在自然中获得生机,富有朝气地生活着。“清明心”是古代日本人视为理想的追求,其原初意义理解为“正直的心”。“清明”(或者说“光亮”)的反对面是“阴暗”、“污秽”(黑、浊、邪),这些又被视为“罪”,妨碍构成自然美的生命力之作物的病害、虫等也被视为罪。肮脏本身就是恶意,洁净本身就是善心。但恶、罪与善、净不同,指外在、附着上去的东西,它是非本原性的,因此,罪或恶主要不是内心或动机的问题,它们都可以通过禊或祓得到清除。
然而,心情主义也有缺陷。它容易陷入非逻辑、非客观的境地。如果主观上要做恶,就会产生自以为是的心理满足,即便出于纯粹的动机,是当事人以真心而行动的行为,但从行为的手段、方法及结果来看,仍然不能被接受。心情主义直接导致这样的简便思想:只要动机善,一切都可以被允许,结果怎样都不重要,日本社会中的溺爱思想(甘え的思想)、至诚可以感动天的动机论都是这类观念的产物。所以,所有民族的文化,都既有长处,也有短处,长处与短处是内在相关的,互为一体的。如果要舍弃其短处,恐怕长处也会被扼杀。在长处、短处互为一体的关系中,形成了每个民族的个性。日本人应当客观地反省和理解包含了长短两方面内容的民族个性。
收稿日期:2003-0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