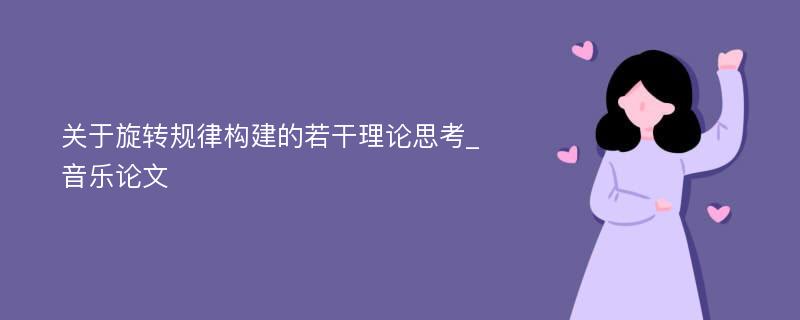
旋律学建设的一些理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旋律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J614.6
一、“旋律”的概念及其构成因素
现代汉语中的“旋律”是个外来词汇,对应于英文中的"melody"。英文melody是指曲调。该词源于古希腊语中由“诗律”与“歌曲”合并而成的一个词——melos,"melos"在中世纪拉丁文中写作"melodia",英文melody即由melodia演变而来。
作为一般概念,“旋律”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声音经过艺术构思而形成的有组织、有节奏的和谐运动。”
作为音乐术语,“旋律”是“曲调”的同义词。“曲调”在《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的解释是:“建立在一定的调式和节拍的基础上,按一定的音高、时值和音量构成的、具有逻辑因素的单声部进行。亦称旋律。……”
该定义将旋律规定为“单声部进行”,显然是为了和多声部的复调与和声相区别。但是应该明确:在复调与和声的多声部进行中,旋律同样是其中的主导因素。复调音乐是多个旋律声部的同时进行;主调音乐的和声正是为加强、衬托主旋律而存在的。
人们在给旋律下定义时一般都注意到构成旋律的两个基本要素:即曲调线和节奏。所谓“曲调线”,实际上就是不同音高的一组音相继出现而形成的音高起伏感。所谓“节奏”,实际上就是声音按不同时值和强弱相继出现而组成的节拍感和律动感。毫无疑问,曲调线和节奏是构成旋律的两种要素,但是,二者哪种更重要?或者是否缺一不可呢?恩斯特·托赫在《旋律学》一书中,虽然也肯定了“音高和节奏对旋律构成来说是同样重要的”,但他还是强调了其中节奏的重要性,说道:
音高线是苍白如蜡的图象,节奏使它有了生命,节奏使它有了灵魂。……一条旋律,如果没有节奏就很难或者根本不能成为旋律,相反,经验说明,单单节奏在许多情况下就能足以成为旋律。当我在桌子上尽可能精确地敲击出下列节奏时:(谱例略)人们会很容易地感觉到其中蕴藏着的旋律。由此可知,节奏是旋律的灵魂。(注:恩斯特·托赫:《旋律学》,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0页。)
《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在给“旋律”下定义时也注意到节奏的独立意义,认为:
在某些民族文化中,节奏因素可能总是优于旋律的表现,如非洲部分地区常用无固定音高的打击乐音响来充当语义通讯或指挥习俗性的身体运动(包括日常工作的某些动作或仪式舞蹈)。(注: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volum 12,p.118-melody)
的确如此,节奏必然伴随着一定的音响而存在。仅仅由打击乐器奏出的的节奏音响,虽然没有通常所说的“乐音”的固定音高,但不能否认它有“噪音”的固定音高。而且,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创作的纯打击乐的音乐,一般都是由多种打击乐器组合演奏的能够产生不同音高和音色感觉的节奏音响。其中除了节奏因素外,同时也产生音高起伏感,这和由乐音构成的音高起伏感没有本质的区别。无论从声学物理现象或从不同民族的传统听觉习惯来衡量,乐音和噪音之间本来就是一个相对值和相对概念。既然如此,纯打击乐器的音乐是否也应该被纳入“旋律”的范围,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新问题。
旋律的变化是无限的,但旋律的构成并不是无序的,而是在一定的秩序中表现着无限的变化和无穷的美感。曲式就是旋律发展的一种秩序,一种结构形式。正如语言的表述有字词、句子、段落、篇章一样,旋律的表达不可能浑然一片,也必须有自身的结构形式,有乐节、乐句、乐段、乐章等不同的结构层次。无论是一支简单的民歌曲调,或是一首复杂的奏鸣曲旋律,都有各自的曲式结构。可以说,曲式是旋律进行中将音调和节奏组织成有序形式的结构框架。因此,曲式无疑也是构成旋律的重要因素。
曲调线、节奏、曲式是旋律构成因素中能被直接感觉到的因素,此外还有音色、音量、速度和音乐的体裁形式(如声乐、器乐、民歌、戏曲、管弦乐)等,也都是能被直接感受到的旋律构成因素。这些直接表现为旋律音响的外在因素,可称之为旋律的“表现因素”。
除了直感的表现因素外,还有一些是不能被直接感受但实际上隐含于旋律之中的内在因素,如:音律、音阶、调高、调式。这些因素虽不易于直接感受和观察,但它们的确是按一定的自然法则或数理逻辑制约着旋律的音体系和音组织,发挥着内在的逻辑作用,所以可称之为旋律的“逻辑因素”。
旋律的“表现因素”和“逻辑因素”均属于音乐型态范畴,是旋律自身的构成因素。然而,作为人类文化现象的旋律,它不可能脱离社会文化环境和人类音乐行为而抽象地存在。同时,每种文化环境都是特定的,每种音乐行为都是具体的;任何一首旋律的产生、传播及其审美效应和社会评价,都与特定的文化和具体的主体密切相关;特定文化及其文化传统既为旋律的产生提供了背景和依托,也规定和约束着主体的音乐行为进而影响和制约着旋的型态样式和艺术手法。《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之所以将“旋律”首先定义为:“根据特定的文化规约(given cultural conventions and constraints),按音乐节奏排列起来的一系列有固定音高的声音。(注: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volum 12,p.118-melody)”说明已经注意到文化环境实际上对旋律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影响、规定和制约。
人类文化都是特定的文化,都是与具体民族具体的生存环境密切关联的具体的文化和传统,不存在抽象的和“一般”的文化。正因为如此,旋律的形成必须受到特定文化的规约;旋律的存在必然依赖于特定的文化;所以,特定文化的特定规约应该作为旋律构成的外部因素看待,它是相对于旋律的音乐“型态”(该词指有型之态)而言的旋律的文化“形态”(该词指无形之态),亦可称之为旋律存在的“文化因素”。这种“文化因素”虽然可能会与构成旋律的“表现因素”和“逻辑因素”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但它们之间的确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因果联系,文化因素不仅为旋律的社会存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同时也像空气和水分一样渗透在旋律型态的自身机制中。
总而言之,“旋律”,就其音乐型态而言,并不是我们抽象出来的只有音高和节奏的一种空洞概念,更不是我们用笔写在纸上的一些音符曲线。而是包含着音高、音色、音量、节奏、速度、结构等直感性“表现因素”和音律、音阶、调高、调式等非直感“逻辑因素”在内的音响的统一体。它包含了除不同音高纵向组合形式(即复调、和声的纵向关系)以外的几乎所有的音乐构成因素。就其文化形态而言,旋律的产生、存在,旋律的类型、样式,旋律的风格特点和美学特征,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群体、特定环境、特定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从而给旋律注入各种外显的和隐含的“文化素”主要体现旋律的技艺特点;旋律的“文化因素”则主要体现旋律的人文特征。这3种因素不可分离,共同构成了一个丰富而复杂的“旋律”概念。
二、旋律研究及其学科归属
“旋律是音乐的灵魂。”人们对这种说法似乎没有什么异议(个别异端学说或极端流派除外)。可是,西洋作曲理论“四大件”中有和声学、对位法、曲式学、配器法,唯独缺少旋律学。旋律的研究能不能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并堂而皇之地走进课堂?这是一个很早就引起人们重视但至今仍有疑虑的问题。
其实,自19世纪以来,西方人在建设作曲理论“四大件”的同时,对旋律的探讨也没有间断过,一些著名音乐理论家如里曼(Riemann,1849~1919)、布斯勒(Busssler,1838~1901)等人,都涉猎了旋律构成的理论问题。仅中国已经翻译出版的此类著作就有:美国音乐理论家盖丘斯(Percy Goetschius,1853~1964)的《曲调作法》、奥地利作曲家恩斯特·托赫(Emst Toch,1887~1964)的《旋律学》(1923年出版,中译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出版)、前苏联音乐学家鲍里斯·阿萨菲耶夫的《音调论》(1947年版,中译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出版)和玛采尔的《论旋律》(1952年版,中译本人民音乐出版社1958年出版)以及匈牙利音乐学家萨波奇·本采(Bence Szabolcsi)的《旋律史》(1950年出版,中译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出版)等。中国音乐院校也编写了不少“歌曲作法”之类的教材。尽管如船从西方到中国的音乐院校中,至今还没有一本可与成熟的“四大件”理论并驾齐驱的旋律学教材问世,作曲技术理论中仍然没有旋律学的一席之地。旋律的创作,依然游离于理论规范之外,基本上是凭借个人感觉的一种经验活动。
既然旋律是音乐的灵魂,为什么西方人不去发展旋律学,却让其它“四大件”抢占了作曲理论阵地,旋律理论反而被挤出圈外?
在寻找其中的原因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对位法、和声学、曲式学、配器法之类的著作和教科书,都是以欧洲17世纪以来复调音乐和主调音乐多声体系为蓝本的作曲技术理论,是对欧洲一段时期内(主要是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专业艺术音乐创作经验的总结和归纳。多声音乐体系创作中需要遵守的声学原理是声部间的纵向关系和谐度问题,于是,复调的对位规则以及和弦的排列、续进原则便成为这一时期创作与理论关注的焦点,从而促进了对位法与和声学理论的形成。此外,随着古典乐派器乐曲式的日益复杂化和管弦乐队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无疑也促进了曲式学和配器法的理论建设。实际上,对位法就是复调的法则化;和声学就是和弦的规则化;曲式学就是结构的程式化。当复调、和声、曲式都被“规范”起来以后,或许由于旋律本身难于“规范”,因此反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所以才没能发展出象样的旋律学来。总之,当人们不再陶醉于辉煌的多声音乐复杂组合而意识到应当重建旋律学时,主调音乐的盛世已过。西方音乐经过古典时期、浪漫时期等阶段跨进了20世纪,从瓦格纳开始,经过德彪西到勋伯格,旋律的观念一直在变化中。旋律不是被复杂的和声淡化就是被绚丽的配器淹没,最后到完全抛弃调性和变为数理游戏。在这种情况下,与主调音乐时期大小调体系相适应的旋律技术理论就只能不成系统地徘徊在“四大件”之外了。
总之,西方人之所以始终没有建立起与“四大件”配套的旋律学,不管是历史的失误还是历史的必然,其中自有原因。今天,当我们回顾历史,重谈旋律学建设时,是不是一定要去填补这个空白,按照已有“四大件”的模式补上这更重要的“第五件”呢?既然西方人自己都没有把“第五件”(旋律学)建立起来,我们步其后尘,是否能成功?即便成功,是否有现实意义?这些都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毫无疑问,现有的西方音乐“四大件”理论存在着地域范围和时间范围的局限性。因为这些理论只是对欧洲一段时期内专业音乐创作实践的总结和归纳,所以它既不适合欧洲早期单声音乐(如古希腊音乐、格里高利圣咏及吟唱诗人、恋诗歌手歌曲等),也不适合20世纪以来的欧洲现代派音乐,更不适合世界其它地区各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这些理论本来并不具有时间上的永恒价值和空间上的普遍意义,也不是全世界音乐创作都必须遵循的“通用语言”。只是由于近百年来西方文化全球化的强势影响,这些理论才被许多非西方国家当作“科学”或“真理”来接受。
其实,“欧洲音乐中心论”早已随着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的发展被西方许多学者自己所否定。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欧洲18世纪以来的专业艺术音乐并不是人类音乐的样板,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音乐,各民族的音乐都有不可取代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
实际上,除了西洋作曲理论之外,非西方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旋律研究或旋律学理论。因为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传统音乐都是单声音乐,在这类音乐中,旋律是音乐思维和音乐表现的主要手段,因而对旋律的研究也就成为民族音乐研究的主要内容。从这种意义上讲,各国各民族传统音乐的型态学研究,其实主要就是旋律的研究。就我国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言,凡涉及到音乐型态本身,无论是民歌、说唱、戏曲、器乐,就必然要对它们的旋律型态进行研究。以往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基本上都属于旋律研究的范畴。
当然,任何一种值得研究的事物都可以成为一个研究领域,但并非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成为一门学科。学科是按照学问的性质划分的门类,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化学;社会科学中的史学、政治经济学;人文学科中的美学、音乐学等。学科划分界限在自然科学中比较清楚,在社会科学,尤其是在人文学科中就比较模糊,这与研究对象本身属性的明确和稳定程度有关,也与学科理论是否具有可验证性有关。除了大的学科划分外,一门学科的内部还以可形成许多不同层次的分支学科,比如音乐学中的音乐史学、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在西方,“音乐理论”(music theory)是“音乐学”(musicology)的分支学科之一,而所谓“和声学”(theory of harmony)、“对位法”(counterpoint)、“曲式学”(formenlehre)、“配器法”(orchestration),则是音乐理论的分支学科。严格地讲,它们都是作曲理论(theory of composition)教学中的“科目”之学,还不能算是自成体系的“学科”之学。这“四大件”的英文名称,也体现了它们只是属于作曲理论的分支科目(英文中独立的学科名称一般是在词尾加"ology"这个后缀)。
大部分学科是按研究对象的范围或对象的性质来划分的;但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相同的对象也会形成不同的学科。如,同样以人类社会文化为对象,但因研究角度、方法、侧重点的不同而形成了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几种不同学科。再如音乐学中的民族音乐学,最初是以研究对象(即欧洲艺术音乐以外的各民族音乐)为特征而形成的学科(早期比较音乐学),后来由于在学科方法论方面的突破,研究对象也随之扩展到人类音乐文化的几乎所有领域,成为“方法论优先”的学科。
旋律是人类音乐文化的一种普遍现象。凡有人类的地方就有音乐,凡有音乐的地方就有旋律。旋律是比复调、和声更为普遍的一种音乐表现形式。旋律因素渗透在音乐的各个方面,研究旋律几乎等于研究音乐的全部内容。试想,如果我们以研究旋律型态为宗旨,就必然会包容音乐型态学(包括传统音乐的乐律学)的对象和内容;如果我们同时还研究旋律的“文化因素”,这又与民族音乐学的观念和方法相重合。假如我们并不想用旋律学来包揽或取代现有的音乐型态学和民族音乐学的话,就必须给旋律学一个比较合理的学科定位,必须对旋律学的目的、对象、方法有个基本的认识。
三、旋律学的目的、对象与方法
旋律学应该是一个“对象优先”的研究领域,一个开放的研究体系。
所谓“对象优先”,是指以研究旋律为前提而形成的一个研究领域。所谓“开放的研究体系”有两种含义:一是研究对象范围的开放性;二是研究方法的开放性。
假如这个提法合理,那么,旋律学的研究范围应该包括: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古今各种音乐的旋律(包括传统音乐、艺术音乐和流行音乐)。(注:目前,西方国家的音乐分类主要有3种,即:古典classical music(名为“古典”,其实包括了从古典乐派一直到现代各个时期各种风格流派的专业艺术音乐)、流行popular music、传统traditionalmusic。近10年来又出现了所谓“世界音乐”world music(传统音乐+流行风格)。)这些对象前人已经在研究并且已有大量成果,旋律学不是要推翻重建,是对以往该研究领域的丰富和发展。
研究方法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多种方法的应用和多学科视角的综合。也就是说,旋律学不仅要为音乐创作总结出一整套系统的旋法规则和应用技巧,更重要的是研究旋律的普遍规律与文化规约下的民族特性,为人们提供一种把握曲调、感受旋律和认识其文化意蕴的方法。
旋律写作,不仅是创作的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创作思维方式;不仅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艺术,一种审美方式和审美习惯。所以,即便是作为作曲技术理论的旋律学,也应该研究旋律与特定文化的关系,在认识这种关系的基础上理解旋律的风格类型和具体的技术手法。
旋律学研究的目的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旋律的结构型态,总结旋法和技艺的规律,重在为作曲实践提供应用技术理论;二是挖掘旋律的文化意蕴,探讨结构与意义的关系,重在揭示人与音乐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也是旋律学发展的两个方向,即:应用理论(前者)和基础理论(后者)。
旋律学研究的对象包括3个领域,即:传统音乐、艺术音乐和流行音乐。
一般讲,传统音乐往往代表着一定的社会特性;艺术音乐和流行音乐总是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特征。对象性质不同,研究目的和方法也不尽相同。就以往研究实践看,因研究对象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理论倾向(或者可称之为旋律学的不同研究方向),如:
作为作曲技术理论的旋律学(如盖丘斯《曲调作法》、托赫《旋律学》及中国音乐院校所用的《歌曲作法》之类教材等),主要是着眼于音乐创作技法的应用理论;
作为传统音乐型态学的旋律学(如众多的民歌曲调研究、民间器乐旋律研究等及其构成旋律的音阶、调式、律制研究等),主要是着眼于音乐型态规律的基础理论;
作为民族音乐学的旋律学(如萨波奇《旋律史》,等),则是一种可以包容音乐型态学、音乐史学、音乐符号学、音乐人类学、音乐民俗学、音乐社会学等各类学科方法的综合性的、开放性体系的人文学科,是着眼于音乐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基础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