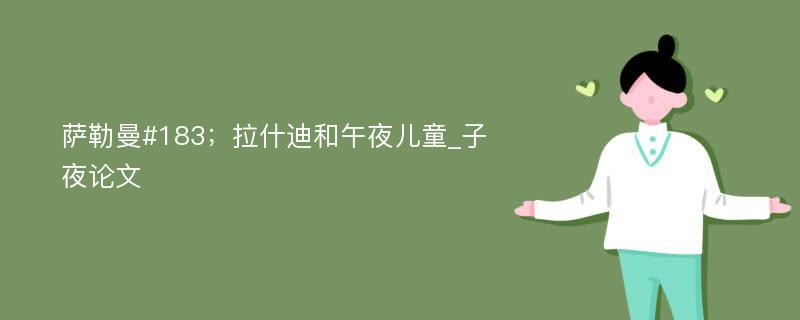
萨尔曼#183;拉什迪与《子夜的孩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子夜论文,萨尔论文,拉什论文,孩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英籍印度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出生于1947年6月,两个月后便是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宣告独立及巴基斯坦宣布自治的好日子,也是他的小说《子夜的孩子》的主人公沙利姆的生辰。和沙利姆一样,拉什迪生长在孟买的一个生活优裕的穆斯林家庭,在教会男子中学接受英式教育,可以说英语和乌尔都语都是他的母语。据他本人回忆,他的童年时代过得平静、快乐,并不象他小说的主人公那样屡经风浪和波折。他的父亲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父母常常向孩子们讲述神话故事和家庭故事。在这样充满故事、充满书籍的家庭环境熏陶下,拉什迪在五岁时就有了当一名作家的愿望。1964年,拉氏全家迁至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定居,不过在此之前萨尔曼已被送往英国的拉各比公学(Rugby School)就学,所以他只是假期里才住在卡拉奇,但不管怎样,巴基斯坦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了他的又一处故乡。
拉各比公学是英国享有盛名的贵族学校之一,著名诗人、评论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父亲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曾任该校校长。此翁竭力推行维多利亚式道德风尚,试图驯服各类“粗野”文化,印度文化自然也在此列。现代的拉各比公学虽已不同于上个世纪,但陈腐的校风仍有遗存。拉什迪在此就读时,常受到些来自同学的种族歧视和小小刁难,这也是他后来不情愿留在英国继续上剑桥大学的原因之一。1965年从拉各比毕业后,他希望在卡拉奇居住下去,当时巴基斯坦和印度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印巴战争的前奏愈演愈烈。在父母的坚持下,拉什迪最终还是同意去剑桥的King's College读书,令他欣慰的是,在大学里他不再受到歧视和刁难了。1965年到1968年间,他在剑桥度过了一段内容丰富、颇具刺激性的生活。那是个政治风云席卷各大校园的年代,连空气里也充斥着文化叛逆,越南战争、学生运动,摇滚乐、吸毒——当时的年轻一代很有一番轰轰烈烈、光怪陆离的经历。拉什迪本人回忆剑桥岁月时说“我很高兴拥有过那个时代,那时的学生生活充满活力”。
1968年,拉什迪获得剑桥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在伦敦一家剧团当了一年演员,因经济上入不敷出,而且自觉表演才能很平庸,所以不久就离开舞台,给一家广告社做起了撰稿人。此后他得以每周工作两、三天以维持生计,其他时间便用于自己的创作。他的处女作小说《拉里默斯》(Grimus)不太成功,出版后售出的册数很少,但在科幻小说界引起了一些注意。第二部小说《子夜的孩子》(Midnight's Children)是他写作生涯中的重大飞跃,这本书的创作历时五年,1981年在美国首先发表后,立刻引来众多的评论,后来又屡次获奖,其中有英国最具声望的布克奖。这本书不仅为拉什迪一举赢得较高的声誉和稳固的作家地位,也给他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迄今它已有十二种语言的译本。此书问世后,拉什迪再也不用写广告谋生了。
《子夜的孩子》发表时,作者已是位英国公民,此书又是用英语写成,尽管它显然是一部关于印度的作品,读者仍然对作者算不算印度作家进行过一番争议。远离故土客居他国的作家在历史上不乏其人,比如约瑟夫·康拉德、T.S.艾略特、詹姆斯·乔伊斯;当今这类作家的人数更越来越多,比如米兰·昆德拉等人。拉什迪可算当代这批“旅外”作家群中的一员,他旅居英伦开始之早、时间之长,尤其是他选择英语进行创作,是一些人不把他看作印度作家的主要原因。姑且不论他算不算一个“纯粹”的印度作家,重要的是,他的生活背景的双重性,给予了他观察事物和创作的特殊角度。《子夜的孩子》虽未使用印度本土语言来创作,但它的语言无疑具有印度特色且与众不同,这也是此书一个重要的成功之处。事实上,自泰戈尔以来就已有过不少优秀的印度作家是用英语创作并获得成功的。拉什迪本人认为,英语是一种富有弹性的语言,已经被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所采用,它比乌尔都语更易于表现二十世纪的生活,它所能展示的一面比任何印度本土语言都更为宽阔。当然,拉什迪的成功并不简单地在于使用了英语,重要的是他特殊的语言风格。他比任何其他印度作家都更善于运用印度英语的结构和语汇使自己作品的笔墨生动、丰厚和独具特色,因而他的小说也不同于“印度——英国”小说的任何一派。就语言而言,《子夜的孩子》对印度生活的描绘是一次创新的尝试,它既在摆脱印度人写印度的模式,也在摆脱英国人写印度的模式,作者也以此在证明:语言并不是固定的,它可以拆散后用不同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
《子夜的孩子》发表两年之后,又一部小说《耻辱》(Shame)问世,这是一部以操纵巴基斯坦政治的两个风云人物为抨击对象的讽刺作品,拉什迪为此而得罪了巴国上层社会的一些人,这本书也因此被禁,但它在英国和美国的出版界得到了不少好评。
作为拉什迪最为突出的作品,《子夜的孩子》和《耻辱》都是以印度次大陆的政治风云为题材的,但拉什迪的写作并不局限于此。他写过不少新闻评论文章批评英国的政治;撒切尔夫人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政策和对来自亚洲、欧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英联邦国家的新移民问题的处理方式,在拉什迪的文章中都受到过抨击。有些人觉得拉什迪的中产阶级出身、所受的贵族化的英式教育、他的英国口音、甚至他的偏白的皮肤——这种种因素都使他无法真正理解和代表第三世界或发达国家贫困阶层的声音。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新闻作品表现出对第三世界地位和生活的真诚的关注。1987年他应邀访问尼加拉瓜,之后发表《美洲虎的微笑》一书,其中表现出对尼加拉瓜民众的真切同情。
尽管《子夜的孩子》被认为是拉什迪最卓越的作品,而1988年发表的小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引起的轰动却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前者所带给他的荣誉。伊斯兰界认为《撒旦诗篇》是对《古兰经》的歪曲和亵渎,世界各国无数伊斯兰教徒纷纷举行示威,声讨并焚毁该书,示威活动中还发生了骚乱并先后导致多人丧生。1989年2月,伊斯兰教的最高领袖霍梅尼颁布了一道对拉什迪处以死刑的命令,拉氏不得不在英国警方保护之下转入地下生活以躲避捉拿。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他向霍梅尼和穆斯林民众作出了公开的书面忏悔,但霍梅尼称,拉氏罪恶之大,对伊斯兰神圣教义和先知穆罕默德的亵渎之深,已使他即便认罪也无法逃脱死刑的惩罚。死列令在霍梅尼去世后仍未收回,拉什迪自此也一直在英国藏身度日,尽管他表示非常希望早日得到重回祖国印度的自由。
拉什迪的创作努力似乎从一开始就常常给自己招致危险。他曾在《子夜的孩子》发表后,因其中某些影射甘地夫人及其家庭的内容而被迫向其致歉;《耻辱》一书直接触怒了巴基斯坦的当政者更不必说;《撒旦诗篇》招来的生命威胁大概是作者本人始料未及的;而他向伊斯兰界作出的忏悔又引起了西方同仁的不解和批评。总之他是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应该说拉什迪是一位富于想象、富有探索精神的作家,他常以多重的或是怀疑的眼光观察和描绘世界,常对权威观察、固定模式提出质疑或直接的批评,这既是他在创作和思维上的贡献,同时也给他的写作道路铺满荆棘。这大概也是一切意欲探索和求新的作家所面临的艰难。
不过,拉什迪在失去公开活动的自由后,并未停止写作。近几年他仍有作品问世,其中有1990年发表的故事集《哈龙和故事海》(Haroun and the Sea of Stories),1991年发表的散文、评论集《想象的故园》(Imaginary Homelands),199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集《东方、西方》(East,West),和1995年发表的《荒野最后的叹息》(The Moor's Last Sigh)。
拉氏有过两次婚姻,均以离婚告终。他有一个名叫扎法的儿子,父子感情笃深,《子夜的孩子》和《哈龙和故事海》都是献给这个孩子的。
2
《子夜的孩子》至今被认为是拉什迪最优秀的小说,它集中而强烈地反射出“后殖民时代”及“后现代主义”时期文学创作对传统的历史观、现实观和创作观的反叛性思考和质疑。小说的主人公沙利姆·希耐(Saleem Sinai)是个既生活于世俗间又具神话色彩的人物。他恰巧出生在1947年8月15日的子夜,也正是印度摆脱英国的长期殖民统治而正式宣告独立的那个时刻。时间的巧合似乎本来就是命运的安排,沙利姆出生的时辰好象注定了他的一生将与独立后的印度的种种变迁息息相关。他个人生活中偶然的经历导致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他本人也不断地从这些关联中寻找意义,寻求自身的价值,以履行历史在他降生时赋予他的某种特殊的责任。不过,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追求,它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疑惑和荒谬感。
如果仅仅通过这本书来了解印度的历史,读者会发现,它完全不是一般意义上对史实的追溯或辨析。与其说它在谈历史,不如说它在表现一种历史观,确切地说,它是在印度独立后种种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对这个民族的特点,对“现实”、“历史”的概念,提出很多促人思考的疑问。沙利姆的回忆将他个人、家庭的经历与印度从被殖民到独立的过渡历史糅合在一起。他既是在回忆更是在展示一种“记忆”的概念,他向听者和读者暗示:记忆的本质并非其“客观性”,现实既是客观的也是想象的,“特点”既是种存在也是种幻觉,历史的主观性比史实更能反映历史的本质。他的回忆被有意地赋予模糊色彩,它喻示着现实和历史本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沙利姆对“意义”,“使命”的追求虽无结局,但他发掘出了人类经历的多重可能性,发现了世界是一个流动的多元体。传统的思维一向是以“真与假”、“正与误”的界限为基本框架的,而这部小说却对这种“真假”、“正误”的关系提出挑战,它将“真实”的与“不真实”的内容相互融合,将框架的中心抛出框架,试图表明“中心”原本并不存在,“标准”终究是一种主观的判定,“真实性”实际上取决于观察与想象。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代表着多元论对经典论(the canon)和中心论的挑战。这是不仅在后殖民时代文学作品中,也是在整个文化思维和文学创作领域中越来越强烈的一种声音。
不难发现,《子夜的孩子》的多处情节采用了常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主人公沙利姆的个人、家庭经历与民族历史间的关联显然是虚幻的,其“可信度”取决于读者的理解方式。“魔幻现实主义”当然不是拉什迪所首创,南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小说《百年孤独》中以这种手法震撼过读者。拉什迪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马尔克斯的影响,但拉氏在自己的作品中利用“魔幻”与现实间的矛盾与融合,独特地构筑起个人的世俗生活与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沙利姆的经历常富于魔幻和荒诞色彩,但这种特征并不使他的故事变得“不可信”,反而赋予他的经历以特殊的喻义。主人公在童年时便发觉自己具有透视他人思想和感情的特异功能,并且可以在自己的头脑中与另外几百名同在印度独立的那个子夜降生的孩子发生和保持联络(这些孩子的身体也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特异功能)。这一神奇的能力使沙利姆的生活由单一的个人经历扩展成丰富的、多层次的群体经历(恰巧,同在子夜降生的孩子的人数正是印度人口的象征性的倍缩)。沙利姆生着一副巨大的鼻子,曾被他的地理老师取笑地称为“印度次大陆”,它虽是外观上的一个缺陷,但它具有嗅觉人间各种气味的功能——不是物理的,而是情感、精神的气味,比如爱、嫉炉、贪婪、羞辱、死亡,等等——,它的主人能用它把整个世界都吸进自己的身体。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我是个吞咽生命的人;要想了解我,仅仅是了解我一个人,你都得把那些整个全吞下去。”
沙利姆与众不同的大脑和鼻子在他和周围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十分神奇的关联,并且把他放到了一个几乎无所不知的特殊位置上。他所经历的不止是一种而是多种生活,他能触摸的不止是一个而是多个灵魂,他的回忆和叙述因而也成了一个庞大的多层面的故事。作为叙述者,沙利姆的视角既是多层面的又是单一的——他的特异功能使他的体验具有多样和多层性,而他对于过去的回忆却不能摆脱叙述的局限,因为叙述本身终究是个人的、世俗的,不可避免地带有偏颇。魔幻+现实使沙利姆的叙述角度既无所不包又不无局限,这一二律背反本身就暗示着世界的多重性和不确定性。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沙利姆有着与生俱来的特殊本领和特殊“使命”,他并不具备改变他所生存的世界的能力。拉什迪笔下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并非要误导读者去相信魔力可用于改变现实,而是要展示一种对现实的反传统的理解:主观的,假想的,并不意味着违背“真实”,它是作为思想的真实而存在的,想象王国的自由和奇异本身就是一种现实。传统的现实观偏重于外部事物和真实性而忽略思想世界的真实。就人类思维而言,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中心可用于判断正与误并给它们贴上标签。历史的内容、民族的特征和形象,在不同的思维中会呈现不同的含义,而每一种诠释都既是真实的也是扭曲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包含着这种“真实”与“扭曲”的辩证统一,不少后殖民主义文学作品采用了这一手法,它并不是简单的幻想游戏,而意味着对以欧洲思维模式为基础的传统现实观的质疑和反叛。《子夜的孩子》有意地使“正常”与“怪异”、“真”与“假”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暗示着“真实”之外还有真实。沙利姆的出生和家庭历史本身就是对“真实”这一传统概念的讽刺。雄心勃勃、执意要为历史尽责的沙利姆并不是希耐家的亲生儿子,真正的儿子是流落街头的席娃。保姆玛丽为复仇而在两个孩子同时降生时将其调换,使他们从此各自在本不属于自己的富贵和贫贱中经历错位的人生。但是沙利姆在希耐家庭里的成长、他与家庭成员的不可分割的感情牵连,使他作为儿子的位置并不因后来错换的被发现而有任何变化,无法否认,他和席娃都是希耐家真正的儿子。实际上,沙利姆和席娃是作为同一个本体的两个方面同时存在的,席娃虽然几乎没有在故事中露过面,但他时刻潜居在沙利姆的意识中并给他以威胁。读者毋需追究他们之中谁更“真实”,因为他们是矛盾统一的一个整体。当沙利姆固执地追求“意义”、“使命”时,为生存而挣扎的席娃则对“理性”、“目标”嗤之以鼻。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简单化、物质化的自我。这一双重自我表现着这样一个喻义:现实不是固定的、单一的,它有多种形态、多个层次,它们之间并无高低、真假的差别,而只是因视角的不同而呈现或隐藏。
《子夜的孩子》的故事情节始终包含着对经典式的中心论、一元论的怀疑和否定,书中每个人的性格和生活都呈多元状态。比如沙利姆与他的另一个自我席娃,比如母亲阿米娜与她先后所嫁的两个丈夫,还有沙利姆与他的六个父亲(他们每个人都给了他某种特别的经历和体验,但他们谁也称不上是他“真正”的父亲)。这种多元状态使每个人的经历都有种流动感和模糊感,甚至每个人的感情也可以象液体一样“漏”到其他人的身体或头脑中去,每一个故事同时也是许多个别的故事。沙利姆用他的大鼻子吸进了无数互相渗透的情感,作为叙述者,他的记忆也象一片永远在流动、永远不能停歇在某个固定形状里的海水。作者正是利用主人公看似纷杂的记忆揭示现实的无形的流动性。现实如同一个多头巨兽,它的多元性才构成它的整体;而“意义”、“真理”并非一开始就存在于某处,它是人的思维和想象所赋予的。世界一方面是多元的、无固定形态的客体,另一方面是永远不能摆脱局限和偏狭的主体。只有主体才给客体以形态,只有思维才给现实以意义。而每个个体的思维又不可能穷尽现实,正如儿时在摇篮里学步的小沙利姆,他一度长时间地睁着双眼,好象要把周围的世界全都吞进去,可他最终还是要明白:“谁也不可能时刻都睁着眼睛面对世界。”一双眼睛所能看到的现实,就如阿当·阿齐兹透过那张穿孔的布单所看到的被分解了的娜西姆。有趣的是,“穿孔的布单”从外祖父阿齐兹起就成了一个家庭传统,或是一种命运。若干年后,阿米娜把她的丈夫分解开来,试试一点一点地爱上他,而妹妹佳米拉隐身在一块绣花的中间穿洞的布单背后,让整个巴基斯坦的歌迷都狂热地爱上了这位他们看不见全貌的歌手。沙利姆苦心寻找的“家庭特点”最终都体现在这块穿孔的布单上,它喻示着:任何个人对现实的理解同时也是对现实的肢解,现实的多元性与认识的偏狭性构成了这个世界最本质的规律。
沙利姆所回忆的个人及家庭的故事始终都与印度独立、巴基斯坦自治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相关连,不过,如果把它当作通俗化的历史指南就会误解这本书的内涵了。稍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沙利姆对历史事件的回忆中有些作者刻意制造的细节错误,他的叙述方式本身就隐含着作者所要表达的喻义。整个故事都是由主人公即叙述者回忆的,因而也受到他的叙述角度的局限,尽管主人公的特异功能使他有多重的经历和丰富的体验,但作为叙述者,他的记忆并不是无所不包、绝对准确的,每个人的记忆都具有选择性,何况,他在叙述时是用语言、文字重新组织和再现记忆的内容,因而他的叙述具有双重的主观性。沙利姆的回忆并不总是遵循时间顺序,过去和现在的事情常常跳跃着出现,有时相互混杂,他自己也常提醒听者帕得玛:他的记忆不一定可靠,因为他正发着烧,他的讲述和写作都是在病床上进行的。他的提醒也在向读者表明,他并不强求读者把他所讲的看作绝对的“真实”。不过,有一点显然是作者希望读者相信的,那就是记忆和叙述的主观性。沙利姆常常对自己叙述中的错误有所意识,但是,在回忆和重述历史时,谁又能做到不犯“错误”呢?什么样的叙述才是“准确无误”的呢?现实的多元性和主体意识的局限性,决定了生活中充满着“不准确”、“不真实”的理解和叙述。历史一旦被写成历史,必定是包含了某些史料而遗漏或摈除了其他。
换言之,历史永远隐藏着未被记录或未被发现的史实,任何人书写的历史都不可能绝对真实和准确。而“失误”既然是记忆所固有的特点,“错误”也就并不意味着不可信。
“正与误”、“真与假”之间的界限的被打破,意味着经典式思维结构中“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受到了冲击。中心论实际上是将多元的现实固定在某个主观的视角,而否认其他视角有同样的合理性,将某种形态强加于本无形态的客体,而否认客体在其他形态下也可以同样真实。在这一意义上,经典式思维最易于扭曲现实的本质。《子夜的孩子》显然是在试图突破这种思维结构,当然,不是通过以另一个中心把原来的中心挤到边缘的位置,而是通过瓦解中心——边缘的关系以及这种概念。“中心”本不存在,对于发生过什么,没有发生过什么,每一副头脑都会有不同于他人的理解,每一双眼睛都会选择所看的事物,这一选择来自主体又服务于主体。对于印度的历史,英国人的诠释只表明英国人的观点,它服务于以英国为中心、以殖民地国家为边缘的帝国主义思维。同样,对于独立后的印度所经历的种种困难、矛盾,印度政府的诠释只反映政府的观点,并不代表所有人对此的理解。不论是印度的还是其他民族的历史,没有哪一种诠释是绝对准确和真实的。有被记录的事件,就必然还有未被记录的事件,对史料的选择取决于选择者的观察和理解角度,“每个人都得以自己的真实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历史”不仅仅是史实,而是一个记忆,选择和叙述史实的过程,它是对“事实”的观察、想象和再造;它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实际上它最大的客观性恰恰在于它的主观性。
“历史”既然是主观的,那么它不可避免地具有偏狭性——《子夜的孩子》用这一观点对政治集权主义提出了对抗。小说对长期操纵印度社会的权威专制不无讽刺:不论是印度的民族文化传统,还是来自外邦的殖民统治,还是独立后的国家政治,都把这个民族束缚在了以某个权威为中心的框架之中,孰黑孰白则完全依据这个中心来确定。拉什迪借主人公和叙述者沙利姆表达了对权威专制的讥讽。“实际所发生的,远不如作者劝导读者去相信的重要”,对历史的每一种解释都有理由劝导他人去相信,而最大的危险在于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而否定其他。既然偏狭和扭曲难以避免,那么就不存在比其他人高明的权威,也不存在固定的真理。拉什迪所表达的这个观念,包含着不仅是对印度的文化和历史,不仅是对帝国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世界观,也是对人类历史观和思维方式的重新思考。经典式的“真假”、“正误”观和“中心”、“边缘”意识,是权威主义的基础,它把人类思维限制在固定的模式中,并且压制着来自“边缘”的声音,而《子夜的孩子》是为打破这个模式、以多元取代“中心”和“边缘”所做的尝试。
拉什迪并不是唯一的或最早的尝试冲破经典论束缚的作家。一个世纪以前,康拉德在他的小说《黑暗的中心》里率先对以欧洲特别是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观提出了怀疑,只是康拉德本人未能体验被殖民民族文化的价值,他的小说也未能走出欧洲中心主义思维的限制。一百年来,世界的变迁,前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和崛起,带来了文化意识的更新和欧洲中心论的瓦解,当代作家的思维比康拉德的时代拥有更广阔的自由空间。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学创作纷纷突破传统的思想禁锢,力求对民族文化和历史达到重新表现和重新理解,《子夜的孩子》以其丰富的历史想象和细微的洞察成为其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不过,简单地称拉什迪为“后殖民主义”作家似乎不足以概括他的作品的内涵,他所追求的远不止是对殖民主义的反叛,他所怀疑和批评的经典式思维模式,并不是欧洲中心主义所特有的;他不仅在《子夜的孩子》中直接讽刺印度政治所表现出的权威主义,他的另一部小说《撒旦诗篇》所掀起的风波也表明印度的宗教文化同样也有一个唯我独尊的“中心”。实际上,这个“中心”存在于任何文化之中,它长期地保护、滋养着权威意识,限制着人们思考、想象和表达的自由。打破它的限制,已成为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化思维的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拉什迪的创作是超越了民族界限的,它反映着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