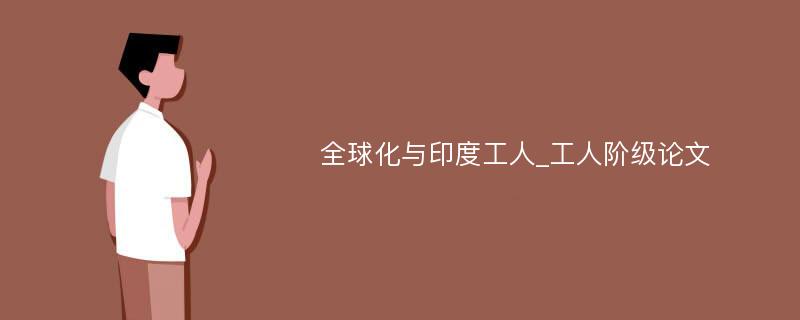
全球化与印度的工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化与论文,工人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8)04-0114-08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全球化进程,尤其是苏联的解体,曾经熄灭了学术界对劳工的研究兴趣。然而,21世纪以来,人们愈益发现全球化给工人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而工人对此作出的反应也不同以往,所以国际学术界对劳工的研究进入第二次热潮①。本文以印度工人②为例,分析全球化给印度工人带来的影响以及印度工人对此做出的回应。
工人身份的多样化及面临的挑战
以往提起工人,人们想到的是那些工作在现代工厂,活跃在工会,以男性为主体的赚工资的有组织的工人。自由化、全球化以来,印度工人的身份多样化起来,主要存在三组相对的工人群体:有组织与无组织的工人,知识工人与物质工人,主体工人和边缘工人。
第一,有组织与无组织的工人。有组织的工人是指在有组织的正规部门工作,有固定的工资收入,能够享受到国家的社会保障和劳动力法的保护。这是一对沿用已久的概念。根据牛津大学印度经济的研究专家芭芭拉的调查,在印度3.9亿的劳动力队伍中,有7%的人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有组织的工人,被称为“工人贵族”,其余的劳动力,大约占劳动力队伍的83%到93%从事“无组织的”或“非正式的”经济工作。如此巨大的差距,从根本上讲,是因为整个印度经济都是“无组织的”。首先,印度的劳动力法和类似的国际规章制度不仅少得可怜,而且根本得不到实施。“在印度,即使正规部门的工人也能够被随意解雇”③,原因在于他们都被置于随便的契约里。其次,一些部门行业,如矿场和码头,本身就介于有组织与无组织之间。最后,即使一个有组织的公司,包括公营公司,也存在很多无组织的劳动力,其比例在40%和85%之间④。
全球化给这一组概念中的工人群体带来的变化就是:有组织的工人数目日益减少,而无组织的工人数目日益增加。相对来讲,就是:有组织部门的就业急剧下跌,无组织部门的就业率上升。从1977-1978年到1993-1994年,印度经济年均增长5%,人口增长2.2%,印度官方宣称公营部门的就业增长率是2.2%,无组织部门的就业增长率为2.6%。但,芭芭拉的研究证明,有组织部门的就业增长率只有0.1%。从1977年到1994年,有组织部门解散了其一半的劳动力;从1990年以来,大约2500万工人失去了工作;从2001年到2003年的两年内制造业部门缩减了70万个工作机会,40万公营部门的工人失业,就业率下降了8%,私营股份公司也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仅纺织业就有40万工人失业。而小企业的生产受到信贷合理性和停滞的国内需求的影响,一直处于不利的境地,其余部门尽管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但对劳动力的需求几乎没有增长。这一现象说明经济增长主要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吸收劳动力最多的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工程与软件业。而且,即使大肆宣传的新经济——IT业,在2002年也大幅度缩减了1万个工作机会。
第二,知识工人与物质工人。这是印度工人群体在自由化、全球化时代的最新分化。知识工人是指阳光产业中的工人,后者指为阳光产业服务的“阴影地带”里的物质工人。就印度而言,知识工人主要是软件组织中的程序设计者、分析者和管理者,从事软件的设计、发展、试验和完成。他们的“思想是全球性的,行动是地方性的”⑤。现在,印度大约有171100工人就业在外购中心⑥。大部分知识工人来自城市、公立学校、受过教育的中上层家庭,而且大多数人的父/母有稳定的工作。他们自身是年轻的、会讲英语的、综合能力高的大学毕业生,平均年龄为25岁;就优越的工作环境和较高的薪水来说,其工作的性质是“高级的”,53%的被调查者月工资超过1万卢比,19%的工资收入在8千—1万卢比之间,相当于制造业或服务业中有资历的个人的工资收入⑦。
知识工人的高收入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面临着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更加严峻的挑战。“与那些能力与成绩更多以物质为基础的工人相比,许多知识工人必须更加努力地挣扎,以取得成就、求得生存和自我身份的渐进转变。”⑧因为,在印度,知识经济的话语代表着这样一种经济:允许公司自由雇用和解雇工人,禁止IT业工会的存在,随意修改契约劳动力法从而有利于弹性的就业。所以,高额的淘汰率和竞争性,日益强化的工作压力和严格控制的工作制度,等等,这些另类的挑战是他们单独面对的。
至于知识工人四周的传统工人,他们的境遇非常低劣。一份专门研究印度的国际化都市班加罗尔的报告充分证明了这一点⑨。班加罗尔市700万人口,其中一半人口是为班加罗尔的扩张而提供服务的工人和其他团体,他们居住在700多个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的贫民窟里。拥挤不堪的马路上垃圾成堆,交通事故频繁发生,平时的积水臭气熏天,雨季到来的时候经常被淹没。在政府的城市发展计划中,这些地方被称之为“阴影地带。“绝大多数的小公司和商业,尽管提供了80%的就业机会,但却生活和工作在‘阴影地带’,缺乏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和服务。相比之下,高科技地带却得到政府提供补贴的高级基础设施、服务和土地。”据统计,班加罗尔的基础设施投资与软件公司集中带的投资相比,数据之比为1∶40,如果与高速公路和高级服务等相关投资相比,比率是1∶60。
生活在“阴影地带”里的物质工人的境遇得到一些民权和环境团体的关注。在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压力下,邦政府决定解决这一问题,然而,这一切都是姗姗来迟。邦政府推出了很多高科技发展计划,一直制定到2015年,然而,没有一个计划涉及“阴影地带”,甚至在主要的GDP备忘录里也没有提及。
与所有的工人群体相比,知识工人是全国挣工资和薪水的人群中组织最好的部分。他们主要以服务业为范围联合起来,相当积极地追求他们的目标。然而,他们远远脱离于制造业部门的蓝领工人的工会和联合会,对全国工运的加强也没有做出很多的贡献⑩。因此,很多印度学者认为,如果利用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推进改革进程的话,那只会加重印度“经济改革”的不平等的效果(11)。
第三,主体工人和边际工。边际工是一个较新的工人概念,是相对于主体工人而言的,即为主体工人服务的零散的个体边际工。根据2001的统计,工人的总数为4.0251亿,主体工人有3.1317亿,边际工为0.8934亿,1991年的统计数字相应的分别为3.1413亿、2.8593亿、0.2820亿,相应的年度增长率分别为2.51%、0.91%、12.22%(12)。可以看出,全球化之后,随着病态国营企业的关闭和就业率的降低,公营经济在印度混合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大规模的产业部门的主体工人增长缓慢以至停滞,而零散的个体边际工人数却急剧增加,所以,全球化后,印度劳动力队伍的增加主要由于边际工人数的增长造成的。作为一个新的工人群体,她们的力量还很弱小,捍卫自身利益的斗争案例很少,集体斗争几乎没有。
工人共同面临的挑战
第一,劳工标准问题。全球化给印度工人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工资下降。那些正式的有组织的部门,不但大量压缩永久性劳动力的人数,而且以契约的形式大幅度降低工人的工资。明显的例证是,印度有组织的部门雇用了不到20%的工业劳动力,给印度带来的却是三分之二的工业增值。然而,1994-1995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无论工人是否组织起工会,与无组织部门的工人相比,有组织部门的工人都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过度剥削”。1994-1995年,有组织部门的工资的总增值率是24.7%;相反,在城市的无组织的制造业部门,是66.1%。就行业来讲,棉纺织业,有工厂的工资增值率是31.6%,无工厂的为82.7%。纺织产品(包括服装)行业的相关数字分别是15%和73.2%,皮革和皮革产品的为21%和63.5%。只有在“资本货的维修”行业,有组织的高于无组织的,分别是64.5%和58.3%(13)。事实上,如果有组织部门的工资收入降低,必然的结果是,无组织部门的工资水平也随着下降。
1997年,印度政府任命了第二届全国劳工委员会来考察现有的劳动力与现有的经济环境和将来的市场需求能够达到多大程度的一致。根据调研结果,政治家和媒体不断地警告国民说,除非劳动力有弹性,否则印度将在国际竞争的战斗中失败。随之,制定劳工标准级别的印度联合制造业部门,竞相把劳动力标准降低到最底端。1998-2004年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政府还试图修改劳动力契约法,以便利于外商降低劳动力的成本。在瓦杰帕伊政府财政部长提出2001-2002年度财政预算报告后,印度共产党、国大党等在野党都指责其是独立以来最残酷的反劳工的预算,是腐朽的和反工人阶级的预算。所以,在2004年大选的时候,工人抛弃了印度人民党。他们认为,“印度在闪耀”不是为工人阶级而闪耀,恰恰是工人阶级为工业重组而担当了第一牺牲人的责任。所以,新上台的统一前进联盟在其最低纲领中宣布了就业保证计划,以法律来保证至少100天的就业,方法是至少为每一个能够工作的城乡穷人和较低的中等收入家庭的一个成员提供最低工资标准的公共工作。然而,印度迄今没有一个全国的最低工资线,尽管其劳动力制度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形成。
这一切的表面原因是印度政府的政治愿望与行政能力相差悬殊,监督劳动力法的部门是掌握着有限资源的软弱官僚,根本没有能力来执行劳动力法案。实际上,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相关理念。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突出代表,印度政府认为,既然国家要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那么,组织国家竞争团队的资本和劳动力必须共同努力,为创造出更多的利润而相互妥协让步,尤其是工人要团结在雇主的周围,因为经济竞争的核心是资本。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结果截然不同于发达国家。所以,全球化中印度劳工标准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政府的能力问题,而是政府的最低纲领使然。
第二,工人的安全保障问题。印度长期忽视工人的安全保障问题,工业灾难事件的比率相当高。改革前史无前例的最大悲剧事件是1975年12月27日在恰斯纳拉煤矿场,约400名矿工被淹死,激起了全国所有工会的强列抗议。然而,全球化带来的更大的悲剧不久又降临到工人身上。1984年12月3日博帕尔联邦碳化物工厂的碳化气泄露,2500人死亡,成千上万人中毒,其中的大多数人终身饱受毒气的摧残。这是一场全国性的悲剧,是印度所有行业中最大的悲剧。该工厂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建立的,将其国内不允许存在的危险性工业转移到印度,却没有建立起基本的安全保障,结果给印度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博帕尔事件充分暴露了印度政府对安全措施的忽视,以及跨国公司拿劳动人民的生命当儿戏的犯罪行为。此后,印度工会运动一方面不断要求政府关注那些远远不够的安全措施和规定,特别是那些危险性极高的行业,另一方面加强了反对跨国公司进入印度的斗争,并将其列为长期的斗争目标。
第三,工人的福利保障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前,劳工的福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特别是医疗问题,但由于没有一个企业所有者会把它看做是其第一要务,所以一般由国家来承担这一工作,建立了很多职工医院。改革后,公营部门逐渐脱离政府的控制,政府的计划无法在那里继续实施,而且这些职工医院的运转都存在很大问题,所以,以马哈拉施特拉邦为例,邦政府在2007年决定关闭三家大型的职工医院,结果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对类似问题的争论。另外,自由化全球化改革以后,在正规部门之外的边际劳动力的规模不断增大,这些边际工作,尤其是IT业带动的服务业,都是小单位,或家庭式的,没有任何的福利范畴存在。而且,一半以上这样的工作是妇女从事的。妇女现在构成300万传统的以家庭为基地的工人总数的80%。他们既没有就业的保障,也没有可以依据的条例和机制来享受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因此,这类群体的福利保障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印度社会保障工作小组已经就此向第二届劳工委员会递交了报告(14)。这意味着,在全球化时代,工人的医疗保障等福利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第四,工人的罢工权问题。全球化后,很多私营企业和跨国公司不允许工人罢工,一直在社会上反响很大,对此,印度劳工经济学会(ISLE)和人力发展研究所(IHD)在2003年提议召开了一次关于“工人和罢工权”的研讨会。在新德里、海德拉巴、孟买和加尔各答分别进行了对话。共有700多著名人士参加,包括工会、雇主、政党、学界、社会活动家、媒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组织。研讨会最后一致认为:工人,不论是全国政府还是邦政府的工人,都有不可剥夺的罢工权,然而,可以通过有效的社会对话对罢工施加合理的限制;罢工权应该列为宪法的基本权,或列入工业关系条例里,如1947年的工业争议条例;印度政府应该立即批准所有相关的国际条约,以尊重劳工的尊严,特别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条约,如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以及组织和集体讨价还价权;相应的地方立法必须立即实施,以保证国际条约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尊重;必须立即加强行政法庭和其他的争议解决机制;工会必须特别努力地保证他们的行动是民主的,她们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工人阶级的福利;永远不能发动闪电罢工;在诉诸于罢工前,必须首先探讨所有可能的冲突解决渠道;工会要罢工,必须尽可能地通过秘密的罢工投票来决定;必须建立起相应的机制来真正扩大工人对管理的参与(15)。然而,在失业率极高的环境中,要求强大的私营企业和跨国公司接受他们的观点,谈何容易!
工人对全球化的回应
第一,举行反全球化的工人大罢工。从80年代经济自由化全球化改革以来,尤其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后,印度的工人运动一直处于低落状态。特别是1982年孟买纺织工人的大罢工失败严重打击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士气,以至于印度的资产阶级不再把工人看做是与其利益相敌对的阶级,而开始称呼为伙伴关系。在2002年的第38届印度劳工大会上,瓦杰帕伊甚至说,“曾经有些人认为劳资冲突是不可协调的。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错误的”。
然而,在2003年4月21日印度爆发了独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工人大罢工,5000万工人参加,目标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经济政策。与以前的罢工相比,这次罢工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作为边际工的农业工人参加进去,以反对WTO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痛苦。第二个特点是全印度的工人实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从南亚次大陆的最南端,到局势不稳的克什米尔河谷,即使在教派冲突十分严重的古吉拉特,工人也在行动中也团结了起来。
事实上,早在2002年,伴随着自由化、私有化和全球化,印度无组织部门的工人就已经猛然觉醒了(16)。在印度,以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部分是有组织部门的工人。然而,在2002年的3月8日,泰米尔纳都的无组织工人发动了一场行程880公里的50天的进军运动,历经泰米尔纳德邦30个地区中的一半,并且在一些重要的地方都举行了集会,最后在钦奈海边举行了数千人的大型集会。无组织的工人的进军表明,非正式部门的工人并不俯首于命运带给他们的剥削与压迫,他们努力争取自己的政治空间和经济正义。应该指出的是,非正式部门的工人斗争得到了传统工会的支持,但不幸的是,这些传统工会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非正式部门的工人斗争能够反过来增强工会运动本身的力量(17)。
在自由化全球化改革的初期,在印度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悲叹:帝国主义太强大了,工人运动太薄弱了,无法团结起来抵抗帝国主义的进攻;一些人认为工会不再会赢得任何一场重要的战斗,罢工也不再有效(18)。但上述的罢工案例表明,全球化在印度造就了新的工人群体,改变了旧的工人群体的力量结构,特别是无组织的工人和边际工的数量激增,他们的斗争精神为全球化时代工人阶级的团结与斗争的加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第二,工人自救——工人合作运动。合作运动被看做是社会弱势群体改善其社会经济条件的一种力量,目的是使参加合作组织的成员的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和幸福。
1985年印度政府颁布病态企业条例,允许工人为了复兴而接收病态的或关闭的企业。所以,工人合作主要是为了接收和复兴那些陷入危机濒临倒闭的公司,是由工人拥有和管理的生产性公司,是一种注重实效的自我管理机制的反应,并非一种意识形态的反应。工人合作的覆盖范围很广,从小的零售商业到大型的制造厂。合作的形式也很多,有的是每一个工人都拥有平等的股份,有的是不同的工人拥有不同的所有权,所有权有一定程度的集中。这种形式的职工所有是一种过渡,有利于病态企业的重组。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得到政府及其机构的支持,工人的合作一般能够复活病态企业(19)。
迄今为止,印度有一些企业通过工人合作获得成功,如斋普尔的金属厂,达里拉贾拉的铁矿厂,加尔各答的新黄麻厂等。促使工人合作取得成功的因素有:(1)劳动者的团结与协作,(2)从工人中诞生出合格的有能力的领导人,(3)企业能够持续有效地获得外部支持(20),(4)工人合作使工人拥有一个共同所有的感觉。这种感觉促使他们努力提高生产力。因为他们知道所有降低的成本和增加的费用都关系到自己的腰包,而非资产阶级的企业主的腰包。然而,总起来看,工人合作获得成功的案例较少。拉马斯瓦米认为,自由化、全球化后,国家的大环境逐渐不利于工人的接管。国家并不认为工人自救是解决病态企业和失业问题的唯一答案,政府和公营部门与私人资本的合作,被看做是解决工业重组问题的唯一出路。这些无疑阻挠了工人及其工会的接收与管理企业的能力。况且,合作制企业要生存,不仅仅工人拥有企业,而且必须工人自我控制,自我管理,形成民主的控制和管理结构。而且,这些工作必须在工人还充满热情的时候完成;否则,等到工人疲怠了,外部的压力和限制增多了,要形成一个民主的控制和管理结构非常困难(21)。所以,苏雷施拉马纳认为,工人合作要取得成功,必须要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一是政府要为工人合作的发展提供一个同情的环境,并提供一个平台使其能与其他类型的组织竞争;二是有一个建立在“合作优势”基础上的战略,良好治理、利用所有相关成员的优点、明确规章制度等等(22)。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球化造成印度有组织部门的工人减少,而无组织部门的工人大量增加,占工人总体的绝大多数,工人队伍中还出现了知识工人和边际工两大新的力量群体。尽管不同的工人群体面临着各自不同的新挑战,但印度工人作为一个整体也面临着一些共同的挑战,如工资问题、安全和福利保障问题以及罢工权问题。这些共同的挑战虽然促进了印度工人前所未有的新型团结与合作,激发了印度工人的创造力和自我发展的潜力,但如上所述,印度工人面临的总体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很多问题仍然亟待解决。所以,如何利用全球化的机遇以实现更大的团结和更成功的自我创造与发展,并利用全球化时代印度市民社会的良好发展机遇来实现更大程度的政治参与,以充分捍卫工人自身的利益,是摆在印度工人面前的最大挑战。
注释:
①印度劳工史学会认为印度的劳工史研究有两个高潮点,一个是在20世纪60年代,另一个是21世纪以来。20世纪60年代对劳工史的兴趣起源于西方学术界,话语也是西方式的,目的是恢复工人阶级激进的、革命的传统,从而与战后的福利资本主义联结起来,研究的重点是传统的男性工人阶级的历史。而这一次的高潮起源于南方国家,焦点不再是传统的工人阶级,因为劳工的空间、时间和相互关系具有非常复杂的多样化特性,非以往那种简单的二元化模式可以交代清楚。从空间来讲,不仅包括传统的西方和非西方世界,而且包括工作场所和家庭、工厂和作坊,城市和乡村;从时间来讲,不仅存在前现代的劳工关系,而且工业化和非工业化的劳工关系并存。从关系来看,自由与非自由的、挣工资的与不挣工资的、正式的与非正式的,界线模糊,而且,劳动力日益非正规化和女性化,男工与工会不再是中心。研究的主题与以往也有很大的差异,包括合法性、流动性、团结性、性别关系,新技术对工作的影响,劳动者身份的多样化等等。详情请参阅:V.V.Giri National Labour Institute,Towards Global Labour History:New Comparisons,A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rganized by Association of Indian Labour Historians(India),November 10-12,2005 at Delhi,India.
②在第二次的劳工研究高潮中,由于时代的变化,学界普遍不再使用“工人阶级”这一概念,而是使用“工人”这一概念。就印度而言,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工人”或“劳工”或“城市穷人”的概念更符合印度国情,例如牛津大学印度历史研究专家南迪尼·古普塔。此外,更多的学者认为,尽管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印度也出现了等级和阶级的分化,但大量的研究数据表明,目前以至将来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内,印度社会关系的主体框架将仍然是种姓制度。
③Jan Breman,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Industrial Working Cla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④更加详细的情况请参阅:Barbara Harriss-White,India working:essays on society and 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1—46.
⑤Marisa D' Mello,Thinking local,action global:Issues of Identity and Related Tensions in Global Software Organizations in India,EJSDC,22(2),2005,pp.1-20.
⑥T.K.Rajalakshmi,Labour Issues:Not all sunshine,Frontline,Volume 22-Issue 24,Nov.05-18,2005.
⑦Marisa D' Mello,Thinking local ,action global:Issues of Identity and Related Tensions in Global Software Organizations in India,EJSDC,22(2),2005,pp.1-20.
⑧M.Alvesson,Organizations as Rhetoric,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30(6),1993,pp.997-1015; Knowledge Work,Human Relations,54(7),2001,pp.863-886.
⑨Parvathimenon,Urban Development:The two Bangalores,Frontline,Volume 22-Issue 22,Oct.22-Nov.04,2005.
⑩T.V.Sathyamurthy,Class formation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post-colonial Indi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39.
(11)C.P.Chandrasekhar,Pitting knowledge against work,Frontline,Volume 22-Issue 26,Dec.17-30,2005.
(12)Sanjay Kumar,N.K.Sharma,Workers in Census 2001,EPW Commentary May 4,2002,p.7.
(13)Debdas Banerjee,Globalisation,Industrial Restructuing and Labour Standards,Sage Publications,2005,p.178.
(14)EPW Editorial,Workers' Welfare:To Those That Don't Have,EPW,August 19-25,2000.
(15)Aseem Prakash,Workers' Right to Strike EPW Commentary September 25,2004.
(16)A.K.Roy,Voice of the Unorganised Sector:Workers' Rally in Tamil Nadu,EPW Commentary October 5,2002.
(17)T.V.Sathyamurthy,Class formation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post-colonial Indi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41.
(18)Dipankar Bhattacharya,Globalisation and Working Class Resistance:Myths and Reality,Based on talk delivered at an anti-globalisation seminar in Guwahati on May 1,2006,hosted by the North-Eastern regional unit of the PNB Employees' Union as part of its silver jubilee celebration.
(19)Sureshramana Mayya,Mysore Kirloskar:Workers' Alternative to Unemployment,EPW Review of Labour May 25,2002.
(20)S.S.Khanka,Workers' Cooperative to Revive Sick Units,Yojana,May,44-46,1995.
(21)E.A.Ramaswamy,Worker Co-operatives in India:Lessons from Kamani,EPW,Commentary January 30,1999.
(22)Sureshramana Mayya,Mysore Kirloskar:Workers' Alternative to Unemployment,EPW Review of Labour May 25,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