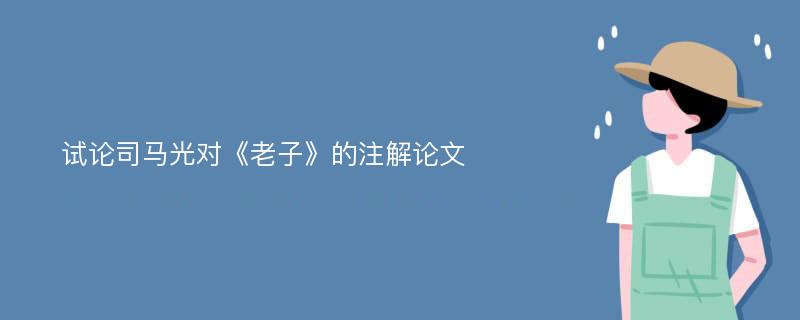
试论司马光对《老子》的注解
尹志华
【摘要】 司马光对《老子》的注解,最大特点是坚持儒学本位、以仁义释道。其迥异诸家之处是主张“道亦可言道”,认为老子所说的道不是常人所说的道。其反映北宋《老子》注家共识的地方是主张有无并重,认为自然之道并不排斥礼乐刑政。其注解的最大缺陷,是丝毫没有涉及新儒学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心性问题。这可能与司马光不擅理论思辨有关。
【关键词】 司马光;老子;道;自然;仁义
司马光(1019-1086)作为一个以“朴儒”自居之人[注] 司马光说:“比老,止成一朴儒而已。”([宋]司马光:《答怀州许奉世秀才书》,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5册,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76页。 ) ,其学术思想的本源自然是儒家圣人之道。二程曾说:“某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即张载)、邵尧夫(即邵雍)、司马君实(即司马光)。”[注]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1页。 苏轼在《司马温公行状》中说,司马光“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注] [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91页。 。司马光自言,其所以不好佛老者,因佛老“不得中道,可言而不可行故也”[注] [宋]司马光:《答韩秉国书》,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5册,第88页。 。
采用健康调查简表(SF-36)对患者进行功能评价,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的生活质量越好[6];采用改良Barthel指数(MBI)对患者的功能评分进行评价,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的恢复越好[7];并且对于所有患者的ICF总分进行评价,分数越低表示患者的功能越好[8]。
司马光面对当时“天下之不尚儒久矣”[注] [宋]司马光:《颜太初杂文序》,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5册,第110页。 、“流俗戆愚,崇尚释老,积弊已深,不可猝除”[注] [宋]司马光:《论寺额札子》,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3册,第210页。 、“近岁公卿大夫,好为高奇之论,喜诵老庄之言”[注] [宋]司马光:《论风俗札子》,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4册,第122页。 的状况,忧心如焚,力陈佛老之弊。他认为“释老之教,无益治世,而聚匿游惰,耗蠹良民”[注] [宋]司马光:《论寺额札子》,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3册,第210页。 。具体到道家,他批判“庄老贵虚无而贱礼法”[注] [宋]司马光:《文中子补传》,吕祖谦编:《宋文鉴》卷14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99页。 ,指斥“彼老、庄弃仁义而绝礼学,非尧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为忧,存亡不以为患,乃匹夫独行之私言,非国家教人之正术也”[注] [宋]司马光:《论风俗札子》,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4册,第122—123页。 。可见,司马光主要是站在儒家礼教的立场上,批判老庄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当然,他对老庄的理解是偏颇的,特别是对老子与庄子之学的区别,没有足够的认识。
司马光处在儒学重构的时代,他自觉地参与到新儒学的塑造过程中。而要塑造新儒学,以应对佛老的挑战,其思想资源自然不能完全局限于儒家经典。因此,司马光虽“不喜佛老”,但对佛老中“不出吾书”之“微言”的内容,则加以肯定和吸取。在《迂书·释老》中,司马光自问自释:“或问:‘老、释有取乎?’迂叟曰:‘有。’或曰:‘何取?’曰:‘释取其空,老取其无为自然。舍是无取也。’或曰:‘空则人不为善,无为则人不可治。奈何?’曰:‘非谓其然也。空取其无利欲之心,善则死而不朽,非空矣。无为取其因任,治则一日万几,有为矣。’”[注] 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5册,第462页。 可见,司马光对佛氏之“空”、老氏之“无为自然”,是在加以辨析和改造的基础上才加以肯定的。
由于《老子》行世已历千年,人们耳熟能详,故司马光在批驳政治对手时,也充分利用《老子》的理论资源,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如,熙宁三年(1070)二月,他写信质问王安石:“光昔者从介甫游,介甫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注] [宋]司马光:《与王介甫书》,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4册,第555—556页。 他谏止西征和要求罢除保甲法的奏疏中,都讲“夫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注] [宋]司马光:《谏西征疏》《乞罢保甲状》,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4册,第85、156页。 ,明显是借用《老子》第三十一章的话。
王安石及其变法助手们纷纷注解《老子》,试图掌握对《老子》的解释权,以扫除变法的理论障碍。司马光也对《老子》作了注解,其动机何在,笔者尚不清楚。
据赵希弁《郡斋读书后志》卷二,司马光的《老子注》名为《道德论述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九则著录为《老子道德论述要》。司马光对《老子》不称“经”,而称“论”,反映了其儒家正统意识,即只有儒家经典才能称为经,道家之书不能称为经。其注今存于明《道藏》中,编者据道家立场而改题为《道德真经论》[注] [宋]司马光:《道德真经论》,《道藏》第12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62—272页。本文所引司马光《道德真经论》均出《道藏》,为避免繁琐,不一一注明页码。 。《道藏》本只题司马氏注。按金朝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南宋范应元《道德经古本集注》、南宋彭耜《道德真经集注》、南宋董思靖《道德真经集解》等所引司马光注,均与此书合。可知司马氏即司马光。
司马光在注解《老子》时,对“道”之体用均从儒学的角度进行诠释。他以仁义为道之体,以礼乐刑政为道之用。他释《老子》第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说“道者涵仁义以为体”,这显然是对老子之道的内涵作了儒家式改造。唐代韩愈曾明确提出,儒家之道与老子之道不是一回事:“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注] [宋]韩愈:《原道》,魏仲举编:《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1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4册,第222页。 换言之,儒家之道以仁义为内涵,老子之道则排斥仁义。司马光与韩愈不同,他不是去批判老子之道,而是直接以儒家的仁义之道诠释老子之道。
一、道亦可言道
生态文明的概念最早是由生态主义者总结的。“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④这是人与社会共同进步的标志,反映了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界关系时由敌对到和谐的改进程度,是人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宋元之交的陈世崇《随隐漫录》中记载陆游在蜀地纳驿卒女为妾的轶事被后人多次转引,而辨疑之声也是不绝如缕,然而不论据实与否,自不是空穴来风,一定与陆游在蜀地的诗酒狂放的生活态度有密切关联,他的诗里对这段生活也多有展现,而他有妾杨氏纳自蜀地并育有儿女一节确是有据可查。今人邹志方在《陆游研究》中有专章论及,他认为陆游纳杨氏为妾的“比较确切的时间当在孝宗乾道九年(1173)春天”,陆游“时年四十九岁”,但杨氏不见容于王氏,一年后被逐出,然陆游终究割舍不下,又在转年的冬天(淳熙二年)把杨氏接回。〔3〕陈祖美先生也在文章中提到这一段故实。〔4〕
司马光则另辟蹊径,将“常道”理解为常人所说的道:“世俗之谈道者,皆曰道体微妙,不可名言。老子以为不然,曰道亦可言道耳,然非常人之所谓道也……常人之所谓道者,凝滞于物。”他从认识水平上将老子之道与常人所说的道作了区分。他批评常人所说的道“凝滞于物”,认为常人的认识局限于具体事物,只能认识表现在具体事物中的“道”,而不能超越具体事物,认识普遍的“道”。司马光在释第三十五章“乐与饵,过客止”时,也批评“众人凝滞于物”。
从图5(a)脉冲压缩的结果可以看出,单子带定标信号经过系统后出现了严重的失真,这种信号无法进行子带合成。图5(b)和3个子带指标计算结果均表明,利用本文使用的方案提取出子带内幅度和相位误差,经过误差补偿以后,单子带信号脉冲压缩结果和理想信号基本一致,为后面子带间误差计算以及最终的子带合成提供了必要条件。
司马光对老子之道与常人所说的道的区分,其思维方式类似于韩非对“理”与“道”的区分。韩非说“理者,成物之文也”“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可见“理”是具体事物的规定性,韩非称之为“定理”。定理是可以言说的。但定理随物之存亡而存亡,故不能常。“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道统辖万物之理,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故常存不灭。“而常者无攸易,无定理,无定理非在于常所,是以不可道也。”[注] 《韩非子》卷六《解老第二十》,《道藏》第27册,第340页。
细绎司马光所引儒典,其与《老子》原文的意思还是可以相通的。这也反映出司马光融通儒道或曰以儒摄道的一种努力。而以上所引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以儒家的“谦”来解《老子》的“不争”;二是以儒家的“仁”来解《老子》的“慈”。
为了贯彻以“无”释道的思想,司马光将《老子》第一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读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他的解释是:“天地,有形之大者,其始必因于无,故名天地之始曰无。万物以形相生,其生必因于有,故名万物之母曰有。”他根据《列子·天瑞》“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和《庄子·知北游》“万物以形相生”的观点,认为天地属有,乃万物之母,而天地本身则起源于无。
但是,司马光也不能无视南北朝以来以“非有非无”释“道”的思潮。如南朝顾欢说:“(道)欲言定有,而无色无声,言其定无,而有信有精,以其体不可定,故曰唯恍唯惚。”[注] 蒙文通:《晋唐〈老子〉古注四十家辑存》,《道书辑校十种》,第174页。 唐代成玄英说:“妙本非有,应迹非无,非有非无,而无而有,有无不定,故言恍惚 。”[注] 蒙文通:《辑校成玄英〈道德经义疏〉》,《道书辑校十种》,第404页。 唐代李荣说:“大道幽玄,深不可识,语其无也,则有物混成,言其有焉,则复归于无物。归无物而不有,言有物而不无,有无非常,存亡不定,故言恍惚。”[注] 蒙文通:《辑校李荣〈道德经注〉》,《道书辑校十种》,第593页。 司马光也觉得不能只强调道就是无,而要指出道不可定言有无的一面。他释《老子》第十四章“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说“曰有曰无,皆强名耳”,“欲言无邪,则物由以成;欲言有邪,则不见其形”,因此道是“若有若无”。
(2) 采用传统的二维模糊控制器对y测(t)进行处理,以误差e(t)和误差变化率ec(t)作为控制系统的输入变量,以位移变化修正值β为输出,对误差进行修正,如式(5)所示:
二、有无并重
前文提到,司马光在《迂书·释老》中说“老取其无为自然”。在注解《老子》时,司马光确实贯彻了这一思想。他认为:“万物生成,皆不出自然。”(释第六十四章“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故他在注文中强调“任物自然”(见第二十九章注、第七十三章注)。他解第二十八章“大制不割”说“因其自然”,解第二十九章“为者败之”说“为之则伤自然”。有意思的是,司马光如此重视“自然”,却对《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句未作注解。可见,他注解《老子》并非出自探究《老子》本意的目的,而是“拿来主义”,觉得有必要阐发的地方就注解,觉得没有必要阐发的地方就不注解。
司马光在这里所说的“有”“无”主要是指政治哲学而言。所谓“常存无不去”,就是要体察自然无为之天道;所谓“常存有不去”,就是要制订礼乐刑政等社会规范。他反对“专用无而弃有”,就是反对纯用自然无为之道治理天下。他在《答韩秉国书》中也指出:“夫万物之有,诚皆出于无,然既有,则不可以无治之矣。”[注] 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5册,第88页。 故他解释《老子》第三十二章“始制有名”说“圣人得道,必制而用之,不能无言”。所谓制而用之,就是制订礼乐刑政等道德规范和政治制度。他注解第五十一章“既得其母,以知其子”说“因道以立礼乐刑政”。自然之道并不排斥礼乐刑政,而恰恰是礼乐刑政之所本。而礼乐刑政的合理性在于它是根据无形之道而制订的。可见,司马光的“常无”“常有”之论是以体用关系来融合儒道政治哲学。
(1)免疫接种。选择与自己猪场血清型相一致的疫苗,产前免疫母猪。目前国内应用比较多的疫苗有K88/K99/987p/f41/f42/f7等。方法是:母猪产前30~40 d,15~25 d按使用说明各注射一次。效果极佳。
不过,司马光又指出,圣人虽以礼乐刑政作为治理天下的手段,但并不以有形的礼乐刑政本身为目的,而是以契合无形之道为最高境界。他说:“礼至于无体,乐至于无声,刑至于无刑,然后见道之用。”(释第十一章“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所谓“无体之礼”“无声之乐”,出自《礼记·孔子闲居》;所谓“刑至于无刑”,出自《尚书·大禹谟》之“刑期于无刑”的说法。可见,司马光试图以代表最高境界的“无”来贯通儒道两家思想。既然“无”代表了合道的最高境界,因此在施行礼乐刑政时,始终“不可忘本弃道”(释第五十一章“既知其子,复守其母”),以防止礼乐刑政走向异化。
“有无并重”的思想,在北宋时期并非司马光一家之言,而是当时许多学者的共识。《老子》首章“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王安石、王雱、陆佃、苏辙等人均读为:“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如苏辙的注解是:“圣人体道以为天下用,入于众有而常无,将以观其妙也。体其至无而常有,将以观其徼也。若夫行于其徼而不知其妙,则粗而不神矣。留于其妙而不知其徼,则精而不遍矣。”[注] [宋]苏辙:《道德真经注》卷1,《道藏》第12册,第291—292页。 苏辙所谓的“常无”与“常有”主要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而言的。一方面“圣人体道以为天下用”,根据自然天道而制订仁义礼乐等道德规范和政治制度。圣人虽以仁义礼乐治天下,却并未忘记仁义礼乐之所本,所以“入于众有而常无”。另一方面圣人时刻体察天道之自然无为,却不因此而废人事之有为,所以“体其至无而常有”。可见,苏辙也是以体用关系来理解天道与人事。
王安石虽与司马光在变法问题上是政治对手,但也同样倡导“有无并重”的政治哲学理念。他说:“道之本,出于冲虚杳渺之际,而其末也,散于形名度数之间。是二者,其为道一也。而世之蔽者常以为异,何也?盖冲虚杳渺者,常存于无;而言形名度数者,常存乎有。有无不能以并存,此所以蔽而不能自全也。”[注] [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1引王安石注,《道藏》第14册,第90页。 按照王安石的观点,道之本虽是一切社会规范的最高合理性依据,但由于它蕴藉于冲虚杳渺之际,既无形可见,也没有具体的规则可以掌握,可以称之为“无”。“无”在政治层面上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道家据此而主张政治应该无为。但是,道并不只是有本而已,它还有末,即道之散殊。道之末,表现在社会政治层面,就是礼乐刑政等具体的社会规范。因此,如果像道家那样,“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无之为用也,则近于愚矣”[注] [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17引王安石注,《道藏》第14册,第299页。 。真正体道的圣人是上知道本、下察道末,而无“有无不能以并存”之弊。“圣人能体是以神明其德,故存乎无则足以见其妙,存乎有则足以知其徼,而卒离乎有、无之名也。其上有以知天地之本,下焉足以应万物之治者,凡以此。”[注] [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1引王安石注,《道藏》第14册,第90页。 上知天地之本就是理解形而上的自然天道,下应万物之治就是推行形而下的礼乐刑政等人道,二者虽有上下本末之别,但就道体而言又是统一的。
总之,北宋《老子》注家的“有无并重论”,其政治哲学意蕴就是既反对纯任自然天道而摒弃礼乐刑政,也反对只用礼乐刑政而忽视自然天道。他们认为,自然天道要落实到政治操作层面,就必须制订礼乐刑政等社会规范;而礼乐刑政制订了以后,又必须从自然天道的角度对之进行审视,以防止其异化。也就是说,自然与名教,一为体一为用,体用不可偏废。这样,就超越了魏晋玄学“贵无”派重自然与“崇有”派重名教的对立。
三、道者涵仁义以为体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司马光所用《老子》文本,与通行本有异。经过比对发现,司马光本是在王弼本的基础上,采撷唐玄宗御注本和遂州龙兴观石碑本(见明《道藏》所收无名氏《道德真经次解》)[注] 《道德真经次解》,《道藏》第12册,第612—626页。 ,断以己意,综合而成。南宋彭耜曾在《道德真经集注释文》中详细分析宋代诸家《老子》注本经文异同,对司马光本的异文一一作了列举[注] 《道藏》第13册,第248—255页。 。司马光对《老子》的注释也非常简略。如第七十章,“吾言甚易知,甚易行”,注曰:“易简”;“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注曰“精一”;“言有宗”,注曰“体要”,“事有君”,注曰“返本”。注文比《老子》原文还少。另有一些原文,甚至整章(如第七十九章),司马光都没有注解。但是,其注虽简略,却也颇具特色,值得一述。
既然司马光认为老子之道并不排斥仁义,那么如何理解老子对仁义的批评呢?如《老子》第十八章说“大道废,有仁义”,儒家如韩愈等人认为老子此说意在贬低仁义,因而表示不能接受。司马光并不这样看。他认为老子不是批评仁义本身,而是批评世人在践行仁义时产生的流弊。他指出真正践行仁义的人应该是“行之以诚,不形于外”,即内心真诚地奉行仁义,而不是彰显其外在形式给别人看,所以“道之行,则仁义隐”。如果只是做样子给别人看,而不是由内心自然而发,则只有仁义之名,而无仁义之实,这就是“道之废,则仁义彰”。
概言之,司马光是以一个“诚”字来化解儒道两家的对立。在他看来,如果世人对于仁义是“推至诚而行之”(释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则符合老子之道;如果只是追求仁义之名,而并非出自至诚之心,则徒具其表而无其实,老子所反对的就是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后一种情况,其用意在于使人复归于“诚”,重其实而不彰其名。
四、任物自然与适当有为
司马光虽然以“无”释道,但并不主张贵无贱有、崇本息末,而是主张有无并重、本末并举。为此,他将《老子》首章“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读为:“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他对这两句话的注解是:“万物既有,则彼无者宜若无所用矣。然圣人常存无不去,欲以穷神化之微妙也。无既可贵,则彼有者宜若无所用矣。然圣人常存有不去,欲以立万事之边际也。苟专用无而弃有,则荡然流散,无复边际,所谓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也。”
司马光强调任物自然,是希望统治者不生事扰民,让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他解第十七章“功成事遂,百姓曰我自然”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这是小农经济时代,农业劳动者所向往的“帝力”几乎不干预民生的理想政治环境。他解第三十五章“往而不害,安平泰”说“不以有为害之”。由此,他认为“善爱民者,任其自生,遂而勿伤”(释第十章“爱民治国”)。他解第七十五章“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说“扰之故难治”。
根据认知心理学解释,语篇记忆输出体现在对字句,意义以及事件的再现,语篇记忆输出是英语学习重要组成部分,长期睡眠不足对词汇,词法,句法及语篇复述产生消极影响造成学习成绩不理想;语篇理解与记忆密切相关,语篇连贯是有赖于与睡眠相关的大脑高质量记忆,在高质量睡眠状态下,易于提取语篇记忆内容促进语篇理解,巩固语篇知识促进英语学习。语言学习依赖与睡眠高度相关的语篇记忆,语篇记忆输出体现英语学习五个层面的水平,高效睡眠下语篇记忆达到最佳状态为语言学习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反之导致语言学习不佳。因此得出,睡得好的状态能促进学习。
但是,《老子》主张“不尚贤”,与儒家的“选贤与能”是对立的,司马光如何面对二者的理论冲突?他说:“贤之不可不尚,人皆知之。至其末流之弊,则争名而长乱,故老子矫之,欲人尚其实,不尚其名也。”(释第三章“不尚贤,使民不争”)这就是说老子并非不知道尚贤的重要性,而是看到了只重“贤名”所导致的纷争祸乱。许多有“贤名”的人并不一定有“贤”之实。老子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其用意是为了让人们崇尚贤之实,而不图虚名。
司马光认同《老子》关于圣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观点,主张圣人的“为”,只是对万物的一种辅助性的“为”,不是强行作为。他说,圣人“不能无为,然辅而不强”(释第八十一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圣人但以辅之,不敢强有所为也”(释第六十四章“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司马光认为,有为本身不是目的,有为的目的是无为。他解第三章“为无为,则无不治矣”说“为之使至于无为”。因此,“有为之教,比之于道,大小绝殊,然亦终归于道”(释第三十二章“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正当的“有为”必须始终以“合道”为依据。司马光对“无为”的理解,还体现在他撰写的《无为赞》中。他批评“学黄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为无为”,认为“无为”的真正义蕴是“治心以正,保躬以静。进退有义,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则天。夫复何为,莫非自然”[注] 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5册,第463页。 。可见,司马光所理解的“无为”,主要是坚守儒家之道,顺应自然,不妄作为。
五、援儒书解《老子》
司马光在注解《老子》时,其儒家本位立场时时流露。我们看到,他常常援引儒家经典来注解《老子》,有时甚至直接以儒家经典的文字作为注文,而不加自己的话。如:
在2017年4月10日与2017年11月6日分别测定所有试验林木的胸径d与树高h,并利用公式V=3.14 d2hf/4(f=0.42)计算材积;之后利用普雷斯勒公式(Jing et al.,2017)计算材积平均生长率:
第二章“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司马光以《尚书·大禹谟》“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解之;第六十六章“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司马光以《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解之。
第二章“行不言之教”, 司马光以《论语·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解之;第六十七章“夫慈,故能勇”,司马光以《论语·宪问》“仁者必有勇”解之。
第二十七章“善闭者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者无绳约而不可解”,司马光分别以《孟子·公孙丑下》的“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两句话解之。
《老子》开篇说:“道可道,非常道。”司马光以前的注家,大多解释为“可道之道非常道”,认为常道不可言说。例如,汉代的《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认为,可道之道,即经术政教之道。常道,乃自然长生之道。“常道当以无为养神,无事安民,含光藏晖,灭迹匿端,不可称道。”[注] 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页。 河上公将道分为“可道之道”和“常道”。常道无为无事,不见其有所作为,故不可道。曹魏王弼说:“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注]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页。 王弼认为可道之道“非其常”,常道不可言说。唐代道士成玄英说:“道以虚通为义,常以湛寂得名。所谓无极大道,是众生之正性也。而言可道者,即是名言,谓可称之法也……常道者,不可以名言辩,不可以心虑知,妙绝希夷,理穷恍惚……可道可说者,非常道也。”[注] 蒙文通:《辑校成玄英〈道德经义疏〉》,《道书辑校十种》,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375—376页。 其意为:道本湛寂,其用虚通,不可测知,当然更不可言说。一说就受到了语词的限制,就不是虚通之道,而是可称之法了。以上注家皆将“常道”理解为永恒常存之道,认为永恒常存之道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第四十章“反者道之动”,司马光以《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解之。
司马光认为,道是超越有形事物之上的,“宗本无形谓之道”(释第五十一章“道生之”)。他继承了王弼“以无为本”的思想,认为道就是无。他释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故几于道”,直接采用王弼的注解“道无水有,故曰几”;释第十四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说“古之道,无也”;释同一章“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说“道以无为纪”;释第二十五章“道生一”说“自无入有”。
当然,司马光的注解,也有以儒家的概念消解《老子》原意的地方。如解第五十七章“我好静而民自正”说“正己而物正”。《老子》原文强调统治者应该安静,不妄作为;司马光则以孔子的“恭己正南面”“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思想解之,掩盖了《老子》“清静以为天下正”的思想。
当然,司马光并不是一个“自治主义”者,他跟北宋其他《老子》注家一样,认为帝王在“任物自为”的同时,还应“因物之为”而采取适当的措施。“圣人于天下,不能全无所为。”(释第二章“为而不恃”)既然有君主,君主就要履行自己的职责。他解第六十三章“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说:“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故能无为而治。”所谓“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出自《尚书·皋陶谟》,本来是形容帝王每天处理政事极为繁忙,司马光却把它与“无为而治”联系起来。前引司马光《迂书·释老》也说:“无为取其因任,治则一日万几,有为矣。”推其意,是说帝王尽力干好自己份内的事,不去越俎代庖,干不该干的事,就是“无为而治”。所以他说:“善治国者,任物以能,不劳而成。”(释第十章“爱民治国”)所谓“任物以能”,就是要“选贤与能”,知人善任。
六、对司马光注的几点思考
北宋儒家士大夫,大多重视《老子》。考各种文献著录的北宋《老子注》,约有30余家,其中绝大多数是儒家学者所作。而研读《老子》,吸取《老子》思想,但未曾注《老子》的儒家学者,更是不胜枚举。北宋儒家士大夫重视《老子》的原因,可以从社会政治和思想学术两个方面来考察。
客服工作基本可分为人工客服和电子客服,其中人工客服又可细分为文字客服、视频客服和语音客服三类,根据服务类型的特点,招聘客服人员的要素主要有专业技能、职业素养、道德素质三方面。
从社会政治方面看,北宋承五代之乱而立国,民心思定。故宋初的政治局面与汉初极为相似,都需要与民休息,静以致治。因而,黄老的清静无为思想又一次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如宋太宗说:“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注] [宋]李攸:《宋朝事实》卷3《圣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8册,第30页。 宋真宗说:“《道德》二经,治世之要道。”[注] [宋]彭耜:《道德真经说序》引《国史·道释志》,《道藏》第13册,第108页。 儒家士大夫大多予以赞同,由此形成了北宋前期贵“因循”的政治风气。受此影响,司马光也推崇老子的“无为自然”思想,并以之作为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
从思想学术方面看,自魏晋迄宋初,儒学与佛、道教相比,在本体论与心性论方面,要逊色得多。北宋儒家要复兴儒学,就必须弥补这方面的差距。但是,先秦儒家典籍在这方面的资源太少,因而宋儒必须批判地吸取佛、道教的有关思想,以充实儒学。这样,富于形上学色彩的《老子》受到他们的重视,便是很自然的事情。
北宋儒学,有三个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注解了《老子》:新学派的王安石父子、涑水学派的司马光、蜀学派的苏辙。将司马光的注解与王、苏二家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宋儒的两种学术取向:一是主张三教融合,一是坚持儒学本位。王安石和苏辙认为天下无二道,三家同一理,只是论述各有侧重而已:佛、道重在明体,儒家重在明用。因此,他们所建立的新学术,实际上是儒释道三教思想的综合[注] 参见尹志华:《北宋〈老子〉注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34页。 。而司马光则坚持以儒学的核心理念“仁义”来改造老子的“道”,提出“道”的内涵就是“仁义”。这一改造抹杀了儒道两家思想的本质区别,因而并未得到普遍认可。理学诸儒认为,从思想体系和根本价值取向来说,佛、老是迥异于儒家的;儒家可以吸收佛、老的某些思维方式和具体的理论观点,但必须强调儒家之道不同于佛、老之道。
司马光与王、苏二家对《老子》的诠释,最大共同点体现在政治哲学。他们沿着郭象的思路,致力于名教与自然的结合。与郭象认为“名教即自然”不同,他们从本末、体用的角度说明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他们虽然认为自然与名教为本末、体用关系,但又与王弼主张“崇本息末”不同,而是主张本末并重、不可偏举。这样,既可从名教出于自然的角度来证明现实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又可从自然为名教之本的角度,以天道(实即政治理想)为参照系,对现实政治进行适当的调整。因而,北宋《老子》注家的有无并重论既起到了对现实的辩护作用,又保持了对现实的批判功能。北宋儒家学者这样一种政治共识的形成,可能与他们意识到此种理论有利于维护他们对政治的发言权有关。
例如,在音乐课堂上学习《爱满人间》时,教师可以根据歌曲的具体内容,进行对音乐教学课件的制作,在课堂上将父母之爱、友谊之爱、师生之爱等因素形象地进行展示,再加上音乐的播放,可以形成一种良好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进行对音乐知识的学习,温暖学生的心灵,培养学生的责任心,提高教学的质量。
2014年,贵州水利系统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快转变水利发展方式,不断破除制约和影响水利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改革促发展,加快解决贵州工程性缺水矛盾,消除水利瓶颈制约,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有效保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司马光注的一个明显缺陷是哲理思辨不足。比如他一反众说,主张“道亦可言道”,虽然独树一帜,却忽略了“道不可道”的言道悖论中蕴含的深刻哲理。他只从认识水平来区分老子之道与“常人之所谓道”,显然有简单化之嫌,因而在整个思想史上,应者寥寥。
司马光注的一个更大的缺陷,是丝毫没有涉及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北宋中期以来,学者们普遍重视心性问题。王安石父子、苏辙等人的《老子注》,其最大的特色,就是以尽性和复性说诠释《老子》。王安石的学生陆佃认为,秦汉以来的注者,没有认识到《老子》讲的是“性命之学”,因而他们都没有抓住《老子》的主旨[注] [宋]彭耜:《道德真经集注·杂说》卷上引陆佃注,《道藏》第13册,第260页。 。所谓“性命之学”,就是《易传》所说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因而北宋《老子》注家大多融通《易》《老》,致力于“性”与“天道”的贯通,从而为儒家本体论、心性论的建构作出积极的努力。反观司马光,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语,使其注本的思想价值大大降低。这大概就是后世苏辙《老子注》广为流传,而司马光的注本湮没无闻的主要原因吧[注] 王安石父子的《老子注》也曾经广为流传,后由于政治原因而逐渐湮没,其失传与思想学术关系不大。 。
司马光不擅哲理思辨,程颢曾有评论。据《河南程氏外书》:“温公作《中庸解》,不晓处阙之。或语明道,明道曰:‘阙甚处?’曰:‘如强哉矫之类。’明道笑曰:‘由自得里,将谓从‘天命之谓性处’便阙却。’”[注]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12,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425页。 对于《老子》这样一部哲理书,不擅思辨的司马光为之作注,同样会是“阙却”处甚多。这恐怕也是其注解异常简略的原因之一。
中图分类号: B244.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60(2019)03-0148-08
作者简介: 尹志华,湖南常宁人,哲学博士,(北京 100081)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中央民族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民族哲学与经学研究”
(责任编辑 李 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