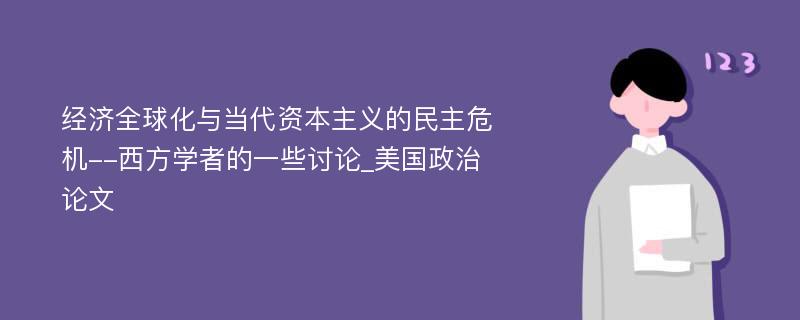
经济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危机——西方学者的若干论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论述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民主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近年来,在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的现状及其所主导的全球化实质的批判性论述中有一部题为《涡轮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赢家和输家》的著作颇为引人注目。这部著作1999年3月初版于美国, 翌年又出了第二版。其作者为曾任里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战略顾问的爱德华·勒特韦克。该书出版后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其中颇耐人寻味的是意大利文译本直截了当地将书名改为《资本主义的独裁》。勒特韦克的一个主要观点认为,所谓全球化,即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超越地理的界限、技术和通信的发展、由于产品的非物质化而导致的运输成本的下降以及消费的同质化等等现象。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推行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一种国际化。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实质上是经济试图超越政治和法律的限制。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相结合,产生了今天的“涡轮资本主义”。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扩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将“私先于公、经济先于公民利益”绝对化,使“受控制的资本主义”失控,造成“社会的失效”。勒特韦克强调,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同脱政治化、政治私有化、反民主结合在一起的,使资本主义成为一部绞杀公众利益和民主的绞肉机, 其结果很可能是走向“民主法西斯主义”。 (注:Luttwak,E.,2000,Turbo-Capitalism:Winner & Losers in the Global Economy,Paperback.)
勒特韦克的论断应该说并非危言耸听或奇谈怪论。同他持类似观点的人在西方学术界绝非个别。例如,中国学术界比较熟悉的著名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在最近发表的一篇题为《第三条道路也有其危险》的文章中(意大利《共和国报》1999年7月6日)着重指出:“决策过程以及一般地说各种行动的国际化,几乎一成不变地造成民主的失落。北约理事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俄罗斯的决策,欧盟部长理事会颁布的法令本身,都不是在任何类型的民主监督下产生的。而世界金融交易的‘私人’竞技场自更不待言”。
政治私有化造成民主的失落,其中一个突出现象乃是今天跨国公司的权力急剧膨胀。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在其被认为是近年来的一部最有份量的著作《劳动的终结:全球劳动力的衰落与后市场时代的发端》中认为:“跨国公司日益严重地篡夺了国家的传统作用,已经对世界资源、劳动储备和市场行使着无可比拟的控制力。大部分这类公司拥有的财富比许多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更多”。因此,所谓的“全球公司”成为一种“准政治机构,通过对于信息和传播的控制,对人员和所在地行使着巨大的权力”。(注:Rifkin,J.,1996,The End of Work: The Decline of the Global Labor Force and the Dawn of the Post-Market Era,Paperback.)其结果正如有的论者所说,资本主义的逻辑压倒了政治的逻辑和民主的逻辑。资本要求它自己的政治,即从它的利益,从它的语言出发的政治。金融市场“调控着”货币政策与之不相适应的国家,并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发动猛攻,而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根本没有招架之力,回天乏术。跨国公司成功地推行着它们的规则,它们的法律,“换言之,它们期望着一种同国家平起平坐的地位,承认它们拥有同国有企业相同的权利,但不向它们要求任何补偿”。其后果是“跨国公司和其他世界化的主角将可以用它们自己的法则来代替国家的法则,给国家剩下的只有镇压和惩处的职能”。(注:George,S., 1998,La mondializzazione e i pericoli per la democrazia, in Critica Marxista,n.4.)
利用经济—政治、公有—私有之间的基本矛盾来进行投机,只能造成穷人与富豪、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一些论者指出,社会分裂、集体焦虑、分配不均、不适应性的扩大,凡此种种是当前的社会学研究在以美国为首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前卫国家现实中清楚地看到的效应。因此,所谓的全球化必然具有“右”的性质,也就是说它必然要求“生产企业的不断兼并,以达到合理化之目的,而所谓的合理化集中到一点,就是首先排斥全体民众和劳动者的利益。因此,归根结底就是扩大社会的分裂”,通过强制“政府极大地缩小自己的再分配职能,不断减轻对于企业以及富裕阶层的税务压力”,扩大社会的不平等。可以说,美国推行的经济自由主义,即是意味着推行政治的私有化和社会的不平等。(注:Recanatesi,A.,1999,La riforma della pensioni é di destra o di sinistra? in Stampa,28 giugno.)
二、
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是福音还是灾祸?许多论者强调它将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和资源的更合理的配置,将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更大的经济繁荣,例如美国已出现了连续112个月的强劲增长势头。但是, 对此持不同看法者着重指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借助“新经济”来加速推动经济全球化,造成了财富的不断集中,不可避免地加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繁荣的背后隐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马太效应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贫困问题不但存在于一般劳动阶层中间,而且日益侵蚀着所谓“中产阶层”。其首先的表现是实际收入的下降。勒特韦克在上述著作中认为,美国一再吹嘘的能够保持比欧洲低得多的失业率的能力掩盖了其劳动者缺乏权利和保障,以及实际工资收入越来越低的事实。勒特韦克写道:“自70年代以来,7/10的美国人的纯小时工资不是停滞, 就是实际上不断下降”。所以美国社会中的消费和福利的增加完全是靠剥削的强化得来的,劳动的价格日益降低。另一位美国学者杰夫·福克斯也认为,美国的生产率与工资水平适成反比:“自1979年以来,美国劳动者的平均生产率提高了22%,而他们的实际工资降低了8%。 美国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在6年的经济繁荣之后,却又比1989年的水平降低了3 %”。 (注:Faux,J.,Spring,1999,Lost of the Third Way,in Dissent.)其结果是贫困人口和无家可归者不断增加。据勒特韦克的估计,如今在美国有1700多万每年工作50周、每周工作40小时的全职就业人员生活在官方公布的贫困线以下。而据另一位学者多米尼科·德马西的看法,在美国有3000万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700 万人沦为没有固定住址的无家可归者,170万人被关进监狱。(注:De Masi,D.,1999,Il futuro del lavoro,Milano,Rizzoli.)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工资下降的趋势不仅存在于普通劳动者中间,而且波及技术人员和知识阶层。据统计,从1968年到1995年,美国的工程师的年均收入(包括劳保福利在内)下降了13%。所以,勒特韦克不无感慨地说,即使是所谓精英也成为涡轮资本主义引发的结构的不稳定性的牺牲品,所谓机会均等完全是意识形态专家的谎言,今天的市场机制“不但不能给缺乏训练的民众提供工作,而且也不能雇用大量有熟练技能的人员”。在少数人财富越来越膨胀的同时,“处于不利地位的公民正在丧失仅有的一点点东西。有人称这个过程为‘中产阶级的空心化’”。另一位经济学家J.里夫金也认为:“中级管理人员特别倒霉:据哈默估计,80%具有中级管理职称的雇员在调整结构的过程中可能被解雇”。正因为如此,有的论者指出,经济全球化尽管导致了美国经济连续将近10年的强劲增长,但湮没了“原有的社会协调,这种社会协调保障着中产劳动者家庭避免工业资本主义滥用权力和反复无常的风险”(注:Marshall,W.,1999,La proposta dei democratici americani,in Europa Europe,n.3.)。 中产阶层中在文化和经济上比较弱的那一部分人存在着被挤出中产阶级的极大风险,因为技术的变革要求以脑力强度大的职业来代替体力强度大的职业。这样的倾向,用国际著名学者I.沃勒斯坦的话来说,即是“改变中产阶级在生产过程(包括服务部门)内部的绝对生存状态和相对生存状态。何况,今天的缩减公共预算的政策将继续下去,这构成了对中产阶级的最大威胁”(注:Wallerstein,I.,1998,Dopo il liberalismo,Milano,Jaca Book.)。
一些论者认为,这种倾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化的论断,尽管马克思的论断今天遭到许多西方理论家和意识形态专家的讽刺。里夫金在前述著作中指出,高技术革命很可能加剧贫富之间日益严重的压力,最终将国家分裂成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日益对立的阵营。不仅如此,技术发展过程“正在迅速地使全世界居民两极分化为两股尖锐冲突的和不可调和的势力:一股势力是号称‘符号分析专家’的世界主义精英,他们控制着技术和生产力;另一股势力是数量日益增多的经常是多余的劳动者,他们在高技术的全球新经济中找到合适工作的希望和前景十分渺茫”。在这样的绝望者中间包括被称为“新的贫困者”的部分中产阶级人士。据里夫金的估计,至今西方已有150多万中级管理人员失去了职位。
同时,资本主义近年来的发展也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的另一个论断:剥削和劳动者的异化的加剧。里夫金指出,今天的新经济表面看来是数字化的、无害的和“纯洁的”,但它有着“另一种面貌”,它的前进道路“沾满进步牺牲者的尸体的血污”。在西方发达国家里,越来越多的异化劳动者感受到高技术劳动环境中的日益增强的高度压力,以及越来越严重的工作岗位缺乏保障性。即使是名噪一时的所谓“丰田”模式,表面看来似乎强调劳动者的参与和责任感,实际上归根结底是一种经过巧妙伪装的剥削方式,可以称之为“压力管理”,其结果是“加大工作的刺激”,“完全破坏了生活和工作的节奏”,引发疲劳过度的“过劳死”。
同贫困和异化加剧密切相关的是西方社会犯罪率居高不下。根据勒特韦克的看法,在“涡轮资本主义”与犯罪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联系,犯罪成为经济自由化——全球化过程的必然产物:“缺乏技能的底层事实上变成在经济领域里不可利用的人,这对于美国来说意味着惊人的高犯罪率”。与过去不同,犯罪已不再是可以克服的局部现象,而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功能性行为”,它“与其说是一种偏离,毋宁说是一种理性选择”,也就是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犯罪不是例外,而是其必然的产物。
勒特韦克的这种看法,得到了其他一些论者的印证。里夫金在其前述著作中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失业加剧与贫富之间分化的增大,正在为社会动荡和近代所未见的大规模的阶级战争制造前提条件。犯罪、暴力与小规模冲突正在扩大,并且发出了清楚的信号表明在未来的年代将会日益加剧的趋势。一种新形式的野蛮在现代世界的墙垒外面等待着我们”。他还引用世界粮农组织的一位经济政策分析家的话说,经济全球化与技术空间的迅速扩展乃是美国饥饿家庭数量日益增多的主要原因。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身为意大利政府总理的朱利亚诺·阿马托也在1999年7月28日参议院的一次会议上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阿马托说:“我们注重美国模式,因为它表现出许多积极的方式和发展了竞争性,但我们不应忘记,由于缺乏坚实的社会政策结构,这个国家、这个制度正在产生着的穷人数量是庞大的、可怕的”。
有的论者指出,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固然是资本主义的痼疾和通病,但今天似乎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人类“全体”从其“对于已变成独立的经济相对功效”来说,被看作是多余的废物。(注:Mortellaro,I.,1998,La lotta per l'egemonia al tempo del mercato unico mondiale,in Critica Marxista,n.1.)贫困、犯罪、暴力严重地威胁着西方的民主价值,成为新法西斯主义滋生的温床。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抱有成见粗暴地把不安定的底层阶级推入社会暴力冲突的急风暴雨道路,乃是一条新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勒特韦克则认为:“美国民主正在变成反自由的民主”,而“美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尽管“完全是民主的,而且基本上不是种族主义的,也肯定不是好斗的”,但它“保持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以非经济的形式表达经济的不满足”。
三、
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或者说自由化+市场经济是多年来许多西方理论家竭力鼓吹的模式。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后,这种美国版的模式被看作是改变和拯救苏东经济的万灵妙丹。但近10年的事态发展说明事实并非如此。著名英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E.J.霍布斯鲍姆在90年代中期就大声疾呼,着重指出20世纪的历史千百次地证实“自由市场与政治民主之间不存在内在的联系”(注:Hobsbawn,E.J.,1995,Il secolo breve,Milano,Rizzoli.)。用勒特韦克的话来说,事实上“自由市场与很少自由的社会是同步并行的”。
有的论者还认为,欧盟国家之所以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停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从本国的国情出发,一味追随美国版的理论模式,“正统的货币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在欧洲造成了一系列社会性灾难。勒特韦克指出,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左派势力虽然历来十分强大,却表现出“走向消极”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迎合右翼的经济政策。勒特韦克写道:意大利“左翼民主党倾其全力来支持普罗迪的联合政府,无论是在保持失业率(在几乎整个南方高得惊人)方面,抑或是在用现代化方式改革处于衰落的学校和过时的大学,使意大利具备适当的医疗救护,将官僚制度标准提高到欧洲水平等方面。其最终目的是要使意大利进入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或者说是使正统的货币主义在欧洲加冕登基”。但事实表明削减公共开支和压缩预算赤字并没有能刺激消费和投资,毋宁说是扩大了失业和导致了“趋向消费的紧缩”。所以,勒特韦克认为,对于一定水平的公共开支率或者说“少量的通货膨胀”,“不必害怕,不论当前的政治雄辩会怎么说”。类似的观点也见诸于里夫金的论述。根据里夫金的看法,“近来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分析”驳倒了那种认为削减公共开支会带来机遇的“流行信条”。这样的分析清楚地说明“在这个世纪里,从来没有过哪一次经济增长长周期不是伴随着公共开支的同样迅速的相应增长”。
在这两位经济学家和西欧的一些论者看来,未来年代的基本问题将是如何管理生产过剩所造成的财富。人们面临的抉择是要么利益得不到“均分”,所有的人都为了追逐利润而耗尽精力,要么确立以公平和公正为原则的分配机制。有的论者认为,寻求严厉的货币政策与发展政策之间的某种平衡,这是21世纪的左派未来的责任。21世纪的左派既应摆脱对于过去的怀旧感,又应摆脱那种周而复始地追随右翼政策的倾向。当前,降低失业率的一个重要策略是缩短所有人的工作时间,扩大公共投资,为被劳动市场排挤出来的人在社会经济中提供就业机会。意大利经济学家保罗·西洛斯·拉比尼强调,公共投资“不仅具有扩大需求的直接的凯恩斯效应,而且具有增强生产基础,特别是刺激私人投资增长的所谓哈罗德效应,因此这两类投资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他认为那种坚持说国家干预迟早将导致税率提高的论点是“老生常谈的错误”:“只有非生产性的开支或转移性的开支才会有这样的结果。生产性的公共投资,即使是赤字财政,就像生产性的私人投资一样,促使收入增长,从而也促使财税总收入的增长,税收无需提高税率而得到了补偿。(注:Sylos,Labini P.,1999,Perché
serve che lo Stato investa,in Affari & finanza,inserto de la Republica, 12 luglio.)
事实上,即使是竭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的西方思想家今天也正在逐步改变想法,从他们的传统的“小国家”或“小政府”理论过渡到“新社会国家”理论,以适应“激烈竞争的全球新经济”。因此,他们为最近的将来提出的模式是自由化+社会国家。美国学者杰夫·福克斯指出,从东京到纽约,所有的财经机构“要求有一个能解脱市场后果的大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克林顿在多年来为市场大唱赞歌之后“出入意料地开始重提‘新政’型的全球解决方案,而布莱尔更直截了当地‘开始呼吁提高国际金融调节水平,这是左翼学者多年来一再建议的’”。在当前没有一个“民主的世界政府”的条件下,全球性冲突的威胁将是21世纪的现实,商业战争的爆发,失控的金融不稳定将成为国内冲突、暴力和犯罪的根源。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福克斯着重指出:“在我们建立既能为劳动界的利益又能为实业界的利益服务的全球政治机构之前,金融和企业的失调将不断产生经济的不稳定和政治的混乱。”
总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和社会危机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有加剧的趋势,这是西方学术界的有识之士不得不正视的现实。如何解决这些尖锐的社会问题,不仅引起左翼人士的关注,而且也成为西方学术界和理论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标签: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经济学论文; 韦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