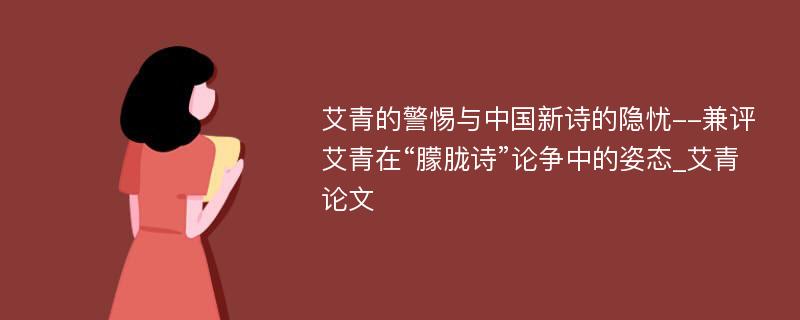
艾青的警戒与中国新诗的隐忧——重新审视艾青在“朦胧诗论争”中的姿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朦胧诗论文,新诗论文,隐忧论文,警戒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朦胧诗”论争当中有一段插曲一直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研究,这就是艾青,这位中国现代诗歌艺术的积极探索者对“新诗潮”诗人的批评,这位20世纪象征主义诗歌的前驱曾经一再严肃地质疑“朦胧”、“晦涩”等等颇具有时代开创意义的艺术取向,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与在当时更具有爆发力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崛起”之争比较,艾青的这些质疑的话语几乎就要被文学史所淡忘了。
然而,它真的能够淡出历史么?我的结论恰恰相反。观察中国新诗在新时期以后的走向,艾青当年的姿态似乎越发显示出了一种特别的意味。
一、误会中的分歧?趣味中的差别?
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青年诗人北岛创作了组诗《太阳城札记》,其中不少是三言两语的精短感悟,而最独特的一首便是《生活》,因为它的内容只有一个字:网。1980年7月23日,在《诗刊》编辑部举办的“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上,艾青这样谈到“关于写得难懂的诗”:“有些人写的诗为什么使人难懂?他只是写他个人的一个观念,一个感受,一种想法:而只是写他自己的,只有他才能领会,别人感不到的,这样的诗别人就难懂了。例如有一首诗,题目叫《生活》,诗的内容就是一个字,叫‘网’。这样的诗很难理解。网是什么呢?网是张开的吧,也可以说爱情是网,什么都是网,生活是网,为什么是网,这里面要有个使你产生是网而不是别的什么的东西,有一种引起你想到网的媒介,这些东西被作者忽略了,作者没有交代清楚,读者就很难理解。”“出现这种情况,到底怪诗人还是怪别人?我看怪诗人,不能怪别人。”①在“新诗潮”刚刚浮出水面,各种争议不断的时刻,来自“归来”的诗坛领袖的这番言论对年轻一代诗人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心理冲击。两代人间的误会与分歧由此延伸,以至引出了黄翔等贵州诗人的激烈的声讨,当然也有了出自艾青的更为直接和尖锐的批评②。
相对于“朦胧诗”论争大潮中那些新颖宏阔的宣言式表述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的较量,两代诗人之间的这些搀杂着误会的分歧似乎并不十分严重,何况“事情过后,就烟消云散了”③,重要的还在于,受哺于法国先锋派艺术与西方象征主义的艾青无论怎样,似乎都不可能成为新时期中国新诗艺术探索的反对力量。
艾青夫人高瑛的一段解释值得我们注意:“艾青并无其他意思,谈论《网》这首诗是出于对青年人的爱护。写诗要让人读懂,是他一贯的主张。”④这的确道出了艾青诗歌观念的真相,完成于上世纪30年代的《诗论》中有论:“晦涩是由于感觉的半睡眠状态产生的;晦涩常常因为对事物的观察的忸怩与退缩的缘故而产生。”⑤“不要把诗写成谜语;不要使读者因你的表现的不充分与不明确而误解是艰深。把诗写得容易使人家看得懂,是诗人的义务。”⑥50年代,谈到“诗的形式问题”时,他批评“古文的构造,常常含糊不清,艰涩难懂,容易引起误解。”⑦诗人在新时期的诸多发言,也反复论及他对晦涩的警惕。他寄语青年诗人:“希望写好诗——让人看得懂。”⑧“一贯的主张”之说,绝对是事实。
在新时期之初的“朦胧诗”论争中,朦胧或者说晦涩是一个具有特定历史意味的指向,这就是对1949年以后愈演愈烈的政治口号般的明晰深感厌倦,他们试图通过对外国诗歌艺术尤其是现代主义诗艺的引进完成对这一僵化的、明白的反拨,从这个意义上看,朦胧与晦涩甚至具有某种历史的正义性。同样历经了历史教训的艾青如何看待这样的正义?他是否对中国新诗僵化的命运视而不见?当然不是。在新时期,艾青多次批评诗坛的沉寂:“假如说现在的诗要有什么突破,就是诗被大话、假话、谎话包围了。”“如果现在的诗都是一般化,调儿都差不多,或者说是陈词滥调,那就需要突破。”⑨“‘文化革命’中发表的诗歌完全没有个人的真正感情,净是标语口号。”⑩在《从“朦胧诗”谈起》一文中,更明确指出:“现在写朦胧诗的人和提倡写朦胧诗的人,提出的理由是为了突破,为了探索;要求把诗写得深刻一点,写得含蓄一些,写得有意境,写得有形象;反对把诗写得一望无遗,反对把诗写得一目了然,反对把诗写成满篇大白话。这些主张都是正确的。”(11)
这里其实有一个特定话语的使用问题,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艾青都没有理由为僵化政治的“明白”而辩护,他依然有着自己的艺术理想,只不过,在艾青的诗学词典里,作为僵化诗艺术对立面的应该叫做“含蓄”,而有别于“概念”的则称为“形象”。他认为:“含蓄是一种饱满的蕴藏,是子弹在枪膛里的沉默。”“不能把混沌与朦胧指为含蓄”(12)。“形象是文学艺术的开始。”“愈是具体的,愈是形象的;愈是抽象的,愈是概念的。”“形象孵育了一切的艺术手法:意象、象征、想象、联想……使宇宙万物在诗人的眼前相互呼应。”(13)“我认为绝不只是现在,而是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把写诗的注意力放在形象思维上。”(14)这里,词汇选择上的差异似乎也指示着一种诗学趣味上的分歧。
对20世纪任何的诗学词汇,我们都可以找出背后深远的“学术史”意蕴,也都可以进行严格的“知识考古”。正是在20世纪诗学发展的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找到质疑艾青的理由(也许后来的青年诗人也可以从这样的理由中获得鼓励),那就是晦涩、朦胧实际上已经成为了20世纪诗歌中一种重要的美学追求,有的称为“晦涩”,有的名之“含混”,有的形容为“诡论语言”。总之,在浪漫主义的明白晓畅之后,西方现代诗人试图传达一种思想的丰富、深密和多义。查尔斯·查德威克说过:“超验象征主义者的诗歌意象常常是晦涩含混的。这是一种故意的模糊,以便使读者的眼睛能远离现实集中在本体更念(essential Idea,这是个象征主义者们非常偏爱的柏拉图的术语)之上。”(15)克林斯·布鲁克斯认为:“诗人要表达的真理只能用诡论语言。”(16)威廉·燕卜荪专门讨论“含混”:“‘含混’本身可以意味着你的意思不肯定,意味着有意说好几种意义,意味着可能指二者之一或二者皆指,意味着一项陈述有多种意义。如果你愿意的话,能够把这种种意义分别开来是有用的,但是你在某一点上将它们分开所能解决的问题并不见得会比所能引起的问题更多,因此,我常常利用含混的含混性……”(17)
出于对抒情传统的一种偏爱,艾青的确没有更多注意诗歌智性化趋向中的繁复思想问题。在艾青的诗学词典里,频繁使用的还是情感、形象、想象、联想、含蓄之类,对朦胧与晦涩的戒备警惕显而易见。不过,即便如此,我依然认为艾青对朦胧与晦涩的警惕所昭示的诗学趣味的差异可能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严重。这里,需要我们透过词语的分歧洞察现代诗人更为共同的方向:对于走出古典之后的现代人生的承担和叙述。“时代与诗歌”始终是艾青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古诗是古人用他们的眼光看事物,用他们习惯的表现手法,写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写得再好,也不能代替我们。”“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歌手。假如我们只是满足于背诵古诗,我们等于没有存在。”(18)艾青对朦胧与晦涩的警戒,也不是为了降低现代诗歌的复杂和丰富,他说:“诗的语言必须饱含思想与情感;语言里面也必须富有暗示性和启示性。”(19)这又分明告诉我们,诗人艾青完全具有自己同样“丰富”的现代诗歌观念,尽管他强调的不是语言的“诡论”与繁复,但是他依然在现代诗歌艺术的道路上完成着自己,而且这样的追求也区别于一般意义的浪漫主义与所谓的现实主义。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能够全面地研读艾青的诗论,就不难发现,他决非朦胧与晦涩风格的简单的否定者,只不过更希望这样的诗歌应该包藏真切的有具体内涵的意义,而不是某种模糊思想的托词。在质疑了《生活》之后,他也表示:“当然,有些别人不懂的诗,也可以是写得很好的诗,像刚才提到的这位诗人,就有一些好诗。诗人感受到的,不为读者所理解,是会有的。”(20)“话又说回来,我不懂,我不一定是最高标准。人民都在受诗的教育,我也要不断受教育,今天不懂,明天懂。我不懂,请作者解释,也许能懂,因为写诗人的思考方式有时同看诗人的思考方式不一样。”(21)这话说得足够真诚。他还认为应该“把朦胧诗与难懂的诗区别开来”(22),“把‘朦胧诗’和一些‘怪诗’区别开来”,表示“我再三肯定‘朦胧诗’的存在”(23)。
二、朦胧与晦涩:艺术史的忧虑?
以上的解释有助于澄清艾青卷入“朦胧诗”论争的一些立场问题、人事关系问题以及因诗学趣味的分别所决定的诗人在当时的姿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艾青在本质上不属于论争的核心,甚至可以为一些不够详尽的“论争史”写作所省略。
但是,问题到此并没有完全解决。从30年代到80年代,艾青到底是长期质疑新诗晦涩与朦胧趋向的人,对此他从不讳言,以至这样的质疑还直接影响到了他对新兴的难能可贵的“新诗潮”的评价。一位具有良好艺术修养与诗歌经验且在先锋艺术的反叛精神的鼓励下一路走来的大家,为什么会在新的探索的时代发出质疑之声?除了人与人之间的误会,除了艺术趣味的分别,他还有没有自己独特的思想角度?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追问:同样推进着诗歌的现代理想,那么艾青警惕的是什么呢?
将一位严肃的艺术家的发言完全归结为人事关系上的误会,似乎缺乏绝对的说服力,而诗学趣味的分别也不能完全说明艾青对“流派”的超越态度(24)。我觉得应该就如同诗人决心跨越“流派”与“主义”提出属于自己的现代“诗论”一样,他对新诗潮的批评也主要是基于一种历史的观察,或者说是出于对中国诗歌曾经有过的创作问题的觉悟。
回顾中国新诗发展史,我们会发现,虽然晦涩或朦胧成为许多“现代”诗人追求的艺术目标,并非每一位诗人都真正理解了其中的内涵,更不是每一次晦涩或朦胧的努力都创造性地完成了现代诗艺术的建设,成为了中国艺术的经典。李金发诗歌最早给了中国读者古怪晦涩之感,但他的古怪晦涩在很多时候来源于他有限的中文能力与法文能力,这已经获得学界的证实(25)。戴望舒、卞之琳等人抗战以前的许多抒情诗篇虽有扑朔迷离之姿,但与其说他们是为了传达诗意的错综复杂,以错综复杂的意义来诱发我们对生命的深入的思考,还不如说一种吞吞吐吐、欲语还休的刻意的掩饰,诗人借助这样一种隐晦的方式来遮掩、回避现实人生中的某些不愿面对的尖锐性。
产生的问题可能也在这里。晦涩与朦胧,如果不是一种更为成熟的语言能力的结果反而是自我语言缺陷的无奈,如果不是思想与感受本身的丰富而恰恰成为了对某些具有压迫性的感受的遮掩与回避,那么,对于它的警惕和批评是不是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呢?艾青批评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象征派”与“现代派”,他认为戴望舒初期的作品“自怨自艾和无病呻吟”,“对时代的洪流是回避的。”(26)他批评李金发“爱用文言文写自由体的诗,甚至比中国古诗更难懂”(27),“他的很多诗是旅居法国时写的,比法国人写的更难懂,不能让他人理解”(28)。这样的评价自然不是出自艺术趣味的分别,而是一位有责任感的艺术家对于诗歌基本成效和贡献的真切把握。这里的逻辑显而易见:20世纪现代诗学对晦涩或朦胧的肯定并不能直接转移为所有晦涩或朦胧诗作的价值,西方现代诗歌的晦涩之美与朦胧之丽同样不能成为中国模仿者的艺术成就的佐证。
新时期之初,当新一代的中国诗人以更为复杂的艺术方式实现历史的“突围”之时,新的感受、新的语言出现了。而有意思的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李金发、象征派、现代派也“归来”了,晨曦与迷雾并呈,希望与忧虑同行,创造与仿造混杂,对于没有历史负担的“新诗潮”而言,挣扎求生是天赋人权;而对于历经诗史沧桑的艾青来说,鱼龙混杂的时代更需要一份艺术的清醒和理性,尤其当“有人仅仅因为难懂而喜欢”的时候,一种对未来艺术发展的隐忧便挥之不去了(29)。所以艾青不断试图告诉我们,还有比朦胧晦涩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以朦胧晦涩为惟一的艺术标准,并且以这样的似乎是理所当然“求新”来掩盖内涵上的空洞和玄虚,那真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噩梦。
当然,中国新时期诗歌史已经表明:“新诗潮”绝不能与李金发的古怪同日而语,对于北岛一代的中国诗人而言,因为朦胧而引发的历史的联想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实际。不过,作为一种潜在的逻辑可能,艾青在当时如此的推导似乎也有他的理由:中国新时期诗歌对外国诗歌艺术的引进是对1949年以后政治口号般的明晰的厌倦,朦胧与晦涩似乎就是反拨口号化明晰的必然,这样会形成一个印象:凡是有艺术性的诗歌都可能是朦胧或晦涩的,尤其是西方象征主义艺术,朦胧或晦涩几乎就是诗歌艺术性的代名词。这里所包含是历史的误会可能极大。
而当北岛之后,中国新诗越来越在“求新逐异”的道路上飙行,越来越多地刻画出自己似是而非各种的繁复形态之时,我们重温艾青关于朦胧晦涩的忧虑,不就有了新的启发?
三、诗的“形态”与“底线”
不过,艾青对“网”的批评似乎还不完全是朦胧与晦涩的问题,因为“网”的意义并不复杂,谈不到什么“不懂”,艾青能演绎说“网是什么呢?网是张开的吧,也可以说爱情是网,什么都是网”,恰恰就是道出了“网”的蕴涵。对于一位谙悉象征主义诗思的诗坛巨擘而言,在很多时候,“懂”应该不是什么问题。那么,艾青想要批评的还有什么呢?我以为是现代诗歌的基本“形态”问题。
中国现代新诗是在古典诗歌“雅言”中衰的末世起步的,古典“纯诗”的没落决定了它只能在“以文为诗”的方向上另辟蹊径,从胡适“作诗如作文”到艾青的“散文美”可谓是这一追求的清晰的线索。但是,以散文取代韵文,以自由取代格律,是不是从此就混淆了诗歌与散文,或者从此就取消了诗歌文体的独立性呢?显然不是,现代新诗依然需要传达一种韵律的美感,也需要自己思想的展开方式。
对于作为现代诗歌主流的自由诗而言,这样的韵律既需要唤起我们内在生命的旋律效应,又不再是固定的僵死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寻找和建构的难度,今天许多关于“诗体建设”的设想都试图从古典诗歌的固有模式中寻觅资源,殊不知这恰恰脱离了自由诗的特性,中国新诗需要在“固定模式”之外寻找旋律,这里的困难可想而知。
但较之于非固定旋律寻找的困难,更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却是另外一方面。这就是我们的情感和思想是否需要某种“展开”的形态,这里的形态不是指一般的遣词造句和诗行的排列,而是指与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思维的展开形式。也就是说,对于一首诗而言,灵感很可能是在一瞬间出现的,但是单独的感受的“点”却不能成为诗,诗人必须努力将这些感觉和思想铺陈开来,在一种有序的叙述中加以完成。整个这样一种叙述的形态,就可以称作是诗的“形态”,中国古代诗歌、西方的十四行诗歌都有它明确的启承转合的方式,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相对固定的形态。自由体诗没有固定的方式,但却必须有自己的展开形式——形态。现代诗歌的思想可能是繁复晦涩的,但重要的还在于如此的繁复应该怎样有效地组织起来,所以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瓦莱里提出,在现代诗歌创作中,应该是“旋律毫不间断地贯穿始终,语意关系始终符合于和声关系,思想的相互过渡好象比任何思想都更为重要。”(30)
提到艾青的诗学主张,一般的研究者都将注意力集中于他的“散文美”论述,其实关于现代新诗如何展开自己的思想“形态”问题,艾青有着一般人很少留意的深刻论述。
“连草鞋虫都要求着有自己的形态;每种存在物都具有一种自己独立的而又完整的形态。”(31)“形态”是艾青对诗歌艺术的一种要求,在《诗论》中,它被诗人放在“美学”而不是“形式”一部分加以论述,与“形态”相关的是关于内涵、风格、思维包括晦涩问题的讨论。在其他部分,艾青也论述说:诗歌“不只是感觉的断片”(32),“不要满足于捕捉感觉”,“不要成了摄影师:诗人必须是一个能把对于外界的感受与自己的感情思想融合起来的艺术家。”(33)“一首诗必须具有一种造型美”“一首诗是一个心灵的活的雕塑。”(34)“短诗就容易写吗?不,不能画好一张静物画的,不能画好一张大壁画。”“诗无论怎么短,即使只有一行,也必须具有完整的内容。”(35)“诗人应该有和镜子一样迅速而确定的感觉能力,——而且更应该有如画家一样的渗合自己情感的构图。”(36)造型、雕塑、构图,这些词语都一再提醒我们诗歌写作的“形态”意义。艾青强调的是诗歌的“完整形态”:这就是如何让诗歌充分地展开自己的思想,如何营造“意义”的丰富性、可感性和艺术的确切性。“不要把诗写成谜语”,“不要使读者因你的表现的不充分与不明确而误解是艰深。”(37)对晦涩的质疑就是在这个前提下作出的。在新时期,谈到晦涩问题之时,诗人阐述说,应该“善于把有意识的变形与画不准轮廓区别开来”,(38)画不准轮廓,依然还是“形态”建设的不足。艾青将诗歌能够清晰而完整地传达思想的形态称为“单纯”,“单纯”在这里不是指内涵与风格的简单,而是某种艺术感受与表达的集中和准确,艾青说:“单纯是诗人对于事物的态度的肯定,观察的正确,与在事象全体能取得统一的表现。它能引导读者对于诗得到饱满的感受和集中的理解。”(39)
今天,一些重提“纯诗”理想的人们对艾青的“散文美”不无质疑,在一些人看来,散文美是混淆了诗歌与散文的差异,对诗歌艺术的独立性形成冲击,其实,对诗歌艺术“形态”的如此的考究,本身就是对诗歌艺术独立性的探索,对于走出韵文束缚的中国新诗而言,所谓诗歌艺术的独立特质并不一定与语法的“非散文化”直接划上等号,它完全可能有另外的艺术表征,当人们关于“诗体”建设的理想依旧过分集中于与韵文形式相关的语言范围之时,恰恰在根本的意义上忽略了现代诗歌的“诗质”。
回头观察艾青对北岛《生活》的质疑,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生活》这样的一字诗固然具有自己联想的特色,但是却属于艾青所忧虑的“形态”的不足,我们可以将生活想象为一张“网”,但是它为什么是网而不是其他,诗人只有瞬间的“摄影”或“捕捉”,却没有更丰富的造型、雕塑与构图,因为它没有必要的造型,所以这种新颖却充满随意性的想象就不能集中而明确地引导读者的理解,读者完全可以任意命名“生活”:海、河、山、钓钩、碗、井、布、云、风……不一而足。
就是这样一种自由随意的联想很可能最终解构了我们创作的“底线”,令诗歌艺术陷入某种始料不及的尴尬。
当然以“新诗潮”诗人之人生执著,以北岛一代的理想情怀而论,创作的“底线”无疑是清晰的,而如《生活》这样一字诗的随意根本也不是北岛诗歌的常态(或许正是如此,诗人曾深感委屈,多年后提及依然情绪难平),那么,艾青的担忧是否属于杞人忧天呢?
不幸的是,历史的发展似乎再一次证实了艾青的忧虑。“第三代”以后,中国式的“后现代”游戏逐步消解了一切严肃的“建构”,包括诗歌“形态”的建构,甚至还包括诗歌本身,艾青当年的隐忧已经演变成了现实的某种“危机”。
在我看来,自“第三代”诗歌开始,不断遭受冲击的主要不是“散文化”与“非散文化”的争论,甚至不也是传统经常讨论的诗歌的韵律形式问题,而是一些更基本的诗歌原则,如诗歌“意义”——什么叫诗歌的意义,在嘲弄传统诗歌的“高雅”或者“严肃”之后,我们能否提供新的“意义”?甚至诗歌还需要不需要表达集中的“意义”,诗歌还需要不需要体验和关注人生,需要不需要思考生命,需要不需要在林林总总的艺术方式(如绘画、影视、舞台艺术)中自我标识,需要不需要有关于句子和词语处理的独特的处理,这些都一再被挪移、被改变,甚至被取消。我们几乎可以说,一切关于“诗”的底线都在消失之中。如果从1949年中国新诗日渐僵化的表达来看,以单个的词汇(或者说意象)传达诗人想象肯定属于历史的突破,但是从时至今日中国新诗不断突破艺术底线的后果来看,恰恰是这样的选择开启了诗歌自我解构的潜在流向,于是,艾青的质疑是否又可以说一种对未来的隐忧?而且是相当敏锐的充满洞察力的远见?
有意思的,多年以后,当同样严肃于诗歌艺术探索的“新诗潮”诗人也忧心忡忡地打量着这个变幻莫测的诗坛,而北岛更是痛心地指出“诗歌正在成为中产阶级的饭后甜点,是种大脑游戏,和心灵无关”之时(40),那么,艾青当年的姿态也就更显得意味深长了。
注释:
①艾青:《与青年诗人谈诗》,《艾青全集》第3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62、463页。
②参看艾青:《从“朦胧诗”谈起》,《艾青全集》第3卷。
③④程光炜:《艾青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20、519页。
⑤⑥《艾青全集》第3卷,第11、26页。
⑦艾青:《诗的形式问题》,《艾青全集》第3卷,第337页。
⑧艾青:《答〈诗刊〉问十九题》,《艾青全集》第3卷,第435页。
⑨艾青:《与青年诗人谈诗》,《艾青全集》第3卷,第460页。
⑩艾青:《祝贺》,《艾青全集》第3卷,第546页。
(11)艾青:《从“朦胧诗”谈起》,《艾青全集》第3卷,第535页。
(12)(13)艾青:《诗论》,《艾青全集》第3卷,第12、30、31页。
(14)艾青:《和诗歌爱好者谈诗》,《艾青全集》第3卷,第447页。
(15)查尔斯·查德威克:《象征主义》,见柳杨编评:《花非花——象征主义诗学》,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16)克林斯·布鲁克斯:《诡论语言》,《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98页。
(17)威廉·燕卜荪:《论含混》,《西方现代诗论》,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296页。
(18)艾青:《和诗歌爱好者谈诗》,《艾青全集》第3卷,第439页。
(19)艾青:《诗论》,《艾青全集》第3卷,第36页。
(20)艾青:《与青年诗人谈诗》,《艾青全集》第3卷,第463页。
(21)艾青:《答〈诗探索〉编者问》,《艾青全集》第3卷,第500页。
(22)艾青:《从“朦胧诗”谈起》,《艾青全集》第3卷,543页。
(23)艾青:《答〈中国青年报〉记者问》,《艾青全集》第3卷,第535页。
(24)在早年的《诗论?美学》里,他曾经明确提出了与“智性诗学”所不同的主张(二十三、二十四及二十五),不过,在另一方面,艾青又更愿意强调自己与“流派”、“主义”的不相容性,“自己不知道我是属于哪一流?哪一派?”(《我算是哪一流?哪一派?》,《艾青全集》第3卷第667页)。
(25)见卞之琳:《人与诗:忆旧说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0页。
(26)艾青:《望舒的诗》,《艾青全集》第3卷,第376页。
(27)艾青:《中国新诗六十年》,《艾青全集》第3卷,第480页。
(28)(29)艾青:《〈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诗集序》,《艾青全集》第3卷,第624、625页。
(30)瓦莱里:《纯诗》,杨匡汉、刘福春编《西方现代诗论》,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222页。
(31)(36)(37)艾青:《诗论》,《艾青全集》第3卷,第11、26、26页。
(32)(33)(34)(35)(39)《艾青全集》第3卷,第24、15、25、25、26、11页。
(38)艾青:《从“朦胧诗”谈起》,《艾青全集》第3卷,第533页。
(40)翟
:《中文是我惟一的行李——北岛访谈》,《书城》2003年第2期。这段评论为北岛在摩洛哥阿格那国际诗歌奖(International Poetry Argana Award)上的受奖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