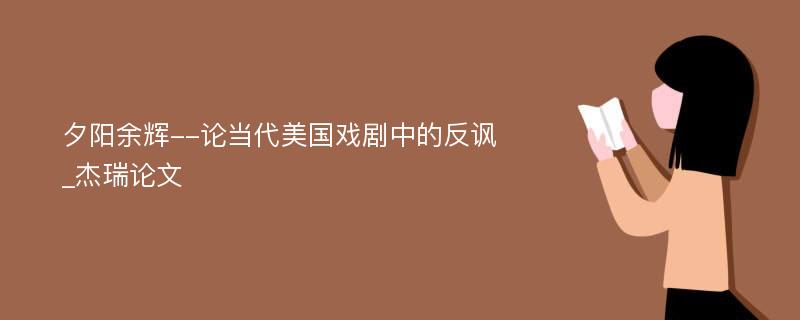
夕阳余晖——论当代美国剧场中的反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剧论文,场中论文,夕阳论文,当代论文,余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文化中,“反讽”一方面是和古希腊文明同龄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文学现代性的决定性标志”(注:Behler,Ernst,Irony andthe Discourse of Modermity,Washington: the
Umiversity
ofWashington Press,1990,p.73,p.71.)。本文以反讽的原初形式——苏格拉底式反讽为参照,以美国当代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和萨姆·谢泼德各自一部代表作为例,同时结合他们以及其他剧作家的部分作品,分析反讽在当代美国剧场中产生的变型,并从后现代角度探讨产生变型的原因。
“反讽”一词在希腊语(eironeia)中原义为“伪装的无知,虚假的谦逊”,与之拼写相似、词义相关的是“施讽者”(eiron)。 史载最早的施讽者为苏格拉底。他在雅典的大街上拦住那些衣冠楚楚、趾高气扬的年轻人,说自己是“以无知自我放纵于胡乱猜想中”的“蠢人”(注:Plato,Great Dialogues of Plato,ed.,Eric H.Warmington &Philip G.Rouse,trans.,W.H.D.Rouse,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Inc.,1956,p.115,p.115,p.115.),恳切地向他们请教关于人生和真理的问题。一系列追根究底的问答过后,青年们张口结舌,发现自己引以为荣的学识原来不堪一击。他们此时的窘态和先前的自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苏格拉底在提问中表现出的大智慧与他提问前自述的卑微无知之间亦造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对比和反差构成的便是原初意义上的反讽。“施讽者”苏格拉底在自贬身份的基础上, 用诘问的方式完成反讽, 以其辛辣的效果刺激他的“受讽者”(alazon)们,打破了他们自得的心境和学富五车的傲态,同时也使他们从一知半解的求学态度中幡然悔悟,进而开始对“真理”的踏实追求。
现代西方文明与古希腊文明一脉相承,而苏格拉底式反讽对后世的影响,正如尼采所喻,“好似在夕阳中逐渐拉长的影子”(注:Behler,Ernst,Irony and the Discourse of Modermity,Washington:the Um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0,p.73,p.71.),虽然随时光流逝变形黯淡,却不轻易消失。时隔2000多年,在后现代的美国舞台上,仍可见这种反讽的遗风,阿尔比的《动物园故事》和谢泼德的《罪恶之齿》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爱德华·阿尔比在50年代后期“以其杰出的独幕剧成名”后,被誉为“在国际上最成功的美国剧作家”(注:Cohn, Ruby, ed.,Contemporary Dramatists,New York:St.James Press Ltd.,1988,p.12,p.482.),独幕剧《动物园故事》也因此成为其代表作之一,并跻身当代美国戏剧经典作品的行列。剧中一个人物的谈话和行动严重动摇了另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建构,两者交谈前后的精神状况悬殊。从反讽的角度看,他们分别饰演了施讽者和受讽者的角色。
幕启时,40多岁的教科书编辑彼得手持烟斗,舒适地坐在公园的长凳上看书。此时,“神情极为疲惫的”杰瑞走过来和他攀谈。开始,彼得出于礼貌,勉强应付这个流浪汉模样的粗鲁汉子。杰瑞时而以近似无礼的直率惹恼彼得,时而又心平气和地与之“交谈”,将话题引向诸如婚姻、家庭、性爱等敏感问题,使彼得渐渐不安起来,而他并不知道这是由于杰瑞看似不经的语言已动摇了他在这些方面的基本生活信念。
杰瑞谈到“拥有”,将彼得的“所有”和自己的作了一番对比:前者是“一个妻子,两个女儿,两只猫,两只鹦鹉”;后者是“厕所用具”和“一个罐头起子,一把刀,两把叉子,两把勺子”(注: Albee,Edward,The Zoo Story and Other Plays,London,Cape,1962,p.23。以下引自该书者仅在文中注明页码。)等厨房用具。杰瑞用并列结构先把彼得的妻儿与宠物置于同等地位,再把彼得温情脉脉的家庭成员与自己毫无生气的生活用具相提并论,以不合常规的遣词造句方式给彼得的家庭观念进行了荒诞的定位,从而使观念本身带上了荒诞的色彩。
杰瑞以同样的方式嘲弄夫妻生活中的性爱。他总结出彼得婚后不再“需要”黄色画片的原因:“黄色画片对于孩子和成人的价值区别”在于,“你小时候用画片代替真正的经历,而你长大后用真正的经历作为胡思乱想的替代品”(Z.27)。在这里,杰瑞以颠倒的逻辑关系把夫妻生活说成黄色画片的替代品,亦即把现实定义为空想的替代品,这事实上是把爱情生活的物质基础虚空化。而对于爱情的精神方面,杰瑞则施以更进一步的嘲讽。他先按彼得的思路进行设问:“我爱那些小妞儿吗”,然后肯定作答:“是的,我爱她们”,随即又补充了一句:“爱一个钟头左右”(Z.25)。
这样,杰瑞消解了彼得关于爱情的种种美好感受,使彼得在不安中急于转换话题,便问起杰瑞提过数次的动物园的故事,杰瑞却用两千多个单词讲了一个“杰瑞和狗”的故事。他告诉彼得,房东的狗老想咬他,于是他试着喂它,企图用“爱”建立“理解”。然而狗吃饱后继续咬他,自己恼怒之余给它下了药。狗大病一场,就此两者互不侵犯。故事并不复杂,但杰瑞竭尽语言之能事描述他与狗之间的仇视和冲突,使彼得的反应由“不耐烦”、“不快”发展为“强烈反感”和“被催眠”。这说明彼得已开始用自己的真实情绪而非不瘟不火的社交辞令与杰瑞交流,他的负面反应正是以自我固有的思维体系对抗杰瑞这一外来消解力量的结果,而到“被催眠”时,他的防御体系已放弃了抵抗,开始消极接受。
杰瑞总结说,狗死里逃生后,和他“带着伤感和怀疑的混合心态对视”良久,相互间“得到了理解”——一种“非常悲哀的理解”,因为他和狗从此各走各的路,“既不相爱也不相害,因为我们不再试着接近对方”(Z.36)。杰瑞向彼得承认,他先用“爱”,再用“残忍”,终于成功地使狗理解了他不愿被咬的心情,但此后狗对他的漠然又使他痛感“失落”。他就“爱”这个价值观体系中的重要概念向彼得提出质疑:“试着喂那狗就是一种爱的行为吗?还有,难道那狗想咬我就不可能是一种爱的表示?如果我们误解到这份儿上,好吧,当初我们干嘛发明爱这个词?”(Z.36)
“爱”是耶稣用以救世的法宝,是基督教文化的首要精神柱石,而杰瑞用反问的方式否定了其正确性与必要性,这已经超出了彼得的心理承受范围。他在杰瑞的诘问下,先是“浑浑噩噩地”说,“我……我不理解……我想我不……”。在支离破碎的程式性反应后,他失控地爆发了——“几乎眼泪汪汪地”大叫:“我不理解!”,“我什么也不要听了!”(Z.36)。这和他原先平静而自信的姿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可见杰瑞的故事对他的震撼。虽然此时他已摆脱了听故事时的“被催眠”状态,但内心世界的防御战却更为激烈。
杰瑞见语言终未使彼得放弃他的防御姿态,便开始采取无礼的行动。他坐在彼得的长凳上,边说话边把彼得往外推,最后要求彼得把凳子完全让给他。在各种侮辱性语言的进一步刺激下,彼得的“愤怒和自我意识”终于突破了理性的束缚。他不再考虑两个“成年人”争一张凳子的事实在别人看来多么“荒唐”,拾起了杰瑞扔在他脚下“干一架”用的匕首。杰瑞就势扑过去“将自己钉在刀上”。这致命一击使彼得在恐惧中陷入疯狂的尖叫,而垂死的杰瑞却“变换了表情”,“舒展了身体”,“微笑着”说:“彼得……谢谢你。我投奔了你,(他笑了笑,极微弱地)你安慰了我。亲爱的彼得。”(Z.47—48)最终,彼得在“一声可怜的哭嚎”中奔下台去,而杰瑞则平静地死去。
至此,彼得精神世界的种种基本信念被杰瑞用怪诞尖锐的语言和鲜血淋漓的行动猛烈动摇了。幕启时,前者怡然自得,后者躁动不安,语无伦次,而剧终时,后者心满意足,前者却歇斯底里,言不成句。前后情况之间的强烈反差构成了上文所述的反讽。此例中的施讽者杰瑞和苏格拉底一样,借各种问题和议论的组合,迫使其受讽者彼得按照“不合常规”的角度重新审视价值观体系中的既成概念,从而以意想不到的力量对之进行消解。而彼得正如被苏格拉底问住的青年们,发现值得可怜的不是看来卑微的对方,而是意欲助人的自己。施讽者和受讽者之间的交流已“超越了彼得井然有序的世界观的极限”,因此,彼得“无法只把杰瑞当作神经病或讨厌鬼而不予理睬”(注:
Dictionary ofLiterary Biography,vol.7,partI,p.5,p.5.)。如杰瑞所说,彼得“永远失去了那张长凳”(Z.47),而与之同时失去的,还有他坐在长凳上阅读时“非常愉快、非常满足的”(Z.45)心情——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能够孕育出这种心情的稳定的中产阶层世界观。
《动物园故事》中的反讽自始至终以施讽者和受讽者之间的正面冲突直接进行,而在十多年后的一部两幕剧《罪恶之齿》中,施讽者仅以其存在就在第一幕中对受讽者产生了作用,而第二幕中施讽者的出现大大强化了这一作用。
《罪恶之齿》是当代极富盛名的戏剧家萨姆·谢泼德“最感人”(注:Cohn,Ruby,ed.,Contemporary Dramatists, New York:St.James Press Ltd.,1988,p.12,p.482.)的一部作品。 该剧主人公豪斯是位已成名的摇滚歌星,击败过无数对手,拥有大片“地盘”,被“圈内人”誉为“天王级”的“英雄”。而对他进行挑战的“吉普赛”歌手克罗则是“业余水平”的“无名小卒”。在剧本开头部分,克罗的挑战看来如乐评人杰所说,“是在找死”(注:Shepard,Sam,The Tooth of Crime,in The Seven Plays,New York:Bantam,1981,p.211 。以下引自该书者仅在文中注明页码。)。豪斯受过正式的专业训练,信奉“规矩”这一行业竞争体系的运行规范,认为比赛“不讲规矩,就是犯罪”(T.216)。然而,第一幕中克罗虽未出场, 却以其破坏“规矩”、连连逼近的消息使豪斯对自己赖以成名的“规矩”——那一套价值体系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怀疑。首先,克罗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使他看到了往日的自己。他在克罗的反衬下发现自己已被所谓的“成功”软化,失去了一度拥有的同样的勇气,开始怀疑成功的价值。同时,克罗“就像当年的我”,这使他开始考虑与之决战的意义何在。“他是我兄弟”,而“我得打败他,要么他打败我”,这无异于“拿刀子捅自己”,无异于“自杀”(T.224)。其次, 克罗破坏了“规矩”,却能一路顺风地向自己逼近,这种按“规矩”不应发生、“不可置信”的事实动摇了豪斯对那套体系的信心。另一方面,克罗的进攻严重威胁了成功赋予豪斯的安全感,使他重新审视自己在系统中的生存方式。他发现,自己的成功是按照规矩定义的,一旦这规矩被人破坏,成功及其所带来的一切便都失去了意义。于是他哀叹:“我什么也没挣到。一切就那么发生了。就像牌发下来。我从来没有作过选择。”(T.218)
如果说第一幕中克罗在后台的存在已动摇了豪斯的基本信念,那么第二幕他出场后对豪斯精神建构的打击则是毁灭性的。第二幕以豪斯与克罗之间的一番谈话开始,其中克罗和《动物园故事》中的杰瑞一样,无情嘲笑了对方奉为圭臬的信念。克罗对豪斯苦心经营的“形象”不屑一顾,“哈哈大笑着”说:“形象炮已经炸过了,伙计。再没合适那个炮眼儿的引信了。”(T.229)他告诉豪斯,歌手是“圈内人”、 听众是“门外汉”的内外划分已经过时。克罗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和豪斯之间的区别:“你选择适合自己歌路的听众。我不是。我可以调整自己的风格来适应他们的品味。”(T.230)对此,豪斯觉得“不可思议”, 但他悲哀地意识到“门外汉已成了圈内人”,而自己这个原来的“圈内人”正受着他所认为的“门外汉”克罗的冲击。
谈话使豪斯沮丧而困惑,但他还没有完全丧失信心。他坚持认为“没有心灵、只有蛮力”的克罗是“可悲的”。他们请来了裁判,进行短兵相接的比赛。赛前,豪斯对克罗宣称,“这个星球上没人能用任何武器或机器赢我。……你死定了”(T.234)。然而,第一轮比赛中, 克罗用喷涌而出的夸张短语描述了一个“小子”的心理变异,给豪斯捏造了一段不堪回首的成长过程。豪斯试图据理力争,却在克罗的唇枪舌箭中插不上嘴。裁判鸣笛,称之为“干净利落的进攻”。豪斯质问裁判“怎么能给一个说谎精加分”,裁判答道,“我只判分给胜利者”(T.237 )。豪斯关于“历史真实性”的信念破灭在克罗仅凭“浮华和张力”取得的胜利中。这时,豪斯仍寄予信心的是艺术传统和文化底蕴。他深知克罗对此的无知和自己在这方面的实力。因此,第二轮交战一开始,豪斯便直指美国流行音乐的源头,启用了“古老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乡村布鲁斯”,演绎出“佐治亚、南加州、褚红旷野。一曲悲歌,传唱数年”。情景交融的“真正的旋律”逼得克罗“紧张起来”,而豪斯接下来对克罗的指责更是一语中的:“你忘了本”,“你这一无所知的滑稽歌手,踩着假模假式的慢舞步”(T.238—239)正当克罗看似已尽失还口之力时,裁判宣布这一轮为平局,“因为它让我摸不着头脑”。豪斯未及争辩,克罗已开始了第三轮的进攻。他接着上一轮豪斯没能取胜的事实指出,豪斯视为艺术生命的“节奏”和“布鲁斯”在当今已成“空想”,而豪斯“买不来时代”,只能“抱着空想布鲁斯无处藏身”。对于一个讲求“艺术性”的音乐人来说,否定其艺术准则就是否定艺术生命,艺术准则的过时相当于艺术生命的完结。克罗在此基础上又对豪斯发出了致命一击, 被裁判定为TKO(拳击比赛中的“技术得胜”或“技术击倒”,指一方虽未被击倒,但已无招架之力时,裁判可宣布对方“技术得胜”),豪斯因此不战而败,全场皆输。令豪斯愤怒的是,这一击竟是一通毫无意义的攻击谩骂。狂怒之下,他拔枪射杀裁判,彻底打破了竞赛“规矩”,宣称他和克罗一样“现在是个‘吉普赛’”了。
至此,克罗的胜利已使豪斯所有的艺术信念破产。豪斯痛苦地向他曾瞧不起的克罗低了头,承认“我没你精。没错,你赢我赢得对。”他甚至孤注一掷地交出了赖以“生存”的“地盘”,从而换取克罗的指导,“学习吉普赛风格”,以期东山再起。正是这“学习”把豪斯推入了完全绝望的境地。
在克罗的批评指教下,豪斯渐渐悟出了他击败自己的奥秘竟是“空虚”,在想象中,他看到了按照克罗风格塑造出的粗鄙、冷酷、无情的新的自我,“那不是我!那不是我!那不是我!那不是我!”(T.247)他狂喊着崩溃了。他能够忍受失败,却无法忍受被“空虚”战胜,更无法生存在以“空虚”为前提的现实中。自杀前,他在绝望中真正地服输了:“你赢得好。所有这一切。身体和灵魂。这看不见的金奖,这集得起的折磨。都是你的了。你是赢家,我是输家。”(T.249)
就这样,幕启时的“英雄”一败涂地,而起初的“小卒”却直捣黄龙。前者在精神上被打倒,在物质上被消灭,后者取得了彻底胜利。两者间的前后对比营造出强烈得几乎过分的反讽氛围。施讽者克罗用语言、更用因自身存在而产生的不争事实,消解甚至毁灭了受讽者豪斯精神世界的基本建构。
《动物园故事》和《罪恶之齿》在当代美国剧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前者“以微缩的形式包含了阿尔比所关注的绝大部分信念”(注: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vol.7,partI.p.5,p.5.),被《美国文学选集》收为压卷之篇,无论对于阿尔比个人或当代美国剧都有一定的代表性。《罪恶之齿》既是谢泼德“个人最喜爱的作品”(注: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riticism,vol.17,p.443,p.447.),也是他“上演率最高的剧作”(注:Conn,Peter,Literature in Americ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479 , p.447.),并为他赢得了欧比戏剧奖,是一部得到了剧作家本人、观众群和专家共同首肯的佳作。这两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相去甚远,艺术风格各有千秋,但在情节建构上都有相似的反讽模式,表现为原先的尊者被初始的卑者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杰瑞的胡言乱言和自杀行为,克罗的嘶声谩骂和犯规行为——击溃。这一相似模式的出现既非罕事,亦非纯属巧合。在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美国舞台上,含有上述反讽模式的剧作不一而足。
在阿尔比1962年轰动百老汇的名作《谁怕维吉尼亚·伍尔芙》中,施讽者乔治人到中年,受制于放荡的河东狮,而受讽者尼克年轻自信,爱妻小鸟依人。在与乔治的无心“闲聊”中,尼克渐渐脱离了对婚姻家庭的满足感,嗫嚅道:“我老婆的确屁股小”(注:Albee,Edward,Whoi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New York:Signet,1983,p.93,p.93,p.110.),过后又承认结婚并非出于爱情:“我娶她是因为她有了”(注:Albee,Edward,Who i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New
York:Signet,1983,p.93,p.93,p.110.) ,最后终于道破了促成这段“幸福”婚姻的真正原因:“我岳父很有钱”(注:Albee,Edward, Who i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New York:Signet,1983,p.93,p.93 ,p.110.) 。短短半小时内,婚姻生活中的失败者乔治用不着边际的谈话瓦解了尼克原先的成功者状态。
对于丰产的萨姆·谢泼德,在他的其它作品中找到这类反讽的例证更非难事。荣膺1979年普利策戏剧奖的《被葬的孩子》就是一例。其中受讽者是回老家探亲的青年温斯,而施讽者是他那些或酗酒、或乱伦、或病态、或弱智的家人群体。温斯和这些他十多年来津津乐道但未再谋面的家人相聚不到24个小时,便被这个家庭不可告人的过去及难堪的现状击垮。他关于“老家”、“老祖母”和“温馨童年”的美好感觉被打得粉碎。幕落时,这个原本健康乐观的青年僵直地躺在祖父的尸体边,心如死灰。同样,在1985年的新作《思想的谎言》中,一群精神变态者或做白日梦者组成了一个施讽群体,而唯一思维正常的人物弗兰克成了受讽者,因为他试图“理性地、现实地”看待问题,结果却陷入了孤独而迷惑的境地。
上述反讽模式在与阿尔比和谢泼德同时期的其他美国剧作家的作品中亦屡见不鲜。杰克·吉尔伯1959年推出的《联系》被誉为“外百老汇首创剧作之一”。其中,两个吸毒者不停地展示他们“不成人样、毫无秩序的生活”,通过对走人歧途的吸毒生活的揭示,使其他“正常”人物在自己井然有序的生活“正道”中发现了“同样可怕的空虚”(注:Berkowitz,Gerald M.,American Drama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Harlow:Longman Group UK Ltd.,1992,p.124.) 。在1965年兰福德·威尔森的《路德洛集市》中,受讽者是一个以严肃态度对待爱情婚姻的女子,而施讽者则是她行为放荡的同屋。在交谈中,后者通过对自己众多男友和随意爱情生活的回顾,使前者恼怒地发现,自己因对婚姻态度认真而清心寡欲,其实却过着“一段糟透了的爱情生活”。(注:Wilson,Langford,Ludlow Fair,in Balm in Gilead andOther Plays,New York:Hill and Wang,p.78 ,p.78.)在1969 年阿瑟·考皮特的《印第安人》中,受讽者是美国大众文化中的英雄——垦荒时期勇敢的“水牛比尔”,而施讽者则是被看作未开化的印第安人。前者原先以为是提携落后民族的天使,但在与后者的接触中渐渐惊恐地意识到,自己创造的、美国大众引以为荣的“西部奇观”并非白人文明给印第安人的慷慨帮助,而是对其固有文明的毁灭性灾难。戴维·马枚特1974年的《芝加哥性变态》中有两个见解迥异的施讽者——一个冷血的浪子和一个火热的极端女权主义者,但他们对正常的性爱抱着同样又恨又怕的态度。在他们的游说下,一对爱侣逐渐丧失了对共同生活的信心,最终分手,成了两个性变态者的受讽者。
以上剧作取材广泛,手法各异,剧作家也不同属于某个创作群体或艺术流派,他们共享的只有当代美国剧场。正是这一共性使本文探讨的反讽模式出现在这些作品中,也正是这一共性使其中的反讽和苏格拉底的反讽相比,在效果上呈现出方向性差异。苏格拉底的某位受讽者这样描述他对反讽的感受:“它开始看来可能是纯粹的胡说八道,包裹在那样的词句中,仿佛一副喧闹的森林之神嘴脸。”(注:Plato, GreatDialogues of Plato,ed.,Eric H.Warmington & Philip G.Rouse,trans.,W.H.D.Rouse,New York:The New American Library,Inc.,1956,p.115,p.115,p.115.)这段话对当代施讽者的言行颇为适用;接着——“但一旦它们被打开,你沉浸其中,会发现他的话中充满真义”(注:Wilson,Langford,Ludlow Fair,in Balm in Gilead
andOther Plays,New York:Hill and Wang,p.78,p.78,p.78.)——这在当代反讽中就只能勉强应景了。而今古反讽间相去最远之处可见于雅典青年的最后一段评论:“接下来的感觉极为神圣,包含着美德的最佳形象,触到人心最深处,事实上,对于任何修身以冀崇高美好者,方方面面均受益良多。”彼得等受讽者虽然被“触到人心最深处”,但他们的感觉非关神圣,无涉美德,更不能从那些精神上或多或少有些缺陷的施讽者处得到“崇高美好”的教益。另一方面,苏格拉底的受讽者们被他“如爱人般地戏弄后”,不嗔反笑,“也以热爱回报他”(注:Wilson,Langford,Ludlow Fair,in Balm in Gilead and Other Plays,NewYork:Hill and Wang,p.78,p.78,p.78.),施讽者的胜利呈现出积极的意义。这也是当代反讽中缺失的成份。在上述两例中受讽者或崩溃或自杀,施讽者胜利的意义也随着杰瑞的鲜血汨汨流逝,随着豪斯死前对克罗将来与自己同命运的预言化为乌有。由此可见,当代反讽虽然在形式上秉承古风,但在效果上已背道而驰。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与其说因为台上施讽者先天不足,倒不如说因为幕后设计者力有不逮。舞台上的反讽虽由杰瑞、克罗等角色施行,但真正的施讽者却是阿尔比、谢泼德等剧作家。与他们的古希腊反讽鼻祖相比,不同的心理基础造就了不同的反讽动机,导致了不同的反讽效果。苏格拉底是“真理和美德谦逊而勇敢的追求者”(注:Thompson,Alan Reynolds,The Dry Mock:A Study ofIrony in Drama,Berkeley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8;reprinted by Porcupine Press Inc.,Philadelphia,PA,1980,p.28.),笃信理性的力量, 认为藉此可以治愈“愚蠢罪恶这些并非与身俱来的可治之症”(注:Highet,Gilbert,The Anatomy of Satire,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p.236,pp.56-57.)。而身处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剧作家们正经受着后现代浪潮的冲击,“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支撑着西方人精神世界大厦的几根重要支柱——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以及对语言的信仰纷纷倒塌”(注:柳鸣九《二十世纪文学中的荒诞》,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4页。),真善美不再是理想,而是空想。苏格拉底怀着乐观的信心,“以耐心承受痛苦”(注:Lempriere,J., ed., Lemprere'sClassicalDictionary,London & Bost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72.),致力于帮助他的同胞们抛弃自满的障目之叶,走上追求真理的正道。他宣称:“奥林匹克的胜利者们使他们的国人在表面上更快乐,而我使你们在现实中如此。”(注:Plato,Great Dialogues of Plato,ed., Eric H.Warmington & Philip G.Rouse,trans.,W.H.D.Rouse,New York:The New American Library,Inc.,1956,p.115,p.115,p.115.)使国人“快乐”是苏格拉底的心愿,也是他使用反讽的终极目的。今古施讽者正是在这一点上分道扬镳。
后现代剧作家面对的是一个“被倏然褫夺了幻景和光明的世界”,人在其中成了“不可挽回的遭放逐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关于失去故园的记忆,也不复抱有踏上神许福地的希望”,由此“人和生活的割裂……实实在在造成了荒诞的感觉”(注:Albert Camus,Le Mythe
deSisvphe(Paris:Gallimard,1942),from Esslin,Martin,The Theatreof the Absurd,3rd ed.,Middlesex:Penguin Books Ltd.,1983,p.5.),这种荒诞的感觉正是上述剧作诞生时的西方社会的时代心理背景。而在美国,50年代中期严酷的冷战气氛将罗森堡推上电椅,1963年的种族仇恨又使马丁·路德·金饮弹身亡,长达14年的越战打伤了财政赤字和爱国主义(注:Esslin,Martin,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3rded.,Middlesex:Penguin Books Ltd.,1983,p.266,p.4,p.361,p.363.)……终于,1961 年尚无二战后英法式深刻“幻灭感”的美国人也在劫难逃地站到了自己文化的对立面,“每条既定价值标准都在不可预知的取舍探索中遭到质疑”(注:Conn, Peter, Literature inAmeric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479,p.449,p.447.)。数年前,欧洲荒诞派剧作家面临相同的疑问,“用作品最敏感地反映折射出时代的忧虑焦点”(注:Esslin,Martin, TheTheatre of the Absurd,3rd ed.,Middlesex:Penguin Books Ltd.,1983,p.266,p.4,p.361,p.363.),此时,他们作品中“表现的存在的随意性、矛盾性和不可知性”被“美国新一代剧作家认同”(注:Hassan,Ihab,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1947-1972,New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Inc.,1973,p.140,p.140.)。爱德华·阿尔比、杰克·吉尔伯、阿瑟·考皮特、兰福德·威尔森、萨姆·谢泼德、戴维·马枚特等人正是这一代剧作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怀着对历史、 政治、 意识形态的疑问”(注:Hassan,Ihab,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1947- 1972, 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Inc.,1973,p.140,p.140.)创作,其作品正如阿尔比所称,是“社会批评卷册中的章节”,是“对一种失序文明的剖析,其中,爱和英雄主义已可想而知地逃逸如飞了”。(注:Conn,Peter,Literature in America,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479,p.449,p.447.)
同样“可想而知地”,构建于这样的时代社会心理上的作品不可能含有古希腊先哲的信心与爱心。幕后施讽者的“营养不良”导致了幕前施讽者凯旋曲中的悲音。苏格拉底的反讽“诚挚”而“轻柔”,让受讽者“能相信它就是真理的流露”,因其“虽然使他们困惑,却极少使他们受伤”(注:Highet,Gilbert,The Anatomy of Satire,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p.236,pp.56-57.); 而后现代舞台上的反讽用病态取代了“诚挚”,以辛辣更替了“轻柔”,受讽者在强烈的刺激下一败涂地,痛感失落。
然而这只是反讽的台上效果,并非幕后真正施讽者的目的所在。正如杰瑞、克罗不是真正的施讽者,仓皇下台的彼得和绝望自杀的豪斯也不是终极意义上的受讽者一样。对于戏剧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和特殊的文学形式,观众是实现其意义的关键因素。而在后现代剧场中,随着各种新兴戏剧理论对舞台中心的消解,观众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上述各例中,他们才是剧场中真正的受讽者,是剧作家们施行反讽的目的所在。
施行这一深层意义上的反讽主要靠观众把自己等同于台上受讽者的心理倾向。尽管布莱希特等戏剧理论家强调观众不应该“入戏”,但“把自己与角色等同的倾向源自人类天性中的基本心理特征”(注:Esslin,Martin,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3rd ed.,Middlesex:Penguin Books Ltd.,1983,p.266,p.4,p.361,p.363.),观众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轻易放弃。在上述各剧中,施讽者的言行不是费解,就是病态,观众一般无法把自己与他们等同。相对而言,受讽者基本属于较为“正常”的角色,拥有被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体系,观众自然倾向于把自己与他们置于同一地位。那么,在台上的反讽施行的同时,台下受讽者的精神世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他们不会像彼得那样失魂落魄地逃走,走出剧院时,他们却也“在无望的迷茫中摇头不已”(注: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riticism,vol.25,p.32,p.32.)。传统剧场给观众养成了被动接受的习惯:“他们不会去费神理解,除非剧作家在普遍接受的舞台常规范围内,以某种相当明显的方式说明自己想说的话。”(注: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riticism,vol.25,p.32,p.32.) 而上述剧本中不合常规的反讽情节却只给他们“几根断续的线索”,迫使他们不得不“运用自己的创造性能力”,把那些线索“装成一幅有意义的图案”(注:Esslin,Martin,The Theatreof the Absurd,3rd ed.,Middlesex:Penguin Books Ltd.,1983,p.266,p.4,p.361,p.363.)。试想, 他们“在办公室里度过了发烧的一天后”,为看戏“甘愿忍受纷乱交通的折磨,从车流中杀开道路,在餐桌上匆匆果腹”(注:Hatlen,Theodore W.,Orientation to theTheatre,4th ed.,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Prentice-Hall,Inc.,1987,p.20.),其结果却是茫然若失,这本身岂非一种反讽?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幕后与台下间的深层反讽,使台上的反讽才不仅限于一种情节建构,更成为富有感染力的艺术表现手法。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剧作家创作时并没有给自己的作品贴上明确的“反讽”标签。本文中的“施讽”只用于指称“创作出具有反讽意味剧情的事实”。反讽作为“在形式上”构成后现代这一“艺术、哲学和社会现象”的“话语”(注:《后现代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70页。),在后现代社会中已俯拾即是, 在后现代剧场更是无所不在。因此,剧作家在无意间启用这一形式也不足为怪。
由此可见,当代美国剧场中的反讽虽在形式上隐约沿用了苏格拉底的传统形式,但“当代美国的精神荒原”(注:ContemporaryLiterature Criticism,vol.17,p.443,p.447.)已不再能滋养其中的真挚温情。夕阳余晖终不堪黄昏将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