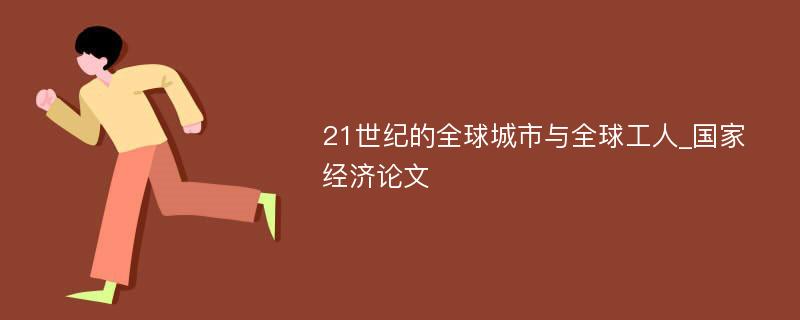
21世纪的全球城市和全球工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球论文,工人论文,世纪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工人的世界中。过去一代人经历的全球性社会变革,已经见证了工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了世界上占据绝大多数的阶级。1970-2010年间,发达国家工人的数量从大约3亿增加到了5亿,而在贫穷国家中,他们的数量——包括他们当时的眷属在内——从11亿增加到了25亿至30亿之间。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不再从事农业活动,我们有史以来也首次生活在了城市之中。在过去的10年中,全球的发展也或多或少地向城市而不是向乡村倾斜。当然,城市的社会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但是城镇和城市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基本事实也同样不容忽视。本文将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主要就这两个方面展开论述。所谓宏观,即本文尝试从全球视野而不是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角度来勾勒出这些变化趋势。所谓微观,即本文没有宏大的理论构建,相反,本文试图归纳数据、提炼共性、获得启发,由此进行更加深入的剖析。
我们将首先勾勒出全球城市化的模式,然后将审视城市是如何发展的,由此我们可以继续探讨城市生活的本质问题——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内——以及它与全球资本主义进程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而,我们将更加简略地探讨乡村以及它是如何与全球经济体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最后,我们将提出工人阶级组织的全球模式问题。
全球城市化
城市化与资本主义发展密切相关。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中心常常是一些特例而不具备一定的规模。因此,城市化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沿革资本主义发展尤其是工业发展的模式,城市化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从它在西欧和美国东海岸的根据地逐渐向外蔓延。这一点体现在欧洲(尤其是西欧)、北美和大洋洲较早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城镇中。所有国家中城市化最为成熟的是英国。其在1851年的统计数据就已经表明,它由于50%的人口生活在城镇之中而名副其实地率先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重要的城市化社会。在1914年之前,德国成为了紧随其后的第二个重要的经济体。
在当时发达国家中的人看来,19世纪似乎是一个城市林立的时代,但是在全球视野中它们还只是一些特例,还算不上具备了一定规模。在20世纪,尽管拉丁美洲的经济形势多有起伏,但它已经开始步入了城市化的道路。今天,欧洲、北美、大洋洲和拉丁美洲均已高度地城市化,在未来尽管在城市组织的形式上可能会有更大的变化,但在城市的分布比重上只会出现很小的变化。大的变化将会发生在非洲和亚洲。尽管在20世纪上半叶城市的数量有所增长,但是这些大陆城市数量的攀升实际上却是在20世纪后半叶开始的,而且现在依然在加速上升,成了21世纪的蔚然之景。特别是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以中国为例,1950年其城市化率仅为12.5%,但至2000年的时候城市化率已经达到36%,据预测,至2030年其城市化率将达到60%。印度在1950年的时候城市化率以17.3%领先于中国,但是在1981年却发展稍慢,仅为23%,至2000年仅为30%,据推测,至2030年其城市化程度将达到40%多。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也正在加速着城市化的进程——从1990年的大约28%攀升至2010年的37%,至2025年有望达到大约45%。
由于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口生活在拉美(5%)、非洲(12%),尤其是亚洲(60%),因此地区性的数据就带有一些误导性。发达国家占有城市化最高的份额,在1950年时,世界一半以上的城市人口都生活在那里。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城市人口却生活在欠发达国家,一些人将这种现象称为“全球南方”现象。现在,仅有大约28%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发达国家中,至2030年,这一数字还将降至17%。这种城市居民(以及潜在的工人)向“南方”集中的现象还将继续。大都市被界定为一座拥有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1950年仅有一个这样的城市,那就是纽约。至2000年,这样的大都市增加到了17个,其中11个位于发展中国家,至2015年,这一数字预计将达到21个。在1976年,亚洲仅有两个大都市,而至2000年,17个大都市中有10个位于那里。这些大都市不仅在人口数量上而且在规模上都在增长——实际上这种增长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大多数这方面的数据只能是大致的估算。
尽管大都市增长的速度惊人,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城市人口中的大多数还是生活在规模较小的城市和城镇之中,它们也许与全球性的经济之间有着不太直接的关系,但却可能比那些引起世界媒体广泛关注的大都市拥有更加显著的问题。比如,1950年有86个城市人口超过100万,但是至2010年也许将会有500多个。不过在它们之下则是无数的生活着成千上万人的城镇与城市,其人口占据了整个世界城市人口的60%。
城市如何发展?
现在每天大约有20万人加入到世界城市与城镇人口之中。这就相当于,在整个19世纪中每月有500万人或者每年有6000万人成为城市人口。在欧洲,每年则有4500万人口增加到城市人口之中。城市人口既可以因为自然增长而增加——当出生率高于死亡率的时候——也可以因为迁徙而增加,或者因为城市的向外扩张而吸引临近地区或其周围众多乡村人口的到来而增加。在19世纪,城镇是主要的疾病中心,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里那里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因此,城市的发展可以主要归因于,在一个国家之内或跨越国境线或海域(比如在美国的案例中)的从乡村向城市的迁徙。尽管城市人口死亡率依然过高——尤其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而言,但如今全世界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已经好多了。但是由于处于婚育年龄阶段的年轻人口的增加,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对于许多城市中心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极为重要也带来了最大好处的依然是从乡村到城镇、从小城市中心向大城市中心的迁徙,尤其是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更是如此。据估计,全球范围内每天有15万人从乡村移民到城镇。为什么呢?对此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推力和拉力的双重作用。人们由于糟糕的生存环境被迫离开乡村,被拥有更美好时光的前景吸引着来到城镇:
与西方将乡村视作城市居民渴望逃往的避难所的理想观念相反,乡村地区的环境恶劣至极……城市也许贫困,但乡村更加贫困……残酷的事实是,当发展中国家有1/3或更多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贫困线水平、甚至低于贫困线时,乡村却仅有大约1/3的人口生活于贫困线以上。有关发展中世界的城市化的一份典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尽管糟糕透顶的住房条件、缺乏清洁的水源及良好的服务、缺乏最低限度的医疗保健、鲜有机会可以找到工作,但是城市贫民依然普遍地“在几乎所有的社会和经济福利指标上都要比他们在乡村的亲戚们好得多”……对于数百万的人们来说,城市是他们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不是增添问题的源头。①
尽管城市存在着自身的问题,但是城镇的收入(甚至当工作不稳定时)也往往比乡村高。城市往往有比全国还要高的人均收入——比如英国伦敦。但是在发达国家,这种差距较小。在比较贫困的国家,大城市的收入也许是全国人均收入的2—4倍。在上海,人均收入就被认为是全国的3倍,这与曼谷相似。在印度,人均国民收入大约是1500美元,但是在德里却高达3500美元。当然,平均数字也可能具有很大的误导性,但是一个生活在城市贫民窟的工人,哪怕一年仅有8个月能够被雇用,他也可能比一个生活在乡村只能有4个月劳作时间的农业劳动者的生活好得多。
尽管社会阶层差异带来的差别巨大,但城市的其他条件也常常要比在小城镇好得多——比如健康水平以及得到医疗的机会。最大的例外是艾滋病,尽管这种疾病是否对最贫困的人影响更大尚未为我们所知,但它却已经被认为是严重影响城市人口健康的重大问题。尽管城市设施陈旧,但是它们依然比乡村设施要好得多。一系列的数据显示,世界上生活在乡村的穷人仅有7%至8%的人能够有机会使用到冲水马桶,47%的人可以使用茅坑,而其他的人则必须去他们能去的地方如厕。但是据估计,对于城市贫困人口来说,对应的数字却是28%和52%。在对水的使用上也存在同样的差距。城市可以给人们带来兴奋以及更多的机会,尽管有时候它并不能够被实现。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导致在城镇和乡村之间发展不均衡的过程。它既促生了贫困,同时也促生了财富,它还加速了消除包括乡村和城市土地所有权在内的财产所有权过于集中的进程。由于农场主和工人双方都与全球经济融为了一体,因此他们的命运也就受到起伏波动的商品价格与经济危机的左右。从借款人那里借钱又为乡村的贫困者带去了更多的压榨盘剥,贫困者经常反抗他们的债主。因此,迁徙是更深意义上的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迁徙者学会了在城市生活,或者当他们往家里汇钱来维持家庭生活而且常常自己也返回家园时,迁徙也有助于这一进程的发展。
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开始意识到在不同的发展类型中的一个根本的差异。其中的一条出路是要通过拓展更加现代化的工业和服务业经济来实现。这里产生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全球经济的活力所在。服务于西方市场的中国城市的发展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却不限于此。工厂,哪怕它们是危险的血汗工厂,也能比在乡村经济或者城市经济的边缘勉强度日更具有吸引力。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写道:“受剥削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诅咒。”②脆弱性依然存在(2008年在中国广东,据估计有7000家工厂关闭,致使数百万的工人下岗),但是当机器一旦运转起来,对于那些操作它们的工人来说就有更大程度的稳定性。
在其他亚洲国家、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等世界经济的失败之处,另一条城市化的道路也变得明朗起来。尽管人们一直在谈论市场活力和消除贫困,但是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糟糕的经济在最近几十年要比早先的经济表现得更加每况愈下。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整体上来说年均增长了3%,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时期却仅仅增长了1.5%。在这个平均数字的背后,一些国家走上了倒退的道路。但是所谓的“没有发展的城市化”并没有停下脚步,实际上在一些情况下,经济的衰败似乎加速了它的发展——也许恰是对最糟糕的乡村情形的一个见证。这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提及了19世纪的爱尔兰。当贝尔法斯特借助机械、造船、纺织业等不断发展的时候,都柏林则成了典型的贫民窟城市,而且竟然还依靠爱尔兰乡村的贫穷以及运输爱尔兰生产的商品而养活着自己。但是如今,随着自由市场政策、债务危机以及结构调整计划对旧的经济结构的削弱,这种增长类型已经变得更加普遍。一份颇具批判性的联合国报告认为,这种类型的城市增长“不是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核心所在,相反,这些城市成了那些非技术性、不受任何保护、低工资的非正式服务行业和贸易领域剩余劳动力涌入的场所”③。
通过对比中国与非洲最大的国家尼日利亚,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模式。从1950年到2000年,中国人均收入增长了近8倍(尽管其起点较低)城市人口比例则从大约13%增加到了36%。但是在1950年至2000年的尼日利亚(人口约1.5亿),人均收入增长极其缓慢,仅增加了50%,而且长期处于近乎停滞的状态(英国的人均收入在同期则增长了3倍),但是城市人口的比重依然从原来的10%增加到了42%,拉各斯则从一座仅有35万人口的城市发展成为约有1050万人口的大都市。这并不会改变移民在这个城市或者其他城市贫民窟中可能过着更好的生活的事实,但是这意味着,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未来的生活就是一种做临时工、当街头小贩、清洁工、苦力、保姆、服务员和妓女的生活。这些差异很清楚地指出了,在平衡城市生活中正式的经济关系与非正式的经济关系中的截然不同的城市生活方式。
城市生活的本质
在贫困世界,那些新兴的城市和城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它是否会沿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同地区的城镇和城市之间及其内部均有很大差异。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探讨其中的一些共同因素。首先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速度。城镇甚至是乡村,可以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变成城市。只有当从乡村向外迁徙的人的数量开始下降的时候,稳定才能真正出现。
接着我们要关注不同程度的不平等。不平等有其外在的表现。城市中心被购物中心和商业大厦所占据。当地的特权阶层从他们的上层人士住宅,有时是从他们的富人封闭社区——“富人的堡垒”——走进这些购物中心。但是对于在城市生活的大众来说,则更多地是生活在边缘地带。戴维斯这样写道,世界上的许多城市贫民不是生活在“灯火辉煌、映亮天空的都市,而是蜷缩在肮脏的东西中间,周围堆满了污染物、粪便和腐烂的物品”④。当然,在这种生活空间和住所不平等的表象背后,屹立的是财富、收入和权利的不平等。
据估算,在本世纪初,世界仅有5%的人口生活在经济地位不平等有所下降的国家之中,而大约有60%的人生活在经济地位不平等不断上升的国家之中,这些国家大都是些拥有最根深蒂固的市场经济政策的国家。城市的不平等往往要比整个国家的平均不平等水平更高。尽管这种不平等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中往往比较严重,但是最近几十年这种不平等状况在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中(包括英国和美国)均又有了急剧攀升:“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趋势就是不平等的加剧。1990-2004年间,最贫困的1/5人口的收入占有比例从4.6%下降到了3.9%。”⑤尽管新自由主义评论家竭力表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正在壮大,但再分配的收入大多数还是进入了上层人士的口袋之中。
衡量不平等的标准使用的是基尼系数,该系数将完全的平等界定为0,而将完全不平等界定为1。联合国将基尼系数0.4界定为警戒水平,不平等接近这一数值就开始达到危险的水平了。亚洲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这个点(中国是0.45),而拉丁美洲和非洲则早就超过了它。个别城市,尤其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城市,甚至有着更高的基尼系数。0.6是大多数人被排除在外并且用来划分精英阶层的警戒线。就这些方面而言,一些最为不平等的城市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可以找到。据估计,有几十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7,而这是因为误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会导致财富受到损害、进而会造成灾难的又一个指标。
随着城市贫困人口超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成为城市社会底层日益严重的现象。这种贫困不仅仅指收入,但收入却是重要的指标。世界银行将生活费用每天仅为1美元的人数作为衡量极端贫困的标准,但是这一统计数字并未考虑到在许多大城市中生活花费更高的人。贫困还指缺乏良好的住宿、健康和休闲,容易受到暴力和犯罪的侵害,以及缺乏去选择关涉自己和所在集体切身利益的实际能力。许多(在一些国家中甚至是绝大多数)城市贫困人口,甚至是所有的城市人口,根本就没有切实的居住权。他们实际上拥挤在或者勉强居住在土地所有权不清或存在争议的地方,这就妨碍了基础设施的发展,使得人们存在依赖性,而且更容易受到压力的影响。一些国家需要人们拥有户籍,而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在中国,约有8000万至1.2亿人据说根本就没有户籍,因此也就容易受到当局采取的一些行动的影响。
城市贫困程度部分地折射出劳动关系的性质。就工人为全球品牌创造的产值来说,为外国公司工作的工人受到严重的剥削,但是他们却往往得到比那些为国内资本效力的工人更好的报酬和待遇,因此他们也往往相应地可以比占绝大多数的非正规经济部门员工做得更好。非正规经济部门在城市中一直存在,但是在新兴城市中,它的规模更加庞大。在拉丁美洲大约有51%的非农业就业据说就存在于非正规经济部门,在亚洲有65%,非洲有72%,而这些也只是一些平均数而已。在整个发展中国家,大约只有1/3的工人生存在正规经济部门之中,其他的2/3则生活在非正规经济部门之中。
这些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的城市贫民有时候被描述为被边缘化的群体,但是就描述而言,边缘化也被认为变成了一个“神话”。杰妮丝·帕尔曼(Janice Perlman)曾经指出,贫穷者不是“在经济地位上处于边缘而是被不断盘剥,不是在社会地位上处于边缘而是被社会所抛弃,不是在文化地位上处于边缘而是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不是在政治地位上处于边缘而是任人摆布和压迫”⑥。而且“非正规”一词本身的意义也在发生着变化,因此边缘化的程度也在变化之中。但是向更高层次的非正规性的转变却有着重要意义,部门类型会混淆城市和城镇的不同群体与对资本的不同依附关系。杰里米·斯布鲁克(Jeremy Seabrook)在对孟买居民区的描述中就抓住了这一特点。他写道:
那里的人们必须在城市经济体已经看似无法渗透的夹缝之中找寻工作,但是他们却在创造着工作,兜售、收集破烂、废铁或者塑料;他们在铸造厂或者钢铁厂辛苦地劳作,这使我们想起了恩格斯对英国黑暗世界的描述,或拖着沉重推车或沿街乞讨,或成为了妓女或肆意走私,或进行毒品交易或在跨国承包合同中找到弱不禁风的暂时稳定,或去缝制短裤或牛仔裤,或给运动衫印刷商标,或擦鞋或兜售报纸。⑦
女性助长了支撑富裕阶层的“广大奴隶大军”的主体的形成,甚至是由儿童所维持的那些循环链最终也被证实是一个复杂经济体系的基础所在。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意味着,在不同的地域贫困群体从来都是不可缺少的——富人需要劳动力,而穷人则需要工作。
这些在非正规经济体内工作的人们,许多居住或挤在城市的贫民窟中——他们的住所是用废弃的木材、砖块、废铁以及塑料搭建而成。联合国将贫民窟的居所界定为住在同样的天空之下却缺乏以下东西:可以饮用到的经过净化的水,可以利用到的经过改善的公共卫生设施,充足的生活区域,长期的住所及其终生使用权的保障。就这些方面而言,世界上大约1/3的城市居民都是贫民窟居民,在贫穷国家这一数字更高,而且他们的数量——也许是不完全统计——从整体上来说正在以比城市人口增长快得多的速度飞速发展,形成了一个“贫民窟地球”的幽灵之族。但是在许多国家中,大多数的城市贫民并不生活在贫民窟中——在印度就有多达80%的城市贫民并没有生活在贫民窟中。同样,并不是所有的贫民窟中的居民都是穷人——至少从收入的意义上来讲是这样。
在贫民窟中,城市的基础设施恰是其最薄弱的环节。由于其城市化发展进程的缓慢以及相对较低的经济收入,贫民窟被改进的前景并不乐观。建造良好的水源与公共卫生系统、清除有形的垃圾、建立可靠的能源供给等等都显得代价过于昂贵。政府致力于推进的发展并没有给予他们应得的优先照顾,而当地政府却又缺乏资源。据估计,尽管在发达国家的当地政府每年要为每人拨款3000美元,而亚洲则是150美元,拉丁美洲90美元,在非洲才仅仅每人15美元。民主的缺乏以及腐败又进一步削弱了来自下层对于改进生存环境的要求而产生的压力。结果是令人痛心的。“就像是在以垃圾为生的穷人的体内普遍存在着寄生虫的景象一样……将存在着的人们截然分成了两类,”戴维斯说道。⑧对此复杂群体予以评价并非易事。赞成新自由主义的人,往往对于城市的发展赋予最积极的评价,而认同世界银行观点的人,却丝毫也不乐观。莫汉(Rakesh Mohan)和达斯古普特(Shuhagato Dasgupta)写道:“奇迹在于世界已经真的很好而不是很糟糕地处理了一切。”同样,这两位作者在写到亚洲时却说:“在发展中的亚洲城市地区,生活质量现在十之八九都比18世纪和19世纪所见证的欧洲城市的情形好得多,而当时欧洲的城市生活质量在类似的环境之下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或许只不过是现在的收入较高而已。”⑨
这就使得他们进一步认为,如果放弃更多的规则并且对私营企业以及公私合营予以更多的强调,一切都将会继续得到改善。这一结论进而被拓展到了对城市民众的分析之中。对于这些评论者而言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在正规经济部门工作的工人往往就像保护自己劳动地位的贵族那样,通过排斥他者而承担了维护自己职位的职责。但是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人却并不会仅仅去叩响他们的大门而已。他们也被想象成为崭露头角的企业家,他们在最绝望的环境中幸存的能力,常被看作只要他们被给予一个机会、一定产权并且拥有少量资本就有望成为当地的比尔·盖茨的证明。于是沿着这个逻辑,贫穷世界的贫民窟居民就是“天生的企业家”。不管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已经将结构改革推进到了什么程度,均已经导致又有数百万的人被抛入了非正规经济部门之中,于是这种对贫民窟商业潜力的谈论,就会促使怀有商业激情的人士投身市场。当他们看到他们的政策的消极后果时,可以去拯救自己的良知。
更加具有批判性的评论家们强调了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以及他们日益严重的脆弱性,这不仅体现在他们受到世界经济波动厄运的影响,还体现在他们也受到诸如山体滑坡、平原以及沿海城市河谷决堤以及地震等类似灾难的影响。这种对于贫民窟地区企业家的浪漫描述,与在西方畅销的每一期《大问题》(Big Issue)杂志上看到的崭露头角的资本家颇为类似。人们实际上正在做的只不过是竭力维持生活。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的人们实际上也处在受到或大或小、程度不一的剥削的网络之中。贫困之中往往可以压榨出巨大的利益。穷人往往会付出最多——也许每平方米最高的租金、最昂贵的饮水等。因此,在发展中国家,一些重要的财富正是建立在对贫民窟以及非正规经济部门的盘剥之上的。这些自上而下确立自己正式地位的尝试——尽管那些提议他们去做的人出于最好的初衷——往往还是会带来损害他们有限既得利益的风险。例如,已经投入非政府组织机构的那些钱,已经赋予了这些机构新的含义,将其看作“海外新上帝”(New Gods Overseas)。这种新自由主义神话,在阿拉温德·阿迪加(Aravind Adiga)的那部关于一个来自乡野的男孩在印度奋斗成功的讽刺小说《白老虎》(The White Tiger)中得以生动的体现。但是即使像《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这样的电影,虽然有种种不足,甚至还提供给了一个贫民窟之子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机会使得他逃离了贫民窟并赢得了真爱,但是它还是戳穿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沾沾自喜的修辞性掩饰的面具。
可是这又使得乡村何去何从呢?尽管存在地区不均衡,农业的产量还是得到了提高,而且这也使得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口以及城市人口得以填饱肚子。但是这并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带去繁荣,现在其30多亿的人口数字不再增加,而且从绝对意义上讲还将开始下降。在贫困国家的乡村地区,大多数人依然“生存在边缘”,贫穷且十分脆弱。全球经济与乡村以及农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但是就是在乡村,人们才最容易忍饥挨饿。由于发达国家高产出及高补贴的生产,给所有的食品生产商在价格上带来了压力,因此全球农业市场也成为世界上最为扭曲的市场。
世界农业出口的大约64%来自工业国家,而仅有36%源于发展中国家。仅有22%的农业出口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这比从发达国家流人发展中国家的要少得多,而且与从南方流向北方的工业制成品也差不多。更糟糕的是,一些大公司垄断了诸如种子、化肥以及食品之类农业商品的进口。据估计,现在有30家公司承担着全球1/3的加工食品的生产。联合利华、美国嘉吉、雀巢、沃尔玛以及乐购公司,在极大程度上既控制了农业的进口也控制了其出口。
这些公司连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之类的机构,已经推动了对原有保护体制的削弱和对贫穷国家的资助,但是它们却认为这些激励从根本上并没有给农民的利益带去好处。这样的观点在过去确实是正确的,但是那种曾经承诺的繁荣景象现在依然遥遥无期。一种糟糕的体系为又一种糟糕的体系所取代,生产商现在也不得不应付随着出口价格下跌以及进口价格上扬而来的价格的疯狂震荡(例如能源)。《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就意识到了农业曾经许诺的快速发展依然没有出现:
20世纪80年代的结构调整,摧毁了原来可以给农民们提供土地、信贷、资金、进口产品以及合作机构的精密的公共服务体系。原本期望通过清除这些机构,可以为私有业者获得自由的市场,进而使之接管这些职能……但是却往往未能如愿。在一些地方,政府的退出至多也不过是尝试性的,反倒限制了私有业者的进入。在其他的一些地方,私营部门的出现是缓慢且具有局限性的——主要是为商业农场主服务的,而那些小自耕农则被暴露在众多市场失灵、交易费用与风险高涨以及服务欠缺的冲击之下。不完善的市场以及相关机构的缺失,使得小自耕农在放弃自身的发展和承受社会福利的损失之后又被迫背负上了巨额的成本,进而威胁着他们的竞争力,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威胁着他们的生存。⑩
但是请仔细阅读这段报告,因为承认失败的严重性,也就是认为由于市场的不“纯洁”和不“完善”,所以失败才自然而然地产生。这就是当市场失灵问题被提及时大家所熟知的借口。然而事实却是,乡村发展进程中存在着绝不亚于在许多城镇和城市中明显存在着的有悖常理的发展进程。作为食品出口重要组成部分的发展中国家的食品出口的减少,反映了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中补助的失衡。
尽管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最贫穷的农民生产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绝大多数食物,但他们依然受制于由于丰收无望而带来的收入上的变化。他们也逐渐地越来越依赖于乡村的非农劳动(小生意越好,平时的体力劳动收入就越糟糕),务工者们也将钱寄回家乡和国外。非洲及其他地区的微观研究表明,现在贫困人口在农村的收入有高达50%是来自非农劳动。
与向大型公司和超市供应产品的国际市场关系密切的更大的一些商业农场和种植园运营较好,因此也在吸引着农业劳动力。但是他们往往依赖于契约式合作,这就致使他们受制于西方买家对产品质量、产品标准以及在及时供货方面的肆意要求。尽管世界银行和其他一些机构认为它们对贫穷世界的乡村经济有所贡献,但那种贡献毕竟是有限的。然而稍事反思就可以发现这并不合乎逻辑。较大的单位往往会使用更多的资金和机器而使用相对较少的劳动力,因此,即使像支持这一观点的人梦想的那样发展势头良好,依然无法吸收乡村贫民以及面临生活压力的小自耕农这些大批的劳动力。正是这种失败将继续驱使更多的人离开土地,进入乡村的非农劳动领域和向城市迁徙。
城市的社会组织
每天都有一些人死于城市生活。人们大规模地经历着由于疾病、意外横祸、自杀和暴力所致的过早死亡。每年有500万人死于水质引起的疾病,其中300万死于腹泻。但是又有更多的人在更大程度上被证实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适应能力,并且还会幸存下来。这之所以会发生,部分是由于国家、当地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雇主等等所创立的社会结构使然,但是就如我们已经暗示的那样,这些结构常常是脆弱且混乱不堪的。幸存和适应力更多地与人们所从事的工作有关,有时候与市场的特性相适应,有时候又与其格格不入。
城市往往被统治阶级看作是等待点燃的潜在的火药桶。在20世纪60年代,巴巴拉·沃德(Barbara Ward)看到早期城市的蓬勃发展时写道:“现在有足够多的爆炸物在世界上至少会促生尖锐的阶级冲突模式。”(11)一个世纪以来,许多评论家并不认同这些说法。但是如果城市阶级斗争还没有达到像一些人期盼的或者像统治者害怕的那么多的话,那么它们也已经很多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世界许多贫困地区,随着城市的发展,大规模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反抗斗争已经取代了农村冲突以及游击战争的中心地位,其中许多反抗斗争在推进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民主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011年,这样的反抗斗争横扫了被认为是僵化了的中东国家。实际上,正是在这里谈及的社会变化削弱了旧的秩序。
这样的反抗并没有像也许曾被期许的那样成为一些正式运动的基础——不管是强大的工会还是左翼政党。这里应该被考虑到的一个明显的因素就是政府和私下的压制。民主化常常是表面上的。私下的压制往往和政府的良性监督共谋。这就可能使得那些出头者受到攻击并传播恐慌——只要形势看似稳定,这种恐慌就有助于遏制反抗或者迫使其转入地下。
但是当冲突发生时,并没有得到那些准备好去动员人们应对全球资本主义深层挑战的政治领袖们的引导,这就使得它们有可能被转变和偏移向其他方向。工会、政党和更广泛的社会运动在政治上被这一体系所左右或者为这一体系所破坏。但是对于这一情况的部分解释往往和主观因素——人们头脑中关于变化方向和变化可能性的观点——有关。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全球南方的政治折射出了不同民族主义与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冷战的相互影响。1991年苏联的解体强化了市场和新自由主义的动力,就这个意义而言,除了与全球资本主义融为一体外别无选择。
作为一项政策,这就更有吸引力了,因为一些国家似乎允许不平等的加剧,而且也允许“改革派”领导人将自己的角色合法地定位为这种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南非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黑人在经济上的掌权被认为是一种进步的方式。据报道,南非副总统普姆齐莱·姆兰博-努卡(Phumzile Mlambo-Ngcuka)在2005年8月曾说:“黑人不应该以获得的非法财富为耻。”当然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之下,西里尔·拉马弗萨(Cyril Ramaphosa)协助创建了南非全国矿工联合会,然后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总书记及其结束种族隔离协调委员会的领袖,继而成为了与麦当劳、可口可乐以及南非商业跨国资本关系密切并拥有亿万财产的商界领袖。
但是一些人还是会认为,任何更加正式的组织无法发展的原因,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应被归结为与阶级形成的潜在过程息息相关的更加“客观的”因素。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存在着的结构性要素是否反映出了阻碍变化力量的恒久状态,或者它们是否反映出了时间和成功的行动可以克服的更多的暂时性因素。
悲观主义者强调,尽管城市生活和工作可以将人们聚集在一起而且创造了一定的团结基础,然而在城市边缘生存的每日的煎熬也会使得人们彼此相向,进而分裂和削弱他们。
城市已经成为了许多人为了争相获得最基本的生活要素而展开竞争的中心:为了在工作地附近租到支付得起房租的一间房子,或者为了得到一片可以在上面建立一个容身之所而不用担心被赶走的地方;为了得到上学的机会;为了因为健康问题或者因为受伤而能得到医疗救治,或者得到在医院的一张病床;为了能够饮用到清洁的饮用水;为了能在公共汽车或者火车上拥有一个位子;为了在人行道上得到可以兜售商品的一个角落或者一块地方——这还完全没有算上为了获得工作的激烈竞争。(12)
然而,更多乐观的描述并不会那么消极地看待生活。为了生存,人们必须对他们自己的生活进行一定程度的主动控制。在这种日复一日的奋斗中,如果我们用心倾听,就会听到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所说的“反抗的尖叫声”。但是如果认为“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的话,就过于简单化了。使自己喝得一塌糊涂或者通过揍自己的老婆、孩子或者邻居而使自我感觉更好一些确实是一些生存机制,但是却鲜有人被鼓励这么去做。非法地窃取当地给富人供应的水或者电是更好的方法,但绝比不上组织起来要求得到足够的供给。问题就在于,我们对世界上那么多地方的这些基本斗争的本质和规模知之甚少。现有的讨论大多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运动基础之上的。在比较贫穷的国度中,常被讨论的反抗例子源于拉丁美洲,但是整个拉丁美洲大陆的运动究竟有多么特别,我们常常并不清楚,更别说其他地方了。
一些记录表明,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集体行动也许都正在变得越来越糟。随着负面力量利用了政府退缩或者失败而造成的空白,一些地方城市的堕落进程也许正在加剧。杰妮丝·帕尔曼——我们之前曾引述了她对边缘化的否认——就认为,拉美的一些城市现在已经为帮派暴力所困,以至于削弱了更加积极的抵抗形式。她声称,在里约热内卢原来曾经有来自底层的充满活力的反抗,现在却只剩下了“一些泄了气的人们,因为担心会惹祸上身而不敢去率先采取任何单方行动或者集体行动”。就这样,“边缘化从一种神话演变成了一种事实”。(13)
这就引发了另一种争议,即当真空存在的时候总会有其他的力量填充进来。寻求解释的人们如果发现那里没有人给他们提供备选方案,那么他们就会变得不太积极。读者将会发现,举出一些在最近几十年世界各地所发生的野蛮的种族流血冲突并不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这些事情助长了分裂、统治与寻找替罪羊的政治的滋生,有时候目标针对的就是所谓的“在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少数群体”(一些沉醉于比他者拥有更多财富和权力的族群)。但是这样的冲突也发生在不同的城市群体之间,由于一方渐渐地将迁徙而来的另一方视作敌人、或者由于一个宗教团体将另一个宗教团体视作敌人而导致的冲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一些冲突不可避免。它们往往会滋生绝望的情绪,以及导致政治真空的产生。它们往往被一些政府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甚至支持的煽动者所利用。如果任对市场有利的政策肆虐的话,那么就会助长导致这种冲突的环境。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一个危机,当时世界银行被警告由于其为解决一场经济危机而致使更多的人陷入贫穷,进而带来了种族和部族的暴力冲突,随后这又波及了一些国家。这比发达国家的情形毫不逊色,只不过发达国家由于更加有建设性的政治对抗和对群众的调动,使得寻找替罪羊的行为受到了限制而已。
比较盛行的是向宗教寻求帮助——在一些情况下向伊斯兰教求助,在另一些情况下则转向了福音派基督教,也许在其他地方转向了更加具有地域色彩的宗教。迈克·戴维斯就认为宗教成了城市堕落以及失败的激进方案的主要受惠者。这部分是由于宗教给人们带来了慰藉,而且当市场和其他政治力量不能奏效的时候,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就会替代它们帮助处于底层的人们。宗教似乎可以超越社会分化,这是其魅力所在,但是它却并不能永远掩盖社会分化现象的存在。书写伊斯兰教义和埃及反抗运动的萨迈赫·纳吉布(Sameh Naguib)就阐述了超越伊斯兰教的观点。无论何种宗教,将上帝看作问题解决的归宿,对于平民运动而言既是其优势也是其弱点所在。“它能够成为一种优势,但也只有当领导层能够平衡彼此冲突,并且避免将会彻底毁掉脆弱的团结力量的那些具体行动时才能如此。”(14)
极端悲观主义者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明因素的困扰之中。而温和的悲观主义者则在等候时机去“抛开工人阶级”,转而支持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以获得民主和改变。温和的乐观主义者并不将工人阶级一直以来所发挥的作用及其有组织的表达形式看作是这些更加广泛的变革力量中的主导力量,而是看作它们的力量中发挥“同样作用”的一支力量。简单的乐观主义者则认为,社会变革一直以来就包括广泛的社会运动,但他们也坚持认为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在更加基础的社会变革中处于中心地位。大多数这样的观点可以追溯至几十年前,甚至可以追溯至19世纪。往往很容易就被打破的正是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而且近来当许多左翼力量的前景变得更加暗淡的时候,悲观主义者就已经意识到了那一点。
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上述观点,有必要铭记资本主义城市的快速发展已经导致了需要很长时间方可消除的一定程度的社会紊乱。对贫困国家有组织的工人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倍感惋惜的罗纳尔多·蒙克(Ronaldo Munck)就认为,在过去,“工业化、城市化和工会化的行动是齐头并进的”(15),但是现在却不是这样了。现在糟糕的历史境遇可能导致糟糕的政治局势。当1851年英国的2700万人口中有一半成为城市人口时,才仅有10万名工会会员,而且他们的大多数组织并没有生存的空间。1900年当4100万人口中有80%是城市人口时,工会的会员人数竟然达到了120万至150万之间。然而正是因为这一点,英国工人阶级的工会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出色的组织之一。因此,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工会化之间就不存在简单的关系。一些人所谓的“工人阶级的大跃进”常常并不等于突然的冒进和随之而来的倒退。
贝弗里·西尔弗(Beverly Silver)在她的著作《劳工的力量》(Forces of Labor)中认为:“20世纪后半叶工人运动的危机只是暂时的,而且将可能随着新兴工人阶级团结的巩固而被克服。”(16)这本书也许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对现在如此众多的分析中盛行的悲观主义持有异议。西尔弗认为,全球范围内的改革在不同的国家创造了或者再造了工人阶级。举例来说,她尤其关注拉丁美洲、韩国以及南非汽车行业工人们的作用,而且她观察到这些工人已经形成了激进的工厂工人的核心组织,并且她还预测这一趋势在中国将会愈演愈烈。
西尔弗还认为,改革在白领以及许多富裕和贫穷国家的教师群体构成的劳动力中,正在形成富有战斗精神的新的中心。因此她认为,激进评论家往往将他们自己看到的发达国家的那种失败景象强加在了贫困国家人们的头上,进而颠覆了那些消极的观点。实际上,纵观全球,工厂的中心地位依然存在,而且其前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光明。这一论点在保罗·梅森(Paul Mason)关于“工人阶级如何走向全球”的更具描述性但却更富有力量的讨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文中他将过去的那种斗争意识与现在的种种斗争意识交织在一起,带着我们从19世纪初的曼彻斯特穿越到了21世纪的中国。(17)
遗憾的是,很难在发达国家之外找到工会化在不同层面的对比研究的出色资料,但是最近的一项研究(使用了部分可以利用的资料)却认为“阶级依然是关键的变革力量”。但是似乎阶级斗争也是关键的变革力量。例如,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紧缩政策占据上风的地区,这不仅削弱了正规的经济体,而且还削弱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机构。在已经签署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协议的国家中,就有60%的工人在货币紧缩项目生效之后不愿意加入工会。这一点在拉丁美洲尤为重要,因为在那里于20世纪80-90年代广泛推行了一些紧缩政策。自从“阶级已死”(the death of class)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阶级斗争的永恒,只不过这些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是自上而下发动的。
但是如果社会的平衡取决于在非正规部门工作的大众,那岂不是削弱了在社会和政治变革中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所发挥的作用的观点的基础了吗?对于许多人来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代表了这种论调的极端情形。正是在这个地方,本已薄弱的正规经济部门及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似乎已经受到了经济变化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政策的极大冲击。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甚至在它们的城市人口成倍增加的时候,依然受到“失业飓风”的袭击,也就没什么值得费解了。但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已经成为了城市存在严重社会不安因素的地区,在那些城市中正规经济部门与非正规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分歧已经变得尤为重要。
为了说清楚这一点,就必须承认在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存在改革的不均衡。已经失去的正式工作很重要,但是那些依然存在的以及已经被创造出来的新的工作也同样重要。往往在“非正规”部门存在的不同程度的非正规群体也不少。将正规和非正规的群体作为两极对立,从来也没有产生过太大的意义。这也反映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生活在家庭和彼此相邻的街区之中,在这里从事着正规经济部门和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的人们在一起生活并彼此关爱,他们也为他们彼此的失败和成功而同悲共喜。泽伊利格(Zeilig)和切鲁蒂(Ceruti)认为,“在工作和失业之间没有密不透风的墙”,而且“如果在工作、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的工作之间没有明确的划分,那么就存在着交叉抗议的可能性。”(18)
在已经发生的许多抗议活动中,这种交叉很明显。但是显然也有另外一些内容。尽管存在着将有组织的工人的被削弱的、甚至是多余的作用看作是对社区组织、非正式协会、压力集团之类组织的反抗的说法,但有组织的工人依然在更广泛的抗争活动中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整个北非以及中东地区在2011年的反抗,已经描绘出真情实景,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前进和后退的经典模式,这些进与退留下的一些传统在未来还将继续被发扬。
尽管在常见的记述中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大街之上,但是正是有组织的工人往往才是团结的核心;正是有组织的工人有助于指明方向;也正是在有组织工人的阶层中间诞生了各种各样的领导阶层。因此,其重要角色与其说是源于理论家们的构想,还不如说是源于某些具体的形势,人们将继续从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我们在本文中致力于将全球变迁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之下进行细致的勾勒与讨论。然而令人震惊的是,那么多关于社会运动的文章仅仅依赖的是发达国家的经验,而且如果这个讨论继续延伸的话,那么就只能基于全球性分析来进行了。因此,我们得出的最基本观点是:阶级并没有在消失。当今世界上的工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人数都要多,而且如果危机已经将他们推回到了某些地方,阶级和组织依然重要。
但这并不是说全球趋势决定一切。斗争源于具体的地区背景之中。就有关要素而言,有关当地和国家的要素而非全球性的要素才是最切实可见的。结果常常是混乱的,但是混乱也往往是斗争进程的组成部分。阶级斗争从不单纯,但是这并不像一些人杜撰出来的那样是多大的问题。看看20世纪初期的世界,尤其是1916年爱尔兰所发生的事件,当反抗将人们与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的背景、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者、天主教徒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列宁作出了在今天看来依然与当时一样正确的一个论断:
如果认为没有殖民地和欧洲弱小民族的起义,没有带着种种偏见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爆发,没有那些不自觉的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地主、教会君主和民族等等压迫的运动,社会革命也是可以设想的。……谁要是等待“纯粹的”社会革命,谁就一辈子也等不到,谁就是不懂得真正革命的口头革命家。(19)
坏消息是,一个世纪以来,对于他所说的社会革命的要求依然存在。好消息是,全球范围内的变化已经形成了一个更大的热衷于那种变化的人群。和一直以来一样,危机——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既形成了一种挑战,也造成了一种机遇。
本文译自《国际社会主义》杂志2011年第132期,作者迈克·海恩斯(Mike Haynes)任教于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文章通过大量数据概述了世界城市发展的状况,探讨了城市的社会组织形式,论证了当代城市生活的本质,并通过分析当代工人阶级在全球各国的分布情况得出结论指出,阶级并没有消失,当代全球工人阶级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人数都要多,并已经成为有史以来在各阶级中占据绝大多数的阶级。
①John Reader,"No City Limits",Guardian,11 September,2004.
②Michael Burawoy,"From Polanyi to Pollyanna:The False Optimism of Global Labor Studies",Global Labor Journal,volume 1 ,number 2,2010,p.308.
③Mike Davis,Planet of Slums,Verso ,2006,p.23.
④Ibid.,p.19.
⑤UN-HABITAT,"Planning Sustainable Cities:Global Report on Human Settlements" (Earthscan),2009.
⑥David Drakakis-Smith,The Third World City,Routledge,1987,p.94.
⑦Jeremy Seabrook,The Myth of the Market:Promises and Illusions,Green Books,1990,pp.64-95.
⑧Mike Davis,Planet of Slums,Verso,2006,p.138.
⑨Rakesh Mohan and Shuhagato Dasgupta,"The 21st Century:Asia Becomes Urban",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15 January,p.217,p.218.
⑩Philip McMichael,"Banking on Agriculture:A Review of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8",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volume 9,number 2,pp.238-239.
(11)David Drakakis-Smith,The Third World City,Routledge,1987,p.49.
(12)Giok Ling Ooi and Kai Hong Phua,"Urbanisation and Slum Formation",Journal of Urban Health,volume 84,number 1,2007,pp.27-28.
(13)Janice Perlman,"Megacity's Violence and its Consequences in Rio de Janeiro",in K.Koonings and D.Kruijt(ads),Megacities:The Politics of Urban Exclusion and Violence in the Global South,Zed Books,2009,p.10.
(14)Rabab El-Mahdi and Philip Marfleet(eds),Egypt:The Moment of Change,Zed Books,2009,p.119.
(15)Ronaldo Munck,"Globalisation and the Labour Movement:Challenges and Responses",Global Labour Journal,volume l,number 2,2010,p.218.
(16)Beverly Silver,Forces of Labor: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71.
(17)Paul Mason,Live Working or Die Fighting:How the Working Class Went Global,Harvill,2007.
(18)Leo Zeilig and Claire Ceruti,"Slums,Resistance and the African Working Class",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17(winter),2007,p.74,p.77.
(19)《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52页。
标签:国家经济论文; 城镇人口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世界城市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经济学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