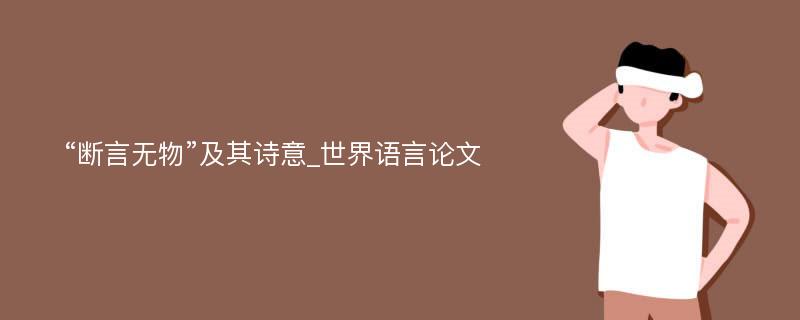
“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及其诗学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词语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4)04-181-03
“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是海德格尔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Unterwegs zur Sprache)一书中重点阐释的一个诗学命题。同时,理解这一命题所蕴涵的诗学意义,也是理解海德格尔《林中路》(Holzwege)、《荷尔德林诗的阐释》(Erl?uterungen zu H?lderlins Dichtung)等其他诗学著作相关问题的基础。本文拟从八个不同的角度对此命题作出解释,以就教于方家。
一 此命题中的两个关键性概念
1.存在(Sein)
可以说,海德格尔一生都在“追问存在”。他认为这是哲学家唯一正当的工作。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他之前的任何一个哲学家的“存在”都有所不同:
第一,他的“存在”不是任何一种“存在者”或“存在者的整体”。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海德格尔甚至还明确区分了“存在者的存在”与“作为存在的存在”。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通常是指后者。“作为存在的存在”是就“存在所固有的意义”亦即“存在之真理(澄明)的意义”来说的[1]。不明确这一点,单单抓住“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或“语言是存在之家”,很容易把海德格尔误视为是一个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者。
第二,他的“存在”是通过追问“存在者”的方式所追问不到的。在《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中,海德格尔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2],而且认为追问“存在者”原本就是经验科学而不是哲学的任务[2]。在《面向思的实情》(Zur Sache des Denkens)中,海德格尔提出,哲学必须“不顾存在者而思存在”(Sein ohne das Seiende zu denken)[3]因此,他的“存在”必须通过“让存在自身达乎显现”的方式而不是经验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方式来获得。
第三,他的“存在”的意义是每时每刻都如此这般地存在着、并且领悟着自己的这种存在的“Dasein”(通译为“此在”)在对自身生存的自我领悟中生成的。因此,它不是现成的、静止不变的,而是鲜活的、开放的、人言人殊的。“Dasein”追问无限,“存在”的意义也就无限。
有日本学者(如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手冢富雄)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Sein)”相当于东方哲学中的“空(Leere)”。但与之对话的海德格尔却宁愿把它说成是“无(Nichts)”。不过,在海德格尔看来,“空”与“无”原本就是“同一个东西”[1]。笔者认为,其实传统西方哲学中的“无”与古代东方哲学中的“空”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而且二者之间的区别正好体现了东西方哲学根本观念上的差异:东方哲学中的“空”讲的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讲的是一切皆“因缘而生”、“因缘而起”,并无永恒不变的实体存在。“缘起”之物非“有”非“无”,且非“非有”非“非无”。因此,在东方哲学中,“有”非“真有”,“无”非“真无”,“空”亦非“真空”。众所周知,僧肇“不真空论”即以此立义,而龙树主“八不”“三是”教义的“中道”哲学的精髓也在于此。但如果考虑到海德格尔受东方哲学影响很深(读过禅宗著作、多次引用《老子》和《庄子》、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译过《道德经》等),如果从“缘起性空”而不是“空无一物”的意义上去理解海德格尔的“无”,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和他的“Dasein”一样,本质上倒真是“空”或者“无”了。难怪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ysik)中要以这样一句话开始并不断重复他的追问:“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4]难怪后期海德格尔要经常谈到“无无化(Das Nichts nichtet)”的问题。然而问题是,如果“存在”真是所谓“无”的话,它又能否以及如何被“语言”道说?
2.道说(Sage)
谈“道说”就等于谈“语言”,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的本质就在于“道说”,它在“道说”中“成就其本质”。
“道说(Sagen)”不等于“说(Sprechen)”,有人滔滔不绝地“说”,但可能什么也没有“道说”。相反,有人沉默,什么也不“说”,却可能在沉默中“道说”了许多[1]。“道说(die Sage)”意味着三个东西:“道说(das Sagen)”、“所道说者(das Gesagte)”、“有待道说者(das zu-Sagende)”。它们分别对应“道说”的行为、内容方式和对象三个要素。
究竟什么是“道说”呢?海德格尔在《出自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Aus einem Gespr?ch von der Sprache)中说,“道说”就是“让显现和让闪亮意义上的显示”,而且这种“让显现”和“让闪亮”乃是“以暗示方式进行”的[1]。“‘道说’意味着:显示,让显现、让看和让听(《Sagen》hei?t:zeigen,erscheinen-,sehen-und h?ren-lassen)”[1]。在《语言的本质》(Das Wesen der Sprache)一文中,海德格尔说,“对世界之澄明着和掩蔽着的端呈,乃是道说的本质所在(Das lichtend-verhüllende,schleiernde Reichen von Welt ist das Wesende im Sagen)”。[1]总之,“道说”本质上是这样一种活动,它借助“语言”以“暗示”的方式、以“澄明与掩蔽的争执”的方式“让存在”自身“显现”,“让存在者”如其所是地“存在”或曰“在场”。
厘清了“存在”和“道说”两个概念还是不够充分的,让我们再来看看能帮助我们理解此命题的另一个命题。
二 语言是存在之家
“语言是存在之家(Die Sprache ist das Haus des Seins)”,是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Brief über den Humanismus)中率先提出的命题[5]。提出该命题的目的是“想要启示语言的本质”,但海德格尔本人也承认,它显然只是一种“暗示”,而“没有提供出关于语言之本质的任何概念”[1]。但“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一说法本身,却清楚地表明了海德格尔对于“存在与语言之关系”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并且早已成为了海德格尔哲学、诗学中一个影响深广的重要思想。
为什么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呢?在《语言的本质》一文中,海德格尔写道:“任何存在者的存在都居住于词语之中”(Das Sein von jeglichem,Was ist,wohnt im Wort)[1];在《词语》(Das Wort)一文中,海德格尔又申述道:“唯词语才赋予在场,亦即存在,在其中某物才作为存在者而显现”(Dem entgegen verleiht das Wort erst Anwesen,d.h.Sein,worin etwas als Seiendes erscheint)[1];在《走向语言之途》(Der Weg zur Sprache)一文中,海德格尔在其结语部分再次写道:“语言乃是在场之庇护,因为在场之显露已然委诸道说之成道着的显示了。语言是存在之家,因为作为道说的语言乃是成道的方式”[1]。
应当如何理解“语言是存在之家”的具体含义呢?在前引《对话》一文中,手冢富雄教授指出:不能把“存在之家”当作一个可以让人任意想象的粗浅比喻,譬如把“家”想象为一座先前在某地建造好的房子,“存在”就如同一个可以搬动的物件被安置于其中。海德格尔表示赞同后补充道:“在‘存在之家’这个说法中,我并不意指在形而上学上被表象的存在者之存在,而是指存在之本质,更确切地讲,是指存在与存在者之二重性(Zwiefalt)的本质——但这种二重性是就其对于思想的重要性方面来理解的”[1]。由于“存在”显现为“在场者之在场”,因此海德格尔又把这种“二重性”说成是“在场者之在场,亦即从两者之纯一性而来的二重性”(Anwesen des Anwesenden,d.h.die Zwiefalt beider aus ihrer Einfalt)[1]。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存在之本质”乃有海德格尔独特的命意,当作动词意义上的理解,意为“让存在本身达乎显现”或曰“让在场者在场”。“存在”如何“达乎显现”?借助“语言”。因为,“语言”的本质即“道说”,“道说”的本质即“让显现和让闪亮意义上的显示”。正是通过“语言”,“存在本身”才得以“显现”。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不正是“存在之家”吗?
三 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
“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Kein ding sei wo das wort gebricht),是德国诗人Stefan George《词语》(Das Wort)一诗的最未一行。仅《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里,海德格尔就写了《语言的本质》和《词语》两篇长文专门为它作注。作为该书的一个核心思想,可以说它与书中收录的全部文章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关性。
这句话显然与“语言是存在之家”有着内在本质上的相通性:既然“存在本身”是在“语言”中才得以“显现”的,那么“存在者之存在”自然也得通过并且就在“语言”中“显现”,因为“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2]。这就是说,“语言”作为“存在之家”,也理所当然是“存在者之家”。这,正是理解“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的枢机所在。
这句诗究竟包含了些什么涵义呢?我们至少可以从八个不同的角度作出解释:
第一,“破碎”就是“缺失”,因此,这句话等于是说“在词语缺失处,亦即在每每命名着物的词语缺失处,无物存在”(Kein Ding ist,wo das Wort felt,n?mlich das Wort,das jeweils das Ding nennt)[1]。为什么呢?这需要从“命名(Nennen)”谈起。“命名”既是赋予某物一个“名称(Name)”,同时本质上又是一种“召唤(Rufen)”:运用“词语”把事物——先前在远处作为“尚不在场者”的“被召唤者”之“在场”带到“近旁”,使之“现身在场”[1]。因此,“在命名物的词语缺失处”,便没有“物”之“在场”被召唤前来,自然也就“无物存在”。
第二,“命名”同时也是一种“发现”,这对于被命名之物和被用来命名的词语双方而言都是如此。所以,这句话又等于说“唯当表示物的词语已被发现之际,物才是一物。......唯词语才使物获得存在”(Erst wo das Wort gefunden ist für das Ding,ist das Ding ein Ding......Das Wort verschafft dem Ding erst das Sein)[1]。当一个事物尚未被命名之时,它的“存在”就被“掩蔽”在幽深黑暗的“混沌”之中;唯当它被“命名”,亦即表示它的“词语”被发现之际,“此物”才从与“他物”浑然无别的“混沌”状态中“跃出”作为“此物”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唯词语才使物获得存在”,而“词语亦即名称缺失处,便无物存在”[1]。
第三,照此,“任何物的存在都居住于词语之中”。但“词语”与“物”之间的关系并非随意的,“只有在合适的词语说话之处才有物存在”(Sein gibt es nur,wo das geeignete Wort spricht)。[1]什么样的“词语”才是“合适”的“词语”呢?唯有最能生动贴切、惟妙惟肖地体现它所指称的“物”的“存在状态”的“词语”。唯有这样的“词语”,才能使某“物”成为如此这般地存在着的一个“物”,从而把当下的“存在者”确立为如其所是的一个“存在者”并让它如此这般地“存在”。严格地说,一个“物(存在者)”,只有当它取得了独特的、与众不同的“存在”时,才算跃出了混沌而真正地“存在”。唯有“合适”的“词语”方能如此,所以“只有在合适的词语说话之处才有存在”,在合适的词语还缺失时,就不可能有物存在。
第四,如果把“Kein ding sei wo das wort gebricht”中的“Sei”不理解为“ist”的虚拟式而理解为命令式,那么,这句诗的涵义就是:“词语破碎处,往后就不允许任何物成其为存在着的物”(Lass fortan kein Ding als seiendes zu,wo das Wort gebricht)。为什么可以做这种理解呢?格奥尔格该句诗的前面还有一句诗,两句连起来是:
我于是哀伤地学会了弃绝:
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sei)。
“弃绝”乃是对旧情状的抛弃和对新境界的期备,一种终结过去面向未来的指令(Geheiss)。虽然这里的“弃绝”后面用的是冒号,但冒号后面的却不是被弃绝的对象,而是弃绝之后必须进入的那个领域,一种进入重新定位的词与物的关系中去的指令:词语破碎处,不允许任何物作为存在者存在。换句话说,必须“弃绝”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当词语缺失之时,某物也存在并且已经存在”(......etwas sei auch dann und sei schon,wenn das Wort noch fehle)。[1]这就是说,“词语”与“物”是共进退、同存亡的,当命名某“物”的“合适”“词语”尚还“缺失”或已经“缺失”时,都不允许此“物”作为“存在着的物”而存在。
第五,“允许......存在”就是“让......显现”或“让......在场”,因此,这句诗又意谓着:“唯有词语才让一物作为它所是的物显现出来,并因此让它在场”(......dass erst das Wort ein Ding als das Ding,das es ist,erscheinen und also anwesen l?sst)。[1]海德格尔进一步发挥道:“词语把自身允诺给诗人,作为这样一个词语,它持有并保持一物在其存在中”(Das Wort sagt sich dem Dichter als das zu,was ein Ding in dessen Sein h?lt und erh?It)。[1]这就是说,是“词语”让“物”得以如其所是地“显现”和“在场”,并因此而被“持有”和“保持”,所以诗人用来“道说”的“词语”乃是“存在之渊源(Born des Seins)”,诗人的天职就是“对作为存在之渊源的词语的召集”。[1]
第六,由于正是词语把一切物保持并且留存于存在之中,所以,“没有如此这般的词语,物之整体,所谓‘世界’,便会沉入晦暗之中;‘我’,那个把他所遇到的奇迹和梦想带到他的疆域边缘、带向名称之源泉的‘我’,也会沉入一片晦暗之中”(Ohne das also verhaltende Wort sinkt das Ganze der Dinge,die《Welt》,ins Dunkel weg,samt dem《Ich》,das,was ihm an Wunder und Traum begegnet,an den Saum seines Landes zur Quelle der Namen tr?gt)[1]。这段话有两层含义:不仅“物”,就是作为“物之整体”的所谓“世界”,也是靠“词语”带入“存在的光亮处”的,没有如此这般的“词语”,“世界”便处于“一片晦暗”的混沌之中;“我”也同样如此:“我”之为“我”、“我”之区别于“他人”“他物”,靠的是“我”对“世界”的独特“道说”,归根结底靠的是“词语”。诗人更是如此。没有如此这般的“词语”,他就无法“把他所遇到的奇迹和梦想带到他的疆域边缘、带向名称之源泉”,也就无从成其为一个诗人而以诗人的身份“存在”。总之,没有“词语”,“我”也将沉入与“他人”“他物”浑然无别的“一片晦暗”之中。
第七,“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意味着,是“词语给出存在”(Gibt das Wort:Sein)。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与印在词典或书上的印刷符号不同,当“词语”“道说”时,它从根本上已不再是“物”,不再是任何“存在者”;而那个需要由“词语”带来的“物”的“存在”本身,也不是作为系于“词语”这个“物”身上的另一个“物”,我们上哪儿也找不到这个“存在”。这就是说,“词语”“给出”“物”以“存在”,实际上是并非作为“存在者”的“词语”,“给出”了本身并不“存在”的“存在”。在这里,无论是被词语给出的“存在”还是给出存在的“词语”,都没有获得“物本质(Dingwesen)”:“存在(Sein)”。但海德格尔说,它们虽然不“存在(ist)”,却“有(es gibt)”,而且“词语”或许还是“先于一切地是有的东西”。在德语中,“有(es gibt)”的字面义是“它给出(Es gibt)”。于是,“词语”又成了“给出者(Gebende)”,其本质就是“它给出(Es gibt)”。[1]既然“词语”成了“给出者”,“物”的“存在”便需要而且能够“被给出”了,于是就有了“词语给出存在”这回事。只是在这里,“词语”俨然已成为《创世纪》中那个仅凭语言的“道说”便创造了世界万物及其存在的“上帝”了。
第八,“词语”是通过“道说(Sagen)”来“给出”“物”的“存在”的。在海德格尔看来,“道说”乃是“开辟道路”,而“道路”一词也许也正是表示“语言的源始词语”(Vermutlich ist das Wort 《Weg》ein Urwort der Sprache)[1]。这就是说,“词语”“给出”“物”的“存在”,是通过“开辟道路”的方式来实现的。正是通过“开辟道路”,“道说把‘存在’发放到被照亮的自由之境以及它的可思性的庇护之所中”[1]。海德格尔甚至说,“一切皆是道路”(Alles ist Weg)[1]。如果“道说”的确仅仅是提供或者充当一条“让通达的道路”(Weg als das Getangenlassen),那么,我们所谓的“词语给出存在”则必须被理解为:“词语”所“给出”的不是“物”的“存在”本身,而只是通向“物”的“存在”的一条“道路”;我们必须先敲破“词语”坚硬的“物质外壳”,方能理解其中所“道说”的“物”的“存在”。海德格尔非常强调这一点,甚至强调说,“词语的这种崩解乃是返回到思想之道路的真正的步伐”[1]。在这个意义上讲,说“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也就等于说:
词语崩解处,一个‘存在’出现。
(Ein《ist》ergibt sich,wo das Wort zerbricht)
四 这一命题的诗学意义
归结起来,“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这一命题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就是:是“语言”赋予了“存在”,是“语言”给出了“世界”。这一思想不仅是理解《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中的诗学思想的关键,而且理解它所蕴涵的诗学意义,也是理解海德格尔《林中路》、《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等其他诗学著作相关问题的基础。限于篇幅,我们只能举一、二例证简单提示。
譬如,在《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一书最重要的文章《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中,作者写道:“惟语言才提供出一种置身于存在者之敞开状态中间的可能性。惟有语言处,才有世界。”[6]这话应当如何理解呢?如前所述,语言的本质在于“道说”,而“道说”就是“让显现和让闪亮意义上的显示”;词语通过“命名”把事物“召唤入词语之中”,从而把先前在远处作为“尚不在场者”的“被召唤者”之“在场”带到“近旁”,使之“在召唤中现身在场”。因此,语言,惟有语言才能“提供出一种置身于存在者之敞开状态中间的可能性”。如若没有语言,“世界”和一切“物”就将被“掩蔽”在晦暗的“混沌”之中,而不能取得自己本真本己的独特存在。唯当“世界”和“物”被诗人作家“命名”,亦即“发现”并运用表示它们的“词语”之际,它们才能从与“他物”浑然无别的“混沌”状态中“跃出”作为它们自身而如此这般地“存在”:显现、闪亮、敞开。这也让人想起中国古典诗学的最后一部杰作——王国维《人间词话》附录中的一段话:“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再譬如诗人荷尔德林在《追忆》一诗的结尾处唱道,“诗人创建持存”。的确,诗人的本性就在于“创建持存的东西,从而使之持留和存在”。[1]诗人所为,乃是将使他迷惑的奇迹和令他陶醉的梦想带到语言之源泉旁,并从中汲取最能表现这些“奇迹”和“梦想”的“合适”的“词语”,从而使之得以永远闪亮地“持留和存在”。用“词语”“给出”“(存在者的)存在”,这就是诗人的使命和职责。当然,如前所述,“只有在合适的词语说话之处才有存在”。于是,我们又懂得了中国古代诗人为什么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而福楼拜教授莫伯桑写作时为什么要从选词练字开始了。又譬如,如前所述,“词语给出存在”必须被理解为“词语”所“给出”的不是“物”的“存在”本身,而只是通向“物”的“存在”的一条“道路”而已。这又仿佛让我们听到了中国传统文艺美学中非常熟悉的声音:“得意忘言”、“不落言筌”、“不死于句下”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