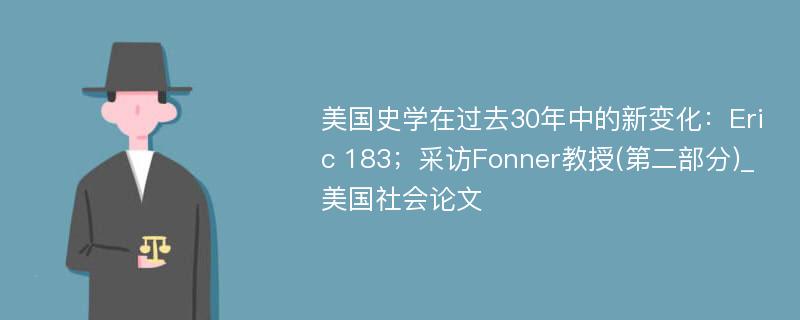
近30年美国史学的新变化——埃里克#183;方纳教授访谈录(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美国论文,之二论文,新变化论文,访谈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学界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是我们如何超越所谓“美国例外论的史学”(the history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我想,从定义上讲,国别史本身就或多或少都带有某种例外论的色彩,因为国别史通常以国界来划分的,民族—国家是历史研究的分界线,人们总是研究法国史、美国史、俄国史或中国史。当然也有许多人研究国与国之间的历史,但绝大部分的历史仍然是以国家为划分的界限的。比起其他民族国家的历史学家来说,美国历史学家更强调美国历史的独特性和例外性。美国历史学家通常把历史分成两类:美国史为一类,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历史归为另一类。但在已经来临的21世纪里,全球化正在迅速发展,传统的国界划分将在许多方面扮演一个越来越不重要的角色,民族国家并不会完全消失,但在经济生活和人权等领域内,有些问题可能会超越国界。所以,我们面临一个如何将美国史研究与更广泛的世界背景相结合和整合的问题。有些领域已经开始朝这方面发展了,如殖民地时期史的研究,现在就是放在大西洋领域和英帝国整体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历史学家现在更强调英国、非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往, 而不再是孤立地研究殖民地史。
丹尼尔·罗杰斯 (Daniel Rodgers)去年出版的名为《Atlantic Crossings》的书是一个优秀的例子。(注:丹尼尔·罗杰斯:《大西洋间的跨越:一个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Daniel T.Rodgers,Atlantic Crossings:Social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哈佛,1998年。 )这本书描述了20世纪初美国进步运动时代的立法如何受到了欧洲社会立法的影响,叙述了欧洲与美国在应对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冲击这方面思想和政策交流的过程。
但是,由于传统的例外论偏见的存在和现在绝大多数史学家所受的训练仍然是国别史这一现实,要想迅速把美国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同时这样做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即由于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将历史简单化。讲“让我们来写一部世界史或国际史”这句话很轻松,但真正有能力在不同的地方(和国家)从事深度研究同时又能熟练掌握各地(国)史学成果的学者却不多。将美国史置于大西洋背景下来研究自然很好,但有多少美国历史学家真正熟悉和吃透了其他各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法国的、西班牙的、甚至英国的。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不过,这样的努力会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史研究逐步向“非民族国家化”(de-nationalize)或“国际化”(internationalize)方面移动,这是一个挑战。总体来看,这样做是有正面意义的。例外论往往使许多美国历史学家无法认识到更广泛的国际趋势,而事实上,无论是劳工或移民模式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都是国界来界定和划分的。
王希:既然你谈到了美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我想问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美国历史上曾有“熔锅论”(melting pot )之说,现在看来,熔锅论基本上是一种虚幻的事实(myth),但美国的历史却也表现了不同群体的美国人为构建同一民族传统而共同奋斗的过程。在当今世界上,如何处理群体与国家、群体的传统与由不同民族群体组成的国家的传统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冷战后的世界表现得尤为突出。您认为美国在处理种族问题上的历史经验能否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一种正面或反面的历史借鉴?
方纳:首先,我对“熔锅论并不存在”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如同许多虚幻的说法一样,熔锅论的说法并不是完全没有真实的成分。对于美国白人来说,熔锅论显然有效而且是可行的。以我的家庭为例,我的祖父母来自俄国和波兰,我夫人的祖父母来自意大利。他们那一代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美国人,而始终自认为是意大利人、俄国人或犹太人等等。他们甚至不大会讲英语。他们的孩子虽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美国,但仍旧保留了相当一部分原来的文化传统。但是到了我女儿这一代,情形就不同了。我女儿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了。她既不是意大利人,也不是俄国人,她的生活中几乎找不到我祖父母那一代人的文化痕迹,也许只是在饮食上有一点点偏好,但她基本上是一个熔锅论的产物。她是一个美国人,她与一个从加里福尼亚来的人的共同之处比起她与一个来自俄国或意大利的人之间的共同之处要大得多。
对于非白人的美国人来说,熔锅论的内容就更为复杂一些。对于美国黑人来说,熔锅论则是不存在的。今天美国社会中存在的黑白种族分界线与过去一样明显。在现实生活的许多方面,这种分界线成为一种不可忽视和不可逾越的障碍,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种族隔离的时代,但对于黑人来说,他们的美国生活经历与白人是非常不同的。拉丁裔美国人则处在中间地带。种族分界线与肤色有关,肤色浅,融入相对容易一些。亚裔在很多方面的融入都比较快。如果我的观察是准确的话,大部分亚裔美国人的女性都愿意与非亚裔的美国男性结婚。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因为白人社会过去对亚裔的歧视并不亚于对黑人的歧视。换句话说,美国社会的族裔和种族的内容正在改变,这些概念都是历史的产物,它们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曾经被认为异类的民族或族裔现在正在变成可以为主流社会接受的群体了。
美国人的“种族”(race)和“族裔”的概念与其他国家或民族对类似概念的理解有重要的区别,区别在于美国式的“种族”或“民族”概念不是与地域概念连在一起的。我们没有类似于巴尔干半岛那样的情形,也没有象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出现的那种不同民族对同一块土地声称拥有所有权的状况。这种土地与种族和民族之间的生死般的联系是数世纪的历史形成的。我们的种族和族裔群体在所有的地方都是杂居在一起的。拉丁裔美国人在西南部有较长的历史,但美国境内的人口流动非常频繁迅速。在美国并不存在那种土地与(民族)血统间的密切联系,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一些民族常常因他们与某一块土地之间的历史联系而要求对其拥有主权,引起冲突,其结果是极大的动乱和破坏。当然,人口流动在其他的国家也在加速。譬如,西班牙的巴斯克(Basques )民族群体就是一种早期民族概念的回光返照,这种概念也许在21世纪就会消逝。或者当它复兴时,它只能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国家认同的概念,如同威尔士语在威尔士的复兴一样。
如我先前提到的,坚持美国例外论的困境之一在于我们有时还没有完全懂得我们所讨论的事物是什么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些事物作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了。许多美国历史学家至今仍在喋喋不休地说,美国之所以例外是因为美国有众多的民族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中国不也是有许多不同民族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内吗?不同的民族和群体生活在同一国度,讲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和遵循不同的历史传统,这一点美国并不特殊和例外。我们只能说美国多元种族和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与其他国家的类似过程是不同的。
王希:除了写作和教学之外,您还同时扮演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在公共历史教育方面投入了许多精力。您是如何看待历史学家与公共知识分子这两个角色之间的联系的?
方纳:我的确希望发挥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尽管我也意识到这样做是有一定危险的。我相信作为学者我们有责任与更为广泛范围的读者分享知识的成果。我的著作有一部分是为专家写的,如我的《自由的立法者们》一书就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书,目的是帮助研究重建史的学者了解黑人与那个特定时期的美国政治的联系,普通读者对此不一定感兴趣。(注:埃里克·方纳:《自由的立法者们:重建时期黑人官员指南》(Eric Foner,Freedom's Lawmakers:A Directory of BlackOfficeholders during Reconstruction),纽约,1993年。 )但另一方面,我也力求用一种为并不是专门研究史、但对历史拥有浓厚兴趣的读者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写作。我最近出版的《美国自由史话》就是属于这一类著作。即便是我研究重建史的专著,虽然是一本典型的学术著作,有成百上千的脚注,但能拥有相当一批普通的读者。(注:埃里克·方纳:《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1863 — 1877 》( Eric Foner,Reconstruction: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1863—1877),纽约,1988年。该书的简写本以《重建简史》(A Short History ofReconstruction)为名于1990年出版。)在该书出版后的12年里,许多人——相当一批人并不在学术圈子工作——都来听我关于重建的讲座,并且告诉我他们读过我的重建史。许多黑人听众——其中也包括那些文化程度看上去并不很高的黑人——也告诉我同样的事。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本书能够为没有受过专门史学训练的人读懂,它所包含的研究成果因此得以传播更为广大的公众。我认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把这样的工作当成很重要的事来做。
我有时也给《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和《民族》(The Nation)这些报纸杂志投稿,也应邀接受电台电视台的采访。当历史学家作这样的事情时,要紧的是记住你此时扮演的是哪一种角色。我给《民族》杂志写稿时,我的角色不仅是一个历史学者而且同时也是一个公民,我写的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意见。我有可能在写作中会涉及到历史上的问题,但我不坚持我在此讨论的历史是一种“绝对的真理”,我的观点是带有历史感的,但只是一家之言。在民主社会,人人有权表明自己的观点,但如果历史学家声称因为自己是研究历史的而对政治问题具有某种特殊的洞察力,那就错了。举个例子,在弹劾克林顿总统的辩论中,有的历史学者经常引用历史研究的结果来证明克林顿总统是否应该被弹劾。我从不发表这样的意见。对克林顿是否应被弹劾,我有自己的看法,但我不认为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意见仅仅因为我是研究历史的就一定比其他人的观点更有价值和说服力。如果一个人要真正懂得弹劾或其他公共政策方面的问题,他必须懂得这些问题是怎样出现和发展到目前这个地步的。正是因为我觉得建立和普及公众的历史认识十分重要,我才决定接受电台电视台的采访,并为报章杂志写一些短文。由于公众的历史知识贫乏才对于历史表现出许多误解,人们太热衷于将历史简单化了,历史学家有责任来努力将正确的历史知识告知公众。这样做实际上也是一种教学活动,一种在教室外的教学。
王希:在成为历史学家的道路上,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方纳:我的父亲是一个历史学家和教师,最近刚刚去世。(注:方纳的父亲是杰克·方纳(Jack D.Foner)(1910—1999), 早年曾在纽约市立大学任教,1941年因参加左翼活动被迫离职,并被列上政治黑名单而长期无法获得正式教职。在这期间,他的研究没有中断,并以工会和社区为讲授历史的课堂。直到1976年,杰克·方纳才被科比尔学院(Colby College)聘为教授,并在那里任教至1982年退休。1986年, 科比尔学院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赞扬他长期以来为“反对种族主义”作出的贡献。杰克·方纳的主要著作有:《美国历史上黑人与军队的关系:一个新的观点》(Blacks And The Military
In
AmericanHistory; A New Perspective),纽约,1974年;《两战间的美国士兵:军队生活与改革》(United States Soldier Between Two
Wars:Army Life And Reforms,1865—1898),纽约,1970年。)由于美国生活的一些特殊情况,他不仅在大学当过教授,而且也在各种非常特殊的环境下教过书。我父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师,他对历史充满了激情。我在两个方面深受他的影响。一方面是他本人在美国黑人史领域内的前沿研究。在我成长的年月里,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了许多在学校学不到的美国史知识,尤其是有关美国黑人的历史。我当时从父亲那里听到的关于内战和重建的许多观点,在今天已经成为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可在当时却是被主流历史观所排斥的,当时学校的课本里也学不到这些内容。父亲对我影响深刻的另一点是他在教学时非常注重教会学生认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他常常告诉学生,只有懂得历史才能懂得现实;为了看清麦卡锡年代,人们必须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发生的“恐红”(Red Scare)运动,或者更早时候出现的惩治叛乱法案, 以及美国历史上其他镇压不同意见的时刻。不了解废奴运动、奴隶制和重建,一个人不可能真正懂得民权运动。历史与现实之间一直在进行一种连续不断的对话。这是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教历史的方法。
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Richard Hofstadter)那里,我学到了一种高品位的史学风格,或者说写作和研究历史的一种最高标准,即始终追求最优秀(而不是次优秀)的研究成果。(注:理查德·霍夫斯塔特(1916—1970),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史研究中“共识学派”的旗手,对1950—70年代的美国史研究有深刻影响,曾被誉为“我们时代最优秀典雅同时也是最富有人文精神的历史智慧”。从1942年直至去世,霍夫斯达特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他曾经拥有的德威特·克林顿美国史讲座教授头衔现为方纳继承。霍夫斯达特最有影响的著作包括:《美国思想中的社会在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
InAmerican Thought)(1944 ); 《美国政治传统及缔造它的人们》(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1948);《改革的年代:从布莱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 The
Ageof Reform:From Bryan to F.D.R.)(1955,获1956年普立策奖);《从革命到内战时期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GreatIssueInAmerican History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Civil War,1765 —1865)(1958);《美国生活中的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in American Life(1962,获1964年普立策奖);《进步时代的历史学家们:特纳,比尔德,帕林顿》(The ProgressiveHistorians:Turner,Beard,Parrington)(1968);《政党制的思想: 美国合法反对党制的兴起》(The Idea of A Party System;The Rise Of LegitimateOppo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1780—1840)(1969);《1750年的美利坚:一幅社会图画》(America at 1750:ASocial Portrait)(1971,published posthumously).)霍夫斯达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但他并不擅长讲课,尤其不擅长给本科生上课。他本人也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尽管他声望很高,又倍受尊重,但要他给本科生讲课,他会觉得是一件很为难的事。可他在给研究生上课或对学生进行个别指导的时候,在他帮助学生改进和提高写作的时候,他的才华就尽显出来了。他总是要求和迫使你去发掘自己最大潜力,他从不接受那种没有最淋漓尽致地表现你的才华的写作。我也是以这种方法来教育和要求我自己的学生。正如你自己体验到的,我对那些我认为是非常优秀的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学生越好,我对他们的要求也就越高。这正是霍夫斯达特的做法。
霍夫斯达特本人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作者,他促使我去努力思考如何使写作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历史学并不向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一门纯科学,历史学是一门文学性很强的艺术。一个历史学者如何传达历史知识和历史影响,取决于他表现他所掌握的历史知识的方式,取决于他的写作能力,取决于他创造叙事、把握思想和史实的流动、以及吸引读者的能力。没有人在写作时可以做到一蹴而就。只有反复不断的修改、斟词酌句和不断的努力和训练,写作能力才有望提高。
我从霍夫斯达特那里学到的另一件事,也是我对他最敬重的一点,是他从不强求自己的学生按他的模子来发展。霍夫斯达特从不打算建立一支浩浩荡荡的追随他的研究大军,跟在他后面去完成他所开创的工作。相反,他总是鼓励和支持学生遵循自己的选择,走自己的道路,但同时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发挥最大的才能。1960年代是一个风云动荡的年代,当时霍夫斯达特与自己的学生在许多政治和其他问题上存有意见分歧,正因为他并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头上,他能够与学生们建立起一种成熟的、带有成年人式的支持精神的关系。这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好教师的典范。
对我具有重要影响的还有其他一些学者。 詹姆斯·申顿( JamesShenton)就是其中一个。(注:詹姆斯·申顿(James Shenton )(1925—),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多次获得该校“伟大教师”(The Great Teacher)的称号。 )申顿教授在学术界不象霍夫斯达特那样有名望,也不是一个特别多产的历史学家,但他对历史研究充满了真正的热爱,并知道如何将这种热爱和对历史的激情通过他的讲课渗透到每个学生的心灵深处,激发起他们对学习历史的强烈兴趣和愿望,这是他的最伟大的能力所在,也是他为什么成为伟大的历史学教授的原因所在。现在我们的历史系不教学生如何教书,令人担忧。如你所知,学生在研究生院接受的训练很多与如何做研究和如何写作有关,学校很少提供有关如何教书的训练。结果是只好自己在实践中去学习。我就是通过观察那些优秀的教师如何上课而学会教书的。
王希:许多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对你叔父菲力普·方纳(Philip S.Foner)教授的著作非常熟悉,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的美国史问题研究者(注:菲力普· S ·方纳( Philip
S.Foner)(1910—1994),美国著名左派历史学家,早期曾因参加左翼活动长期受到政治迫害, 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林肯大学(
Lincoln University)任教,著、编的著作多达百种, 主要代表著作有:《美国历史上的劳工运动》(History of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1947-);《弗里德利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Frederick Douglass)(1950-55); 《古巴的历史及其与美国的关系》(A History of Cuba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1962); 《西班亚-古巴-美国之间的战争与美国帝国主义的降生》(The Spanish-Cuban-American War andthe Birth of American Imperialism,1895-1902)(1972);《美国黑人史》(History of Black American)(1975); 《美国革命时期的黑人》(Black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76); 《美国社会主义与美国黑人:从杰克逊时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American Socialism and Black Americans:From The Age of Jackson
to World War Ⅱ)(1977);《1877年劳工大暴动》(The Great LaborUprising of 1877)(1977);《殖民地时期到世界大战间的妇女与美国劳工运动的关系》(Women and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Eve of World War);(1979);《种族主义,异见与亚裔美国人:1850年至今的文献集》(Racism,Dissent,and Asian Americans from 1850 to the Present:A DocumentaryHistory)(with Daniei Rosenberg,1993).)。您如何评价您叔父在美国史研究方面的成果?
方纳:我来自一个用美国话讲是“老左派”(Old Left)的家庭。我叔父菲力普·方纳是一个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他写了很多书,也编了很多书,他是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正是因为如此,他在美国受过很多迫害,吃了很多苦,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不能教书,他的著作也被主流历史学界排斥在外。他所代表的历史学流派的最大优点是将历史研究的重点放在工人群众、黑人、妇女和受排斥的人民身上。他不仅是劳工史的先驱,也是黑人史的先驱。早在人们还并不关心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时候,他就在研究道格拉斯了,而今天无论谁写美国史的教科书,都必须提到道格拉斯。他的其他一些著作,如他的博士论文《商业与奴隶制》表现了北方资本主义与南部奴隶制之间的联系,至今仍被看作是这个领域的前沿著作。(注:菲利普·方纳:商业与奴隶制:纽约商人与不可扼制的冲突》(Philip S.Foner,Business & Slavery;
The New
YorkMerchants & The Irrepressible Conflict),北卡罗来纳,1941。)
当然,如同所有人的写作一样,我叔父的著作也不是没有缺点或弱点的。缺点之一是他的写作中常常表现出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僵硬和武断,他在著作中有时会对历史人物作过于绝对的政治判断。譬如在他的劳工史著作里,他会肯定地说“这个人是错的,那个人是对的,那个劳工领导人出卖了工人阶级”之类的话。我认为他的著作中也有一种将一些事先决定和设定的概念强加于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倾向。在他早期的劳工史研究中。他往往重工会的活动,而不重视普通工人的活动和生活。但他晚年的研究开始注重劳工运动中的黑人和妇女,他在这方面的成果对后来的研究有关键的影响。对任何一个写作和编著了近一百部著作的人来说,这种研究和写作中不平衡的现象是在所难免的,而且是可以理解的,即便在今天,我叔父的著作在许多领域中是仍然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我刚刚与一位研究拉美史的女研究生谈话,她提到我叔父对古巴和美西战争的研究至今仍被作为该领域内的最重要著作之一。这是一个我并不十分熟悉的领域,但他却能够收集和出版有关的原始史料,供他人研究,尽管其他人使用这些材料时也许与他的出发点不一样。总体来说,我认为他的工作对美国史研究有重要的贡献。
王希:您刚才谈到霍夫斯达特促使您将写作看成是历史研究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也记得刚到哥大时您讲过的一句霍夫斯达特的名言:“百分之九十的写作是重写”(Ninety percent of writing isrewriting),对于许多人来讲,写作,尤其是要写得好, 是一件非常难的事,能不能请您谈一谈您是如何写作的?
方纳:写作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我不害怕写作,而且写得也比较快,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我在牛津大学所接受的训练。我从哥伦比亚学院毕业后,到牛津学习过两年。牛津的教育制度与美国大学不同。我不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如何,也许也有差别。牛津实施一种导师—学生个别指导式的(tutorial)教育方式,每个星期学生都得就一个历史问题写一篇学术论文,这样你就不得不强迫自己多读快写,而且还要学会快速地写不同的史学题目。通过两年的训练,我觉得自己写东西的速度提高了许多。老实讲,一个人如何写作以及为什么能够写得快是一个很难说明的问题。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历史学家可能很少去反思这个问题。对此,我还真得仔细想一想。
至于我著作题目的选择,有一部分是出自于我对当代问题的兴趣,如我的第一本书《自由领土,自由劳动,自由人》,就出自我对美国历史上种族问题的兴趣,也与我所处民权运动时代有关。如果你浏览一下我的著作,你会发现我一直在力图研究美国历史中的不同问题,但这些问题又都集中在弄清政治思想、政治行动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史与政治史之间的联系,这些问题也就是历史学界常称的所谓的“霍夫斯达特问题”(Hofstadter Issues)。
王希:我注意到您与霍夫斯达特的写作中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你们两人都喜欢关注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即一些涉及整体性的问题,而不是倾向于注重个体或个别史实的研究。换句话说,你们不刻意忽视枝节性的东西,但你们注重主干,或者说,你们重森林胜于重树木,而相当一部分历史研究则是对细小的单个的题目精雕细凿,往往出现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现象。这算不算一个比较客观的观察?
方纳:这种观察很有意思。但奇怪的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些写作往往是树木取向性的(tree-oriented)。 譬如说:我在《除了自由一无所有》一书中那篇关于重建时期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小罢工的研究是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注:埃里克.方纳:《解放了的工人》, 刊于方纳:《除了自由一无所有》(Eric Foner,"The Emancipated Worker",in Nothing but Freedom),路易斯安娜,1983,第74—110页。)这是一桩发生在地方的罢工事件,但我把它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来揭示重建政治在不同方面的表现。我的确对类似的微观史做得不多,一般来讲,我的著作是通常采用比较广阔的题目为基本框架。
王希:意识形态是您早期写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分析手段。现在您如何看待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否还算一个有效的研究题目?
方纳:在我过去30年的写作中,意识形态的概念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最初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时,基本上是沿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观点,即将意识形态看成是连结某种社会阶级关系的一种连贯性的世界观。现在人们使用“意识形态”时,更多是以我们先前提到的话语、形象或表象所表现的思想。人们对于思想本身抱有一种比从前更为怀疑的态度,总是力图揭示隐藏在这些表象后的臆想或思想等。但我认为意识形态还是非常重要的。我早期所属的那一代历史学家总是力图重新捕捉(意识形态的)概念。1950年代有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终结的说法,好像美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任何严肃的思想辩论,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意识形态是社会经验与政治行动的连结体。这种认识曾对我的写作影响很大,但我对意识形态的认识的确也改变了不少。在过去若干年,我受赫伯特·戈得曼(Herbert Gutrnan )和汤普森(E.P.Thompson)的影响很深。(注:赫伯特·戈特曼( Herbert Gutman)(1928—1985),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在美国劳工史、 奴隶制史和黑人史研究方面有重要的影响,主要代表著作包括:《工业化美国时代的工作,文化与社会:关于美国工人阶级和社会史的论文集》(Work,Culture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izing America:Essays inAmerican Working-Class and Social History)(1975); 《奴隶制下和获得自由后的黑人家庭》(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Freedom,1790—1925)(1976).爱德华·P·汤普逊(Edward PalmerThompson)(1924—1993),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新劳工史学的创始人,最著名的代表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他们也注重意识形态的研究,但他们总是致力于将丰富的社会史学置于意识形态的画面之中,使意识形态充满了更为丰富、复杂和深刻的内涵,而霍夫斯达特对这种研究意识形态的方法却并不真正地有兴趣。所以,我把自己的写作看成是新旧史学的混合产物。我研究的问题是传统的历史问题,但我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方法却更多更强烈地受到新史学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你也许可以把我现在从事的史学研究称为一种综合性史学(synthe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