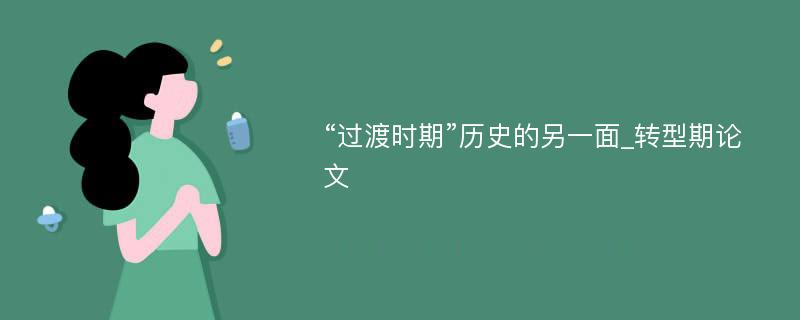
“过渡期”历史的另一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渡期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熟知近代掌故的人都知道,《采菲录》乃是至今为止收集缠足评论最为详尽的一本文集,同时也是观点最受争议的一本文集,因为当时缠足在公共舆论中已被贬为陋俗,文集中却多录奇趣诡异、惊世骇俗之论,读之每每让人拍案叫绝。其文本采择缠足史料不偏不倚,既有旧式文人嗜癖小脚的淫辞艳语,也有对缠足之丑的刻薄谩评,对视缠足为美俗与恶俗者之议论均有载入,这既显示出作者均衡兼容的立场,同时也难免会被误解成有为缠足辩护之嫌。编者姚灵犀曾为三十年代天津休闲刊物《南金》创办人,他在天津一家娱乐性小报《天风报》副刊“黑旋风”上主编了一个专栏,名字就叫“采菲录”,《采菲录》成书出版时,副题为“中国妇女缠足史料”。没想到初编出版后,就颇遭非议,舆论斥之为“专写妇女缠足的风流韵事”,甚至丑诋编者为“拜足狂”。
因此姚灵犀在续编自序中被迫做出反应和解释,对于那些“以此为提倡缠足相责难者”,姚氏表示不能缄默无言。他随即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时至今日,缠足之风岂一编提倡所可得乎?”宣称编辑此书的目的“原欲于纤趾未尽绝迹之前,搜罗前人记载,或赞美之词,或鄙薄之语,汇为一册,以存其真,更取纤趾天足之影,弓鞋罗袜之属,列之以图,附之以表,使阅者知所印证,引为鉴戒”,目的纯粹是为风俗史研究者作参考。这里随即又扯出了一个颇令人棘手的问题,即面对行将消失的风俗,一个历史观察者到底应持有什么样的感情尺度。
一提起“缠足”,现代人的脑海里马上会条件反射出一个古代畸形妇女的形象,各种文学和纪实作品中对缠足妇女双脚备受摧残的反复申诉已变成旧中国黑暗生活的标准写照,与之相对比,处于另一极的“天足”女性却占尽了心理优势,成为印证女性解放的鲜活证据。几乎很少有人注意到,天足形象与一个世纪前文人笔下的小脚美妇形成的巨大反差,终于使生活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二万万中国女性从“美”的化身沦为了丑陋无比的“弱势群体”。可历来的舆论和近代研究者却对此群体遭受的身份与情感的巨大崩落过程置之不理,不愿抛洒一点同情之泪,他们宁愿把所有的鲜花和赞美抛向了享受“天足”愉悦的女性们。
物不平则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个叫老宣的写手终于挥洒出了一纸荒唐言,他说“缠足”与“天足”之分应有一个时代界限,依当时之境况评价美丑的分野才是正理,因为“以古人的眼光议论今人的是非,固是顽梗不化,用今人的见解,批评古人的短长,更是浑蛋已极”,“当今视为圣人的天足妇女,早出世三十年,她们的祖父母,难免不会因为他们家中妇女脚不小,视为奇耻大辱,我们以古证今,更不当对侥幸的她们,妄加推崇!所以美的观念并无一定标准,随一时多数人的习俗眼光就是美。看熟了,就是美,看不惯,就以为丑而已”。这段话出自《对于采菲录之我见》一文,其调子与现代化的主流声音极不合拍,很容易让人误判为“拜脚狂”的同党,不过我倒认为这位老兄面对已经被凝固化的历史观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历史如何“情景化”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看待历史的方式多少有点“成王败寇”的心态,经过现代性目光的反复过滤筛选,现代历史观早已把复杂的历史现场刷满了“善”“恶”二分的黑白对比色,却还自欺欺人地处处打着发现客观历史的招牌,让人们误认为这“现代眼镜”下的历史就等同于“那个时代”的实况,他们没有意识到,缠足女性的丑陋恰恰是被一系列的现代程序“制作”出来的,正如缠足之美亦是在前现代的语境下被制作出来一样,它们分属不同的历史情境。
令人叹服的是,《采菲录》对两种情境的评论均有观照,文集中有述缠足之乐极尽美轮美奂者,如《相莲经》所谓:“双钩翘然,微露膝畔,红尖一角,纤瘦如菱”,再所谓:“房栊深掩,玉盆中注兰汤,背人轻濯双莲,时闻红中蘸水声,若竹梢泻露,濯毕抱膝展素帛,作者蚕自缚状,潜以玉尺偷量,恰在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之折中度数。”更有高呼小脚万岁者,搬出“穷变通久”的古意,歪批“因势利导”的原则,所谓“盖足自具可缠之性,人但因势利导,顺理成章”,高唱“缠足之乐无疆,缠足之福实大,缠足实为舒心快意之事,缠足更为消愁解闷之方”。字里行间喧腾着一股刁蛮的才气,可视角全是男人窥视偷情的目光和意淫的想像。然而谁又能否认,在那个特定场景之下,缠足的确给人带来了美感呢?
缠足被刻意进行由美转丑的现代“制作”,传教士可谓是始作俑者,一开始传教士认为,妇女缠足限制了女性走出家庭奔赴教堂,无疑对灵魂的洗脱不利。不久传教士又倾向于把缠足看做是应在医疗领域中予以观察的行为,试图直接建立起缠足与“疾病”表现症候之间的关联性,从而确立起了一种评价缠足的“卫生话语”,当时像《万国公报》这样的教会报纸曾经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评缠足是戕害女性身体,导致女性健康衰弱的祸首,这种舆论迅速在知识界传播开来,成为主流声音。如《采菲录》初编序言的作者陈微尘医生的话就很像标准的“传教士+卫生话语”,他说缠足女性由于缺乏运动,“气先不足已成定论,加以足帛之层层压迫,使血管受挤,血行至足,纡徐无力。一人每日之血液,本应环行全身一周,若在足部发生障碍,则其周流必生迟滞之弊”。于是各种疾病纷至沓来,都和缠足攀上了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有的说缠足是害所谓“节片淫乱症(fetischismus)”的表现,有的认为缠足应为中国疯癫和灾荒的频繁发生负责。
不过具有悖论意义的是,医疗视角的介入其实并没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证明缠足与健康优劣有什么直接关系,当时非常有名的西医传教士雒魏林在一份报告中就表现出了这种狐疑的态度,比如他说出的这段话真是既啰嗦又暧昧:裹脚的折磨以及其难以为人察觉的后果对健康和安逸带来的危害,也许并不比西方的时尚给妇女带来的痛苦为甚。尽管如此,医疗卫生评价体系的流行确实对缠足的传统形态实施了“丑”的再建构,这种体系使“缠足”与“天足”的区别从仅仅是不同的审美类型,转向了“美”与“丑”的二元对立状态,从而彻底隔开了与“性审美”的实际联系。道理再清楚不过,无论是“天足”还是“缠足”,在赤裸裸的解剖学透视下,只有生理上的公共差异性,没有私人化的审美意义上的差别。结果,解决生理差异性的办法就是寻求女性在生理上与男性平等,而忽视和压抑其原有的身体形态的性征表现,由此展开的“欲望的规训”终于成为近代中国女权主义的滥觞。
在研究十八世纪以后西方医学的变化时,福柯曾经发现,西方近代医学总是把一些不可见的疾病症候通过医学表述为可见的,医学经过凝视与语言,揭露了原先不属于其管辖之事物的秘密,词语与物体之间形成了新的联结。更重要的是,医学视角不但重新设置了“正常”与“不正常”的边界,而且赋予它社会意义,甚至与国家利益和政治动机也建立起了联系。十八世纪以前,治疗和健康的关系基本上被限定在属于医学范畴的圈子内,它和社会秩序是否正常的判断没有太多关系,换句话说,“医学”更是个人化、家庭化的选择,没有人把它硬拉到社会秩序的维持这个层面上来考虑。十八世纪以后,健康/病态的二元对立从医疗语汇扩散为一种社会行为,人们在社会中的行动甚至心灵活动也被用此二元结构加以区分。人们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在历史特定情境下的行为意义,而是由现代性视野内所规定的正常与非正常的两极表现。
传统中国妇女的一双小脚一旦被置于健康/病态的二元框架里加以审视,就会完全超出传统审美的范畴,进而层层被赋予日益复杂的社会内涵,如早年的官方话语就已反复暗示缠足与国运兴衰的关系,张之洞还仅仅是讥缠足使“母气不足”,袁世凯则已说到了缠足“其于种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长之原,有隐相关系者”。这个程度,到了基层知识分子的嘴里,缠足女性又罪加一等,不仅要为女学不兴,民智不育,乃至国人智商的高低,体质的强弱负起责任,而且更要为“国势不昌”承担罪名,以至于各种煽情的结论愈来愈耸人听闻,好像马上就要“举国病废”,到了所谓“四百兆黄种人”瞬间要沦为牛马和奴隶的最后时刻。
进入晚清后期,缠足与国弱民穷的关联性就不是什么“隐相关系”,而是可以大说特说的直接因果关系了。一位四川地方官的表述更加直白:“女子缠足,就会把一国的男子,天下的事情弄弱了。”这种上纲上线的说法大多间接直接源自传教士大胆的医学想像,至于缠足与弱种退化之间素有关联的无稽之谈,则更像是在医疗想像之外,平添了一种政治想像,根本无法加以验证。在这样的氛围里,缠足女性一下子变成了万恶之源,她们恰如吸取男人阳髓的狐精,要为天下兴亡负如此之大的全责,这简直就是变相的现代“祸水论”。如果再说得严重一点,也可以说是男性中心主义话语。因为在这种评价的尺度内,天足妇女也不过被看做生育的机器,而没有女性作为主体自身的位置,其区别仅仅在于,缠足女性担负着家庭道德的象征角色,而天足女性则以隐喻的形式体现民族主义人种延续的实践角色,两者均是男性权力操纵的结果,只不过男性权力分别被贴上了“传统”与“现代”的标签。
如果再稍做申论,缠足女性的身体是在政治化的过程中被改造的,它其实是不断变换的政治需求的载体,这一套身体政治化的策略运作与女性的个体自主意识无关。所以当年老宣就呼吁:“劝人不缠应当以天理人情为题目,不必高谈阔论离开当前的事实,用虚而且远的‘强种’或‘强国’做招牌!说着固然是冠冕堂皇,好听已极,怎奈打动不了愚夫愚妇心坎!应从女性个体对缠足的感受出发立论,以免用高远的政治口号遮蔽了普通百姓的真实感受。”老宣发现,北平各处天足妇女所生的儿女,并不比缠足妇女所生的特别健康,缠足妇女的死亡率也不高于天足妇女,而且天足妇女的疾病也不少于缠足妇女,所以国家的强弱“在人民智愚勇怯,在内心而不在外形,更不专在妇女的两只脚上”。
健康/病态的二元框架也重新分割了“美”“丑”观念相对峙的内涵,同时又想极力剔除女性性征对现代社会秩序的危害性,对缠足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性征”的欣赏,原先只具有私人化或家庭化的特征,可是在现代社会的医学管理观念中,对缠足的审美行为却有可能对社会秩序甚至国家利益造成威胁,因此,对“天足”优点的鼓吹一方面是在女性解放的大旗号下为足部松绑,另一方面又刻意强调在男女平等的意念下尽量消灭女性的特征,女性解放的这把双刃剑终于使缠足具有的审美内涵,经过卫生解剖观念的筛选,使女性重新变成了男性“管理的对象”,只不过这种管理不是在家庭和传统的社交视界内,而是在国家强盛和种族延续的意义上重新定位。近代以来,西方医疗观念对缠足内涵的性征意义带有“禁欲主义”色彩的贬斥逐渐扩散到了服饰穿着和社交礼仪等方面,出现了与男性趋同的社会风气,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五十年代以后出现的女拖拉机手、女飞行员等等并不适合女性从事的职业中出现了不少新女性的面孔,其意义仅仅是想从生理特征上建立起与男性平等的表面关系。
没有人能否认,中国历史课本中写满了激昂亢奋的现代化故事,可这些故事始终给底层的人群投射出的都是一幅幅背影,而且即使能摸糊看到这些背影的存在,也只能是同一尺寸的批量描绘,如量身订做的“农民英雄”形象之类,却透视不出不同阶层的人群千差万别的日常境况,更别说他们的细腻真实的快乐与幸福,失落与忧伤。平心而论,现代化发轫伊始,即是以忽略弱势人群的境遇为代价的,但我们的历史研究往往仅仅从总体入手评价其终极效果,而忽略了所谓“近代过渡期”中不同人群的历史处境及身心感受,我们对历史用暴力获得的合理性结果总是不假思索地予以认可,热衷于暴力训练后达致的快感,甚至写进了历史教科书使之常识化,可独缺一块对变迁中普通人群所付代价的同情性理解,并把这种理解转换为一种严肃的历史反思和分析,仅仅是因为反思这种过程的发生可能会威胁到对最终结果合理性的评价,在这样的历史观的支配下,数千万缠足女性在放足过程中的呻吟与挣扎被压抑在了历史记忆的深处而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对由“缠”到“放”这中间地带的追忆被无情地抹去了,变成了一纸空白,读这种“规律性”铸就的历史容易造成某种阅读惯性和惰性,让人变得心硬如铁。
感谢姚灵犀!《采菲录》改变了我们越读历史血越会变冷的麻木感觉,尽管收录了不少驳杂斑斓的淫辞艳曲,但其中也采择了相当一批当时为缠足妇女请命的文字,如邹英在《葑菲闲谈》中对缠足女性痛苦与愉悦心理相互转换的描述,就颇符当时的历史状态,如其所言,在小脚盛行的时代,裹脚的时候,即使痛泪直流,“待到双脚裹小之后,博得人人瞩目,个个回头,在家时父母面上有光辉,出嫁后翁姑容上多喜色,尤其十二分快意的,便是博得丈夫深怜密爱。所以在那裹足时代,凡是爱好的女郎,没有一个不愿吃这痛苦的”。此话今人看来实属大逆不道的“怪论”,然而却是当时女性的真实心态。今人往往用变化后的眼光去揣摩评估过去人的心思,最终缺乏对历史现场事件缘由的同情性理解,也就难以把握“过渡期”历史转换的真相。而姚灵犀的采择标准却很独到,他把处于不同时期缠足女性的见解平行加以推介,特别注重从“缠”到“放”过渡期女性的亲身经验及其感受,关注她们的痛苦和需求,读起来让人心热。如有位叫余淑贞的女士就认为缠足女子固然深受痛苦,但是变革期的缠足女性除遭缠足的惨毒外,还要身受放足的痛苦,纵然勉强解放,一到寒季十之八九会犯冻疮,到了春天溃烂得无法移动,结果“惟及早复缠,仅肉部做不规则的扩张,绝难增加足力。倘御大而无当之鞋袜,更似腾云驾雾,扭扭捏捏,东倒西歪,转不如缠时紧凑有劲”。余淑贞的建议是,天足之大方既不可改,毋宁略事缠束,以玲珑俏利见长,犹不失旧式之美。不要以为这仅仅是复古怪论,它实际上流露出了对弱势女性的真正体贴,每读到这类文字,我都会涌起一阵莫名的感动。
按经验而论,半大足行走最为困难,缠小了反而容易行走,故时人云:“其不利于行者,多为裹僵之半大足,若紧缠之真小足者,步履反极便捷。”但行政当局往往不分轻重,“禁缠”与“放足”均以一刀切的年龄为断,所以当即就有女性站出来说话,说“放足”与剪辫不同,当街逼剪,一下可以了断,而大多数缠足女性已成断头难续之状,“放足”之后反而难以正常生活。加上各地反缠足黑幕中甚至出现沿街鞭足,拿缠足女性取乐的镜头,更有通过罚款进行贪污的虐政曝光,所以才有了如何使“放足”妇女减轻痛苦的大量议论。另外,缠足痛苦的程度还取决于缠裹时的手法,比如在一篇题为《缠足小言》的文章中,就详述缠足疼痛与否的关键有“熟脚”“生脚”的讲究:“骨又有软硬之分,骨硬者不易裹,易软者易裹,易裹者越裹越小,越小越不疼,妇女谓其脚裹熟矣,不易裹者,一裹即疼,越疼越难裹小,妇女谓之生脚。”没看《采菲录》之前,我还真不知道缠足背后有如此多的讲究,不了解这些讲究,就不会准确知道缠足女性当时的心态,更不理解缠足女性在转型期遭遇到了多大的苦楚。
民国初期,有关“天足”与“缠足”的舆论正处于激烈较量的时期,虽然社会风气转变之快,使“天足论”在精英圈内已占据优势,但底层风气转换显然慢了半拍,这使得“缠足论”时时发起的短促突击颇能奏效。就拿女子体态来说,在持有不同审美习惯的人看来,确有见仁见智的效果,所以“天足论”以体态美丑攻人,显然占不到便宜,所以“缠足论”者反驳说:“故雅观不雅观,须就各样体态范围内而评定优劣,不可以龟鹤同列,而比较其颈之短长也。排斥者取缠足之拙劣者为标准以相讥,驳之者假使取天足之最笨滞者以相稽,其不哑然失笑乎。”
这就是过渡期的舆论状态,一切事物均未有定型,一切变化均未有定论。新与旧,美与丑,善与恶的伦理标准亦难定位,据《采菲录》中的记载,一些年龄偏大的缠足妇女往往以复缠的方式恢复自己理解的美态与舒适,这不但是过渡期的普遍现象,也是女性的自觉行动。如当时的复缠女性严珊英就曾在《复缠秘诀》中小心翼翼地说:“以未缠者缠,固属环境所不许,然已缠者之永葆此宝,与夫已放者之重加缠束,籍返其固有之美,则人各有志,似亦未可厚非。”过渡期出现的“缠足论”与以往缠足鼓吹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强调缠足的现代审美意义和内涵,如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谈美和金莲》,文中旁征博引,专举托尔斯泰与苏格拉底这样的文豪对美的定义为缠足之美加以辩护。严珊英更把“金莲”的缠法分为“古式”与“近式”,增强了“缠足论”的时代感觉,她说,“金莲虽有认为古式美者,然亦有时代之价值,如光宣前犹尚弓底,民初则尚平底,今之复缠者,自应就近代式,刻意缠束,果能尖瘦称是,则底平趾敛,亦列上品”,这是复缠方式迁就现代审美趣味的特例。所以新法行缠,务求极度尖瘦,不求极度短小,而且也开始用现代卫生观念做包装,如复缠后要求多饮开水,多吃水果蔬菜之类,禁吃辛辣浓茶咖啡及其他含有刺激性的食品。
由此可见,转型期的言论,尽管反映出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真实心态,却经过现代舆论机器的有意筛选被排除在了中心话题之外,难免边缘化碎片化的命运,需要有足够耐心的历史研究者把它们重新拼贴起来予以辨析。“转型期”这个词国人并不陌生,但国人心目中的转型概念是在欣赏现代暴力对“封建迷信”的打击快感中获得的。只要能够满足现代化进程的效率,弱者的呻吟不过只是为美好旋律伴奏付出的些微代价而已,可以轻描淡写地忽略掉。如此一来,太多“规律化”的历史使我们习惯于变得如此心硬,心灵感受弱者在历史角落中呻吟的能力脆弱得还不如几十年前的姚灵犀。我手头有一本一九九八年版的《采菲录》选本,这个选本打着全面保存四册《采菲录》中具有史乘价值资料的旗号,实际上仍明显倾向于收录丑化缠足与劝禁缠足的史料,完全无法反映缠足女性在过渡期的抗争命运和复杂心态,这不得不使我们发出疑问,难道我们还要继续心硬下去吗?有鉴于此,我开始考虑拒绝使用“转型期”这个已经过于意识形态化的词汇,而宁可使用“过渡期”这个相对中性的表述,虽是一词之差,但自以为颇有深意焉。
(《采菲录》,初编、续编,天津时代公司一九三六年版;三编、四编,天津书局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印行;辑录本,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