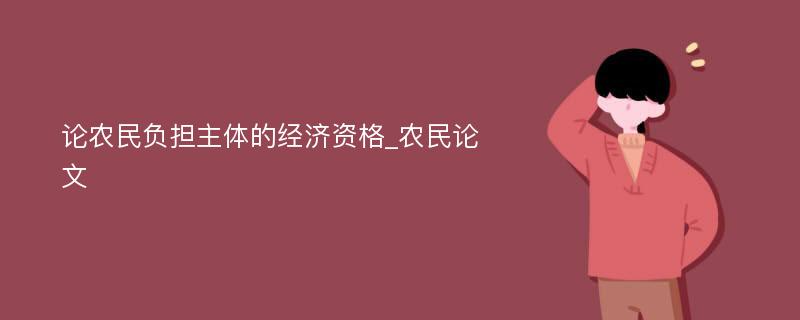
浅论农民负担主体的经济资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负担论文,主体论文,资格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收稿日期:1997-05-29
(黄贻修 怀化地委党校 讲师)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减轻还是加重农民负担绝不仅仅是少拿多拿几个钱的问题,而是保护还是挫伤农民积极性的问题,是促进还是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必须把减轻农民负担问题,提高到这样的政治高度来认识。”[1]也就是说,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是保护农民积极性、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重大问题,是我党在农村工作中的基本政策。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农民负担的构成要素,即农民负担的主体、客体或对象、比例、环节等问题弄清楚。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就是规范农民负担的主体,即弄清农民负担究竟由具有什么样的经济资格的人来承担。
农民负担的主体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把农民负担的主体看成谁,不仅仅是一般的称呼的变化问题,实质上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理论问题。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所称的农民负担,是指农民除缴纳税金、完成国家农产品定购任务外,依照法律、法规所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费、劳务及其他费用。也就是说,农民负担中纳税缴费的主体是农民,真可谓是再明了不过了,可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在农业税、农产品定购任务、乡村统筹提留和劳务负担分摊方面,通常采用这么三种做法:即按农户承包耕地的面积来分摊;一部分按人口分摊,一部分按田亩分摊;全部按人口分摊。这些做法实质上就是忽略了划分农民负担主体的经济标准,混淆了农民、农业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概念。
一、界定农民的经济含义,确认农民负担的真实主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庚德昌说:“农民首先是一种职业,专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口。”[2]这是相对于工人、教师等其他各种职业的人而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广大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追求的是一大二公,很少或几乎没有从事非农业生产和非公有制经济活动,那时的农民和农业劳动力几乎是同一概念,二者不仅在质的方面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在数量上也基本一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农村全面推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尤其是在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农民从土地中解脱出来了。分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的成为离土不离乡专门从事乡镇企业生产的职工,有的成为既离土又离乡进入城镇的打工族。自1989年春节期间第一次出现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寻找工作沿着铁路、公路南下北上,涌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或部分大中城市开始,每一年春节前后都出现一次“民工潮”,至今已有9个年头。据统计,目前我国专门从事乡镇企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大约1亿以上,外出找工作,进入城镇打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1992年达4000多万人,1993年达6000多万人,1996年达近8000万人。就是说,原有的农业劳动力实质上已分离为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从事乡镇企业的职工、进入城镇的打工族等三个部分。也就是说,如果按目前有4.2亿农村劳动力进行统计的话,扣除从事乡镇企业生产的1亿劳力和进入城镇打工的近8000万劳力,实际上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只有2.4亿左右。由此可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负担的主体非但在数量上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在质量上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显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农村劳动力看成是农民负担的主体。一方面,真正的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并能取得一定农业收益的农民只有2.4亿左右,这部分农业劳动力完全具有农民负担主体的经济含义,无可争议应看成农民负担的主体。另一方面,专门从事乡镇企业生产的职工以及远离农村进入城镇的打工族能否作为农民负担的主体,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在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状况下,土地仍是广大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也是农业人口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越是经济落后的地方,这种依赖性越高。因此,耕地承包基本上是按人口平均的。据此,绝大部分农村把家庭承包耕地作为分摊农民负担的根本标准。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告诉我们,农民在拥有一定量耕地经营权的条件下,就可以取得一定量的绝对收入。这一收入的产生条件是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的资本有机构成,产生的原因是国家作为土地所有者所具有的垄断所有权,国家就凭着这一权力获得参与农民纯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经济权力。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还告诉我们,农民在拥有一定量耕地经营权的条件下,土地的地理位置好坏和肥沃程度不同,投在生产条件不同的土地上的同量资本,具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收益,即土地的级差收益。国家作为土地所有者和对特殊土地的经营垄断权也可获得参与级差收益分配的经济资格。加之农业税、农产品定购任务、村提留乡统筹都具有收益税费的性质,是农业劳动与耕地结合所得收益的一部分,劳务又是针对具有劳动能力的人而言的。因此,在现阶段,对土地的经营权和对土地所有的垄断权及特殊土地的经营垄断权是农民负担和国家参与农业收益分配的经济前提。无论怎样,如果乡镇企业职工和进入城镇打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在继续承包的话,那么他们仍是农民负担的主体,这恐怕也没有什么异议。但如果作为乡镇企业的职工和远离农村的城镇打工族转移了耕地承包关系,已放弃了基本生产资料土地,那么这部分人就丧失了作为农民负担主体的经济资格,这部分人如果仍被看成农民负担主体的话,那就有些名不副实了。
二、农业人口能否作为农民负担主体的经济分析
“农业人口是指农民以及他们所赡养的人口。”[3]这不能完全作为农民负担的主体。这其中只有真正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并能取得农业收益的农村劳动力才是真正的农民负担的主体。而不直接或不能直接参与农业劳动的人就不能作为农民负担的主体。根据确定劳动力年龄阶段的界限,凡年龄在规定的具有劳动能力范围以外的人口,即年龄小于18周岁,或者男的大于55周岁,女的大于50周岁的人,这部分人本身不具备或不再完全具备从事农业生产并获得农业收益的能力,相反还要依赖他人抚养方能生活。这部分人因为不具备或不再具备作为农民负担主体的经济资格,所以在农民负担问题上显然是假主体。农民负担问题的实质是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也就是说农民负担是国家及各级政府凭借政治经济权力参与农民纯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体现方式。农民负担的对象是农民纯收入,即“农民总收入中实际归农民个人所有并可直接用于积累和消费的那部分收入。”[4]农民及赡养人口所消费的那部分实际上是属于满足其生存需要的,只有积累部分是用于享受和发展需要的。严格意义上说,只有积累部分,才能够用于国家参与的农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正因为如此,在农民负担问题上才有对贫困人口及没有劳动能力人口负担的减免问题。可见,农民负担问题,其实是对农民纯收入中用于积累部分的再分配问题。不具备农业劳动能力由农民赡养的人口,其自身的生存资料都是由他人提供的,因此就无从谈起为社会提供积累的事。所以,这部分人就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农民负担的主体。
三、农村人口能否作为农民负担主体的经济分析
“农村人口是指农民、乡镇企业职工、进入城镇打工的人以及他们所赡养的人口。”[5]农村人口实际是以户籍制度划分的所谓拥有农村户口的那部分人群集合体。这是世界上包括朝鲜、我国在内的少数几个国家的特殊的户籍制度所导致的特有现象,这往往成为农民负担实际工作中划分主体的重要标准。把农村人口当作农民负担的主体有其便于操作的优点,因为一方面由于我国广大农村受半殖民地半封建思想的影响较深,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严重;另一方面在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地方是按人口平均分摊耕地的,有的为了体现所谓的绝对公平,甚至根据耕地的地理位置和肥沃程度使丘块细分。把农村人口当作农民负担的主体,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土地作为农民负担前提条件的要求,体现了所谓“公平”的社会要求。但忽视了农业劳动作为农民负担源泉的经济条件,因而导致了看似公平合理实则不均衡的畸形负担,没有真正体现按负担能力负担的根本要求。更何况从事乡镇企业的职工、进入城镇的打工族在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已经负担了一定税费。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不考虑其耕地承包关系而一味地将他们作为农民负担的主体的话,无疑有重复负担之嫌。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乡镇企业的职工和远离农村进入城镇的打工族,要根据其离土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其是否属于农民负担的真实主体。凡转移土地承包关系,不再具有农业基本生产资料的真正离土但不离乡的乡镇企业职工和真正既离土又离乡的城镇打工族,当然不能成为农民负担的真实主体;凡没有转移土地承包关系,即真正不离土又不离乡的乡镇企业职工或者虽然离乡但不离土的进入城镇的打工族,理所当然地仍是农民负担的真实主体;凡不具备农业劳动能力或丧失农业劳动能力的人,即由农民、乡镇企业职工、进入城镇的打工族所赡养的农村人口,显然不能成为农民负担的真实主体,充其量是农民负担中的假主体。鉴于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民负担的真实主体应该是具有完整经济意义的、拥有一定耕地经营权的农村劳动力,和既拥有一定耕地经营权、又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
注释:
[1]《农民负担读本》第8—9页,湖南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97.2
[2][3][5]《中国农民二亿四》,《经济晚报》1997.3.16
[4]《经济计算辞典》第123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1.9,第1版
标签:农民论文; 农业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城镇人口论文; 三农论文; 农村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