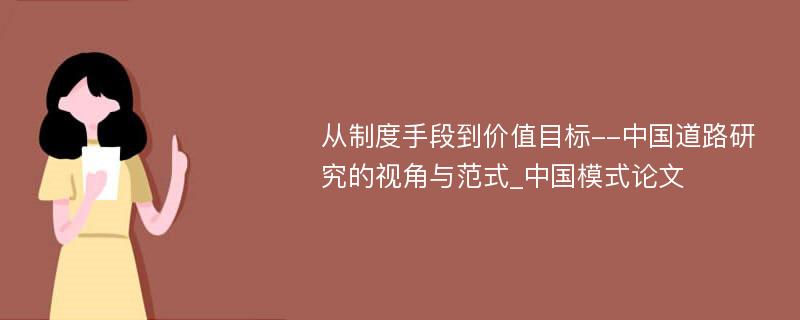
从制度手段到价值目标——中国道路研究的视角与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手段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4)9-0165-06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国经济保持连续三十余年年均国民生产总值9%以上这一同期全球最高的增长速度,不仅温饱问题早已解决,而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比较而言,可以说我们“富”了、“强”了,我们因此在国际社会赢得了“中国奇迹”“中国震撼”等各种美誉,同时也遭遇着“中国崩溃”“中国威胁”等种种猜忌,国内广大民众在见证和分享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由于巨大社会变革及其所带来的一些负面问题而开始对中国道路产生质疑。面对美誉、猜忌和质疑,我们只有弄清楚“道路”的本质属性,然后才能重建共识,做到道路自信,也才能从特殊走向普遍,进而为人类文明做出较大贡献。 一、几种基本视角 面对三十多年来的中国发展历程,国内学者习惯称之为“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境外学者喜欢用“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来指称。不管使用什么概念、称谓,人们对于中国道路的研究大致呈现三种视角。 第一,经验-模式的视角。这个视角主要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什么或者说中国道路缘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对此,国内学者大多习惯于沿着主流意识形态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种形态(即道路、理论、制度)的思路,使用官方话语,从“三位一体”“四位一体”或“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出发总结经验。按照这个逻辑来看,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那么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不言而喻的。① 但是,如果抛开这个逻辑,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建设等具体实践维度来看,中国发展道路在经济上实际遵循的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曾尝试过的东亚模式,即“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②在政治上表现为“混合体制”,即中国道路吸取了东亚威权主义、苏联列宁主义、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拉美社团主义等优秀因素,并与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政治体制相结合;③在社会上则表现为由“分散流动的家庭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平等社区和工作单位构成中国的社会网格,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天然重合而形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等四个支柱构成的“社稷”型社会模式。④ 如果将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放在一起来考察,相比原苏东地区转型国家,中国道路坚持的是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的“渐进改革”;⑤相比经典社会主义或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国道路可以概括为“市场列宁主义”或“市场社会主义”,即经济上已经实现了市场化改革,而政治体制、政治结构还是列宁主义的;⑥相比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国道路似乎又像是经济自由主义与共产党长期执政相结合的“自由(市场)威权主义”,⑦或者说是在保持强势国家行政力量的基础上、让社会成员与企业获得一定经济自主性的“强国家-弱社会的新权威主义”,⑧甚至被人看作是既融合了资本主义发展原理、又受国家指导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⑨ 第二,现状-未来的视角。这个视角主要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现状来评估其未来走向。一般而言,从中国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所表现出的超强学习能力和适应性来看,可以坚定地认为它是非常有前途的,即使有再多问题,也是体制内问题,因此也都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而得以解决。⑩尤其是考虑到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城镇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目前中国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城镇化率也只有45%,离完成工业化和达到城镇化中等发达水平还有很大空间,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经济还将继续保持二十年到三十年的高速增长。(11)这种观点在西方就表现为中国道路“胜利论”,即中国不改革也能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已经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中国普通民众对中央政府一直保持高支持率和高信任度,导致中国崩溃的社会力量还没有形成。(12) 但是,如果考虑到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结构失衡、环境污染、权力寻租、贫富分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的经济长期以来“两头在外”(即“技术”和“市场”依赖于人),我们既不掌握工业生产的核心技术也不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我们“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3)因此,中国道路的未来,要么是“回到新民主主义”,因为“只有通过新民主主义道路才能解决贫富差别和腐败问题”(14)要么是“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因为“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5)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在经济上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在政治上必须转向西方民主模式,即中国道路“改革论”;否则,不仅经济不可持续,而且社会还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动荡,中国或将走向“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崩溃”,即中国道路“崩溃论”。(16)事实上,一旦采取西方式的体制和价值观,那么也就意味着放弃中国道路而与西方趋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所谓的“改革论”和“崩溃论”可以说是同一个概念。如果承认腐败和两极分化已经演化成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同时又认识到中国未来仍然存在的巨大发展空间,那么中国未来显然是存在各种可能性的,也即中国道路“不确定论”。(17) 第三,影响-意义的视角。这个视角主要关注中国道路具有怎样的国际影响或者说能否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意义。一般而言,如果承认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就,承认中国的成功向世界展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那么中国的成功就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也“丰富了世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18)或者说“为多元现代性提供了生动范例”,尽管中国的发展模式像任何国家发展模式一样没有类型上的普遍意义,但是却具有因果上的普遍意义,因为中国是一个特大型国家,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使得其他国家今后的发展或多或少要对中国发展作出回应。(19) 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政府对经济领域强有力的国家干预,以及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口红利”等,那么,中国道路的具体经验和独有特征恐怕只能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具有借鉴意义,甚至只有朝鲜、老挝、越南和古巴这样的列宁主义政党国家才有可能借鉴。(20)也许正是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强大吸引力和影响力,才导致西方社会将其视为“挑战”“威胁”,因为这种影响或将终结西方的自由市场制度并引起发展中国家拒斥西方的多元化民主政治。(21) 就中国道路研究的现有成果而言,无论是基于“经验-模式”的视角,还是基于“现状-未来”以及“影响-意义”的视角,都属于“制度手段”的研究范式,即突出中国道路在制度手段上相对于其自身过去以及其他发展道路/模式的结构性特征,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中国道路所为之追求的价值目标。按照这种研究范式,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相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或经典社会主义标准,中国道路似乎已经“异化”“变质”;相比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中国道路是个“异类”,其未来要么与其“趋同”,要么成为其“威胁”。 二、关键在于回答“我是谁” 历史本身是一个多棱镜,在不同学者眼中,自然会呈现不同面貌和色彩,更何况中国最近三十余年的发展是一个连接着过去和现实并将走向未来的当代史,中国发展本身又是一个涵盖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多重任务的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面对“成就”,人们希望搞清楚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国内外的研究往往倾向于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揭示中国推动发展的具体做法。所以,就有了“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渐进改革”“强势政府”“威权主义”等各种说法。但是,孤立地看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在有些人看来是成功的经验,在其他人看来则可能是很多现实问题之所以存在的根源或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何况有些因素在改革开放前就存在,有些因素在其他制度环境下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并未产生相应的效果。即使我们承认这种经验模式下的这种成就,我们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经验模式下的成就对于当今国人以及未来子孙又意味着什么的问题。相比探讨“成功的要素有哪些”,搞清楚这些要素普遍遵循着怎样的价值原则并追求怎样的价值目标更为重要。 面对“问题”,人们希望搞清楚中国道路的未来走向。国内主流话语一般强调,所有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因此可以通过改革在现有模式和体制内解决;一些人往往把所有问题都简单地解释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结果,因此主张回到改革开放前甚至新民主主义;另一些人则倾向于把一切问题都归因于没有按照西式民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因此主张放弃社会主义。(22)退回“老路”,显然不可能,因为国人对其痛苦记忆犹在;复制西式道路,也行不通,在当前无论欧洲民主社会主义还是欧美新自由主义都为危机所困,都在反思并努力寻找出路,更何况事实早已证明西方所秉持的“经济-趋同”(23)逻辑根本解释不通中国现实。要搞清楚中国道路的未来走向,首先要明确发展中的问题的实质。 面对“影响”,人们希望搞清楚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人们往往强调中国道路相对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从而证明其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但是,如果说中国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对威权政治的坚持,体现在具体做法上对“华盛顿共识”或新自由主义某些信条的拒绝,那么中国道路就很容易成为西方人眼里的“挑战”“威胁”。当然也有学者强调中国的经济总量以及世界各国因此而做出的回应,从而说明中国道路具有“因果意义”上的普遍性。但是,强调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更会导致周边国家的担心和西方的顾虑,因为国际上尤其是西方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大国崛起必然引发对抗和冲突”的理论和思维。如何看待中国相对于其他道路/模式的共性和个性,如何说明中国道路之于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贡献而不仅仅局限于对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借鉴和启示意义,才是我们更需要回答的问题。 人类发展道路是指以现有社会条件为起点、通过包括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手段而走向理想目标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目标与手段的统一,也是价值与制度的统一。价值、目标相对稳定,而制度、手段相对易变。因此,判断一条道路的本质属性,其主要依据应该在于前者而非后者。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性,导致国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对中国道路的性质充满质疑和歧见,也成为国际社会认为中国道路“神秘”“异类”甚至“威胁”并对中国未来发展表示“不确定”的重要根源。 三、从“制度手段”到“价值目标” 中国道路要想谋求更长远的发展和更大的影响力,就需要论证其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就要首先弄清楚“我是谁”,然后明确“将向何处去”以及“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但当我们面对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就和存在的严重问题时,我们陷入国内话语不统一、国内外话语不交融的尴尬。(24)这在客观上,是由于中国发展所涵盖的历史任务的多重性和当代中国社会实践所呈现的不同发展模式、不同文明要素的纠结甚至胶着状态;在主观上,则是由于我们囿于“制度手段”的思维逻辑和解释框架,而忽视了价值追求才是制度设计的灵魂和国家认同的载体。 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正反面的经验教训也已充分展开,尤其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寻找出路,曾一度宣称意识形态终结的西方右翼也在自我反思。因此,我们现在有必要、有条件、也有信心创新意识形态,追问中国道路的目标指向及其成就背后的动机与意义,建构一种向世界“讲得通”、世界也能“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系统。这种“创新”不是从无到有的另起炉灶,而是在既有理论基础上建构一种基于“价值目标”的话语系统;这里的“理论基础”正是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最新成分”(25)的社会主义。 第一,“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西语中的社会主义总是和现代性问题联系在一起,在那里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目标,一种“永恒的超越”和“乌托邦”,然后才是一种手段;在中国这样的后发的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首先是作为实现赶超式现代化的手段,其次才是一种目标样式。但是,如果对世界各社会主义流派及其实践进行追问,对它们所追求的目标以及用来实现目标的途径、政策和用来诠释这些目标、途径的意识形态进行辨别,不难发现,其间最大的共识在于价值追求而非实现价值追求的具体制度和手段。相比价值,制度往往是阶段性存在。就世界社会主义共识性的价值追求而言,如果按照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结构,可以将其大致归结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公平正义”“人的全面发展”等多个维度。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不是单个维度,而是由一系列价值目标和价值原则构成的相互联系的整体,因此不能孤立地看,更不能片面地强调哪一方面。但是,这些价值追求之间的排序方式,在不同国家、不同时间可能会有变化。在横向上,不同民族国家选择不同的排序,就会影响到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最终在实践上表现为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样式,在理论上就表现为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在纵向上,同一个民族国家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历史任务而选择不同的排序,从而表现为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26) 第二,从价值维度来审视“中国道路”的本质属性。价值追求没有什么象征,却可以进行比较,比较的最终标准是人的解放程度,比较的对象要么是同一空间环境下的时间上的前后比较,要么是具有相似时间性的空间上的横向比较。因此,从价值追求来审视“中国道路”的本质属性,除了要明确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和“价值目标”,还得选择合理的“参照坐标”。基于世界的、历史的、现实的视野,从社会主义价值维度,全面且动态地考察中国道路,无论是相比西方现代化走过的路,还是相比我们自己的前三十年,无论是相比原来模式相似但后来剧变的原苏东地区,还是相比发展基础相似但是路径选择截然不同的印度和拉美,我们都可以自信且负责任地说,执政党的纲领政策的目标指向与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更契合了,我们的综合发展成效相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目标更接近了,而不是相反。显然,我们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而是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在性质上,不是在经典社会主义意义上作为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利用资本并试图超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缺陷;这条道路也不是苏联模式理解的片面强调结构性特征的社会主义,而是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功能的新社会主义。如果说中国道路超越马、恩等经典作家的理论预设,超越民主社会主义等西方实践,超越苏联式的传统社会主义,也有别于我们自己的过去,那么这种“超越”或“区别”,主要体现在价值追求排序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制度手段”上,而非价值追求本身上。相比较而言,前者可以是“特色的”,而后者往往是“普世的”。 第三,从价值维度来指引“中国道路”的前进方向。从社会主义价值维度来考察中国道路,不仅仅在于肯定成绩,明确方位,更是为了在肯定实然的同时直面发展中的问题,直面我们当前与社会主义应然之间的差距。事实上,只有从社会主义价值维度来审视中国道路,才能看清当前这个世界正在失去什么,我们又希冀着什么,从而认清中国道路的未来方向与发展趋势;只有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和本质要求出发,我们才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自觉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主动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而不必囿于既有制度、体制的束缚。尽管我们不像西方社会那样时刻面临在野党的意识形态挑战,但是我们却存在来自国内各类思潮的压力和来自国际上新自由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竞争和比较。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大背景下,如果还继续改革之初“摸着石头过河”的准则,我们将丧失话语权,也很容易为其他思想或思潮所干扰而迷失方向。因此,我们应以社会主义价值原则为标准来准确判断现实问题的性质和程度,既不因忽视问题存在而错失改进机会,前功尽弃;也不因夸大问题严重性而惊慌失措,自己吓倒自己。(27)囿于制度束缚而踯躅不前,是不足取的。现实而可行的,是以社会主义价值追求来指引中国道路的前进方向。 第四,从价值维度来理解“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政策变迁过程置于世界视野来考察,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设置自己的政治议程,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经常面对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两难,进而揭示我们在解决中国问题背后所凝结的普世的思想原则、价值理念和政治智慧。价值语言是走向大同和赢得尊重的关键。社会主义是“普世的原则”,也是“世界级的梦”,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中国道路在世界层面的重大贡献和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目前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而在于它正努力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一种替代经验;不仅仅在于它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而在于其通过自身的“成功实证”彰显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振兴的曙光、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重塑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并为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添加新的元素和标记。显然,强调“特色”不会增加我们对发展规律的认识,也不利于我们把中国经验推向世界。(28)一味地强调“中国模式”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或者一味地强调“中国特色”,主张各人自扫门前雪,都不是社会主义应有的情怀,也很难赢得世界的认同和尊重。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不能理解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就很难理解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总之,要把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中国故事讲好、讲通,把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中国道路的本质属性、未来走向和世界意义讲清楚、讲明白,就必须重构社会主义解释框架,必须转换研究范式:从制度手段走向价值目标。 ①李君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俞可平:《我对中国模式充满期待》,《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24日;程恩富:《如何理解“中国模式”》,《人民日报》2010年9月15日;袁秉达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②Thomas I Palley,Ex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Model:Export-led Growth and the Dangers of Global Economic Contrac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6 15(46); Nicholas R Lardy,China:Toward a Consumption-Driven Growth Path,Policy Brief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Oct.2006; Seung-Wook Baek,Does China Follow 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35,No.4(2005). ③David Shambaugh,China's Communist Party:Atrophy and Adap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Apr.2008)。 ④潘维:《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http://ccga.pku.edu.cn/html/chengguo/20090903/1833.html。 ⑤⑩张维为:“中国模式背后的理念及对解决世界问题的影响”,2009年7月17日做客人民网“七一社区·理论论坛”访谈。 ⑥朱学勤:“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总结”,2007年12月15日在广东省科技图书馆的报告;T.安德烈阿尼:《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是否意味着“中国模式”的必然终结?》,《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5期。 ⑦Rowan Callick,The China Model.The American,Nov /Dec.2007 Issue. ⑧萧功秦:《中国模式的弱势与不足》,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1_01_04_52816.shtml,2011-01-04. ⑨Ian Bremmer,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Who Wins the War between States and Corporations? Portfolio Hardcover,May 2010; Yasheng Huang,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11)龙永图:“城镇化将推动中国高速增长二三十年”,在2010年12月26日“央视财经全国巡讲”上的演讲。 (12)David Shambaugh,China on the Road to Prosperity,TIME Magazine,Sep.28,2009; Andrew Nathan,Reframing China Policy,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events/?fa=eventDetail&id=854.The Carnegie Debates,Oct 5,2006; Anthony Saich,The Outlook for China,http://www.brookings.edu/events/2010/0318_china.outlook.aspx. (13)戴旭:《中国能否摆脱下一场战争劫难》,http://news.xinhuanet.con/mil/2010-01/27/content_12881754.htm。 (14)《张木生再举新民主主义大旗》,《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37期。 (15)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16)Thomas I.Palley,Ex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Model:Export-led Growth and the Dangers of Global Economic Contractio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6.15(46); Roderick Macfarquhar,The China Model Vs.Democracy,http://www.associatedcontent.com/article/2111319/the_china_model-vs_democracy.html?cat=37; Will Hutton,The Writing on the Wall: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21st Century,2007. (17)姚树洁:《中国未来发展之我见:路漫漫其修远》,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50-4104.shtml。 (18)黄仁伟:《中国道路的历史超越和国际解读》,《求是》2012年第21期。 (19)童世骏:《中国模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社会观察》2010年第12期。 (20)姚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1页;David Shambaugh,Is there a China Model? http://debate.chinadaily.com.cn/debate.shtml?id=13; Martin K Whyte,Paradoxes of China's Economic Boom,Th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July 2009。 (21)Ian Bremmer,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Who Wins the War between States and Corporations? Portfolio Hardcover,May 2010; Stefan Halper,China model.www.economist.com/debate/days/view/553. (22)萧功秦:《警惕激进主义的陷阱》,《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25期。 (23)所谓“经济-趋同”逻辑,就是指以经济改革为起点和以政治民主化为目的,或者说经济自由化必然导致政治民主化。英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G.怀特(Gordon White)在《骑虎难下:后毛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一书,所说的“虎”,就是指“经济自由化”。言外之外,就是中国一旦开始经济自由化,其目标指向必定是“政治民主化”,否则经济成功会引发“政治衰竭”。参见Gordon White,Riding the Tiger: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London:Macmillan Press,1993。 (24)公方彬:《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人民论坛》2012年第28期。 (25)童世骏:《中国模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社会观察》2010年第12期。 (26)轩传树:《社会主义本质再追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4期。 (27)张维为:“百国归来的思考:中国模式及其国际意义”,2008年10月30日在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的演讲。 (28)姚洋:《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第80页。标签:中国模式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