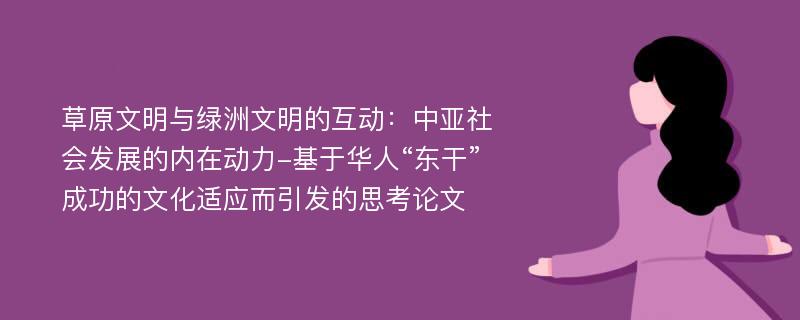
草原文明与绿洲文明的互动:中亚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基于华人“东干”成功的文化适应而引发的思考
李建宗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7)
摘要: 在中亚草原和绿洲的基础上生发出两种文明类型——草原文明与绿洲文明,它们不仅相互嵌合在一起,还一直处于互动状态。由于内生性需要,游牧社会需要农业生产,19世纪东干人在楚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受到当地民众欢迎,就是一个典型个案。绿洲作为孕育中亚地区草原文明与绿洲文明的基地,使得草原与绿洲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性关系。中亚地区的草原文明与绿洲文明是动态的,一直在进行着相互转换。草原文明与绿洲文明之间的互动是中亚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 绿洲文明;草原文明;互动;中亚
“东干”是中亚地区最大的华人群体,也是成功地适应了中亚社会的华人。作为移民的“东干”为何能够成功地融入中亚社会?笔者以为,其成功性不仅在于其自身文化主动变迁的积极适应性,而且在于其与中亚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的契合性,即草原文明与绿洲文明的互动为之成功的文化适应提供了契机和场域。如果说“东干”的主动文化适应是内因,那么后者就是外因,正是内因与外因的合力使“东干”成功地嵌入在了中亚社会中。本文主要探讨的是这个外因。
(4)查询模块。该模块主要完成用户对的搜索内容的认别及对认别结果的反馈。分别制定以“内容”为主的查询规则(关键句查询)和以“主题”为主的查询规则(关键字、词查询),设定查询控制方式并与信息采集模块、索引模块的信息抓取和索引方式对应,通过对关键字、词、句进行精确解读,建立与索引文件的联系和信息比较,便于用户完成筛选和获取所需信息。
中亚是一个地理概念,关于中亚范围的界定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概而言之,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界定,李琪指出:狭义的“中亚”,“东联中国,北靠俄罗斯,南邻伊朗、阿富汗,西达里海,构成一个具有独特地缘结构的纵横捭阖之地。”[1]本文所说的中亚是指狭义的中亚。中亚地区的地貌形态主要有草原、绿洲、戈壁、沙漠、雪山、湖泊等,其中草原和绿洲不但承载了人类,还相应地形成了一些文明类型,主要是草原文明与绿洲文明。每当提到绿洲的时候,人们总是把绿洲与农耕文明关联在一起,同样也把草原和游牧社会相结合,形成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其实不然,在中亚地区的草原文明与绿洲文明之间密切关联。袁剑指出:“当我们具有针对性地面对中亚各个阶段的文明样态及其表现形式时,就必须呈现这一区域农耕与游牧及其所在区域之间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联。”[2]草原文明与绿洲文明之间的互动是理解中亚社会的一把钥匙,也是深入认识丝绸之路的关键,就像黄达远所说,丝绸之路 “作为巨大商路网络连接起游牧、农耕与绿洲世界。”[3]
属于干旱气候的中亚地区,降雨严重不足,但在其内部有相对丰富的河流与地下水资源。中亚周边地区有兴都库什山、天山等一些大的山脉,来自这些高山的冰雪融水,是中亚地区众多河流的源头。中亚地区的河流以及丰富的地下水资源是绿洲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往往在大河流经之地或者不同河流汇聚之处,生成中亚地区的大绿洲。一般情况下,一旦提及中亚,人们总会想到的是大草原以及在草原上的游牧社会,甚至曾经统治过中亚地区的一些有影响的草原帝国。中亚地区边缘及内部的高原和山地,是欧亚大陆适于游牧的地带之一,历史上出现过有影响的游牧社会。就中亚地区的游牧本身而言,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形态。在不同海拔地区的牧场和草原类型有一定的差异,饲养着不同的畜群。当然,中亚地区不可忽视的一种游牧是戈壁游牧,在一些大面积的戈壁地区,形成了戈壁草原,历史上出现过一些游牧社会。然而,在绿洲附近的戈壁地带,往往不同于纯粹的游牧社会。
一、内生性需要:游牧社会中的农业生产
杨建华等认为:“在游牧文化的最初形成阶段,整个欧亚草原地区发现的属于游牧遗存的数量还非常少,这说明游牧可能最先是在小范围内发生的,但是一旦部分地区产生了这种经济方式,就需要有足够的辅助生业来支持,很可能这时期人们选择了掠夺作为辅助。”[4]游牧社会内部需要多样化的生产方式,当内部无法满足这种要求的时候,就会从外部世界来获取资源。因此,历史上的游牧社会与周边地区的物品交换、商业贸易,甚至对农耕社会的掠夺几乎是一种必然。同时,在游牧社会的内部还出现了一些规模不大的农业、手工业以及狩猎等辅助性的生产方式。在中亚大草原地区,需要大量的农业产品来满足游牧社会内部的广大民众,毫无例外,这些农业产品的获取主要有两条途径:其一是内部生产,其二是外部获得。相对于内部生产而言,外部获得的成本更高,在这种情况下,中亚草原游牧社会更多地考虑农业产品的内部生产问题。于是,在一些适宜耕作的地区,特别是能够利用水资源的地区设法开垦农地,从事农业生产。当农业生产出现一定规模时,便出现草原内部的绿洲社会。不过,与大绿洲相比较,在草原内部形成的绿洲规模显然还是比较小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曾经把绿洲分为沙漠绿洲和草原绿洲,[5]在中亚大草原的内部或者边缘地区,出现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区域,形成了一些零零星星的草原绿洲。中亚七河地区在历史上已经有大片的草原绿洲,出现过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据《七河史》记载,公元六世纪时期,在阿姆河与楚河之间,“居民一半务农,一半经商。贸易中心是素叶水城,亦作碎叶”。[6]19世纪以来随着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控制和经营,中亚的农业规模空前扩大,大量其他地区的移民进入中亚,在中亚草原进行开垦土地,从事农业生产。于是,中亚草原的绿洲面积进一步扩大,特别是楚河流域的平原地带。
与绿洲相关的是城市,在中亚绿洲上兴起了大规模的城市,这些绿洲地区的城市在中亚的族群流动与文明传播过程中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中亚绿洲城市的规模有所变化,中亚的商贸业贸易中心也在进行转移,曾经一段时间,布哈拉、撒马尔罕是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G.勒·斯特兰奇(Guy Le Strange)在论述中亚的乌浒水(Oxus,阿姆河)地区时指出:这一区域“最重要的就是粟特(Sughd)地区,即古代的索格底亚那(Sughdiana), 其有两座首府——不花剌(Bukhārā)城和撒马儿罕(Samarkand)城”。[16]中亚历史上兴起的一些大城市,比如布哈拉(不花剌)、撒马尔罕等,不仅仅曾经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商业贸易的中心。《世界境域志》中关于“河中地区及其诸城镇”的描述中提到了布哈拉、撒马尔罕,粟特、渴石、忽毡、费尔干纳等城镇和地区,[17]并对当时中亚的两座大城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是这样描述的:“布哈拉,是一座大城,它在河中算是最为繁荣的。”[18]“撒马尔罕,是一个巨大、繁荣、很美丽的城镇。全世界的商人都到这里来。”[19]以布哈拉、撒马尔罕等这些重要城市为基础形成了一些大的城市群,其中包括苦盏、讹答喇、基什、梅尔夫等,[20]其实在《世界境域志》中对这些城市群进行了更为详细地描述。就如G.D.古拉提(G.D.Gulati)指出:“中亚地处中国和印度、中东、欧洲的贸易交会处,欧亚之间的货物运输需要依靠中亚的城镇和绿洲作为中转站。”[21]这些中亚地区的绿洲城市群成了商业贸易的重要基地,相应地也成了中亚地区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平台。
历史上中亚地区的草原与绿洲二者之间一直在进行着相互转换,即便规模不是太大。不同时期草原与绿洲之间的比重是不一样的,在特定历史时段的草原过一段时间之后可能成了绿洲,同样,某一历史时期的绿洲在另一时期可能会变成草原。就中亚绿洲社会的规模而言,也呈现出一种动态性,由于政治中心的变更,中亚地区的一些绿洲有可能被冷落,相反,一些绿洲由于某种机缘开始变得热闹起来。塔什干的兴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8世纪末,以塔什干城为首的锡尔河北岸城市取代了河中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城的地位。”[32]如果用长时段的眼光来认识中亚地区的社会变迁,就会发现中亚地区草原与绿洲格局的变化,以及中亚绿洲城市的变迁呈现出一种动态的过程,特别是19世纪以来绿洲面积的扩大,就意味着草原面积的萎缩,同时也是草原文明趋向衰落的开始。
脱离人民群众,一切是空中楼阁。群众路线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路线。1925年10月中央扩大执行会的决议特别强调: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的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和依靠群众。作为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方志敏谙熟党的根源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方志敏始终把党和人民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一生履行“忠实的为群众谋利益”。在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他总是从解决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引导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方志敏自述》)[1](P3),方志敏忠实地践行了党的根本宗旨。
二、共生性“基地”:绿洲及其城市的意义
如果从地理形态来看,中亚地区的草原与绿洲呈现出一种相互嵌入的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的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类型也呈现出一种共生关系。历史上中亚的草原与绿洲地区之间的互动从未间断过,在中亚草原与绿洲地区的关系正常化时期,经常通过交换、贸易等方式获取双方各自需要的物品。即便是在特定历史时期草原与绿洲地区之间关系恶化,双方也会通过战争、掠夺等方式满足各自所需。尽管在中亚地区的草原文明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明类型,但是在历史上作为“基地”的中亚绿洲,为草原地区的社会发展与文明传播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孔隙水压力静力触探技术(CPTU)通过在常规静力触探(CPT)探头上安装孔压传感器元件,除可测锥尖阻力qc、侧壁摩擦力fs外,还可测试地下水位以下各土层的孔隙水压力u及超孔隙水压力消散过程。根据测得的超孔隙水压力消散曲线,可以推求土层的渗透系数Kh及固结系数Ch等重要的土的工程性质参数,对土层进行有效应力分析及计算,亦可对其渗透固结及沉降变形进行分析计算。
草原对于绿洲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绿洲地区的民众有时候非常看好草原地区的物品,在特定历史时段,马匹备受绿洲地区民众的喜欢。当提到马在中亚草原的经济意义时,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认为马既可以出口,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原王朝是潜在的买家,同时还可以用于战争。[11]历史上中亚地区兴起了大量的汗国,无论是草原国家还是绿洲国家,不同汗国之间在中亚政治舞台上出现过无数次的角逐与争夺。不管这些汗国争夺的是草原还是绿洲,战争是一种最基本的手段,历史上马在战争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丹尼斯·塞诺指出:内亚的马,特别是在适应气候的能力以及自身耐力方面胜于其他一切战马,从斯基泰时期到二战一直如此。[12]在这里的“内亚”就指的是中亚。在一个战争频发的年代,绿洲地区的汗国统治者自然会关注草原地区的马匹,进一步引发对草原地区的重视,以及在特定时段会对草原发动战争和进行征服。“从自然地理特征来看,中亚有大片的草原和牧场,这里的居民一直把饲养马匹作为主要的谋生手段。”[13]中亚地区出现了很多放养马群的基地,同时中亚地区也以出产“宝马”而闻名,中古时期出产于大宛的“汗血宝马”曾经引起中国西汉王朝统治者的青睐。就丝绸之路来说,当时在丝绸之路上流通的商品中,马是比较重要的。张国刚在谈到丝绸之路上的马匹时指出:“献马除了政治利益,更重要的是,这是丝绸之路上官方对官方的贸易形式。中原王朝回赠的物品,主要就是丝绸。”[14]盛产马匹的中亚草原地区,对于绿洲地区的城市以及商人群体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绿洲地区的汗国统治者随之对草原有一种强烈的占有欲。
水源是绿洲社会形成的基础,中亚地区有很多大的河流,比如阿姆河、锡尔河等,这些河流浇灌了沿岸的大片绿洲,中亚地区历史上有影响的绿洲有花剌子模绿洲,以及后来兴起的费尔干纳绿洲、塔什干绿洲等,其中有些地区的大绿洲是由不同形状与规模的绿洲形成的绿洲群。在土库曼斯坦境内,卡拉库姆沙漠边缘有几块大的绿洲,“沙漠的西缘有科佩特山溪水形成的阿克哈尔绿洲,以及戈尔甘河和阿特列克河流域;南缘有穆尔加布河下游形成的莫夫绿洲,再往南是穆尔加布河上游的彭狄绿洲;东缘有以查尔朱为中心的阿姆河中游流域,以及阿姆河下游的花剌子模绿洲。土库曼人的迁入和定居对这些绿洲的开发起到了促进作用。”[15]在中亚地区阿姆河下游的花剌子模绿洲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影响,锡尔河流域的塔什干绿洲也是规模相当大的绿洲。
游牧社会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善于接纳外来文化,农耕地区的人群在历史上随时会向游牧社会流动。与农耕社会相比较,游牧社会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和接纳能力,相应地造就了游牧人开放、包容的意识。历史上在中国游牧社会的内部,曾经接纳了很多的外来人群,特别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族群。中亚游牧社会也不例外,19世纪后期进入中亚楚河流域的东干人,由于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掌握了比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这就提升了他们在中亚大草原的社会地位,中亚大草原也很快接纳了这些外来移民。从1877年开始进入中亚地区的东干人为楚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在楚河流域开垦农田,利用水利灌溉技术。中亚的东干人居住区域,后来都发展成为有影响的农业区,并各自形成了一些特色,就像七河省大规模的水稻种植,伊塞克湖附近的经济作物种植,如药用植物、亚麻、豆类等,奥什地区的棉花种植,江尔肯特(今潘菲洛夫)和阿拉木图一带的蔬菜和水果栽培。[7]东干人在自己居住地区的农业生产,使得楚河流域的农耕面积和规模都有所增大,农产品的数量也得以增长,同时还出现了农产品的加工,大量农产品流入中亚草原内部,备受草原地区的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的关注。“到‘二战’前,许多东干村因为农业的高产而闻名,特别是伊尔德克、米粮川(Милянфан)东干村的劳动者很有名。20世纪30年代,由于出色的劳动表现,米粮川的王麻子(Вонмаза Ч)、冯老二(Фунлоэр С)及吴董拉尔(Вудунлар Η)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第一批获得列宁勋章荣誉的人。”[8]东干人进入中亚楚河流域之后,就是因从事农业生产的能力与农产品的加工技术,在当地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其他族群的民众当中获得了一定的认同度。由此可以看到,在中亚游牧社会内部,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的。
由于中亚绿洲地区有相对丰富的农产品,以及通过商业贸易获得的大量商品,绿洲地区的富庶与市场繁荣为世界各地的商人所知,于是,中亚地区的绿洲及城市成为欧亚地区很多民众向往的地方。历史上中亚地区的一些绿洲或者草原帝国的统治者意识到占据大绿洲的重要意义,他们在觊觎和盘算着坐落在绿洲上的大城市。长期以来关于绿洲城市的争夺成了不同汗国统治者关注的焦点,“布哈拉汗国和哈萨克汗国之间进行过几次大的战争,争夺的焦点是锡尔河北岸城市,特别是塔什干。”[22]因为塔什干是中亚地区后来兴起的城市,也是当时有影响力的绿洲,自然就成了中亚草原与绿洲地区的帝国之间争夺的焦点。其实,历史上在中亚地区的绿洲帝国之间也在进行城市的争夺,特别是像布哈拉、撒马尔罕等这样的大城市。可见,在绿洲上兴起的城市对于中亚的帝国来说,有非常大的吸引力。长期以来,在中亚绿洲上兴起的一些大城市几乎都是当时中亚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占据了中亚的城市就意味着对中亚财富的占有。因此,在中亚地区兴起的一些汗国历来都非常重视绿洲以及绿洲上的城市,比如18世纪布哈拉与西瓦两个汗国对于莫夫绿洲的争夺,[23]直到19世纪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进入中亚之后,特别关注中亚的大绿洲以及建立在绿洲上的城市。俄罗斯在征服中亚的过程中,于1865年占领了塔什干,1868年占领了撒马尔罕,1873年占领西瓦。[24]接下来便是俄罗斯对于中亚大绿洲的经营与开发。
农业社会孕育了发达的手工业,中亚地区绿洲农业社会亦为如此。早在中亚的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城市就有相当发达的手工业,进而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中亚的主要城市之一撒马尔罕是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拥有供商人参观、居住所需的一切必备设施。”[28]如果把中亚绿洲社会的历史放在全球史的视域下,就会发现中亚的手工业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17世纪下半叶和18世纪初,中亚手工业最发达的国家是布哈拉汗国,它的纺织业和造纸业继续成为中亚的强势产业。”[29]手工业产品对于中亚地区来说是非常重要,在这些中亚大城市的手工业产品不仅仅满足绿洲和草原地区的需要,同时也满足世界其他地区的需求。特别是在草原游牧地区,手工业产品的制造非常匮乏,中亚草原地区是中亚绿洲手工业产品输出的一个重要的流向。“在哈萨克草原,无论是定居地还是草原,手工业产品都依赖于锡尔河沿岸和七河流域的居民,哈萨克人与他们进行着频繁地贸易。”[30]这样,中亚地区城市手工业也是连接草原游牧与绿洲农业文明的一条纽带。
纵观中亚社会发展史,历史上中亚地区兴起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大汗国,很多曾经以大绿洲为根据地,把势力范围向周边的草原和绿洲地区延伸,从早期的帖木儿帝国,一直等到后面的希瓦汗国等都以中亚的绿洲地区为中心。“到1380年,帖木儿亲自控制了察合台的领地,并且在撒马尔罕拥有了一个设施齐备的都城。他继续以不同寻常的暴力征服了整个波斯和阿富汗、高加索地区、金帐汗国的领土以及印度北部地区。”[25]中亚绿洲城市的兴起与中亚绿洲统治者的经营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中亚汗国的统治者把都城建立在特定的一座城市的时候,比如“1500年,成吉思汗后裔昔班尼以撒马尔罕为都建立了布哈拉汗国。1505年昔班尼汗率领乌兹别克人攻占了花剌子模绿洲的重要城市乌尔根奇,在此派驻官员。”[26]“阿拉布沙希王朝最初以维泽尔和乌尔根奇为都,17世纪20年代,都城从乌尔根奇迁往花剌子模绿洲的希瓦城”。[27]希瓦后来发展为中亚绿洲上的一座重要的城市,就是因为希瓦汗国当时对这块绿洲的开发和利用。
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指出:“在沙漠中生活的人们,他们的智慧还在发展,创造出一种不同于游牧的生活样式。这种生活样式,在历史揭开帷幕之前,早就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它便是oasis(绿洲)的建设。倒不如说,我甚至认为,以绿洲为基础,世界史才写下了它的第一章。”[31]在这里松田寿男看到了绿洲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意义。其实,在中亚社会发展史上,绿洲是文明传播与再生的温床,这一点草原地区有所不及。作为文明十字路口的中亚接纳了多种文明,其中绿洲是非常重要的文明接点,不同文明往往首先进入中亚地区的绿洲,然后再向周边草原地区进行流播。
精准定位客户需求解决了公司发展的第一步,那么如何精准培训,对泓福泰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以培训月嫂为例,泓福泰把员工送入医院,进行为期1周的医院实习,让其接受系统、全面的母婴护理或育婴师培训,之后可持证上岗。学习结束后,公司为学员采集资料,包括:个人基础信息、工作简历及合格的体检表,并为其定级。所有培训工作结束后,就可根据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不同种类的“月嫂服务”。
三、转换生成:中亚文明格局的动态过程
其实,如果用长时段的眼光审视历史,就会发现历史上中亚游牧兴盛的地区,也未必是单一的游牧形态。“考古资料清楚地显示,在楚河流域,农业显然比游牧活动出现得早。绿洲农业和草原游牧交替出现,耕作在间隙中得以恢复,农耕和游牧得以相互共存共兴。”[9]中亚草原的部分地区海拔较低,地势平坦,并且有大的河流通过,一旦作为游牧政权的中心,这些地区就会出现相对发达的农业生产。历史上在中亚地区游牧帝国的内部,出现过发达的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由于内部的农业、商业可以更好地满足游牧社会的需要,减少到其他地区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成本。粮食是游牧社会的必需品,游牧社会历来在想方设法解决内部的粮食生产问题。历史上中亚地区兴起的游牧帝国,经常发生战争,这就意味着需要大量的武器,曾经一段时间,中亚游牧社会广泛使用铁制武器,铁器的制造也就成了游牧社会的重要手工业。就像简·伯班克(Jane Burbank)和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所说:“游牧帝国还为自己获得了某些定居民族的技艺(冶铁技术是一门专长),并且工匠和手艺人颇受尊敬。”[10]在游牧社会内部出现的草原绿洲,由于规模的相对有限性,尽管满足了游牧社会的部分需求,但还有更多的农业产品需要从草原外部输入。由此,在中亚草原游牧社会出现的农业生产,是一种内生性需要的产物。
所有纳入对象男女性别比例为726∶77,女性错失早期诊断时间为3(1.5,10)年,男性为3(0.5,8)年,两组无统计学差异(Z=-1.13,P=0.258)。其中女性的肺功能FEV1%为51.0%±17.7%,男性为53.8%±21.7%,组间没有统计学差异(t=1.21,P=0.231)。
当中亚周边地区的一些农业文明所属的族群受到其他族群的挤压时,他们就会进入中亚草原地区,在中亚草原适宜耕作的地方开辟农业用地,把草原改造成农田,然后在此基础上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中古时期粟特人在中亚的活动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公元6~8世纪,粟特人开始向七河流域等哈萨克斯坦南部和东部地区迁徙。粟特人的活动主要与国际商贸发展以及阿拉伯人的入侵有关。”[33]粟特人进入哈萨克草原之后,打破了中亚草原的宁静,在游牧社会中从事农业生产、商业贸易活动。如果以“层累结构”的视角观察中亚,就会发现中亚文明是多层文明沉淀和聚集的结果,而且不同的文明层级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希腊文明在“中亚文明层”中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希腊文明是一种城邦文明,进入中亚之后,肯定首先在绿洲上发展,或者说以绿洲地区的城镇为基地向周边地区传播。在希腊人群流动的基础上,希腊文明进入中亚地区,创造了中亚文明史上所谓的大夏(bactria)文明,就像孙隆基指出,亚历山大在东征过程中把不少的移民带到中亚定居,位于今天阿富汗东部和乌兹别克南部大夏(bactria)成了希腊人的中心。[34]无论是伊朗高原东部的粟特人还是欧洲的希腊人,从早期的活动地域来说,他们后来都是以外来者的身份进入中亚地区的,而且在语言上都属于印欧语系。这些外来族群进入中亚之后,不但改变了中亚的民族分布格局与文化地理结构,而且影响了中亚的生计方式,同时还改变了中亚地区草原文明与绿洲文明的格局。
草原向绿洲之间的转换是中亚社会一个重要特色,这种转换引发了中亚地区的族群生计方式与文明类型的转型与变迁,中亚地区不同族群生计方式转型的原因是多样的,既有趋利、自愿性的选择,也有被动、无奈的应对。18世纪以前,中亚地区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农业化,在这场农业化的过程中,中亚地区的草原与绿洲之间的转换加快了步伐,农耕文明在中亚地区的占比进一步得到提升。当然,中亚地区农耕与游牧之间转换的原因亦为复杂多样,其中游牧向农耕转换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定居族群人口的增加。17世纪由于准噶尔与哈萨克人的战争,锡尔河下游的卡拉卡尔帕克人南迁到中游地区和泽拉夫善河谷,在封建化的过程中丧失了大量牲畜,加速向定居农业过渡的进程。[35]准噶尔汗国兴起之后,把自己的势力范围伸入中亚草原,与欧亚草原上的另外一个汗国——哈萨克汗国之间进行哈萨克大草原的争夺,在这两个草原帝国的战争中,中亚草原地区的一些族群成为受害者,其中有些被迫放弃原有的生计方式,从游牧社会转向农耕定居。
费尔干纳盆地是中亚地区一个适宜进行农业生产的地带,随着灌溉技术的提高,费尔干纳盆地的耕地面积也在逐年增加,这就意味着费尔干纳盆地一部分从事游牧生产的族群改变生产方式,从游牧转变成定居农耕。从18世纪开始,由于灌溉技术的提高,“耕地面积的增加,游牧转向定居农业的过程加速,牧民的比重逐渐降低,半游牧半定居人口在费尔干纳占据了重要位置。”[36]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中亚地区的族群形成了一种误解,以农耕和游牧的二元标准进行划分,其实不然,即便在同一族群的内部,有从事农业生产的,也有进行游牧生活的。就当前来说,人们普遍认为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地区的一个游牧国家,然而在吉尔吉斯斯坦内部分布着大片绿洲,特别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费尔干纳盆地,有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农业区。笔者在2018年的考察过程中发现,在楚河流域和伊塞克湖附近是大片的绿洲地带,也是吉尔吉斯斯坦北部的重要农业区域。就塔吉克人而言,不同地区的人群的生产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塔吉克人分为平原塔吉克人和高山塔吉克人。居住在撒马尔罕、布哈拉、赫拉特、喀布尔、霍占、呼罗珊等地区的为平原塔吉克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居住在帕米尔高原和兴都库什山一带的为高山塔吉克人,从事农业和畜牧业。”[37]历史上在阿姆河流域就已经出现了大片的绿洲,18世纪以来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在阿姆河流域出现了农业扩大化与农牧业之间的转换。“西瓦汗国的土库曼人,特别是阿姆河中游的牧民,在18世纪上半叶就开始从游牧转向定居”。[38]在中亚草原与绿洲的接壤地带,出现了一些农牧过渡带,特别是在绿洲地带的边缘区域,为农牧兼营的族群提供了条件,出现了半农半牧的人群。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亚社会的发展史就是草原文明与绿洲文明互动的历史,进一步来说,就是游牧与农耕社会互动的历史。在草原文明与绿洲文明的互动过程中,实现了中亚资源的最大化整合,把来自于草原地区的重要商品集中到绿洲城市的市场上,然后,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商人从中亚地区的市场,沿着丝绸之路把这些商品带到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同样,欧亚地区的商人把其它地区的商品带到中亚的绿洲市场,然后进入中亚草原。历史上的中亚曾经是一个欧亚商品的中转站,草原与绿洲地区的商品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商人,这些商人不仅把自己所属的文明带到中亚,同时还把世界其他地区的商品和文明引入中亚地区,这就是中亚“文明的十字路口”之称谓的由来,也是中亚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意义。归根结底,历史上中亚地区商品的多样性以及市场的规模,就是草原文明与绿洲文明深度互动的结果。在中亚地区首先是草原文明与绿洲文明之间内部的互动,在互动过程中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东干人等农业移民进入中亚之后很快能被当地人接受的原因。其次是中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外部互动。如果说中亚地区草原文明与绿洲文明的内部互动生成了一些文明形态,那么在中亚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过程中,再把这些中亚文明传播到整个欧亚地区,甚至世界其他区域。
参考文献:
[1]李琪.历史记忆与现实侧观:中亚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3.
[2]袁剑.区域、文明,还是历史连续体?——中国的中亚叙述及其话语分类[J].西北民族研究,2019,(1).
[3]黄达远.从鞑靼利亚到亚洲俄罗斯与中亚:17~20世纪初的东方主义、地理考察与空间建构[J].青海民族研究,2019,(2).
[4]杨建华,邵会秋,潘玲.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267.
[5][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06~109.
[6][俄]巴透尔德.七河史[M].赵俪生,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7.
[7]王国杰.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50~54.
[8][吉尔吉斯斯坦]A.A.张.序言·东干人的习俗、礼仪与信仰[M].丁宏,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4.
[9]努尔兰·肯加哈买提.碎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5.
[10][25][美]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珀.世界帝国史:权利与差异政治[M].柴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87.102.
[11][12][美]丹尼斯·塞诺.内亚史上的马与草场[A]//文欣,译.[美]丹尼斯·塞诺.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C].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111.104.
[13][20][21][28][印度]G.D.古拉提(G.D.Gulati).蒙古帝国中亚征服史[M].刘瑾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11.135~148.70~71.135.
[14]张国刚.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75.
[15][22][23][26][27][29][30][32][35][36][38]蓝琪.中亚史(第五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34.68.310.42.43.186.65.291.140.186.287.
[16][英]G.勒·斯特兰奇(G.Le Strange).大食东部历史地理研究——从阿拉伯帝国兴起到帖木儿朝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中亚诸地[M].韩中义,译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622.
[17][18][19]佚名.世界境域志[M].王治来,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06~111.106.108.
[24][英]吴芳思.丝绸之路 2000年(修订版)[M].赵学功,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146.
[31][日]松田寿男.丝绸之路纪行[M].金晓宇,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7~8.
[33][哈]坎·格奥尔吉·瓦西利耶维奇.哈萨克斯坦简史[M].中国社会科学院丝绸之路研究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39.
[34]孙隆基.新世界史(第 2卷)[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6.
[37]赵会荣.塔吉克民族传统文化[A]//吴宏伟主编.新丝路与中亚——中亚民族传统社会结构与传统文化[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367.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asis Civilization and Steppe Civilization:The Motive Force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sian--Thinking Based on the Success of Chinese“Dunggan's”Cultural Adaption
LI Jian-zong
Abstract: On the base of Oasis and Steppe,oasis civilization and steppe civilization is appeared and interlocked with each other in Central Asian.On account of inside need,the nomadic society nee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Central Asian.As a typical case,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at Dunggans do in Chu River watershed is popular in 19th century.Oasis is a base of cultivating oasis civilization and steppe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Asian,and symbiotic relationship is taken shape between oasis civilization and steppe civilization.Oasis civilization and steppe civilization is dynamic and taking mutual transformation all the time in Central Asian.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asis civilization and steppe civilization is the motive force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sian.
Keywords: Oasis Culture;Grassland Culture;Interaction;Central Asia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2019)03-0026-0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亚回族侨胞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批准号:18XZZ007)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9-03-20
作者简介: 李建宗(1972-),男,甘肃通渭人,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社会、西北民族走廊和民俗学研究。
[责任编辑 骆桂花]
[责任校对 王淑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