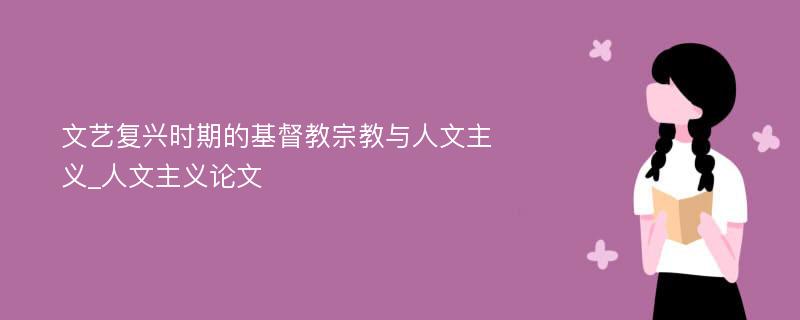
文艺复兴中的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论文,人文主义论文,文艺复兴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7)01-0106-06
在中国的西方历史研究和教学中,从罗马帝国灭亡到英国革命以前的时代被称为“中古时代”或“中世纪”,而中古时代以前的时代则被称为“上古时代”或“古代”。在中国的很多学者和一般读者中,对与之有关的重大问题,普遍存在三个相互关联的误解:一是认为,代表人文精神的西方古代文明即希腊罗马文明,遭到了代表宗教精神的基督教的毁灭或压制;二是认为,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因此也就是文明湮灭或曰“野蛮”、“落后”的“黑暗时代”;三是认为,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文主义运动,因此也就是要返回古代文明并反对基督教的一种思想运动。
这些看法并非毫无事实基础,但是却以一些较为枝节的事实遮蔽了最为根本的事实,因此歪曲了事情的全貌,误解了问题的性质。因为,第一,古代的希腊罗马文明包含着某些人文精神,但也包含着明显的宗教精神,而这两种精神是相互关联的。这不但表现于尽管具有人文特色、但仍然是宗教的希腊罗马宗教之中,而且表现于一般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有的关于人事受制于神意的宗教观念之中;不但表现在那些有代表性的诗歌、戏剧和艺术作品之中,而且表现在那些有代表性的哲学思想之中。①
更重要的是,就西方古代而言,摧毁罗马帝国所代表的古典文明的,乃是日耳曼“蛮族”所代表的“野蛮”;而基督教本身既非文明,亦非野蛮,既非被毁灭者,亦非毁灭者。因为,文明是相对于农耕和定居之前的生活方式而言,是包括农业技术、城邦管理、文字使用等等成分在内的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② 导致罗马帝国及其文明灭亡的,除了蛮族入侵这一外部原因,当然还有内部原因,那就是包括道德滑坡、穷兵黩武以及阶级和民族压迫在内的(汤因比所说的)“腐化”,也可以说是这个文明内部的反人文主义③。至于作为一部分人的精神性信仰而且对罗马人来说是外来信仰的基督教,尽管影响日益上升,却并不是这一文明的精神源泉或精神支柱。作为一种全新的精神力量,基督教在这个正在没落的文明的躯体内挣扎生长,没有随着这个文明的灭亡而灭亡,反而同化了摧毁这个文明的各个野蛮民族,使它们能够在古代文明的废墟上建设起一种新的文明,即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文明,实际上也是一种比古代文明更富于人文精神的文明。④
第二,因此,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同很多人的误解正好相反,乃是一个在老朽的文明被年轻的野蛮摧毁后的废墟上,使野蛮变成文明并建设新文明的生气勃勃的时代。当然,使那些为了抢掠而冲出森林、嗜杀狂饮且目不识丁的蛮族武士,变成尊卑有序并安居宫廷、彬彬有礼且爱好文艺的贵族,这个过程用了大约五百年(从西罗马帝国衰落到加洛林文艺复兴);使这个新的文明获得和谐的秩序、创造的机制和思想的活力,从而造成它后来在各个文明之中居于先进甚至主导地位的条件,这个过程又用了大约五百年(从加洛林文艺复兴到哥伦布地理发现)。如果说,使用本应限于前五百年的“黑暗时代”一词去描述中世纪前半段的文明废墟上的暗淡景象,甚至去指责当时一般教士(以及绝大多数人)对古代文化的无知和狭隘保守心态(这正是现在一些书常常说起的“刮掉羊皮纸上的古代文献以抄写圣经”之类现象发生的不难理解的原因),还有某些事实基础的话,⑤ 那么,把这个词的运用扩大到整个中世纪,甚至用来概括这一千多年的西方文明,或者还引用这类零星的事实而忽略整体的事实,以维持上述歪曲和误解,那就不仅表现出对中古文化的无知、视野的狭隘和心态的保守,而且会陷入一种明显的自相矛盾——一种后来居上并遍布世界的文明,如何能够从文明湮灭或野蛮落后的状态中变戏法似地冒出来?“文明”这一概念,本来不就是“野蛮”、“黑暗”等概念的对立面吗?
第三,人文主义运动反对基督教之说,暗含着这样一种逻辑:中世纪西方文明既然以基督教为精神,则其主导倾向就是神本主义的,就是反人本主义的,就是反人文精神的(也可以在非历史阶段论的意义或道德意义上说它是“野蛮”或“落后”的),因此,文艺复兴要倡导人文精神,要返回古代文明,就必然与基督教对抗,就要反对基督教。
姑且不论人本主义不等于人文精神,⑥ 因此反人本主义绝不等于反人文精神;也不论宗教精神不但不同人文精神相冲突,而且可以与之并存并成为其最终的支持;⑦ 更不论道德意义上的“野蛮”和“落后”在此所指者,多半是从后来的文明习俗看来不可接受的以前的习俗或“反人道”的行为或做法,它们存在于历史上每一种文明之中,往往还得到当时人文活动的支持和辩护,只是在人道主义或人文精神得到某种程度的张扬之后,才被人们普遍谴责为野蛮或落后的。事实上,文明总是同人文分不开的(《易经》说:“文明以止,人文也”),或者说,任何文明总是具有范围不同的人文事业、人文活动和人文制度,也具有程度不同的人文精神。就前一方面而言,中世纪的西方文明不但不例外,而且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基督教,才具有了范围很广的人文事业、活动和制度(从修道院之保留和研究古代文献,到教会学校之教授“七艺”,从众多的修士之从事科学和哲学活动,到不少教会之热衷于高等教育和艺术事业)。就后一方面而言,基督教的信仰从最深的层次上支持了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张扬,所以,作为基督教文明之子或基督教社会产物的文艺复兴,既然要倡导人文精神,就不可能与基督教产生真正的对抗。文艺复兴的许多活动是同古代文明的材料有关⑧,但它的精神并非复古或要返回古代(如孔子和老子)⑨,而是前瞻的甚至常常是乌托邦式的(如康帕内拉和莫尔),它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用古代文明来反对基督教(如几百年后的尼采),而恰恰是用基督教的精神,来反对人文主义者所知的文明中一切有违人文精神,也是有违他们所理解的基督教精神的东西(如从但丁到伊拉斯谟的无数天才)。
当然,每一个人的视野都是有限的。人文主义者们虽然眼光犀利,其批判的矛头所向,还是主要局限于他们周围,也就是所谓“基督教社会”或“中世纪文明”中的这类东西,其中首先是教会的腐败、僵化和种种弊端。因为他们作为人文主义者看到了教会弊端与人文精神的冲突,作为基督徒更看到了那些弊端与基督教精神的冲突,而他们用以反对那些弊端的人文精神,则是以基督精神作为基础的。只有基督宗教精神与人文主义精神的根本一致性,才能解释文艺复兴运动中的这一基本现象。
关于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我们在前页注3中的总结,应该同一般人的理解相去不远。至于基督宗教的基本精神,我们当然首先应该从《圣经》去看。“(圣经的)的核心信息是,天地之主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活动,要使人性摆脱一切危害人生的东西,最终完全实现他要给自己的子女即人类的一切力量与欢乐。”⑩ 这不但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而且同至今普遍理解的人文精神都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所谓广义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基督宗教中更多了一种超越的基础,一种神圣的根据。例如,《创世记》的故事赋予人以超出其他一切造物的地位,特别是赋予人以某种创造性和能动性,《出埃及记》表明上帝会拯救忠诚和公正的人群,而《诗篇》作者们则为上帝创造的美善和做人的奇妙而赞美而感谢。“圣经的特征在于宣称,上帝在人类的人格和环境之中并通过人类的人格和环境,表达了他对人性的仁爱的目的。关于人世充满罪恶的状况,圣经绝对是现实主义的,而对于上帝宽恕和治愈之爱的力量,圣经同时又是满怀信心的。”(11) 因为按圣经的描述,人既是出自尘土,又赋有上帝的形像。
其实,这正是由莎士比亚的下述著名片断所代表的人文主义对人的看法:
“人,是何等样的一件杰作!
在理性方面,是多么高贵!
在能力方面,是多么无限!
在形态和行动方面,是何等动人而值得欣羡!
而在行为方面,又多么像一个天使!
在智慧方面,多么像一个天神!
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
可是对我来说,这尘土的精粹又是什么?(12)
“新约圣经”以耶稣的复活,昭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通过上帝的圣灵在所有相信这福音的人的生命中的工作,这个新时代的种种美善——生命、完善(13)、自由与和平——就能够在此世实现。”(14) 这恰恰是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人生和完人的追求,到宗教改革对人的思想解放,再到启蒙运动对人类“永久和平”(15) 的憧憬等等人文主义理想,在西方思想中最深厚的根基。
在新约圣经结尾处,圣城即新耶路撒冷并非远在天庭,而是“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上帝自己也要来到人间,“与人同住”。(16) 所以,从“旧约”开篇的《创世记》,到“新约”末篇的《启示录》,整部圣经自始至终都一直关注着的,绝不仅仅是上帝,而是上帝与人的关系。(17) 从人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整部圣经都指向人要走向的最高境界或所追求的最高理想。这正是基督宗教精神同人文主义精神在根本上一致的原因。因此也就难怪,从总体上说,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几乎所有重要的人文主义者,都会把他们对人的观点的基础归结到圣经或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或者把他们关于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境界同基督教的理念相联系。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在二十世纪受到不少批评、被认为过于强调了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者的世俗一面的布克哈特,在他那部权威著作的结论中也承认:“这一群优秀的人物所主张的学说是:这个有形的世界是上帝以爱来创造的,是在上帝心中先有的一个模型的仿制,上帝将永远是它的推动者和恢复者。人能够由于承认上帝而把他纳入自己灵魂的狭窄范围之内,也能够由于热爱上帝而使自己的灵魂扩展到他的无限之中——这就是尘世上的幸福。”(18)
他最后又总结说:“中世纪神秘主义的回响,在这里和柏拉图学说合流了,和一种典型的现代精神合流了。一个关于世界和关于人的知识的最宝贵的果实在这里已经成熟,只是由于这一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就必须被称为近代史的前驱。”(19)
从后来几百年的历史来看,这种关于世界和人的知识成果,这种新的精神潮流,从中世纪所吸纳的绝不仅仅是神秘主义和柏拉图学说,而且还有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回响”,因为事实上,亚里士多德主义在文艺复兴最兴盛的十五世纪和宗教改革兴起的十六世纪,仍然在不少大学和学术界存在,其精神和方法也刺激或影响了十七世纪的自然科学和启蒙时期的经验主义哲学(20)。更重要的、而且在我们的知识界中被忽略了的一点是,这种知识成果的基础,是基督宗教关于上帝与人关系的学说,这种新的精神潮流的兴起,是基于对这种关系的一些新的理解,但仍然是基督教影响下的理解。
对神人关系的这种新理解,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人的自由意志的突出强调。这种强调导致了人的自由之高度张扬,从而赋予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以不同于古典时期(希腊罗马)人文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使之同后者强调宿命的特征明显地区分开来,成为一种崭新的、也可说是真正的人文主义。
但是,我们不可忽略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意志自由作为基督宗教的人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在中世纪从来没有消失,而且得到了无数的神学家的反复论证。一方面,圣经关于人的创造与堕落之说,与人不同于其他造物的特征即自由密切相关,也一直是千百年来不断得到基督教神学探讨和深化的重大神学主题。另一方面,尽管奥古斯丁在此问题上与佩拉玖的论战极其著名,但是在整个中世纪教会中最为流行的,并不是彻底的反佩拉玖主义或反自由意志学说,而是所谓的“半佩拉玖主义”,即有所限制的意志自由学说。(21) 正因为如此,中世纪教会中通过苦修或善功求得就赎的实践和制度才普遍流行——假如没有意志自由,善功就会成为毫无意义的“傀儡行为”,不会具有拯救灵魂的功效。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有不少猛烈批判了教会的腐败和弊端,但却为意志自由作了认真的论证,罗伦佐·瓦拉也许是其中最著名的之一。他对所谓“伪君士坦丁赠礼”的揭露在中国学术界知者甚众,但是,他为人的意志自由与上帝预知并不矛盾所作的论证,却极少有人提到。(22) 他那抽丝剥茧的长篇大论,是要说明这样一个道理:“虽然上帝会预见由人所做的某些未来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之实行并非出于必然性,因为人会自愿地去做。而且,凡是自愿的,就不可能是必然的。”(23)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还有一个重大特征,即人类尊严的高扬,这一特征也与古典时期希腊罗马观念中作为命运玩偶的人的地位,迥然有别。而这一点,在当时人文主义者的论证中,同样是以上帝的旨意作保障,因而是以基督教精神为本源的。在这方面,最好的例证是一位极其著名的人文主义哲学家皮科的论述。事实上,皮科在他最著名的作品《论人的尊严》中,也是把这种尊严的地位奠基于上帝赋予人的意志自由之上的。他写道“(在创世时)上帝把人作为本性不定的生物,赐他一个位居世界中央的位置,对他说:‘亚当啊,我们既没有给你固定的居所,也没有给你独有的形式或特有的功能,为的是让你可以按自己的愿望、按自己的判断去取得你所渴望的住所、形式和功能。其他一切生灵的本性,都被限制和约束在我们规定的法则之范围内,但是我们把你交到自由意志的手中,使你不为任何限制所约束,可以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你的本性之界限。我们把你安置在世界的中心,使你从那里可以更容易观察世间的一切。我们使你既不属天,又不属地,既非可朽,亦非不朽,于是凭着选择自由,凭着你的尊荣,你就好像是你自己的塑造者,可以把你自己塑造成你喜欢的任何模样。你能够沦落到低级的生命形式,即沦为畜生;也能够出于灵魂的判断而重生为高级的生命形式,即升为神圣。’”(24) 十分显然,正是这种选择自由,才使人拥有尊严,因为一个人如果生来就被塑造成圣人或善人,既不出于自己的选择,就无任何可钦可敬的内心奋斗,因此也就毫无尊荣可言,而不过是一个高级的木偶。(25) 正如伊拉斯谟所说:“假如上帝造人同陶工造瓦罐一样,或者同他造石头一样,那么人作为整体有什么价值呢?”(26)
我们当然不能忽略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对教会种种弊端的嘲讽和抨击,这些抨击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人文主义与基督宗教具有张力的辩证关系的某种表现。在此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问题,不单是片面强调了二者关系中紧张或冲突的一面,而更是表现了某种误解或无知。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对堪称最重要的人文主义者、“十六世纪的伏尔泰”伊拉斯谟的《愚颂》的误解,认为它是无情嘲笑和讽刺基督教的作品。伊拉斯谟无疑是教会弊端无情的批判者和尖刻的讽刺者,但是,他又是公认的“基督教人文主义”的领袖人物,是“基督教的善良的卫士”。(27) 他抨击教会,但只是用基督教的精神去反对教会对这种精神的背离,所以他也反对由改良走向了革命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因此,尽管他的思想之表述形式有时“令人迷惑不解”(狄尔泰语),(28) 但如果记住他的总体思想倾向,是不该把《愚颂》中的“愚”,包括教会和基督徒之“愚”,误解为纯粹负面的攻击嘲弄之对象的。更何况,从逻辑上说,作为攻击和嘲弄对象的纯粹负面意义的“愚蠢”,同时又作为“颂”或“赞”的对象,是说不通的;如果把“颂”或“赞”理解为纯属“反讽”,则又无法理解全书中许多并非反讽而是赞美的例证。其实,这种误解还有一个根源,即对圣经《哥林多前书》有关段落的无知。该书第一章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29) 这一章以及第二章的一个重要意思,是表明对宗教的“愚”之肯定和对世俗的“智”之否定。(30) 因此,对“愚”的正面认识甚至赞颂,在基督教思想中本有根基,伊拉斯谟以之表达的东西,绝不是像中国多数读者(甚至按此误解去翻译的译者)所误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对基督教的嘲讽!
正如布克哈特所说:“早期对于上帝的信仰是从基督教和基督教的外部象征,即教会,得到它的来源和主要支持的。当教会已经变得腐败时,人们应该划清界限,并无论如何保持住他们的宗教。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是十分冷静,或者十分迟钝来容忍原则和它的外部表现之间存在着一种持久的矛盾的。”(31) 他还谈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中上层人士对教会的混合感情,即既有强烈的反感,又有信赖圣礼和圣典的意识。(32) 布克哈特又指出,“这些现代人,意大利文化的代表,生来就具有和其他中世纪欧洲人一样的宗教本能。但是他们强有力的个性使他们在宗教上完全流于主观……而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发现在他们身上起作用的那种巨大魔力,使他们明显趋向于世俗化。”(33) 这就造成了文艺复兴时期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这个新文化的某些最热心的倡导者是最虔诚地崇敬上帝的人乃至是禁欲主义者。安布罗吉奥·加马多莱斯修士,……他的同时代人,尼科洛·尼利利、吉安诺佐·曼内蒂、德那多·阿奇亚佐利和教皇尼古拉五世把高深的圣经学识和极端的宗教虔诚与多才多艺的人文主义结合在一起了。”(34) 事实上,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有比这里所列举的多得多的人物,比这里所列举的多得多的教皇,把其基督宗教的“宗教虔诚与多才多艺的人文主义”相结合,正因为如此,又因为他们“在宗教上完全流于主观”和“明显趋向于世俗化”,就在一方面造成了教廷支持赞助下的文化艺术大发展,特别是建筑、绘画、雕塑以及某些方面的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的繁荣兴旺,另一方面更鲜明地显现了教廷和教会的腐败,更突出地表现出基督教的“原则和它的外部表现之间存在的”矛盾了。终于,有一个民族,即日尔曼民族,已不能容忍这种矛盾。于是在它的一个儿子、一个年轻的修士,到罗马目睹了这种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的辉煌结合及教会明显的腐败,回家后再思考了这种“原则与外部表现之间存在的”惊人的矛盾,并抛出了其思想的一粒火星之后,这个民族就像一堆干柴一样,熊熊燃烧起来了。
在总结文艺复兴时期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的关系时,回顾一下保罗·蒂里希的说法是很有启发的:“文艺复兴对尘世的肯定,将尘世提高到天国的地位,肯定尘世并不比天国离神的本质更远,断言神的本质无所不在——这就是基督教创世论的深刻真理。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与流行于整个古代的人生观相对立。而且,基督教的一神论还意味着,统治世界的并不是各种各样的神灵力量,所以不能把世界看成是分裂的和邪恶的。神就是一个精神和道德的统一体。世界是注定由神进行统治的场所。文艺复兴相信尘世是进行有意义的创造性活动的场所,反复出现在文艺复兴时代种种乌托邦计划中的对正义和人道的统治的承诺,这些都并非来源于古代,而是来源于基督教。”(35)
注释:
①除了关于人力无法抗拒神力的俄迪浦斯故事之外,苏格拉底关于“人的智慧毫无价值”,“真正的智慧只属于神”(《苏格拉底的最后日记——柏拉图对话集》,上海三联,1988年,第48页)等说法,也可算一大代表。
②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册,第4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③“人文主义”应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用法:狭义指文艺复兴时期兴起于西欧的那场思想运动;广义指从古到今东方西方都出现过的强调人的地位和价值、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重视人的权利和自由、追求人的旨趣和理想的一般主张。晚期罗马帝国的趋势同广义的人文主义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④即使是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既然主张“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更“先进”,承认农奴的处境比奴隶要好,也就应该同意这一结论。其实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学者们的说法所反映的,更多地是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和要求。例如,可参见齐思和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译本(商务,1979年)写的序言,与张椿年《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12页)对美国学者哈斯金斯(C.H.Haskins)的评说,从中可看到中国学者在不同时期对中世纪与古代文明关系以及对中古文明本身的不同说法。
⑤其实这种无知和狭隘保守也已经被大大地夸大了,因为正是中世纪教士中的精英(他们构成了当时知识界的主体)学习和传递了拉丁作家们的文学、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和古希腊的哲学,我们才能看到中世纪的七艺教育、吸收了希腊哲学的诸多神学体系以及中世纪后期自然科学的发展。
⑥“人本主义”不是一个日常生活用语,而是一个哲学术语。“本”意为“本源”,故“人本主义”应指与“神本主义”相对的主张,后者主张神是世界的本源,而前者主张人是世界的本源(或中心)。至于“人文精神”,在此大致相当于广义的人文主义的精神,如前页注3所言,含义十分宽泛,重在社会生活。
⑦关于二者的关系,笔者另文论述。这里只需指出,当一种宗教强调人的地位,又以神圣者为其根源、为之辩护之时,这种宗教的精神就不与人文精神相违,而且还给予了强大的支持。
⑧20世纪西方历史学界在否定布克哈特(J.Burckhardt)把文艺复兴等同于人文主义的结论之余,更指出了文艺复兴同对古代文献的研究,实际上只有部分的关系。参见布洛克(A.Bullock):《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6-9页。
⑨伏尔泰在《论各民族的风尚与精神》中早已指出,文艺复兴的意义不在复古,而在创造。(参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1979年,第2页。)
⑩J.M.Shaw,R.W.Franklin,H.Kaasa and C.W.Buzicky eds.,Readings in Christian Humanism( Augsburg Publishing House,1982) ,p.65.
(11)同上书,第66页。
(12)Hamlet,Ⅱ,ⅱ,315.
(13)Wholeness,既有完全或完美之意,又有通过医治而恢复健康之意。
(14)Readings in Christian Humanism,p66.
(15)从但丁直到康德,都有对此主题的阐述。直到二十世纪,潘尼卡(R.Panikka)又把对和平的论证从理性的政治学层面,重新回溯到形上的神学层面。(见其《文化裁军》,王志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16)《新约·启示录》,21:2-3。
(17)参见Readings in Christian Humanism,P66。
(18)布克哈特,前揭书,第543页。(译文略有改动。)
(19)同上。
(20)许多人声称人文主义者都反对作为经院哲学基础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但事实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多半不很关心哲学,不少人(如克列莫诺尼、彭波那齐、撒巴列拉等)则坚持亚里士多德主义(见后引书,第110页)。
(21)当时还有许多“半佩拉玖主义”的观点被归诸于奥古斯丁这个大权威(参见Paul Avis ed.: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y,Vol.,p.108.(Marshall Pickering,and Wm.B.Eerdmans Publishing Co.,Grand Rapids,1986))。
(22)参见E.Cassirer et.al.eds.The Renaissance Philosophy of Man,pp155-182.(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周辅成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有选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
(23)前揭书,p163。(参见周辅成译本,第25页。译文有改动。)
(24)前揭书,pp.224~225(周辅成译本,第33-34页,译文有改动)。
(25)从但丁(见其《炼狱篇》第16歌,第73行)到伊拉斯谟(见其《论意志的自由》),无数人文主义者都信仰并论证过“意志自由”这一基督教的学说。(参见G.桑迪拉纳编《冒险的时代》第153~16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
(26)《冒险的代价》,第161页。
(27)(28)G.桑迪拉纳编:《冒险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150、151页。
(29)《新约·哥林多前书》,1:18-19,20-21,27。
(30)其实在古代中国,老庄等思想家也表达过类似思想(如“绝圣去智”、“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大智若愚”等),只不过现代以来,国人的思想习惯丧失了类似的辩证和深度,日益肤浅地看待美丑智愚等等了。
(31)布克哈特前引书,第447页。
(32)同上书,第448页以下。
(33)同上书,第481页。译文略有改动。
(34)同上书,第490-491页。
(35)蒂里希:《政治期望》,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页。
标签:人文主义论文; 人文精神论文; 基督教论文; 中世纪论文; 意大利文艺复兴论文; 上帝的教会论文; 西欧中世纪论文; 宗教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耶稣论文; 圣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