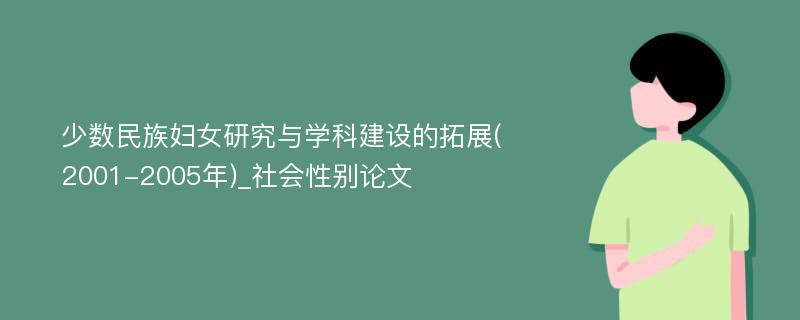
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拓展(2001—2005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少数民族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C913.6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867X(2006)06-0024-06
我国的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和妇女学学科建设,随着《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的签署,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制定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执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颁布,以及“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贯彻,近5年来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些进展主要表现在:
一、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主要进展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问题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妇女问题,尤其是处于边缘的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地位、政治参与、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受教育的状况、婚姻家庭及家庭暴力、人口健康及艾滋病的预防控制、权益保障及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越来越受到世人关注。
(一)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参与
广泛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不仅是少数民族妇女的基本人权,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及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同时还是政治发展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条件,也是提升少数民族女性地位的重要手段。
自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后,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以来,少数民族妇女参政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少数民族女性在国家最高领导层面——人大、政协及地方政府中的比例有所增加。据统计,在全国660个设市的城市中,有500多位女市长或副市长,其中不乏少数民族女性;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村委会选举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也在逐年提高。
与此同时,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妇女参政也进行了深入探讨。韩小兵基于少数民族妇女在人权保障体系中处于的基础、核心地位,阐述了少数民族妇女参政在人权保障范畴内的特殊意义。她认为我国对少数民族妇女参政保障方面的法律有了新的进展,具体表现在我国已加入多个相关国际公约,进行了各个层次的相关立法(宪法相关规定、相关法律、地方性法规);在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参政权方面,我国采取了包括加强少数民族女干部的培训、制定颁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建立专门的政府机构等举措,以促进包括参政在内的少数民族妇女各项人权的发展,结合不同民族特点及发展情况,采用一定的倾斜措施从而取得了明显成就。[1] 古丽阿扎指出,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的参政道路,同全国一样经历了由法律参与向事实参与、由民主参与向权力参与的发展道路。但是,由于民族特点和文化观念的差异,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的参政状况有着自身的特点。[2] 孙继虎、刘军奎在对甘南藏区卓尼县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认为藏族妇女政治参与相对来说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层面,存在着历史与现实相互交错的种种制约因素,只有从经济、教育、民族传统影响及现行民主制度运作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才能在充分考虑这些制约因素的基础上,为解决问题提供有力参考。[3] 孙懿在《探寻西部民族地区发展之路》[4] 一书中,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西部少数民族干部现状的研究之中,指出少数民族女干部偏少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强调少数民族女干部的成长是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关键。[5] 关于这一论题的相关论文很多,刘玉英的《关于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妇女干部的几点思考》[6]、韦峥芳的《从自身实践探讨少数民族妇女干部成长的内因》[7]、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党建调研课题组的《关于新形势下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选拔问题的调查与思考》[8]、李桂秋等的《注重培养民族妇女干部,积极促进民族团结繁荣》[9] 等等文章及观点的产出,均表现了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参与有了明显的提高。
(二)少数民族妇女的经济参与
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少数民族的贡献,少数民族妇女的经济参与,及在振兴民族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新千年以来,少数民族农村妇女成为农业劳动的主力军的趋势越来越突出。潘洪钢以南方少数民族女性为例,指出民族女性平等参与除狩猎以外的所有各项生产劳动,并在农耕、纺织、商贸等生产领域起着重要作用[10];熊坤新等认为,少数民族妇女逐渐在经济发展浪潮中成为农牧业生产的主要经营者和重要管理者,成为城乡经济开发与商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1];袁少芬对京族地区的调查显示,京族形成了“商女军团”,在海产养殖、收购、加工及旅游业等经济活动中成了主力军,成为稳定家庭收入的经济支柱,理财、管家的当家能手[12];拉毛错、丹珍卓玛指出,藏族妇女广泛参与了西藏自治区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做出了巨大贡献。[13]
在论及妇女与贫困问题时,齐顾波提出,在中国扶贫进入制度性扶贫阶段以后,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妇女贫困的原因,政府规定了对妇女发展的支持,例如开展小额信贷等项目[14];徐鲜梅在谈及扶贫效果时证实,云南小额信贷反贫困政策、措施与机制的执行和实施,促成了成千上万农村中的农民,也包括为数不少的少数民族妇女获得生产、经营及生活的资本和资金,并且从中受益[15];余鸣提出,把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传承与妇女脱贫联系起来,契合妇女的利益及情感,是民族区域经济发展项目可以尝试的一个方向。[16] 可见,少数民族妇女参与经济的范围越来越广,作用越来越大。
(三)少数民族妇女教育的发展
教育是民族地区发展的根本,也是少数民族妇女发展的关键。少数民族妇女地位的不断变化和经济参与的不断拓展,均与其接受学校教育的程度息息相关。因此,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少数民族妇女教育地位的指标之一,而教育地位正是少数民族妇女地位的核心内容。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少数民族女性青壮年文盲率降低到5%以下,基本杜绝了小学适龄女童失学,少数民族边远、贫困及流动人口中的女童受教育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在“妇女与少数民族”国际学术会议上,少数民族女童教育问题引起与会者的关注。会议认为性别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极有影响力的因素,儿童的性别及成人教育者的性别因素相互交织,影响着儿童的发展。有学者以甘肃省国家级少数民族贫困县——积石山县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女童教育为个案,探讨影响女童接受教育的社会根源;从夏河县牧区寄宿制小学的女童生活中,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描述藏族女童在课堂上、游戏中和宿舍里的学习及生活,运用文化认同、母性角色复制等理论对她们的生活现状进行解释[17];强海燕、张旭认为,少数民族女性教育必须关注处境不利的儿童,特别是农村儿童、女童及少数民族儿童;在赵琳提出的改善农村女童环境教育的项目中,包括训练教师及父母帮助女童增强自信,鼓励女大学生积极参与项目[18] 的主张;杨国才通过对云南少数民族教育的跟踪调研,呼吁并倡导尽快解决高中阶段教育的瓶颈,提高少数民族女性参与高等教育的比例,让更多的少数民族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消除少数民族女性教育中的民族与地域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性别之间的差距,指出制约女性接受学校教育主要是受到教育资源的不公平与贫困、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和民族传统文化、农业社会的传统农耕方式、社会性别制度建构的男尊女卑、民族女性早婚早育及弃学经商等因素的影响,提出发展少数民族女性教育的措施关键是消除对女性的歧视,让女性公平、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宋凤宁、张琼认为,历史的积淀和民族文化的渗透对少数民族地区女童的社会性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少数民族女童社会性健康和谐发展的措施[19];针对少数民族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李光明认为主要来自于学校、学生及社会观念等不同因素影响,建议从学校建设、毕业生就业观、学生创业、学校服务、社会环境等方面寻找对策[20];安学斌则从个人层面出发认为应该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优秀道德品质教育,构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优秀道德品质,从不同视角切入,提升女性教育。[21]
(四)少数民族妇女的婚姻家庭、就业、人口流动和健康
少数民族妇女的婚姻家庭和健康不仅是社会科学学者关注的领域,医学和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学者也对此作了大量研究。传统社会性别制度建构认为男性在公共领域,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去主宰一切;而妇女则在私有领域,围着锅边转,处于从属地位,然而在许多少数民族中则不尽然。赵瑛撰文揭示,布朗族妇女在社会生活当中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具体表现在:家庭主妇负责管理家庭内部事务和农副业生产,有更多的参与决策权,并享有一定的经济地位,掌管部分家庭开支;老年妇女可以担任氏族长,主管村寨内大小事务;实行母子联名制;有婚姻自主权;婚后男子行从妻居或望门居;女子拥有继承家庭财产的权利;有离婚、改嫁、再嫁的自主权。[22] 黄淳通过调查证明,随着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女性人口的文化和就业状况也发生了较大变化。[23]
潘洪钢认为,历史上南方少数民族妇女在婚前婚后都不落夫家,并且在寡居期间有着广泛的社交活动及性选择的自由。虽然婚后受到某种限制,但基本上仍然处于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仅仅用“母系社会残余”来解释是不够的,应运用历史和民族志材料进行论证,探索两性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地位与行为差别[24]。文华通过对佤族神话传说、祭祀神器、历史遗迹和民居建筑中的女性生殖崇拜特征的解析,认为这正是折射出佤族远古曾存在过的母系氏族阶段,从最深的层次建构着佤族的性别结构的缩影。[25] (P111)这些研究均证明一些少数民族妇女在其社会、家庭、宗教祭祀及村落文化中都有一定的地位。
少数民族地区人口与生育问题是社会热点问题之一,晓根指出,拉祜族人口生育状况高于全国、云南省的平均水平,属于婴儿出生率较高的民族,而且早婚早育情况比较突出。[25] (P243)然而,在民族地区虽然生育率高,孕产妇死亡率也高,在和虹的《丽江县妇女生育保健和孕产妇死亡情况分析》一文中也予以证实。[25] (P258)
从性别出生比来看,少数民族地区出生男女性别比为100比104、108,相对比较平衡。可是,目前老少边穷的民族地区妇女外流问题严重,许多年轻妇女的外流,造成了婚姻挤压。李勤以云南贡山县为例,发现妇女外流的产生,除了贫困的原因之外,家庭暴力、被诱拐以及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观念及早婚早育等对妇女的外流也造成了一定影响,而妇女外流在对当地农业生产、社会经济、家庭婚姻、子女教育等方面也同样造成严重影响。[26]
关于少数民族女性农民工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新的进展。金春子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民族工作》[27] 通过对少数民族流动的动因、特点及影响的研究,提出了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行管理和服务的建议,以引导和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和融入城市。针对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中的妇女群体,冯莎等的《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外流现象的实证研究》[28] 等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相关研究表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特点是:青年人是主体,女性占较大比重。少数民族女性农民工是现化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之一,为城镇提供了经济运转和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各种服务,从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镇劳动力的来源和商品的市场需求,推动了城市多元文化的发展,改变了城市人口的民族结构。
针对作为威胁少数民族人口健康之一的艾滋病问题,有学者提出在社会性别主流化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到少数民族妇女在原有社会性别机制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及其带来的对艾滋病传播的易感性,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尽快适应城市生活提供良好的服务,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规范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行为。
(五)少数民族妇女的权益保障
近年来,少数民族妇女权益保障水平不断提升,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法规和政治体系及监督机制进一步健全,维护少数民族妇女的权益网络进一步拓展,侵害少数民族妇女权益的违法行为和社会丑恶现象受到打击,少数民族妇女依法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也有所提升。但是,少数民族妇女特别是老年妇女的社会保障问题却日益突显。
高芙蓉指出,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包括少数民族妇女在内的优惠政策和法制保障,在国家帮助和少数民族妇女的自力更生和努力之下,少数民族妇女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及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少数民族妇女成为本民族、本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29]。有学者提出,应当重点关注农业少数民族妇女的权益保护,在基本法律中明确规定对少数民族妇女参政的保护,在地方法规、自治条例或单行法规中加入具有可操作性的权利保障条款,完善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监督机制和侵权行为的法律制裁规定,建立和完善教育培训法律制度以及相关法律宣传机制,才能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妇女的权利。李玉子以朝鲜族妇女为例做了认真调查,发现老年妇女的生活状况、养老设施、娱乐设施等都比较差,提出了改善和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的措施[25] (P200-201),逐步探索和解决少数民族老年妇女的老有所依、所养。
(六)少数民族妇女与传统文化
传统的刻板印象认为少数民族没有知识,少数民族妇女更是如此。为了更好地证明少数民族妇女拥有的知识和文化,发出少数民族妇女的声音,云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女性与社会性别研究中心于2004年组成课题组,对少数民族妇女民间手工艺中体现出的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少数民族历史、历法、自然环境、地理等进行了口述史调查,发现这一切都可以从妇女的手工艺中找到答案。如白族妇女木雕、刺绣、扎染、草帽编织,傣族妇女的织锦,壮族妇女的草织,彝族妇女的绣花,纳西族妇女的造纸等,都包含、凝聚着少数民族妇女的心声和智慧。这些都与少数民族妇女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少数民族妇女的知识沉淀。金少萍指出:纺织是女性的性别认同,是女性利用空隙空间的时间劳作,也是衡量女性的标准和尺度[30]。伍琼华指出,云南少数民族妇女手工艺品是云南旅游文化纪念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走向市场化[31]。可以说,云南少数民族妇女与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组织和学科建设的发展
随着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的凸现和妇女研究的拓展,少数民族妇女研究队伍在逐渐扩大及研究组织的设立和女性学学科建设也被提到议事日程。
(一)少数民族妇女组织机构的壮大
为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多学科、多视角、多层面的优势,借助社会各界力量对少数民族妇女与社会发展的理论、实践和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为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研究和民族妇女参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为决策部门和社区组织提供决策依据及信息,关注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机构相继成立。
在这一进程中,全国成立了一批少数民族女性学研究机构。以云南为例,21世纪初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发展成为云南健康与发展研究会,随后又相继成立了云南PRA学习小组、云南社会性别研究小组、丽江民族文化与性别研究会等机构。随着1999年云南民族大学女性学硕士的招生与发展,云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女性与社会性别研究中心于2000年3月8日正式挂牌,打破了在云南高校中尚无相关研究中心的先例。此后,2001年,云南大学社会性别研究中心正式成立;2002年,云南省曲靖市委党校妇女研究中心成立,之后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农业大学、云南财经大学的妇女研究中心和女高知协会也相继成立。
在全国范围内,同一时期成立的少数民族女性研究机构还包括:2001年5月西北师范大学成立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心,2001年11月由白族女作家景宜积极倡导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支持下成立的中国少数民族妇女文学交流中心。这一时期,民族地区高校、妇联的妇女研究中心相继成立。2000年3月,内蒙古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成立;2001年,福建师范大学女性学研究所成立;2002年,内蒙古师范大学女性问题研究中心成立;2003年,广西大学妇女与发展研究中心成立;2004年内蒙古妇女儿童研究会的建立等。少数民族女性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健全,促进了各民族学子和妇女工作者到民族地区开展各种调研活动,同时,这些机构根据民族地区妇女的需求,进行了许多有益于妇女发展的项目。
(二)国际项目进入民族地区后对研究的推动
在少数民族研究机构、女性学学科建设和建立过程中,国际项目的进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包括资助很多“少数民族妇女发展”项目。以高校为项目载体,实施妇女发展项目在云南是一大特色。如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昆明医学院三家共同开展的福特基金项目“女性与社会性别研究”,又如云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女性与社会性别研究中心的“高校女性学学科建设与农村少数民族妇女能力提升”、云南大学的“西部大开发中女性高等教育的地位与作用——以云南为个案”,以及“纳西族、彝族社区社会性别案例资料开发项目”、“云南少数民族女性生育健康中社会性别与参与式研究”等。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妇女问题,云南民族大学还组织完成了少数民族妇女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少数民族妇女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少数民族妇女与宗教、少数民族妇女的涉外婚姻、少数民族妇女的教育、少数民族妇女参政等与少数民族妇女切身利益相关的项目。
在云南,妇联、党校、高校、社科院结合进行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研究,也成为其一大特点。云南民族大学与省妇联共同申报完成的“少数民族妇女的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研究”,有力促进了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的理论研究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
同时,伴随着各种项目的进入,少数民族妇女的觉悟逐渐提升,她们开始认识自己的生存同环境的关系,在资源分配(主要是土地、森林、水)、接受教育、参政议政、脱贫致富等问题上,开始发出她们的声音,反映她们的需求。
(三)少数民族妇女学对象和方法的提出
进入21世纪,学术界力图用科研成果为决策提供依据的做法,远远不能满足各族妇女的需求和解决各族妇女的实际问题。因此,通过教育,把妇女问题,特别是少数民族妇女的教育纳入到高等教育中,使决策者通过接受先进的性别文化教育武装自己的头脑,逐渐消除头脑中的性别盲点,才能把贯彻实施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落到实处,于是,少数民族妇女学也就应运而生。在学习借鉴西方女性主义和方法的过程中,学术界也进行了本土化的尝试,并对少数民族妇女学的对象和方法进行了探讨,认为少数民族女性学是从性别的视角来研究民族女性和与民族女性有关的问题,是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它已由少数民族女性为研究客体向民族女性为主体发展,由最初的“女权主义批评”向“性别分析”转型;由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研究逐渐向学科内部结构渗透。它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而且还具有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内容涉及少数民族女性的文化、少数民族妇女与法律、政治、经济、宗教、人口、生育健康、教育、公共政策、婚姻家庭以及民族妇女与多元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少数民族女性学的研究方法,是通过运用质性研究、田野调查、深入访谈、分析历史文献和材料来了解分析少数民族社会状况;并且综合运用典型调查、个案调查、口述史等方法搜集材料,运用行之有效的分析工具,如社会性别分析、农村快速评估RRA、农村参与性评估PRA、参与式监测与评估方法等,力求使少数民族妇女学有自己的特点,使女性学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实证性和应用性。
(四)少数民族女性学的推广
目前,少数民族女性学的学科建设尚处在起步阶段,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西藏民族学院以及广西、湖南、贵州等地区的高校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少数民族女性学学科建设虽已起步,但仅仅是一种尝试,还缺乏理论的深度和高度,尚有待于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改进、提升与创新,以丰富少数民族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三、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特点和展望
新千年以来,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和学科建设普遍开展,异军突起,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从多学科切入,逐步整合学科优势
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已从20世纪的婚姻家庭中的妇女指标拓展到妇女参政、经济参与、教育、就业、人口流动、健康、家庭暴力、权益保障、文化交流、妇女发展等现实问题和基本理论问题。
(二)以少数民族妇女为对象的学术团体的成立
2000年以前,虽然我国妇女研究的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但很少有研究少数民族妇女的机构。2001年以来,以少数民族妇女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团体不断涌现,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组织的建立,为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提供了组织保障。
(三)少数民族女学者在研究教学中成长
少数民族妇女问题引起了一部分少数民族学者和汉族学者的关注,逐渐研究者以少数民族女性为主体,她们以自觉的女性认同,积极投身于少数民族妇女的调查研究和教学实践行动中。这种研究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实证性、应用性,研究队伍呈多元背景,并出现了一批以研究本民族社会性别与发展为己任的少数民族女性学研究人员,如纳西族学者和钟华、苗族学者张晓、满族学者定宜庄、朝鲜族学者郑玉顺等等,均在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和学科建设过程中成长起来。
(四)社会性别的理论和方法的引入
近5年在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和学科建设中,最富有特点的是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研究在社会性别理论、性别分析方法论影响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由初期的大量搜集资料、调查报告或沿袭传统文化研究方式的阶段,逐步过渡到对妇女问题的理论抽象,以女性为主体去探讨少数民族妇女的生存状况、文化贡献、社会地位等重大问题,探讨民族妇女在民族社区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五)少数民族妇女学学科建设的兴起和推广
少数民族妇女学的缘起和课程设置及女性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开设,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结晶和特色,也是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研究从理论到实践再到行动的本土化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