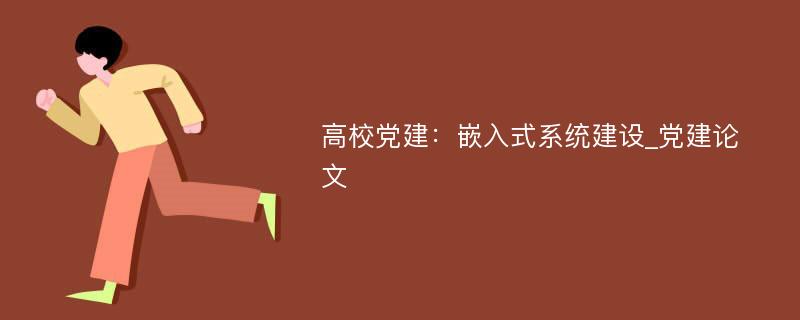
高校党建:一种嵌入性的制度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建论文,高校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10)06-0036-03
近年来,制度建设日益成为高等学校党建工作中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在探讨如何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促进学校事业发展的时候,无论是理论工作者还是实际工作者,都有相当一部分人将焦点集中在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方面,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制度化诉求。但是,制度建设是否必然促进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高等学校党的建设与事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旨在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的各种制度建构是否必然促进学校事业的科学发展?这些其实是鲜有关注却颇值得深入反思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制度建构:高等学校改革的新取向
所谓制度,是一个社会人类相互交往的游戏规则,它约束着人们的相互关系,抑制着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的和乖僻的个人行为,使人们的行为更可预见并由此促进着劳动分工和财富创造。①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思认为:“制度构造了人们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②正因为制度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人们一般认为,对于高等学校的改革与发展而言,制度同样具有突出的功用与价值。
第一,制度所具有的明确和具体的特点,能够为高校共同体成员提供发展的目标指向。在高等学校治理过程中,制度一般以尽量详尽和细致的条约形式明确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区分允许行为类型和禁止行为类型,界定对与错、是与非、善与恶。制度规范的这种明确性和客观化,不仅为高等学校师生群体成员的行为与发展提供了明确的目标指向,而且也便于高等学校里个体成员掌握、遵守,以及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与评判。
第二,制度对特定价值与行为的规范和约束,能够抑制学校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方面,制度的确定性所显现的人的一定行为与一定后果之间恒常的因果关系,能够使人们预测自己行为的后果,而行为后果的利益得失,则能够成为影响人们行为选择的重要权衡因素。另一方面,正因为制度是对人类社会行为和利益关系的一种调整与规范,同时使得它也具有对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抑制功能。高等学校治理中的制度往往通过对特定价值的崇尚和对特定行为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和抑制学校治理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提高学校的治理绩效。
第三,制度对破坏利益关系的行为所体现的制裁性,能够弥补日常口头约束的软弱性。在社会急剧变革和转型时期,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利益诱惑和刺激,主要依赖内在约束的学校教育往往显得苍白无力。然而,将学校教育转化为具体可行的制度则较好地弥补了这一缺憾。它通过国家政策、法律、条例、规定等,对社会成员具有程度不同的外在强制和约束功能。
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的背景下,这些年来,以现代大学制度为核心的制度建构,逐渐被认为是推进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甚至是核心的问题。围绕高等学校改革发展问题的各类制度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建立起来。
二、高校党建:一种嵌入性的制度类型
道格拉斯·C·诺思认为:“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的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的。”柯武刚和史漫飞的界说更为清晰,他们认为,从规则的起源来看,制度可以划分为内生性制度和外生性制度(又称外嵌入性制度)两类。
内生性制度(internal institutions)是从人类经验中演化而来、体现着过去曾最有益于人类的各种解决办法,如习惯、伦理规范、良好礼貌和商业习俗等。违反内生性制度通常会受到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非正式惩罚,例如,不讲礼貌的人发现自己不再受到邀请等。我们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规则多数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而演化、发展起来的内生性制度。外生性制度(external institutions)是由统治共同体的政治权力机构自上而下地设计、强加于社会并付诸实施的制度规范。它们被清晰地制订在法规和条例之中,并由一个诸如政府那样的、高居于社会之上的权威机构来正式执行,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具有规范性影响。④
运用这一分类方法考察高等学校的制度建构,我们认为,从这些制度的起源来看,同样可以划分为内生性制度和外生性制度两大类型。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认为将“外生性制度”翻译为“嵌入性制度”更能体现这种制度类型的内在涵意。
以高等学校为考察对象,所谓内生性制度,是指根源于大学这一特殊事物的发展历史,与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这三个基本职能直接相关,由大学校园的师生群体互相约定,经较长时期的生活经验冲刷和共同生活积累而成,与大学独立自主办学精神自然契合的习惯、习俗和规则等。这种内生性制度既包括大学自中世纪以来已经普遍内化、认同、遵从的基本准则(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新等),也包括大学基于具体的发展目标和愿景需要而拟订的共同章程和达成的共同协议(如大学章程等)。它们虽然形式各异,但从制度衍生的角度来看,都是内在而自然生成的。与内生性制度相对,高等学校的嵌入性制度,则是指由大学师生群体以外的国家、政党及其他社会组织设计,并通过一定的方式加之于大学这个共同体之上,从外部要求大学遵从的制度形式。按照制定主体的不同,这些制度既包括国家层面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如《高等教育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及教育部出台的相关政策规定等,也包括各地、各高校乃至学校各院系结合实际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等。按照规定内容的不同,这些制度既包括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与大学职能直接相关的内容规定,也包括内部管理、党的建设、校园文化等间接相关的内容约束。按照表现形式的不同,这些制度既包括如法律、行政规章、各类文件规定等文本性规则,也包括约定俗成、潜行于学校日常工作中的非文本性规则。
从这一视角来考察我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应该看到,它总体上是从执政党的目标与价值追求出发,从外部嵌入高等学校的一种嵌入性的制度体系与类型。这种制度嵌入,根本的目标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工作的载体是党在高校的基层组织、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工作的抓手是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应该说,这种制度的嵌入,集中代表了执政党的诉求,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反映了社会的需求。
三、制度过密:党建工作中的潜在误区
基于制度规范在高校治理中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与功用,加之执政党对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迫切需求,近年来,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通过发挥学校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和推动高等学校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日益成为一个不证自明的思维逻辑和日渐盛行的话语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围绕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的各项制度开始不断输入高等学校,并有不断强化之势。
就高等学校外部的宏观形势来看,2000年以来,我们党先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系列集中性的教育活动。高等学校作为党执政的一个重要阵地,历来被列为重要的教育领域。与此同时,除了中央的统一教育活动和工作部署以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还自行确定主题,开展了诸如“固本强基工程”、“两思”(饮水思源、富而思进)、“三有一好”等系列教育活动。相应的,各地还结合本地实际,针对所属高校,制定了一系列工作制度。如高校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制度、高等学校党委工作规定、校长工作规定、领导干部任期制等。
就高等学校本身这个中观层面来看,配合上级的要求和学校党委的工作设想,各高等学校党委除了完成上级党委和职能部门的“规定动作”外,往往根据学校特点,创造性地开展了许多“自创动作”,形成了一大批制度规范。据笔者的调查显示,仅2008年一年时间里,某高校以学校党委名义制定下发的各种文件和制度规定就达40个之多,这还不包括学校六七个党委工作部门以部处名义制定下发的大量通知规定和下属近30个二级学院党委和近500多个党支部结合自身实际制定的庞杂的细化措施和规定。
就高等学校内设院系这个微观环境来看,某高校的二级学院党委一年就制定出台了10余项制度规定,个别二级学院甚至将总计10余万字的各类党建工作文件和规定汇编成册。
仅从逻辑推理而言,如果我们赞同加强党的建设是推进我国高等学校发展的重要抓手,制度建设是加强高校党的建设的重要途径的话,那么,上述围绕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的各项活动和制度规定(按照新制度主义的界定,制度不仅仅包括文本性的制度规定,也包括与之相关的各类活动等)就应该较好地促进高等学校的事业发展,并获得高校师生群体的广泛认同。然而,结合笔者近年来对许多学校的深入考察和对包括部分学校领导、中层干部、教师和学生代表在内等不同层面、各类群体的访谈,大量的经验事实表明,这些活动不仅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学校的办学精力,耗费了人力物力,干扰了正常的教学和科研,无形之中阻碍了学校的发展,部分师生对这一问题的反应尤为突出和强烈。当然,并非类似上述所有制度的建构都遭到否定。也有很多师生们反映一些活动和制度的确在促进学校理清思路、调整策略、改进方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学校的发展。
这就产生出几个十分尴尬而迫切需要厘清的问题:从执政党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等良好愿望出发,为什么一些旨在通过加强学校党的建设的制度建构并没有促进学校的事业发展,得到师生的广泛认同?为什么一些制度能够较好地促进学校的发展,而另一些制度却难以奏效,甚至背道而驰?什么样的制度建设才能有效地促进学校的事业发展?对于高等学校这个颇具自治共同体色彩的组织而言,这种密集而庞杂的制度嵌入,是否已经处于一种“制度过密化”⑤的状态?
四、内在契合:高校党建工作制度建构的基本精神与启示
回到制度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为一种嵌入性制度,高校党建工作及其相关的制度建构因其正式性、明确性、强制性的特点,在节约信息成本、保证制度执行、提高制度绩效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但是,源于大学历史、符合办学规律、经千百年经验冲刷而自然积累形成的大量内生性制度,却因为包含着大量经过精练和检验的先人智慧,在规则的遵守与运用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正是基于内生性制度和嵌入性制度各自所具有的优点与缺陷,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提醒人们要十分注意二者的协调与匹配问题。嵌入性制度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是否与内在演变出来的制度互补。⑥这表现在大学治理过程中,就是强调由国家、政党以及其他外在组织机构制定并依赖一定惩罚措施予以强化的嵌入性制度必须真实地得到大学师生群体的普遍接受与认可,必须支持大学校园内已经形成和认可的根深蒂固的规则、文化、传统和精神,必须与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这些内生性制度形成内在的契合。
基于上述讨论,关于新形势下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加强高校党的建设,真正促进学校的事业发展,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几点启示:
第一,就高等学校党建工作而言,制度和制度建构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但制度本身具有不同的结构与类型,这些不同结构与类型的制度在实践中既可能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也可能互相冲突,因此制度建构并不必然带来高校党建工作水平的提高。
第二,我们在进行党建制度的建构过程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要根据大学的内在发展需求开展外在的制度建设。如果不考虑这一点,而只是一味地通过施加外在的制度约束,不仅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使大学发展的“自主空间”受到过分的挤压,并最终违背制度设计者的初衷,有碍于大学的健康发展。当然,这种嵌入性的制度在实践中也必然因为招致个人的漠视或群体的抵抗而减损绩效甚至无效。
第三,事实上,每一项预期能带来收益的制度设计与安排都需要耗费成本。如果不考虑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成本以及制度的实际效用之比较,而是一味地迷恋制度,期求通过制度解决所有问题,其结果只能是制度绩效的低下甚至无效,并最终导致“制度过密化”。
第四,要保证高校的健康快速发展,一个重要的选择就是尊重制度均衡的规律,减少对大学无序的制度嵌入,按照“适度制度化”的原则检视现有制度,增强制度供给的实际效用与价值,防止高校党建滑入更为严重的“制度过密化”陷阱。
五、结语
“大学只能作为一个制度化的实体才能存在。”“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尽管说每一种制度架构都要责无旁贷地推动科学研究的进步和研究成果的传播,但是只有毫不懈怠地对它进行补漏纠偏,才能保证它不偏离正轨,尽心尽力地服务于大学之理念。”⑦
注释:
①③[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②[美]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④⑥[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2-37、36页。
⑤“制度过密化”是王金红先生和笔者近年来在研究村民自治问题时,受黄宗智和杜赞奇先生的启发,提出的一种理论假设,其内涵指源于外部嵌入的制度超过了村民自治实践的实际需求,导致制度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形。具体而言,就是指制度的增长超过制度的实际需求而形成的制度剩余状态,也是制度的增长与制度的边际效益递减同时存在的现象。后来,笔者发现,这一假设同样适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领域。具体参见:王金红、蒋达勇:《制度过密化:解释村民自治发展瓶颈的一种理论假设》,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⑦[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08、1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