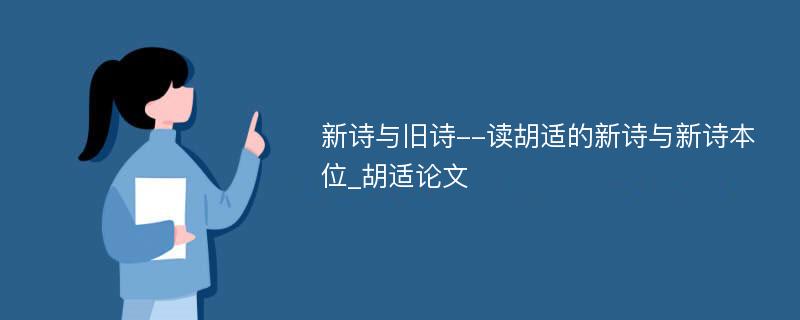
新诗与旧诗——重读胡适谈新诗兼论新诗的标准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胡适论文,旧诗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重读胡适谈新诗
中国现代新诗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对于它的批评就一直不绝于耳,关于新诗与旧诗的高下优劣也一直成为困扰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的重要话题。对于新诗的批评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和针对性,但其实质则是怎样看待新诗的标准问题。近来有关新诗二次革命的呼声再次掀起有关新诗标准问题的论争,特别是所谓新诗二次革命的说法与胡适当年提出新诗革命的主张一脉相承。因此,重读胡适当年谈新诗的有关论述,结合中国现代新诗90年发展历程中的成败得失重新思考新诗的标准问题,也许可以给我们思考今日新诗所面临的问题有益的启发。
在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史上,胡适本身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批评家,而更像是一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人物。因此,他对于新诗的评论,既奇特又复杂,并且产生了深远影响。胡适关于新诗的理论批评,较为集中地反映在他的《谈新诗》(1919)、《〈尝试集〉自序》(1919)、《〈尝试集〉再版自序》(1920)、《〈尝试集〉四版自序》(1922)、《谈谈“胡适之体”的诗》(1936)等文章中。此外,胡适早期的一些重要文章,如《文学改良刍议》(1917)、《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以及后来的《逼上梁山》(1933)等,虽然是从总体上论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但也多少涉及到新诗的问题。
《谈新诗》是胡适早期集中论新诗的一篇文章,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及胡适的多种文集中。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称此文是新诗的“金科玉律”。胡适该文所谈到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因此,也可以说“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新诗革命的目标。这个目标具体说来,就是用自然的语言,以自然的方式写出自然而然的诗。用胡适的话说,就是“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胡适还谈到,“新诗大多数的趋势,依我们看来,是朝着一个公共方向走的。那个方向便是‘自然的音节’”。在谈到新诗用韵的问题上,胡适认为,“新诗有三种自由:第一,用现代的韵,不拘古韵,更不拘平仄。第二,平仄可以互相押韵,这是词曲通用的例,不单是新诗如此。第三,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新诗的声调既在骨子里,——在自然的轻重高下,在语气的自然区分——故有无韵脚都不成问题。”其次,所谓“诗体的大解放”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从《三百篇》到南方骚赋文学发生,这是第一次诗体大解放,到汉以后五七言古诗的产生是第二次解放,唐五代以后词的产生是第三次解放,新诗的产生则是第四次诗体大解放。由此可见,新诗是从旧诗脱胎出来的。胡适称他所见到的“新诗人”,“除了会嵇周氏弟兄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这说明新诗的发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自然趋势。“自然趋势逐渐实现,不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那便是自然进化。自然趋势有时被人类的习惯性守旧性所阻碍,到了该实现的时候均不实现,必须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的实现,那便是革命了。”第三,新诗并不是不讲艺术,甚至比旧诗更难做好,但新诗并没有自己的特殊方法,“做新诗的方法根本上就是做一切诗的方法”。而这个所谓做一切诗的方法归结起来就是:“诗需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凡是好诗,都能使我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逼人的影象。这便是诗的具体性。”从以上可以见出,胡适早期谈新诗的一些观点的确都是一些给早期新诗定位的大问题,但所谈既不够系统,也不够深入。在写于1936年的《谈谈“胡适之体”的诗》一文中,胡适则对自己的诗歌主张做了清理,将其归纳为三点:第一,说话要明白清楚。“一首诗尽可以有寄托,但除了寄托之外,还须要成一首明白清楚的诗。意旨不嫌深远,而言语必须明白清楚。古人讥李义山的诗‘苦恨无人作郑笺’,其实看不懂而必须注解的诗,都不是好诗。”第二,用材料要有剪裁。这类似于人们说的诗要精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第三,意境要平实。胡适自己解释说,“我自己总觉得‘平实’、‘含蓄’、‘淡远’的境界是最禁得起咀嚼欣赏的。‘平实’只是说平平常常的老实话,‘含蓄’只是说话留一点余味,‘淡远’只是不说过火的话,不说‘浓的化不开’的话,只疏疏淡淡的画几笔。”[1]胡适的这些关于新诗的思想主张颇能反映出他个人的审美趣味和早期白话新诗的发展轨迹。特别是他的所谓新诗革命论,更是对后来的新诗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胡适关于新诗革命的主张与他的文学革命思想有着密切联系。“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据胡适在其文学回忆录《逼上梁山》(1933)中讲,“文学革命”的口号是他在1915年夏天与梅光迪、任叔永、杨杏佛等一帮朋友“乱谈”出来的。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思想最早见于1915年9月17日他在美国写给梅光迪的一首打油诗。其中写道:“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1915年9月20日,胡适又在从纽约到哥伦比亚大学的火车上写了一首给任叔永的打油诗,明确提出“诗国革命”的主张和要求:“诗国革命何自始,应须作诗如作文。”10年之后,穆木天在《谭诗》(1926)中指出,“中国的新诗的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胡适说:作诗须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错。所以他的影响给中国造成一种Prose in Verse一派的东西。他给散文的思想穿上了韵文的衣裳。”[2]穆木天的说法固然有道理,但胡适所主张的新诗革命所要解决的,则是比作诗更为重大的问题,即胡适在《谈新诗》(1919)中所说的,“文学革命的目的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活的文学”。
一般认为,胡适关于新诗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主要来自于英国湖畔派诗人和美国意象派诗人。唐德刚先生则认为,胡适所倡导的“文学革命”运动,实际上是受了辛亥革命的影响[3](P124)。而胡适自己在《谈新诗》中也认为,新诗的出现,正是辛亥革命以来的一件大事。因此,把“文学革命”或“新诗革命”的口号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革命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应该是更为合理的解释。事实上胡适在《谈新诗》一文中一开始就是把“新诗革命”和“辛亥革命”放到一起讨论的。有学者指出,“梁(启超)、胡(适)的‘诗界革命’或‘文学革命’,既称之为‘革命’,就必然与那个政治的革命主潮难分难解,且两者的关系极富于戏剧性。”[4](P242)而胡适之所以又竭力把他的文学革命思想表述为文学改良的提法,并且竭力把新诗革命的主张局限于语言工具的范围,除了与他在国外所受到的改良主义思想有关以外,更与他在“五四”时期特殊的“文化上的焦虑感”有关。[4](P239)所以,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新诗革命还是文学革命,都不是从文学本位提出的口号,其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效果,也都不是诗和文学所可以企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诗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口号也许都可以看作是近代国势衰颓后政治变革与文化激进心理在文学中的体现。至于诗和文学是否真的可以革命,则不是他们那一代人所要考虑的问题。
由此,新诗和旧诗就远远不只是文学问题,而被认为反映了文化立场乃至政治立场的保守和先进的问题。像这样对新诗的理解或许从一个方面促进了文学革命的历史进程,但也可能因此妨碍了对于诗和文学的恰当的理解。新诗和旧诗,无论还可能具有什么样的宏大意义,首先和最终都必须作为诗来加以认识和讨论,都必须按照诗的艺术规律去加以分析和评价,才可能获得正确的理解。胡适当年论新诗显然忽略了这一点,新诗“二次革命”论者是否也会这样呢?
二、诗就是诗,新诗与旧诗都有好诗和不好的诗
自20世纪初新诗诞生以后,把新诗与旧诗加以比较,或以旧诗的标准非难新诗,或以新诗的尺度否定旧诗,一直是诗歌理论批评中的突出现象。但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文学问题。新诗或旧诗实在只是一种形式的尺度,并不是真正诗学意义上的判断标准。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有好的新诗,也有不好的新诗,正如有好的旧诗,也有不好的旧诗一样。进而言之,如果现在有一些诗歌作品不好理解或者写得不好,并不是因为它们是新诗,而是因为它们是不好的新诗。这就把问题引向了深入,即引向了诗学本身。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样的诗才是好的诗?或者说好诗的条件是什么?它们在文言文诗里是如何表现的?它们在白话文里又是怎样表现的?这些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说新诗二次革命的主张是为了解决新诗中存在的问题,那么在我们看来,首先还得解决理想的诗歌的标准问题,包括理想的旧诗、理想的新诗以及古今中外一切诗歌的理想尺度。
旧诗中的好诗和不好的诗其实早在胡适以前的时代就已经被相当充分地讨论过了,不过今天仍然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不同时代的古人对于诗的看法并不相同。今人跟古人的看法更是相去甚远。古人认为好的,今人未必认为好,或者今人未必会认为好在同样的地方。典型的例子是历代对于陶渊明的评价代有不同。与陶渊明时代相近的晋代钟嵘在其《诗品》中将陶诗列为中品。大约700年以后,宋代的苏轼才对陶渊明的诗给予了全新的评价。现代诗人闻一多读到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后则激动不已,认为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5]革命时代的文学史则将其视为形式主义的作品。类似情况在诗歌阅读史上不胜枚举。不过,我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古代旧诗中的好诗究竟好在哪里。宋代严羽在其所著《沧浪诗话》中对此似乎有一个大致的总结。按照严羽的说法,“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则认为古诗之妙在于无我。今人则另有说法。俞平伯在《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1919)中讲,“我们现在对于古诗,觉得不能满意的地方自然很多,但艺术的巧妙,我们也非常惊服的。”[6]
这种“艺术的巧妙”究竟“巧妙”在哪里?归结起来说,中国古代旧诗中的好诗的一个特点是它的感性品质,始终以生动的形象说话,在直观中把握世界,由此构造出一种日常生活之外的虚拟世界和审美境界,使人们的精神得以安顿。“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一种境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又是一种境界。“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既是诗中的生活,更是生活中的诗。当然,这样的诗的生活使人陶醉,也容易使生活变得停滞。中国古代旧诗中的好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语言精练含蓄,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中国古代旧诗语言精练含蓄与古代文言的特点有关。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文言被称为是一种“人治”的语言,多用单音节词,词性灵活,没有严格的词序要求,也没有形态变化和时间等人为限定,讲究的是所谓神而明之的文气。叶维廉先生曾指出把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翻译成英文碰到的诸多问题。这其实也是整个文言诗都存在的普遍问题,甚至把文言诗翻译成白话新诗亦有此类问题,而这正好反映出文言旧诗在语言上的特点所在。不过,文言旧诗在语言上的精练含蓄,从根本上讲,源自中国自古以来的世界观以及“以物观物”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旧诗中的好诗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便是音韵和谐而有韵致。音韵和谐的诗的最大优点在于它的音乐性。如果说所有艺术都以逼近音乐为指归的话,有理由认为音乐性是诗歌语言感染读者激荡人心的重要原因。而且中国旧诗的音乐性除了押韵,还有平仄。魏晋时期沈约等人所说的“四声八病”就是说的这一问题。至于后来把押韵和讲究平仄当作做诗的主要甚至唯一功课,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旧诗也有坏诗和不好不坏的诗。但这并不是因为它用的文言。文言对于中国旧诗固然有功绩,但成就中国古典诗歌的关键毕竟还不在文言,而在于中国古人的世界观和艺术的审美方式。
不言而喻,新诗对于旧诗而言,是一种异质的东西。但新诗中也有好诗、坏诗和不好不坏的诗。新诗中的好诗好在哪里?是不是正好就是完全跟旧诗相反?恐怕问题还不是这样简单。白话新诗的特点和优点,现代以来的诗人和诗论家已经谈得很多。有一些共同的意见,也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概括起来,新诗的优点和特点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诗是自由诗,即是用白话语言写出的诗歌作品。这可以说是新诗之为新诗的最基本的特征。这在胡适的时代被表述为“白话诗”或“诗体的大解放”,也就是胡适在《谈新诗》中所说的,“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郭沫若早期关于新诗的看法在这一点上也与胡适相似。郭沫若在20世纪20年代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集《三叶集》中就谈到:“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Intrinsic Rhythm),内在的韵律(或曰无形律)并不是什么平上去入,高下抑扬,强弱长短,宫商征羽;也并不是什么双声叠韵,什么押在句中的韵文!这些都是外在的韵律或有形律(Extraneous Rhythm)。”[7]此后戴望舒又特别强调“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8]艾青则根据新诗的特点提出“诗的散文美”的命题。直到废名在总结此前新诗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基础上,才进一步明确提出“新诗应该是自由诗”[9]。因此,尽管在这一问题上早期白话新诗从创作到理论都还不够成熟,也产生了闻一多等的新诗格律论和种种矫正理论及其创作,但在白话语言基础上形成的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观点,已成为新诗无可更改的特点和新的艺术传统,对新诗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其次,诗歌无疑是表达情感的。“诗是主情的文学。”(康白情《新诗底我见》,1920)“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之纯真的表现,生命源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之颤动,灵的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欢乐的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7]但新诗的特点是着力表现现实的、世俗的思想情感。这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中的“三大主义”里就已有所规定,即所谓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以及“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俞平伯在《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中也谈到:“中国古诗大都是纯艺术的作品,新诗的大革命,就在含有浓厚人生的色彩上面。”茅盾在《论初期白话诗》中集中论述了初期白话新诗的三大特点,认为初期白话诗的第三个要点——也是它最主要的精神就是“写实主义”。[10]后来新诗走向民间,甚至走向革命,都是这一特点的反映和发展。
第三,新诗继承了传统诗歌的感性品质,同时又表现出更多的开放性,大胆融合了西方现代诗歌的艺术手法,形成新的艺术传统。新诗的这一特点也就是胡适所说的“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的意思。其实胡适说得很明确,“做新诗的方法根本上就是做一切诗的方法”。这种“具体的做法”在早期新诗中主要表现为写实的方法,包括描写和叙述。沈尹默的《三弦》、周作人的《小河》、俞平伯的《孤山听雨》、康白情的《和平的春里》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新诗中的描写和叙述的方法在以后还有进一步的发展,但随着新诗的进步,特别是随着对于早期白话诗的反思,早期白话诗在艺术方法上的简陋受到冲击,逐渐被更为丰富和更为成熟的艺术方法所取代。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受西方影响产生的象征主义和意象主义的方法。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冯至、艾青、穆旦等都为此作出过贡献。这也显示了新诗在发展中的开放姿态。
新诗和旧诗中都有好的诗和不好的诗,这一事实说明,新诗和旧诗,并不是评价诗歌的真正标准尺度。而且,如果说在80年前,新诗的老祖宗们更多的看到的是新诗和旧诗的区别甚至势不两立的话,今天我们则看到,新诗和旧诗既有不同之处,也有诗之为诗的相同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讲,诗就是诗。新诗的老祖宗们碰到的问题与我们既有很大的不同,也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同样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相同的一面。如果所谓新诗的二次革命要成为一个合理的口号的话,显然不能只是从新和旧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也不能停留在“五四”时代的思想水准上。
三、现代新诗应该是更适应现代人的诗
1917年,钱玄同在一篇《寄胡适之》的书信中曾这样写道:“先生‘自誓三年之内专作白话诗词,欲借此实地实验,以观白话之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此意甚盛。玄同对于用白话说理抒情,最赞成独秀先生之说,亦以为‘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11]这似乎是一种新诗绝对取代旧诗的论调。
1937年,叶公超先生写了一篇《论新诗》的文章,其中的看法与钱玄同则有所不同,认为“新诗和旧诗并无争端,实际上很可以并行不悖。不过我们必须认清,新诗是用最美,最有力量的语言写的,旧诗是用最美,最有力量的文言写的,也可以说是用一种惯例化的意象文字写的。新诗的节奏是从各种说话的语调里产生的,旧诗的节奏是根据一种乐谱式的文字的排比作成的。新诗是为说的,读的,旧诗乃是为吟的,哼的。”[12]这似乎是一种新诗旧诗并存论。
到了50年代,毛泽东又认为新诗50年来迄无成功,并认为新诗的出路在于古典和民歌。不少原先著名的新诗人如郭沫若、臧克家等,都干脆写起了旧诗。事实上当代新诗仍然有不少值得一读的作品。80年代产生的朦胧诗更是推动新诗发展到一个高峰。但近年来,新诗的先锋姿态以及另类诗歌写作却使不少人望而却步。著名诗人周涛在若干年前曾一口气对新诗发出十三问,其中有好几问都涉及到新诗与旧诗,有一问这样问到:新诗发展的大方向是不是错了?如果不错,为什么这条路越走越窄?如果错了,那么会不会是一个延续了近百年的大误会?又问,毛泽东多次高度赞扬鲁迅和鲁迅的旧体诗,却从没有称赞过任何一位新诗人的作品(包括郭沫若),这是为什么?[13]言下之意,似乎仍是新诗不如旧诗。近年来,随着学校教育重心的转移,古典诗歌作品大量印刷,形成新的旧诗的天下。这似乎又转回去了,难道历史真的要回到旧诗?
在我们看来,新诗和旧诗都有好的诗,也都有不好的诗。这固然不错。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对新诗和旧诗完全是等量齐观,没有选择。不错。从审美对象的类型方面看,旧诗有旧诗的美,新诗有新诗的美。它们应该是各得其所,不可替代。但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动态关系方面看,旧诗产生于封闭的农耕时代,是那时人们审美趣味和审美方式的产物。它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主要是一种回溯的美,是一种对过往的、不可回复之物的偶尔的顾盼。正如人们欣赏希腊神话的美,却并不是仅仅是要用希腊时代的作品来满足今天的审美需要一样。今天的人们更需要的,是对当前的生活的审美评价及其审美表达。这里用得着对新诗和旧诗的社会基础、文化背景和语言基础作一点简单的分析。
新诗和旧诗的社会基础其实是很不相同的。胡适的《谈新诗》对此几乎只字未提。在中国古代,写诗的人和读诗的人主要都不是一般老百姓,而是少数所谓读书人。他们大多衣食无虞,不少大诗人有钱有势或在宦海沉浮。从屈原开始,包括魏晋的曹氏父子、陶渊明、谢灵运,唐代的陈子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以至宋以后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辛弃疾、元好问等,都是做大官的居多。晋代的陶渊明据说比较贫穷一些,他的同代人颜延之在《陶徽士诔》中说是“少而贫病,居无仆妾”。这些社会基础决定了古代旧诗的闲适基调,也决定了旧诗只能是少数人写给少数人的作品。用今天的话说,旧诗的社会基础其实是那时的统治阶级而不是劳动人民,是为少数人的而不是为大多数人的。这一点恐怕无法否认。过去在大讲阶级斗争的时代曾把这样的社会基础强调到极端,以至完全否定统治阶级集团中的成员的作品也可能包含人民性,自然是不合理的。但完全忽视这样的社会基础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相比较而言,新诗的社会基础则是社会的大多数人,同时更有一种积极的现实态度。这与社会的进步,教育的普及和民主的扩大是一致的。因此,新诗是民主的,也是大众的。这是新诗的社会基础所决定了的。显然,新诗中的问题一直都存在,但人们始终无法回到旧诗。这是有深刻的理由的。
新诗的文化背景与旧诗也不尽相同。概而言之,旧诗的文化背景是农业文明,而新诗的文化背景则是工业文明。旧诗中的理想是自然和田园、朴素与和谐,然后还有诗人在其中悠闲自得,因此旧诗是宁静和谐的世界。新诗中则是另外一番景象:“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郭沫若《笔立山头展望》)。显然,新诗是世俗的和矛盾的世界。剧烈的社会动荡在诗人心灵中的投影以及在市场带来的大开放大融合中产生的异质文明的激烈冲突,往往是新诗人所无法回避的内容,即使也是写个人的沉思,主体觉醒之后的内在矛盾也在所难免,典型的如戴望舒的《乐园鸟》:“是从乐园里来的呢,/还是到乐园里去的?/华羽的乐园鸟,/在茫茫的青空中/也觉得你的路途寂寞吗?”若干年前,一位现代诗歌的鼓吹者把“古典+民歌”称作是小生产歌吟者汪洋大海中的典型标志。这位评论家曾受到严厉批评。但平心而论,旧诗的文化背景的确是小生产者。也正因为如此,旧诗可以创造空灵的境界。这是世俗的矛盾的新诗所无法或难以达到的境界。更重要的是,历史不能倒转,后来的人和诗歌都无法再回到过去的空灵的悠闲的世界。假如我们仍然把空灵和悠闲当做好诗的标志,我们便会无比怀想逝去的过去和过去的诗。但是为什么要把诗的理想固定在过去呢?
新诗与旧诗的语言基础更是差别不可以以道里计。旧诗的语言基础是文言,新诗的语言基础是白话。这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个事实来之不易,既来之后则影响深远。但我想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以来中国诗人用白话取代文言进行诗歌创作的过程尽管的确可能在世纪之初有过一番如胡适在他的《逼上梁山》中所说的戏剧性的激烈表现,但白话取代文言乃是一个经历了长时期酝酿的自然过程,甚至也可以这样说,没有《马氏文通》也会产生现代汉语,同样,没有胡适也会产生新诗。从文言到白话、从旧诗到新诗主要不是一种共时性的选择,而是历史的进步,包括语言和文学的演进。如果不是这样来看问题,新诗旧诗的争辩就会进入一种简单的历史循环论之中。当然,旧诗的语言基础是文言,新诗的语言基础是白话,这也是一个复杂的命题。胡适当年在论证白话语言应当作为新诗的工具的时候实际上讲了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讲由文言旧诗到白话新诗是历史进化的产物,二是讲中国古代历来就有白话做诗的传统,胡适为此还专门写了半部《白话文学史》。这反映了旧诗语言基础的复杂性。废名在《新诗应该是自由诗》里也提出,像“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些句子里头“没有典故,没有僻字,没有代字,我们怎么能说它不是白话,只是它的文法同散文不一样而已”。同样,新诗中语言也存在相似的复杂性。胡适《尝试集》中的许多所谓新诗其实也都是旧诗的格调和写法。胡适后来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也认为它们是一年一年放大的鞋样,还带着旧时缠脚的血腥气。胡适的打油诗之类更是具有一种白话与文言杂糅的特点。类似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后来。1958年的大跃进民歌既是当代口语的诗歌写作,同时有些作品又具有明显的旧诗的句式特点。文革中聂绀弩、李锐等人在狱中所写的一些作品也具有这种语言上的新旧杂糅的特点。新诗和旧诗的语言基础虽然不同,但白话和文言的杂糅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新的诗体特征,充分反映了新诗在语言上的复杂性。但毕竟白话语言是当今人们使用得最为普遍的语言,是人们在创造语言的艺术作品(包括诗歌)时所无法回避的语言基础。而且,从文言到白话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当代诗人不仅承担了这个时代的情感表达的艺术天职,而且还负有完善和更新语言的文化使命。
因此,无论旧诗多么完美,它都无法完成这样的文化使命。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说现代人更需要现代的诗歌。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说现代新诗是更适应现代人的诗。与此同时,中国的旧诗以及外国的诗歌等仍将占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地位。那既是人们精神生活丰富性的需要,也是诗歌艺术生态自身多样性的需要。
四、有的东西正在离我们远去
在谈到新诗与旧诗的标准问题时,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常常使人们想起过去诗歌时代的辉煌以及诗歌在今天的衰落,似乎这既是今日诗歌的过错,也是新诗一贯的过错走到今天的结果。人们常常责备今天的诗歌写得大众“读不懂”,从而导致了诗歌的边缘化。这当然不是没有道理,但这之中也还存在一个很大的误解。新诗的写作似乎比旧诗更容易,其实也有比旧诗更为困难的一面。当代诗人柏桦曾经写过一首题为《表达》的诗,隐喻了诗歌写作的艰难。而这又必然带来了新诗的边缘化。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边缘化现象。
在我们看来,新诗在今日的边缘化虽是不争的事实,但今日的新诗较之过去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并发生了深刻变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上世纪20年代,穆木天在《谭诗》中批评胡适是新诗的罪人,并提出纯诗的主张。这在当时如同空谷足音。直到30年代戴望舒的出现,才使这种对于新诗主体性的追求有了具体的样本。同样,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诗坛刚刚从文革的绝境中复苏,朦胧诗开始崭露头角,有批评家开始批评“令人气闷的朦胧”并质问“为什么要写人们看不懂的诗”,而经过朦胧诗运动的诗人,甚至包括当时猛烈批评朦胧诗的诗人,实际上都已经熟悉并且广泛采用了朦胧诗的写法,也就是所谓意象和象征的诗歌方法。因此,我倾向于认为,文学和诗歌的发展,其实是一种有始无终的、有方向性的运动。中国的旧体诗在唐代开始定型并且达到高潮,对于魏晋时代旧体诗的刚刚开始兴起,自然是一种进步,但宋诗一改唐诗的风格,以一种更具智性的姿态抒写更为细腻复杂的情感,也未必不是一种进步。同样,旧体诗词在诗体诗式定型之后,往往因所谓“诗家语”成就了或遮蔽了诗情的发现和表达,而新诗在破除了这样的诗体诗式之后,迫使诗人以更为本真的方式呈现那些属于诗的情感。这也应该是一种进步。这就是废名先生所总结的,旧诗往往是诗的语言和散文的内容,新诗则是散文的语言表现诗的内容。假如有一个理想的诗歌的标准的话,从旧诗到新诗,离理想的诗歌标准是更远了还是更近了呢?有人可能认为更远了,那就是退步。我认为在总体上应该是更近了,新诗较之旧诗是一种进步。也有人会举出新诗爱好者以及新诗作品绝对数量的减少现象,这被认为是新诗衰落的一个标志或新诗边缘化的标志。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像这样简单。这里涉及到诗歌与时代的关系,包括相对的关系和绝对的关系。
就诗歌与时代的相对关系而言,任何时代的诗歌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都有一些相同或相似的规律。例如,所谓愤怒出诗人,就被认为是诗歌与时代关系的一个普遍规律。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大量举到大量中外诗人因愤怨而生诗情的例子。[14]现代诗歌中的情况大抵也是如此。至于当代颂诗的大量出现,一方面反映出诗歌情感内涵的扩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某些诗歌作品情感的浮泛,而恰好是这些情感浮泛的诗歌作品因其缺乏深挚的情感体验和凝练的艺术表现而被文学史所淘汰。这又反映出另外一种各个时代普遍遵循的诗歌艺术规律。说到底,都反映了诗歌与时代关系的相似规律。我们过去对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的认识往往停留在这一点上。
但事实上还存在一种诗歌与时代的关系,我把它称为文学与时代的绝对关系,那就是,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文化发展处在不同的历史水平。诗歌与文学的关系还具有某种不可重复和不可比拟的特殊性。我们在思考今天的诗歌为何不像唐代诗歌或五四时期的诗歌时,还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中国古代是一个诗的大国,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了的,包括前面提到的旧诗的社会基础、文化基础和语言基础。而其中有些方面新诗不具有可比性,甚至正好相反。例如,导致中国古代诗歌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诗性文化或者所谓乐感文化、泛审美文化。中国古代的建筑、音乐、绘画、书法,以至戏曲、小说,没有哪一样不浸透了诗的灵韵、诗的精神。中国的文化是感性的、非功利的、空灵的。但与之相关的另一面则是思辨理性、进取精神和效益观念的缺乏。这些或许又正是这个泱泱大国几千年周而复始、步履蹒跚的内在质素。因此,我们说,新诗对于旧诗而言是一种异质的东西,就在于新诗的精神源于新文化。这是一种从西方学习而来的、明确反对中国传统旧文化的新的文化形态。民主与科学固然是其最基本的精神。而在具体的文化表征上,从感知事物的方式、价值判断、审美趣味等方面,新诗人已与旧诗人有了根本的不同。实事求是科学世界观的建立、对于时空转瞬即逝的焦灼感以及对于现实物质利益的追求等等,都使得传统的建立在乐感文化基础上的诗性文化心理荡然无存。而这正是新诗赖以产生的新的文化基础所在。仅就诗歌本身而言,这或许很难被认为是一种进步,但这不是进步又能是什么?不联系到社会进步这个最基本的尺度,我们还可以怎样去评价这个社会的文化包括其中的诗歌呢?
也许,人们在用诗性文化或者乐感文化这样的词语对中国古代文化命名的时候就已经包含了一个潜台词,那就是,中国古代的社会基础、文化基础乃至语言基础都是最适宜诗歌的生存和发展的。以大工业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夺走了这一切,也就夺走了诗歌生长的好时光。理想的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新诗不得不在艰难中发展,甚至在发展中走向自己的反面。我们何以会固执到用唐代的盛况来要求今日的诗歌呢?我们越是深入讨论诗歌的标准问题,我们就会越是深刻认识到新诗既是诗歌的进步、又是诗歌步入新的蜕变的开始,同时我们又会越是深刻体会到黑格尔那个关于艺术消亡的著名命题。不过我相信,人类是不会让诗歌消失的,除非人类自己要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