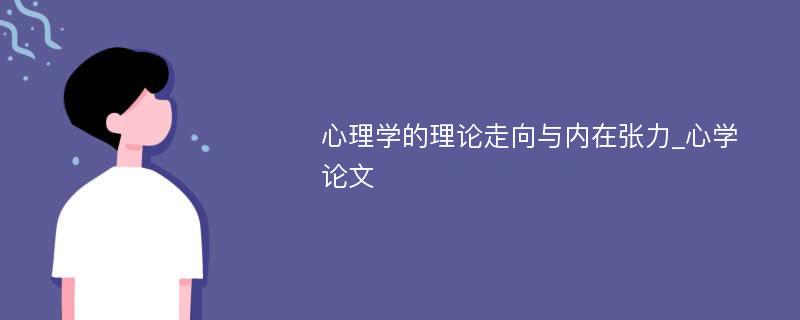
心学的理论走向与内在紧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紧张论文,走向论文,理论论文,心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王阳明早年即以如何成圣为第一等事,晚年的四句教也没有脱离这一主题。本体作为根据仅仅为成圣提供了可能,这种可能的实现以后天的工夫为其条件。相对于正统理学的本质主义立场,王阳明的心学确实展开了不同的哲学视野。然而,心学的思考一开始便呈现出二重品格:心所内含的个体性与理所表征的普遍本质、先天本体与后天的工夫如何定位,始终是一个理论的难题。从心学的历史演进看,以二重性为表现形式的内在紧张又引发了王门后学的分化。
王阳明晚年以四句教为心学宗旨。四句教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参见《传习录下》及《年谱·丁亥年》)在嘉靖六年(1527年)征思、田前夕的天泉证道中[①],王阳明再一次向他的二位高足(王畿与钱德洪)重申了这一宗旨。天泉证道是王阳明一生中最后一次重要的论学,它使四句教具有了晚年定论的性质。从心学的逻辑脉络看,四句教既带有总结的意义,又蕴含了理论上的内在紧张;后者同时潜下了心学分化的契机。
一 无善无恶与可能的存在
四句教的首句涉及心体,所谓“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可以看作是对心体的一种界定。王阳明以心立说,心体的重建构成了心学的逻辑出发点。关于心体,王阳明在居越以前便已作过规定。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阳明作《大学古本序》,其中对心体作了如下界定:“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体也。”(《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页。以下引该书,简称《全集》)在晚年定稿的《大学问》中[②],王阳明又重申了这一点:“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则志有定向。”“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全集》第790、791页)在王阳明那里,心性之辩始终关联着如何成圣的问题,以至善规定心体,同样没有离开这一主题。按王阳明的理解,成圣(走向理想的人格之境)并不是一个外在强加的过程,它的根据内在于主体的先天善端之中;正是心体之中善的秉赋,构成了人走向理想之境的前提:“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③]
心体之中这种善的规定,与理有着逻辑的联系。王阳明以心即理阐释心与理的关系,这一命题的涵义之一,便是理内化于心而构成心的内容。正是内化之理,决定了心体的至善之维。在王阳明的如下断论中,心体与理的这一关系便得到了进一步的阐明:“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传习录中》,《全集》第42页)“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传习录上》,《全集》第36页)就心体以理为内容而言,心与性无疑有彼此重合的一面:二者均表现为一种善的秉赋。要而言之,心与理的联系,赋予心体以至善的规定,后者又为成圣提供了内在的根据。
然而,心体的至善之维尽管为达到理想之境提供了根据,但毕竟又不同于现实的善。作为根据,心体所规定的是一种可能的向度,而并不表现为主体发展的现成形态:从逻辑上说,可以成圣并不意味着必定成圣。就先天的或逻辑的向度而言,心体的至善之维,为主体的成圣提供了可能;就后天或现实的形态而言,主体的发展方向又具有不确定性。将二者结合起来,则似乎亦可以说,主体的现实发展,是一个可善可恶的过程。从可善可恶这一方面加以反观,则作为内在前提的心体,亦很难仅仅以至善加以规定。当王阳明在四句教中以无善无恶界定心体时,无疑已注意到如上关系:无善无恶在逻辑上意味着可善可恶。
从另一方面看,心体固然在以理为内容上与性体有一致之处,但又非性体所能范围。性体的特点在于与理完全重合,所谓性即理,强调的首先是性体与理的这种重合关系。与性体不同,心体并非仅仅限于理这种普遍规定。在融理于内的同时,心体又包含情、意等多方面的内容。理体现的主要是人的普遍本质,情、意等非理性的侧面,则更多地关联着人的具体的存在;普遍之理诚然规定了人发展的方向,但这种发展方向,在化为现实以前只是一种可能,它的实现方式始终受到情、意等非理性因素的制约。进而言之,心体的多重规定,不仅制约着普遍之理所决定的可能,而且本身蕴含了多样的发展方向。当王阳明强调“尔身各各自天真”(《示诸生三首》,《全集》第790页)时,便内含着对个体差异的某种确认:所谓“各各”,即兼含个体发展可能上的区分。也正是在相近的意义上,王阳明一再肯定“人要随才成就”,而所谓才,则不外乎与不同资质相联系的不同可能:“人要随才成就。才是其所能为,如夔之乐,稷之种,是他资性合下便如此。”(《传习录上》,《全集》第21页)相对于普遍之理,才具有个体的特征,其中蕴含了多样的发展可能。
总之,就其包含内化之理言,心体具有至善的性质;就其不限于理而具有多重规定,并相应地内含多重发展可能言,心体又表现出无善无恶的特点。从至善这一维度看,心体为成圣提供了根据;从无善无恶这一维度看,成圣又并非个体发展的唯一定向。不难看到,以无善无恶规定心体,着重的是主体作为可能的存在这一向度。也正是这一规定,使王阳明所重建的心体进一步区别于正统理学的性体[④]。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的提法固然较明确地出现于四句教,但从心体的无善无恶说存在的多重可能,却并非仅见于四句教。如前所述,就心体内含普遍之理言,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可以成圣并不意味着将人都纳入单一固定的模式。正是在此意义上,王阳明反对将实现成圣的可能理解为拘于死格:“圣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于良知同,便各为说何害?且如一园竹,只要同此枝节,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节节,都要高下大小一样,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辈只要去培养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异。”(《传习录下》,《全集》第112页)心体的至善之维固然为成圣提供了根据,但成圣的方式、理想人格的具体形象则并非一一先定,它们总是随个体的差异而表现为多重可能的样态。换言之,心体之中的普遍之理尽管内含了成圣的定向,但这种定向的实现又包含了多重可能的方式。
心体所规定的发展可能不仅仅表现为成圣方式的多样性上,在更广的意义上,它亦体现于一般的人格培养过程。从心体无善无恶这一前提出发,便应承认人格具有多样发展的可能,所谓随才成就,亦意味着人格的培养并不只具有一种预定的模式。正是有见于此,王阳明认为:“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传习录下》,《全集》第104页)通做一般,是仅仅以至善之维律人;才气的不同,则对应于心体的多重规定,正是后者,构成了狂、狷等不同衍化方向的根据。
概而言之,在“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命题下,存在的可能之维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就狭义言,心体的无善无恶意味着在人的后天存在中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就广义言,无善无恶则泛指人格的发展可以如此,亦可以如彼。按照这种理解,人的本质最初并不是以现成的形态存在,人格的模式也并非凝固地预定;质言之,它所强调的,是人的可塑及存在向未来敞开这一面,人的这种可塑性及未来向度,与致知的过程性及工夫的历史展开有其逻辑的一致性;二者都涉及时间之维,而不同于形而上(超然于时间之维)的预设。
以无善无恶突出可能的向度,同时亦意味着扬弃本体的超验性。从逻辑上说,心体无善无恶即表明本体并不具有既成的、绝对的性质。心体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不可着意滞执:“心体上著不得一念留滞,就如眼著不得些沙。些子能得几多?满眼便昏天黑地了。”“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头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开不得了。”(《传习录下》,《全集》第124页》)不滞于心体,亦即不着意于好善恶恶:“然不知心之本体原无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恶恶,便又多了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传习录上》,《全集》第34页)所谓着意于好善恶恶,也就是执着善的本体,并以此支配范围自我。
从本体与自我的关系看,本体总是具有普遍性的一面,这种普遍的品格常常呈现为善的规范,如果将本体的普遍之维加以形而上化,以善的品格为宰制自我的规范,那么道德本体便往往会成为压抑个体的“超我”。正统理学以性体为道德本体,并以此为前提,要求化心为性。在性体的形式下,普遍的道德规范构成了涵摄个体的超验原则,本体被理解为决定个体存在的先天本质,自我的在世成为一个不断接受形而上之规范塑造、支配的过程。由此导致的,往往是先验的超我对自我的压抑。王阳明以无善无恶规定心体,其理论的旨趣之一便在于化解本体与自我之间的紧张。如前文所述,无善无恶,意味着心体并不是既成的、超然于自我的本体,心体作为成圣的根据,也并非以强制的方式塑造自我。王阳明曾对其门人说:“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传习录下》,《全集》第116页)拿一个圣人与人讲学,象征着以超验的规范(圣人模式)去塑造人,这种外在强制的结果则是普遍原则与个体存在之间的紧张:所谓“怕走”,便形象地点出了这一层关系。可以看到,心体的无善无恶,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避免以超我压抑个体的本体论前提。
本体的超验化体现于道德行为,往往赋予行为以人为(artificial)的性质,所谓着意为善去恶,便常常表现为执着本体而有意为之。有意为之趋于极端,总是不免走向外在的矫饰和虚伪化:本体的标榜常流于为人(追求外在的赞誉)。正统理学以超验的规范律人,要求化人心为道心,但如此刻意挺立性体,却往往沦而为伪道学。王阳明从心体无善无恶的前提出发,反对滞留执着于本体,其中亦包含着拒斥虚伪化之意。有意为之,行为往往缺乏自然之美;不执着善恶,则常常从容而中道。在王阳明看来,善恶之执,往往来自习气:“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则无善无恶。”(《传习录上》,《全集》第29页)为善去恶本属合乎理之行为,但执着于此,则善恶之分便成为习气中事,这无疑是本体的异化。王阳明的以上看法,与其注重德行的自然之维[⑤],显然有着理论上的联系。
王阳明以至善与无善无恶对心体作了双重规定,至善是就其为成圣提供了根据而言,无善无恶则强调了个体存在的可能向度;在晚年的四句教中,王阳明将着重之点主要放到了后一方面。在至善这一侧面,心体与性体并无实质的差异,无善无恶则更多地表现了心体不同于性体的品格。从本体与自我的关系看,以无善无恶说心体,意味着扬弃本体的超验性和先天预定:本体的无善无恶决定了个体的存在虽有向善的根据,但其发展并非完全由超验的本体所绝对预定。与这一事实相应,普遍本质对个体的强制亦失去了本体论的根据。王阳明的以上看法,无疑表现了对理学本质主义立场的某种偏离。就本体与工夫的关系而言,无善无恶所突出的可能向度,又使后天的工夫成为自我实现的题中之义:从可能的善到现实的圣,乃是以后天工夫为其中介。
二 可能的展开
心体的无善无恶逻辑地蕴含着可善可恶。当心体随着人的在世过程而显现于外时,以可善可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可能,便取得了有善有恶的现实形态,王阳明以“有善有恶是意之动”表述了以上关系,这一命题同时构成了四句教中的第二教。
从文义结构上看,四句教的前二句首先涉及心与意的关系。按王阳明的理解,心作为本体,具有未发的特点。在天泉证道中,王阳明便对心体作了如下解说:“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传习录下》,《全集》第117页)这里的未发既含有先天性之意,又指心体尚未呈现于现实的存在过程。未发之体体现于个体的具体存在过程,则首先以“意”为其表现形式:“心之所发便是意。”(《传习录上》,《全集》第6页)心体作为本体带有某种类的普遍规定之义,意则是与个体存在相联系的现实观念。个体在世,总是不免应物起念,意即形成于这一过程:“凡应物起念处,皆谓之意。”(《答魏师说》,《全集》第217页)受所处环境等多方面影响,意念往往有善恶之分。恶念便源于习染:“夫恶念者,习气也。”(《与克彰太叔》,《全集》第983页)
关于心与意的关系,王阳明的二位高足(钱德洪与王畿)在理解时发生了分歧。王畿认为心体既然无善无恶,则意亦当无善无恶。钱德洪的看法则是:心体虽无善无恶,但人有习心,故“意念上见有善恶在”(参见《传习录下》)。王畿似乎更偏向于强调先天的心体与后天的意念之间的一致,由此加以逻辑地推绎,则包含着如下趋向:即以先天的形态为现实形态。相形之下,钱德洪在此似乎更注意先天的可能形式与现实的存在形态之间的距离:后天的习染使无善无恶的心体在个体的现实存在中取得了有善有恶的具体形式。在这方面,钱德洪无疑更接近王阳明的思路:他已较自觉地注意到,心体的“无”(无善无恶)与意念的“有”(有善有恶)之分的背后,是先天本体所蕴含的多重可能与个体存在的具体现实之间的差异。
以应物起念界定意,此“意”乃系泛指。作为心体在个体存在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形式,意常常与行为相联系:“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传习录中》,《全集》第41-42页)此所谓意,即是行为的意向和动机。行为是个体在世的具体方式,个体存在的现实性,总是通过行为(从生活世界中的日用常行到生活世界之外的广义实践)获得确证。在这里,由心体而发之意,便具体表现为行为过程中的动机与意向。正如个体在世过程中所参与其间的行为总是具有多样的形式一样,行为的动机、意向也往往非预定而不变;如果以伦理的规范加以衡量,它常常呈现出善恶的差异。
无善无恶的心体发而为有善有恶的意念,构成了个体在世的一种本体论状态。按照心学的理路,就应然而言,个体的存在应当是一种向善存在,而向善在逻辑上则以分别善恶(知善知恶)为前提,如何在现实的日用常行中分别善恶?四句教的第三教便涉及了这一问题:“知善知恶是良知。”王阳明曾对良知与意念作了明确区分:
意与良知当分别明白。凡应物起念处,皆谓之意。意则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与非者,则谓之良知。依得良知,则无有不有矣。(《答魏师说》,《全集》第217页)良知既是内在的准则,又是评判的主体;良知对意念的评判,亦相应地表现为一个自知善恶的过程:“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大学问》,《全集》第971页)
在王阳明的心学系统中,良知往往因侧重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涵义。作为心与理的统一,良知与心体处于同一序列,事实上,这一意义上的良知常常与心之本体彼此相通。在本体这一层面上,良知主要表现出先天性的品格。由无善无恶的本体转换为知善知恶的主体,良知的内涵亦相应地有所变化:相对于无善无恶所表示的先天可能,知善知恶更多地呈现为一种现实的道德意识。个体的存在总是展开为一个过程,先天的本体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具体化为现实的道德意识。尽管王阳明并没有对先天的本体如何转换为现实的道德意识作出具体的说明(这种说明对心学来说是一个理论上的难题),但对有善有恶的意念作出评判的良知,确实表现出现实性的品格。从心、意、知的关系看,无善无恶的心体在个体的在世过程中发而为有善有恶的意;相对于先天的心体,意已体现于个体的后天存在之中,并作为已发而取得了现实的形态,良知虽非形成于后天的存在过程,但作为已发之意的评判主体,其呈现却离不开知善知恶的过程;而意的已发性质,则在逻辑上赋予良知以现实的品格。
知善知恶本身当然并不是终极的目的。知善知恶之后,必须继之以为善去恶的工夫,后者即构成了四句教中第四教的内容:“为善去恶是格物。”心体发而为意,意味着先天的可能开始在个体存在过程中向现实的形态转换,而意之有善有恶,则决定了要实现成圣的可能,不能不经过一个为善去恶的过程。诚然,在天泉证道中,王阳明曾预设了所谓利根之人,以为“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工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传习录下》,《全集》第117页)从逻辑上看,以悟本体为工夫,似乎有消解工夫的意味。不过,王阳明紧接着便强调:“利根之人,世亦难遇,本体工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传习录下》,《全集》第118页)不难看到,从本体悟人的利根之人,在此主要表现为一种逻辑上的可能(从逻辑上说,可能存在着这类人),在现实的存在中,它并不具有实在性:所谓“世亦难遇”、“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便表明了此点。
与悬想本体相对的,是实地的工夫:“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是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传习录下》,《全集》第118页)习心导致了无善无恶向有善有恶的衍化,意之有善有恶又使后天的工夫不可或缺。心体所包含的向善(成圣)的可能,最终惟有在为善去恶的工夫中才能化为现实。无善无恶(可善可恶)的可能趋向,在个体的存在过程中展开为有善有恶之意,经过良知的自我评判(知善知恶),逻辑地要求诉诸于为善去恶的切己工夫。由良知而引发工夫,本质上表现为一个知行统一的过程:从知善知恶到为善去恶,乃是以知与行的互动为其内容。
无善无恶的心体在个体的存在过程中,发而为有善有恶之意,作为已发,意超越了可能而展示为一种现实的意识现象。与意相近,良知作为评判的主体也表现出现实的品格,不过,与意主要呈现为一般的意念不同,良知的现实性品格首先与道德意识相联系:它所挺立的,乃是现实的道德意识。无善无恶蕴含着可能的向度,从无善无恶之心,到有善有恶之意,可能的展开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自发的特点。相形之下,由知善知恶而为善去恶,则以知行互动为形式,展开为一个化善的可能为善的现实(成圣)的自觉过程,四句教的这一内在结构,概要地表现了心学的基本思路。
三 二重趋向与内在紧张
从文义和结构上看,四句教似乎并不复杂,以上的分析亦已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就其内涵而言,四句教却包含着值得注意的多重理论意蕴,它在一个较深的层面体现了王阳明对本体与工夫、存在与本质、个体性与普遍性等关系的思考,其中亦蕴含了心学在理论上的某种紧张。
四句教首句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如前所述,无善无恶在逻辑上意味着可善可恶,它所标立的,是存在的可能向度。从无善无恶心之体这一前提出发,可以逻辑地引出:个体首先是一种可能的存在。不难看出,这里多少蕴含着对先天本质的扬弃:作为可能的存在,个体并非由某种先天的本质所决定。这种看法与正统理学显然有所不同,正统理学以性为体,要求化心为性,其致思的趋向在于挺立人的理性本质。朱熹主张“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答陈同甫》,《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实质上也就是要求以先天的普遍本质来塑造自我。这种看法的特点在于从普遍的性体出发来规定人的存在,其中渗入了明显的本质主义立场。王阳明以无善无恶界定心体,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了对本质主义的偏离。
不过,扬弃超验的本体,并不表明完全放弃对本质的承诺。事实上,在同为晚年之作的《大学问》中,王阳明便同时确认了心体内含的至善之维。四句教以无善无恶为心之体,但在无善无恶所蕴含的多重可能中,亦包含着善的向度。更为重要的是,知善知恶与为善去恶作为向善的过程,本身亦渗入了对理性本质的确认:为善意味着认同体现类的本质的道德理想。这样,一方面,心体的无善无恶蕴含着人是一种可能的存在,而并非仅仅是先天本质的化身;另一方面,知(知善知恶)与行(为善去恶)的互动,又以自觉实现善的可能(成圣)这种方式,表现了对理性本质的承诺。四句教的以上论点,无疑包含着沟通存在与本质的意向。
与存在和本质之辩相联系的,是个体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无善无恶之心体所包含的多重可能,首先体现于个体发展过程之中:它意味着个体具有不同的发展向度,而并非仅仅为类的单一模式所决定。就此而言,以无善无恶规定心体,亦内含着对个体性原则的肯定。从心学的逻辑演进看,王阳明在心即理的命题下重建心体,已表现出对个体性原则的认同;心体不同于性体的重要之点,亦体现于此。四句教通过对个体发展不同可能的肯定,在更深的层面上确认了个体性的原则。
然而,正如以心即理界定心体的同时亦内在地肯定了心体的普遍性向度一样,在可能形式下呈现的个体性,并不排斥普遍之维。事实上,当王阳明将“知善知恶是良知”纳入四句教时,已表现了对普遍性原则的肯定。如前所述,良知作为评判的准则与主体固然具有个体的形式,但这种个体的形式并未消解其普遍的内容。在王阳明那里,良知的普遍性品格往往被赋予“同”或“公”的形式:“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传习录中》,《全集》第79页)天下古今之所同,意味着良知具有超越于特殊时空的一面,正是这种普遍性的品格,决定了以良知为评判的准则与主体,可以达到公是非、同好恶。要而言之,心体的无善无恶为个体的多向度发展提供了本体论的前提,但这种发展,同时又受到具有普遍性品格的良知之制约,个体性的规定与普遍性的认同在此受到了双重关注。
四句教所内含的另一重要问题是本体与工夫之辩。事实上,个体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已涉及本体之域:二者在理论上表现为本体的二重规定。在天泉证道中,钱德洪与王畿的分歧,首先便表现在对本体与工夫关系的理解上。王畿所重,在于由本体而悟入,钱德洪则更强调工夫的作用。从四句教的内在结构看,无善无恶之心体,主要为个体规定可能的发展方向,在这种多重的方向中,亦包括善的向度;良知之知善知恶,在某种意义上则蕴含了对善的可能的认同与选择。从这方面看,心体与良知实际上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本体作为存在根据的作用。
不过,本体尽管规定了个体发展的多重可能,但并不担保某种可能必然成为现实;要实现其中所蕴含的善的可能,便离不开后天的工夫。王阳明虽然设定了由本体悟入的所谓“利根之人”,但如前所述,这种世亦难遇的利根之人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虚悬一格的性质,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在知善知恶之后,“实用为善去恶工夫”。可以看到,本体包含多重可能与通过工夫实现善的可能具有逻辑上的统一性,这种统一实质上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扬弃本体与工夫对立的趋向。
四句教蕴含的如上看法,以集中的形式表现了心学试图统一本体与工夫、存在与本质、个体性与普遍性等理论意向。这种理论意向与王阳明重建心体、以良知转换天理等总体构架相一致,反映了心学与正统理学在哲学路向上的差异。然而,如果对四句教作进一步的分析,便不难看到,尽管王阳明在实现如上的统一上似乎表现出某种理论的自觉,但对他来说,如何真正达到这种统一却依然是一个历史的难题。
如前所述,心体的无善无恶,蕴含了人首先是一种可能的存在,而并非一开始便与本质完全合一,而有善有恶则从现实的形态上表现了存在对本质的某种优先:人的现实的存在并不是由本质所规定的绝对的善。然而,四句教的后半部分所展示的思路,则有所不同。从逻辑上看,良知的知善知恶,是以对善的确认及理性本质的预设为前提的,其中蕴含着向善的维度,当良知的知善知恶进一步引向为善去恶的格物工夫时,这种向善之维便得到了明确的呈现。从知善知恶到为善去恶,人所具有的多重发展可能似乎被化约为一种,即走向至善之境。知善与为善体现的主要是对人的理性本质的追求,在知善与为善的形式下,人的存在多少表现为向理性本质的某种复归。在这里,对存在的多重可能的设定与返归善的本质呈现相互对峙的形式:无善无恶的前提如果贯彻到底,则个体的存在便应向不同的可能敞开,而不能单纯以知善和为善的方式去实现和完成理性的本质;反之,如果存在仅仅是通过知善为善而反归善的本质,那么,以无善无恶预设存在的多重可能便缺乏理论上的合法性。在四句教的如上结构中,内在地蕴含着存在与本质的某种紧张。
这种紧张同样体现于个体性与普遍性之辩。如前文所论及的,无善无恶所规定的多重可能,具体往往表现为个体发展的多样形式,就此而言,以无善无恶说心体,亦意味着从一个方面肯定了个体性的原则。在群己关系上,王阳明要求成己(成就自我),并强调在成己过程中应当:“随才成就”,四句教的以上立场,可以看作是这一思路的逻辑引申。然而,当个体的存在被理解为通过知善知恶与为善去恶而向本质复归时,个体发展的多样形式则亦似乎被架空,作为一个完成本质的过程,个体的自我成就主要便表现为自觉地纳入善的普遍模式。这种致思趋向上接了群己关系论中的无我说,其中明显地蕴含着对普遍性原则的抽象强化。概言之,以无善无恶心之体为前提,可以逻辑地引出个体性原则;个体存在向本质的复归,则意味着以普遍性原则消解个体性原则,二者并存于四句教之中,呈现出某种二重化的理论格局。
在本体与工夫的关系上,我们亦可看到类似的二重趋向。本体与工夫之辩是王阳明心学的重要论题,作为心学宗旨之一的致良知说,便以本体与工夫关系的辨析为其主题。王阳明强调“功夫不离本体,本体原无内外”(《传习录下》),其理论意向亦在统一二者。然而,本体的先天性与工夫的过程性之间,同时又内含着理论的紧张:工夫是一个在时间中展开的过程,本体则表现为超时间的先天预设。这种紧张亦体现于致良知说之中:“良知”作为先天本体,具有超过程的一面(其形成并非通过后天工夫),“致”则突出了工夫的过程性。在四句教中,这种二重性同样得到了折射,如前所述,王畿与钱德洪曾对四句教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依王畿,心体既无善无恶,则意、知、物皆应无善无恶,而由此引申的结论便是知善知恶与为善去恶之工夫皆可消解。与王畿不同,钱德洪更侧重对工夫的维护:“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工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参见《传习录下》,《全集》第117页)在天泉证道中,为了帮助王、钱更完整地理解其思想,王阳明对四句教立言宗旨作了如下解说:
我这里接入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王畿)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传习录下》,《全集》第117页)利根之人与其次之人的划界,在此与本体和工夫之分似乎具有了某种对应关系。利根之人由本体而悟入,其方式近于王畿的悬置工夫;其次之人则从工夫入手,其方式近于钱德洪的以工夫复本体:王阳明认为王、钱之见分别适用于利根之人与其次之人,即表明了此点。尽管王阳明所谓利根之人带有虚悬一格的意味,“世亦难遇”等等已点出此义,但利根与其次的划界,毕竟在逻辑上潜下了本体与工夫分离的契机。
从早年开始,王阳明即以如何成圣为第一等事,晚年的四句教并未离开这一主题。以心体的重建为逻辑起点,王阳明试图将成圣与成己结合起来:成圣是个体追求的普遍目标,而成圣的过程又离不开个体的随才成就。就内容而言,走向内圣之境表现为一个成就本质、完成本质的过程;成己作为实现自我的过程,则始终关联着个体的存在。按其本然形态,内圣之境并非对个体的外在强加,而是以本体为其内在根据,但本体作为根据仅仅为成圣提供了可能,这种可能的实现以后天的工夫为其条件。从如上的总体思路出发,王阳明力图在理论上达到个体性与普遍性、存在与本质、本体与工夫等的统一,相对于正统理学的本质主义立场,王阳明的心学确乎展示了不同的哲学视域。然而,如心即理、致良知这些基本命题所蕴含的那样,心学的思考一开始便呈现出二重品格:心所内含的个体性与存在的维度与理所表征的普遍本质、先天本体(良知)与后天的工夫如何定位,始终是一个理论的难题。在四句教中,王阳明试图提升个体并确认其存在的多重向度,但又难以放弃普遍本质对人的预设;试图走向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无善无恶已多少暗示了此点),但又不愿拒斥对本体先天性的承诺(利根之人的设定即表明了此倾向)。这种理论上的紧张,亦表现了心学在哲学上的转换特征,而从心学的历史演进看,以二重性为表现形式的内在紧张,又进一步引发了王门后学的分化[⑥]。
注释:
①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受命出征广西思恩、田州。是年九月八日起程前夕,王阳明会门人王畿、钱德洪于越城天泉桥,并应二人之请,对四句教的宗旨作了具体阐释,这次论学,在王门后学中称为“天泉证道”。
②钱德洪在《大学问》的卷首曾作了如下说明:“师征思、田将发,先授《大学问》,德洪受而录之。”(《全集》第967页)由此亦可见此篇乃王阳明晚年之作。
③在本体与工夫之辩中,王阳明所着重的,亦主要为心体的至善义。
④朱熹从提升性体的立场出发,强调心有善有恶:“心是动底物事,自然有善恶。”(《朱子语类》卷五)这似乎更多地是就已发和现存形态而言心,较之王阳明以心为未发之体,其意味颇有不同。
⑤参见杨国荣:《良知与德性》,《哲学研究》1996年第8期。
⑥参见杨国荣:《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第3-6章,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