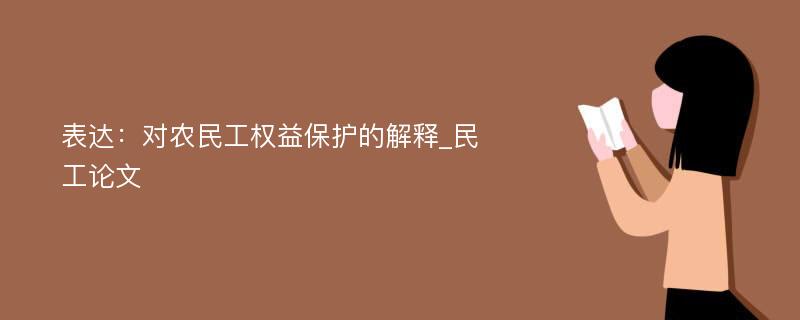
表达:农民工权益保障元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权益保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农民工权益问题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学界也提出了诸多对策和建议。笔者在梳理这些成果时发现,它们主要着重于农民工的就业、工资拖欠等法律与社会问题,多从市民歧视、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农民工素质等角度进行分析,在文本中,研究者大都以“代言者”自居,把农民工作为“他们”,而不是作为“我们”中的一部分的“他们”来进行讨论的,农民工只是其研究中的“他者”,是需要各界来帮助和拯救的“对象”,而非自身权益表达的主体,从而导致研究所得往往脱离实际。
实践证明,农民工权益能否获得保障,最终应取决于他们的自主表达能力,表达是其权益保障的元解,无表达者无权益,而各界目前对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涉及较少。因此,本文拟从此视角对其权益保障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元解:权益表达与保障的关联
权益,即权利和利益的复合。权利这一术语主要有三种使用方式:(1)描述一种制度安排,其中利益得到法律的保护,选择具有法律效力,商品和机遇在有保障的基础上提供给个人。(2)表达一种正当合理的要求,即上述制度安排应该建立并得到维护和尊重。(3)表现这个要求的一种特定的正当理由即一种基本的道德原则,该原则赋予诸如平等、自主或道德等基本的个人价值以重要意义。[1](在现实语境中,权利多表述为“受到法律保护的一种利益”。[2])因此,本文中的权益话语主要从利益路向进行叙事和建构。
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3](利益的争取和实现离不开一定的过程,表达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利益主体日益分化的条件下,不同的群体要想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就必须拥有运作良好、展开充分的表达机制,表达已经成为权益保障的首要前提,即元解。所谓利益表达,是指在多元社会中不断分化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利益群体代表及个人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向社会和政府表述自身的利益要求。[4]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公民利益表达的途径主要有利益群体的结成、利益代表的选举、利益要求的提出、利益受侵害的申诉等等。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的框架基本得以确立,公民的利益意识已经觉醒,表达的愿望日趋强烈,“但理应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种种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5] 结果就是社会的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社会分层相应加剧,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开始拥有不同的利益。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与那些以占有财富、权力和知识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在争取自己合法权益能力上的差距越来越大,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明显增加。如果国家再不主动为农民工提供相应的渠道,那么他们就会自发的寻求表达,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甚至是过激的非理性行为,从而对社会的发展造成巨大破坏。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农民工权益表达机制,已成为各级政府必须解决的课题。
二、困境:农民工权益表达的缺失
农民工群体的弱势地位,使得他们在“努力让整个国家、社会听到自己的声音”时力不从心,其利益诉求得不到应有的表达,从而影响了权益的实现和保障。
首先,农民工权益表达的组织渠道缺乏。现代社会中,个人通过利益聚集而从属于一定的组织,并借助组织的力量来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农民工虽然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合法权益却屡遭侵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远离组织,没有组织,就必定缺乏政治和舆论资源,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权益诉求。“进城务工人员已是工人阶级队伍的新成员”,可是据全国总工会统计,到2003年底,全国非公有制企业组建工会数虽然已达113万个,会员数近3600万人,但组建率和职工入会率才分别为30.07%和32.9%。[6] 另一方面,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农民工中有着共青团员身份的人数越来越多,其中共产党员的人数也不少,只是因为用人单位和就业所在地的党团组织不愿接受他们的关系,而很少能参加组织生活,也就无法借助政治身份权利来维护自身的权益。由于合法组织渠道缺乏,许多农民工转而依靠具有同乡情谊性质的地缘组织,譬如在各地曾经出现的“安徽帮”、“江西帮”等自组织,它们向农民工收取数额不等的保护费,解决纠纷时多采取极端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定时炸弹”。
其次,农民工权益表达的制度渠道缺位。由于现行体制的区隔以及自身素质阻滞等因素的“合力”,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正走向边缘化,成为很少参加乡村政治又不能融入城市生活的“漂泊的政治人”,无法借助法定的政治权利来表达自身权益。我国宪法规定:凡年满18周岁的我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被剥夺政治权利人除外)。该规定保证了农民工当家作主,依法表达其意志、维护其权益的权利。但由于没有城市户口,现实中,农民工很少能与市民一样平等的享有城市政治生活中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无法选举自己的利益代表,从而失去了话语权,成为被动的“无政治群体”(通过对武汉市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的调查发现,农民工参加过城市管理,比如社区居委会选举的只有20.1%的比率。[7])。虽然有江苏籍民工沈厚平,于2006年1月15日上午走进上海市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市民旁听席,成为旁听人代会的首批外来务工人员,但其背后的现实语境却是——千名人大代表中并没有属于400多万外来务工者自己的代言人![8] 到目前为止,在绝大多数的政治叙事场合,农民工依然只是被建构为“他者”的景观,其权益只能通过其他阶层或间接渠道来表达,如传媒的道德同情,学者的正义感,以及其他阶层代表的呼吁。
最后,农民工权益表达的话语渠道缺失。农民工虽是我国产业工人中人数最多的群体,却是社会上声音最弱的群体。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的话语已逐步被媒体的主流话语所湮没,他们正面临着失语的危险。以报纸为例,虽然数量已从1978年的186种增加到了现在的2000余种,但其中以面向城市居民的晚报、都市报为主流,办给农民工看的,为农民工立言的几乎没有[9](虽有官方大报《农民日报》,可是刊登的文章多为写给领导们看的赞歌,与农民工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就业、生活信息以及相关的法律和政策却少而又少)。城市中流行的杂志也多为面向白领、公务员等中产阶层的《都市丽人》、《休闲》等刊物;同时,全国已注册的上千家电视台开办对农(农村、农业、农民、农工)栏目的只有1%,省级电视台中这类栏目的开办率也只有4%,[10] 甚至连中央电视台也在2005年实行“栏目末尾淘汰”机制时,将唯一的“农业新闻”列入淘汰范围。[11] 有些媒体即使对农民工进行报道,也多以负面信息为主,多把农民工这一“以他们自己的存在来填补城市和农村,工人和农民之间的鸿沟”[12] 的独特群体,“妖魔化”为粗鄙无知、没有法律和组织观念、集体看黄色录像、经常聚众打架的形象,而有关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固有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却极少报道。
三、愿景:农民工权益表达的重建
如果农民工的利益表达不能借助于“圆桌政治”来实现,他们就有可能选择“街头政治”和“夜晚政治”(即各种刑事犯罪)等极端的非制度化的参与方式,长期就会造成对政治秩序的疏离,销蚀政治合法性,最终为剧烈的社会冲突孕育能量。近年来,农民工跳楼“自杀”、群体性骚乱、报复性攻击等恶性事件频频发生,说明重建农民工的表达愿景已刻不容缓。所谓愿景,就是“一个具体的目标,是一个心向往之的将来的生动画面,它既是可以被描述的又是具有挑战性的”。[13]
1、工会和党团组织应承担农民工权益表达的载体之责。有人说过:拿起一个瓷瓶远比捧起一堆碎瓷片来得容易。农民工权益易受侵害,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作为个体太分散,没有自己的表达与维权组织。只有组织起来,他们才能增强自身的表达和维权力量,改变个体在与用人单位博弈中的弱势,通过组织与资方谈判,更好的表达和维护自身权益。为此,输出地的工会和党团组织要在外出民工就业集中的地区,建立流动工会和党团组织,及时把握民工的权益动态,积极协助他们维权,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其次,输入地的工会要积极动员辖区民工参加企业或行业工会,党团组织也应主动接纳农民工党团员参加活动,让他们“外者有其归”。最后,改革工会会员的管理模式,针对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特点,工会应采用先进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对农民工会员实施动态管理。将其入会、转会以及其他信息录入计算机,使转会的民工凭身份证从转入地工会的网络系统中调出信息后,就能拿到新发的会员证,从而一次入会,进城务工期间有效。
2、流入地政府应赋予外来民工与其贡献相等的政治权利。农民工的政治权利主要表现为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赋予他们选举权,让他们选举自己的代表,并在人大代表中具有恰当的比例时,农民工才具有了与社会强势群体谈判的资本。同时,针对当前农民工的政治素质与权利现状,流入地政府还应进一步作为。首先,加强对农民工政治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工作,提高他们表达的素质。农民工进城的主要动机是挣钱,政治参与意识淡薄,参与能力较弱。只有对他们进行教育,培育他们的参与意识,提高他们的参与水平,他们才有可能通过合法渠道维权。其次,针对多数农民工顾虑选举成本,很少专程为在居住地参加选举而回原籍开户口证明或选举资格证明的情况,流入地政府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以对外来人口的信息化管理为依托,建立以居民身份证管理为基础的选民登记系统,赋予农民工选举权,为他们最终融入城市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最后,各地应积极修订有关法规,创新选举制度。通过制度创新,保证辖区民工能够有自己的人大代表,实现群体权益的表达,并享有平等的经济与社会权利。目前已有浙江、深圳的部分市镇,小范围为农民工参选当地人大代表开启了民主政治的大门。如在2002年12月28号,12位外来打工者“优者有其荣”被选为浙江省义乌市人大代表,从此结束了中国流动人口无人当选人大代表的历史。但参与的人数还十分有限,在义乌市首次有外来人口参加的三个镇的人大代表选举中,36万外来人口中仅有7699人参加。[14] 实践证明,赋予农民工平等的政治权利,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城市政治,他们就会更加成熟,就能自觉的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并增强了对城市的归属感。
3、媒体应纠正边缘化农民工的倾向,建立常态的报道机制,还原他们生活和生命的原生态。首先,针对农民工权益表达载体稀缺的情况,有关部门可以给予媒体适当的政策支持,鼓励它们为农民工开辟专栏、专版或专业频道,为其提供强大的表达阵地。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新闻媒体应充当“社会公器”,及时传达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为他们摇旗呐喊。其次,要治理“妖魔化”农民工的行为,建立原生态的报道范式。对于那些为追求新闻的刺激性和轰动性而刻意扭曲农民工形象的行为,要给予严厉整治,同时要鼓励记者深入工棚,体察民工的真实生存状态,加大对农民工群体中的先进事迹、先进人物的报道力度,发掘展示他们勤劳、朴实、忠厚、坚韧的品行,积极评价他们对城市做出的巨大贡献。最后,要大力扶持“打工文学”和打工者文化团体的健康成长。“打工文学”是农民工自己创作的表现打工生活的作品(典型莫过于广东的《佛山文艺》和《打工族》),是他们“心灵的呼唤”,也是他们利益诉求的文学表达。打工者文化团体不仅丰富了农民工的生活,而且他们创作的许多作品从不同角度诉说了农民工的现实处境以及遭遇挫折时的真情实感,是他们利益诉求的艺术化叙事。毫无疑问,当媒体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客观报道,为他们争取应有的话语权时,其权益才能获得有效的保障。
4、政府决策部门应创新政策设计,确保维权措施的效能。近年来,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但大多收效甚微,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农民工的积极参与。倚重民工参与,才是维权决策的科学之道。为此,要建立农民工参与决策的民主机制。政府部门在进行涉及农民工利益的决策时,要公开决策程序,举行公开听证会邀请民工代表参加,鼓励他们畅所欲言,为其权益的表达提供制度化渠道。其次,决策部门应积极转变观念。部分决策者认为,农民工只是消极静待政府赏赐的阶层,是需要他们“拯救”的对象,如此思维前提下制定出的政策,其公正性和实践性也就可想而知。因此,决策者应摆正角色,主动深入民工之中,倾听他们的利益诉求,真切把握他们的需求,并邀请他们参与相关问题的讨论,才能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最后,改革政府政绩考核制度。政绩考核是对官员进行管理的基础,考核的标准引导着各级官员的行为方向。目前我国政府的政绩考核是以GDP指标作为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尺度,从而导致许多官员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视了弱势群体的利益,造成政府在其权益保障上的缺位。唯有通过改革,把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状况作为衡量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引导他们以社会公正为公共政策的价值首选,才有可能把更好的服务民工,改善其境遇,维护其权益纳入和谐社会的建设大局。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支持,是项继权教授主持的2004年度基地重大研究项目《农民权益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05JJD880012)的研究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