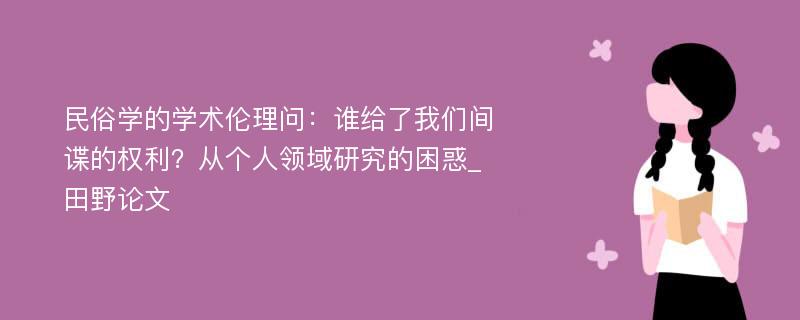
民俗学学术伦理追问:谁给了我们窥探的权利?——从个人田野研究的困惑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俗学论文,田野论文,伦理论文,困惑论文,权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瞽叟杀人,舜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乐而忘天下。
——《孟子·尽心篇》
一、尊重“你”的诉求:当下民俗学的进步
和研究异文化的人类学所面对的是“我与他”的关系不同,研究本土文化的“民俗学从起源时起就是一门直接面对‘你’的学问,就具有比其他人文学科更浓厚的人文关怀和价值诉求”①。“你”是谁?有什么样的特质?早期民俗学不太考虑“你”的位置和诉求,但“你”只是被忽略,并非不存在。当下的民俗学却越来越“关注人之为人的基础层面、人的生活世界以及民如何成为人”②,因此学者越来越重视民众的话语权,“你”的特性、诉求也越来越要求得到尊重。
在这样一个从对物的研究到凸显人的研究的转型过程之中,民俗学对“你”的关注和定位在不同的阶段差异甚大。对物的研究阶段,民俗学的田野作业常常被称作“采风”。采风阶段极少看到“你”的存在,即使存在也是隐藏起来或蜻蜓点水式的。简单来说,把访谈对象的文本搜集上来以后,这时候最多考虑一个著作权的问题,通常要提供姓名、性别、文化水平(这当然也是为了研究的需要),或者是应该感谢人家提供文本。歌谣或故事的搜集整理,面对的问题都是是否尊重人家付出的劳动,这是那个阶段的学术伦理。但是现在不同了,民俗学正在凸显对人的研究,无论是田野还是书写,我们在关注村落里丰富多彩的故事的同时,越来越重视访谈对象作为面对面的“你”而非远方的“他”的生活经历及其对生活的纤细感受。
二、学术与“你”之间能否平衡?
报道田野,从表面上来看,我们尊重了民众的文化权利,让他们站出来说话,呈现他们的话语。但社区内部不是均质化的,我们面对的是每一个个体,他们处在不同的利益格局之中,个体之间、个体和集体之间也存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当我们用民俗志的形式来叙说一个村落故事的时候,其中既包含了我们的调查与分析,也有我们和村落不同个体的对话,这些要呈现给公众社会,这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对我们所研究社区的一种关心。将村落故事呈现给公众社会,可以促进社会关注,本质上应该是一件好事,因为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诉求被更大范围的群体所了解。但是,由于经常要报道民众生活中的实际故事,在尊重民众人生经历和话语的时候,有可能同时会带来一些以所谓隐私权和话语权为核心的伤害的问题,会带来我们的研究是否会影响民众利益格局的问题。譬如,我们所报道的故事,反映了谁的诉求?我们的判断是站在何种立场?民俗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人和人之间的利益纠纷,或者是对话语权的争夺,或者是不同意见的表达,这时候我们怎么处置?每一个个体都是民众,我们要以怎样的立场去平衡这一切?
更多的时候,是访谈对象在谈话的时候愿意畅所欲言,但实际上可能不想让其中一些信息呈现给外界,而我们却没有顾及到这种诉求,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伤害。这种伤害有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访谈对象的伤害。
非遗的申请和保护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利益争夺的关系,我们的研究初衷是怎么能更好地处理好这种文化保护和个体生活改善、社会发展的利益关系。笔者今年指导一个研究生写作毕业论文,题目是有关当地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调查中发现对该项非遗的保护涉及同一村落两个群体的内部矛盾。我们明知这是非常可贵、难得的田野资料,但为了保护个别访谈对象,只得舍弃,重新安排论文的大纲和逻辑。因为其中的群体矛盾,只要是村子里的人看到了论文,必然能知晓矛盾的双方,大体上也能猜测到谁透露了具体矛盾,尤其这篇论文几乎百分之百会进入村委会,接下来更有可能扩大阅读面。从研究生本人的角度而言,她能够获取到这样的资料,说明确实建立了良好的田野关系,得到了访谈对象的深度信任。但是我们并不后悔舍弃,首先这能够避免访谈对象遭到可能的误解;其次至少研究人员本人通过这些资料获得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运作过程的深刻理解。当然也是有损失的,这一内部矛盾没有进入论文,导致读者只能得到对村落内部某一事件的千篇一律的主位理解,而其实在一个文化时空里存在着更多面、更复杂的观点。由此来看,我们最需要保护的可能是民众个体的话语权和民众的文化权利,民俗学确实到了该尊重“你”的时候了。
为什么建议学生舍弃那些精彩的材料?2007年我们在做山东一个村子的调查时,将所有的田野作业资料整理好以后打印成册交给村委会一本,结果不久就有一个访谈对象遭到了报复,因为材料中有涉及村民对某一个村民的评价,而这种评价的来源,只要是这个村落的一分子都心知肚明,以至于所做的匿名工作毫无意义。这件事情一度在我的内心掀起波澜。这个村民所受到的伤害让我以后每每在调查时坚持广泛、深入地搜集,在整理资料、选取进入公开(或小范围)发表的资料时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从不同角度预想材料的公开会对访谈对象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将调查成果以文本的形式反馈到调查地点,这不是中国民俗学所独有的。2004年王杰文在进行博士论文写作时,受到了美国民俗学家斯蒂汶恳请自己的信息提供者对他的专著发表评论的启发,把草成的论文底稿返回到几位信息提供者那里。③王杰文借鉴了这一做法,肯定是有学术意义的,首先是作者承认“信息提供者既是伞头秧歌展演活动的表演者或组织者,也是记录、转译、阐释、批评文本及表演活动的研究者与地方专家”,这一“对话的编辑”精神最终使得“文本不再是一个声音的‘独自’,而是‘众声嘈杂’的‘复调’”④,能够更为立体地呈现文本及表演活动的真相;其次,作者相信,“作为陕北、晋西传统文化的携带者与忠实履行者,我的信息提供者们清楚地意识到了研究自己传统文化的重要性”⑤,这使得当地人对自身所承载的传统民俗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唤起了人们的文化自觉。
这似乎是在提醒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做法,比如当可能会遇到矛盾的时候就回避。但是民俗学怎么可能回避争论、差异、隐私和矛盾呢?和人类学者一样,民俗学者也喜欢观察仪式,尤其是公众仪式,因为“仪式能够表达某一社会所流行的社会价值观”⑥。而且,任何民俗观念都必然有其适当的礼仪表现方式,作为表达的、象征的文化,仪式趋于统一,更能体现规范性的东西,易于观察、记录和理解、阐释。但是人们的实践除了仪式以外,还会面临更多复杂的态势和处境,这些处境往往就是交错着事件的前因后果、时间、空间与关系主体等多重脉络的存在关系网。在这些复杂的网络里,由于个体的情感、观点不容易受到规范的影响,因此许多民俗规则就呈现出明显的伸缩性。个体实际上大多还是依据规范来行事的,但是他们的主观意图也有机会贯穿在具体行动之中。因此仪式所表达的象征规则和个体的实际规则是有差异的,仪式偏于理想、规范、单一,而个体的行为体现了更多的多样性和灵活性。譬如丧葬仪礼,全套程序尽管头绪繁多,但借助充裕人力仍然是可以做全面调查的,丧礼中体现的亲属制度通过一些机制也可以很方便地观察到。但是在丧礼中,人们往往还要协调个体、家庭、家族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均生发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属于特别考验研究人员“田野功夫”的问题。我在做姻亲关系的研究时,也总是会涉及一些家庭、家族之间进行交往的具体事件以及个体之间深入的情感纠葛。正是这些事件才能够看出姻亲关系的实践形态,展示普遍存在于姻亲、宗族之间的张力以及敌意、冲突。然而这些相对要克服很多困难才能搜集到的资料,最能体现个体文化逻辑和实际行动之间的矛盾,显示个体在一定程度上既会遵循普遍的社会交往规则,同时也会借助不同场合将个人的利益诉求表达出来。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研究者在调查中经常会发现村落的某一习俗在结构上类似而在细节上具有个体、家庭、阶层等方面的差异。
在写作《嫁女归属问题的民俗学研究》一文⑦时,我强调要对研究者的身份进行客观评价。文章的论述要从嫁女的生活经验出发,而研究者同样具有嫁女这一身份,这一点当然有助于理解被研究对象。另一方面研究者的生活经验也成为一种研究对象,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者同时也是局内人和被研究对象。在具体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我也常常警醒自己,要注意分离、解读这三种身份。身为局内人,在搜集资料、理解被研究对象、深入挖掘嫁女情感格局方面的优势自不待言,然而也正是因为了解得太多,才自然延伸出有关伦理问题。比如,访谈过程中研究者从局内人角度出发进行的自我抒发,是否客观?是否存在着借此“引诱”访谈对象坦诚内心的意图?甚至存在着将这种坦诚扩大到超出访谈对象实际心理承受能力的危险。
从田野中归来,经常会有这样的纠结,一方面是我们不能离开田野,另一方面却是我们的田野的确干扰到了人们的生活。2000年我做红山峪村婚俗变迁的调查,是我第一次独立田野作业。由于经常惹得访谈对象不胜其烦,结果他们质问我:“你结婚了吗?凭什么来问我?”凭什么来问你?那个时候我考虑的不是对人家会有多少打扰,想的只是不问你又去问谁呢?在这个时段里结婚的就你最合适啊。2008年在山西做调查,遇到一户人家养奶牛,恰逢访谈对象全家都在挤牛奶。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了解到这户人家对于研究目的来说极为合适以后,还是照常进行了访谈。我们并非没有看到女主人脸上的忍耐,所以当时购买了四人份的牛奶。现在我每每想到当时的状况,内心就感到无比的羞愧和悔恨。我们买了一些牛奶,难道就可以让对方无条件地来接受我们的访谈吗?我们凭什么认为自己的田野工作就比访谈对象挤牛奶的工作重要呢?
中国民俗学的田野调查基本的立足点还是农村,在面对访谈对象时,研究者是他们眼里的“报社记者”、“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山大的研究生”、“北京来的博士”,等等。我们有没有以一种心理上的“自上而下”的优越感来面对访谈对象?尤其社会学、人类学在做底层社会的调查时,假如人家拒绝访谈,可以利用研究者的身份一层一层往上找,终会找到人强制接受访谈。若是官方参与,访谈对象更是诚惶诚恐、毕恭毕敬,但是谁给了我们这样的权利?假如我们去访谈报社主编、政府官员,人家不接受,我们能做什么?⑧
在访谈对象的利益和学术研究的目的之间存在的这种矛盾,以前并非没有遇到过,但现在民俗学处于学术转型时期,不管是庙会还是表演,不管是村落还是传承人、社会组织,尤其是社会处于城镇化的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和边缘声音也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个矛盾也就会越来越突出。毫无疑问,学术转型的结果是更加尊重“你”,我们开始关注一个一个“你”的日常生活及其之间的情感纠葛和矛盾世界,这是一种更加积极的学术研究方向。“你”不再是一个列席的对象,会逐渐地从不占显要位置到凸显个性和特质从而完全掌握自己的话语权。我们越关注个体,这一矛盾就越突出,但我们不能为了回避矛盾就逆转学术往前追求的方向。
三、“我”和“你”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2004年,高丙中指出民俗学的专业人员不能对访谈对象单纯利用,“民俗学在今天要关心自己的专业队伍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使学科具有自我反思的能力;要使自己的专业活动避免原有的单纯利用调查地点的民众,而让作为对象的‘民间’有机会在一定的意义上成为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主体,从而奠定本学科适应新的时代的学术伦理基础,我们就有必要尝试把民俗学者的工作过程也纳入观察的范围、对象。”⑨高丙中所强调的,是要让访谈对象“发声”,以表达自己的诉求,所采取的措施是像《摩洛哥田野作业》那样将田野语境详细描述给读者,从而显示主客观之间的张力,展示出文化意义的多重性,这是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
几乎同时,吕微强调民间文学家和民俗学家们不能再仅仅考虑使用某种实证的方法去把握被研究的文本客体,还要考虑把研究过程中交互主体的伦理关系也纳入到反思的范围之内,即从伦理学的角度重新思考研究者主体与被研究者主体之间的知识关系。吕微实际上指出了“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从单纯的奠基于方法论、认识论的学术范式朝向以伦理学的知识论为主导的学术范式的转换”,其途径是强调“有效对话”,“所谓有效对话的意思是说,对话是富有成果的,而富有成果的对话将有助于被研究者主体无论作为承载何种知识类型的主体都能够在后现代知识体系的整体格局中享有与承载其他不同类型知识的主体同样平等或者接近平等的身份、地位。”⑩
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显示出民俗学研究范式已经从对物(文本)的研究转换到了对人(生活)的研究。民俗学,从其建立之初起,就无法离开生活本身。这种生活,无论是自我还是他者,无论是身边还是远方,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下,无论是文本还是实践,都是民俗学最核心的观照对象。就此而言,民俗学甚至应该比其他学科要更进一步,因为它“不只是以生活文化为研究对象,而且是懂得怎样研究生活文化的学问”(11)。不同个体、群体的日常生活,是田野知识的生产基地,民俗学力图观照日常生活,包括观照人的行为方式、价值理念,甚至观照人的内心世界和隐私,我们根据进入田野之前的理论预设获取基本的分析资料,建构或推翻某些模式,这是民俗学的立身之本,但是窥探他人生活必然会对其造成某些影响。探究、记录他人生活的这一权利是谁赋予的?从基本的伦理而言,每一个人的隐私都要得到尊重。尤其是在民俗学转型时期,在我们对“民”的关注和思考越来越多的时期,伦理问题该如何考虑?
特别常见的做法,是按照学术惯例对进行田野调查的村落名字以及访谈对象的姓名进行技术化处理。在访谈对象对研究人员坦率地诉说、表达对某一事件或某一亲戚的态度和观点的同时,他们极少有人明确地知晓我们如何处理他们的言语和行为。作为研究者,在论文中直接呈现这些事件,一般是通过直接引文的形式,在注释里加入访谈信息,采取匿名原则。匿名惯例自然是为了保护访谈对象。但我们处于当下信息传递如此迅速的时代,在老人的心目中,农村男青年依靠网恋得以从远方娶到妻子都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民俗学不是研究遥远的异文化的人类学,访谈对象不仅能轻易接触到民俗志文本,更可凭借同一种语言阅读到。在这样的背景下,匿名惯例真的能完全实现“匿名”的效果吗?
有人说在访谈之前若要录音,应当告知访谈对象以取得允许,但事实上假如访谈对象得知我们要录音,可能信息的效度会大打折扣,甚至很难顺利进行田野作业,更别提获得材料了。所以在调查的过程中,起码就我而言,很少主动告之访谈对象我会录音。我会说,我是来做研究的(比如写老师布置的作业,比如写毕业论文),以后会写成论文公开发表。我个人做得最多的,是给访谈对象带去自认为适当的礼物;为他们拍照,并将邮寄地址记录清楚以便日后邮寄;逢年过节致电问候。若是长期做田野的地方,会建立更为亲密的联系,比如认干亲,这是许多民俗学、人类学的学位论文后记中常常会提到的。有一些学者(主要是海外学者)提议给访谈对象劳务费,平心而论这是应该的,但我们的实际情况(如经费预算不够或者没有发票无法报销)却不允许。在民俗学的学位论文里见到的最多的,是深情致谢,附上一长串名单。鲜少有人帮助改善当地人的生活,遇到当地人有所求的时候,我们往往无能为力。其实,退一步而言,若非在长期而深入的田野作业中充分尊重访谈对象,我们如何了解他们的内心感受和地方社会的真正需要?又怎能谈及提供有意义的帮助、实现访谈双方共赢?
如何寻找到一个合适的距离平衡学术伦理?如何既对访谈个体和研究社区既有所帮助,又能促进田野研究?水族中的水书先生,既是人与神之间的沟通者,也负责指导水族人的人生仪礼。他对村民的生活极为熟悉,但都是跨村惯例,避免了本村人的事情被本村的水书先生完全了解,而最有名的水书先生经常是跨县惯例。(12)这种在世俗和神圣之间寻找合适距离的做法,提示我们学术伦理也要找一个“度”。
当下最权威的《民俗学概论》指出,“民俗学的任务,是帮助我们认识民族历史与文化传统,解释和改造现实社会生活”(13),可见民俗学最基本的东西应是深刻的人文关怀。这应该是我们回报在田野中或羞涩或坦率而在论文中却默然无声的访谈对象的一个根本路径。
人文关怀,体现在要深刻理解和尊重主位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研究者确实也是这么做的。“当下的民俗生活中雅和俗应该怎样被思考?”李松在一次讲座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云南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牡帕密帕》被传统乐器土琵琶演奏时远不如吉他演奏让城里人更顺耳。但是《牡帕密帕》只有代表他们民族历史的老人才能传唱,从这个角度而言,吉他演奏看来就是俗和业余了。在他们那里,雅俗完成了互动,他们的音乐、他们的语言传统,从传统的乐器到吉他,都受到宗教音乐的影响,既有宗教的史诗,也有仪式来传承民族历史,其中也包含着新的创造,像《快乐拉祜》这首歌,流行在整个拉祜族,起初由一位不识谱的年轻母亲教人演唱,村里人都喜欢后扩大到整个拉祜族。(14)民族古歌也好,其他风俗也罢,究竟孰雅孰俗,研究人员如何看待和评价?游客可以欣赏一番就罢了,学者如何给予应有的尊重?
幸好,以个人的田野研究唤起文化自觉、自重已经成为研究者的一个具体目标。冯莉博士近十年来,数次赴纳西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其博士论文《民间文化遗产传承的原生性与新生性——以纳西汝卡人的信仰生活为例》指出民间文化遗产的传承,是多种力量本着不同目的来实践各自不同的表达。传承不仅是学者们构建的本真性神话理想,更是民众精神家园和内价值的需求,也是国家政治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诉求。但究其本质而言,民间文化遗产传承恰恰是原生性与新生性的交织和纠缠。而从传承实践来看,无论是相对自足的传承,还是基于保护政策的传承,传承主体在场实践参与的多少,决定着传承中原生性和新生性二者比例的大小,这是构成民间文化当下多样面貌的重要因素。(15)冯莉的这种来自研究实践的思考,也是一种参与文化发展的途径。民族文化多样性需要呈现,有多样性才有中国特色,才有我们的历史文化大传统。(16)
但理念是一回事,执行起来是另外一回事。尊重文化多样性,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是尊重每一个个体、尊重每一个访谈对象的内心感受。“当民俗学者把研究‘对象’确定为特定的‘你’时,总会在‘你’身上或多或少地发现‘我’,‘你’会隐秘地通向‘我’,至少他们会隐约地觉得自己也生活在民俗之中,自己也是‘民’,民俗学的研究也是学者自我理解的延伸或一部分。”研究者从“你”发现“我”,也经由“我”去理解“你”,如此才能走进一个“对话的中间地带而不是一个对象化的世界”(17)。
“民俗学研究的是生活文化,首先是交往,然后是感觉他是怎样的存在。我感觉他的时候他也在感觉我”(18),从这个角度而言,民俗学者的最大优点应该是善于交往。研究人员和访谈对象之间因此先天地存在着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建构这种亲密关系确实有很大难度,但并非不可以做到。访谈对象既是研究对象,也是材料的提供者,但我们还要将他们视为可亲可爱的可交往的对象,将“他们”变成面对面的可亲可感的“你”和“你们”。
在“我”和“你”的交往中,要坚持一种平等的原则,凭着平等之心去建构双方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做到纯客观地不干扰人家的生活。因为我们是文化实践者,访谈对象也是文化实践者,在田野研究中双方都会进入当地历史的建构过程,区别只是我们带着学术的目标进入社区。关系的一端是研究人员,另一端是作为“朋友”的访谈对象,田野工作必然会给后者带来干预和干扰。而研究人员同样作为“朋友”,应该学会适当干预,学会保证“朋友”的利益不受损害,学会倾听对方主动诉说的感受、考虑对方的位置和立场以及他所处的关系网络,而不是单纯地、一味地只关心自己的问题意识。尤其避免一些对访谈对象来说不敏感的伤害,没有意识到伤害不等于没有伤害。总之,我们要处理好我们和“你(你们)”的关系,“你”和“你”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你(你们)”和公众社会的关系。
访谈塑造的是对话双方的未来,应是平等对话的过程。一旦对话以一种开放且诚恳的方式展开,双方即进入彼此相互关怀的建构过程,其结果不再是以研究假设和问题意识为唯一目标的“审问式”访谈,必然会导向彼此相互关心的“聆听式”访谈。“我”和“你”在对话的时候,要遵循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原则,这或许不是唯一原则,但会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和“你”对话,是民俗学的工作方式,这肯定是有特殊性的,把一个社区的民众生活呈献给公众社会,本身就是有学科特殊性的。我们只有尊重那种日常的人和人的平等关系,才使得民俗学跟其他学科不同,才能实现回归生活的追求。
很多时候,我们说做田野不容易深入,理由可以找到很多,比如我们不在那里生活,缺乏敏感度或过于陌生,比如想象力不那么丰富,比如悟性不够,比如时间紧、任务重,因此常常叫喊着“长期而深入的田野作业”却在有重要仪式的时候才现身参与观察。我们是依靠民俗学对我们的专业训练还是依靠足够长的田野时间来捕捉对田野的敏感?当建基于深刻的人文关怀之上的交往关系正常运转的时候,我们不止能够细致探查到访谈对象纤细的生活感受,同时也能够(至少是一个途径)避免那种单方面剥削、利用而不了解甚至罔顾对方内心感受和愿望的田野作业。在解决伦理问题之后,民俗学者面对的将是一个良性循环的田野关系,因此会促进感悟能力和学术发现。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刘铁梁教授的指导,特此致谢!
注释:
①户晓辉:《从民到公民:中国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结构转换》,《民俗研究》2013年第1期。
②户晓辉:《从民到公民:中国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结构转换》,《民俗研究》2013年第1期。
③王杰文:《仪式、歌舞与文化展演——陕北·晋西的“伞头秧歌”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252页。
④王杰文:《仪式、歌舞与文化展演——陕北·晋西的“伞头秧歌”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254、253页。
⑤王杰文:《仪式、歌舞与文化展演——陕北·晋西的“伞头秧歌”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256页。
⑥参见[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潘蛟等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页。例如社会基本价值观的灌输、执行和强化尤其是通过婚礼、丧礼这些仪式图示来表达的。
⑦刁统菊:《娘家人还是婆家人:嫁女归属问题的民俗学研究》,《民族艺术》2012年第1期。
⑧2011年11月27日,景军教授为山东大学哲社学院师生作了题为“穿越成年礼的中国医学人类学”的学术报告。此处受到清华大学人类学家景军教授的启发。
⑨高丙中:《知识分子、民间与一个寺庙博物馆的诞生:对民俗学的学术实践的新探索》,《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
⑩吕微:《反思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术伦理》,《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5期。
(11)刘铁梁:《感受生活的民俗学》,《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
(12)李松:“雅俗之辨”讲座,山东大学,2011年11月2日。
(13)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9页。
(14)李松:“雅俗之辨”讲座,山东大学,2011年11月2日。
(15)冯莉:《民间文化遗产传承的原生性与新生性——以纳西汝卡人的信仰生活为例》,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16)张海洋:“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讲座,山东大学,2011年11月27日。
(17)户晓辉:《从民到公民:中国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结构转换》,《民俗研究》2013年第1期。
(18)刘铁梁:“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研究的历史视野”讲座,山东大学,2012年1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