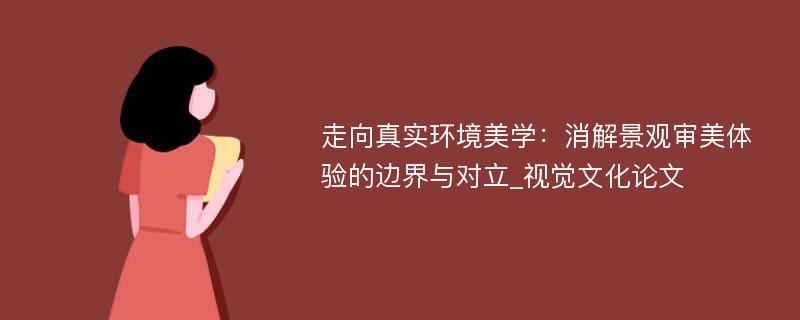
走向真正的环境审美:化解景观审美经验中的边界和对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界论文,对立论文,景观论文,走向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8)04-0011-05
[生态精神与美学、文艺学研究] 特约主持人程相占 教授
在反思如何从环境美学走向公共行动时,我觉得我们需要化解一系列边界。通过化解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各种边界,我们可以促使美学在公共领域发挥重要而有意义的功能。
一、美学与环境
在哲学美学领域,许多思想家已经将注意力从艺术转向对于自然审美鉴赏的分析。尽管过去也有许多哲学家如康德曾经讨论过自然审美问题,但是,19世纪60年代末期标志着英美这种兴趣的苏醒,正如罗纳德·赫伯恩(Ronald Hepburn)的经典论文《当代美学及其对自然美的忽视》所表达的那样[1]。从那时起,环境美学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哲学美学的一个领域。尽管艺术哲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许多哲学家已经认识到理解自然世界审美体验的重要性,也认识到理解各种环境审美体验的重要性——环境混合着非人类与人类因素,如乡村景观。这种认识与另外一种更大的分支学科环境伦理学携手并进。总之,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对于环境的兴趣和新的自然美学,都是由当代全球环境危机促动的。
(一)超越风景模式
当前讨论的重要论题之一是拒斥自然审美鉴赏中的“风景”或“景观”模式。这种立场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如画运动(Picturesque movement)中有其理论渊源。在如画理论遗产支持下,当代审美实践将自然视为眼前展开的大地,而不是将自然体验为“环境”——在环境中,审美主体被自然客体、自然过程和自然现象包围着。
如画审美理论、景观设计和休闲实践无不强调以人类为中心的立场。这种立场借助由艺术确立的标准来估价景观:景观被当作绘画来欣赏,克劳德玻璃(Claude glass)代表了对于自然的精确展示[2]。这种审美欣赏的基础不仅狭窄而且错误,它假定自然只有按照绘画范畴才能得以恰当地欣赏,似乎景观只是帆布上的二维固定图像。这种模式使审美欣赏变得贫乏,因为它只关注景观的如画性质,诸如颜色和设计的外貌。自然环境需要艺术品以外的其他欣赏框架。自然作为环境是三维的动态空间,具有多重感性特征。如画欣赏模式将感官注意仅仅限定在欣赏绘画时使用的视觉上,因而无法捕捉三维环境空间的丰富感性意蕴。在这种模式中,欣赏者成了自然“帆布”的外在观察者,而不是身处环境中的审美参与者。
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然景观只有与艺术比照而构图时才具有审美价值。这种观念引起了如画理论中的一些伦理问题:它没有认识到自然具有独立于人类设计的欣赏价值,因而缺乏对于自然对象、自然过程和自然现象突出特征的尊重。依据如画观念进行设计的设计师对于自然缺乏基本同情,他们将自然视为杳无人迹的荒野,把自然当作私人财产一样从外部观看它[3]。只有在自然被人化之后的安全状态下,人们才会欣赏自然的不规则和混乱;而“人化”自然的方式要么是重新设计它,要么是将之视为艺术家的作品。
(二)新的环境美学
当代哲学家如罗纳德·赫伯恩、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齐藤百合子(Yuriko Saito)、艾伦·卡尔森(Allen Carlson)一直从事于倡导一种新的环境审美模式。这种模式认为,自然环境首要地并非被体验为“景色”,而是被体验为“环境”;身处环境“之内”的审美主体将自然欣赏为动态的、变化的和不断展开的。这种审美立场重视事物的多重感性特征,综合运用生态学知识、想像、激情,将自然理解为讲述着自身故事的新型自然[1],[4],[5],[6],[7]。当然,这种审美模式依然是人类中心的,也就是说,它依然是人类做出的审美判断。一种真正的环境审美将祛除人类主体的中心位置,将促成一种更加深入的、也可能是更加丰富而敏感的环境审美体验。
由于视觉美学和视觉标准在当前景观估价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上述哲学工作意义重大。当视觉特征是我们评估景观的重要准则时,它们仅仅构成了我们审美判断的一方面。而且,在规划语境中,视觉特征向来主宰着相关论争。这一习惯力量使环境的多种审美特征贬值,妨碍了对环境进行更加密切、更加亲近的审美欣赏。
二、主体与客体
上述新的环境审美立场有助于化解惯常的主客二元对立。审美中的主客二元对立植根于纯粹的视觉审美。在这种审美模式中,人与环境隔离而从一定距离之外来欣赏环境,自然被当作能够带来审美愉悦的风景而判断其审美价值。此时,审美主体是作为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出现的,主客二元对立由此得以强化。一些美学家已经批评了审美无利害性(aesthetic disinterestedness)观念,对此,二元对立、人与环境隔离也负有责任,我曾经在其他地方重新解释过无利害欣赏(disinterested appreciation),认为它与消极的或者保持距离的欣赏(distanced appreciation)并不相同[6]。通过强调审美体验中想象力和感知的积极方面,我们重新理解了无利害性如何在审美反应中发挥作用——它使我们集中感知,集中注意力。无利害性使审美主体深深地沉浸在审美环境中,通过积极的、集中的感知,环境潜在的审美维度得以打开,散乱事物的审美特征也由此得以强化。
阿诺德·伯林特提出的“融合美学”(an aesthetics of engagement)既与艺术相关,也与环境相关。它拒斥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身体的二元对立[4],[8]。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美学,梅洛·庞蒂(Merleau- Ponty)现象学中的身体-主体观念,都支持着伯林特的理论。对于发展一种真正的环境审美,伯林特的观点非常重要。尽管需要打破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但是,与伯林特不同,我并不同意在深层的整体意义上,人与自然环境是潜在一体的(或者,用深层生态学的术语,是“一”)。特别是,人类主体并没有消失在审美对象/环境中,审美对象/环境也并没有消失在审美主体中。更确切地说,当审美主体积极地融合于自然或文化环境之中时,他们也还保留着其身份,保留着他们作为欣赏者的人类特性。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自然整体有其自身的生命,按照不同于人类生命和人类价值的方式发挥着功能、展示着生命样式。否则,上述理论假设将导致将自然被人类主体据为己有[9]。也就是说,假设人与自然是一体的将会导致我们不尊重自然整体和生态系统。而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差异和连续性,审美判断潜在的与伦理意识以尊重自然的方式合并在一起。
因此,我保留了主体与客体这样的哲学语言;但是,同时又想强调,我并不认为这些术语将人类与环境深深地分隔开来。与各种环境的审美融合就像感性的、想象性的激情体验一样丰富,它使我们能够更加亲密地体验自然,无论它是森林、湖泊、岩石耸立的山顶、沼泽地、鲜花盛开的草原,或者是城市公园。这种审美体验尽管亲密,但是不必设想自然与人类是合一的。
三、非人类与人类
如果真正的环境审美能够打破主体与被观察的客体——环境之间的障碍,它对于解决历史上不断强化的一种观念将是一种进步:这种观念将非人类与人类分开,并认为人类对于自然具有统治地位。环境美学为生态美学提供了机会。在生态美学中,人类不再是中心,而是整个生态共同体的一部分,就像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0] 所表达的那样,通过审美体验,人类积极地参与到自然整体之中。这种融合将有助于人类更加敏感地感受环境特征并更高地估价它们。如果我们将审美价值作为一种非工具性价值,我们将根据环境自身的审美价值、显著特征来估价环境,而不再根据它们对于人类的工具性价值来估价它们。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思路,审美估价将使我们对自然形成一种富于同情心的伦理态度[11],[12]。对自然的审美估价是一种所有人都会有的体验,它能够增加我们对自然价值的认识,而这一点又有助于指导和支持景观保护。
摆脱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状态,自然与人类之间就会有更多的互动,跨生态共同体的活动(cross-ecological community activity)就会产生,人类实践与自然过程就会有更多的一致。人类可以审美地融合的环境是非常宽广的:从本原自然到城市环境中的自然,还有大量的经过人类改造的环境,如农业景观和大地艺术。我们常常在更加符合人类感知刻度的范围内欣赏环境的积极(和消极的)审美特征,如园林,城市公园,或运河。确实,只有在这些更加日常生活化的景观中,人们才能够与自然“交流”:无论是简单地通过休闲,或通过园艺、种植这样的工作实践。
自然与人的关系使我们打破人与自然的等级。尽管这种等级尚未消除,人类中心主义依然是许多人类文化的标准,但是,环境美学能潜在地加强和鼓励人类与环境之间建立一种更加密切、更加融洽的关系。在这里,审美体验如何发挥作用?通常说来,审美体验是直接的、第一手的感性体验,它使得人们直接地融合到音乐、雕塑、环境等之中。尽管不能说这种直接体验能够加深对于审美对象的理解,增强审美对象的价值,但是,它使我们对于世界的体验更加丰富、更加密切。
四、个体与共同体,私人与公共
到现在为止,我讨论了一种真正的环境审美,通过更富参与性的审美,它有可能提供一种更加密切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从而,用一种更加亲密的、直接的关系取代与自然的隔离和对自然的统治。
审美体验无疑是个体的。在审美活动过程中,个体带着各自的信仰、价值、激情和生命体验。因此,一些哲学家如康德认为,审美判断是特殊的主体间的,而不是客观普遍的(康德使用的概念是“主观普遍性”)[13]。在审美判断的常识中,通常将审美价值理解为个体偏好、个体观点的表达,而不是一种“就是如此”的“判断”(就像“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一观念表达的那样)。这一观点在环境保护政策中同样流行,至少在英国是这样,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情形:它坚持认为对于景观的审美欣赏和估价是主体性的事[6]。
产生这种观点的当代语境是风能发展或风力发电。风力发电能够提供可更新的绿色能源,但是,相关研究明显地表明,人们有些赞同这种发展,有些则反对。反对的原因是审美方面的[14]。这种情形再一次显示,审美被视为主体的、个别的和无法测量的。当人们试图测量对于景观的审美反应时,这些反应通常仅仅被归纳为视觉数据,因为这是最容易被客观化的方式:由于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所以,视觉数据是公共经验而不是私人体验[15]。但是,审美反应中除了视觉感知外还有其他各种感官感知。如果我们将所有这些感知与想象力、激情和知识合并在一起的话,我们就会认识到,视觉数据只能够显示审美反应的很小一部分。
在其他地方,我已经讨论过审美判断是主体间性的[6],在此无暇详论。像其他审美判断一样,特殊的环境审美判断是可以交流的。通过发展出审美体验的语言,通过对于环境的讨论和共享体验,我们有可能就审美判断达成一致。不同意见当然还存在,导致不同意见的原因也是很多的,并不仅仅是因为审美反应(例如,共同体内部早就存在的冲突,个体偏见或无知)。在任何情况下,不同意见自身都表明了源自审美判断的审美背景、审美体验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就像我们在其他判断中发现的那样。多样性可以通过讨论来分享,从这种审美交流中可以得到更深的反思。这种讨论能够促成一种审美交流和谈判,它使审美体验超越个体而为共同体所共享。私人与公共对于景观和环境审美反应的理解是不同的。而通过审美交流,审美体验可以成为打破公、私边界的催化剂。审美体验并非精英人士的专利,所有人——来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经济社区、无论老幼,都具有同样的潜能。就其自身而言,审美体验并非排除性的;相反,它是可以论证的。现代公共机构创造了公共审美空间,情形就更是如此。或许有人会说,现代公共机构也创造了排除性空间,例如,在英国,到国家公园中休闲娱乐的主要是白人中产阶级[16]。然而,必须记得,自然是在更加日常的环境中被体验着的,如城市公园、园林、运河、城市海滩等等。任何人都有许多潜在机会去发现环境的审美特征。
五、地方民众与专家
知识是制订景观保存和保护决策的基础。但是,要看到,审美体验和判断中明显存在的主体性(而不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使地方性知识和专家知识存在着尖锐分歧。地方性体验、特别是对于审美特征的体验被认为是主体的,而专家的体验则被典型地认为是客观的或者科学的。当然,专家的知识诸如景观生态学是重要的。但是,当地居民熟知其栖居的空间,必须重视地方性审美判断和审美知识,并聆听当地居民的声音。当地居民从其特殊的生活和工作景观中获得了特殊的地方性知识,已经有许多论著探讨过应当发展一种场所意识。就环境审美而言,当地居民比一般观光客有着更坚实的基础。如果我们能够显示,根据地方性尺度的审美估价更富于反思性、更是主体间的、而且是更加详尽的,那么,当地居民就成了专家。
这里,我无意抬高地方性,只不过提醒我们认识到:要确保地方性在决策中的严肃而关键的作用,而不是将之视为松散而有问题的。有可能发现一些途径将地方性理解为专家。例如,最近,英国已经采取了许多行动,旨在使当地居民参与到景观发展和改造计划中,尽管我不知道这在何种程度上涉及人们的审美体验问题。例如,曾经使用了股东工作坊的方式,使公众参与到相关的新景观选择中,即“景观特征评估”。但是,难以判定这种尝试是否成功[18]。行政堂区图(Parish maps)和股东工作坊只是其中的例子。行政堂区图是英国采用的让当地居民参与场所的草根办法:
行政堂区图已经被普遍地采用为人们估价其场所的生动方式,并作为产生和解放从事某些事情激情的途径。了解你的场所,积极地参与其维持,承传智慧,对各种观念、人物、发展保持开放头脑,同时又同情自然和文化传统,凡此种种,将打开不同意见的大门。但是,交谈、宽容和对于记忆的承传,都是全民发出的力量。
这种总结、测量、事实搜集、分析和政策制定,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即那些使一个场所对熟知该场所居民的意义。你自己制作地图的伟大事情是,你不能选择加入什么,遗漏什么。你不必为习俗和时尚意识所束缚。你可以决定如何搜集材料并讨论,如何调和自然史与建筑,传说与生计,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工作,去使用何种边界、材料、象征、图画、语句,以及悬挂地图的地方。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步调运动[17]。
我在这里的讨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对待地方性知识:是应该拒斥“反对本地发展主义”(Nimbyism)自身,抑或赞同发展应当是某个人自己后院的事?这意味着,需要区分纯粹自私的个别原因,以及更加富有公德心的景观保护原因。在这种语境中,要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在事实上优待地方性审美知识?而这一点自然引发的问题是:地方性共同体的冲突。我们是否应该拥抱这种可能的冲突?我们能否从中学习?“审美谈判”这种表达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需要留给那些在决策和公共行动方面富有经验的人来思考。
最后,让我回顾一下我的主要观点。我试图表明新的环境审美的潜力,它是参与性的、积极的。环境美学可以使我们跨越一系列边界,诸如主体与客体之间、非人类与人类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私人与公共之间,地方性与专家之间。我在论文中勾勒的美学有助于我们发现一种共同的语言,使我们能够讨论:我们为什么要关心景观,景观为什么应该得到保护,等等。
[收稿日期]2008-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