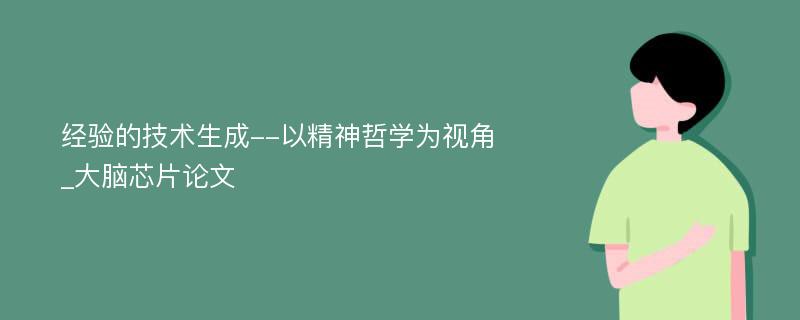
经验的技术性生成——从心灵哲学的视角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哲学论文,心灵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验的通常来源:经历 经验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它是一种心智现象,但又不是心智的全部。经验通常来自人的实在经历,即行为、实践、在现实世界中的活动等等。因此经验通常是指心智中来源于亲身经历的部分。一般的词典也将经验解释为“从多次实践中得到的知识或技能”;日常用法中也是如此,如《红楼梦》第四十二回描写刘姥姥进大观园后,“虽然住了两三天,日子却不多,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没听见的,都经验过了”。在这个意义上,经验记载了一个人的实在活动的过程,如同杜威所说:“‘经验’……不仅包括人们做些什么和遭遇些什么,他们追求些什么,要些什么,相信和坚持什么,而且也包括人们是怎样活动和怎样受到反响的,他们怎样操作和遭遇,他们怎样渴望和享受,以及他们观看、信仰和想象的方式——简言之,能经验的过程。”①总之,杜威把经验看作是一种行为,看作是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行为。在经历的意义上理解什么是经验,将两者视为一回事,这在英文词experience同时兼具“经验”和“经历”的含义中也可以看到。 但在另外的语境中,经验和经历又是有所区别的,这就是当经验指的是心智现象,而经历指的是人的物质性活动的实在过程时,此时经历是经验的基础,经历产生了经验,经验就是我们从经历中所学到或记住的东西,是我们的经历在大脑中留下的心智图像,是人的客观经历的主观积淀。用现象学的术语说,经历是“在场的”的过程,是时间上的“当下”;而经验是对经历的记忆和再现,是不在场的过程,是在缺席的情况下对在场的一种唤醒,是时间上的“过去”。这种分离还可以表现为“有经验而无经历”,例如人通过言传、梦境等等而形成的经验,就是没有经历作为基础的经验。这里,经历也可以视为生活实践,而经验视为认识。于是经历和经验的关系问题也是一个认识论和价值论问题:实践(经历)的价值在于产生认识,形成对以后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经验。 梅洛-庞蒂尤其看到了经验与身体的紧密相关,所以用“身体的经验”(body experience)即“体验”来替代“经验”的使用,从而将胡塞尔的直觉经验与狄尔泰的生命性体验概念融为了一体。他说:“我所知道的……是根据我对世界的看法或体验才被我了解的,如果没有体验,科学符号就无任何意义。”②他的这一学说的提出,还被视为西方从经验哲学到体验哲学、从体验哲学到身体哲学转变的标志。 “体验”作为一种身体的经验,也就是“亲身的”经验,与刚才提到的“经历”具有类似的含义。但由于包含了作为认识成果的“验”(即经验),所以可视为“经历”和经验的集合。这也意味着,如果有另一种不是来自身体的亲身经历所形成的经验,就是一种“非体验性”的经验,如通过书本或言传所了解到的某地的风土人情,作为一种“间接经验”,就是一种非体验性的经验。这也类似于“亲历性经验”(first hand experience)与“非亲历性经验”(second hand experience)的区分,前者是身体在场时直接接触到对象或事件所形成的经验,后者为身体不在场时获得的对该对象或事件的经验。 从直接经验的意义上,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就不会有相关的经验,这就是所谓“实践出真知”的道理。从间接经验的意义上,我们对没有经历的事情即使获得了经验,也是一种“非体验性的经验”。 那么,可不可以不经历什么也能获得相关的体验性的经验?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询的“经验的另一种来源”:通过特定的技术方式去获得非经历经验,甚至使得这种经验有“体验”的性质。 二、探询经验的另一种来源:技术性生成的经验 作为心灵图像的经验,无疑是与人脑处于特定的活动状态相关的,导致这种特定的状态可以有多种方式,不同的方式可以导致的经验类型也可能不同,从而形成了经验的不同来源。如果超出传统的获得间接经验的方式,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我们正在日益扩展经验的来源,那就是利用技术——尤其是当代信息技术——来帮助我们生成经验,其中包括虚拟环境的刺激、记忆物质的移植、神经网络的建构等,它们形成一个从初级到高级方式的演进链条,嵌入到我们的认知过程中,从而正在渐变为经验的另一种重要来源。 初级方式——虚拟经验:主要是通过虚拟实在技术使人产生的“虚拟经验”,可以说这是已经实现的一种通过技术生成的经验。 如果广义地理解“虚拟”,那么从过去的信息技术中人们就已经可以获得虚拟经验,那就是我们是从广义的符号或符号系统(也是一种信息技术并且是“软技术”)中获得的经验,也即通过媒介获得的经验,如从书本或影像中获得的间接经验,这种方式在今天通过3D或4D电影而达到了最新的水平。狭义的虚拟经验则专指现代虚拟经验:人们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在虚拟的互动环境中所获得的经验。这种技术在赛博空间中创造了对现实世界的三维表征,使人如同在与真实世界接触,即“经历”一个实在的过程。这种技术的扩张可以使人“实际地”体验到任何能想象出来的场景,前提是只要人能将这样的场景加以数字化编程。著名的美国科幻片《黑客帝国》就形象地展示了这一前景:Matrix是超级智能机器,根据人的特征和生活环境设计的一套高级虚拟现实系统,其中的所有自然现象(如太阳升落、鸟语花香、万有引力等等)都是由不同的程序所实现,在其中与之互动无疑会产生出丰富的经验。当虚拟环境愈加生动逼真,人的体验就会越“真实”,以至于现实和幻想之间的界限将愈发模糊,“由于你全身心地沉浸在虚拟的世界之中,所以虚拟实在便在本质上成为一种新形式的人类经验——这种经验重要性之于未来,正如同电影、戏剧和文学作品之于过去一样”③。而且,这种具有互动性的新经验很大程度上具有“体验”的性质,它给人留下的记忆或经验,与文字符号或影视形象给人留下的记忆和经验具有了本质上的不同,其长处是可以超出现实世界的限制而更加丰富人的经验世界。但又不得不承认,这种经验毕竟不同于现实经历中生成的经验,例如在虚拟实在环境中学会驾驶汽车的经验与在现实中学会的驾驶经验毕竟有所不同。 中级方式——记忆移植:主要是通过记忆物质的移植,使相应的经验信息随之转移到被移植者的脑中,从而获得或具有(生成)了另一个经验主体的经验。 关于记忆物质的移植,目前已有一些动物实验的报道,如美国休斯敦贝勒医学院的乔治·安伽博士将通过电击而使一只老鼠形成的“恐惧黑暗”的记忆,并发现了相关的记忆物质将其命名为“黑暗恐惧素”,然后将其注射到另外的老鼠身上,结果未受训练的老鼠也有了避暗行为。当另外的研究小组将“黑暗恐惧素”注射到金鱼脑中后,金鱼也产生了避暗能力。这种物质经过化学家们分析,是由15个氨基酸组成的氨基酸序列。④不少人由此相信,将一个人大脑组织中的记忆移植到另一个人大脑里一定能获得成功,甚至整个脑的移植都是可能的。⑤我们也可以从目前在人身上进行的器官移植推知,以后这种移植必定可以提高到脑器官的水平,其中脑组织的部分移植(脑拼接)或克隆,就可以将储存于其中的经验记忆加以移植。此外还有将载有经验信息的芯片植入人脑的技术,它或许比起脑组织移植能更早实现,这无疑也是经验移植的一种重要手段。当不同的经验的物质载体之间建立了可行的通道后,原来的经验和植入的经验之间也可能建立起通道,技术性植入的经验就可以在新的载体中有效地发挥作用。 高级方式——神经操作:主要指脑内神经相关的技术性建构,或称直接的“神经操作”,以此生成所需要的经验,这可谓是更彻底的“人工经验”。 心智活动是依赖人脑进行的,经验作为一种心智现象,无疑与脑神经(和其他神经)的特定构型与活动相关。普特南的“钵中之脑”本是讨论外部世界的实在性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解读为用电刺激神经系统可使人产生经验图景:“设想一个人(你可以设想这正是阁下本人)被一位邪恶的科学家作了一次手术。此人的大脑(阁下的大脑)被从身体上截下并放入一个营养钵,以使之存活。神经末梢同一台超科学的计算机相连接,这台计算机使这个大脑的主人具有一切如常的幻觉。人群,物体,天空,等等,似乎都存在着,但实际上此人(即阁下)所经验到的一切都是从那架计算机传输到神经末梢的电子脉冲的结果。这台计算机十分聪明,此人若要抬起手来,计算机发出的反馈就会使他‘看到’并‘感到’手正被抬起。不仅如此,那位邪恶的科学家还可以通过变换程序使得受害者‘经验到’(即幻觉到)这个邪恶科学家所希望的任何情境或环境。”⑥在这里,经验来源于神经系统所受到的有序的电刺激,即神经末梢的技术性建构。今天的脑电科学已经揭示,用科学的方式激活相应的脑皮层区,可以使人产生出相应的感觉,呈现出某种经验获得的状态。 比上述“神经操作”更高级的方式,还有经验信息(或记忆)的直接植入,类似信息场的无创伤渗透。一些科幻片(如《少数派报告》、《盗梦侦探》、《记忆碎片》、《盗梦空间》等)已有描述,如《盗梦空间》中的“盗梦”就是造梦,设计梦境就是设计经验,从而“造梦”就是制造经验、制造观念;对人实施这一技术就是改变其看法和经验。从人造梦到人造经验,可以给人一种如同鲍德利亚所说的“比真实还真实”的经历。在这些科幻片中,涉及了意念、梦境、看法、观点、意愿、信仰、雄心等等的读出与植入,都是被经验包括或包括经验在内的心智现象,它们成为人们期望能够人工操作、合成的对象,其蕴含的想法就是:人的经验世界在未来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甚至是无创的方式来改变和重塑。 如果说经验的直接植入距离现实性还相当遥远,那么通过“神经操作”的技术方式来生成经验则有着多方面的现实根据。心灵和认知本质上是涉身的,是神经系统整体活动的显现(appearance)。经验作为一种心灵现象,无疑也是特定的神经连接状态相关的,或者说“存在着能够完成认知任务的神经机制”⑦;甚至有人认为,“科学的信念就是,我们的精神(大脑的行为)可以通过神经细胞(和其他细胞)及其相关分子的行为加以解释”⑧。目前,认知神经科学就是寻着这一进路在探讨作为心智的经验的奥秘,它试图通过研究来定位各种意识经验产生时所对应的神经活动区域,这就是找到特定意识的神经相关(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ncc),然后整合所有ncc而形成大写的NCC:一幅关于意识的神经相关整体图画。人工神经网络理论所进行的也是类似的工作:对神经元的工作机制加以解释和简单模拟,其未来发展就可以利用这些成果反过来对人脑的神经系统进行人工操作,以“编织”所需要的结构并生成相应的心智内容,也包括我们所需要的特定的经验。因此,弄清楚经验的神经相关并技术性地建构这种相关,将一个人经验到什么时的神经相关在另一个人那里再造出来,就成为技术性生成经验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且,与认知技术同为当今“会聚技术”的纳米技术,在未来也可以为我们在微观层次上甚至在原子或亚原子层次上为我们建造经验的神经相关结构提供实际操作上的技术可能性。 “人类脑计划”也为揭示经验的生理机制了提供了基础,其中的“大脑蓝图”就是要弄清楚人类大脑的神经元连接组(connectome),即人的神经组织中的神经连接的全部信息。正如特定的基因组合构成特定的遗传信息,特定的神经元及其电、化学组合构成特定的记忆信息——包括经验,或者说一个人的经验记忆等均编写在他的神经连接组中。正如基因工程可以改变遗传信息,“神经工程”也可以改变脑中的经验信息,这个过程就是技术性生成经验的过程。拿欧盟的人类大脑计划来说,就是要了解数十亿个互相联系的神经元是如何运转的,这一计划将把全世界神经学家提供的大量数据整合成为单一的模拟装置,使用超级计算机来对人脑进行模拟从而形成虚拟“大脑”,使科学家能在其中“穿梭飞行”,观察到神经元个体的精细结构,或进行缩小操作以观察信息在不同大脑区域间流动的情形,从而有可能对大脑的任何层面进行测量和操纵。 本世纪初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也为我们认识经验的技术性生成提供了新的启示。起初科学家在短尾猴的前额叶发现特定神经细胞的特殊现象:猴子自己吃水果时,和自己不亲自吃水果,但是看见其他猴子甚至实验者吃水果时,同样的神经元被激活,产生放电活动。科学家将这些像镜子一样可以映射其他人动作的神经元系统定名为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后来,神经科学家发现人脑中具有比猴子复杂得多的多种镜像神经元系统,分别完成理解别人的动作,甚至意向。在人观察他人做某些动作,或从面部、动作表现出某种情感和意向时,人脑中会激活不同区域的镜像神经元,产生出与动作相关的认知表征。镜像神经元的存在表明人可以在自己内心再造出别人的经验、体会别人的情感和意图,也说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所具有的内在认知基础。可以认为,镜像神经元便是充当人脑和心智系统耦联的重要神经元件;对于理解他人的经验来说,人类的镜像神经系统则给个体编码他人的行为意愿、情绪体验提供了便利,让个体感觉这些意愿和体验似乎是自己的,消除了自己和他人之间存在的那种心理隔离,让社会沟通变成现实。⑨由此也可推知:通过镜像神经元的建构有可能造就与其相对应的经验;或者说,承载特定经验的镜像神经元不仅可以被发现,而且在未来可以被不断地“发明”出来,以此作为建构“崭新经验”的技术通道。 对脑部疾病的治疗也间接地展示了技术性生成经验的前景。例如,一些生物技术公司和大药厂已经着手开展以多重识别机制为靶点的药物开发项目,目前已有所谓“认知增强剂”等,用于治疗老年痴呆、注意力缺陷障碍、中风、帕金森氏症和精神分裂等脑部疾病。随着这些药品疗效的提高,那些饱受这类疾病折磨的患者可以恢复正常的认知功能。由此进一步去推展,从“脑治疗”走向“脑增强”在以后不是没有可能的,而人造经验就是“脑增强”的方式之一。如果目前药物的认知治疗发展到认知增强后,再过渡到非药物的技术手段(如神经操作或对神经的“内科手术”来达到治疗并走向增强),那么经验增强就获得了更多的技术途径。当然,在这里也提出了“经验治疗”与“经验增强”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超出为了获得正常经验能力的“经验治疗”之外而成为“经验增强”,就是违背了医学技术使用的伦理原则(只治疗不增强)。但由于正常与异常界限的模糊性,有可能导致“经验治疗”与“经验增强”之间界限的模糊性或不断变动性,这也为经验的技术性生成提供了道德空间。 此外,脑成像的研究有助于确定脑系统在推断他人意图过程中的功能定位,而“读心术”实验也表明了心智内容与物理表现(电信号及仪器上的光电符号)之间可以找到对应的关系。可以说,随着认知神经科学及相关学科的进步,随着对大脑功能即意识生成机制的揭示,不断搞清楚记忆等心智现象的神经元基础,把握经验形成或经验过程的神经活动机制与神经生物学细节,再“反向地”利用这种机制生成我们所需要的经验,在原则上是可行的。 三、技术性生成经验的性质和意义 如上所述,对于经验的技术生成方式来说,心灵哲学中的某些理论提供了解释其可能性的哲学根据,而认知科学和技术则正在探索从而将要提供实现它的方式。这样,在坚持经验的后天形成的唯物主义视野中,经验便增加了一种新的生成进路:自然进路之外的人工进路,使得后天经验除了自然形成外,还可以通过技术而生成。这样,经验的来源从此就可区分为“常规来源”(亲历、学习、反映、行为、实践……)与“非常规来源”(记忆物质的植入或脑中相关神经的人工建构),由此还形成了对经验的新分类:先验论的经验、反映论的经验、技术论或制造论的经验。技术为经验所开辟的这一新来源表明,技术在认识论中的作用更加突显,成为影响认识(经验)的重要因素。它也促进我们思考关于经验的更多问题:当一部分经验是由技术设备制造而成即“人工合成”的时候,这种新型的经验有什么不同于传统经验的特性?它是有客观内容还是无客观内容的经验?它对原有自然经验会造成什么影响?从功能的角度看神经操作与信息输入或反映对于经验的生成是否具有同等功效? 从经验的哲学分类上,技术性生成经验无疑是非先验性经验,但又不是后天经验中的直接经验。如果说在传统意义上,基于亲身经历的经验就是直接经验,而没有亲身经历的经验是间接经验,那么作为技术性生成的“非体验经验”,就是介于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之间的一种“新型经验”,它比传统的间接经验更靠近直接经验,是非实在性地在场而获得的感知经验,一种具有鲜活性和直接性的间接经验。从技术性生成经验不是某人的亲历来说它是间接经验,但从其最初的来源来说则是直接经验;或者说,它是直接经验变换载体后的存在,是经验被“非直接化”后的“再直接化”,是变换了经验主体的直接经验。它不能改变我们的经历,但能改变我们的经验甚至体验;较之传统的“间接经验”,这种技术性生成的经验更加接近“经历”,乃至在“体验”中与直接经验合为一体。在这个意义上它是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的衍生,是两者的交集。 这种新型的经验极大地扩展了经验的功能,也使“反映论”获得了新的含义。例如,如果技术性生成经验是通过移植方式实现的,那么反映就是借助“他脑”来完成的,此时“他脑”成为经验主体的“延长”(“外脑”),而经验的“脑际传递”就使得经验主体的反映活动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开阔性和兼容性;如果技术性生成经验是通过神经网络的人工建构实现的,那么反映中的“工具”或“中介”成分就更多,即反映中的“脑机”相互作用就更强。无论是“脑际”或“脑机”式的经验增强,都可以视为经验主体之反映能力的增强,最后归结为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这也表明,如果以前人的经验仅仅是心智状态与实践状态的统一,那么现在它也可以是心智状态与技术状态的统一,也进一步表明技术状态与实践状态可以走向实质性的交融。 由于技术性生成经验的技术目标之一就是要使人工(技术)过程导致类似自然过程的结果,使得人虽说没有亲身经历某一过程,但也如同“身临其境”地经历了该过程,因此它也是非亲身经历的体验化,可以极大地扩张人的体验世界,克服因种种条件限制而无法或难以通过直接经历而形成的经验,使人的经验更加丰富,或使更多的人成为经验丰富的人。例如人类的足迹虽已伸向太空,但亲身遨游太空的人为数极少,如果将后者的经验记忆移植或建构到普通大众的头脑之中,就可使“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延伸到我们的直接经验之外,甚至延伸到可能的经验世界之外:我们也知觉到我们永远不能亲身到达的太空领域”⑩,这样既节约了昂贵的太空旅行成本(其普遍的意义就是为人类节约产生昂贵经验的成本),也避免了“太空交通”的拥堵和污染。从“长远后果”上看,直接体验和技术生成的经验最后留下的都无非是一种“记忆自我”,而记忆的丰富此时反向地造就了人“阅历”丰富和人生的丰富,形成了“实在的”人的发展效果。 这也意味着,技术性生成经验可以改变传统的学习和认知过程。我们知道,知识经验尤其是一些技能经验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当代著名人工智能哲学家德雷福斯将这个过程概括为新手、进步的初学者、有能力的执行者、熟练的执行者和专家五个阶段。(11)如果将负载于“专家”的经验之上的神经构型把握清楚并在“新手”的神经系统复制出来,那么技能经验就可以不再只是通过漫长而艰苦的模仿过程而习得,而是可在短时间内就成为“专家”。这样的知识传播方式对于意会知识的承续或许更为重要。目前对意会知识的形成机制还没有在“显科学”的层次上加以清楚的揭示,但它肯定具有其生成的神经结构,通过技术性再造这种神经结构,就可以使其更为容易和迅速地传递、交流和世代承续,从而解决技术认识论所面对的这一传统难题。这或许也展示了学习方式的一种变革前景。 技术性生成的经验还是一种主体间性增强的经验。在通常情况下,“他人的‘内在经验’对我们来说是无可化约地缺席着;无论你对我多么了解,我的实际的内在情感和经验之流永远不可能以某种方式与你的内在情感和经验之流真正地融合,以至于——比方说——会让我的记忆或幻想突然开始浮现在你的意识中”(12)。但是,假如有经验的技术性生成,就可以使他人的经验在我的经验世界中由缺席变为在场,从而消弭两者之间的鸿沟,形成与他人的经验沟通,使主体间经验的不可通约性变为可通约性。 当然,不同来源的经验之间仍是有区别的,如果直接经验是鲜活的感知留下的记忆,那么技术性生成的经验具有这种鲜活性吗?回答是:可能没有,也可能更加鲜活。例如,当一个感受的生动性能力较差的人被植入某个这方面能力较强的人的经验时,就会如此。当然,当不同来源的经验相“混合”时,出现“混乱”是有可能的,这就是梅洛-庞蒂所说的,“外来体验带来的东西模糊了自己的体验的结构……处在既压抑他人的体验也压抑自己的体验的一种普遍的思维中”(13)。也就是说,即使在常规经验的生成方式中,经验上的混乱也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在混乱中去厘清和整理经验,才成为推进认知的一个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技术性生成经验使得人的认知发展获得了新的动力。 技术性生成经验也是一种超感官形成的经验。传统意义上的经验是人用感官直接获得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感官是经验来源的通道,经验要有外物作用于人的感官才能产生,从而在传统意义上任何人类经验都有赖于感觉,这也是经验产生的自然方式,此即杜威所说的,“经验既是关于自然的,也是发生在自然以内的”(14)。但技术性生成的经验中的中级和高级方式可以在经验来源的通道上超越感官,使人并没有用自己的感官去亲身感知某一过程就有了关于它的经验。这种经验生成的超感官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克服感官的局限性,如感官通道的“狭窄”或缺失,尤其是可以使感官缺陷者也能产生相应的经验,例如使盲人产生视觉经验、聋人产生听觉经验,甚至使人产生某些动物从其特有的感官“看”世界的感觉经验,由此解决心灵哲学家内格尔提出的问题:我如何知道成为一只蝙蝠会是什么样子?这样,技术性生成经验就可以极大地克服自然的经验过程所具有的某些局限性,扩展人(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类)的经验世界,以至于从“他心”扩展至“它心”的经验世界,这或许也是经验世界的更大“共享”。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技术性生成的经验虽然是超感官的,即不是外物作用于感官后产生的反映,但又绝不是主观唯心论所主张的主观内部自生的,而是“后天的”和“外来的”,即它虽然具有非感官性但又不是主观自生的,在这一点上,即本体论前提上,它是和唯物论相一致的,但它又使得经验的来源在“后天的”和“外来的”形式上得到了新的丰富,也使得唯物主义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技术性生成经验可以补全经验的完整性。经验成为记忆后,其“客观性”和“可靠性”并不牢靠,记忆会因种种原因而被扭曲和变形,导致经验的“不真实”。例如,人在幻觉时也会形成种种经验,像做梦、睡眠麻痹时的“被外星人绑架”经验……如果再陷入某种精神上的错乱,则会将幻觉中形成的记忆当作真实经历的经验。就是说,记忆被虚幻信息干扰时不断发生的重构,使得经验常常成为真实经历与虚幻构造的混合体,使得经验难以“准确再现”经历本身。换句话说,经验无非是经历留在我们脑际中的心智图像,到一定阶段后,这种图像可能会“不问来历”,使得另一种来源造就的经验同样“栩栩如生”地将我们带到一种不受实在条件限制乃至更令我们有实在感的“经历”之中去。这也是塞尔所主张的:“在经验本身之中,在实际经验的质的特性之中,不存在什么东西能够把幻觉的情况与真实情况区分开来。”(15)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经历”和“非经历”、“真实”和“虚幻”之间有时会具有主观不可分辨性,从而为技术性生成经验提供了认知功能上的可能性,也使经验主体在一定意义上不再问“我经验到什么”之类的问题(因为搞不清楚第一手的与第二手的经验之间的区别),而只问“我有什么经验”;其进一步发展就意味着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之间、自然生成的经验和技术性生成的经验之间的界限在一定意义上的消失。 由于即使是常规来源的经验,也不是对经历的“准确再现”,于是,用非常规来源的经验去填补常规的经验,使经验具有完整性,本身就是常规的经验形成中的一部分。技术性生成经验的这种“补全”作用,也就相应地导向了人的经验世界的多样性和广阔性,某种意义上也导向经验构造的更加“人性化”。例如,当经验的人工操作变得可根据人的需求进行时,当“记住”和“遗忘”具有高度的技术可操作性时,我们回忆被遗忘的经验,巩固珍贵的经历经验,摆脱痛苦的记忆和经验从而医治精神的创伤等等就成为易事,随之也就可以提高我们的精神生活质量。这一功能的自然延伸,也就成为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有利条件,其中包括治疗经验匮乏,尤其是治疗因认知障碍(认知能力异常者)而导致的“经验障碍”,使经验能力低下者恢复正常,这也正是认知神经心理学——尤其是基于脑损伤病人的认知神经科学(Patient-based Cognitive Neurosychology)——所致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注释: ①[美]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0页。 ②[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页。 ③[美]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金吾伦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 ④[英]罗赛尔:《大脑的功能与潜力》,滕秋立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页。 ⑤贾爱斯主编:《神经心理学》,杜峰译,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⑥[美]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⑦[英]哈瑞:《认知科学哲学导论》,魏屹东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⑧[英]克里克:《惊人的假说》,汪云九等译,湖南科技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⑨叶浩生:《镜像神经元:认知具身性的神经生物学证据》,载《心理学探新》2012年第1期。 ⑩[美]索科拉夫斯基:《现象学导论》,高秉江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11)H.Dreyfus,"How Far is Distance Leaning From Education?",in The Philosophy of Expertise,Edited by Selinger,E.& Crease 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6,pp.196-212. (12)[美]索科拉夫斯基:《现象学导论》,第34页。 (13)[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132页。 (14)[美]杜威:《经验与自然》,第40页。 (15)[美]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实在世界中的哲学》,李步楼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