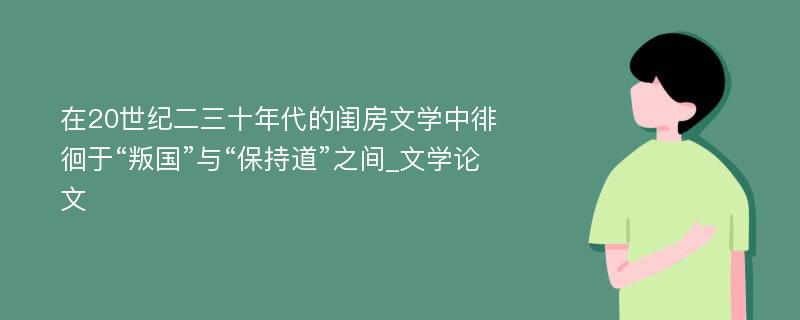
踯躅于“叛道”与“守道”之间——论论二三十年代闺阁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闺阁论文,二三论文,文学论文,叛道论文,守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I206.6;B849;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1999)01-0024-31
一
五四时代,文坛涌现一批令人刮目相看的女作家。她们大多是出身于簪缨世族、书香门第的名媛闺秀,如陈衡哲、冰心、凌叔华、林徽因、绿漪(苏雪林)、袁昌英、沉樱等。她们早年一方面深受封建传统文化的熏陶,一方面又沐浴着迷漫西方文明的“欧风美雨”,从而形成思想和创作中“叛道”与“守道”的冲突。她们既是五四时期最早觉悟的知识女性,用笔对婚姻家庭问题作敏锐的观察、及时的反映,充分展示了各自“得风气之先”的横溢才华,同时,她们对那个曾给她们同时代一般女性不可企及的优越生活环境有着藕断丝连之情,她们的文明之脚,一直踯躅于闺阁朱门内外而无法迈远。憧憬新生活与依依惜别过去的感情交织共存,使得她们那些描绘闺阁生活的作品,既有时代浪潮震动的涟漪,又有深深庭院飘荡秋千的轻吟和闲愁,与同时代的丁玲、冯沅君、庐隐等人的作品形式截然相反。
二三十年代文坛已有人将当时女作家分成三派:一曰“闺秀派作家”,以冰心、绿漪为代表,在礼教范围内写爱,婚前爱的对象是母亲、自然、同性,婚后爱的对象便转为丈夫,这些爱皆为社会和礼教所允许;二曰“新闺秀派作家”,以凌叔华为代表,虽不像前者那样受礼教牵制来写爱,但因有礼教的顾忌而不敢过于浪漫,人物行动上貌似新女性,精神上还是闺秀小姐习气;三曰“新女性派作家”,以丁玲、冯沅君为代表,敢于大胆反抗礼教,表现自由恋爱。本文所述“闺阁文学”,界定更加明确具体,仅指由女作家创作的、反映上层家庭中青年女性闺阁生活和心理的作品,同一作家其它题材的作品不在所述范围之内。
从界定来看,闺阁文学似乎范围狭小,作品数量亦有限,但把它们提出归为一类研究,还是有意义的。首先,这些作品是“五四”时代女作家最早或较早的创作,不可小觑。其次,这批女作家都是名门闺秀,闺阁文学反映的正是她们最了解最熟悉的生活,有些作品简直就是她们本人生活的写照,是她们思想感情最真实最自然的流露。她们特有的“叛道”与“守道”双重人格的矛盾,在此也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所以现在选取“闺阁”一角切入,便会发现中国封建堡垒另一生活内幕,启开一道直视堡垒里现代文明人的窗口,对探讨民主革命初期上层知识妇女的思想心态颇有价值。再次,作为女性,无论从个人素质还是文化修养来讲,闺阁文学作家们都是最优秀的一类,中西合璧的文化熏陶,形成了她们独特的审美观,爱与美成了她们本人和作品的共同追求,写作手法和技巧的发挥也达到了最佳境界,可以说,闺阁文学作品都是这些作家创作中的精品。
二
“五四”妇女解放运动是整个“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先驱们一开始就以“人”为标准,强调男人女人都是人,应该有一样的权利,一样的自由。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指出,“一问节烈是否道德?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可见无论何人,都怕这节烈。”女人是人,是活生生的人,有理想有追求,想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家庭生活,而节烈却阉割了女人作为人追求幸福的天性,男人是人却可以与节烈无关,这就是作为人的不公平。胡适1918年写的《贞操问题》,也阐述了类似的思想。他说,“因为贞操不是个人的事,乃是人对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双方面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爱情,心思专一,不肯再爱别人,这就是贞操。贞操是一个‘人’对别一个‘人’的一种态度。因为如此,男子对于女子,也该有同等的态度。若男子不能照样还敬,他就是不配受这种贞操的待遇。”鲁迅、胡适的观点比较集中的体现了“五四”人文精神,从这个高度指出了人的解放必须由男性解放和女性解放共同构成,单纯的男性解放绝非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反之亦然。他们是以科学的性观念看待节烈和贞操的,性的本能需要,对于男人女人来讲,都一样重要,所以独对女人的节烈和贞操,实际上是在压抑人性毁灭人性,毫无道德可言。
相比之下,对于这场关系中国妇女命运和切身利益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自身反而显得比较被动和迟缓,正如庐隐感叹的那样,“为什么妇女本身的问题,要妇女以外的人来解决?妇女本身所受的苦痛,为什么妇女本身又不觉得呢?妇女也有头脑,也有四肢五官,为什么没有感觉?样样事情都要男子主使提携。这真不可思议了!”庐隐的感叹令人深思。从当时文坛看,女性直接写文章谈论妇女问题的确实少见;创作上也只有庐隐、冯沅君、丁玲的小说比较大胆揭示了青年女子躁动不安的心声,为妇女命运鸣不平。闺阁文学的一批作者,无论知识结构还是艺术才华,原本都应该成为为广大妇女命运大声疾呼的先行者,但是她们没有积极行动。她们早期的作品只是温和地反映了自己大院里的小姐太太以及女仆的某种不幸,感叹闲适的无聊,最多不过是以平静的眼光审视着上层家庭存在的并不严重的问题,如冰心的《两个家庭》、《别后》、袁昌英的《玫君》、林徽因的《窘》、凌叔华的《绣枕》等。这些作品以其清丽温婉的风格与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五四”文学那种深刻的战斗性和狂飚突进精神恰成鲜明对照,其所涉及的问题,与现实中李超抗婚自杀事件和易卜生带来的“娜拉出走”问题相比,只能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对于妇女运动,周作人认为,“中国妇女运动之不发达实由于女子之缺少自觉,而其原因又在于思想之不通彻,故思想改革实为现今最应重视的一件事。”同样,思想障碍也是闺阁文学之所以踯躅于“叛道”和“守道”之间的关键。与“五四”妇女运动的思想家们张扬的人性观相比,闺阁文学的作者首先表现出一种对人和女人的困惑,她们过分强调了女性的性别意识,而没有将“女人”上升到“人”的地位,这种“人”与“女人”的错位,既使闺阁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入与“五四”精神不太合拍的思想支路,又使闺阁文学这朵盛开在“五四”文坛百花园里的奇卉异草散发出她那特有的芳香。
三
“人”与“女人”的错位,使得闺阁文学作品里的女性角色基本按照传统的男性标准来塑造。长期以来,中国文化以父系男权观念占统治地位,“男性中心”的文化意识要求完全把女性纳入自己的价值系统之中。女性美的唯一标准是男性的审美愉悦程度,其基本特点是由男性来欣赏女性,这种欣赏观经过长期积淀,成为套在女性头上的传统的审美模式。它要求女性有阴柔之美,外表应该“娇”、“柔”、“弱”、“秀”,内里则应是从属的、善良的、贞节的、缱绻的。
当然,传统文化也包含大量的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经验和智慧,有许多独具风格的民族精华。闺阁文学相当程度上比较合理、得体地吸收了这些精华。从美学角度看,其中许多女性形象,虽然是符合传统男性审美标准,表现出一种女子自觉不自觉地以男性标准来规范和调整自己行为的特点,但是由于千百年来这种审美观已深入人心,约定俗成,普遍得到人们包括女性自己的认可,所以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人们长期积淀的审美观较为合拍,从某种角度说,确实体现了一种民族的审美情趣。不仅如此,而且由于作者比较注重赋予作品中女性以知识和智慧,有些新女性还富有思考和进取的美德,如凌叔华《绮霞》里的绮霞,袁昌英《人之道》里的梅英,沉樱《旧雨》里的琳珊等,这些女性形象在旧有标准的基础上,更进步更解放一些,因而成了具有现代女性某些特点的新闺秀。不过,在洋溢着“五四”时代精神的大环境下,她们依然显出一种病态的不足,给人以“小家子气”的遗憾。
闺阁文学里的女性形象大多是柔弱的,她们普遍有着苍白病态的秀美面庞,有着纤弱玲珑的身段;她们感情细腻,时而眉锁春山,时而温柔娇嗔。请看凌叔华《花之寺》中燕傅借陌生女子之口向丈夫的一段表白:
我在两年前只是高墙根下的一根枯黄的小草……我过着那沉闷暗淡的日子不知有多久。好容易才遇到一个仁慈体物的园丁把我移在洒满阳光的地方,时时受东风的吹拂,清泉的灌溉。于是我才有生气,长出碧绿的叶子……幽泉先生,你是这小草的园丁,你给他生命,你给他颜色(这也是它的美丽的灵魂)。
现在我发生奢望,我想变成一只黄鸟或蝴蝶飞到郊外,任我歌唱,任我跳舞,赞美大自然,赞美给我美丽灵魂的人。
在这里,女性视男性为园丁,自己为小草。小草的生命、颜色和灵魂都是这个园丁给的,女性没有独立性,男女之间仍然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可是,做这种小鸟依人、花草般柔弱的女性,又是女性的自愿和刻意追求。闺阁文学用笔偏重于弱化女性的外表和感情,突出女性的温柔和顺从,实际上是对女性依附性的肯定和承认。闺阁文学以小鸟依人状取悦于人,并赋予这种柔弱以美感,其实这柔弱里隐含着女性缺乏独立人格,不愿经风雨见世面的贵族的惰性。
作小鸟依人状的多情女子,比较集中体现了文明女性知识女性的特点。此外闺阁文学里还出现了一些旧式的或处于新旧交替夹缝中的女性,如凌叔华的《太太》、《送车》、《旅途》中的人物,林徽因剧本《梅真同他们》中的文娟、大太太,袁昌英剧本《结婚前的一吻》中的李雅真,沉樱《生涯》中的钰等。这些太太小姐不管怎样的时新,骨子里却只比农妇们的生活内容多了应酬这一项(打牌、交友、请客、送礼等)。这些角色的心理深处,还是根深蒂固的女性依附性,依附的是男性家道之兴旺,门楼之高深。现代文明之风的吹拂,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至多不过是使她们多了一些应酬,其依附地位和心理未变,比起那些温柔智慧的新女性,她们对男性的依附性更强更迫切,本质上也更软弱。
一翻开闺阁文学作品,一个个端庄典雅、纤弱柔媚、温和含蓄、聪慧多情的小姐太太,从高门深院款款而出,宛如展开了一幅幅半古半新的仕女图,她们或低头刺绣心起微澜,或团扇轻摇淡说闲愁,或微笑欣赏童贞稚趣,或娇眼含笑依恋夫君,她们个个美丽动人,读来令人感到温馨备至。女性本来比男性更富于情感、直觉等人性的某些原始品质,因而女性作家的作品自然显得细腻柔和些,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塑造这些“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高门巨族的精魂”的作者们,也有着同样高贵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这就使得她们不知不觉抱有一种高高在上、自我欣赏的心理,锦衣玉食的生活环境更使她们疏远了充满矛盾斗争的社会实践,因而势必拘囿了她们以“人”为参照系来审视男女平等的视野。在闺阁文学作品中,作者们总是有意无意地从自己的优越地位出发,同样甚或轻视那些不能像自己一样生活的低层的或世俗的女性。如凌叔华的《无聊》,通过清高的女主人如璧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老仆张妈的无知和可笑,白太太和那个四十岁左右母亲,因忙于一大堆孩子和家务而变得琐碎、俗气、粗暴,还有那小洋楼里的年轻女人,每天过着与异性朋友交往过密而又高声喧哗不止的不安份生活。作品中这些佣人和太太的种种不幸或不文明,都是与如璧的高雅情趣、文明举止、周到应酬、得体衣着等行为原则相背。这样的参照和对比,就很难从作品中看到“五四”时代精神的投影,顶多在表现同是无聊中,如璧不像另一些女人那样俗不可耐,而后者则不像她那样耐得寂寞而已。我们不难发现,作为肯定形象的如璧,也映射出作者本人清晰的身影。
大多数闺阁文学作品,充分展示的是女性可爱的“女人味”,给读者的是一种见“女”不见“人”的感觉,作者没有超越女性的性别意识,把女性上升到揭示女性作为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高度统一上,而是固守于女性的圈子里描写女性。鲁迅的《伤逝》和冯沅君的《隔绝》、《旅行》等,同是写爱、写家庭生活,但作者把爱和家庭生活看成是双方的选择和要求,女性以“我是我自己的”、“没有自由毋宁死”的独立人格审视着自己,也审视着男性,追求一种平等的爱。相反,闺阁文学作品里的男性,无论是温存的偶像还是令人生厌的浪子,总是以主宰者自居,使女性为之感到幸福、得意,或为之流泪、失望。作品强调的是女人的可人(对于男子),强调女人有了男人的爱就是幸福,反之,便是悲剧。
闺阁文学用一种温恬的笔调描绘着身受封建压抑千百年的中国女性。在许多作品里,女人作为“人”的东西隐而不见,她们只是按照男性社会的标准要求自己,甚至奴化自己,自愿以男性为寄托为依靠。社会麻醉着女性,男性麻醉着女性,女性也麻醉着自己,麻醉了对现实的真正反抗,除了一点幽怨,剩下的就是无奈和顺从。即使作品中的新女性,要的也只是口头上的自由,当真正得到自由的允诺后,热烈的行动又戛然而止,“守道”究竟是占了上风。如凌叔华的《酒后》,当采苕看着酒后醉态的子仪时,突然萌发了想吻子仪的念头,可是当丈夫同意她的要求后,她又主动压制了这个冲动;在真正得到了自己向往的自由后,又犹豫后退了。冰心《我们太太的客厅》、沉樱的《生涯》等,也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这种“叛”与“守”的矛盾。这类作品,与文化先驱力倡妇女解放的精神相比,过多强化了女人的弱态,终而导致“人”与“女人”的错位。
纵观闺阁文学里的众多女性,都在礼教范围内来表现爱,最多是适可而止地表达一点幽怨和不满。作为女性,闺阁文学的作者们自身也面临不少困惑,而以表示爱为中心内容的闺阁文学,最能反映她们在男女性爱问题上的困惑,甚至是忌讳,因为她们终究是“守道”的女性。
“性”是人的生理本能,是恋爱婚姻的自然基础。但是中国这个封建道统无所不在的大国,对人性的压抑,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人们谈性色变,“性”已被视为最可怕的禁区。文化先驱们曾经借着张扬人性的“五四”劲风,直闯这个禁区。一批男性作家,也从人的本质出发,在二三十年AI写作出了人性极度受压抑受扭曲的现状,如郁达夫、沈从文的作品,坦露了性爱的冲动,刻画性心理,讴歌人性美。同时,以冯沅君、丁玲为代表的女作家,一登上文坛,就大胆率直地剖析自己恋爱的心理,真切地描绘了热恋中情人间那不可抑制的冲动,怀春的少男少女那不可抗拒的渴望,作家就是企图通过隽华、莎菲这些传统礼教的反抗者叛逆者,向人们宣告;女人也是人,和男人一样,有灵的追求,也有性的渴望和冲动。
相比之下,闺阁文学里的众多女性,对情爱的追求就不喜欢“太过充沛的感情”,她们行为极其检点,即使有点思想的偷情,也绝无行动的放纵,两性间的灵与肉、形与神是截然分开的,即使是夫妻,也决没有《卷葹》和《莎菲女士日记》中的男女间那种放浪形骸的爱,一切都是那么规矩,那么适可而止,决不能越雷池一步。她们的感情相当理智,虽然她们也向往爱情,追求幸福,但不论内心多么有热情,外表言行总是宁静而持重,时时处处显示着大家闺秀的风范,犹如一池春水,微风吹过,泛起层层涟漪,旋又复归沉寂。《绣枕》里的大小姐,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对爱的渴望和满腔柔情,都化为刺绣那对整整化了她半年时间的绣垫上,“光是那只鸟就用了三四十样线”,但当她精心绣制的枕垫送到寄托着自己希望的白少爷家后,当晚就被玷污了,这或许意味着那个“许多小姑娘追她看,很羡慕她,许多女伴面上显出嫉妒颜色”的“新娘梦”破灭了。尽管如此,她的不满也仅表现为“只能摇了摇头算答复了”。即使在《酒后》这样比较大胆表白爱和冲动的作品中,女主人公也是那么理智地适可而止。苏雪林的《鸽儿的通信》、《绿天》等作品里的女性,简直就是一只小鸟,对着自己心爱的人唱着爱的圣歌,这种爱似乎只停留在口头上,圣洁得显出了苍白、无色、无味。林徽因的作品算是闺阁文学中比较热烈大胆的一类,但在其代表作《窘》里,表达的也只是一种极有节制的朦胧意念和不可言状的瞬间的灵与肉的触电感:“维杉踌躇了一下,从袋里掏出他的大手绢轻轻地替她揩发上的水。她两颊绯红了,却没有躲走,低着头尽看她擦破的掌心。维杉看到她肩上湿了一小片,晕红的肉色从湿的软白纱里透露出来,他停住手不敢也拿手绢擦,只问她的手怎样了,破了没有。她背过手去说‘没有什么!’就溜跑了。”叛与守的区别应该以是否张扬人性为尺度,像这样含蓄过度的描绘,实际上已经绕开情感正常的表达方式,人物反而显得缺乏活力,缺乏真实感情。
冰心创作中也有一个现象很能说明问题。“爱”是冰心早期创作的中心内容,她讴歌母爱,吟咏童心,赞美自然,然而,作为爱的最重要内容的爱情,在冰心作品中几乎是空白。比如“少女怀春”,应是人生花季最美妙的感情,竟然被这位20来岁的青年女作家完全遗忘了,实在有点不合情理。当时就有批评家这样分析过:“有人说冰心在作品中,总是爱小孩子,这便是变态的爱的发泄,其实她未尝不想男人。这话自然是有相当的真实的。”话虽说得不太雅,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倒是揭示了冰心在创作中对“性”的忌讳,对“怀春”的难言以及她心底视“性”为不洁不端的隐衷。即使冰心那些表现现代知识女性家庭夫妻生活的作品,也只展示了好朋友式的婚姻形式,而缺少实质内容。(远不如沉樱写得真实)夫妻间亲昵有限,更多的是彬彬有礼,不太近乎人情。沈从文对此也有评说:“一个女子可以嘲笑冰心,因为冰心缺少气概显示自己另一面生活,不如稍后一时淦女士对于自白的勇敢。但一个男子,一个端重的对生存不儿戏的男子,他却不能嘲笑郁达夫,放肆地无所忌惮地为生活有所喊叫。”可见沈从文对冰心回避自己不可缺少的另一面生活是颇有微词的。
大家都知道林微因早年在英国与徐志摩的一段感情纠葛,最终他们也只是好朋友。对此,林徽因的儿子回忆说:“母亲后来说,那时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地那样去同一个比她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可见林徽因很大程度上把自己当初的行动,归因为“旧伦理教育熏陶”。事实也是这样,从当年大多闺阁文学作家,作为女人所走的路,可以看出,尽管“五四”开放自由之风带来不少“娜拉”的出走,但她们几乎都是符合传统标准的好女人,从好女儿到好妻子到好母亲,女性人生中每一个角色她们都扮演得十分到位,这既是女人的天性使然,也是传统礼教使然。
闺阁文学的作者们,不仅拥有显赫过人的家庭出身,她们还是才女,其中不乏美女,这种难得的集才貌于一身的优势,使她们总是博得人们的爱幕和仰视,她们也很明白自己非同一般的优势,潜意识里便有一种满足感,其作品自然就显得满足自得,显得居高临下,散发出浓浓的贵族的闺秀气。这种闺秀气除了表现在对下层平民施舍式的同情和关怀(如凌叔华的《无聊》、沉樱的《主仆》等)外,更多体现在女性形象典雅闲静的神态描绘和闺阁温馨氛围的营造方面。小姐太太们,时而琴棋书画,时而品茗轻语,时而牵着哈叭狗,呼换着仆人,这种矜持自赏悠然得体的举止,正是她们内在修养的外化。闺秀气虽然强化了她们的可爱,但这“可爱”却使读者产生一种需仰视才能看见她们的感觉。她们的贵族精神贵族派头,使她们与平民之间有着一道分明的界线。周作人在《贵族的与平民的》一文中指出,“平民精神可以说是叔本好耳所说的求生意志,贵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说的求胜意志了。前者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后者要求无限的超越的发展:前者完全是入世的,后者却几乎有点出世了。”这段话准确地道出了平民与贵族的精神差异,前者要求入世地求生,是一种独立奋进有时代感的精神;后者要出世地求乐,是一种逃避依赖的惰性精神。这两种精神体现在作品中区别也是显明的。闺阁文学塑造的孤独清高自觉自满如诗如画的小姐太太,描绘的远离时代风云的闺阁情趣,都不同程度地传达着一种依附的缺乏独立性进取心的贵族精神。冯沅君、丁玲笔下的女性完全是别一番模样,她们以直视的眼光剖析男性,剖析自己,表现了她们赤裸裸地追求真正人的生活的勇气,显示出强烈的参与意识和批判意识,富于时代精神。因此,尽管两位作者并非平民出身,但她们的创作却具有平民化倾向。闺阁文学正因其非平民化的倾向,而缺少投入现世的批判精神。
四
闺阁文学作家早年所受的家庭教养和后来所具备的现代知识、开阔眼界、认识水平,使新旧之差,中西之别,在她们的思想上形成一种冲突,一种极大的不平衡。一方面她们想要抗争,为广大妇女的命运鸣不平,她们应该有条件成为当时中国妇女界最早一批反封建礼教的坚强战士,肩负起妇女解放运动的重担。另一方面她们毕竟出身于高门巨族,再加上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使她们既受家庭利益的诱惑,高高在上,有曲高和寡的孤独,又促使她们有回归家庭躲进阁楼的愿望,对家庭的脉脉温情恋恋不舍;维护和享有自己拥有的优越条件的要求,使“守道”成为她们潜意识走向的最后归宿。这一叛与守的冲突,最终淡化了她们的心境,磨损了她们的激情。温顺的反抗,恬适的不满,为闺阁文学营造了一种平和的境界。鲁迅评价凌叔华时说得好:“凌叔华的小说……恰好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们的故道了。”鲁迅这席话从本质上深刻地揭示了这些作家及其作品普遍存在的“叛道”与“守道”的冲突,指出她们踯躅于现代文明之门而又最终被旧礼教羁绊于闺阁之内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
笔者于1992年秋采访过现代女诗人陆晶清,交谈中她讲到这样一种形象。二三十年代北京的女学生女作家中,明显地分成“洋派”“土派”,洋派以凌叔华、林徽因、冰心为代表;她们出身高责,喝过洋墨水,出入校门有车接送,有仆人跟随,她们不关心时事,不爱理睬旁人;在当时一些斗争中(如女师大学潮),土派的庐隐、石评梅等均能挺身而出(陆本人在学潮中就曾受过伤),与洋派们那种对别人不屑一顾的清高或仅抱以轻描淡写的同情形成鲜明对比。两派之间也互相瞧不起,但冰心是洋派中比较平易温和的。从陆晶清的介绍,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名门闺秀当年那种贵族气质和派头,也不难理解她们身上那种逃避现实、缺乏直面严酷人生的勇气的弱点。自然也可以理解她们作品中那种虽有对窗外绿叶春色的欣喜,但又依恋从闺阁居高临下观风景的乐趣这种特别的格调。闺阁文学犹如一位凭栏眺望的佳人,她或许也欣赏眼底那一往无前的奔流的壮观,但眼看一去不复返的滚滚东逝水,又勾起她一种美人迟暮的凄婉,她情不自禁地凭栏唱晚,那歌声里传达着温馨的惆怅,恬适的不满,其中自然也夹杂着不少无病呻吟、顾影自怜的情调,体现了她们贵族血统里天然矫饰的心态。
闺阁文学中也有一些作品,如沉樱的《女性》、《中秋月》、凌叔华的《绮霞》等,透过婚姻现象,触及到一些社会问题,表现了笼中鸟对飞翔的向往,或初试飞翔后的迷茫。但正如沉樱所感叹的,“我觉得好象是跌落在无边的海里。一块落下去的人们,有的是奋勇地向着岸边游泳去了,有的是抓着木片之类的在苟安着,只有我是既不会游泳,而又连一根草也抓不到地只在浮沉。我还想生活,但我将怎样生活下去呢?”如果一旦沉在海里,既不会游泳,又连一根草也抓不到,只有等别人来救,或者只好等死。当然还有更稳妥的办法,那就是把自己关在笼子里,不飞翔,不跌落在茫茫社会大海中。所以,闺阁文学作品大多只能绕开时代主潮,唱着一支支爱(情爱、母爱、自然之爱)的赞歌,绘出一幅幅古代仕女的“春困图”。它们实际上是一曲疏离时代、赶不上时代主旋律节拍的不谐和音,不过决不是反调,也不是杂音,而是“五四”交响乐章中一支别具一格的“小夜曲”。当然,这并非说闺阁文学所有作品都充满不谐和音,如陈衡哲的《姑姑》,就塑造了一个旧家庭里具有独立自强精神的新女性,冰心的《两个家庭》在揭示婚姻与家庭问题上也有一些深度。但是,闺阁文学就其总体而言,不谐和音毕竟是其主要思想倾向。
才华横溢的闺秀作家们只能凭栏唱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