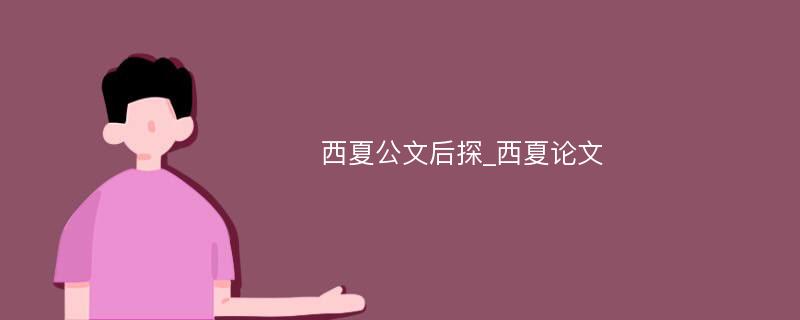
西夏公文驿传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夏论文,公文论文,探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01)02-0084-05
西夏驿传,因资料所限,鲜有专文研究。现根据新近公布的《西夏天盛律令》(以下简称《律令》),结合其他文献和文物考古资料,对西夏的驿路、驿馆、符牌和驿传制度等问题,作一粗略探讨。
一、驿路、驿馆
关于西夏驿路,史书记载不详。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首载有两幅地图,其中之一为《西夏地形图》。据考证,此图由宋代官吏绘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即为西夏中晚期地形图①。图中详绘有宋至夏,夏至契丹、西蕃、鞑靼境驿路以及各州、军间交通路线,有的地方沿路还绘有驿站、驿名,沿黄河两岸还注出数处渡口,是现存详细绘载西夏驿路交通的第一手材料。
从《西夏地形图》看,西夏驿路干线是以京师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为中心向外辐射的。现分述如下。
国信驿路 是宋与夏国间信使、国书所经由的官道。自兴庆府,经静州、永州,由吕渡过黄河,向东南至苦井,以下在白池、乌池间,分为两支:一支经盐州,从界首工井进入宋境,与宋环州、庆州相接;一支由洪州进入宋境延安府。该图在苦井注“夏贼犯边之路”,在界首工井注“国信驿路”,可见这条路既是西夏的军事要道,又是重要的信息通道。夏、宋时战时和,对峙近二百年,战时绝使封路,和时“朝聘之使,往来如家”。此路即是夏宋国书驿传的重要通道。
至契丹驿路 从兴庆府出发,向东渡过黄河,途经马练驿、吃啰驿、启哆驿等12个驿站,横跨毛乌素沙地,进入契丹境内。夏曾称臣于辽,两国贡使、信使往来频繁,此路即是夏辽通信的重要干线。
至鞑靼界线 自兴庆府,沿黄河至河套北,途经怀州、定州,路分两支:一支向东北直至黑山威福军进入鞑靼界;一支向西北,经贺兰山、麦呵啰磨、阿啰磨娘、碧啰山、麦块啰娘至黑水镇燕军,进入鞑靼界。
至回鹘界线 自兴庆府向西沿河西走廊经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出古玉门关进入高昌回鹘界。《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碑铭》载:“况武威当四衢地,车辙马迹,辐辏交会,日有千数。”可见这条路线还是十分繁忙的。
至西蕃界线 自兴庆府,沿黄河北岸向西南,经鹘罗漫、阿罗磨娘、阿罗把岭、碧林口,过折河,至卓啰城和南军进入西蕃界。
除以上主要干线外,西夏境内还有许多联系州、郡、军的支线。由契丹路向南分出支线至左厢神勇军,然后向北至宋麟州、府州界。在灵州东境,从顺化渡以南经夏州、讹河石堡、石州祥祐军、银州,沿无定河直至宋绥德州。在灵州西境,由袋袋岭向西分出两条路线:一经天丰仓、鸣沙县、割踏口、杀牛岭,至永寿保泰军;一线钱哥山、灵州界、打冷沟川、八猪岭,至轻啰浪口,南下便可到萧关和天都山。这两条路也是西夏南下侵宋的常经之路。
另外,地图中还标出3个渡口,都在京师兴庆府附近。一是郭家渡,在黄河北岸,是兴庆府到达南岸灵州的重要渡口;二是吕渡,三是顺化渡,在黄河南岸,都是兴庆府东渡黄河到达国信驿路和契丹驿路的重要口岸。
驿馆、驿舍、驿站等是专为过往使节、差人休息和提供粮草的地方。驿站较之驿舍、驿馆简陋一些,都属于西夏驿传供给系统。西夏早在德明时期就在境内设置驿站。曾巩《隆平集》卷二十载:“至德明,攻陷甘州,掠西凉府,其地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驿。自河以东北,十有二驿而达契丹之境。”契丹驿路横跨沙漠,人烟稀少,到西夏中晚期,仍保留驿站旧制,《西夏地形图》中绘有到契丹界的驿名与路线、位置,首起马练驿,终于横水驿,恰好是12驿,与《隆平集》中记载的一致。至于腹地的东西25驿和南北10驿,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可能早已升为郡、县了,改驿站为驿舍,故地图中没有标注。有关西夏驿舍的记载则在元昊时期。据《宋史·天竺传》载,西夏大庆元年(公元1036年),天竺僧人善能一行9人,到宋朝京师汴京贡献梵经、佛骨及铜牙菩萨像等,归途中路经西夏,“抵夏州,元昊留于驿舍,求贝叶梵经,不得,羁之,由是西域贡僧遂绝”。到西夏中晚期,西夏建立驿路网络,驿馆已较为发达。《西夏天盛律令》卷十一载:“他国使来,住于京师馆驿,依官买卖,未住诸人不许随意买卖。”卷十三载:“他国使来者,监军司、驿馆小监当指挥,人马口粮当于近便官谷物、钱物中分拨予之,好好侍奉。”从这两条律文可以看出,西夏上至京师,下至地方,均已设置驿馆,并专门配备“驿馆小监”进行管理。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西夏以兴庆府为中心,驿路干线纵横交错,遍布全国,沿路广设驿馆、驿站,星罗棋布,已经初步形成集交通、邮驿、供给于一体的交通通信网络。同时西夏为了保障驿路的畅通,非常重视驿路桥道的修治和管理。《西夏天盛律令·桥道门》规定,不许损坏驿路、桥道,“诸租地中原有官大道,不许断破、耕种、沿道放水等”;“沿诸渠干有大小各桥,不许诸人损之”;要经常注意桥道的修治,“各大道、大桥,有所修治时,当告转运司,遣人计量所需笨工多少,依官修治”,“小桥,转运司亦当于租户家主中及时遣监者,依私修治”;“诸大小桥不牢而不修,应建桥而不建,大小道断毁,又毁道为田,道内放水等时,渠水巡检、渠主当指挥,修治建设而正之”。
二、符牌
符牌是驰驿的凭证。传世的西夏符牌计有20多面,但并不都与驿传通信有关,需加以区别。
“敕燃马牌”,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枚,为圆形铜质合套式,合盖上镌西夏文“敕燃马牌”4字,牌直径15厘米,带窍18.2厘米。圆牌部分上下有符嵌,字外围有一个宽0.6厘米的圆圈,背底部有四连忍冬花纹饰。西安市文物管理处也藏有一枚,其形状、文字、花纹与历史博物馆所藏基本相同,只是牌的直径略小一点,为14.7厘米,文字笔画也略有差异。是西夏传递军令和紧急文书的信牌。
“防守待命”牌,现传世有6枚,均为圆形,直径为5厘米左右。正反面皆有文字,正面是西夏文字“防守待命”4字,背面为西夏人名。是西夏军营中守御者的信物标志,或是防守军人的名牌。
“内宿待命”牌,传世有多枚,形制一般为长方铲形,长约5厘米,宽4厘米左右,上有穿,可悬佩,正面为西夏文“内宿待命”4字,背面为西夏人名或“番号”。还有形制较大者,铜质,长方形,长9.5厘米,宽6厘米,正背两面各有相同的西夏文6字,一为阳刻,一为阴刻,汉译为“宫门后寝待命”。“内宿待命”牌和“宫门后寝待命”牌都是西夏宫廷宿卫者所执符牌。
除上述3种外,还有其他西夏符牌传世。如现藏于故宫博物馆的马蹄形铜牌,高7.6厘米,底边5.5厘米,一面无字,一面刻西夏文4字。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长方形铜牌,长7厘米,宽4.2厘米,一面刻西夏文“限置依”3字,一面刻西夏文“苏铁黑”3字;同馆还藏一圆形铜牌,直径8.8厘米,纽长2厘米、宽1.5厘米,一面有西夏文5字,有穿可佩带。对于这些符牌的性质和用途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②。
以上所述符牌中,与公文传递有关的是“敕燃马牌”,或曰信牌。西夏文辞书《文海》释“信牌”:“此者官语执者,诸人所信名显用,迅速紧急之燃马上用,故名信牌也。”西夏信牌从材质上可分为两种,一是金属制成,一是非金属制成。”金属的主要是铜牌,传世符牌均为铜质。另外还有银牌,《宋史·夏国传》载元昊“发兵以银牌召部长面受约束”。《西夏天盛律令》规定:诸人“执鍮符而折之,曰我带银符语及所领符不带腰上而置家中等,一律徒三年”。律文中“鍮符”即铜质符牌,“银符”即银质符牌。非金属的符牌有木质和纸质等。史载,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陕西宣抚使韩降遣将出麟府,“破贼马户川,斩馘数千,获绣旗、木符、领卢印”③。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鄜延经略使吕惠卿言:“自六月以后五十日间,第一至第七将前后十四次俘斩甚重,并获副军大小首领、副钤辖及得夏国起兵木契、铜记、旗鼓。”④《律令》卷十三曰:“诸人执符出使处,不许藏符于怀中,致符面上纸揉皱折叠。倘若违律藏符于怀中,又揉皱面上纸等,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从这条律文来看,似乎西夏还使用过纸符牌。另《律令》数处提到的“头字”、“捕骑头字”,也是具有凭证性质的纸质驿券。
符牌是重要的凭证。因此,西夏非常重视对符牌的管理。朝廷的符牌,均藏于宫中,并派人看护,闲杂人员不得打问和靠近藏符重地,“待命任职人等,不许自专引无职人入于内宫、官家住处、待命者当值、信牌箭置处、局分前内侍住宿处等,不许问示”⑤。授予地方的符牌,登记注册之后,则一般由地方最高长官保管,“诸监军司所属印、符牌、兵符等当记之,当置监军司大人中之官大者处”⑥。地边和畿内诸司签发符牌时,则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非官事不发,《律令》卷十三规定:“诸人非以官事,因私擅自令执符者,派者当绞杀,执符者及行头字者、司吏等判断比派执符罪当减二等。”“令执捕坐骑头字,有因私使之时,因私使者及行捕坐骑头字者之局分所使人等,与因私擅自遣执符之高低罪情相同。”二是非急事不发,《西夏天盛律令·执符铁箭显贵言等失门》规定,凡报告敌情,点集兵马,引伴使人,地边畿内有事奏告,唐徕、汉延等大渠水涨,催促草工、笨工,传递圣旨等,“除依法派执符以外,事大小有急者,当遣神策使军、强坐骑”。如果在不应派执符的情况下派时,大人、边检校、习判、承旨、城主、通判、城守等一律徒5年,“局分都案、案头、司吏当比之减一等”。
三、驿传制度
公文驿传的基本要求,一是迅速,二是安全。西夏为了确保文书传递的迅速、安全,制定了一系列制度。
1.信使骑乘实行征用制。和西夏同时代的宋朝将马分为十五等,大致前十三等充战骑,末二等“低弱不被甲”,则供应厢军或作递铺铺马,说明宋朝的信使坐骑实行的是供给制。而西夏则不同,其实行的是坐骑征用制。《西夏天盛律令·执符铁箭显贵言等失门》规定,公差人马所需粮草禄食均由官府统一划拨,沿途“不许于家主摊派食粮、马草等”。但是,为保证文书尤其是机要文书和时限性文书及时送达,信使所乘坐骑则实行沿途征用制度。所有被征人员必须无条件服从,诸人与执符使人相遇“殴打,不予骑乘等时,当绞杀”,“不予骑乘而逃,及予之骑乘而打之,及未打而不予骑乘等,一律徒十二年”。传递一般文书的信使与传递紧急文书的信使相遇而需要捕骑时,也必须予之坐骑,“若不予执符坐骑而争斗”要治罪。当然,信使征用坐骑时也必须遵循以下规定。
不得差用“官马” 即不能征用军用马匹,只能骑诸家民所属私畜及官之牧场畜等有方便可骑乘者。如果确实没有私畜和牧场畜,或者有但不堪骑乘,则允许捕骑“官马”。倘若违律,“附近有堪骑之他畜不用而无理用官马时,徒二年”。和西夏同时代的辽则不然,契丹带牌天使乘以驿马,“驿马阙,取它马代”⑦。
不能超捕 执行公务的使人一般都持有官府签发的“捕骑头字”——征用坐骑的驿券,上面明确规定捕骑的数量。如果信使擅自多带随从或超捕骑者,“已捕多少勿论总数,当以一日捕一畜计之,一人一日引徒一年,二日徒二年,三日徒三年……九日徒十二年,十日无期徒刑,自十一日以上一律绞”。
用完还畜 使人使用坐骑虽然是无偿的,但是用完后必须归还畜主人。如果途中畜因患病羸弱而死时,近则须将“畜尸”归还主人,远则可把皮肉“依当地现卖法当卖之,卖价当还畜主人”。如果是故意杀畜,当偿畜。
2.逾期罚罪制度。为保证文书的迅速传递,无论是紧急文书还是一般文书,西夏均有时限性要求,不过在时限的宽严程度和逾期处罚的力度上有很大差异。
西夏紧急文书可分为两种,一为火急件,一为急件。“因来至边地敌寇不安定之地,我方发兵马,又十恶中判逃以上三种情等,执符火急要言”是为火急文书。传递文急文书,误自一时至三时八杖,四时至六时十杖,七时至十时十三杖,自十一时以上以误全日论,误一日徒一年,二日徒三年,三日徒五年,四日徒十年,五日以上一律当绞杀。“十恶中,判逃以上三种事以下,及地边、畿内事有所告奏,又安排发笨工,催促种种物,依法派执符”是为急文书。传递急件延误者,自一日至三日徒三个月,四日至七日徒六个月,八日至十日徒一年,十一日至三十九日徒二至十二年,四十日以上一律无期徒刑⑧。
西夏一般文书可分两类:定期文书和不定期文书。定期文书包括每年京畿3月1日、中地4月1日、边境6月1日上交的军籍册;10月1日全国性的对官马(军马)、坚甲、杂物、武器季校的报告;11月1日各郡县上交转运司的上计;三年一番各郡县核查土地变动情况的“地册板簿”等。不定期文书则包括需要上级审核的司法文书,以及诸司往来的普通文书等。
西夏对一般文书的传递也有时限性的要求。《西夏天盛律令·物离库门》记载了全国各地到京师兴庆府的一般公文送达期限:沙州、瓜州两州到京师40天;肃州、黑水二司到京师30天;西院、啰庞岭、官黑山、北院、卓啰、南院、年斜、石州八司到达京师20天;北地中、东院、西寿、韦州、南地中、鸣沙、五原郡七司一律到京师15天;大都督府、灵武郡、保静县、临河县、怀远县、定远县六司到达京师10天。如果不按上述时限送达,逾期者,“自一日至五日不治罪;自六日至十日,有官罚钱五缗,庶人十杖;十日以上至十五日,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自十六日至二十日徒三个月,自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徒六个月,自二十六日至一个月徒一年,一个月以上一律当获二年徒型”⑨。
3.合符制度。合符是西夏为保证兴兵文书传递安全而采取的一项措施。通常兵符都分左右两半,一半授予军事首领,一半藏之朝廷,任何一方要调动兵马都要合符。
朝廷下发兵谕文,必须到地方去合符。《律令》卷十三规定:“诸监军司所属印、符牌、兵符等当记之,当置监军司大人中之官大者处。送发兵谕文时当于本司局分大人刺史等众面前开而合符。”如果大小、长短、字号相合,则发兵。若“取显合中,同体以外稍有不合者,依军法何行,彼符有若干不合,变处当由刺史、监军同官共为手记而行,京师局分人派发致误者徒一年。监军司见符不合,懈怠而不告,亦徒一年”。
地方要发兵,必须奏报京师去合符。《律令》卷十三还规定,边疆敌人不安定,界内有叛逃者,应立即急速发兵,“求取兵符,奏报京师而来显合”。如果符不合,但需要发兵是真话,刺史、监军司则应当先发兵,至于符为什么不合,“来者当枷而问之”。
4.盗隐、损毁、亡失文书罚罪制度。按性质,西夏文书大致可分为机要文书、司法文书、会计文书和其他文书等几类。《律令》卷十二《失藏典门》规定,以上文书“行之未毕及已毕”,盗隐、损毁、亡失等都要受到相应的惩罚。
“写秘事及牒诏书,兴兵文字,恩敕等”是机要文书。秘事中写有谋逆、族人议逃、用计谋追捕叛逃者及其同党等,“欲受贿而盗隐、损毁文字者与犯罪者同。其中无心失误而失之时,推问中有碍则当绞杀,无碍则徒六年。若推问已毕,典已置库中而盗隐损之者,徒三年,失之则徒二年”;“盗隐、损毁、亡失所记文字秘事中”,有关敌国官员、首领和部族归降,两国之间的牒敕、誓文,接壤邻国分我土地,四方接壤诸侯归附我朝等,“于所谋事有碍无碍,轻重如何,视其时节语义,奏报实行”;传递朝廷所颁恩诏,信使不得懈怠,若期限内不到,要承罪,“若恩诏已至所属司内,依恩施行已毕,藏量局分人处,有名亡失时,徒一年”;传递边中兴兵文字者,“局分人失之及他人盗之等,当绞杀。失、盗军品文字者,一律徒三年”。
在审判诉讼中“诸司为种种文字”是司法文书。司法文书“行之未毕”诸人盗、隐、损、失时,释放罪犯者,处以和罪犯相同的罪,未释放罪犯,则比罪犯减一等;“行之已毕”已藏置中而盗、损时,徒三年,如果无心失误而失者,徒一年。
“官畜、谷、钱、物、武器、杂物种种权正分领之状文、升册等”是会计文书。亡失会计文书,以有无相同钞本加以区分并根据文书中登记钱物数量的多少来定罪。有相同钞本存放之罪法:自一缗至二十缗十三杖,二十缗至四十缗徒三个月,四十缗至六十缗徒六个月,六十缗至八十缗徒一年,八十缗至百缗徒二年,百缗以上一律徒三年。无同本存放之罪法:自一缗至十缗十三杖,十缗至二十缗徒六个月……八十缗至九十缗徒十二年,九十缗至百缗无期徒刑,百缗以上一律绞。
其他文书包括“移军册及因赏赐臣民之功、升任官事等为文典”。这类文书“行之未毕而盗、隐、损之时,徒三年,无心失误失之则减二等,行之已毕,已藏置中盗、隐、损之及失之等,比前述盗、失二等罪情当各自减一等”。
从上述可以看出,西夏在量刑时,明确区分文书“行之未毕”和“行之已毕”两种情况,且处罚差距较为悬殊。行之未毕是指文书正在发生现行效用,包括发文、传送、处理、执行等文书运行过程,如果在这一段时间里,文书被盗、丢失或损坏,当事人要受到比较重的惩罚;行之已毕则是指文书处理完毕,“藏于置中”成为档案以后,若被盗、丢失和损坏,当事人所受处罚相对轻一些。驿传人员若损、失文书当属前者。
除以上制度外,西夏对文书传递人员还有一些具体规定。不得取民畜物。“执符及诸大人、待命者等经诸城市场处,不许于家主摊派食粮、马草等”,“无理取诸人之畜物者,计量,依枉法贪赃罪判断”。不得欺民行淫。“执符及诸臣僚大人等……于诸家主中强征他人妻以为不义者,其丈夫告则执符等徒三年。”不得打架斗殴。“执符沿途往捕畜时,不许于家主中为无理,与诸人争斗殴打,若违律时徒一年。”“执符无理与他人争斗,他人动手杀执符,执符动手杀相争等,一律当绞杀。”不许饮酒。西夏规定“除统军以外,诸执符不许饮酒。若违律饮酒时,已生住滞者罪状分明外,未出住滞则因饮酒,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⑩。
收稿日期:2000-0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