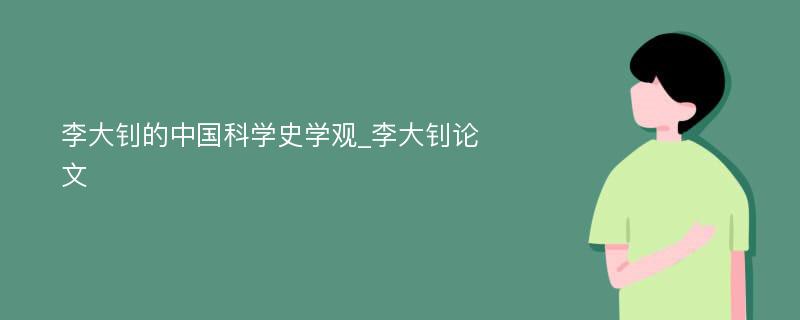
李大钊对中国史学科学化的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史论文,对中论文,李大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初期,建立科学的历史学,使中国史学走上科学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史学界探讨较多的一个问题,以不同理论为背景而提出的不同的见解,在史学领域内引发了对“科学的历史学”的基本特征及其实现途径的引人注目的争论。其间,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李大钊从指导理论、学科形态、目标追求、研究体系等不同的层面提出了对中国史学向科学化形态发展的构想。在当时,李大钊的论述因其本身的科学性而成为对这一问题的具有启蒙性质的理论阐释。
一、指导理论的科学化
1920年,李大钊在其撰写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指出:“‘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是Karl Marx和Friedrich Engels一八四八年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所发现的。”[1](P316)李大钊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先进的历史观,是促使历史学走向科学化的指导性理论,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使人们能够重新认识历史,获得新的见解,把握“历史的真义”。他在《史学概论》一文中指出,过去的许多记录,与历史的本来面貌不相符合,不能真实地反映人类历史的发展状况。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诞生,使人们得以用新的历史观念去重新审视人类历史的发展,从中“得着新的见解,找出真确的事实”,并在此基础之上把握“历史的真义”。他强调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学说,“把历史真正意义发明出来”了。[2](P338、340、342)
其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作出了富有创见的合理的解释。在《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李大钊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的唯物史观,其要领在于“认经济的构造”在人类社会所有现象中是最重要的,是“基础构造”,而决定经济构造“进化”的“最高动因”,则是“依其性质必须不断变迁”的“物质的生产力”。李大钊强调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的这一解释“是合理的”。[1](P324-325)
复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出现,开创了历史学的新纪元,使历史学走上了科学的发展道路而日趋兴盛。在《史学要论》一书的《什么是历史》一节中,李大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从整体上全面考察和准确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从中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把历史学提到了科学的地位”。在《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一节中,李大钊进一步论述说:马克思对历史的“根本理法”的发现,使“历史学在科学上得有相当的位置。治史学者,亦得有法则可循。”[2](P381、411)因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出现,“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使历史学走上了科学的发展道路而“日益隆盛。”[1](P304-305)
综上所述,在李大钊看来,要实现中国史学的科学化,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实现指导理论的科学化,这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学科形态的科学化
李大钊认为,作为科学的历史学,其最基本的表现形态是历史理论的建立。他在《史学与哲学》中十分明确地说:“以历史为中心,史学可分为二部:记述历史;历史理论。”记述历史的目的,是确定历史事实并以“活现的手段”将其描写出来,这属于“艺术的工作”;而历史理论的目的,则是将已经确定了的事实“合而观之”,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这乃是科学的工作。”[2](P294)
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学》中,李大钊再次强调说:历史学是包含艺术性和科学性双重属性的学科,而使其科学性得以体现的,是对事实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探究的历史理论的研究,它决定了史学的性质与其他科学“全无异趣”。因而,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2](P387-388)
然而,在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中国史学在科学化方面的状况却很难令人满意。尽管在历史的记述上成果累累,独步世界史坛,历数千年而不衰,但历史理论的研究却十分落后,直至20世纪20年代,仍旧是“治史学者,类多致其全力于记述历史的整理,而于一般史实理论的研究,似尚置之度外。”[2](P392)这种对历史理论研究的普遍淡漠,直接影响了对历史科学基本问题的探讨与研究,使作为“一种科学的学问而言”的历史学,在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中国并不没有普通的记录,而专攻历史,以历史为一门科学的,却是没有。”[2](P290)显然,观念上的滞后与理论研究上的贫乏,给中国史学向科学化形态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为此,李大钊提出,中国史家应当打破旧史学的局限,重视历史理论的研究,矫正以往史学在学科形态上的明显偏差,推进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他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学》中指出:“各种学问的发展”,无不由对事实的确定、记述进展到对其相互关系的理解、说明、概括、推论,并最终形成“关于其研究的系统的理论”,这是包括史学在内的各种学科发展的共同规律。因而,为了实现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中国史家不能“置一般的理论于史学的范围外,而单以完成记述的历史为务。”[2](P389-390)应当把历史理论的研究放在重要的位置。
对于如何使历史理论的研究取得进展,从学科形态的层面实现中国史学的科学化,李大钊认为,这首先要求史学家改变旧有的观念,要明确“史学的目的,不仅在考证特殊史实,同时更宜为一般的理论的研究。”在对历史事实进行记述的同时,也要致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其次,要做到构思研究框架,确定研究范围、收集研究材料等方面的前期准备:“有志于历史理论的研究者,宜先立关于其结构的大体计画,定自己所当研究的范围,由与记述史家不同的立脚点,自选材料,自查事实。”再次,要吸收其他学科所取得的成果,进行跨学科的研究:“须采用生物学、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及人文科学等所研究的结果,更以征验于记述历史,历史理论的研究,方能作到好处。”复次,要对历史科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及其与历史哲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历史科学一旦成立,果为如何的性质?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究有若何的关系?其界域若何?其考察法的相异何在?历史科学所当研究的事实为何?这都是治史学者所当加意研考的问题”。最后,要根据历史理论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需要,采用新的方法进行新的研究:“理论史家……,其观察法与记述历史家不同,必须立在他的特别立脚点以新方法为新研究,”要“自辟蹊径,不当依赖他人”。只要这样研究下去,“历史理论即历史科学,终有完全成立的一日。”这是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肩负的历史使命:“真挚的史学者,幸共奋勉以肩负此责任!”[2](P388、392-393)
三、目标追求的科学化
在《史学要论·历史学的系统》中,李大钊明确指出:“历史理论是以一般就种种史的事实研究其普通的性质及形式,以明一以贯之的理数为目的的。”历史理论“是说明历史现象的一般性质、形式、理法的。”[2](P393-394、403)也就是说,历史理论的研究,是围绕探求贯穿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理数”或“理法”——即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而展开的。因而,史学的科学化,历史理论的建立,归根结底是要通过认真的探求最终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这是科学化的历史学的终极目标。围绕这一认识,李大钊提出了下述几个方面的见解:
一,规律普遍存在于一切领域,人类社会也不例外,怀疑史学可以发现历史规律而成为一门科学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他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学》中指出:有些人认为历史研究在性质上不能与其他科学同日而语,怀疑史学能够成为科学,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李大钊论述道:虽然各种学科伴随其研究对象的不同,不能不多少具有其特色,从而使作为“人事科学的史学与自然科学自异其趣”。但是,不能以此便认为“史学缺乏一般科学的性质”。他强调说:尽管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使其发展规律不是以单纯的形态显现出来。但不能因此便否认这一规律的存在,“此理法的普遍存在”,是“毫不容疑”的,所不同的是,与自然界的规律相比,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蕴含于错综复杂人事关系之中而“不易考察罢了”。他在文中深刻地指出:“世界一切现象,无能逃于理法的支配者。人事界的现象,亦不能无特种的理法,惟俟史家去发见他,确定他了。”[2](P390-392)
其二,致力于历史规律的探求是使史学跻身于科学之列的一项“伟业”,是确立史学科学系统中不可动摇的位置的基础。他在《史观》一文中指出:马克思等近代西方的一些学者对历史规律的探求,使历史学同社会学等跻身于“科学之列”,这是学术界的“一大伟业”,它使史学取得了“不能撼摇”的“科学的位置”。[1](P228)在《史学要论·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中,李大钊再次指出:马克思等对历史“法则”的发现,使历史学“得以在科学系统中占有相当的位置”。[2](P408)
其三,与对历史事实的单纯记述相比较,对历史规律的探求是史学研究进一步深化和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表现,是史学研究终极目标之所在。他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学》中说:进行科学研究的史学家,不能“仅以精查特殊史实而确定之,整理之,即为毕乃能事;须进一步,而于史实间探求其理法。”正是这种对蕴含于史实之中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的性质、理法”的探求,使史学成为“与其他科学同性质同步调的东西”。因而,现代的史学研究,不应当停留在单纯考证史实的阶段,而应当更进一步,“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这是史学研究进一步深化和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表现,是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2](P388-390)
四、研究体系的科学化
李大钊认为,要实现历史学的科学化,还必须构建一个科学的研究体系,这是史学走向科学化的重要保证。他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学》中指出:在当时,科学的历史学之所以未能“成立”,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作为一种“严正的历史科学”没有能够完成其“整齐的系统”。[2](P388)因而,要建立科学的中国史学,还应当努力构建一个完整、科学的研究体系,以此为依托,实现中国的史学科学化。为此,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一书中辟出专章,以文字论述与图表示意相结合的形式,提出了他对这一体系基本构架的设想并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李大钊在文中指出:“最广义的历史学”的主体由普通历史学和特殊历史学两个类别构成。其中,普通的历史学也即“广义的历史学”分为两大部分:记述的历史和历史理论。它们又各分为六个部分,记述的历史分为个人史(传记)、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历史理论则相应地分为个人经历论(比较传记学)、氏族经历论、社团经历论、国民经历论、民族经历论、人类经历论。
对于记述的历史和历史理论的区别,李大钊论述说:记述的历史是对上述六个领域中人类经历的考察与记述,即“考察叙述活动的主体的人或人群的经历”。而历史理论则是对这些领域中的种种现象作出理论上的说明与“解释”,探求其中的“原因”,发现其中的“理法”。[2](P396、398-399)
由上述六种“史”构成的“记述的历史”与六种“经历论”所构成的“历史理论”,共同组成“普通历史学”。尽管李大钊出于对理论的高度重视并针对中国史学的现状而强调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历史理论“实为构成广义的史学的最要部分”。[2](P405)但他同时指出,在科学的史学研究体系建立的过程中,记述的历史与历史理论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它们的共同发展与进步,是史学科学体系得以完成的基本保证。他在《史学要论·历史学的系统》中说:“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有相辅相助的密切关系,其一的发达进步,于其他的发达进步上有莫大的裨益,莫大的影响。……二者共进,同臻于健全发达的地方,史学系统才能说是完成。”[2](P395-396)
除上述普通历史学之外,李大钊指出,“尚有种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史学家于其所研究的事项感有特殊兴趣者,均可自定界域以为历史的研究。”这便是“特殊历史学”。特殊历史学也分为“记述之部”与“理论之部”两部分。其中,记述之部又称为人文史或文化史,它包括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伦理史(道德史)、宗教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教育史,……等等。理论之部又称为人文学或文化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理学、伦理学(道德学)、宗教学、文学、哲学、美学、教育学……,等等。以普通历史学与特殊历史学为主体,加上历史研究法、历史编纂法和历史哲学,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科学的史学理论体系。李大钊强调说,要使这一体系得以“完成”,需要史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他告诫说:“科学不是能一朝一夕之间即能完成他的系统的。历史科学的系统,其完成亦须经相当的岁月,亦须赖多数学者奋勉的努力。”[2](P396、397、404、388、392)
可以看出,李大钊对中国史学向科学化形态发展的构想及其相关的理论阐释,是针对当时中国史学的现状,针对推动中国史学发展而应当消除的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而提出的。在20世纪20年代,这些观点的前瞻性和科学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在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奠定坚实基础的同时,也对此后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