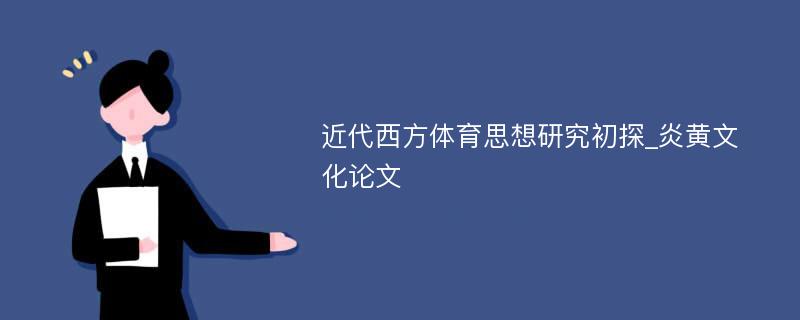
近代我国学习西方体育思想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思想论文,我国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1世纪以来,我国体育思想在体育发展全球化的不断冲击下逐步完善与提高,体育思想的日臻完善指导我国体育教育的深入与发展。然而,当我们回顾我国体育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时,会发现我国体育思想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学习与扬弃的历史。它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互为传承与扬弃的过程中,创造了我国体育思想的发展史。在我国体育思想发展过程中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西方体育思想,学习西方体育思想的社会条件以及驱动因素等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与研究。
一、中西方教育中体育认识差异的剖析
(一)中西方古代教育对体育的认识
从教育的角度看,自古以来中西方对体育的认识就存在着差异,这一点可以从中西方古代教育家、思想家对体育的理解中窥见一斑。
早在先秦时期,儒家思想在教育领域里的一个集中反映就是儒经与仕途相结合,读书做官,所谓“满朝朱紫冠,尽是读书人”。孔子把“仁”和“礼”附于体育活动之中,使体育活动脱离了强健身体、提高技能的作用。孔子还提倡“学而优则仕”,影响到封建社会的教学内容,使之偏重于“文”。孟子提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论点,这是明显对“力”的轻视。经过秦汉近百年的探索,汉武帝又执行了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文教政策,推崇“文德为贵,而威武为下”的观点,从而奠定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文教政策的基础。宋代以后,采取“恢儒右文”政策,重文轻武愈演愈烈。重文轻武的教育思想束缚了我国体育思想的发展,封建时期的体育未能得到足够重视和正常发展。
而与我国封建社会同时期的西方社会对体育的认识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诸如,苏格拉底十分强调身体健康对人的重要性,认为健康的身体是工作与事业的保障。“由于身体不好,健忘、忧郁、易怒和疯狂就会猛烈地袭击许多人的神智,以致把他们已获得的知识丧失净尽。但那些身体健康的人却有充分的保证,他们不会遭受由于身体不好而遭受的危险,与此相反,身体健康则很可能获得和身体衰弱完全相反的有益效果”。[1]柏拉图也认为“幸福中最高的要算:第一为健康;第二为美;第三为体格的强壮与活泼”。[2]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体力教育应该先于智力教育”。“关心身体应该先于关心精神,关心身体之后须要关心性格的教育,这样可以使他们的教育服役于智力教育,而使体力教育服务于精神教育”。[3]“生命和世界都在运动,没有运动就没有时间,空间和物质”。[4]这些思想为西方体育思想及体育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也为西方体育思想传入我国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正是中西方古代对体育认识存在的差异,导致了西方体育思想在传入我国时必然面临重重困难,成为我国对西方体育思想认识上的障碍。
(二)中西方近代教育对体育的认识
时至近代,中西方教育思想家们对体育的认识有了进一步发展,但认识的程度与角度却有所不同。
西方的教育思想家们继续秉承古人对体育的卓臻见识。诸如,洛克在他的教育名著《教育漫话》开篇就论及“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这是对于人世幸福的一种简短而充分的描绘”[5],认为健康之精神是最主要的,但健康之身体是其前提。洛克把学校教育的任务分为体育、德育和智育。认为体育是教育的基本要素,并把它放在全部教育的第1位。卢梭认为自然人是身、心协调发展的人,身体和思维互相依存,身体活动可以增强思维能力,思维又可以进一步扩大身体运动范围,在发展过程中,二者在不断的差异中达到统一。而教育家斯宾塞在西方教育史上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智育、德育和体育的理论概念,并把智、德、体三育作为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主张“身体即是心智的基础,要发展心智就不能使身体吃亏。”[6]
在我国,由于清王朝统治者和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积极宣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理论,除了轻视武人外,还实行弱民弱种的政策。因此,有识之士多从救国救民的角度来阐述自己的教育思想。诸如,作为近代我国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德、智、体三育并重的先导者之一,严复认为我国落后的根本症结在于教育,而中华民族的昌盛则取决于国民“体育、智育、德育”的全面发展,取决于整个民族素质的全面提高。康有为在其所著《大同书》中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思想,并强调青年学生应在“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和谐地发展。后来,梁启超又提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通过教育为手段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民”,并尖锐地抨击我国“重文轻武”的传统教育,认为它招致了“武事废堕,民气柔靡”的严重后果。当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我国刚刚萌醒的教育思潮相接触时,我国的社会整体生态环境还不适应西方教育思想,但西方的教育理念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教育的发生、发展。
二、我国学习西方体育思想的社会因素考察
我国学习西方体育思想不仅需要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而且还需要一个适宜的社会条件。在近代西方体育思想传入我国以及我国学习西方体育思想的过程中恰恰出现了这种条件。
(一)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客观上创造了西方体育思想传入我国的契机
19世纪伊始,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第二次扩张,西方传教士也掀起了新一轮的传播福音的运动。鸦片战争前的清朝,经过史称“百年禁教”的闭关锁国时期,这一时期因英美传教士东来,西学输入活动又重新恢复起来,第二次西学东渐成为西方体育思想传入我国的一个重要起因。在1807年至1840年,欧美派遣来华的传教士总共不超过20人。诸如英国的马礼逊(1807年来华)、美国的裨治文(1830年来华)等,这些人是鸦片战争前在华传教士的代表人物。他们主要通过办刊物、翻译书籍等形式向中国介绍西方的宗教和文化。如马礼逊就创办了第一份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了英文版的《中国丛报》。他们有的通过办医院和学校吸收信徒,如美国传教士伯驾就在广州创办眼科医院,借医病之机“熟悉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收集情况”。[7]
19世纪30年代,英美传教士的活动集中在叩开我国大门的政治活动上。他们一是收集情报,鼓吹采取强制措施;二是为在我国开展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做准备。由此,英美传教士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是以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出现的。他们来我国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传播西方文明而是为了发展基督教事业。他们向我国传播的西方文化,只是他们发展传教事业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炫耀基督文明并以此吸引中国人加入基督教。然而,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8]西方文化给我国人民带来的效果与传教士的目的并不完全一致。从一定意义上说,西方传教士传播的西方文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科学与进步,使了西方体育思想更快的被中国人所接受。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经历了‘实利主义的一代’的欧洲,受民族主义、福音传道派和资本主义的推动,在亚洲、非洲和中东更加活跃了。工业化起了对原料和海外市场的需求,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又承认扩张是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宗教热情激发了信徒们向异教徒布福音的神圣使命感。”[9]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一股不可遏制的世界潮流,我国的封建主义统治已经抵挡不住这一冲击,不得不采取一些变革措施。西方列强入侵造成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使我国社会的发展和教育改革,改变了前进的路径,西方列强的入侵既提供了变革的外力、契机,又提供了变革的参照。
(二)洋务派与维新派的主张加速了西方体育思想传入我国的进程
无论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在西方体育思想传入我国的进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他们所处时代的背景不同,因此在西方体育思想传入我国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具体情况如下所述。
鸦片战争后,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深深体会到传统文化的不足,要求改革吏治和向西方学习,萌发了初步的改良思想。如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鸦片战争中,西方战胜我国主要依靠的是坚船、利炮,那么,坚船、利炮之类的军事技术就成了魏源所指的“长技”。学习西方就是要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洋务运动的兴起,把魏源的思想主张变成了现实。洋务派通过举办洋务教育为自己培养人才。诸如新学堂的建立,留学教育的实行,教会学校的开办以及西方著作的翻译和传播,这促使一部分中国人加深了对西方的认识,看到了我国与世界的距离。于是他们主张在不改变封建政体的前提下,推行对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由此洋务派所推行的西文、西艺教育,为西方体育思想在我国的传入奠定了思想基础。
甲午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民族矛盾空前激化,早期维新派也从后台走向了前台,资产阶级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于是1898年设立京师大学堂,统管全国的教育事业,并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设立了中西两类课程。在为期6年的课程中,西学的比例高于中学。戊戌变法失败后,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继续举办。维新派的许多教育主张在维新运动期间得到了实践,对封建旧教育形成了强大的冲击。然而由于封建势力强大,封建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维新派在与顽固派斗争中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镇压下去,维新教育也随之进入了低潮。但是,维新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即“民智已开,不可遏抑”,在清政府施行的“新政”改革中,维新教育的主张又以新的面孔出现。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维新运动暂时走向低潮。但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却进一步激化。诸如,义和团运动此起彼伏,席卷整个华北地区;孙中山领导的惠州起义;八国联军进军中国,等等。在严酷的内外时势逼迫下,慈禧太后不得不承认“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指令“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详悉条议以闻”,[10]由此揭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之后在所接到的奏章、条陈和清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措施中,教育改革的内容占有相当分量,这为西方体育思想在我国的传播铺平了道路,而新政时期制订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中规定的体操课的开设则充分体现了西方体育思想在我国的具体实施。
(三)留学教育与新文化运动加快了我国全面学习西方体育思想的步伐
清末新政时期的留学教育是洋务运动时期和维新时期留学教育的继续和发展,且较以往留学不同,从政府到个人,从学习目的到学习内容都有很大的变化。甲午战争后至新政前,据估计留日的学生有200人,[11]1906年达12 000人。[12]留日学生虽然成分复杂,程度参差不一,但较广泛地传播了资本主义思想观念,推动了我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另外,在留日高潮的刺激下,美国人认为应采取一种“从知识上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来控制中国的发展。[13]于是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从1909年起,将美国所得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退还给中国用于发展留美教育,其他国家也先后响应。这就是所谓的“庚款兴学”或称“退款兴学”。我国政府也相应地出台了一些配套政策,如设立机构,筹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等。通过“退款兴学”,美国确实达到了“把中国的留学潮流引向美国”的目的,1909年后,留美人数逐年增多,而且呈常年不衰的劲头。留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既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可程度,也反映了国家对西方文明态度的转变。留日教育与留美教育的发展促进了西方体育思想在我国的传播速度与快速发展,诸如,民国成立初期,教育部就召集留日和留美归国人员征求对学制的修改意见。最初意向是以欧美学制为蓝本,后因对欧美学制缺乏了解,以其不符合中国国情为由,决定仍参照日本学制,结合中国的教育实践经验,制定出我国自己的学制方案,即史称壬子学制。
由于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落入了封建复辟势力之手。我国封建势力的强大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丢失,激起了进步人士对我国革命历程的反省,人们认识到在一个封建专制影响深入骨髓的国度里,如果不从思想观念领域进行一次或多次的革命,那么,不论技术的引进,还是制度的变革,都不能将我国带出落后愚昧的境地。于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对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地批判,倡导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对传统教育和文化进行深入的反思和重建,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促进了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和空前的思想解放。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思想领域的变革是巨大的,我国的教育者积极加以选择、吸收改造,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教育试验,从而带动了我国体育思想的全面改革和发展。
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促使我国现代教育观念发生巨大变化。在继洋务教育在技艺层面、维新教育在制度层面上接受西方教育后,新文化运动时期,我国在思想观念层面上开始自觉接受西方教育。中国人对传统教育、教育现状的反思和对学习西方先进教育的鼓吹,使我国教育的改革进入到了思想文化的层面和自觉主动的阶段。教育观念的转变直接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在体育领域也带来西方体育思想及其体育教育在我国的迅速传播,1922年“壬子学制”的制订就是最好的佐证。
三、我国学习西方体育思想的驱动因素分析
学习西方体育思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长时间的磨炼,更需要一定的动力因素去加速学习的进程。
(一)强势文化的涌入迫使我国接受西方体育思想
在不同的背景下孕育、产生和发展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无论在逻辑形式还是知识构造上,都有本质的不同,这使得东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东西文化在古代有过交流,但是交流比较局限,尤其从清朝初年开始中西文化的交流有过一次百余年的中断,而当时西方文化由于近代科学的崛起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使得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缺乏沟通和相互了解,构成了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前提。1840年,当西方国家用枪炮打开了封闭已久的中国的大门时,中西两种文化开始了“短兵相接”。西方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全方位侵入、威胁东方文化。庞朴指出:“当两种异质文化在平等的或不平等的条件下接触时,首先容易相互发现的,是物的层面或外在的层面;习之既久,渐可认识中间层面即理论、制度的层面;最后,方能体味各自的核心层面即心的层面”。“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的发展,依然有条不紊地循着自己的逻辑,表现为文化三结构的依次展开”。[14]伴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西方体育思想也在我国开始传播、发展,我国学习西方体育思想已成为西方强势文化发展的使然。
(二)强国强种时代要求促使我国学习西方体育思想
鸦片战争使“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同时也拉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序幕。在戊戌变法期间,虽然维新派试图在政治制度层面进行改革,但客观上在引进西方文明的同时,对西方体育思想的传播也起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作用。如维新派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提出了“德、智、体”三育,提倡学校体育。严复认为,改良中国社会,自强图存,保种保国,主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就是要使国家三强:“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他提出的自强保种的三大要政中的“鼓民力”,就是要使人民具有强健的身体,有“血气体力之强”。[15]梁启超认为“尚武之风,由于人民之爱国心与自爱心,两得和合而成也”。[16]他认为,中国“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17]孙中山也曾多次提出了“强种保国。强民自卫”的问题,他说:“因二十世纪立国于地球之上者,群雄竞争,未能至于大同时代,非兵力强盛不能立国。”[18]所以他主张国人要加强体育锻炼,强健体魄,从而把体育提到了强国强种、救亡图存的认识高度上。
在强国强种的时代要求下,我国不得不学习西方体育思想及体育教育,从此我国在体育思想及体育教育上也走上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道路。
(三)民族科学意识的提高推动我国吸收西方体育思想
当西方体育思想伴随着军事侵略、文化强势涌入时,我国社会自身为摆脱屈辱或在被动接受或在主动接受西方文化的前提下,本着强兵、救国、强国、保种的民族情节,去认识、学习西方体育思想。然而,自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开始用近代科学的观点去认识、研究和提倡体育。如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指出,体育的重要性在于“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吴蕴瑞在《体育原理》中认为“吾人之所谓体育者,乃为人之整个之机体之教育。体育之意义乃以身体活动为方式之教育也”。[19]“体育主旨不在于练成粗腕壮腿,重在团队精神的培养,吾们在今日提倡体育,不仅在操练个人的身体,更要借此养成团队合作的精神,体育活动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培养个人为目的,并以身体活动作为唯一手段,体育不是观念上的问题,而是以身体在进行具体活动的行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体育,在实践中才能显示它的特性”。[20]“五四”运动前后,自然主义思想被引进,在我国学校体育中得到传播。建国初期,由于当时我国正遭受着以美国为首的十八国集团的围堵,所以“以俄为师”、全面学习前苏联经验则成了新政权根据建国初期国际国内形势而确定的方针。随即毛泽东为我国制定了体育根本方针,即“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并指出:“体育是关系6亿人民健康的大事”。概而言之,伴随着民族科学意识的提高我国开始了主动吸收西方体育思想的精髓继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思想。
四、结语
由于中西方自古代伊始对体育的认识就存在差异,因此近代以来当西方体育思想伴随着军事、文化、教育进入我国之时,为抵御外侮、强国强民和挽救民族灾难,我国不得不向西方学习先进体育思想。学习西方体育思想不仅需要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而且还需要一个适宜的社会条件做保障。伴随着中华民族科学意识的提高,我国渐渐开始由被动接受西方体育思想转向主动学习西方体育思想中的精华,吸收、容纳适合我国国情的思想,进而形成我国特色体育思想。可以说,我国体育思想虽与西方体育思想历经了近百年的冲突与碰撞,但最终必将走向融合与发展之路。
